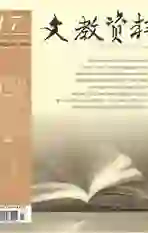唐传奇女妖形象特征的道教文化观照
2020-09-02冼雨彤
冼雨彤
摘 要: 與前代相比,唐传奇中的女妖形象出现了具有时代性的特点:仙性化、艳情化和道德化,具体表现为才貌兼美、品格高尚、恪守正统和身负家国的思想境界。与唐朝重道、崇道的社会氛围有着莫大的联系。道教的重阴思想和女仙崇拜融塑了女妖形象的才貌双全和高尚品格,女冠制度与文化与女妖形象的艳情化紧密关联,儒道融合是造成女妖或恪守妇德,或身怀家国的直接原因。
关键词: 唐传奇;道教文化;女妖形象
所谓女妖,是指本体动植物或器物且具有人形的女性。从先秦伊始,不同时代的小说家塑造了众多女妖形象。行至唐代,女妖形象在唐传奇中出现的频率大幅增加且风格独特。从其才貌、行为品格及思想境界来看,女妖群体其实是唐代文人沙龙文学中的道教文化观照的特殊产物。
有关唐传奇与道教的研究,学界皆是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探讨道教对于唐传奇的影响,如庄申《浅析道教对唐传奇侠义小说的影响——以〈红线传〉为例》[1],从情节和主题等角度全方位说明其中的联系;黄东坚《论道教对唐传奇的影响——以〈玄怪录·张老〉〈玄怪录·裴谌〉及〈传奇·裴航〉篇为例》[2]从道教对唐代文人影响的角度进行研究;卢柯青《唐传奇仙境营造的道教情怀》[3]选取仙境题材,研究道教对其中所有基本要素的影响;微观角度例如形象研究等不在少数,在此不一一详举。然而,对于唐传奇中女妖形象与道教联系的关注还不多。本文选取唐传奇中的女妖形象群体,总结归纳其特征并探讨道教文化对其角色形象塑造的影响。
一、女仙崇拜与女妖形象的仙性化
与前代强调其物性和凶残截然不同,唐传奇的女妖充满了仙性化的特征。与唐代道教的女仙崇拜及唐代女性尚修道有着特殊的联系。
唐代女性求道是富有时代性的社会现象,许多女性放弃闺阁生活,转而投向道观,投道的女性无论是财富还是阶层都相差甚远。唐代部分贵族女性曾为女冠,如太平公主、玉真公主和寿安公主等。不仅是贵族女性,民间的平民女性亦然,如服用丹药,升为“八仙”的何仙姑等。各阶层的女性入道是风靡唐代的时尚,说明唐代女子将修道求仙视为一种光荣和理想,人们也以道教女仙之标准对俗世女子进行衡量、要求。
女仙,最明显的特点是长生不死,永葆青春。她们是“美好”的代名词,是男性心中向往的理想女性。她们是容貌出众、姿态优雅的绝色女子,貌美而生动是道教女仙最显著的外形特征,也是道教对修道女性所作的要求。反观前代的小说作品,妖怪女性的形象并非是相貌妍丽的,在《山海经·西山经》的记述中,西王母集人的面相、豺豹的尾巴与老虎的牙齿于一身,常常恶啸,头发高耸蓬松 [4]。其相貌可谓是奇丑无比,令人可怖。反观晚唐传奇,其中狐、虎等动物可以转化为容貌艳丽的女子,比如《潇湘录·焦封》[5](1001)中本体为猩猩的女妖没有顽劣性和长毛等动物性特征,摇身一变为身态袅娜的美人;《宣室志·计真中本体为狐狸的计真之妻李氏毫无狡诈色彩,反而姿色姝丽,风情与贤淑兼具[5](889);《纂异记》中本体为烛灯的女妖西明夫人,雅妍淑丽,风姿不凡,一袭红裳衬得容色绝代,明艳动人[5](923)。可以说,从唐传奇开始,女性妖怪的容貌身姿逐渐向女仙的形象靠拢,光彩照人。女性之美来源于神仙,这与道教的女仙崇拜是离不开的。一改前代对于女妖的贬低性、憎恶性写法,唐传奇对女妖容貌不遗余力的描写和赞美,体现道教对文人审美取向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对美貌的赞美背后,是文人对于道教女仙的现实化想象,是对于现实伴侣的审美要求,亦是对道教文化的推崇。
女妖仙性化,还体现在她们的才华见识和品质人格上。从道教文化的层面上看,男女共谋,取长补短,以女阴之助辅男阳之力,与道教的阴阳合一思想相契合。除此之外,道教思想还有崇阴的倾向,“道”乃万物本源,“道”生“一”“一”生“二”,这里的“二”的所指即为阴阳,以此为肇始,“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6]。因此,“阴”是万物起源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道教重阴崇阴的思想便由此而来。只有男女共修,才可得道升仙,重视女性在修道时的作用和地位,所以教义中素有推崇妇女的才能与品格的习惯。妖怪都是由动植物或器物幻化而成的,最突出的特点是物性。而女仙则以心善著称,能够救济苍生、普度众生,以一己之力报答恩人。唐以前,女妖形象大都千篇一律,雷同,模糊不清,而且大都带有负面色彩:邪恶、恐怖、自私,勾引人类吸取精气以维持生命等。而唐传奇中的女妖则改头换面:多存有善良、聪慧的心灵,有些女妖甚至具有一定的文学才华。这些特点在唐以前的女妖形象中多不常见。如《传奇·卢涵》中的冥器婢子精便“言多巧丽,意甚虚襟”[7]。《宣室志·计真》狐妖李氏识大体、明大义。计真好赌,李氏当面痛陈赌博之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直言赌博不仅消耗钱财、精力,更消磨心志,赌徒终其一生亦只能做赌博的奴隶,永远不得脱身,劝服其夫不要汲汲于道而一事无成[5](889)。李氏以高尚品格和温柔贤淑对丈夫予以鞭策,不仅对丈夫情深义重,而且明辨是非,对赌博等陋习深恶痛绝。男女合力,乃能通达顺畅,正是道教所谓“阴阳相与合,乃能生”。
又如“灯精”西明夫人。对于爱情,她钦慕杨祯的幽隐之志,是高洁的精神之爱,而并非贪恋情欲,因此她声明自己“非敢自献”[5](789)。当杨祯怀疑她乃狐精以蛊人为生时,她非但不以其为女妖之实为羞,反而不卑不亢,掷地有声,亦从不会做出“苟媚而欲奉祸”[5](789)之事。她性格高洁,不与狡诈惑乱之同类同流合污,“奸生乱色,不入于心”[5](790)。
由此可见,唐传奇中女妖才、貌、品格兼美,皆与道教的女仙形象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二、女冠制度、文化与女妖形象的艳情化
如果说唐传奇小说女妖形象的才貌兼美和品格高尚与道教的女仙崇拜密不可分,是道教影响下仙性化的具体表现的话,那么她们身上体现的艳情化、媚俗化色彩则显示出道教女冠制度和文化的影响。在《山海经》等文学作品中,人与妖通常是对立和对峙的关系,始终以敌对的姿态审视对方,妖是危险堕落的,是致人迷惑的,对人是有害的。唐传奇开始大量出现描写人妖相恋为主题的作品,其中不乏艳情化的描写,与道教在世俗中的入凡有关。
唐代的女冠文化是道教下沉最直接的例子。与传统男性道士不同,她们是贵族沙龙聚会中的常客,自诩为女仙的凡身,与许多文人往来结交并以“修道”为名缔结情感联系和肉欲关系。孙昌武曾著述,女冠的身份“兼有神秘和低俗、超逸和平庸的十分暧昧的色彩”[8]。唐代女冠放荡的生活风气对女妖形象的塑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许多描写女妖形象的作品都带有香艳的色彩,比如《灵怪集·郭翰》中“柔肌腻体,深情密态,娇艳无匹”[5](233)运用细节化和意象的密集堆叠,描写女妖与郭翰共赴云雨时的体态情状。
现实生活中道教女冠仙妓同一的现象与许多女妖形象高度重合,女妖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女冠在文学中的投射,多是作者在现实世界中交往频密的女冠的艺术化形象。除了才貌双全之外,她们的共通点如下:其一,出身不明或低贱。虽然唐代不乏贵族女性入道的例子,但放眼整体,多数女冠皆是因为家道贫寒或无家可归,难以在俗世生存才入道为冠,与从器物、动物或植物等“物”升化为“人”的女妖有异曲同工之妙。其二,充当知己的角色。女冠与文人雅士交往甚密,弹琴唱和、吟咏谐谈,谈笑皆欢,是欢朋亦是知己。然而,出于能与恩客有更多共鸣或唱和谐谈的目的,才是女冠学习技艺,广览群书,提高文化素养的根本原因。女妖与人类男子超越人妖界限和人物界限的交集常常通過唱和与情爱体现,这种贴近“人性”的行为本身即具有讨好的意味。其三,艳情性质。由于道教“阴阳合一”与“房中术”等教义的影响,女冠与文士往往通过肉体的亲密关系达到对义理的升华和领悟。无论是起始的艳遇还是过程中的爱欲纠缠,女妖与人类男子的结合都带有妓女与恩客的性质。其四,感伤的结局。女冠与恩客的感情维系是短期的、暂时的,映射到唐传奇中,不仅人妖之爱大多结局坎坷,女妖甚至还会遭遇不测:死亡、受严惩、还原为本体。
由此可见,女妖才貌兼具,高贵与低贱并存、纯洁与色欲兼有、可远观亦可亵玩,呈现出仙妓同一的特点,这种剧烈的冲突和反差恰恰是现实中道教女冠所具备的。唐代的文士多与女冠交往频密,传奇作为文人交游的沙龙文学产物,其中的女妖形象多为女冠的映照。
三、儒道并融与女妖形象的道德化
根据学者唐大潮的观点,“道教的伦理道德同传统的世俗伦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它假神的名义,把以忠、孝为轴心的‘三纲五常道德规范说成神的旨意,用宗教特有的方式神化世俗封建伦理,借神的权威要求人们恪守各种适合封建统治秩序的道德规范”[9]。《太平经》强调“旦夕忧念君王”[10](20),以“臣忠”“子孝”为“上善”的最高境界,失忠失孝不仅不能得道,还将落得罪无可赦的下场:“子不孝,弟子不顺,罪皆不与于赦。”[10](21)唐朝儒道并融的趋势亦让儒家“三纲五常”和“君君,父父,臣臣,子子”的伦理道德观引起了道教对修道者思想境界要求的变化。
由此,唐传奇的女妖身上另有一层道德化的表现。她们婚后与人类女子无异,相夫教子,恪守妇德,对夫情忠,对子慈怜,为小家燃烧自我。恰恰体现了儒道合流后道教重礼重德的准则要求。小说艺术取材于生活,源于生活。生活于儒道氛围浓厚环境中的作家,作品很大程度上不由自主地体现观念所向,唐传奇小说的女妖在才貌双全、胆识过人之余,亦是纲常伦理的忠实信徒,正是缘于道教这种富有儒家伦理观念的思想观念。《宣室志·计真》的狐妖李氏临死将现狐形之时,对丈夫计真推心置腹,将所有真相全盘托出并说出遗愿:“一女子血诚,自谓竭尽,今日求去。不敢以妖幻馀气托君……愿少念弱子心。”[5](890)饱含真情的言语和卑微诚恳的道别,在李氏临死之时,她在意并期望求取的仍是获得丈夫的谅解,担忧的仍是孩子的未来,她将道教对女性要求承担的责任完成了,甚至临死遗言亦并无提及与自己相关,全身心地将自己献给了“小家”。从天下家国的角度看,还有一些女妖心怀天下,身怀仁泽大地的责任感,正是与儒家融合的道教所提倡的。《酉阳杂俎》记载云安险滩水深且急,不少渔民货船皆葬身于此,翟乾佑以方术制伏了十四处,唯剩一滩难以对付,翟乾佑急令神吏追查缘由。不料三日后,一女子独自前来解释难治的因由:“某所以不来者,欲助天师广济物之功耳。且富商大贾,力皆有余,而佣力负运者,力皆不足。云安之贫民,自江口负财货至近井潭,以难衣食者众矣。今若轻舟得涉,平江无虞,即邑之贫民,无佣负之所,绝衣食之路,所困者多矣。余宁险滩波以赡佣负,不可得舟楫而安富商,所以不至者。”[11]待翟乾佑处理妥当后才发觉女子原是险滩之水精。以操纵险滩恶水警醒当权者,凭道家方术兼济天下,或许正是道教之于世俗的终极要义。如果说女妖的才貌与艳情特点显现的虚无和媚俗为人所诟病的话,那么,其身上在以往小说作品中鲜少出现的忠孝仁义色彩和身怀兼济天下与家国责任的信念,则体现了儒道融合影响下道教倡导的原则和理念。作为贵族沙龙中相互传阅、以供消遣的产品,虚构的女妖身上寄托着士大夫的理想也是不难想见的。
总而言之,唐传奇中的女妖普遍出现与以往文学作品相异的形象特点。唐代道教氛围浓厚,道教的女仙崇拜、重阴思想、女冠文化及儒道合一的趋势在很大程度上对文人的创作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唐传奇中女妖形象仙性化、艳情化和道德化的特点实际上反映了作为创作者的文人在道教思想观念和文化影响的潜移默化下对现实局限的超越和自我信念。
参考文献:
[1]庄申.浅析道教对唐传奇侠义小说的影响——以《红线传》为例[J].今日中国论坛,2013(07).
[2]黄东坚.论道教对唐传奇的影响——以《玄怪录·张老》、《玄怪录·裴谌》及《传奇·裴航》篇为例[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3,29(10).
[3]卢柯青.唐传奇仙境营造的道教情怀[J].陇东学院学报,2017,28(04).
[4]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5]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6]王弼注,孔颖达正义.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裴铏撰,穆公校点.传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9]唐大潮.明清之际道教“三教合一”思想论[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
[10]龙晦等译注.太平经全译(上中下)[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11]段成式.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