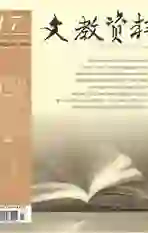先秦冰制的文献考证和考古发现
2020-09-02孔书馨
孔书馨
摘 要: 从古至今,冰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关系都非常密切。先秦时期是我国制度习俗的形成时期,冬纳夏出的藏冰之俗可追溯至此。本文结合先秦“冰”相关的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分析探讨先秦时期的用冰制度、用冰方式等内容,以求更好地理解中国古老的用冰文化。
关键词: 凌人;冰制;凌阴;用冰
冰是现代生活的必需品,它的使用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凌阴,冰室也”[1](506)。所谓“凌阴”,即藏冰的地窖,可看作中国古代的一種冷藏设施。本文通过搜集先秦时期“凌阴”相关的文献资料并结合考古材料,对先秦时期的冰制进行研究探讨。
一、冰制人员分配管理
先秦时期,相对成熟规范的用冰制度已经形成,相应地,朝中亦建立了相关的人员管理制度。据《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次》记载:“凌人,掌冰。”郑玄注:“言‘掌冰者,谓凌人总掌藏冰出冰之事,故云掌冰也。”[2]先秦时期,朝中设有“凌人”一职,专职负责管理冰政工作。在“凌人”之下,设有“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2]。下士管理众事,府主藏文书,史主作文书,胥管十徒,八胥有徒八十名,胥徒是冰窖出纳的主要劳动者[3]。根据先秦文献《左传·昭公四年》可知,从凿冰、藏冰到取冰,先秦冰政的具体工作具有一套完整规范的工作程序。在这一流程中,“山人取之,县人传之,舆人纳之,隶人藏之”,各个环节亦有明确分工和专人负责。
二、冰政制度的流程
先秦时期,朝中设置了专门负责管理冰政工作的“凌人”,也形成了一个规范完整的“用冰”工作程序,这一流程主要包括凿冰、藏冰、取冰等环节。
(一)凿冰(采冰)
1.凿冰时间
根据先秦文献可知,这一时期的凿冰工作大多在冬季十二月进行。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入凌阴”,《诗经·豳风·七月》的末章为我们留下了目前发现最早的采冰和藏冰的记录。对于“二之日”“三之日”的理解,郑玄《笺》曰“一之日,十之余也。一之日,周正月也”,又曰“二之日,殷正月也。三之日,夏正月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朱熹《诗经集传》卷三曰:“一之日,谓斗建子,一阳之月。二之日,谓斗建丑,二阳之月也。变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后凡言日者放此。”结合现代高亨、张剑等学者的解释,可知学界多认为“二之日”“三之日”即为夏历的十二月和正月。也就是说,《诗经·豳风·七月》反映的凿冰时间为夏历十二月。《礼记·月令》中亦有十二月凿冰的规定:“季冬冰方盛,水泽腹坚。命取冰,冰以入。”此外,《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次》中“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也证明了先秦时期的凿冰工作于十二月进行。之所以选择十二月进行凿冰工作,正如《礼记·月令》所描述的,是因为“孟冬水始冰,仲冬冰益壮”,孟冬之冰还未冻坚固,仲冬之冰又太过坚硬,不易凿取,季冬之时,所结之冰相对容易凿取,且量多而坚硬质优,能够储存至来年取冰之时。
2.凿冰地点
凿冰是冰政工作流程的第一步,因此,选择合适的地点是人们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其藏冰也,深山穷谷,固阴冱寒,于是乎取之。”先秦时期人们往往选择“深山穷谷”的阴寒之地凿冰,根本原因在于其优质的冰源。相比河流池塘之地,“深山穷谷”气温低、日照少、水质优,且鲜少有人破坏,因此是凿取优质冰源的最佳选择之地。
(二)藏冰
藏冰是冰政工作的中间环节。在隆冬之时采冰过后,人们需要将所采之冰藏于“凌阴”之中,等待来年夏季取冰。因此,藏冰工作在整个冰政工作流程中极为重要。
1.藏冰时间
《诗经·豳风·七月》记载了先秦时期的藏冰时间为“三之日纳入凌阴”,即夏历正月之时。据《左传·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对于“日在北陆”,孔颖达注:“日在北陆,为夏之十二月也。”[4]“是夏之十二月,日在虚危也。于是之时,寒极冰厚,故取而藏之也”[4]。据此,“北陆”即虚宿和危宿,《左传》所记藏冰时间为夏历十二月,与《诗经》所记相差一月。
2.祭祀活动
古时,人们在藏冰前要举行祭祀活动,以祈求寒神保佑藏冰事务顺利进行,正所谓“有事于冰,故祭其寒神”[4]。《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其藏之也,黑牲、秬黍,以享司寒。”秬黍,即黑黍。所谓“司寒”,《春秋左传正义》解释为“玄冥之神”。因其为“北方之神”,所以“物皆用黑,从其方色也”[4]。
(三)取冰
在隆冬的采冰和藏冰工作结束后,来年春夏的取冰工作是先秦冰政工作的最后一个环节。据先秦文献分析可知,古人大致分两次取冰。
首次取冰时间为二月春季。《诗经·豳风·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四之日”,意为古人首次在夏历二月取冰。对于其中的“蚤”字,孔颖达解释为“早朝”,早朝“是古代一种祭祀仪式”[5](272)。也就是说,在取冰之前,首先仍需进行祭祀司寒之神的仪式。“祭寒而藏之,献羔而启之,公始用之”。《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了取冰前的祭祀仪式,与上文的“藏冰”仪式相对应。《礼记·月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鲜羔开冰,先荐寝庙。”“仲春之月”,即二月,此时,天子应祭祀司寒之神,然后开窖取冰。由于周人“敬天法祖”,在祭祀寒神时,要先拜祭祖先[6]。因此,周天子在享用藏冰之前,要“先荐寝庙”,以表达对祖先的恭敬,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由“公始用之”“天子乃鲜羔开冰”可知,二月春季所取之冰,应为天子而非普通平民甚至贵族所享用。正如杨伯峻先生所言:“二月即开冰窖,此乃唯君王如此。”[7]
第二次取冰时间为四月夏季。《周礼》云:“夏颁冰,掌事。”《左传·昭公四年》记载:“西陆,朝觌而出之。……火出而毕赋。”据孔颖达解释:“此云‘火出而毕赋,谓以火出而后赋之,以火出为始也。《周礼》云‘夏颁冰,为正岁之夏,即四月是也,故杜兼言四月。”[4]由此可见,第二次取冰时间应为四月。在第二次取冰工作中,所取之冰的享用对象仍非面向所有人。据《左传·昭公四年》:“食肉之禄,冰皆与焉……自命夫、命妇,至于老疾,无不受冰。”所谓“食肉”,《春秋左传正义》曰“在官治事,官皆给食”;而“老”,则为“致仕在家者”。据此可知,四月第二次取冰的享用对象应为王室的高级贵族和官员,其中包括退休或生病不能治事的大夫以上的官吏。
此外,在取冰之前,古人往往会举行一个仪式活动,以希望免除灾难。据《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灾。”“桃,所以逃凶也。棘矢者,棘赤有箴,取其名也。盖出冰之时,置此弓矢於凌室之户,所以禳除凶邪”[4]。当把冰取出之时,人们采取“桃弓棘箭”的方式,达到消除灾难、禳除凶邪的目的。
据《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次》记载,在春夏取冰工作结束后,“凌人”和相关人员还要进行“秋刷”的工作。春夏取冰过后,“凌阴”内的藏冰应已用尽,而“凌阴”地下窖穴此时则会因数月藏冰致使内部原有的草秸、泥土等遭到损毁破坏,因此“凌人”需在秋季对冰窖进行清理整治工作,达到维护冰室的目的,准备冬季新一轮的藏冰入库。
三、用冰的方式
《左传·昭公四年》云:“宾食丧祭,于是乎用之。”先秦时期冰的利用方式大致可分为四种,即上引文所称“宾”“食”“丧”“祭”。
(一)“宾”——宴饮用冰
“宾”,即招待宾客,宴饮所用。《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次》云:“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春天初始,“凌人”需要检查冰鉴,以备宴饮使用。“鉴,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于中,以御温气”[2]。冰鉴中盛放宴饮时宾客所享用的酒肉美食,达到防止食物变质从而保鲜的目的。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曾出土一“青铜冰鉴”,这一“青铜冰鉴”是由方鉴和方尊缶组成的青铜套器,方尊缶置于方鉴内,二者间的空隙内可置冰块,使尊缶内的酒变凉[8],达到冰酒保鲜的目的。
(二)“食”——饮食用冰
“食”,即日常食用。同“宾”的作用类似,先秦时期古人对冰在饮食方面的利用应与现代类似,即主要用于防腐保鲜、降温消暑,满足口腹之欲。
(三)“丧”——丧礼用冰
“丧”,即丧礼所用,达到为尸体防腐的目的。《左传·昭公四年》云:“大夫命妇,丧浴用冰”,表明先秦时期大夫一级的官员及其夫人在死后要用冰清洁尸身。《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次》云:“大丧,共夷盘冰。”郑玄注曰:“夷之言尸也。”故“夷盘”应为寒尸之盘,具体的位置应为“置之尸床之下”[2]。也就是说,尸体应置于尸床之上,盛冰的夷盘置于尸床下方,达到寒尸的目的。丧礼用冰的目的主要在于防止尸体腐烂,盛冰的冰具因等级的差别有所不同。据《礼记·丧大记》,“君设大盘造冰焉,大夫设夷盘造冰焉,士并瓦盘无冰,设床襢笫,有枕”。由此可见,冰具种类、尺寸等的差异,亦是先秦时期等级观念和礼制的体现。
(四)“祭”——祭祀用冰
“祭”,即祭祀所用。根据上文,在取冰之前,首先应“献羔祭韭”,以祭祀司寒之神;天子应“鲜羔开冰,先荐寝庙”,在祭祀司寒之神后,开窖取冰,将二月春季首次取出的冰块首先献给祖庙中的先人,以表示對祖先的恭敬之意。
四、“凌阴”的考古发现
《诗经·豳风·七月》云:“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入凌阴。”所谓“凌阴”,《周礼注疏》解释为“凌,冰室也”。作为冰政工作的中间环节,“藏冰”的地位不容小觑,“凌阴”即为储冰之所,纳入所藏之冰。文献中记载“凌阴”已被考古发现证实,目前发现先秦时期“凌阴”遗存主要以陕西凤翔秦都雍城和河南新郑郑韩故城两处为代表。
陕西凤翔秦都雍城凌阴遗址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先秦凌阴遗址。该遗址为近方形的夯土台基,台基东西长16.5米,南北宽17.1米,其中央是长方形窖穴,窖穴底部铺有一层砂质片岩。窖穴四周有回廊,西回廊正中有一个呈等腰三角形有一个呈等腰三角形状的通道[3]。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凌阴遗址为长方形土圹,口部南北长8.9东西宽2.9米,四壁分层夯筑而成,有向内收缩的台阶。遗址的南壁东端有宽0.56米—1.15米的阶梯状的走道,东侧有五口竖井,井之外的地面用方砖平铺,凌阴四壁也用方形凹槽砖镶嵌[9]。
根据目前发掘的两处代表性凌阴遗址,结合先秦文献资料,不难发现凌阴遗址具有以下特点:
(一)服务对象
根据秦都雍城与郑韩故城遗址平面图可知,雍城的凌阴遗址位于姚家岗宫殿遗址西北部,韩都的凌阴遗址位于新郑阁老坟村北部,均在宫殿区范围内。凌阴遗址与宫殿区的位置关系表明,凌阴遗址与都城的宫殿区有着密切联系。由文献可知,国家专设“凌人”管理冰政,设“凌阴”作为藏冰之处,并建立了相关用冰制度。结合相关考古发现,凌阴遗址均位于都城宫殿区附近,则应具有特定的服务对象,服务于王室和宫殿生活而非平民生活。
(二)建筑形制
从雍城与韩都考古发现来看,两处凌阴遗址的规模都偏大,与藏冰的特性有关。《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次》云:“令斩冰,三其凌。”所谓“三其凌”,即冬季藏冰之量应为用冰所需之量的三倍。先秦时期王室贵族本就需要在宴饮、祭祀等多种场合用冰,再加上古人从十二月凿冰后开始藏冰,经历数月才取冰利用,且取冰时间为春夏两季,极大可能造成一定数量的冰块融化,因此,需要储备用冰所需量的数倍,才能够确保来年有足够的冰可用。体现在考古遗存上,则为所发现的藏冰之处均规模较大,能够储存足量的冰。秦都雍城凌阴遗址的窖底面积为8.5米(东西)×9米(南北);窖口面积为10米(东西)×11.4米(南北),窖深2米。依据推算,该冰室始藏冰为190立方米。如果按《周礼》上的消释比率,那么来年最少还应有冰65立方米[3]。郑韩故城现存凌阴遗址口部南北长8.7米,东西宽2.8米—3米,底部南北长8.6米,东西宽2.35米—2.5米,深度为2.4米—3.35米[9]。相对于普通窖穴,“凌阴”的规模显然偏大。
(三)冷藏功能
在郑韩故城凌阴遗址地下室的底部偏东侧,发现有南北成行的5个地下冷藏井窖。在地下室和井窖的填土中,出土了大量兽禽骨骼,约占冷藏室内出土遗物总数的二分之一左右。其中以牛、猪骨最多,马、羊骨次之,并有少量的鹿、鸡骨[9]。根据这一发现,可推知郑韩故城“凌阴”遗址应以冷藏肉类食物为主。郑韩故城“凌阴”遗址发掘者认为,这些兽骨在填入冷藏室之前应是堆积在冷藏室走道口外的南面附近,推想冷藏的兽肉都是在冷藏室南面宰杀,经剔骨后储存到冷藏室的井窖内,而将兽骨弃于屠宰处[9]。结合前文所举《周礼·天官冢宰·酒正/掌次》“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可明确先秦时期藏冰具有冷藏食物以使其保鲜的作用,“凌阴”遗存也具有冷藏食物的功能。
(四)特殊设计
《左传·昭公四年》云:“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孔颖达注曰:“周,密也。”[4]藏冰是冰政工作的重要环节,为了保持藏冰的质量,藏冰之处应有良好的密封隔热条件,以防止冰融化。在秦都雍城和郑韩故城两处“凌阴”遗址中,均可发现先秦时期的建造者为保持低温而进行的特殊设计。在雍城“凌阴”遗址中,深挖坑、木板、泥土封窖口、麦草秸、谷壳覆盖窖顶、土墙、盖有厚草瓦的歇山顶、严格隔热设施的门道等的发现[10],体现了建造者为保持窖内温度而进行的特殊设计。此外,在窖穴西回廊正中的通道中有东西平行的槽门五道,在第二槽门之西的通道底部,铺设有东高西低的水道一条,与白起河相通,是窖穴内的排水设施[3],能够排出窖内藏冰融化形成的冰水。冰水通过两道槽门再入水管,目的是减少外面气候的变化对窖穴内的影响[10]。在郑韩故城“凌阴”遗址中,亦发现有特殊的密封设计,即在四周夯土墙表面抹一层草拌泥,并在底部粘贴一层方形凹槽砖,除井窖口外,在底部地面上全铺上一层方形砖。如此平整、光滑、尽可能密封的建筑设计,应是出于保持室内温度低于外界温度的考虑[9]。
五、先秦冰制中的智慧
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开拓了多种用冰方式并建立了相对成熟的用冰制度。先秦的冰制不仅服务于生产生活所需,而且蕴含了古人的智慧。
(一)“凌阴”的修建体现了先人的建筑智慧
根据第四部分对于“凌阴”建筑的分析,可见古人为了保证凿冰、藏冰、取冰工作的顺利而对“凌阴”进行了特殊的设计与建造。同时,修建于地下的“凌阴”,亦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空间的合理高效利用。东周时期礼崩乐坏,诸侯国先后开展了争霸或兼并战争,也从外部压力的角度促进了出于自保的东周城市的发展。为了高效利用都城空间,各诸侯国在充分使用地面空间的同时,发展出高层建筑形式,并结合特定目的建造不同类型的实用型地下建筑,“凌阴”就是其中代表之一。从一定程度来说,对地下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促使都城空间的利用走上了立体化的道路,推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蓬勃发展[11]。
(二)先秦的用冰制度体现了人们对气候生态的了解、认识与准确的把握
根据对冰政工作的分析,可知先秦之人冬藏冰、春启冰、夏用冰、秋刷冰,充分利用自然气候特点合理用冰。《左传·昭公四年》云:“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不出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民不夭札。”周人认为用冰对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倘若能够正确利用冰,便能平衡生态、安定百姓。如果违反了古者的用冰之道,则“风不越而杀,雷不发而震。雹之为灾,谁能御之”?由此可见,古人认为用冰之道对自然生态有重要影响,其用冰之道亦体现了对自然生态规律的认识和对气候规律的尊重與利用。
综上,结合文献资料与考古发现分析可知,冰政制度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相对规范完整的体系,并在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先秦时期的冰政制度体现了古人对用冰的重视和认识把握自然生态的智慧,亦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与发展,具有较大的历史研究价值和现代启示。
参考文献:
[1]李学勤.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郑玄.周礼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韩伟,董明檀.陕西凤翔春秋秦国凌阴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78(3).
[4]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6]李川豫.《诗经·七月》与先秦礼乐文化[D].郑州:河南大学,2010.
[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8]唐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青铜器赏析(下)[J].荣宝斋,2015(3).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韩故城内战国时期地下冷藏室遗迹发掘简报[J].华夏考古,1991(2).
[10]单先进.略论先秦时期的冰政暨有关用冰的几个问题[J].农业考古,1989(1).
[11]李麦产.东周列国都城实用地下建筑述论[J].延安大学学报,20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