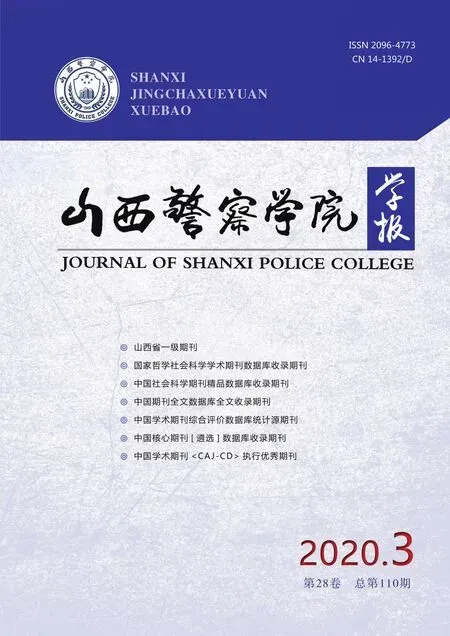危险驾驶罪案件中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对接问题研究
2020-09-01李美荣傅淑均
□张 楠,李美荣,傅淑均
(陕西警官职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3)
危险驾驶罪是典型的行政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危险驾驶罪案件一般都不复杂,但是却普遍存在着行政犯案件中诸如刑事违法行为与行政违法行为的重叠和交叉、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对接等一系列问题。如何在危险驾驶罪案件办理中建立有效的二法(行政法和刑法)衔接机制,实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无缝对接?需要从行政犯的基本理论入手。
一、行政犯相关理论
(一)行政犯
1.行政犯的概念
学界普遍认为行政犯与刑事犯的理论渊源是古罗马法中自体恶(mala in se)和禁止恶(mala prohibita)的法律思想。自体恶是指无论是否被法律所禁止,某些行为天然就存在着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恶性,其恶体现在本质中。禁止恶是指某些行为之所以称之为恶,不是由于其恶的本质,而是由于法律的明文禁止性规定,其行为本身并不具有明显的恶的内容。对行政犯在刑事法领域进行系统论述并正式提出自然犯与法定犯概念的是著名的意大利刑事人类学派的代表人物加罗法洛,他在经典力作《犯罪学》中提到:伤害怜悯感和正直感这两种基本利他情感的犯罪是自然犯,而法定犯则与特定国家特定环境有关,它们并不说明人的行为异常,不证明它们缺少社会进化几乎普遍为人们提供的道德感。[1]从此开启了代表自体恶的是自然犯、代表禁止恶的是法定犯的先河,目前已是学界共识。被誉为近代刑法学之祖的德国刑法学家费尔巴哈在加罗法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刑事犯和警察犯概念,刑事犯侵害的是社会普遍伦理道德,而警察犯侵害的是社会行政管理法规确立的行政管理秩序。
我国的法学理论受德、日法学的深刻影响,探寻我国的行政犯理论,需要沿着德、日行政犯概念的发展脉络进行。在德国,提出行政犯概念的是学者高尔德修米德,他第一次用行政犯的概念替换了警察犯的概念,并指出刑事犯和行政犯的区别在于所违反的对象不同,刑事犯违反的是法,行政犯违反的是国家对社会的行政管理活动。但是行政犯所代表的行为类型并未由此确立下来,1952年之前,德国的行政犯是指旧刑法中的违警罪,1952年之后指的是《秩序违反法》中违反行政秩序,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日本继受和发展了德国的行政犯理论,并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广义和狭义之分:在行政法领域内,学者们阐述的行政犯是广义的,其不仅包括违反行政秩序且构成犯罪的行为,还包括违反行政秩序应受行政处罚的行为。而在刑法领域内,学者们将行政犯作为刑事犯的对应概念进行论述,认为二者都具有犯罪的本质,但所触犯的刑法规范属于不同类型,行政犯触犯的是行政刑法。
我国目前的行政犯概念最接近于日本的相关学说,基本形成行政犯具有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双重违法性的通说,且讨论行政犯都是在刑法领域内进行的。学者们普遍认为行政犯存在的基础首先是行政法令,其次是刑法将严重违反某行政法令的行为规定为犯罪。立法上大多数也采用这种模式,行政法中规定行为类型和表现形式,并将严重违反的行为指引向刑法,刑法上利用空白罪状予以援引,从而形成了某一行为既违反行政法又违反刑法的现象。基于此,我国的行政犯概念可以这样理解:严重危害社会,违反行政法律法规(有人认为这里不包括治安管理处罚法),触犯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2.我国刑法典中的行政犯
我国刑法典以犯罪客体而非是否存在前置法律规范为标准区分类罪,因此行政犯散见于不同章节。根据其罪状形式可以分为形式的行政犯、实质的行政犯和混合的行政犯,形式的行政犯以空白罪状为标志,比如交通肇事罪:“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律法规……”。实质的行政犯虽然没有以空白罪状的形式援引相关行政法律法规,但实质上某行为要构成犯罪,一定在相关行政法律规范中也存在相应的禁止性规定,比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混合的行政犯是以上两者的结合,比如本文将要讨论的危险驾驶罪。危险驾驶罪有四种类型,其中醉酒型、追逐竞驶型、超速超载型在法条中没有明确需要援引《道路交通安全法》中的相关规定,但是其存在却是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为前提的,因此是实质的行政犯,而违规运输危险化学品型在法条中规定了该行为违反的行政法律规范类型,因此是形式上的行政犯。
3.行政犯与法定犯
学界对行政犯是否完全等同于法定犯一直有不同认识,笔者认为二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重合,但还是有区别的。虽然二者的思想渊源都是罗马法中mala prohibita,但行政犯和法定犯概念正式提出存在先后顺序,且产生的现实依据不同,行政犯源于对严重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刑罚处罚的需要,法定犯源于犯罪学产生后对犯罪分类的需要,是指不违反伦理道德的犯罪。从内涵来讲,行政犯和法定犯有相交叉的内容,但是,行政犯认定主要以是否存在前置性行政法律规范为标准,而法定犯以是否违反伦理道德为标准,二者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本文讨论的是危险驾驶行为的双重违法性质引发的问题,因此是以行政犯理论而非法定犯理论为起点的。
(二)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关联
行政处罚是指对触犯行政法律规范禁止性规定的行为进行行政制裁的法律实施活动;刑事处罚是对犯罪的行为定罪量刑的法律实施活动。二者性质完全不同,但是在对具有双重违法性的行政犯进行制裁的时候,二者在适用上就出现了诸多问题,比如能否对同一行为既处以行政处罚又处以刑事处罚?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如何对接?在程序上是先行政还是先刑事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法理入手。
如前所述,行政处罚是对行政不法行为的制裁,而行政不法行为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单纯的行政违法行为,一种是在违反行政法的同时又违反刑事法的行政违法行为。因此行政处罚也就有了广义和狭义的区分。狭义的行政处罚仅指行政法范围内的行政处罚;广义的行政处罚是指对具有双重违法性的行政不法行为科处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之和。我国理论界一般采用狭义的观点,这也是我们讨论行政犯案件中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对接的理论前提。
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处罚对象截然不同,但是在处罚种类上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如下图)。行政处罚的8种类型与刑事处罚的9种类型中,罚款与没收财产、罚金都是对行为人全部或部分财产权的剥夺;拘留与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在剥夺行为人人身自由的方法方面有相似之处。这种既联系又区别的现象,是我们在司法实务中对接行政犯行政处罚和刑罚的基础。

(三)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的区分
讨论行政犯处罚时的二法对接,除了弄清上述问题外,还需要对作为二者的处罚对象的行政不法与刑事不法进行正确认定。如何区分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理论上有质的差异说、量的差异说、质量差异说等不同观点。质的差异说认为行政不法行为和刑事不法行为具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性质,行政不法是对行政法律规范确立的行政秩序的违反,刑事不法是对自然伦理道德的侵犯,这样的理论架构显然不适于具有双重违法性质的行政犯。量的差异说认为二者仅存在违法轻重的量差异,其本质都是对“法”的违反,这种观点的理论起点是刑法没有独立的规范领域,是其他法的二次调整规范,其他法的调整范围都是刑法的调整范围。这种观点否认“不法”量变可以达到质变的过程,不利于划分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的界限以及划定严格的犯罪圈。持质量差异说的学者主张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由于量的差别导致了质的不同,从质上来讲,行政不法是违法行为,刑事不法是犯罪行为;从量上来讲,二者虽然都具有社会危害性,但由于数额、情节、危害后果上的区别导致了社会危害性程度上的差异。每一种学说都有它产生的现实依据,其是否科学合理应放到现实的法律环境中考虑。我国刑法采用的是既定性又定量的立法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质量差异说最能反映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的区别,进而用于区分罪与非罪。
二、二法对接机制的理论争鸣
(一)刑事优先
在追究行政犯法律责任时的二法对接过程中,刑事优先是最流行观点,目前虽饱受争议,但仍处于通说地位。刑事优先一般认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刑事责任优先于行政责任。对行为人科处刑罚以后,其应科处的相应行政责任原则上将不再追究,只有法律明文规定有刑事处罚性质相异的行政处罚形式时,二者并行。简言之,刑事责任优先,当行政责任形式与刑事责任形式相同时,行政责任形式不再适用;当行政责任形式与刑事责任形式不同时,行政责任形式可以再适用;免于刑事处罚时进行行政制裁。二是刑事程序优于行政程序。基于刑事责任优先原则,在诉讼程序中刑事程序优于行政程序,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一旦发现行政违法行为涉嫌犯罪则移送案件进入刑事程序。
(二)行政优先
刑事优先是学界和实务上都认可和践行的观点,但是在运行中却一直存在矛盾,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行政优先原则。该观点认为,追究行政犯刑事责任的前提是对一行为行政违法性的确认,而行政专业知识是认定的基础。[2]因此,行政犯法律责任追究应以行政违法性审查为先,即由行政机关对行为人的行政违法行为予以认定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再移送司法机关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进行刑事违法性判断,最后若需进行刑事处罚,按照责任形式相同时折抵、不同时合并的原则处理。
(三)亦刑亦罚
“亦刑亦罚”的观点的主要内容是在程序上,其认为行政犯处理时应秉承相对的刑事优先的原则。程序上法院应在法庭辩论结束后移送案件文书副本给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依据庭审认定的案件事实作出行政处罚,法院也依据庭审定罪处刑,实现在这一意义上的“亦刑亦罚”,最终由法院结合行政处罚确定宣告刑。[3]
(四)二元犯罪模式
二元犯罪模式是学者根据立法实例总结出来的一种解决行政犯二法对接问题的特殊立法模式。支持行政犯二元犯罪模式的学者认为该种模式实现了在立法层面的行刑对接:行为人自愿接受并履行行政处罚的将排除在犯罪行列以外,同理,若不接受或不履行,则以犯罪论处。[4]。比如经《刑法修正案(七)》修正过的第201条:“……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观点是基于现行立法事实的讨论,其科学合理性是经过一定实践检验的,但是该模式的适用范围问题却不好解决。有学者将行政犯分为三类,一类是暴力性行政犯,比如寻衅滋事罪;二是贪利性行政犯,比如偷税罪;三是职务性行政犯,比如滥用职权罪,认为二元犯罪模式仅可适用于贪利性行政犯且应在贪利性行政犯中广泛应用。虽然该观点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是以上三分法并不能穷尽行政犯的类型,贪利性的行政犯的范围还需要再解释。对于二元犯罪模式,笔者认为仅可作为特例在刑法中存在,大量的行政犯还需要在司法上进行行刑对接。
三、危险驾驶罪案件中的行刑对接机制探索
危险驾驶罪是《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罪名,《刑法修正案(九)》进一步扩大了其行为类型。目前危险驾驶罪的四种类型,均具有行政犯特征,既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或化学品安全管理规定,又触犯刑法,是比较典型的行政犯。此类案件不复杂而上诉率偏高,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都暴露出了问题,究其根源还是在于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对接时的矛盾上。
(一)行刑在实体上的对接
在危险驾驶类案件中大量存在这样的情况:行为人除了存在危险驾驶行为外还同时存在其他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比如醉酒驾车的同时无证驾驶、为逃避责任而驾车闯卡、车辆超期未检。这样的案件本身并不复杂,但是办案人往往觉得棘手的是不知道该如何区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分别负责的行为范围。笔者认为,讨论单纯的行政违法和行政犯交织案件中的“一事”“二罚”应该分别在行政法和刑事法范畴内进行。
1.行政处罚时的“一事”。行政处罚中的“一事”认定有两个内容:一是认定行政违法的“一事”和“多事”。何为行政违法中的“一事”?其判断标准学界有自然行为说、法益标准说、构成要件说等不同认识,笔者同意构成要件说,即某一行为是否是行政违法行为,应该依据相关行政法律法规判断是否符合某个行政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一个案件中有几个符合行政违法构成要件的行为,就是“几事”,有“几事”就进行几次单独评价,然后进行行政处罚的合并执行。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在行政处罚时,由于本身都属于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政违法,所以同一案件中的“几事”之间一般不互为处罚裁量情节。二是需要科处刑罚的行政不法还是不是行政处罚中的“事”。此问题的理论映射就是“一事不二罚”的法律原则。如前文所述,在我国的立法模式和法律传统下,行政不法和刑事不法在质和量上都是有区别的,行政犯同时具备双重违法性质,而刑事范畴内的“一事不二罚”在我国主要指的是对同一犯罪行为不能重复起诉,且严格限制再审的提起,维护刑事判决既判力。所以“一事不二罚”指的是同一性质的处罚不能重复,而不同性质的处罚是在不同范畴内做出的,并不违反“一事不二罚”的原则。上述理论在立法上也是有反映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1条第2款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可见,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行政不法仍属于行政处罚中的“事”。
2.刑事处罚中的“一事”。一般认为,刑事案件中的“一事”,应该是指能够反映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犯罪情节轻重、人身危险性大小的全部案件事实,因此,可以这样说,在刑行交织案件中刑事处罚的“一事”大于或等于行政处罚的“多事”。
3.在刑事处罚中,如何对待已经宣告或执行的行政处罚?若危险驾驶罪案件中包含了无证驾驶和驾驶未经审检的机动车等行为,那么公安机关往往会在危险驾驶罪刑事责任确定之前对无证驾驶、驾驶未经审验的机动车的行为决定并执行行政处罚。那么接下来的刑事程序中,应如何对待上述行政处罚呢?
首先,针对非构成要件行为的行政处罚,有学者认为,既然行政处罚中的“多事”应纳入刑事处罚中“一事”进行评价,那么公安机关针对这些“多事”的行政处罚权应予以剥夺,以此来践行“一事不二罚”或“禁止重复评价”的法律原则。[5]还有学者认为,在危险驾驶案件中的非构成要件行为一经行政处罚,就不能再作为刑事处罚中量刑情节予以评价。[6]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在理论上都能自圆其说,但是在实践中却难以操作,公安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不可能被刑事处罚权吸收,公安机关也不可能将行政案件作为相关刑事案件的附随,完全转入刑事程序,已经公安机关行政处罚的行为在事实上与刑事违法行为有牵连性,甚至是同时存在的,比如无证与醉酒同时体现在驾驶行为中,这种情况下,无论案件审理过程中还是作出刑事判决时,都无法也不应将此类行为割裂出去,因此,笔者认为非构成要件行为符合行政违法构成要件时,理应依法进行行政处罚,在对其相关行为进行刑罚评价时,其作为量刑情节的一部分也应予以考虑,但是鉴于已被行政处罚,因此在决定宣告刑时应秉承相同形式折抵、不同形式并罚的原则处理。理论上这样对接既考虑到非构成要件行为与相关犯罪行为的密不可分、附随存在性,又避免了对当事人实质上的双重不利结果。实践中,同一行为在行政法范畴内的处罚与在刑法范畴内作为情节考虑对量刑的最终影响并不等同,这样综合评价更为科学,既体现了行为的双重性质,又避免了处罚实质上再次不利影响。立法上也有相应依据:2013年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驾驶机动车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醉酒驾驶机动车,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133条之第1款第5项的规定,有严重超员、超载或者超速行驶,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牌证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行为的从重处罚。该规定明确要求要将醉酒驾车的犯罪行为的附随非构成要件行为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评价。在落实该条的司法实践过程中,要体现“一事不二罚”的法律原则,就应对已科处的行政处罚在刑事处罚中予以折抵。
其次,对危险驾驶罪案件中的四类行为的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如何并罚?这一问题在危险驾驶罪案件中并不突出,原因是一旦发现危险驾驶行为涉嫌犯罪,就转入了刑事程序,行政处罚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仅涉及吊销驾驶证,而吊销驾驶证与后面的刑事处罚属于不同性质,可以同时适用,法律没有规定其他的处罚种类,因此不存在双罚后的折抵问题。
(二)行刑在程序上的对接
危险驾驶罪案件处理程序上的二法对接,其实还是涉及理论上争议的先刑事还是先行政,或者亦刑亦罚的问题。僵硬适用先刑事后行政,会导致实务上的难点。因此,在危险驾驶案件中,虽以刑事处罚为主,但刑事程序不可能事事、处处优先,且不会因全案转入刑事程序而阻断案件其他部分的行政程序。因此,危险驾驶罪案件中,法院判决时应充分考虑该案中非构成要件行为的量刑意义,给出应判处的刑罚,然后再将其已经承担的行政处罚在应承担的刑罚中折抵,最后确定宣告刑。这种情况下,行政程序先于刑事程序开始,也必然要先于刑事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