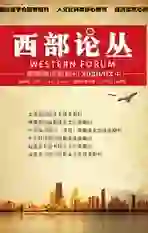人工智能辅助人类从“物役”走向“役物”
2020-08-16巩欢欢王英慧
巩欢欢 王英慧
摘 要:“异化”作为重要的哲学概念涉及内容极为广泛,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到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乃至张一兵教授所提出的“物役性”思想无一不彰显着人被其创造物所奴役的生存窘态。而在如今的智能时代中,立足于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异化”概念进行再阐释有助于找到摆脱“人为物役”的理论武器,从而实现消灭异化、复归人类主体自由的伟大愿景。
关键词:异化;物役性;人工智能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异化现象日渐凸显,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产生了威胁,因此消除人工智能所带来的“异化”现象则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时代任务。从哲学维度上看,在逻辑上厘清“物”与“人”的主体地位、实现人与机器的和谐发展才是消灭“异化”、摆脱“物役性”的根本所在。
一、异化概念之再辨析
人所共知,“异化”这一概念早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中就已出现,并且贯穿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始终,这对马克思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异化”主要是指主体丧失自我而成为他物的状态,但二者由于立场不同对于“异化”概念的理解存在着极大差异:黑格尔将“异化”的主体设定为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并且认为绝对精神的异化与辩证法运动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他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用“异化”概念所创建的“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的哲学体系彰显着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而费尔巴哈则与之不同,他立足于唯物主义的立场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异化”,他用“异化”揭示了基督教的人学本质,并且又提出了“神是人类自我异化的产物”这一论断,由此形成的人本主义异化与对黑格尔哲学背道而驰。但由于费尔巴哈把人的意识和宗教理解为现实生活本身,将人类解放归结为意识的转变,所以再一次陷入唯心主义。
国内外关于“异化”理论的研究层出不穷,曾有学者用“好”与“恶”来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异化”理论进行区分[1],但这并不是单纯的褒贬,而是对于“异化”逻辑的深层理解。这里的“好”是指黑格尔依据辩证法的辩证逻辑对“异化”的运动过程进行诠释,即“它在它的异在本身里就是在它自己本身里。”[2]258换句话说就是“绝对精神”经过否定之否定过程而最终达到的是主体自身的复归状态,是一种肯定“异化”状态;而这里的“恶”则是指费尔巴哈将“异化”理解为人的永恒的自我丧失状态,即“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然后,又使自己成为这个对象化了的,转化成为主体、人格的本质的对象。”[3]56这里的“对象化”可理解为“异化”,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异化状态。而马克思则对二者的“异化”理论实现了“天才超越”,他继承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人本主义立场,吸收了黑格尔哲学辩证法中的合理成分,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结合,从实践維度构建了“异化劳动”理论,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本身即劳动活动的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人与人的异化。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理论的构建是异化史观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不仅实现了对无产阶级劳动者的关怀,更多体现的是他对人作为一种类存在的尊重与关爱。
二、从“异化”到“物役性”
青年时期的马克思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痴迷者,他曾在《博士论文》中,将“现象世界”视为其概念异化而生成的“原子”的产物。但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他开始对黑格尔的异化思想持批判态度,并且转向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利用“异化”思想对国家和法进行探究,将“异化”则引申到人的本质的异化。在《论犹太人问题》的撰述中,他又将“异化”的视角切换至经济领域,指出“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4]52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厘清了资本主义时代中劳动者与资本家在经济领域的对立矛盾,由此他将异化的逻辑贯穿于劳动的分析中,进而将对立和矛盾的源头归结为“劳动的异化”,从此异化劳动理论被创造性的提出。而在他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时,“异化”概念虽然也一直在被沿用,但他却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与费尔巴哈哲学做了彻底清算,此时的“异化”与从前人本主义哲学视中的“异化”所要表达的意义并不相同,虽然马克思用“劳动”来进行修饰加以区分,但并不能明确地凸显出人被自己的创造物所奴役的特性,于是他在后来的作品中加入“物化”一词来进行区分,对此张一兵教授重新做出了强调,并且用“物役性”概念来界定这种特殊的人的异化状态。
“物役性”一词自始至终不曾出现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它是由张一兵教授在《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简称《主体向度》)的攥写中提出的,其含义是“我们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力量所驱使。”[5]199“物役性”的提出,最主要的目的是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人本主义异化相区分,彰显马克思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转向,以此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这种伴随着“物化”的异化状态。[6]在《主体向度》中,张一兵教授认为马克思在《形态》以及之后的作品中所阐述的“物化”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5]193,换言之,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下通过生产而达到对自然的占有。其中的“物化”是指以人类为主体,通过劳动而对劳动对象作出改变,从而达到自己目的的积极过程;另一层是资本主义时期人的物化表现为“个人在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7]176在这一层面上,生产的物化过程却表现为“产品支配生产者,物支配主体”,马克思由此指出,这里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相互关系被颠倒了”,而“物化”究其本质来说则是人的创造物反过来奴役人![5]193可见,“物役性”所要表达的正是这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与物的主客体颠倒的关系,也就是“物化”的第二层含义。
张一兵教授根据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的划分,将“物役性”一词赋于了两层含义“其一是自然物役性,其二是经济物役性。”[5]247人的依赖性的阶段所表现出的是自然的物役性,物的依赖性的阶段表现出的是经济物役性,在这两个阶段中,人都处于被制约的状态中。马克思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所面临的暂时的必然性,而最终将迈向人类发展的自由国度,也就是必然王国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迈进。在共产主义自由王国中,人的生产劳动将不再被自然和经济所奴役,人的劳动不仅仅局限于谋生,而是既创造财富又实现自我价值。
“物役性”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可以强调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人本主义立场;另一方面也突出这种带有资本主义气质的“异化”不断从经济领域蔓延到对人内心的支配,从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发生异化,推进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现状的批判进程。[8]由此可见,张一兵教授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以“物役性”作为《主体向度》批判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点,形成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总体认识。
三、从物役走向役物: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人类实现主体自由的复归
在资本主义时期“物”不仅对工人产生了奴役,同时也对资本家产生了禁锢,而“资本家”所体现出的只是被人们设定的“物”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使物与工人相分离,这种对于“创造物”(利益)的占有,导致了人被“物”的力量所驱使,因此在逻辑上厘清“物”与“人”的主体地位是摆脱“物役性”的根本所在,同样也是迈向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理论武器。在如今的智能时代中,技术改变了人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如智能手机、无人驾驶车辆等机器设备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为人类节省了大量的劳动时间,让使用者能够有更多的自由时间从事其热爱的劳动活动,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劳动自由;但另一方面使人类的劳动活动被智能机器所取代,催生了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所定义的“无用阶级”[9]288,同时也增加了人类对机器使用的依赖性。人工智能原本是僵死的机器,但在资本的诱惑下变成了奴役人的工具,可见智能技术的发展始终与其“物役性”的蔓延是相伴相随的。
在智能技术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无用阶级”的群体越来越壮大,一些简单的重复性的体力劳动逐渐被工厂的自动化生产线所取代;农业、服务业等行业的技术性工作者也逐渐被机器人所取代;甚至一部分脑力劳动者也正在被相应的数据处理程序、智能算法所取代。在智能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无论是技术工人还是艺术家、科学家也都可能沦为“无用阶级”,因此立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来塑造新型和谐的“人-机”关系是迫在眉睫的时代任务。面对“无用阶级”的产生,笔者认为展开社会调节是至关重要的,根据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所创造的经济价值來实施相应的“全民基本收入”等社会财富再分配的保障措施,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的物质需求,缓解人们因失业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人们的工作不再只追求物质利益而是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与此同时,劳动者一方面应该提升自己的劳动能力和创新意识,开拓更富有创造力的新工作;另一方面还应该转变劳动意识,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将劳动与娱乐融为一体,从事更能实现自由与自我的劳动活动。智能技术对人的“人”排挤以及“人”在技术中产生的“物役性”都只是表象,其实质则是资本积累的不断扩大导致资本家使用低成本、高效率的智能机器来替代使用劳动力,是资本驱动技术从而产生了“人为物役”的异化现象,因此回归人的主体逻辑、利用智能技术辅助人类实现主体自由的复归才是智能时代人类的立命之本。
面对智能技术给人类带来的焦虑与挑战,我们应始终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建立和谐的人机关系,使“人”从“人为物役”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让技术服务于人,从而实现“物为人役”的革命性转变、实现人类劳动的自由与解放、实现人类的主体地位的复归,以至于“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4]189,并以此打破资本对人的奴役状态,将人的发展、人的生存境遇以及整个人类的和谐共生作为历史进步的评介标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势不可挡,因此我们应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合理利用智能技术辅助人类迈向共产主义“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自由与解放。
参考文献
[1] 韩立新.从费尔巴哈的异化到黑格尔的异化: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一个解读[J].思想战线,2009,3506:67-71.
[2] [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M].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费尔巴哈著作选集》(下),荣震华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6] 张一兵. 物役性:马克思哲学新视域中的科学性批判话语[J]. 社会科学战线,1996(03):97-10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刘丽. 物役性概念之再辨析——兼评张一兵教授《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J]. 江苏社会科学,2013(04):13-17.
[9] [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M].林俊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