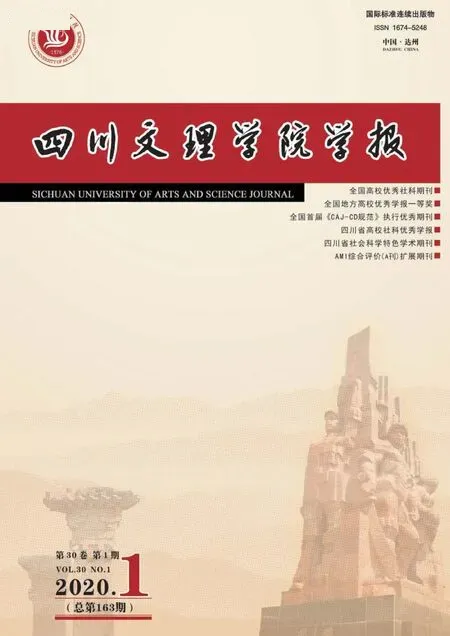酌定不起诉制度的双重审视
2020-08-13陈雪莲
陈雪莲
(深圳大学 法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0)
酌定不起诉,又叫相对不起诉,是指对构成犯罪的案件符合特定情形时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制度,是一种不予起诉制度。[1]酌定不起诉本质上体现了起诉便宜主义精神:虽实施了犯罪行为,满足起诉要件,但检察机关综合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提起公诉的,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决定不起诉。[2]检察机关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重要使命,[3]酌定不起诉的价值在于通过程序分流功能合理配置诉讼资源,缩减司法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浪潮下,我国检察机关一直在推动该制度的完善及适用率的提高。然而,相关数据表明,该制度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有效适用。本文拟从酌定不起诉适用现状入手进行分析,以期发现其在适用过程中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
一、酌定不起诉域内外适用之对比
2006—2015年期间,如图1所示,日本起诉犹豫率呈曲线式上升状,2006年就达40.7%,到2013年则攀升超过50%。以2015年为例,日本该年被提起刑事公诉的有77268人,而适用起诉犹豫的达78467人,起诉犹豫率高达50.4%。从以上数据可知,适用起诉犹豫的人数略多于被正式起诉的人数。相较于我国,德国酌定不起诉适用现状更好。2012年德国检察院共了结刑事案件4556600件,其中予以酌定不起诉的案件数为12691563。如图2所示,德国酌定不起诉率为27.85%,远高于提起公诉率10.66%。法国2015年共法院登记案件4827542件,处理案件4260836件,其中检察官决定采取替代刑事审判的其他程序463960人,占36.7%,检察官决定不提起公诉的有153667人,占12.2%。除德、日外,我国台湾地区2003至2007年间不起诉率均处于30%以上,适用率高。[4]
表1涵盖了2013年至2015年中国检察机关适用酌定不起诉的数据,[5]统计项目涵括起诉人数、不起诉人数与酌定不起诉人数,不起诉率与酌定不起诉率,共计五项。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不起诉率极低,平均为5.3%左右,而酌定不起诉作为不起诉之一,其适用率更低。
我国酌定不起诉制度始建于1996年《刑事诉讼法》,至今已二十余年,但它在实践中仍然呈现出适用率低的现状,这说明其在实践中适用仍存在很多问题。酌定起诉率低直接影响了其程序分流功能的实现,即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增多。进入审判程序后,即使是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法院也要遵循程序正义原则,按照法定程序审理,而这些案件的审理结果又通常为判处罚金、缓刑、管制,这难以避免“杀鸡用牛刀”尴尬局面的出现。换言之即是这些案件本可以通过酌定不起诉制度由检察机关裁量分流出去,但实则因未适用该制度而进入审判程序,由于案件性质本身较为轻微,导致审判结果轻微。相比于性质严重的犯罪而言,浪费了大量司法成本,得到的成效小,拖延了诉讼效率,同时也增加了控辩双方的讼累。要完善酌定不起诉,必须探析其适用率低的成因。

图1 日本起诉犹豫率

图2 德国检察院处理案件情况比例图

图3 台湾地区2003-2007年不起诉率

表1 :2013年至2015年中国检察机关适用酌定不起诉情况表
二、酌定不起诉适用率低的原因
我国与1979年通过《刑事诉讼法》,该法第101条规定了“免予起诉”制度。出于实践层面制止该制度被滥用的可能,为杜绝检察机关行使法院专属定罪免刑权的现象,立法机关于1996年废除了此项制度,但同时赋予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权,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且不需要判处或可免除刑罚的案件,公诉机关有权作出不起诉决定。立法机关基于节约司法资源、提升诉讼效率、改造犯罪嫌疑人的初衷设立了该制度,然而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检察机关对酌定不起诉有限适用,未能发挥出酌定不起诉的应然价值,亦并未能体现最初的立法目的。究其本质,笔者认为可以分为制度内与制度外的原因。
(一)制度外成因审视
1.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难以把握,此为酌定不起诉适用率低的基础原因。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为酌定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款规定犯罪情节轻微的案件,依照法律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机关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不起诉决定。由此可知,确定一行为适用酌定不起诉,需满足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这两个要件。
适用的严苛性体现为适用该制度须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这限制了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如此一来,即使犯罪情节轻微,但因不满足第二个要件也不能得到适用;或者满足依照法律规定不需判处或可免除刑罚这一要件,但由于犯罪情节不够轻微也不能适用酌定不起诉,这在根本上限制了酌定不起诉价值的发挥。而实际上,其中有很多案件用酌定不起诉进行分流的效果比起诉到法院会好很多。[6]
酌定不起诉适用条件的不明确性,导致实践中适用该制度较为困难。因此,如何理解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条件至关重要。首先,犯罪情节轻微的内涵以及存在的范围为何?其次,两个要件间是什么关系?
激光雷达作为一种新兴的探测手段在大气环境监测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由于其技术实现难度高,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一些缺点。例如:受大气的光传输效应影响(包括光速、折射率的变化和散射现象),会使激光光束发生抖动、畸变,直接影响激光雷达的测量精度,因而不能全天候工作;激光一般在晴朗的天气里衰减较小,传播距离较远,而在大雨、浓烟、浓雾等坏天气里,衰减急剧加大,传播距离大受影响;由于激光雷达的波束极窄,在空间搜索目标非常困难,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搜索、捕获目标,直接影响探测效率等。
针对“犯罪情节轻微”的范围,学界有两种不同观点:犯罪情节轻微存在于所有犯罪类型中,重罪也可以有情节轻微之说,即不论何种性质的犯罪,都可结合其他情况不予起诉。另一种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仅存在于轻罪中,即仅存在于法定刑为三年以下的轻罪中。[7]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更具合理性。理由有二:其一,若承认重罪也有犯罪情节轻微之学说,相当于肯定重罪也能免于刑罚,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滋生犯罪人的侥幸心理,导致重罪案件数量增多,扰乱社会治安,与《刑法》第37条之立法目的相违背。其二,承认重罪也有轻微犯罪情节,实际上扩宽了检察机关权力边界,难免导致检察机关对权力的过度适用,不利于司法职能的配置,而且破坏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7]此外,某些学者主张重罪也应具有犯罪情节轻微的特性,以此扩大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1]完全可以通过处理适用条件之间的关系加以解决,而非承认重罪也有犯罪情节轻微。
对“犯罪情节轻微”应作何理解,《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并未给予明确定义,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查逮捕和公诉工作贯彻刑诉法若干问题的意见》4曾对其进行过如下直接说明:犯罪情节轻微指虽已触犯刑法,但从犯罪的动机、犯罪的手段、犯罪引发的后果、犯罪后的态度等多方面综合考虑,认为依照法律无需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处罚的。但该解释也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犯罪动机、犯罪后的态度等罪前或罪后情节纳入考量犯罪情节的考量范围内,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犯罪前后的行为不能称之为犯罪,因此也谈不上犯罪情节的问题;二是将“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处罚”当做了犯罪情节轻微的考量因素,这就将酌定不起诉的第二个适用条件予以形式化。[8]
关于酌定不起诉两个要件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理论界大多数学者认为“犯罪情节轻微”是“不需判处刑罚”和“可以免除刑罚”的共同前提,但也有观点认为“犯罪情节轻微”只是“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前提,而与“免除刑罚”不存在前提关系,只要被认定为属于“免除刑罚”的情形,不论其情节是否轻微均可适用酌定不起诉。[9]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为合理,依照文义解释法,立法者想要表达的也是前者为后两者的共同前提。因为假设第二种观点成立,则立法者应将此表述为“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或者依照刑法规定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显然立法者并没有这样做,因此这样理解有失偏颇。
2.法律规定的酌定不起诉适用程序繁琐,这是酌定不起诉适用率低的直接原因。《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2012年修订)第406条规定,满足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检察长或检委会有权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司法实践中,酌定不起诉决定的作出流程为:第一,先由承办检察官对案件进行审阅,审阅后认为可以适用该制度的,向部门负责人提交意见;其次,由负责人进行审核,如同意承办人意见的,则报送检察长审核;第三,检察长审核后报检委会审核;最后,经检委会审核后,还得报请上级检察机关批准。即使是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案件,也要先经本级检委会讨论决定后,报上一级检察院备案。[1]
要适用酌定不起诉必须经层层审批,如此繁琐的程序导致运行过程的复杂化,直接结果就是检察机关为了减少办案压力,从严适用酌定不起诉。此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检察机关对不起诉裁量权的滥用,但其减少了酌定不起诉适用的可能性,直接造成了适用率低的现状。在司法责任制推行的浪潮下,部分地方检察机关创新了审批机制,改为由办案组决定,报检察长审批。不得不说,此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程序对酌定不起诉适用的束缚,但针对全国范围而言,这毕竟只是个案,在法律没有作出修改,承认此种做法的前提下,该做法不具有普遍适用力。
3.酌定不起诉制度运行保障机制不健全,这是酌定不起诉适用率低的现实原因。运行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有利于酌定不起诉的扩大适用。保障机制要求检察机关关注被不起诉人回归社会后的表现,如果他们回归社会表现良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酌定不起诉决定的正确性,可以鼓励检察机关适用酌定不起诉制度。保障制度缺失主要表现为:缺乏对被不起诉人的有限监督与制约机制、运行机制的不完善。
首先,保障制度缺失表现为缺乏对被不起诉人的有限监督与制约机制。对被不起诉人的有限监督与制约机制指酌定不起诉后对被不起诉人的监管、教育问题。宋英辉教授认为,实践中,最艰巨的任务在于不在于酌定不起诉的适用问题,而在于被不起诉人的监督及再教育问题。[6]诚如所言,实践中立法机关对于酌定不起诉仅规定了其适用条件,忽视了适用后对被不起诉人的监督制约机制。笔者认为,完善对被不起诉人的有限监督与制约机制,可以通过与村委会(或居委会)、家庭、企业建立共同监管机制加以实现。同时政府加大在相关的机构设置和活动组织方面对被不起诉人的关注程度和践行程度,使被不起诉人获得更多法律咨询、心理矫正及适当教育的机会。
其次,保障制度缺失实属酌定不起诉运行机制不完善。第一,酌定不起诉决定是通过检察机关内部的审批程序作出的,具有封闭性,导致运行过程不透明;第二,酌定不起诉决定通常忽视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被害人的意见,未充分保障其程序参与权;第三,检察机关的绩效考核将酌定不起诉的运行作为指标之一,在内心不愿适用酌定不起诉,更别说完善酌定不起诉的运行机制了。
(二)制度外的成因审视
然而实践中,不论是办案人员或普通百姓均存在“有罪必诉、有罪必罚”的观念。对于办案人员而言,这种观念一方面来源于个人对刑罚的认知,另一方面来源于舆论的压力。个人刑罚认知来源于其自身的法学基础,通常与接受的法学教育有关。舆论的压力则来自于案件当事人,如果其作出“有罪不诉”的决定,被害人认为自身权益未得到保障,就会采取如申诉、起诉、信访等救济措施,这会影响办案人员的绩效考核,因此,其认为限制适用酌定不起诉是最理想的做法。
2.不起诉专项检查和考评制度的异化,此为酌定不起诉率低的人为因素。一方面,严格的不起诉专项检查是对运行结果的考察,能起到防止权力滥用的效果,另一方面又使检察人员对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慎之又慎,影响了不起诉率。同时,考评制度的异化体现为将不起诉率作为检察机关内部绩效考评标准,这无异于案件承办人员人为限制不起诉适用,减少了酌定不起诉适用的可能。
三、酌定不起诉制度的改良
(一)制度内改良
1.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酌定不起诉的适用需同时满足两个要件,具有形式上的严苛性。同时,对“犯罪情节轻微”的考量缺乏法律依据,也会致使酌定不起诉条件模糊,实际操作较困难。这两方面的原因严格限制了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不利于其功能的最大化发挥。
笔者认为应明确酌定不起诉的实体条件,适当扩大酌定不起诉的适用范围以保障其应有价值的实现。针对“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其实质上与《刑法》第37条之规定是相一致的。《刑法》第37条规定赋予了法院基于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可以免除处罚的司法裁量权。这也意味着在我国“免除刑罚”有法定免除和酌定免除两种途径,“免除刑罚”需满足刑法中16种情形,并在这些情形中,只要没有出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关于印发〈人民检察院办理不起诉案件质量标准(试行)〉的通知(2007修订)》中不宜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八种情形的,则应肯定其适用酌定不起诉。[8]
除此,笔者认为厘清酌定不起诉与附条件不起诉之间的关系实为必要,是扩大酌定不起诉适用范围的应有之义。因为酌定不起诉决定是检察机关行使裁量权的体现,其与附条件不起诉存在一定共性,正确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界定酌定不起诉之适用范围。对于二者关系,有学者将附条件不起诉视为酌定不起诉的补充制度,二者虽然存在一定共性,但实为两种不同的制度。《刑事诉讼法》第 271条规定了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条件之一为“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可得出在适用未成年人涉及《刑法》第二编分则第四、五、六章规定的犯罪,并且可能被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时,二者适用范围上存在一定的重合。[7]
最后,可将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就轻微刑事犯罪的和解纳入酌定不起诉的考量范围内,即和解不起诉。和解不起诉是指刑事案件双方当事人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由加害人向被害人认罪悔过并征求被害人的谅解书,在双方自愿达成和解协议的情况下,检察院可以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11]
2.简化酌定不起诉适用的内部程序。法律对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程序规定了较为冗杂的内部审批制,三级审批制的繁琐在一定程度上阻却了检察机关运用酌定不起诉。即使实践中部分检察院在遵守法律底线的前提下创新了审批机制,但针对全国范围而言只是作为个案存在。如1999年北京市检察院在保证符合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规定基层检察院自主决定酌定不起诉的权力并报上级检察院备案。[1]再如这两年,实践中部分检察机关跟随司法责任制改革的浪潮,实行酌定不起诉由检察长审批决定。以上例证毕竟只是小范围内的创新,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不具有普适力。要想做到从根本上简化酌定不起诉适用程序,还是只能通过立法的途径加以实现——积极响应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号召,取消现有的内部审批制度,实行检察长负责制。
3.建立健全运行保障机制。首先,建立健全对被不起诉人的监督制约机制。现有的酌定不起诉制度被称为“一次性”制度,通常而言,检察机关没有时间精力去关注被不起诉人回归社会的程度如何,这实际上与使犯罪分子早日回归社会的立法目的相偏离。故笔者认为应完善对被不起诉人的监督制约机制,可以通过与村委会(或居委会)、家庭、企业建立共同监管机制加以实现。同时政府加大在相关的机构设置和活动组织方面对被不起诉人的关注程度和践行程度,使被不起诉人获得更多法律咨询、心理矫正及适当教育机会。
其次,试行听证程序,公开不起诉决定书,提升酌定不起诉的透明度。酌定不起诉决定的作出具有内部性,实行试听程序,检察机关可以将被害人方和犯罪嫌疑人方聚集在一起,互相听取意见。这不仅能保证酌定不起诉决定作出的正确性,还能通过这种方式化解双方矛盾,提升双方对决定的接受度。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对酌定不起诉决定书进行说理分析,并公布上网。
(二)制度外改良
1.转变陈旧的刑罚观念。“有罪必罚”“有罪必诉”是国家为了达到绝对的正义对所有违反刑法的犯罪行为无一例外的加以惩罚。单纯的报应刑理论,现已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轻刑化、非刑罚化政策。托尔斯泰曾说“文明的建立的不是机器而是思想”,那么思想的停滞也会影响文明的前进。刑罚观念在检察机关工作人员适用酌定不起诉时会起潜移默化的作用,因此转变陈旧的刑罚观念势在必行。
首先对于检察机关整体而言,需要改变现有不起诉检察制度和考评机制,将人为选择适用酌定不起诉的做法扼杀在摇篮。其次对于办案检察人员而言,要不断学习新的理论,转变自身根深蒂固的“法定起诉”情节,对于只要满足酌定不起诉条件的案件必须适用。最后,对于被害人方而言,只要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诚恳,积极弥补损失,在检察机关的主持下,二者可以达成和解,签署和解协议书。
2.改革不起诉检查制度和考评制度。改革不起诉检查制度,可以从司法责任制角度入手,与酌定不起诉的审批程序相联系。立法者鼓励在司法改革政策下推行检察长责任制,可以由检察长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因此在对不起诉检查时,可以通过检察长汇报工作的形式进行。同时,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应该充分说理,并予以公示,这在一定程度也解决了因为不起诉检查而限制酌定不起诉适用的问题。现有考评制度将不起诉率作为考评标准,限制了酌定不起诉适用。相反,检察机关应顺应非刑罚化世界潮流,遵循宽严相济政策,鼓励办案人员在满足法定情形下多用酌定不起诉。
注释:
① 德国酌定不起诉包括有负担酌定不起诉案件188657件,无负担酌定不起诉案件 1080499件。
② 虽然该文件现为失效状态,但在《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均未规定何为“犯罪情节轻微”的情况下,能为我们理解“轻微”的内涵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