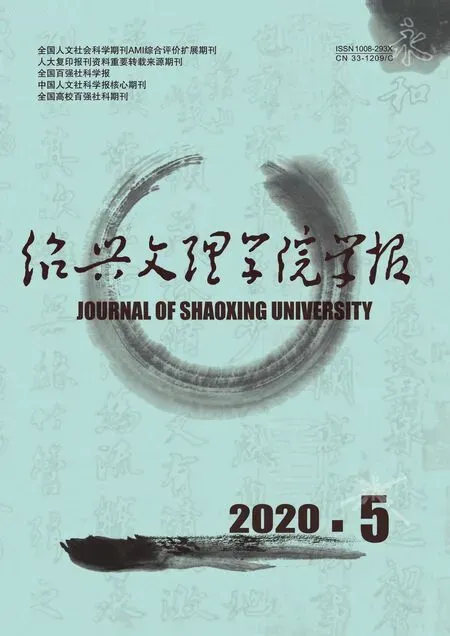晚明米芾轶事小说的辑撰动机及叙事特色
2020-08-12刘天振
刘天振
(浙江师范大学 江南文化研究中心,浙江 金华 321004)
晚明江南文士对北宋米芾的追捧,不仅体现于对其书画艺术的崇尚,更体现在对其狂放不羁个性的崇拜,这后一方面可以从当时许多文士竞相参与米芾轶事搜辑、编刊、传播的盛况中得到证实。对于米芾的畸行怪癖,宋钱愐《钱氏私志》、元脱脱等《宋史·米芾传》、张雨《句曲外史集·中岳外史传》、陆友《砚北杂志》等书已有零星的记载。如《宋史》本传不仅记载米芾为文、书法、画品等方面的成就,也略述其嗜好与怪癖:“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观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又不能与世俯仰,故从仕数困。”[1]5154另几书则收录了更多的米芾逸闻趣事。但总起来看,晚明之前的此类记述数量较少,且多有重复,使米芾形象流于类型化、脸谱化之状态。即使载录米芾轶事较多的《南宫遗事》,也不过十数条而已。晚明包衡《米襄阳志林序》就说:“米老事不多经见……《南宫遗事》为陆友仁所辑,计楮仅十有八。”[2]406范明泰编撰《米襄阳志林》时也叹惋,《南宫遗事》仅占其搜集米芾轶事之“什一”[2]405。陈继儒曾有辑撰米芾轶事的谋划,曾说:“予读陆友仁《米颠遗事》,恨其故事未备。”[2]400这种状况至晚明时期发生了根本的改观,由于众多江南文士的竞相参与,尤其一些名士硕儒的推毂助力,使五百年间流传于口头与书面的米芾轶事得以汇辑成多种著作,蔚为大观。这些纂著的成书动机及其文献、文学价值均值得后人深入探究。
一、米芾轶事诸集问世时间集中
晚明江南地区出现了多部米芾轶事小说集(1)《四库全书总目》虽将这些著作归入“史部·传记类存目”,但通览其内容,多属传闻轶事,如四库馆臣称《米襄阳外纪》“纪米芾遗事……多不著出典,未足依据。”(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2页。)又称郭化《苏米谭史广》“杂采苏轼、米芾轶事可资谈柄者……皆摭拾小说。”(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3页。)又谓毛晋《苏米志林》“掇苏轼琐言碎事集中所遗者,编为二卷。又以米芾轶闻编为一卷。”(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3页。)因而它们并非正宗的“传记”。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将《苏米谭史》《苏米谭史广》归于“子部·小说类”。今人宁稼雨编《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明代·志人类”著录了《苏米谭史》《苏米谭史广》《苏米志林》诸书。是故本文称这些作品为“轶事小说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存目”著录此类作品有范明泰撰《米襄阳外纪》十二卷、《米芾志林》十六卷(2)《四库全书总目》卷六〇著录范明泰撰《米芾志林》为十六卷,但今存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范氏清宛堂刻舞蛟轩重修本《米襄阳志林》实有十七卷,计《米襄阳志林》十三卷,《米襄阳遗集》《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砚史》各一卷。当是《四库总目》著录有误。而《四库总目》所著录《米襄阳外纪》十二卷当为陈之伸参补本,今存崇祯间刻《宋四家外纪》中《米襄阳外纪》即十二卷,分十二门,陈之伸删去了“世系”一门,与《四库总目》著录本吻合。而馆臣所撰提要称,是编“分恩遇、颠绝、洁癖、嗜好、麈谈、书学、画学、誉羡、书评、杂记、考据十二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2页),实际只列举十一门,漏掉“麈谈”一门。同时,馆臣又称,《米襄阳外纪》与《米芾志林》并同,则可知《四库全书总目》卷六〇对《米襄阳外纪》与《米芾志林》的著录均有疏误。,毛晋撰《苏米志林》三卷(3)后人自《苏米志林》中析出《米元章志林》一卷,题名《米襄阳》或《海岳志林》,曾有多种单行本及丛书本。,郭化撰《苏米谭史》一卷(4)《四库全书总目》卷六〇著录郭化《苏米谭史》为一卷,当误。一是其提要文字自相矛盾:“是编杂采苏轼、米芾轶事可资谈柄者,各为一卷。”(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2-543页)既云苏轼、米芾轶事各为一卷,全书当为二卷。二是今存明末闵于忱《枕函小史》所收《苏米谭史》为二卷,《苏长公外纪》与《米南宫外纪》合编为二卷,其中米芾部分仅有20条,其余均为苏轼轶事。因此该书原刊本至少为二卷。、《苏米谭史广》六卷,佚名辑《宋四家外纪》四十九卷(5)《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该书“不著编辑者名氏”(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544页)。但今国家图书馆藏有崇祯间刻本《宋四家外纪》四十九卷,题“陈之伸辑”。。这些书按编刊方式又可分为二类:一是米芾轶事专辑,二是米芾与苏轼、黄庭坚等人轶事合刊。据《四库提要》记载,同题范明泰撰的《米襄阳外纪》与《米芾志林》前十二卷内容一致,《米芾志林》在前十二卷后附刻范明泰辑《襄阳遗集》一卷,《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研史》各一卷[3]542。此外,《宋四家外纪》中所收录的《米襄阳外纪》亦题为范明泰撰,四库馆臣指出,此书所收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四家外纪“本各自为书,此本盖明季坊贾所合刻也”[3]544。因此,以上三部辑录米芾轶事的作品当为同一书的不同版本,内容稍有出入,当是出于书贾的任意取舍。该书存世版本有二:一是南京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范氏清宛堂刻舞蛟轩重修本《米襄阳志林》十三卷,后附《襄阳遗集》《海岳名言》《宝章待访录》《研史》各一卷,已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84册。二是国家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所藏明崇祯刻本《米襄阳外纪》十二卷。郭化辑《苏米谭史》二卷,据辑者自序,初刻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今有闵于忱辑《枕函小史》本,为明末吴兴松筠馆朱墨套印本,将《苏长公谭史》与《米襄阳谭史》合编为二卷,其中米芾部分仅录20条,其余皆为苏轼轶事。卷首有梅敦伦《序》及郭化《自序》。《苏米谭史广》六卷存明末胡正言十竹斋刻本,藏于国家图书馆,内含《东坡先生谭史广》四卷及《南宫先生谭史广》二卷。毛晋撰《苏米志林》三卷存明天启五年(1625)毛氏绿君亭刻本,国家图书馆等多处有藏,辑录苏轼遗事227则,米芾轶闻115则。其中《米元章志林》一卷对后世米芾书画研究界影响甚大,常以单行本刊刻行世,屡屡为学者征引。另外,华淑撰《癖颠小史》汇辑历史上各种癖颠之事50篇,多数是每篇一条,但有的篇目下并陈多条,如《洁癖》一篇下列宗炳、王思微、何修之、王维、米芾、倪瓒等6人的洁癖轶闻。此书辑录了3条米芾癖事。
综上,晚明产生的米芾轶事小说集虽经过多人辑撰且版本纷乱,但大致可归为四部:范明泰撰《米襄阳志林》十三卷、郭化撰《苏米谭史》二卷、《苏米谭史广》六卷和毛晋撰《苏米志林》三卷。其中范明泰《米襄阳志林》最迟成书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问世最早,卷数最多,除去卷一“世系”摘录的15条有关米芾家世、生平的记载,其余十二卷辑录米芾轶事612条,是诸书中内容最为丰赡者。而毛晋的《海岳志林》成书最晚,刻于天启五年(1625)。短短二十余年时间问世了四部多种版本的米芾轶事小说集,这种现象颇令人关注。

表1 晚明米芾轶事小说集存世情况
二、辑撰主体:基本全是江南文士
考察这些著作辑撰者、作序跋者及校阅者的籍贯及主要活动区域可以发现,他们几乎全是江南文士。此处所言之江南,仅取学界共论的文化意义上的江南,包括苏南、浙北、皖南等地区。《米襄阳志林》的撰者范明泰是今浙江嘉兴人,父祖均为进士,范明泰本人也有举人功名。《海岳志林》的撰者毛晋乃苏州府常熟人士,是晚明著名学者、藏书家、出版家,今存毛氏绿君亭刊刻的书籍常被目为善本。为《苏米志林》撰序者魏浣初为毛晋之舅,亦为常熟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曾官广东提学参政,有诗集及论著传世。《苏米谭史》的撰者郭化乃皖南宣城人,作序者梅敦伦亦为宣城人。《枕函小史》本《米襄阳谭史》的校者闵于忱是吴兴(今属浙江湖州)人,评者屠长卿是鄞县(今属浙江宁波)人。为《苏米谭史广》六卷作序者有18人之众,其中何伟然是临安(今属浙江杭州)人,吴从先为常州(今属江苏)人,其余16人大抵皆为宣城人士。校阅者为徐日昌和胡正言,前者亦为宣城人,后者是休宁人。胡正言十竹斋位于南京,是当时著名的私人书坊,尤以出版书画笺谱闻名。《宋四家外纪》编者陈之伸为浙江海盐人,是著名戏曲家陈与郊之孙,曾中崇祯七年(1634)会试副榜第三名,历官湖南布政使司参议兼按察司佥事,也是著名出版家。撰序者王道焜为钱塘(杭州)人,系天启元年(1621)举人,曾任南平知县、南雄同知,明亡殉国。以《米襄阳志林》为例,为其作序者有3人,题辞者有9人,12人籍贯分布情况如表2:

表2 《米襄阳志林》题辞作序者籍贯简表
12位为米芾小说集题辞作序者中有10人是江南士人,1人为长期寓居江南者。其中不乏名闻天下的名士,如为《米襄阳志林》作序的赵宦光、张献翼、王穉登等均为吴中名士,华亭陈继儒更是声动海内的大名士。这些江南文士不遗余力地推崇米芾轶事小说集,强力助推了它的传播与影响。张一绅《苏米谭史广》小序写道:“往见秀山坊中有《苏米谭史》一书,其为帙无几,友人争得之,一时纸贵。予每把玩,津津不置。意编是者必襟期旷远、磊落不羁之士,雅契其风者久之。一日游白门,晤于曰从斋头,从旁询名姓,知为肩吾氏,相与抵掌而谭,舌锋谭剌,令人惊怖,乃知其与苏米合神,故肖速也。复出《广》一帙见示,余纵观之,犹河汉无极,一过一倾倒,因为之订交,而从庚其梓。”[4]5其于当日士林中的传播盛况可见一斑。
《米襄阳志林》十七卷的校阅者大多是嘉兴府人,其次为苏州、杭州、松江等地人。
从表3(见下页)所列可知,《米襄阳志林》十七卷的35位校阅者中有30位是江南士人,籍贯分布以浙江嘉兴为中心,其中不乏出身于江南世家者,例如卜二南出身嘉兴曲学世家卜氏,嘉兴卜氏与吴江沈氏世代联姻,吕世延出身明代“祖孙父子五朝恩眷,三世赐葬”的秀水吕氏,钱应曾出身秀水书画世家钱氏,郁嘉庆乃科举世家秀水黄氏之婿,等等。
综上所述,米芾轶事小说集的问世,在时间上集中于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在地域上集中于江南地区。
三、编纂动机:晚明江南文士的志尚载体
米芾、苏轼等人直从所好、不用世法的人生态度契合晚明江南士人的人格追求。米云卿《米襄阳志林题辞》云:“士有不经世故、直从所好者,上古洗耳、投渊之徒皆是也。省其意更无他奇,第不肯以所好易所不好耳。近世有之,便谓之‘僻’,甚而谓之‘颠’,可知率真者寡矣。读书好古如元章,而子瞻尚有从众之谑,可叹哉!及得《宝月观赋》,因与书曰:‘恨相从二十年,知元章不尽。’……(范明泰)又嗜元章书,殆与我家同癖也。”[2]406-407陈继儒《米襄阳志林序》说:“古今隽人多矣,惟米氏以颠著,要之颠不虚得,大要浩然之气全耳……冠盖衣襦,起居语默,略以意行,绝不用世法,而公之颠始不落近代。”[2]400所谓“直从所好”“略以意行”“不用世法”,均是标举米芾脱略礼法、磊落不羁的人格独立精神,而这是士人主体人格的最本质体现,也是晚明士人的理想人格,以致于米芾的“癖好”与“颠行”成为这种理想人格的标签,为某些江南士人竞相佩戴于个人言行之表。范明泰书法学米芾,癖好踵米芾,姚士粦称其“殆亦南宫流亚也”[2]406。王穉登《米襄阳志林序》称:
范长康购奇石曰“舞蛟”,盖李唐时物,元赵魏公所题也。长康买宅临之,青萝赤薜蒙幕其上,朝而吐云,夕而含雾,神奇莫可测矣。长康日夕婆娑其下,与名流韵士、高僧道者执螯捉麈无间日,拊石叹曰:“我不能如米家具衣冠拜汝若丈人行,第相昵为尔汝交可已。”人以是目长康石癖与元章同,其他癖往往同。

表3 《米襄阳志林》十七卷校阅者籍贯简表
才品文艺又同。乃若布衣柴车,不惮追随,见大冠长裾则却走,将无颠又同?长康颔而不让曰:“颠我固当,张颠、米颠、我且鼎峙,幸甚!”于是搜集襄阳行事为《志林》若干卷,胪列分类,“癖”与“颠”各具其一焉。[2]406
范明泰对米芾“癖”与“颠”的刻意而机械的模仿,实际是在令人窒息的礼法社会高举起一面张扬个性、独立自主的旗帜。其《米襄阳志林自序》如此阐述编撰缘起:“襄阳含才,尽以其牢骚之气寄之颠,甘自标置,目三公以萧杌,不蹶挫于蔡持正、黄庆基诸辈,卒优游脉望,从金题玉躞间以老,似得长算居多。予故叙列其行事,作《襄阳志林》。”[2]402范明泰认为,米芾的癫狂行径是其蔑视权贵、背弃纲常的正常表现,而醉心书画、迷恋奇石则是其于险恶官场中存身自保的手段。戚伯坚《题辞》云:“弇州先生作《苏长公外纪》,人谓其风流文采千载符合,当是长公后身。长康有奇癖,绝同海岳嗜好……非其精神嘿券,何以至此!长康亦岂海岳之后身耶?暇日举此言质其叔氏君和,君和颔之,曰:‘子言别具一理。’”[2]405曹仲麟题辞亦称,范明泰“《志林》成,余读之卒业,诧曰:‘有是哉!长康之僻与米老同,岂其后身耶?’”[2]407这种“长康为海岳后身”之论,无疑是相当浅薄的。晚明官场险恶甚于北宋末年,范明泰出身秀水范氏,祖上历代以科举出仕立身,而范明泰在取得举人功名后却再无仕进之意,沉迷书画,耽于奇石,俨然以实际行动践行米芾的处世哲学。范氏编撰《米芾志林》既是为偶像立传,更是为自己的人格张目。当然,苏米的处世哲学、人格境界在晚明江南士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张献翼也以“颠”名自负:“余所效南宫一斑,浪得‘颠’名。”[2]404徐日观《苏米谭史广》小序云:“苏之达,米之逸,作世法观,均余药也。”[4]4徐造的小序称赞郭化纂《谭史广》:“见嬉笑怒骂皆丈夫烈也。”[4]5魏浣初《苏米志林序》称编者毛晋“素敦尚友之好”[5]511,均证明了这一点。
江南士人还将米芾崇拜现象溯之于魏晋以来的士风传统,推举“风流”胜过“道学”的价值取向。范明泰《米襄阳志林序》说:“自江左风流蕴崇后七百余年,濂洛数公递起……独米襄阳出入世法,以颠自号,同盟苏眉山最擅人伦鉴,乃至推重襄阳不去口,岂江左未绝之线耶?”[2]404他认为,北宋濂洛诸公的道学是浊流,米襄阳的率性任意是江左风流的未绝之线,是士人中的清流。王道焜特别强调,阅读蔡、苏、黄、米外纪,“然后知濂洛之际,别有此一种奇宕不平之气在。四家比晋轶唐而畴,谓士生于宋,尽汩没理障乎哉?是集成,喜为拈出。”[6]79徐暾《苏米谭史广序》称此书:“联牍皆云,片言等煜也。人劣今异古,江左清言莫不口之,漂说于今且宛舌矣。兹之《史广》箴世夫。”[4]5他认为,苏、米之谭就是新版的江左清谈。吴从先说:“不知有晋,安知有宋?若知有宋,则苏、米二老,举足风流,政不必求之晋人。而一言一字,可歌可泣,能作是观者,肩吾其人。收其谭而归之史,史之者,其有编辑之思乎!盖求道学于风流,复以风流还道学,肩吾晋人耶?宋人耶?”[4]2苏、米二老举足风流,将二老之谭归之史,以供今人借镜,因为“风流”的境界远高于“道学”。闵于忱甚至设想,若刘孝标复生,定会将苏、米隽语韵事补入《世说新语》:“东坡、南宫两称伯仲,故苏趣米颠,古今文人骚士往往步之。其单辞片语便足千秋,而诙谐谑浪不减江左清谈。孝标而在,必补入《世说》。”[7]江南本是魏晋风流的埋骨之地,江南文化基因中深藏着魏晋名士疏狂蔑俗的风骨,离经叛道、放浪形骸是其表现形式。有意味的是,宋元时期几位米芾轶事的辑录者也都是江南士人,《钱氏私志》的撰者钱愐为临安(今杭州)人,《句曲外史集》撰者张雨为钱塘(今杭州)人,《砚北杂志》著者陆友为苏州人。狂士精神的延续脉络在江南士林中是清晰可见的。明中叶的祝枝山、唐寅乃至后来的徐渭都堪称江南狂士的代表。“癖”与“颠”在晚明士人口中是真情至性的代名词。华淑《癖颠小史自序》云:“嗟乎!癖有至性,不受人损;癖有真色,不被世法。颠其古之狂欤?癖其古之狷欤?不狂不狷,吾谁与归?吾宁癖颠也欤!”[7]汤宾尹《癖颠小史小引》也说:“凡人有所偏好,斯谓之癖。癖之象若痴若狂,手口耳目不可以自喻,恩不能喜、雠不能怒者也,士患无癖耳。诚有癖,则神有所特寄,世外一切可艳之物犹之未开其钥,何自入哉?”[7]袁宏道甚至说:“余观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皆无癖之人。”[7]张献翼在当时以放诞无礼名满吴中,袁宏道却在信中嫌他不够颠狂,戏称“若实颠狂,将北面而事之”。在同一封信中,袁宏道却对米芾推崇备至:“夫‘颠’‘狂’二字,岂可轻易奉承人者?……颠在古人中,亦不易得。……求之儒,有米颠焉。”[8]58陈继儒也在《米襄阳志林》序中盛赞米芾之颠“不俗”“不寒”“不秽”“不落近代”“不屈挫”“不诈”[2]400-401,称颂其“颠”大有浩然之气。晚明士人与米芾、与魏晋名士于追求主体人格一途可谓异代知音。
尚友千古,立言不朽。借辑存米芾轶事以立言传世、彰显人生价值也是其编纂动因之一。《周易·大畜》云:“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9]40《孟子·万章》有“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并推而广之的论世尚友之论[10]324。《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答范宣子问中有“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1]140-141之语,此即后世儒士在兹念兹的“三不朽”说。晚明米芾轶事的辑撰者也深受这种儒学人生观的影响。《米襄阳志林》后附《米襄阳遗集》一卷,系范明泰搜辑而成,是集后附识语云:“元章《宝晋集》有称百卷者、十四卷者、十卷者,岂在当时固已散佚耶?近历采之藏书家,亦并鲜其集。今略以传记所见,纠之成帙,后当随益随补,备一家言云。子伋子范明泰元吉氏识。”[2]524米云卿《米襄阳志林序》称:“今元章已证仙品,其不可磨灭者籍籍人间,至吾友长康始裒理成帙。长康尚友千古,而所造已足不朽。”[2]406沈寿昆的《序》亦称:“余窃谓,肩吾欲藉苏米不朽,苏米还藉肩吾以不朽也。且肩吾之豪不异两仙,其遇岂两仙异耶?余更执此为左券矣。”[4]4因此,为米芾作传亦是为自己作传。陆鸣和《米襄阳志林序》称,范明泰“每谓丈夫七尺,宁能以寂寂老,陶古范今勒成一家,以副金匮,吾党事耳”[2]407。毛晋《苏子瞻志林》后识语认为,尽管历代编刊的苏轼诗文集乃至小品、禅喜文字不啻千百亿本,似乎不必再刻了,但“小碎尚有脱遗,余己未春闭关昆湖之曲,凡遇本集所不载者,辄书卷尾,得若干则,既简题跋,又得若干则。聊存嗜痂,见者勿讶为辽东白豕云”[5]573。其《米元章志林》后附识语又云:“余觅《宝晋斋集》十余年矣,惜乎不传,凡从稗官野史或法书名画间见海岳遗事遗文,辄书寸楮,效白香山,投一瓷瓶中,未可云全鼎一脔肉也。辛酉秋,偶编《东坡竹纪》,友人索余,合元章梓行,因简向来拾得者,录成一册,略无诠次,至其《净名斋》《西园》诸名篇,久已脍炙人口,不敢复载云。湖南毛晋识。”[5]605毛晋不辞艰辛、孜孜搜求米芾文献之自述,范明泰“备一家言”之自期,郭化以“史”命其书且“欲借苏米不朽”,均是对这份搜辑事业不朽价值的自觉体认。可见搜辑米芾轶事,刊布于世,并非一人一时之冲动,而是藉此以立言不朽的主体意识的体现。
而且,借用搜辑米芾轶事的方式以寄托情志,具有其他传统撰述方式所不具备的优势。陆鸣和《米襄阳志林》题辞说:“长康酷有宝晋之嗜,故作《志林》,历年所而成,使米氏神情气韵千百年后一披展间,如再起其人而昕睇夕聆之,此无论传记有所难备,即年谱、日录亦逊遐稽……盖不但为米氏策勋,而湔浣一切俗汉,其惠远矣。”[2]407戚伯坚《米襄阳志林题辞》谓,该书可使“米老四十五年佳谈胜事,历历可睹”[2]406,姚士粦《题辞》亦称:“兹编使人人毕见南宫之为快乎!长康其真能画南宫于千载者也。”[2]406梅士俶《苏米谭史广》小序说:“《广》若《谭》,而苏米之豪宛在睫矣,肩吾不步苏米之尘、印苏米之神者乎?”[4]5所谓“米氏神清气韵”“历历可睹”“画南宫于千载”云云,均揭示米芾轶事的传播效果可使其人千百年后宛在眉睫,栩栩如生,而这是文集、传记、年谱、日录等枯燥文字难以企及的。魏浣初认为,毛晋辑《苏米志林》三卷使“读之者恍遇苏得意时漫裂短幅,乞得其枯木竹石之供,而米家片石所谓嵌空玲珑可爱者,不必袖中夺取,具列纸上矣。且并两公同堂相对,一则长髯伟身,挥洒谈笑,一则摩挲翰墨狂走叫绝之生气,俨然并作《苏米图》。快哉!诚韵事也”[5]511-512。对《苏米志林》接受效果的描述绘声绘色,并以画《苏米图》相比拟。王道焜《叙四家外纪》说:“兹四家之集,折轴充栋,弇州且谓:‘公等之奇,不尽于集。’乃别汇小言逸事,年谱传志,与诸家之评骘,纪述琐屑为外纪,拟诸义庆《新语》,点缀王谢诸人,一一呵活眼前也。”[6]79这类著作的特点是:“其旨浅,其情深,其语少,其致多,不必概公等立朝大节,侃侃风裁,而即此跌宕文史,品题翰墨,旷代风流,于焉是在。”[6]79为历史人物作传,不必特书其“立朝大节”,“小言逸事”自可表现其“旷代风流”。王道焜概括此类轶事体传记的优势颇为精当。
米芾轶事的整理还迎合了晚明文士的娱乐需求。追求娱乐是人类自然本性的重要内涵,而礼教的极端发展则试图禁绝人类的娱乐欲望,因而追求娱乐也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对礼教的背叛,对人的个性的张扬。陈继儒《米襄阳志林序》赞米芾具有游戏殿廷的凌云豪气:“滑稽谈笑,游戏殿廷,东方朔、李白得其豪。”[2]400郭化《苏米谭史》自序云:“拈得苏、米二老隽冷可绎之语,与夫褒刺可讪之谭,裒集成帙,佐茶水,消永日耳。”[7]郭化本人性喜调笑,里人梅敦伦《苏米谭史序》称:“座中无肩吾,一座不欢。得肩吾之兹集也,世机尽解。”[7]汪襄贤《苏米谭史广》小序说:“天地古今一史局也,亦一谭资也。举世不以庄语语,则谈言微中,可以内外无障矣。用史巫纷若,何暇清谭哉!昔苏、米二学士,文章丰骨棱缝,更无未尽。其摄身应世,往往得之虚实实虚、动静静动之间,故其留诅盟而发机括者,每能当世波而巧电转,使当之者获愧而不能恚,或激而不能挠。”[4]1-2吴台引赞叹苏、米二人:“议论磅礴,谈笑风生,开千古未开之眼,披千古未披之襟,二老差堪伯仲。余往时欲撷拾一帙,佐友人谭麈,而肩吾先得我心。”[4]3晚明士人崇尚苏米“调笑风流”,至于称其为“仙”。沈寿昆《苏米谭史广序》说:“苏、米才情丰骨,栩栩乎仙也。他不具论,即声咳间禅那玄理,调谑风流,令人领取,神思跃然。”[4]4徐日昌的序又云:“或问肩吾:‘苏长公、米南宫之谭何如?’曰:‘苏也仙,米也颠。仙也无烟火气,颠也无人间世。咳唾谭笑,俱可千古,千古而下,因以不刊典传之。片语只字,掷地有金石声,搜剔可不尽乎?’”[4]3晚明江南清谈之风盛行,文人雅集不谈政事,不论诗文,而醉心于书画古玩、花鸟香茶等韵事,言谈间往往征引大量文史故实以炫其博,玩弄文字游戏以逞其机巧,米芾轶事的搜辑即是这种风气的一种体现。
四、米芾轶事小说的叙事特色
米芾轶事小说的情节面貌尽管各呈异彩,但宗旨只有一个,就是展现颖异多姿的米芾个性,塑造丰满的米芾艺术形象,而这正是叙事文学的本职功能。
首先,米芾轶事集的选材重心与编排体例突显强烈的叙事旨趣。范明泰《米襄阳志林》共分十三门,每门各一卷,但只有“书学”“画学”“书评”“画评”四门四卷有关米芾书画创作及理论,其余九门九卷皆为轶事杂记类文字。其将“世系”“恩遇”冠于卷首,仅表示对君父伦理的尊敬,次以“颠绝”“洁癖”“嗜好”“麈谈”四门突出米芾的独特个性,以下才是“书学”“画学”等书画学内容。在纂者看来,米芾的逸闻趣事、个性魅力比他的书画成就更为重要,也更能吸引读者。毛晋《米襄阳志林》不分门类,但每一条故事都精拟标题,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且便于检索。他将《奇绝陛下》《上天梯》《俊人掷笔大言》等张扬米芾颠狂个性的篇目编排于前,而将《石刻不可学》《十纸说》《印不可伪》《样品》等体现米芾书画造诣与艺术主张的篇目排列于后,足见其旨趣所在。郭化《米南宫谭史广》并非专采米芾谈论及调笑文字,而是致力于搜集米芾轶事。此书不分门目,亦不撮条目标题,但它将米芾轶事与其书画理论分开编排,主体部分专辑米芾逸事,而附录《海岳名言》《李伯时雅集图序》方展示其书画造诣。尽管各家米芾小说集体例面貌各异,但其叙事旨趣则是一致的。
其次,米芾轶事集的虚构特征显著,多属小说家言。许多故事焕发传奇色彩,且不乏荒诞的灵怪成分。如屡屡叙述米芾戏耍天子、冒犯龙颜,皇上总会以“俊人不拘礼法”开脱其罪,米芾每每能从皇帝那里讨到便宜,舞蹈而退。这类故事虽可表现圣恩隆渥,但显然违背最基本的纲常伦理。再如广为流传的米芾择婿故事:“芾方择婿,会建康段拂,字去尘,芾择之,曰:‘既拂矣,又去尘,真婿也。’以女妻之。”[4]59米芾竟以文字游戏为女儿订下终身,奇则奇矣,但有悖人之常情,只能出于好事者的附会。有的故事则近于志怪小说,如《蟒精》:
元章知无为军,每雨旸致祷,则设宴席于城隍祠,东向坐神像侧,举酒献酬,往往获应。得新茶果,辄以馈神,令典客声喏传言以致之。间有得缗钱于香案侧,若神劳之者。尝晨兴,呼谯门鼓吏曰:“夜来三更不闻鼓声。”吏言:“有巨白蛇缠绕其鼓,故不敢近。”米颔之,叱吏去,不复问。故郡人皆疑其蟒精,至今传之。又凿墨池,尝治事池上,蛙声聒人。因取瓦,书“押”字,投之池。由是蛙不鸣。[5]581
这个故事直把米芾构造为精怪的化身。而另一篇《留马渡采石矶》则侈谈人与神相通互应,更是传统志怪小说的烂熟套路。这类作品的性质不言而喻,无怪乎四库馆臣斥其“皆摭拾小说”[3]543。
米芾轶事的许多篇目叙事讲究章法,情节富有张力。其情节的设计颇具匠心,擅长层层铺垫,至高潮处却陡然转折,结局出人意料,在读者心中造成断崖式坠落般的撞击,如《弄石》:
元章守涟水,地接灵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目,入玩则终日不出。杨次公为察使,因往廉焉。正色曰:“朝廷以千里郡邑付公,那得终日弄石,都不省录郡事?”米径往前,于左袖中取一石,嵌空玲珑,峰峦洞穴皆具,色极清润,宛转翻覆,以示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殊不顾,乃纳之袖。又出一石,叠嶂层峦,奇巧又胜,又纳之袖。最后出一石,尽天划神镂之妙。顾杨曰:“如此石,安得不爱!”杨忽曰:“非独公爱,我亦爱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径登车去。[2]422
该故事叙述元章出守涟水,却沉迷于奇石而不视政事,惊动上司杨次公前往纠察问责,元章采用乌贼战术,欲将上司也拉下水,我黑你也黑,你也就不能再说我黑了。他前两次用奇石诱惑上司,上司均不为所动,元章只好纳之于袖。看似元章必败无疑了,但这只是铺垫之笔,以吊起读者的胃口。元章第三次出示极妙之石,上司这次终于中招,叹道:“非独公爱,我亦爱矣”,并夺奇石而去。结局来了个大逆转,元章转败为胜,制造了强烈的喜剧效果。再如,众多米芾夺宝故事中,基本都是叙米芾靠耍赖、欺诈乃至盗抢的方式夺得他人宝物,但《追想笔法》一篇的叙事者却逆向操作,写米芾欲得到关蔚宗珍藏的虞世南《枕卧帖》,不过这次他遇上了难缠的对手,关蔚宗之子长源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使米芾不仅未得《枕卧帖》,还连失两宝。第三次长源竟提出拿米芾的头交换《枕卧帖》。情节至此,悬念已足。不过,结局却柳暗花明,米芾因曾见过《枕卧帖》,仅凭记忆竟然临摹出此帖,足可乱真。本故事用先抑后扬、诡谲莫测的方式,凸显了米芾的卓越才华,与顺向叙事的效果殊途同归。
米芾轶事中一个主要题材类型是戏谑与调笑,洋溢着浓郁的娱乐趣味,有些故事属于以文滑稽,纯为制造诙谐之趣,如《捕蝗》:
米元章令雍丘,蝗大起,邻县尉司禁瘗,后仍滋蔓,责保正并力捕除。或言:“尽缘雍丘驱逐过此。”尉移文,载保正语牒行雍丘,请勿以邻国为壑。时元章方与客饮,视牒大笑,题纸尾答云:“蝗虫原是飞空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传者莫不大噱。[5]579
无论是雅趣抑或是谐趣,都是追求娱乐效果,而娱乐性正是叙事文学的一种突出特性。
毋庸讳言,这些著作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首先,诸书之间内容重复严重。其次,故意把米芾塑造成一个半神半人、近乎神话中的人物。如有学者指出:“晚明在董其昌‘开口米元章,闭口米元章’的影响下,米芾已成为一位神化了的书法家、鉴赏家和画家。”[12]当然这肇因于官史及稗史系统米芾事迹均有“民间化叙述的一面”[13]。再次,这些著作所辑故事大多不注出处,以致于严肃的书画艺术论著很少征引其文字,难怪《四库总目》斥其“多不注出典,未足依据”[3]542。这也是此类著作传播不广、影响不彰的重要原因。尽管存在以上缺陷,但对有些作品来说,学术层面的不足并不意味着其文学价值的缺失,有时还恰恰相反。因此,晚明米芾轶事小说集的文学价值还有较大的探究空间。
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徐黛君同学曾提供资料,特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