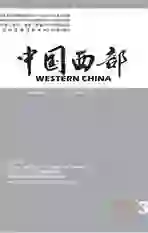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刑法规制
2020-08-11敬力嘉
敬力嘉
[摘要]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具备重大法益侵害风险,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需从严规制。文章认为应在厘清“虚假信息”边界,确保政府部门及时、准确发布疫情信息的基础上,促进网络监管部门与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治轨道内充分发挥技术治理机制作用,支持司法机关依法从严适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实现对此类犯罪行为的精准打击,以保障疫情防控工作在法治轨道内顺利推进。
[关键词]虚假疫情信息;技术治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依法从严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0)03-0106-06
[作者]敬力嘉 讲师 武汉大学法学院 武汉 430072
一、问题提出
在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逐步向好,但仍面临促进国内逐步复工复产与防止境外输入病例骤增容易催生疫情风险的当下,在深刻嵌人社会组织结构的互联网语境下,网络空间内虚假疫情信息的编造与故意传播是重要的危害性活动,可能给疫情的有效防控带来较大障碍,引发社会化的法益侵害风险。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刑法具备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本文拟以虚假疫情信息的依法从严治理为视角,围绕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技术治理机制及其限度,以及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依法从严适用两个方面展开探讨,以期为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刑法规制提供法律适用参考。
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技术治理及其法治限度
1.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技术治理
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治理是一项需要多方主体参与、综合、体系化的系统工程。美国著名网络法学家劳伦斯·莱斯格就认为网络空间是被现实世界的市場规则、社群规范、技术架构以及法律规范所规制。互联网控制的焦点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空间的市场规则、社群规范、技术架构以及法律规范都围绕它形成与运行。在以TCP/IP协议为基础的互联网现有中立技术架构下,法律规范难以直接有效规制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但在政府疫情防控的公共政策与商业利益的驱动下,网络服务提供者正在推动网络空间架构向更有利于规制的方向转变。按照功能标准,互联网可以大致分为网络链接层、网络互联层、传输层与应用层,从传统的IP地址追踪、cookies、SSO身份验证、标识层技术直至当前愈加发达的生物信息识别技术,互联网基础架构的中立性允许通过改写其任意一层代码,加强网络空间的身份验证与行为追踪机制。随着国家陆续颁布相关具体规定,网络空间身份验证与行为追踪机制的构建与完善逐步有了规范依据。网络空间架构的这一转变,使网络监管部门以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特别是网络媒体平台、社交服务平台等,以《网络安全法》《刑法修正案(九)》等为参与网络活动的一般企业与公民创设的法定义务为依据,②事实上也具备了强大的规制权力,比如微信可以对用户封号、删帖,微博可以禁言,视频网站违规违法的音视频内容可以被网站下架,它们应当承担起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治理责任。
2.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技术治理的法治限度
虽然技术治理是规制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的利器,但除了应当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加强政府部门与相关企业间以及行业内部的协同合作,最大限度控制虚假疫情信息在公共网络空间的传播以外,还应当对网络监管部门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治理进行规范,明确其法治限度,力求取得公民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信息流动自由保障与虚假疫情信息防控之间的平衡。
为了实现以上目标,应当明确什么是“虚假”疫情信息。在刑法学界,虚假信息通常与谣言在同一意义上被使用,其核心特征为未经证实,“是‘没有根据的信息,而非‘与事实不符的信息”但是,未经证实的信息未必是虚假信息,未经有关部门证实的信息更是如此。④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来看,从疫情初露端倪到快速发展以致全面暴发,医学专家、政府与公众的认知都有一个渐进深化的过程,这也是研究与认识新型病毒的科学规律。在未对SARS-CoV-2病毒形成科学认知之前,及时向政府决策机构与社会公众预警,对于防控重大疫情具有重要意义。2019年12月,李文亮等8位医生因发布了警告疫情的信息,②被武汉警方以制造传播谣言予以训诫,引发了巨大争议。原因就在于,事后证明SARS-CoV-2病毒与SARS病毒基因序列的相似度较高,传染性比SARS病毒更强,且有正规三甲医院的病毒检测报告为依据,将其认定为虚假信息确实有待商榷,也难以认定“编造”行为。对于此类信息的传播,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监管部门应当在法律准则内抱以宽容。⑧
三、严格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标准
当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符合我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第2款规定的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标准,④应依法从严适用本罪,以精准打击此类行为,为疫情防控提供有效的法治保障。
1.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适用前提
对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行为,可适用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与寻衅滋事罪进行规制。鉴于前者明确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构成要件行为以及虚假信息类型,对于此类行为进行规制的基础罪名应为前者。对于编造、故意传播的包括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等四类虚假信息内容应作严格文意解释,编造、故意传播这四类以外的虚假信息不能构成本罪。尽管如此,司法实践中仍较为普遍地适用寻衅滋事罪规制编造、故意传播这四类以外虚假信息的行为。⑥
本罪所规制的虚假信息应是虚假的事实陈述,不应当包括行为人的主观评价和判断。但只作此限定还不够,司法实践中往往认为通过网络实施此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证自明,进而将制造、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人罪,这样的认识无疑是将已被我国刑法单独入罪、在网络空间制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造成法益侵害的行为,再次作为量刑情节进行了重复评价。明确本罪的适用标准,最重要的是应当明确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并以此为基础,厘定本罪中的“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造成严重后果”。有观点认为,《刑法修正案(九)》生效后,利用信息网络或其它媒体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原则上应不再处以寻衅滋事罪,④因为这类行为侵犯的是独立的网络空间管理秩序。但本罪与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法益均为现实的社会公共秩序,网络只作为工具存在。基于这样的认知,本文认为只能以造成现实公共场所秩序的混乱为本罪成立的构成要件结果。
2.“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与“造成严重后果”的认定
需要明确的是,作为认定本罪构成要件结果的前提,对作为本罪保护法益的现实公共秩序的侵害,⑧是以侵害其相关的个体法益为前提。学界有人在认可存在独立网络空间秩序的前提下,认为本罪应当参照放火罪等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模式,认定本罪的基本犯为抽象危险犯,只要实行编造、故意传播法定类型虚假信息的行为,即推定具备抽象危险,允许被告人进行反证,“造成严重后果”的才是实害犯。基于对其理论前提的否定,本文不赞同这一解释路径。本文认为,既然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需要认定造成了对现实公共场所秩序的实害,“造成严重后果”属于对结果加重犯的规定,作为与其并行的罪名,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人罪标准也不能低于以上要求。
以最高检发布的第二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之四——辽宁省鞍山市赵某某涉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案,本文对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与“造成严重后果”的判断,④认为在该案中,我们可以认定赵某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但是否就已经达到了“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仅凭大量市民向相关部门打电话核实该信息真实性,将其行为认定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仍不免显得有些牵强。事实上,在一般情况下,对于该信息对疫情防控工作造成的负面影响,通过相关技术手段的合理运用与政府部门及时有效的澄清即可消除。
四、结语
在疫情防控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更应注意言论发表。我国宪法第51条也对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①具体划分自由与权利界限的是部门法。鉴于有关事件信息的模糊度与虚假信息的滋生、传播一般成正比关系,政府在疫情防控中及时回应社会公众的关切,及时、准确发布相关疫情信息,对于虚假疫情信息的有效治理也是非常必要和关键的。
只有政府部门及时、准确、全面地发布疫情信息,而非适用行政权力加持的技术手段,对未经政府部门证实的疫情信息一律予以封锁,才能真正提高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的技术治理效能。
同时,我们也只有厘清技术与刑法机制的功能限度,确保依法治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疫情信息,才能实现对此类行为的精准从严打击,切实保障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