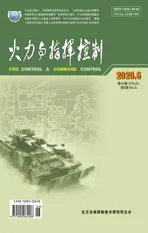基于功能和效应的作战能力指标体系设计*
2020-08-10刘兆鹏曹占广
刘兆鹏,罗 睿,王 强,曹占广
(1.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北京 100091;2.国防大学联合作战学院,北京 100091)
0 引言
对作战能力定量分析的研究大致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从综合作战能力体系构成的角度研究指标体系的设计和聚合问题[1-7];一类是聚焦在某一指数计算和应用方面[8-14]。对指标体系的研究大多是建立在作战能力结构与功能分解的基础上;对指数的研究或者是建立在杀伤效应基础上,或者是一种聚合计算框架下的抽象定量指标。本文通过建立功能域和效应域的多维度指标体系,力图将现有指标体系的研究和指数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并探讨了构建侵彻穿甲、时空控制两类新效应指数的构想和技术途径。
1 相关研究综述
从部队综合作战能力的构成要素角度进行作战能力分析和指标的设计是一种通行的研究思路[1]。首先涉及作战能力的分层次分析问题,文献[15]称之为结构分解,文献[3,5,7]等将之区分为单元级(或称装备单元)、系统级(或称作战单元,能够遂行一定作战任务的最小作战运用单位,通常由载具和武器装备单元联结而成)、体系级(或称作战编成、装备体系)。文献[16]将航空武器的能力指标层次分为性能、模式、任务、系统指数4 个层次,其中模式指单件武器,任务分别对应对空、对地、对海作战,系统指整体作战能力;其次是如何分解能力要素问题,也就是功能分解[15],多数都从形成打击能力任务链[1,4-5,7,11-13]的角度来进行功能分解,如文献[1]将部队综合作战能力分为4 种:火力打击能力、机动能力、C4I-EW 能力,保障能力,文献[5,11-13]等将武器装备作战能力的基本构成要素概括为“五力”即武器装备打击力、防护力、机动力、信息力与保障力,其中打击力指主动攻击目标的能力,防护力指抵御杀伤与破坏的能力,机动力指位移机动的能力,信息力指获取处理利用信息的能力,保障力指保持自身或其他武器持续作战的能力[5],文献[4]在五力的基础上提出感知、指控、作战、互操作、行动、保障6 种基本功能,文献[7]将信息力分解为信息感知能力和指挥控制能力,形成6种能力。能力构成要素也有一些其他的分析方法,如文献[17]以信息流过程作为武器装备体系效能发挥与建模的基本框架,根据信息流将武器装备系统分为传感类装备、指挥控制通信类装备、行动类武器装备,提出相应的评价指标。文献[18]从战场监视、指挥、交战、综合保障,文献[19]从武器子系统、电子信息子系统、决策指挥子系统、后勤保障子系统4 个方面建立数字化部队的指标体系等,都是很有意义的尝试。此外,还有大量的针对单一军种或系统的研究,一般从自身作战任务[16]或作战任务链[20-22]的角度出发。要注意的是,从综合作战能构成要素方面进行作战能力的分析研究,仍然还是一个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一些综合性的分析报告也必须加以重视。
指数法是评估军队武器装备综合能力的常用方法[1,10,23-24],研究方法大致有基于历史战例数据统计、基于定性经验知识判断、基于启发式的经验公式、基于定性定量解析方法[8],主要的成果有T.N.Dupuy 的理论与实际杀伤力指数(Lethality Index);武器能力指数(Weapon Power Score,WPS)和广义武器能力指数[1,9,23],以及国内学者提出的幂指数[8-9]、联合指数[11-13]和对数模型[25]等等。杜派指数建立了指数与武器射速、射远、单次攻击目标数等武器性能参数的经验数学模型,实际上是武器在理想条件下运用效果的体现。武器能力指数考虑了武器本身的生存、机动能力,广义武器能力指数进一步考虑了战场环境和战斗激烈程度的影响[23],都可视为杜派指数的扩展。还有部分指数如火力指数、邓尼根分级指数等经验性质更为显著。对数模型、幂指数、联合指数更接近于一种抽象能力指数的聚合框架。幂指数充分利用了幂函数性质,提供了一种严密的多影响因素聚合方法,但需要以AHP 方法确定各种因素的作用影响因子[8];联合指数提出各分要素指数以及不同要素指数聚合形成单一的综合指标的方法。此外,还有相当部分的研究成果重点是指数的聚合[2,7],指数法同样存在大量针对特定军种或特定系统的应用研究[27-28]。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指数的主要局限是信息量太少,物理或战术意义较模糊,不能反映编制体制差异、大都没有涉及工程、技术、后勤等方面的保障因素[1,8,10]。
2 指标体系构成分析
能力指标体系是度量军事系统执行军事斗争任务从顶层(如战区战役)直到底层各层次达到各类任务目标的能力的一系列指标[23]。设计能力指标的要求可以归纳为4 个方面[1,5,23],一是全面性,能够反应各方面能力及组织因素的影响。二是独立性,即指标间没有重叠交叉,同一层次能力指标间有明显区分性。三是可比性,即指标能够使不同武器系统相对可以比较。四是技术性,主要是需要低层次指标应具有明确的物理意义,最低层次的指标必须能反映某类武器装备的主要战术技术性能,高层次的指标值必须由其下一层次的各项指标值按照某种方法综合而成,每一层次能力指标具有与该层次任务目标对应的聚合程度,顶层能力指标聚合度最高。
现有能力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对作战能力的体系层次划分基本形成共识——即分为单元- 系统-体系三级,都将装备单元的性能参数作为基础或输入层[3,7,13,16]。在单元和系统级,作战能力主要取决于武器装备自身因素和典型任务环境;体系级的影响因素则包括编配数量、人员、指挥保障、训练等。由于评估作战能力时,通常都是从部队编制的武器装备入手[1],因此,很多研究直接针对武器装备体系进行。针对装备编配及运用方式固定的装备体系作战能力研究,相当于系统级的分析;针对考虑编配变化、使用模式、训练保障影响的武器装备体系研究,无论面向的是作战武器装备体系,还是国家武器装备体系[29],都与部队作战能力研究本质相同。
在具体指标选择上,能力可以基于任务划分或基于效果划分[23,30]。基于任务划分的能力指标,是与任务相适应的装备自身的本领[30],相对直接,类似MOP,指标设计以体系功能的层次分解为依据[18];而基于效果划分的指标,是产生结果的潜能,与MOE、使用性能[30]或固有性能[2]类似,相对隐含,文献[8]称之为作战能力函数,是标准条件下能力运用的结果。这类指标易与作战效能混淆,国内学者[2,23-24,30]大都认为作战效能主要与实际运用有关,是达到预期目标的有效程度,文献[23,30]更进一步将效能看作一种比率,在这种情况下,效能含义与measure of efficiency[31]更接近。因此,为与之区别,本文将基于效果、但面向能力度量的指标称之为效应域指标。显然,愈倾向于宏观层次,实际运用的影响越显著,作战效能与效应指标的区分越明显,而在装备和系统层次,可以认为基本等同,国外术语MOE 应视为二者的综合。
在指标的聚合方法方面,多数研究对不同层次的指标和聚合方法较少区分。能力体系的层次划分与多分辨率分析相关,基于一般性观点,局域小尺度效应和宏观大尺度问题,必须以不同方法分别处理,同一方法难以解决多尺度问题[32]。因此,高层次指标难以由低层次指标简单综合而成,具有相似结构的多层次指标体系是很难满足不同层次作战能力描述需要,应该在不同层次选用不同的指标,并设计针对性的聚合方法。
基于上述观点,作战能力的指标体系设计为如图1 所示。

图1 功能域和效应域的能力指标体系框架
其中,功能是产品提供的某种行为能力,性能作为产品实现其功能的程度和在使用期内功能的保持性度量,通常是区分比较不同产品的最直接而可靠的度量。从功能域进行能力比较的主要困难是功能实现存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这需要在建立指标过程中抓住主要的关注特性,聚焦共性指标,在单元级可直接采用性能参数,而在系统级也可使用性能参数或转化为分类的无量纲指数形式,在体系级应主要以无量纲的综合性指数为主。在指标聚合方法方面,在系统级可以用确定性的串并模型,而在体系级,则应该使用适当的统计模型、基于合理的统计分布进行聚合。在体系级的最高层次,使用描述性的净评估[23]、定性评价分析为主,并且是以专门非结构化分析报告形式存在。
效应是某种动因或原因所产生的结果。效应域能力指标反映的是产生期望结果的潜力,是标准运用条件下的效能,是功为用的结果,并且具有简单系统的功用关系明晰,复杂系统则要间接、隐含得多的特征。以效应作为评价指标应考虑这样几个因素,一是有聚向性或综合性,即主要性能指标能够对其产生影响,也就是直接或间接关联,例如杀伤效应,火力的射远和精度、雷达探测的远近、定位准确度,弹药的持续供给都可以不同形式对杀伤力产生影响;二是有正相关性,效应指标的增强、减弱代表整体能力的演进方向,不同的效用指标可以相互关联,但其关系应是正相关关系,即一个效用指标增强,其他的也都是增强,反之亦然。效用指标在低层次宜用单位时间或极值表示,而在高层次,则宜用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的累积指标表示。指标的聚合原则和方法与功能域类似。
3 功能域指标
功能域指标的确立取决于功能的分解方式,主要分解方式有3 种,如图2 所示。

图2 功能域的典型分解方式
其一是军兵种维度,联合作战经历了单军种向多军兵种作战分化的历史阶段,尽管现在从运用上又转向一体化,但包括美军在内,还处于军种分建、联合运用阶段,因此,按军种进行功能的分解也是比较常见的方式。对于我军可以区分为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陆军又可区分为炮兵、装甲、工程、防化、机步、陆航、特战等兵种,海军可分为水面舰艇、潜艇、海军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岸导等兵种,空军主要是航空兵、防空兵、雷达兵、空降兵等,火箭军分为常规导弹和核导弹部队等,战略支援分为航天和网络等。
其二是空间维度,按空间维度又有两种角度,一是组织维度,其实是“在陆、在海、在空、在天、在网电空间”的作战能力,与军种划分接近,因为军种划分本就是根源于不同维度作战特殊要求而来的;二就是作用维度,还是陆、海、空、天、电磁网络,实际意义是“对陆、对海、对空、对天、对网络电磁空间”的作战能力。有些亚空间具有特殊性,如在组织运用维度上必须考虑水下和临近空间,而在对象空间维度上还需要加上地下,但可以将临近空间对接为“天”。此外,人们经常讨论的问题是是否将中远程导弹部队作为跨域使用的兵种,类似问题注意把握主要的组织维度空间进行划分就够了。
其三是任务链维度,鉴于形成打击能力的过程因素包括发现、决策、机动、防护、打击、保障等环节,从不可分割的任务链角度[34]进行功能分解也是适宜的。因此,依据在任务链中的不同作用,将作战能力划分为侦察预警、指挥控制、火力打击、机动投送、综合防护、综合保障6 个方面[7]是常见做法。考虑到指挥控制主要是与人相关,而实际上,在对复杂体系进行能力分析时,人的因素是在所有环节都考虑的,单独考核指挥控制的必要性有所不足。因此,将侦察预警和指挥控制归结为更为综合的信息力应更为合理一些,文献[11-12]提出的信息力、打击力、机动力、防护力、保障力划分方式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认可。实际上,应该结合不同维度来进行功能域的分解,这样可以形成军种-空间-任务、空间-军种-任务、任务-军种-空间等不同的分解层次关系。由于早期军种和空间维度有直接的对应关系,随技术的发展,军种在空间域方面界线渐趋模糊,因此,主要由任务和空间维结合,形成任务-空间、空间-任务的分解层次关系就足够了。
4 效应域指标
战争作为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其目的必然并且始终是打垮敌人,使敌人无力抵抗[34]。打垮敌人,包括打垮敌人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精神力量的损伤很难量化评估,因此,现阶段作战能力的效应应该体现到对敌人物质力量的损伤上来,包括杀伤力、侵彻破甲力、空间控制力。
4.1 杀伤效应
对人员的杀伤始终是传统作战理论关注的主要方面,基于人员杀伤力的指数研究比较成熟。1964 年,杜派(T.N.DUPUY,早期译为杜普伊)与同事为美国陆军战斗发展司令部开展了一项“武器杀伤力的历史发展趋势”研究,考察了从古代的剑到现代的导弹一系列武器的全部物理属性与能力,通过一个假设“在一个宽度和纵深充分大的阵列里,每平方米站1 个士兵,用各种武器分别攻击这个阵列,得出每小时内有多少士兵失去战斗力的数值”,然后把它们结合到一个经验公式中,得到“理论杀伤力指数”(Theoretical Lethality Index,简称TLI),其基本公式为[35]:

其中,RF 为射速,即每小时内该武器能够有效打击目标阵列的次数;PTS 为每次攻击的潜在目标数,等于一次攻击的有效作用面积乘以人员分布密度(1人/m2);RIE 为相对致死效应,即击中目标使目标致死的可能性,冷兵器小于1,热兵器一般直接设置为1,有些文献中省略了这一项;RN 为射程因子,这一因子反映武器对不同距离上的目标进行射击能力的大小,表明随着有效射程的增加,使用这种武器击中目标的数量也会增加。A 为精确度,指武器运作正常时命中特定目标的概率。RL 为可靠性,也经常忽略这个因素。
杜派将理论杀伤力指数乘以部队疏散因子,得到武器实际杀伤力指数(Operational Lethality Index,OLI),在杜派指数的基础上,还有很多扩展性的研究成果,都可以视为杀伤效应类的指标。杜派指数作为装备单元级的能力指标是适宜的,作为体系级的指标,显然无法体现指挥组织、训练保障的作用。杜派在其定量判定模型中[36],通过将地形、季节、天气、机动性、后勤和防御态势等战场可变因素变为权因子,从而计算作战潜力和判断战争结果,前者可以用于体系的能力评价。
4.2 侵彻/穿甲效应
侵彻效应是指弹体高速撞击并钻入靶体对弹体和靶体产生的破坏效应,若弹体穿透金属靶体,人们又习惯称为穿甲[37]。进入机械化战争时代后,装甲化的平台成为作战的基本依托,混凝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性基础原材料,在现代国防及民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着核心支撑作用,如机场跑道、大型水坝等[38],因此,在侵彻/ 穿甲效应基础上,研究能够综合体现对作战物质基础和战争潜力破坏能力的指标应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侵彻/穿甲效应主要来自弹头的动能撞击、聚能射流穿透和爆炸,由于军事应用的原因,穿甲/侵彻力学的发展成熟,得到广泛研究[39-42]。侵彻穿甲能力主要取决于弹头动能、形状、弹头材质、射角,以及对象材质,针对不同土质、岩石、混凝土有很多经验公式,影响较大的有美军陆军工程兵推出的ACE 公式,美国防护研究委员会推出的NDRC 公式、美国圣迪亚实验室SNL 公式、Bernard 公式、Forrestal 公式等[42-44],针对装甲的穿甲效用有Krupp 公式、Jacob de Marre 公式等[45]。聚能侵彻主要受药罩材质、形状的影响[38,42],而埋深是影响爆坑形成的决定性参数,在实际使用中,可以认为这取决于弹头的动能侵彻深度[46]。因此,在装备单元级可以使用形如式(2)的侵彻能力作为指标参数:

其中,m 为弹头质量,v 为入射速度,N 为形状因子,J为聚能增强系数,w 为装药当量,RF、RN 同杜派指数。在系统级,可以是其累积量或统计量。在体系级,要综合地体现对战争潜力的破坏,可参照文献[47]对舰船毁伤效果评估的做法,首先将典型武器、防护工事、经济目标进行装甲和混凝土目标等效化,然后获取侵彻/穿甲的破坏作用与相应吨位的比值,而战争潜力则表现为维修、生成相应等效吨位的能力,通过这种方式,有可能获取更好体现综合作战能力的指标参数,但显然,这需要一个广泛领域的研究基础作为支撑,需要指挥控制领域更深入地吸收爆炸力学、防护工程、武器设计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4.3 时空控制效应
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意味着战争的潜能,因此,保证在特定时间条件下对特定空间的控制力仍然是军事能力的基础效应,从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马克的海权论,杜黑的制空权论,到其他地缘政治及军事地理研究,以及现在的一体化联合作战理论研究[48]中,都突出反映了空间控制对军事的重要意义,文献[31,49]将战场空间控制和人员伤亡都作为信息化军队的MOE 指标。
时空控制能力类似动物对“领地”的控制,动物对领地的控制表现为对随机进入领地的竞争者作出反应的能力,这实际上是综合了它的攻击能力、发现能力、机动能力诸多因素的结果。时空的控制往往采用一段时间范围内的等效能力进行计算,在短时间内,主要取决于武器系统的射远、命中精度、机动能力,在较长时间或在特定的空间范围内,则能够综合体现指挥组织、投送等能力因素的影响。相对于传统的指数方法,这种方法能够在装备单元和系统级进行严格的解析分析,也易于实现单装(系统)能力向体系能力的聚合,平时的部署以威慑控制为主,时空控制分析在这方面很有优势[49]。
5 结论
作战能力指标的设计和选择应服务于多层次作战能力分析的需求,充分顾及高层次分析强调整体和综合,受组织、训练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低层次分析需要分解精化、更贴近系统固有能力的客观实际。随着未来指控系统向智能化方向发展,作战能力指标参数的采集、评估、演化必将成为智能化指挥控制信息系统的基础能力,迫切要求我们在能力指标体系的设计和构造上取得一致认识,扎实推进系统建设。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尽管杀伤力指标方面的研究已经有很长历史,但随作战思想和作战支撑物资条件的变化,应该在新的假设条件下对现有主要的武器系统进行重新评估。侵彻/穿甲效用在力学方面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但在能力分析、效能评估方面的应用研究还比较少,基于空间控制效应方面的能力指标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尚需持续不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