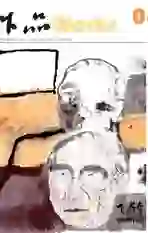超越现实之上的想象世界(访谈)
2020-08-06罗海娆张悦南翔
罗海娆 张悦 南翔
罗海娆:南翔老师您好,我们了解到,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尝试了各式各样体裁的写作,虚构与非虚构都有涉猎。从宏观的视角来看,您认为在文学创作中,虚构写作与非虚构写作的关系是怎样的?它们各自涵盖什么?
南翔:考驾照分A牌、B牌和C牌。如果考了A牌,基本什么车都能开;拿了B牌,类似货车牌,除了大客车不能开,基本上什么都能开;C牌就只能开小车。我认为文学写作也分为三块牌子:小说和戏剧,就是虚构写作,属于文学的A牌,优秀的诗歌、长篇报告文学和长篇散文是B牌,短小的散文和一般的纪实文体为C牌,B牌、C牌一般就指的是非虚构写作。但是与考驾照有所不同,著名的文学大家汪曾祺就不会写公文,所以考C牌的人不一定比考A牌的人差。文学上的A牌、B牌、C牌更像是目前对三者的重视程度的排名,我们往往认为非虚构最能体现文学水平。例如,诺贝尔文学奖主要奖励给谁呢?小说、戏剧和少数的诗歌,唯有一个奖励给纪实文学的,在我印象中是阿列克谢耶维奇。
张悦:您最新的作品《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是一部非虚构作品,如您所言,应该算是文学的C牌。您是如何看待非虚构写作的呢?在这部新作中,您是以怎样的心态为中国手艺人记录的呢?
南翔:我一点也不看轻非虚构创作,我郑重推荐刚刚提到的纪实文学家阿列克谢耶维奇。我的非虚构新作叫作《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我在全国采访了几十位手艺人,优选十几位,写了这本书。书出来之后,没有一个手艺人不感激的,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他们。
我们在北京开了这本书的研讨会。随后新华社特意派记者来给我做了一个专访——《大国小匠“守”艺人》。这篇专访在《新华每日电讯报》登出来之后,新华社的微信公众号客户端浏览量一万一万地往上跳,三五天内超过了一百万,这篇专访的浏览量的零头盖过了我以前所有作品在所有公众号的浏览量。
我在《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里重点写的是人物的沧桑,但在搜寻资料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采访的困难。有人问,南翔,你可不可以写三代中国手艺人?我说不可能。为什么?且不说民国时期的手艺人经历了多少战乱,1949年以后的手艺人经历了多少公私合营、拆碎打散的冲击,即使我们写一个九十年代的蜀锦蜀绣手艺人,也基本上是下岗的手艺人。让这些连儿子上大学都筹集不到学费的人去重新挖掘手艺,难上加难,他们基本上都是靠自己创新走出来的。
日本作家盐野米松有一本《留住手艺》。他说:“我这本书的手艺人,他们的源头都在中国。”所以说,我这本书是向盐野米松致敬的,他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写田野调查和民间手艺的日本作家,经常在日本讲学。我们作为文字工作者,要有一种抢救心态,用文字和影像把文化固化下来,让后人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么璀璨的文化。而且我一直认为,学习传统文化不仅要背诗诵文,更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我们的传统文化更多地活在田园、活在民间。
罗海娆:我们重视写作的A牌,也就是非虚构写作,包括小说和戏剧。非虚构写作强调想象力,想象力可以带给文学作品无限的美感和张力。您觉得现在人们的想象力怎么样?我们又应该如何提升想象力?
南翔: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重点关注虚构作品?就是为了鼓励想象力。非虚构会受到素材的制约,你不能弹出来太远。但是我们发现,经过中考、高考上来的大学生,想象力严重匮乏。这种匮乏,不仅束缚写作能力,也束缚欣赏能力。
把时间倒推到以前。在我上五年级时,“文革”发动,我劳动了三年,当了七年铁路工人,1978年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所以我一共就上了几年学,大学毕业以后留校。它的好处在我作为一个作家,没读什么书,所以我的想象力没什么束缚。它不好的地方也在于读书太少。
莫言也是想象力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和我同年,也在五年级去劳动。他当兵前觉得表格上填小学太难看,填了初中。当兵的时候呢,一个战友让他帮着写情书,他一看高中毕业连情书都不会写,又将自己的学历改成高中。这些事都挺好玩的,都是想象力的问题。他的老师徐怀中先生九十岁高龄了,前段时间还凭借《牵风记》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我认为培养想象力应该注意几个问题:第一,书还是要读的;第二,书要在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要加快读都很重要;第三,想象力一定不要在二十岁的时候终止了,应该往极致发挥。比如我干铁路出身,铁路上什么人都有,我会说长沙话,会说江西平江话、宜春话、南昌话,甚至也能说说山东话,但是我调到广东多年也不会说白话,我还是在韶关出生的——这是因为我过了学语言的阶段。而想象力,同样也是有年龄阶段的,否则就会事倍功半。所以我呼吁大家重视想象力的培养。
张悦:虚构小说可以说是您文学的主要阵地。您的代表作《绿皮车》就曾登上2012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绿皮车”已经不属于我们这个时代了,但您还是写了一列绿皮车上的茶炉工、学生、卖菜人的故事。这列车应该是一个特殊的隐喻,它有怎样的深意呢?
南翔:我今天坐动车过来,也看到对面有绿皮车,但这不是我意义上的绿皮车。我的绿皮车是慢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铁路上能看到的带蒸汽机的绿皮车。我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茶炉工在绿皮车里的最后一班,回去以后他就要退休了。这一班车里头的人都是彼此熟悉的,铁路员工上班、學生上学,还有一些农村人卖菜的,都要靠这列绿皮车往返。
绿皮车,人们说它是流动的茶馆,里面有一种温馨的底层气息。比如《绿皮车》里写着一个单亲的女孩,没有多少钱吃饭,同班的男同学就耻笑她。卖菜的蔡嫂,自己也很贫穷,却悄悄给女孩书包里塞了五十元。小女孩第一次来例假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时候,蔡嫂还把小女孩带到卫生间去。绿皮车跟快车、慢车、动车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刚刚说的这些人,他们都能上绿皮车,因为绿皮车站站都停,你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也能上去。
几年前,广铁集团的总编带我去湖南怀化采风,看到绿皮车行驶。那是我很熟悉的景况,但在当时也几乎是最后一幕。有一趟慢车,从重庆,经过怀化的一个小站,到贵州的铜仁,一共二十四个站。在怀化的这个小站,只有三个职员。他们站长跟我说,为了节约成本,估计这个小站可能要取消了,而且这列绿皮车也要取消了。绿皮车要走向消失了。
但是十几年前,我到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参观,去看他们的火车头博物馆,我才知道原来最早的火车头,是用马拉着的,马拉着车在铁路上跑,车厢也很轻便。他们对自己国家历史发展的“痕迹”保存得非常好。
我常常跟一些家长说,多带孩子到工业博物馆去参观一下,不要总是待在电脑前。比如去曼彻斯特工业博物馆,看最早的蒸汽机。到森林工业局,到钢铁厂,去看钢花飞溅、铁水奔流。还有中山的岐江公园,它由原来的造船厂改造而成,就搞得很好,保留了铁轨,卷扬机也用玻璃保护起来,钢骨架的房子作为中山籍画家的陈列室,中山籍的画家有黄苗子、方城、方塘等。工业时代的遗产,广州还有,深圳几乎没有,因为深圳是个新城市,唯一能看到的是很多的挖掘机。让孩子看这种东西,他们才能感觉到生命的钙质,否则他们每天对着电脑、iPad,不郊游了,不去外面感受了,他们这种成长过程中就没有耳濡目染最需要的东西。
所以《绿皮车》表面上是写了这一群人在车里的人情冷暖,但是我其实有个更深的隐喻,我是呼吁处在全民都在奔跑的时代的我们,能慢一点。慢下来才能左顾右盼,扶老携幼,让所有的——腿脚不便的、收入过低的、文化不高的、底层的乃至于山乡的——人,都能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
正如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人们写道:“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不要让列车脱轨,不要让桥梁坍塌,不要让道路成为陷阱,不要让房屋成为废墟,慢点走!”
罗海娆:您的小说《老桂家的鱼》讲述了疍民们在水上艰辛的生活,但其中也不失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部小说和《绿皮车》一样,也是一个从现实生活中即将消失的群体中衍生出来的虚构作品,它的创作背后有什么故事呢?
南翔:疍民,是指世代都生活在船上的人。十多年前,我和研究生去惠州西枝江上,碰到一群疍民的船。有一家叫我们上去,他们的跳板颤颤巍巍地架在船上,家里的孩子还在身上吊个带子。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看了说,这个在国外可能不允许,因为你束缚了孩子的自由,这样的话,这个孩子要被政府领走。但是疍民为什么要束?因为他们怕孩子掉到河里去。大人在船舱里面煮饭、洗衣服,孩子掉到河里头听不见声音的。
《老桂家的鱼》其实不仅仅想写底层的苦难。第一次去那条船上,我印象很深,没有电,灯是烧液化气的,液化气上面有一个罩子。水要到岸上去挑,河水很脏,不能喝的。家里的鱼,永远一股煤油味。这个老疍民患了肾性高血压,一般人得了这样的病都起不来了,但他还在放鱼排。
我问他什么鱼最好?他说是翘嘴斑。我就设计小说里有条翘嘴斑鱼,也出现了一个患了乳腺癌的潘家婶婶。她一个人在那种菜,老疍民就帮她挖菜地,修水池,铺水管。潘家婶婶是公费医疗,就用自己的公费醫疗卡去拿药给老疍民。我就写,老疍民一直想报答这个女人,但没有私情。最后他捕到一条翘嘴斑鱼,想要送给潘家婶婶。这条鱼有玛丽莲·梦露般鲜红的嘴唇,而背脊却是像钢一样的,接近雌雄同体,因为我认为底层的情感、最好的情感就是几乎要到雌雄同体的默契。
这条鱼其实就是象征着,哪怕是底层的人也是有最好的情感的。老疍民一直想把这条鱼送给潘家婶婶,他从小船爬到大船。你看他那么笨重的身体、水肿的身体,最后能以这么大的毅力把鱼放到船舱顶上。但是他还没来得及送到种菜的潘家婶婶手上,他就已经死了。他的老婆情动于衷,在风中号啕大哭,有忏悔,也有追忆。
张悦:自然文学是一个很新的文学概念,在您的自然文学作品中,现实环境生态是创作的重要对象。例如,《珊瑚裸尾鼠》中就写到用中国传统的祭祀方式拜祭已灭绝的哺乳动物珊瑚裸尾鼠。您是怎样关注到这一种现实题材的写作的?
南翔:第六次人类的灭绝跟人类自身关系很大。六千五百年前,一颗小行星——十公里的直径,穿过了地球,释放了地底下大量的碳,然后百分之七十五的生命都消失了,包括恐龙。而现在,工业革命以来,地球碳的排放已经超过了当时浓度的两倍,而且还在急剧释放。
不要认为人类聪明,人类就可以洞察一切,人类就自律,不可能的。你让车子全部停驶,哪怕私家车停驶,做不到的。人类就是在朝一条黑暗的,没有尽头的甬道奔跑。仅仅塑料就很致命。现在海底的塑料,已经远远超过了海洋生物的总和,连最深的海沟里都有。我看到我家楼下的超市,几个西红柿都要用塑料袋,还有剥了皮的香蕉用塑料袋封起来。你觉得人类离自己的灭绝还远吗?所以我不觉得《流浪地球》写得很好。未来地球应该还在,但动物没了,包括人类。当海平面整个上升之后,地球是一片汪洋。
这部小说写作的缘起,就是今年二月份,澳大利亚宣布首个因为人类活动导致气温上升的哺乳动物灭绝。很多人移民到澳洲去,就是觉得它生态好。但在公认生态良好的地方,一种可爱的哺乳动物灭绝了。记住,我们也是哺乳动物。还有南太平洋,有一些小的国家,海平面上升之后,国人痛哭失声,只能到别的国家去寄生。而此时美国还要退出世界气象组织,泱泱大国对生态环境一点担当也没有。
《珊瑚裸尾鼠》发出来之后,《人民文学》第九期头条的卷首语,全部是讲自然文学的概念。以前我们写自然文学都是萌的、大的动物,都是讲人到野地里面去。而我这部小说的角度不一样。我是写一个家庭,丈夫和儿子准备去珊瑚裸尾鼠消失的地方做一个凭吊,做个观察纪念。妻子就拼命阻止丈夫。小孩小升初已经很忙了,更管不了天边的事。最后只有丈夫独自去了,录视频回来给他们看。丈夫找到了珊瑚裸尾鼠消失的地方,从澳洲回来,竖起了一块牌子,叫“珊瑚裸尾鼠终焉之地”。写这么一个故事,结尾有一点点翻转,小孩喜欢养仓鼠,但是妻子过敏,一见到小动物全身就痒。
有一位朋友说,南翔,第一例因为人类的活动导致气温上升而灭绝的哺乳动物——珊瑚裸尾鼠,很多作家都没有关注到,可是被中国作家关注了,而且写了小说,发在《人民文学》上,这是要留下一笔的。我听了很感动,我也知道这个事情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我经常买菜拖着回来,甚至我说,你这个塑料袋不要给我打个结,不然这个塑料袋就浪费了。现在垃圾分类是一方面,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少制造垃圾。日本有零垃圾制造者的夫妇,没有垃圾制造,剩下一点厨余垃圾都当作花的肥料,这种人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我写自然文学,一是角度不一样,从家庭写起,因为我对澳洲不熟悉,要扬长避短。另外是角度比较新颖。所以我后来写这个“创作谈”,叫《有多少消失可以重来》。这些例子,其实我很多年前就关注。比如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就做过一个小小的统计,仅仅美国人的隐形眼镜,扔到抽水马桶里,一年有六到八吨流入海里,最后被动物吃掉,又回到餐桌。何况不只是隐形镜片,有更多的垃圾进入海里,腐蚀,冲击,细碎化。那它到哪里去了?有沒有回到人的身体里?我们能看到海滩边搁浅的鲸胃里掏出多少个塑料袋啊,死了多少啊,但没看到的是,塑料是否进入到你的体内,是否大量存积,会有什么由质到量的变化?
气候变坏的一个很显著的标志——火,山火增多。瑞典山火多到消防队员不知道怎么处理。以前没有这么多山火,这么冷的地方。美国的5号公路,一两千年的松,火烧起来,美国人只有逃跑,再先进的消防也管不了。当年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着火的时候,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吗?火还没有到你身边的时候,房子已经倒了,汽车已经毁了,热浪就像冲击波一样。最近阿来也在写这些东西,我希望我们作家的视野更开阔一些。
罗海娆:听您刚刚对您几部作品的分析,现实似乎是连接虚构与非虚构的桥梁。我们可以认为,您的虚构作品与非虚构作品是互相打通的,文体之间是相互补充的吗?
南翔:是的。例如小说《回乡》也是从我的家庭经历中提取素材的。我的大舅在1949年前去了台湾,当时只有十九岁。“文革”的时候,我们读小学,我们从来不提大舅,不能出现。因为境外关系,尤其大舅在台湾,这样你的就学、你的工作,还有当兵都要受到影响,出身决定一切。他老家的孩子,受尽了屈辱,因为有个爸爸在台湾。老家的原配也在“文革”时候一打三反上吊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回来的时候,我和我妈去看他,他一人给了一个金戒指,现在看来一两百块钱的,薄薄的。他也不富裕,刚刚去台湾的时候在眷村里生活也是艰难困顿。后来我大舅找了一个金门的太太,慢慢日子好了一点。我大舅十多年前就去世了,虽然他比我妈小,小很多。由此可见,他们夫妇也是艰难困顿,但好不容易有点钱,还是寄到家里,想弥补自己的亏欠。由此我就写到这部《回乡》。
我用第一人称写大舅的近乡情怯,再想回来的时候,心中也是裂伤。后来我写到大舅把台北的房子卖了,台湾的孩子留一部分钱,又给大陆的孩子建一个房子。一个八十年代在农村很不错的土砖房,是很值得骄傲的。大陆孩子总算扬眉吐气了,不再是原来那个“黑五类”子弟。他每年都给房子刷油漆。到了九十年代,农村都富裕起来,他的房子已经不值一提了,但是他还沉迷在那个境界里头,最后得白血病死掉了。我大舅也在台湾去世。所以这个经历是有点悲怆的。
《回乡》中还贯穿了一个很有名的诗歌——《边界望乡》。1979年的时候,洛夫和余光中骑马在香港的落马洲,那时候还没有“三通”,对面的深圳看得到却过不来。“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震升起,我们在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生汗,望远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我这部小说开篇是这么一段。结尾是最后一段,“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回乡终究是一场镜花水月。
这样的小说应不应该让它获奖?小说结尾的意境跟余光中先生写的这首诗非常贴,就是:“故国的泥土,伸手可及,/但我抓回来的仍是一掌冷雾。”火热的乡情都变成了赤裸裸的物质,或者是补偿,或者是裂伤。
所以这个父兄辈的经历,我的经历,历史和现实,虚构和非虚构,我的原创,我的个人经历,我的个人感受,最后形成一个文本。它看上去像是一部散文体小说,看上去像一个跨文体、跨文本作品,但是它确实有更感人的力量在。
张悦:您的作品中多围绕底层生活艰难的人,但是他们都能够倔强地面对生活,在他们身上折射着人性的光辉,非常的真实、接地气。而《绿皮车》中的蔡嫂、茶炉工等虚构人物在生活中几乎都有原型,也是您“三个打通”创作理论下的产物。那么,您在小说创作上是怎样处理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的?
南翔:这就凭经验了,和做手艺有点相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理是——短篇小说是做减法的艺术,它不像长篇,不停地堆成一座大山,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泥沙俱下。短篇小说是要把最没用的东西都去掉,要学会留白。学会了留白,才能写好短篇小说。
写虚构,首先是可信,其次是要出新。光可信还不行,你有些虚构得合情合理,但它没有新意,别人都写过了,不行。所以还是要有些出人意表的东西。在题材上的挖掘也很重要,你的经历,你的感受,包括各行各业的。例如在广州,道里巷间,作坊,多做一些观察。不要吃完饭就走了,我看他怎么收银的,怎么递盘子的,一举一动。观察回来写观察日记,积累生活。积累生活不仅仅是观察,还有写作、阅读。在想象力的训练上则要多写,写点小说,三千字以内的,两千字的,把生活中的东西虚构,带点虚构性。像我今天讲的,都是从非虚构滑向虚构。一定是有原型,有的是取一个主要的原型,有的是拼凑,把几个人拼凑在一块。还有一个就是多读,多读一些虚构的东西,让你的想象力有一个跃升,觉得这样的东西我也能写。
责编:李京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