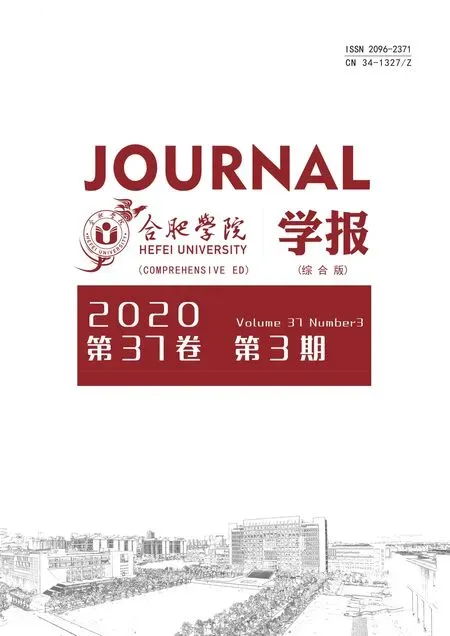天花板上的鞋印
——试论《无声告白》叙事伦理建构
2020-07-23汤琳
汤 琳
(合肥学院 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601)
叙事伦理要探讨的是一种生命的创伤性经验如何形成,又将如何继续产生着影响的问题。[1]这一术语最早源自亚当·纽顿(Adam Z. Newton)1995年的著作《叙事伦理》,他提出叙事伦理是“叙述行为所引起的讲述者、倾听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伦理对话”。[2]
美国华裔80后女作家伍绮诗(Celeste Ng)小说处女作《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讲述的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在美国中东部只有三千居民的米德伍德镇上,一个由美国二代华裔移民詹姆斯李和美国人玛丽琳,组成的混血家庭所经受的杂糅了历史、身份、族裔与性别等问题的创伤叙事。
无论是叙事人物塑造还是叙事主题选择,《无声告白》都显现了相对高超的艺术水准。2014年问世后好评如潮,在美国亚马逊2014年度最佳图书的评选中,凭借此书伍绮诗力压村上春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科尔姆·托宾、斯蒂芬·金等九十九位当代文坛名家和畅销书作家,荣获第一名。[3]同年,该作还被评为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最佳图书、《学校图书馆期刊》年度最佳图书、《赫芬顿邮报》年度最佳图书、《纽约时报书评》年度百佳图书等。
同《俄狄浦斯王》一样,小说文本叙事“不采用规约性的开头,不描述事件的起因”,采用“从中间开始叙述”的手法,[4]以回溯的方式,通过找寻家里大女儿莉迪亚死亡的原因,将这个家庭的悲剧以多重叙事的方式,抽丝剥茧般地逐一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小说开篇作者用极其淡然的语气写到“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Lydia is dead. But they don’t know this yet.)”(伍绮诗,1)冷峻口吻让读者极易联想起加缪《局外人》的首句:“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Mother died today. Or maybe, yesterday; I can't be sure.)”。但是通过阅读读者却发现,事实上,詹姆斯一家人相互间拥有深厚的情感,互相依恋的程度之深,有时候甚至构成了让对方感到呼吸困难般的重压。
1 复式叙事结构
《无声告白》叙事结构设计巧妙,全文共分12章,叙事时间横跨前后二十年。作者打破常规线性叙事方式,全文采取多视角、多叙事主体、多层套叠的非线性多重叙事策略,穿插使用了倒叙、正叙、插叙、预叙等多种叙事手法,将现实与回忆并置与交叉,使得文本各章节的叙事时间,与叙事事件发生的物理时序交错。
文本叙事涉及三个重要时点和两个叙事核心,分别对应的家庭事件是1957年到1959年间,父亲和母亲相遇及结婚、1965年圣诞节到1966年,母亲梦想回来了,然后离家出走和1977年大女儿莉迪亚突然死亡。这三个事件发生的时点基本相互间隔十年。图1以文本叙事所对应的物理时序为中心轴线,重新排列了文本各章节,直观地展现《无声告白》的叙事非线性叙事技巧。

图1 《无声告白》复式叙事结构
从事件发生的自然时间角度来看,被安排在第1章的“莉迪亚死了”,发生在文本叙事现实与回忆的中心节点上,是文本显性的叙事核心事件。第6章“母亲离家出走”,作为文本隐性的叙事核心,被安排在文本叙事的中心章节,但其发生的自然时间,却是仅仅位于“父母相识”和“母亲梦想回来”这两个叙事事件的时间节点之后。
文本中第2、4、6、7、9、11各章,采用不同叙事人物的第三人称有限视角,以回忆的方式叙述莉迪亚死亡事件发生以前的故事。而第3、5、8、10、12各章叙事事件与叙事时间同步,用现在时态讲述莉迪亚死后,全家人陷入的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生活上的混乱状况。从篇幅上来看,全文以“莉迪亚死了”为界,回忆和现实叙事相当,各占一半。各章节叙事人物,在一家五口人中交替变换。交叉使用限制性全知视角与人物外聚集的有限视角,让他们通过对同一个故事进行不同视角地叙事,展现叙事人物自我伦理取位。
文本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视角,和貌似避重就轻、极具主观色彩的讲述,一方面将事件中各个当事人,逐一离析出来,更为客观地为读者展现事件的真相。另一方面也通过展现莉迪亚作为“缺席的在场”,依然可以制约其他人物的情感发展与行为走向的事实,表现出其在家人心目中不可替代的位置,从而更进一步地引发读者的悲剧共鸣。这种众人讲述、多视角的叙述手法,使得读者的阅读行为,仿佛是在把玩一面多棱镜,在不同的人手中,随着各自转动的方向,展现着不同的色彩组合。
2 多维人物塑造
在人物刻画方面,《无生告白》中的叙事人物兼具扁形人物概念化与圆形人物复杂化性格特点,这与文本将正叙与倒叙、现实与回忆并列的叙事结构,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文本中五个主要叙事人物,在不同的叙事事件和时空中,面对其他叙事人物时,仿佛是在审视镜子里的自己。玛丽琳和自己的妈妈,詹姆斯和内斯,内斯和莉迪亚,内斯和汉娜,他们要么是存在于同一叙事事件中;要么是相较于某个叙事事件,一个是与叙事并行人物,另一个是处于回忆中的人物;要么是虽然并行在同一叙事时空中,却因各自不同的伦理选择,互相映衬。
亲情、血缘作为这家人最重要的联系纽带,就如同内斯和莉迪亚小时候参加学校运动会,玩两人三足的游戏时绑起他们的手绢,“捆得很紧,把两人的脚踝勒得难受,像一条套住了两头并不匹配的牲口的轭,连他们各自朝着相反方向仰而朝天地摔倒,都没有松开。”[5]153“十年后,那种羁绊仍旧没有丝毫放松的迹象。”[5]154
2.1 追求与众不同的玛丽琳
玛丽琳是美国人,学生时代一直成绩优秀,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在她有清晰记忆前,自己的父亲就离开了。她随着做中学家政课教员的妈妈一起生活,一生执着于“与众不同”。在她大三时,在课堂上遇到了即将获得教职、看着“像个大四学生”、“小个子”、身为“东方人”[5]32的詹姆斯。他的与众不同深深吸引了玛丽琳,玛丽琳还没有毕业,他们就结婚了。事实上那个时代,和异族通婚,在美国有些州甚至还不合法,玛丽琳的妈妈对此也说“不合适”。但是玛丽琳义无反顾地选择和詹姆斯结婚,并断绝了与母亲的关系,直至母亲去世,都没有再见她一面。
作为一名知识女性,玛丽琳在当时的那个男权社会中,深切地感受着被边缘化的痛苦,当医生的梦想显得非常“与众不同”,让她陷入了在“自己熟悉的房间,门却被锁住了[5]5”般的困境,在婚后留在家里相夫教子。但是,在婚后十年,她的母亲去世了,回想着母亲“渺小、孤独的一生”,玛丽琳毅然下定决心离开丈夫和年幼的儿女,独自去托莱多社区大学学习。然而,在离家求学期间,玛丽琳除了面对来自男性社会的怪异眼光外,还突然发现腹中有了一个意外到来的小生命,这让她不得不放弃了仅仅持续了九个星期的计划。她梦想“简直如同猫变老虎一样,门都没有”,[5]92就此黯淡退场。
2.2 梦想合群的詹姆斯
詹姆斯的父亲是在美国排华法案时代,以“契纸儿子”的身份,非法来到美国的。即使詹姆斯出生在美国,接受了典型的美国教育,在哈佛毕业,通过努力,获得大学终身教授的身份,讲授“美国文化中的牛仔”课程二十年,说起英语“听不出口音”[5]33,仍然将“不被发现、不被遣返回国……拼命融入人群,极力避免与众不同”[5]42视为人生最大的梦想。平日里他尽力不谈起中国两个字,就如同“不去过多谈论这些词汇(地球围着太阳转)一样的天经地义”。[5]199对于他个人的人生经历,学生时代经受的嘲笑和捉弄,即使是面对家人,詹姆斯也同样绝口不提。
儿子内斯体弱瘦小,不善运动,唯有学习成绩优异。这让詹姆斯“想起自己,想起他试图忘记的童年往事……让他感到难过和羞愧。”[5]152因此,他从没有对内斯表现出些许的骄傲和自豪,只是将自己“融入人群”的梦想,寄托在遗传了母亲“蓝眼睛”的大女儿莉迪亚的身上。对这个梦想的渴求与急切,使得他在圣诞节送给已经15岁的莉迪亚的礼物,是一本让她感觉自己的心“仿佛掉进了冰窟窿”[5]173的名叫《如何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的书。[5]172
2.3 承载父母希望的莉迪亚
大女儿莉迪亚是家中唯一遗传妈妈的外貌的“美国”孩子。在她5岁的时候,母亲玛丽琳因梦想离家出走了九个星期,这给莉迪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5]220。在母亲离家的日子里,她发誓只要妈妈能回来留下,那么“她母亲的所有心愿都变成她的承诺”[5]270。于是等玛丽琳回来以后,莉迪亚极力地表现出对于数学的兴趣,因为在她看来,这样才能让妈妈高兴,让她留下来。
对于父亲对她融入社会的期望,莉迪亚也极力的满足。甚至不惜假装和朋友看电影,打电话。事实上,在莉迪亚的同学眼中,她“安静孤僻,缺少朋友,她最近的成绩直线下降。她的家庭也很奇怪,没有朋友,与环境格格不入。”[5]109这样拼命迎合父母心意生活了十年以后,莉迪亚最终发现“继承父母的梦想是多么艰难,如此被爱是多么令人窒息。”[5]271
2.4 被父母忽视的内斯和汉娜
内斯是家里的长子,因为遗传了父亲的华裔外貌,虽然成绩优异,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但是“因为‘太瘦’不能参加橄榄球队,‘太矮’不能打篮球,‘太笨’不能打棒球,只能靠读书、研究地图、玩望远镜来交朋友。”[5]154时刻感受到父亲对他的“失望”,母亲对他的“视而不见”[5]168。在母亲离家出走的日子里,内斯喜欢上航空学,是家里最了解莉迪亚的人。他一方面很理解莉迪亚在父母期望重压下的痛苦,不时地想办法帮她解脱,给她安慰。另一方面和小妹妹汉娜一样,对莉迪亚独享父母的宠爱非常嫉妒。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就曾经将莉迪亚推进米德伍德湖里。在内斯看来,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让他获得自由的承诺”[5]168,是逃离令他窒息的家庭的时空门。
小女儿汉娜内向而敏感,和哥哥内斯一样,遗传了父亲的肤色、黑发、黑眼睛和瘦削的个头,这些典型的亚裔特征不仅使他们在白人社会里很显眼、异类、“与众不同”,而且在家里也不受父母关注,不被重视。常常躲在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默默观察家人,对夺取了父母所有的爱的莉迪亚又羡慕又嫉妒。
3 那些没有告诉的事情
《无声告白》的英文书名是EverythingINeverToldYou,直译为“我没有告诉你的所有的事情”。中文翻译为一个状中偏正结构,由状语和中心词构成。英文题目则是一个由中心词,和对其起修饰作用的定语从句构成的定中短语。中文译文可以理解为一种动作,而英文原文则表达的是一个概念。这里没有告诉的事情,不仅仅是莉迪亚真正的死因,更多的是作者对民权运动后华裔生存状态的多元化反思,以及生存空间的现实性思考。
3.1 莉迪亚的痛苦
莉迪亚因为遗传了母亲美国人的外貌、乖巧懂事、喜欢数学,被母亲玛丽琳视为实现自己“与众不同”的梦想寄托,而父亲詹姆斯也因为莉迪亚和自己长得不像而欣喜,认为她可以不被察觉完美地“融入人群”。然而,母亲对于莉迪亚的期待和关爱,对她来说,就如同博物馆里展出的琥珀,非常美丽,却令人窒息。父亲送给她的项链,在莉迪亚看来也只是一个时刻提醒她要“合群、受欢迎”的枷锁。莉迪亚几乎没有朋友,驾驶证考试也失败了。为了不让全家最了解她的哥哥内斯离开,莉迪亚偷偷藏起了他的哈佛大学录取通知书;为了引起他的注意,甚至还刻意和内斯讨厌的杰克交朋友。
3.2 家庭的秘密
詹姆斯和玛丽琳的婚姻从根本上来讲是建立在对双方的错误认知上的。[6]玛丽琳当初违背自己母亲、种族、社会的意愿与詹姆斯结婚,是因为詹姆斯的华裔出生符合她“与众不同”的要求。对于詹姆斯而言,当年被白人姑娘主动示爱,“是美利坚这个国家对他敞开了怀抱”[5]46的表现,是让他得以实现“融入社会”的愿望的渠道,符合他潜意识里的东方文化——“合群”的标准。至于玛丽琳的梦想、她母亲的红色烹饪书和詹姆斯身为“契纸儿子”后代的事实、莉迪亚的尸检报告都是他们相互隐瞒的秘密。一起生活了二十年,詹姆斯和玛丽琳的互相了解似乎仅限于他们认识的那一刻,这无疑是预埋了这个家庭在文化临界空间里必然发生的危机。
寄全家希望于一身的大女儿莉迪亚,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总是假装学习优秀,假装在朋友中很受欢迎。事实上,“莉迪亚从未真正拥有过朋友,她的父母却从不知道这个事实。”[5]17为了取悦父母,莉迪亚假装和朋友打电话;趴在洗涤池上学数学;拒绝好不容易等来的同学的聚会邀请,回家做物理作业;不惜作弊来掩盖自己到高中阶段已经跟不上的物理成绩……,莉迪亚“是全家人的宇宙中心,尽管她不愿意成为这个中心——每天都担负着团结全家的重任,被迫承载父母的梦想,压抑着心底不断涌起的苦涩泡沫。就这样过了一年又一年,……”[5]156
这家人互相还有很多的秘密。莉迪亚和汉娜都知道她们的邻居杰克对于内斯的感情,但是从没有告诉一直对杰克怀有厌恶与憎恨的内斯。内斯讨厌杰克,但是发现莉迪亚和杰克做玩伴时,也没有告诉父母。内斯和汉娜都不满父母独宠莉迪亚,但是他们都选择了接受事实。他们也都知道莉迪亚在死去的那天晚上偷偷的跑出门,但既没有告诉父母,也没有告诉警察。孩子们都发现了他们的父亲和他的助教路易斯的关系不同寻常,却没人告诉母亲。
互相保有着秘密,但同时又为自己的秘密所制造的假象所困。玛丽琳与母亲断绝关系,却因她的红色烹饪书而重新思考人生,最终触发这家人悲剧的多米诺骨牌;莉迪亚极尽全力取悦父母,可现实最终如毒蛇般越缠越紧让她不能呼吸;詹姆斯出轨和自己有相同东方背景的露易莎,却不得已直面自己多年来不敢面对的过往。这一家人虽然相互关爱,但因由当时的社会语境,各自的伦理取向,一直在维持着一种“奇怪而脆弱的平衡”[5]270。他们本人对各自问题都很清楚,但是却像莉迪亚学开车一样,“知道该怎么做,只是做不到”[5]222。
4 悲剧根源分析
4.1 “契纸儿子”的悲哀
《无声告白》延续了美国华裔女作家擅长的家庭叙事的写作习惯。不同的是,伍绮诗选择的叙事时间,设定在美国社会出现剧烈动荡的二十世纪中后期,舍弃了有关一代、二代移民的基本生存的叙事话题,转而思考生存下来后,华裔移民生活质量的问题。文本中华裔父亲詹姆斯,没有像其他传统华裔文学叙事中的男性角色一样的“隐身”,反而走到了前场。虽没有摆脱文弱的男性刻板形象,但是他已经不再执着于家园的建构,转而正面的积极追寻对“美国身份”认同。
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尽管美国社会经历的种族平等运动,对保守的道德价值观念产生猛烈冲击,华裔依然无法摆脱缺乏现实的归属感、自我身份不明确、无法拥有正常人的自由与权力的境遇。在詹姆斯一家所生活的位于中东部俄亥俄州的小镇,华裔被视为“异类”,他们一家人的在美国出生成长的事实、口音、智商、名校教育和显赫的职业,已经都没有意义。在内斯和莉迪亚还是幼年的时代,他们去学游泳时,就被其他美国孩子嘲笑“中国佬找不到中国啦!”[5]88。一张亚裔皮囊已经决定着他们的“他者”身份。当地报纸在报道莉迪亚死亡的新闻中写到:来自混血家庭背景的孩子,通常难以找到自己的定位[5]197,这可以说是这个家庭面临的致命钝痛。
平日里,他们享受的只是一种与外人隔离的幸福。孤立无援的处境,致使他们平时不上教堂做礼拜[5]60,“从不出门交际,也不在家请客,没办过晚餐派对。没有桥牌牌友、猎友或者午餐会上认识的哥们,他们没有真正的朋友”[5]59,不被周围白人社会认同的孤独感如影随形、挥之不去。长得很像母亲的大女儿莉迪亚,只是实现詹姆斯“融入白人社会”的梦想,和玛丽琳“与众不同”的期望的一个一厢情愿的道具而已。
詹姆斯的父亲背负着“契纸儿子”(非法居留的人)的身份;詹姆斯是出生在美国,具有美国终身教授的身份;家族第三代内斯拥有来自母亲一半的美国血统、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但生为华裔是他们不能摆脱,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在美国文化的强势语境中,这为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生存困境。另外一位美国华裔女作家伍慧明(Fae Myenne Ng),在她1993年出版的《骨》(Bone)中就假借书中女主人公丽拉之口,反思了美国反华历史上“契纸儿子”这一畸形现象,“我绝不忘记。我是一个契纸儿子的继女儿。我继承了一整箱的谎言。”[7]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指出,历史并不是简单的过去,而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结构构成。[8]这段历史对于早期华裔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在精神上抑或是在现实生活中都造成深远影响。
詹姆斯父子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可谓是美国华裔移民的微缩历史。他们饱受种族歧视的命运,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迁,因由种族歧视政策,而导致的身份真正意义或者是实质上的“缺失”也依然存在。如果说,詹姆斯的父亲是来自中国的“契纸儿子”,詹姆斯则是美国文化的“契纸儿子”。三代人中,祖父和父亲终身都与“身份的缺失”抗争,而儿子内斯则受到来自“文化内化地挑战”。
4.2 中西家庭观念的冲突
“家”这一概念,“最直接的意义包含家长秩序,性别的辈分,庇护所,养育和保护的私人的活动范围”,[9]是建立在血缘结构上的稳定组织。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对于家和家乡的观念在移民文学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在英语文学还是在华文文学,还是在离散理论中,对“家”的描写和阐述已经逐渐历史化、民族化、政治化和多元化。它本身的内涵也早已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在以大规模的移民、难民、旅行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家的意识已经双重地或多元地在居留地和老家之间徘徊,原本“归属”的家已经可以离开具体的物质形态,成为文化精神上的家,用阿姆斯特朗的话来说就是“最强有力的家是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能带在脑子里的家”。[10]
来自不同文化的詹姆斯和玛丽琳,异质相吸,最终组成跨种族婚姻。然而,单亲家庭里长大的玛丽琳,骨子里埋着西方文化中所追求的标新立异、个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梦想,以个人主义为最高生活原则,一生追求的是“与众不同”。她不愿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将一生奉献给“丈夫、孩子、房子”[5]76,结果却落得孤独终老——丈夫抛弃了她,女儿离开了她,唯一没有离弃她的只是她烹调的食物。来自同学、老师的性别歧视,致使玛丽琳年轻的时候发奋读书,成绩优异,她原本立志当一名女医生,而这并非易事,因为“二战后女性就业人数成倍增长,但是商业、法律、医生等行业女性很难涉足。”[11]
信奉集体主义的华裔后代詹姆斯,尽管是在美国出生成长,受美国教育,但是骨子里还抱有家国同构的中国人传统伦理主张。但是兼有美国人与华裔移民后代的双重身份本就是一种矛盾的结合,詹姆斯经历了自我身份与民族身份的双重困惑。尽管乐天知命的儒教思想,从不鼓励对不可企及的东西的追求,但对于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的踏实感和归属感的追求,致使他甚至都看不到家庭的真正含义。
一方是安于维护家庭现状、理性的东方父亲,一方是以情绪为中心、执迷于追求自我价值的西方母亲,构成了这个混血家庭扭曲的伦理关系。他们各有一次离家出走的经历,暗示着这个家事实存在着某种令他们都想逃离的气息。但他们对各自出走不同的解决方式,却印证了他们不同的家庭伦理。崇尚自我的母亲是在发现自己身怀有孕的无奈下,被父亲寻找回家庭的。而具有中国传统伦理本位思想的父亲,几乎看不见自己,出于对家庭的依赖,自我反省以后,主动回归家庭。在异族文化中失去自我的父亲,作为“契纸儿子”的后代,延续着自己在异族文化中原生家庭有限的亲情,无法为自己的子女营造温馨安宁的“天伦之乐”。感性的美国母亲对于自我的执着追求,远超于中国传统母亲为了家庭自我牺牲。双重文化背景下的女儿最终成为无奈的文化牺牲品,自我毁灭,令人唏嘘。
5 结 语
在莉迪亚学习开车的时候,她知道如果要学会开车,就要控制好油门和离合器这对好伙伴,如果一个上去,另一个就得下来,可是莉迪亚无法协调好这两者的关系,最终也没有通过驾照考试。在自己生活上,莉迪亚也同样有无法处理好各种矛盾,虽然外表长的很美国,但在美国社会中,她就如同是,她和内斯小时候打死蜘蛛时,留在天花板上的鞋印,确确实实存在,却难以被人注意、理解与接受。
早在1926年,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罗伯特·艾茲拉·帕克(Robert Ezra Park) 在《种族与文化》(RaceandCulture)就指出种族关系发展过程的四部曲,即“接触”“竞争”“适应”和“同化”。[12]如果说在“接触与竞争”中莉迪亚毁灭了,但是追求“适应与同化”过程中,内斯得以摆脱历史创伤,实现自我重构,最终以一个积极的行动者的姿态,去面对社会与时代的发展。
在文本最后一章,内斯和杰克打架后落入米德伍德湖中,但是因为太熟悉水性,他的身体已经自然知道怎样不被淹死。当他在水中睁开眼睛,看见杰克的手和汉娜的脸的时候,那一刻所有的历史、种族尘埃仿佛顿时消散,内斯摆脱了阴霾,或者说是主动与杰克代表的美国文化,和汉娜代表的中国文化达成了和解,就如同詹姆斯和玛丽琳最终携手,准备好共同迎接未来。因为内斯和美国历史都清醒地知道,“天花板上的鞋印,是一样荒唐的东西,无法解释,毫无意义”[5]276,但是它“魔法般的存在”是无法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