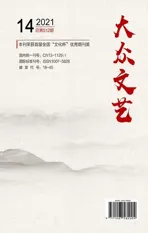《吉姆爷》中殖民空间的建构与解构
2020-07-13宋维汉
宋维汉
(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河南洛阳 471000)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空间”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正不断崛起,空间成了一种赋予了深刻文化意义的文本,不再是时间的附庸或纯粹的地理景观。这样的转变离不开法国理论家福柯和列斐伏尔所引领的“空间转向”,列斐伏尔反对将空间看作是静止的“容器”或“平台”“强调空间作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以及社会秩序建构过程的产物,而福柯则认为空间是各种权力关系交锋的场域”(郑佰青)。
在空间批判的研究中,空间不仅具备着物理属性,也不断被赋予社会和权力属性。结合文本对空间进行分析,人们可以从小说中的空间或者空间场景感知社会的运作规则,以及权力的运行法则,进而更好地理解小说当时的社会背景、政治状态以及历史环境。康拉德的《吉姆爷》真实记录了西方殖民者吉姆在马来亚的活动,白人水手吉姆依托马来亚村落巴多森中的贸易站构建了一个西方城堡式的殖民空间,但来自空间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压力又最终导致了殖民空间解体,这似乎也预示着殖民地在慢慢地走向独立,西方的殖民统治终将结束。
一、《吉姆爷》中的空间建构
小说《吉姆爷》着力描写了海洋与丛林两个空间,海洋的无限宽广既象征着吉姆实现冒险理想的机遇,又潜藏着理想破灭商船沉没的危险;丛林的安定深邃一方面给予吉姆继续梦想的可能,另一方面又暗藏种种阻力。从海洋到丛林,空间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是西方的影响无处不在。小说中与海洋空间相关的场景主要是轮船和码头,与丛林空间相关的场景是西方的贸易站和内陆殖民地。轮船是大航海时代西方走向东方的主要交通工具,码头是轮船停留的地点也是西方殖民者向殖民地内陆深入的跳板;贸易站是西方最初向内陆深入的据点,依托贸易站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进而不断提升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进而将当地转变为殖民地。从轮船到码头再到贸易站,场景不同,但西方殖民扩张的深度、广度、和强度都在提升。在西方殖民扩张的过程中,海洋和丛林两个空间都被西方所掌控,共同构成西方的殖民空间。
凭借自身的航海技术,西方人能够从欧洲出发,向世界的各个角落迈进。这背后不仅有着先进的造船业为支撑,同时也依赖于完备的船员培训机制和国家的鼎力支持。小说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吉姆小时候“显露出对于海的兴趣之后,他家里人立刻把他送到‘商船船员训练舰’去了”(康拉德:3)。在那个时代,水手似乎被认为能够克服大海上的种种困难,驶向成功的彼岸,水手身上体现的那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被“视作民族优良品质的同义词”(Peck:170)。
但“帕特纳”商船发生船难之后,吉姆因为和其他船员一样逃跑而丧失船员资格,在各个码头上流浪,最后被推荐去马来亚的一个贸易站工作。巴多森当时还是个闭塞的原始村落,吉姆住在普通木屋里。但是,他先帮助巴多森的居民赶走之前压迫他们的酋长,在村民中树立起威信,之后根据自己的构想,将自己的“住宅变成堡垒”,堡垒周围有“一条深沟渠,土墙顶上筑有木栅栏,所有拐弯处的平台上都架着角炮,可以扫射广场的任意一面,”在这座堡垒的周围,“一旦遇到突发的危险,每一个忠诚的支持者,都可以在这里避险和集合起来”(康拉德:322)。当地居民的房屋环绕着城堡而建,城堡宛如一座瞭望塔位于城市的中心。这样的城市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证了地区的稳定,而实际上这样的结构也渗透着一种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ism),西方居中,俯视统摄四周。这种空间结构方便统治者“根据相互关系分布人员、按等级体系组织人员、安排权力的中心点和渠道、确定权力干预的手段与方式”(福柯:231)。在这种结构中,只需要控制住空间的中心,便能够有效地控制边缘,吉姆正是凭借这样的机制才得以在殖民地站稳脚跟,主导丛林中的殖民空间。
二、《吉姆爷》中的空间解构
主导空间,并不意味着绝对的控制着空间,空间在被建构的同时,也在被不停地解构。这里的解构不单是指解构原有的社会秩序,确立新的社会模式,并引入新的社会规则和道德判断,还预示着如果新的秩序和道德规范与现实不符,则会导致新一轮的解构。因此,小说中殖民空间被建构的同时,也一直经历着解构,而背后原因又是什么呢?
吉姆对巴多森进行的社会改造的确给当地带来了稳定,但是并没有改变那里的社会状况。吉姆刚到巴多森时帮助当地居民赶走了原先压迫他们的酋长,但只是换了另一个酋长继续统治着那里,巴多森需要的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而这一变革的诱因来自海盗白朗的入侵。
海盗白朗率领一支十几人的海盗小队对巴多森发起攻击,而此时吉姆因事离开了巴多森,最初的抵抗由当地首领的儿子邓华力指挥;在他的指挥下,当地村民凭借优势兵力包围了海盗,控制住了局势,但是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应对,等待着吉姆回来处理。最终,两个外来的白人坐到了谈判桌上,商讨殖民地问题,不管商讨结果如何,这里体现出的依然是一种西方主导殖民地的状态。商谈的结果是,吉姆答应放走白朗,但是在逃走过程中,白朗偷袭了村民,杀死了邓华力以及其他的村民。吉姆此前向巴多森的首领都拉明承诺,如果发生意外则愿意用自己的性命做担保,最终吉姆也实现承诺,走向了死亡。
整个动荡的结果是,象征西方野蛮力量的海盗逍遥法外,象征西方文明力量的吉姆最终走向死亡,而巴多森则不再有西方的力量,在某种程度又恢复到殖民地人民自治的状态。与此前封闭落后的状态不同,这时的巴多森殖民地已经经过西方的武装,他们能够守卫自己的家园。但是小说最后并没有明确交代,殖民地最终的状态,小说以吉姆的死为结尾。但是,当人们回顾历史,西方的殖民统治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就逐步走向消亡,殖民地人民独立的意识不断增强,在与西方殖民者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获得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殖民空间最终彻底瓦解。
三、空间变化背后的思考
小说中,殖民空间在经历建构之后,又走向解构,康拉德对殖民空间的书写不仅展现了当时殖民地的地理图景,还记录了西方殖民者在殖民过程中如何改造殖民地,建构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空间。在空间建构的过程中,殖民者带去西方文明,在殖民地树立政治秩序,但在文明进程中往往也伴随着野蛮的入侵,这种入侵消解了此前确立的秩序与稳定,最终导致空间走向坍塌。“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production),是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与人类干预形成的,又是一种力量(force),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行为与方式的各种可能性”(Wegner:181)。位于殖民空间中心的西方殖民者主导一切的时候,忽视了位于边缘的殖民地人民,他们以一种主人姿态行走在殖民地,忘记了他们一直以来都只是外来者。而处在边缘的殖民地人民在被西方殖民统治时,也在向西方学习,他们从骨子里希望与西方进行平等的对话,获得与西方殖民者一样的地位。
在殖民主义之后是“后殖民主义”的兴起,它是“一种遍及世界的文化思潮,基本思想取向是呼唤一种来自文化边缘的本土化理论,解构殖民帝国的文化霸权和西方中心的话语统治”(王小晴)。在小说的叙事中,西方掌控着一切,马来人似乎完全不会思考,在危险面前往往是一种茫然。“帕特纳”商船上的两名马来水手在船难发生时呆呆地站在那里,“眼睛发光,望着白种人,但是他们棕黑色的手还是抓着[船舵的]攀手”(康拉德:21)。他们身旁的西方船员忙着逃离发生故障的“帕特纳”商船,坚守岗位的他们在西方人眼中被看作是丧失了理性和思考能力。小说并没有交代马来水手坚守的原因,但正是凭借他们的坚守,整艘船才会那么顺利地被救起,叙事者眼中的茫然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勇敢。
小说最后巴多森的人民赶走了海盗,吉姆爷被处死,西方在巴多森的势力得到了削弱,但这才只是开始。巴多森所处的殖民空间开始走向解体,但是离最终的解构仍有很远的路要走,而它只是西方众多殖民地中的一个。这样的空间变化也预示着,处在边缘的殖民地人民正在努力走向中心,成为他们自己家园的主人。
四、总结
作者康拉德在小说中描写了海洋和丛林两个空间,揭示西方在这两个空间中的主导地位,进而建构出以西方为中心的殖民空间。随着小说的推进,作为殖民空间一部分的巴多森殖民地逐步摆脱了西方的掌控。小说并没有写巴多森人民如何进行独立斗争,而是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了西方殖民者自身身上。通过探究空间的变化,指出西方自身的道德堕落是导致殖民空间解构的根源。历史证明,西方的殖民统治不断走向解体,小说中空间的逐步瓦解体现出康拉德对于西方殖民无法持久的先见。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去殖民化相对简单,国家独立是在现实层面的,但是要在思想和文化上去殖民化,尤为困难”(Sharp:5)。当今世界的格局仍然是西方在主导,曾经的殖民地人民要想真正走向独立和富强,仍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未来总是光明的,终有一天会建立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