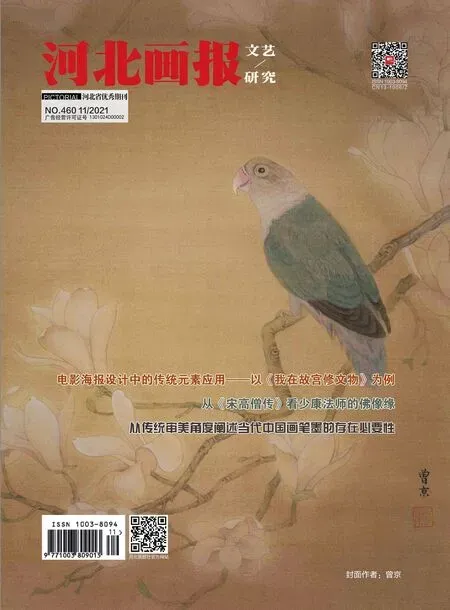艺术功能与城市文化漫谈
——以广州为例
2020-07-12马宇亮
马宇亮
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政府鹤龙街道办事处
关键字:艺术功能;城市文化;广州
广州是一座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城市,同时又是艺术创新发展的高地。行走在广州,古老与现代、传统与前卫的激情碰撞随处可见。本文将以与广州息息相关的绘画作品、热点项目、标志性建筑物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探讨,就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实际情况,加以阐述。
一、艺术具有社会功能
艺术是通过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众所周知艺术具有三大社会功能即: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艺术作为认识世界的方式,首先表现为它有助于人理解世界。清代画家郑燮所言“一画有千秋之遐想”,指的就是认知功能,人们往往能通过艺术作品去认识和了解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生活情景,进而促进对历史、现实及未来的思考,加深对事实真理、价值真理及具体真理的理解。例如19世纪兴起于广州的通草纸水彩画,色彩浓郁艳丽、场景生动形象、人物惟妙惟肖,蕴含了清末广州的礼仪风俗、市井百态、花鸟草虫、园林建筑等大量信息,由于其借鉴西方绘画技巧及原理,反映中国本土风情,迎合当时西方人的审美趣味,而且在尺寸各方面又具有特殊优势,因此深受当时西方人的喜爱,大量外销,成为19世纪西方认识、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之一,这充分体现了艺术的认知功能和审美功能。艺术从古至今都有教育功能,人们在享受艺术作品带来的美的同时,意识和行为也在受到艺术家潜移默化的影响。笔者认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艺术作品所带来的政治教化功能,例如《平定粤匪图》和《平定粤匪功臣战绩图》(又称《金陵功臣战绩图》)。《平定粤匪图》共计7幅,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馆,作者是清末宫廷画家仿照乾隆时期风格绘制的战图,其历史纪实价值颇高。《平定粤匪功臣战绩图》,清末画家吴友如编绘,收录了曾国藩、胡林翼、骆秉章、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沈葆桢等48人画像,以及清军与太平天国军交战图16幅,主要采取白描手法,并附注图说。这些绘画作品主要是从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和表彰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出发点进行创作的,一定程度体现了“左图右史”,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国家统一。清末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较低(据相关学者推测清朝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为2-10%[1]),各类以文本为依托的宣传途径效果必然受到民众识字率的影响,而通过描绘镇压战争场面以及“平定”太平天国功臣画像,则能最大程度扩大影响面,起到宣扬战功,警告、规劝、教化民众的作用,特别是对广西、广东等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较深的地区民众来说有极大的威慑力和恫吓力。
二、艺术承载了历史的变迁
艺术承载了历史的变迁。众所周知,广州古称番禺(亦作“蕃禺”“蕃隅”),早年在广州区庄螺岗秦墓出土的铜戈,西村石头岗1号秦墓出土的1件漆奁,象岗山南越王墓里出土的6件铜鼎、1件铜壶和1件铜匜等分别刻或烙有“蕃”或“蕃禺”字样,与史书所记载的南越国都城“蕃禺”互相印证。“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这饱含古风韵味、甚至可以说带有早期广东民歌雏形影子的字句,是出现在广州客村晋墓出土的其中一块铭文砖上所刻写的阳文,查阅相关记载资料以及有关专业人士的观点,该批铭文砖中“广州”字眼应属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现,同时还具有一定的诗歌文学及书法艺术价值。这些古代的艺术精品印证了广州的过去,可谓“字字千金”。
《珠江春饯图》(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绢本设色)为清代南海画家谢观生于道光年间(1825年)赠予他人的临别送行之作。该画属典型的“江岸送别”图式,采用了常用的半边式构图,设色淡雅,画中人物、景物都集中于左半边——珠江沿岸山水气韵秀润,左侧堤岸有树丛、船舶,还有临江告别之人;而在画面右侧珠江江面上,我们可以留意到有个被城墙围绕的小岛,城墙内有庙宇、房屋、树木等。熟悉广州历史的人一眼就可辨认出,此岛便是海珠岛(又称“海珠石”,广州海珠区得名于此),根据地方志的记载,此岛上曾建有海珠寺、李忠简祠和探花台,清顺治年间又曾在海珠岛上修筑炮台,这和此画互相印证。随着城市的发展,1931年,国民政府广州当局认为海珠石造成该河段水流湍急,对行船不利,于是决定炸毁海珠石,填河开路,该马路被命名为新堤大马路,即是现今的沿江西路,海珠石自此烟消云散。在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珠江春饯图》忠实地记录了城市的昔日面貌,艺术承载了历史的变迁,不仅包括思想、风俗、名称的变化,甚至还包括了自然地理地貌的变化,真是印证了成语“沧海桑田”!
总书记在2018年考察广州永庆坊时提出:“让城市留下记忆”。颇受关注的广州恩宁路永庆坊旧城改造工程,将城市的过去和现在很好的连接在了一起,现在的永庆坊既有雕花彩塑、满洲窗、趟栊门等传统广府元素,也有餐饮娱乐、创意办公、文艺演出等现代气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老旧街区的风华不再,但在处理新旧关系上,该改造工程不同于其他城市热衷的“推倒重建”做法,而是很好地秉持了“修旧如旧、新旧融合”的城市微改造精神,微改造模式基于原来外轮廓不变的前提进行建筑立面更新,让“新”“旧”充分碰撞融合焕发出新的活力,城市艺术的形式更加多彩、多样,行走在永庆坊,就如同站在过去看现在。
三、关于城市发展的思考
在过去的几十年,全球化让全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留意到越来越多的大都市呈现出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现象,都在以相同或者近似的几种模式建设城市,在追求潮流的同时却忽视了塑造特质,其后果便是摒弃了各自城市本来拥有的灵魂与精神。以体育场为例,众所周知,全国各地都有大型综合体育场,然而国内体育场的设计大多数追求“大、洋、怪、重”,特色并不鲜明,这也算是千城一面、千篇一律的具体表现,究其原因,与建设时的时代发展背景息息相关,许多被命名为“某某奥体中心体育场”的大型综合体育场,基本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建成,主要是为了迎合当时申奥以及全民健身的形势,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因此大多数大同小异。个人认为这些体育场虽然在增加体育设施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未能兼顾到审美性,日后的改造升级空间也非常小。
然而在广州却有两座“与众不同”的体育场——越秀山体育场以及广东奥林匹克体育场。越秀山体育场始建于1950年,位于广州越秀山南麓,镇海楼下方,是广州青年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的人民体育场,特殊之处在于:一是东向不设看台,建有塔状门楼,色彩古朴稳重,线条刚劲有力,因此越秀山体育场与其他体育场的区分度高。二是:三面环山,看台依山而建,视觉上更加干净和更加条理化,观众席距离赛场比较近,且全部呈45度角向下俯冲,当进行足球比赛时山呼海啸、气势撼人,被视为广州足球的“福地”。广东奥林匹克体育场建成于2001年,位于广州天河黄村,虽然它是广东省人民政府为承办九运会而专门建设的,命名模式也与其他“奥体中心体育场”无异,但是在建筑审美层面上却与众不同,甚至被评选为新世纪羊城八景之一。从高处俯视,该体育场犹如两条飘舞相交的绸缎带,有一种由静变动又由动入静的节奏美感。从平地主视,该体育场的顶部曲折起伏、升腾跌宕、浪漫飘逸,既像充满仙气的绸缎带,又像翻卷翱翔的游龙。该体育场自由、浪漫、新颖的造型打破了大型综合体育场传统圆形的设计概念,为国内首创。放眼中国,具有强烈的艺术特点的体育场并不多见,越秀山体育场、广东奥林匹克体育场算是典型代表(其他别具一格的体育场还有南京中央体育场、上海江湾体育场、武汉新华路体育场等,此处不再累赘)。
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艺术可能会影响一个人甚至一座城市的价值观念。在未来的城市发展进程中,如何化解千城一面、文化趋同现象,重塑城市灵魂,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或许充分运用艺术功能处理好历史变迁与时代前进的关系,珍视过去、把握现在、展望将来,能为我们寻找到城市未来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