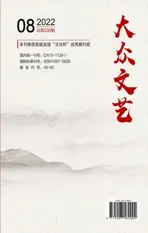试论开高健《裸体国王》人物场景
——以“我”两次大笑为例
2020-07-12南昌大学330031
(南昌大学 330031)
一、引言
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之一,开高健于1957年发表短篇小说《裸体国王》,次年击败大江健三郎著《死者的奢华》获得芥川文学奖。从获奖评语来看,《裸体国王》好评颇多——中村光夫曾称“这是一篇具备新颖构思和有力度、深度的批判精神,并充分发挥了作者优良本性的小说”,佐藤春夫也表示“选题精良、文风诚挚,这才是现在最该受珍视的(作品)”等。
有关该作品的文学研究,池山佑子曾表示日本国内将其解读为“批判社会体制”的论述较多。与此相对应,胡建军也曾称该小说对“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战后日本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本文将从更小的切入点着手——从主人公“我”在小说中唯独出现的两次与性格不符的大笑场景出发,以学生太郎创作的画和“我”贯彻的教育来探究其大笑背后的含义。
二、“我”的性格
主人公“我”是一名儿童美术老师,在小说中一直是处事十分冷静的形象。例如,小说着重描写了“我”对同僚山口老师的态度。在接受了大田创办的美术用品公司的“好处”之后,只要该公司一发售新产品山口就会第一时间让学生们试用,并将试用结果写成报告公之于众。凭着这份“热心肠”,山口在年轻教师及社会上都深受赞誉。然而,“我”却看出“热心肠”的山口其实只是一位“计算名利的野心家”。即是说,“我”并没有受到外界评价的影响,而是通过自己冷静地剖析了山口行为的本质——只为追逐名利。
其次,“我”是一个非常有自我主见的老师。山口介绍了大田的儿子太郎来“我”这里学习画画。“我”秉着一视同仁的态度,拒绝太郎父母接送,要求小孩自己步行来画室。此外,当得知大田邀请自己去参加由他主办的绘画大赛时,“我”回答道:“设奖金可无法获得优秀的儿童画作啊。孩子们都是十分敏感的,会揣测大人的喜好。这样征稿来的只是取巧而作的作品罢了。”对话中,大田不断地提到了利益问题,而“我”却对此抱有抵触心理,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的邀请。可以看出,虽然“我”在心理上对这位“能干的商人”大田十分抵触,但口头上仍旧十分冷静、淡然地拒绝接受邀请。与山口不同,“我”并没有屈服利益的诱惑,是一个能坚持主见的人。
然而,小说后期却出现了两处不符合“我”性格设定的场景——“我”情不自禁地放声大笑——十分激烈地外露出主人公的情绪。本文将以主人公这两处场景为论述中心,探讨主人公“我”放声大笑背后的含义。
三、太郎的画作
太郎自从来到“我”的画室之后,画画一直都在进步。
最开始进入画室时,太郎拿到白纸之后什么都没画。“我”对初次见面的太郎描述为“一具披着由自我本能形成的无感知防护罩的肉体”,就像空白的白纸一样。太郎也不和小伙伴们玩耍,总是一个人对着什么东西发呆。在“我”看来,他只是坐着,仿佛在害怕什么又仿佛什么也感觉不到。
剧情的转机出现在太郎第一次说出自己想要画画的时候。在得知太郎曾在乡下生活过一段时间的第二天,“我”带着太郎去了河边。太郎在河里看见了鲤鱼,对企图逃跑的鱼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我”便就着这个话题和他聊了很多次,有天太郎终于主动向“我”要了一张白纸。那天,太郎仍旧没有画出什么东西,但在他下一次来上课时发生了巨变。当“我”示意太郎放在一旁的手指画颜料瓶时,他将手指径直伸了进去,并用手将整张纸涂满了红色。此时,太郎“画”出的还只是一个单纯的颜色,但渐渐地进步越来越明显——他的画从“一个房子+分散的点”,到“大片的点+粗糙的小孩人像”,再到“用粗笔描绘出一个小孩的模样”。最后,太郎在一个非上课时间带着他创作的五幅画找到了“我”。其中,当看到最后一幅时,“我”放声大笑。
这幅画展现的是同其他四幅完全异样的世界。画的是一个穿着越中裈、在种了松树的护城河边行走的男子。他头上梳着丁髻,腰间别着一根棍子,像士兵般挥着手阔步而行。当察觉到这幅画含义的瞬间,我放声大笑,感到自己的身体都因为这泉涌般的笑劲摇晃了起来。
画中的“裸体男子”正是呼应了小说的标题“裸体国王”。这是太郎在听完抽象的童话故事《皇帝的新装》之后,通过自己的理解将“裸体国王”画成了日本大名的样貌。“越中裈”“丁髻”等日本传统形象其实与真正的西方国王大相径庭,使“我”不禁大笑出声。这是太郎脑海里的国王形象,体现了孩子独有的个性思维。在“我”看来,这幅画体现出太郎是“真正完全消化了安徒生童话”。
在“我”的教导下,太郎从最初见面时画不出任何东西,到一幅单色的画、只有点的画,最后完成一幅完整的画作,实现了质的飞跃。因此“我”在此处放声大笑,除了画作本身带来的趣味之外,也包含了对太郎成长的感慨。山田有策曾表示太郎的这份成长是“主人公‘我’潜入了太郎内心的荒芜之地,帮助太郎让他自己动手开垦”的过程。另外,从小说剧情来看,通过“我”第一次情绪泄露地放声大笑,并伴随“裸体国王”形象的初次登场,全篇小说在此达到了一个高潮。剧情的节奏也更加明朗,一直持续直到文末主人公的第二次放声大笑为止。
四、“我”的儿童画教育
“我”在教导孩子们画画时有一套自己独特的方法。“我”既不会使用任何教科书,也不会提供示范画作,只是通过与他们交流让孩子们加深对一幅画的构思能力。“我”是领导者,指引孩子们走在绘画的道路上。在“我”的教学方法下,“孩子们欢乐地呼喊着,他们笑着,打闹着、幻想着,画室里充满了各类情感最原始的样态”。“我”的教学毫无疑问是取得了成功,并且在太郎身上也有体现。实际上,“我”的这种教育形式是符合当时战后日本“新教育”政策的。开高健于1957年发表《裸体国王》,在此前一年日本社会开始实施了“新教育”政策。贝塚茂树曾在《战后日本教育史》中指出:
1946年5月,日本文部省为教师职业公布了“引导书”“新教育指针”,提出将以“尊重个性发展的教育”作为今后教育发展的重点之一。
1947年3月,日本颁布并实施《教育基本法》。其中第2条指出教育应当做到“尊重学问自由、贴合实际生活、培养自发精神、敬爱自我与他人、通力协作,从而为文化创造与发展作贡献”。
可以看出,日本战后推行的“新教育”旨在尊重个性发展、重视培养创造力。“我”的教育形式正吻合这一点。然而,小说中其他大人的教育行为却未能体现“新教育”政策。例如,同僚山口作为一个“计算名利的野心家”,他的学生们画出的作品带着“无感情的美感”。再如,太郎的继母大田夫人“虽然十分热衷于教导小孩,但结果送来的太郎仅仅是一具什么都没有的肉体”。最后在小说的末尾,以安徒生童话为主题的儿童画大赛的评选会场里“我”的教育方式与其他人发生了剧烈对冲,同时也将剧情推向了最高潮。“我”的第二次放声大笑也在此处登场。
在会场中,“我”看到了一圈都是几乎风格相同的作品,尽是“精致可爱、有条不紊、完美得令人微笑的画”。而最大的问题也正在于这样的“一致”性上。从某一层面来说,选出这些“一致”的画作确实是一次“公平”的选拔。但在“我”看来,实际上这些都是“缺乏理解、失去情感、没有肉体的画”。即,每个孩子独有的特色与天性没能得到充分发挥,画上表现出来的都是大人们所理解、认可的想法——实际上这才是不公平的。
与被选拔出来的画相比,“我”带着的太郎的画着实突出了孩子的个性。“我”认为太郎画的身穿越中裈的国王才是真正的“日本孩子的画”。“我”一直以来追求着画背后的含义,它会受作画者身处地区的风土习俗发生异变,甚至可以说它体现了当地人们独特的思维方式。然而,大田举办的比赛却无视了这一点,导致了这样“一致”的局面。因此,选拔出来的画无法体现出日本的特色和日本儿童的思维。这令“我”十分失望和厌恶。
而这份情感在评审们得知太郎是大田的儿子时,达到了最高潮。当“我”最开始展示出太郎的作品时,遭受了评审们严苛的嘲讽。太郎的画是“我”偷偷带进会场的,评审们只是轻蔑地评价“看过了”“没什么大不了的”“画得真差”。可当“我”告知“这是大田儿子画的”之后,评审们却突然沉默了。如此这般态度的骤变,在“我”眼里定是十分丑陋的景象。
我不禁心生一股强烈的厌恶感,任其代替了发笑的冲动。窗外斜射着流淌进来的阳光宛如一条明亮的小溪,沐浴在阳光里的我再次捧腹、放声大笑。
“我”将代表自身教育成果的太郎画作描述为“窗外斜射着流淌进来的阳光宛如一条明亮的小溪”。面对着会场丑陋的现实,自己与画室的孩子们所代表的“新教育”正如光明般的存在,这样强烈的对比正是令“我”放声大笑的原因。
五、结语
从前文来看,“我”一直是一个冷静思考、有主见的角色,但在《裸体国王》的后半程中却出现了与“我”性格完全不符的两次放声大笑。本文以这两次大笑的场景为出发点,探讨了主人公大笑背后的含义。第一次大笑,既是由于太郎所作的画极具趣味性,也是因为“我”看到了太郎不断的进步和成长。第二次大笑,则是因为面对比赛本身及评审们的选拔方式过于丑陋,令贯彻“新教育”的“我”不禁放声大笑。前者在小说的中后期出现,将剧情推向了一个高潮。后者在小说的最末尾,剧情再次高涨却也在此戛然而止,留给了读者十足的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