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 聪明与笨拙
2020-06-21孟依依
孟依依

第七个仓库
因为强直性脊柱炎,张立宪的背弓得越来越厉害,现在已经不会疼,但基本上失去弹性。有时候他拿手机回消息,手臂往前伸着,为老花的双眼找到一个合适的看屏幕的位置,又弓着躯干,风迎面一吹,他好像能顺势抱住那团风。
2005年底,他创办杂志书《读库》,到2020年3月,《读库》第100期完成。在豆瓣网站上,七成评分高于8分。《读库》每期约30万字,一共3000万字都经由他编校。编辑部扩展到十余位编辑,由读库出版的其他图书上百本,也都由张立宪终审。
《读库》十周年时,张立宪发现读了那么多人的命运和故事后,最大的感触是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他想打破人们对他孤胆英雄式的“造像”,让《读库》去人格化,去老六化(张立宪与数字六有缘,干脆与之结为好友,自称老六),“但是你最后发现这个根本不现实。你在微博上发的一条几十字的小消息,它背后流淌的就是你的基因,躲都躲不掉。你还是必须为它负责,它就是与你相关的。”
索性,就这样了。
2019年十一期间,得知北京的库房不能继续使用,张立宪几经辗转,找到现在这间。11月4日,为了给搬家筹措资金以及减轻库存压力和搬迁成本,《读库》发出求助信,将几乎所有产品八折出售。在一场声势浩大的促销、整理后,2020年4月,四十余辆载重卡车每车拖上30吨书籍、纸张或员工的物品,行驶1200公里,整体迁移至此——这是《读库》第六次换库房,一步步从北京的三环外到四环外到五环外到六环外,最后落脚长江口北边的江苏南通。
这里位于苏州和南通交界处,周围都是农地。天气闷热起来,下午去附近一间临时工房办公室开会时,大家拎着一个西瓜,沿着空无一人的马路走,油菜籽已经收割,稻子还没成熟。
纸箱被堆积在库房里,18组货架3300个货位上码着“读库1906”“巴赫”“莎士比亚”“玄奘”“黄昏”“塞尔达三十年”等等,都是2015年出版的图书。张立宪面庞通红,看起来心情不错,尤其是站在这些货架之间。听作者朱石生说,张立宪昨晚顺口说起到南通收拾新库房,晚上喝多了。

2007年,张立宪办 《读库》 的第二年 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库房最大的问题是消防,这一个门槛就把大多数给我们提供线索的场地否决了。以前我们也是‘惶惶不可终日,纸书的消防标准属于丙二类,要配多少立方米的消防水池,喷淋烟感系统要达到多少,防火分区要做多少……”两天前的电话中,张立宪大概给我普及了10分钟的消防知识,末了讲,“我是个编稿的,按理说何必对丙二类什么的这么了解啊。”
话是这么说,消防问题的解决还是让他大松一口气。除此之外,新库房最让他得意的地方是引进了一套智能分拣系统,一进大门便能看到,黑色的双层传送带尽头连接着一个白色的圆形钢架设备,圆形中间立着一支机器手臂。一位专家看到,说,千万(元)级别的。
“我去过那种阴暗拥挤的、甚至很脏乱差的仓库,我就舍不得我们的书被放在那样的地方,我也看过那种巨无霸式的仓储,感觉书在那里头——当然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矫情——有点没有生命的感觉。” 张立宪说,“我觉得我们的书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只要有这个条件,我是愿意把它放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头。”
傍晚采访结束,他踩着平衡车慢慢滑过去,在自动分拣设备旁边停下来,弯下腰。组装近一个半月的机器进入到测试阶段,张立宪站在那里咂摸一下,说,“我喜欢工业文明。”他起身正准备往前,想起什么似的回过头来笑说,“农耕文明中长大的孩子的迷恋。”
一个做书的
大概到初中为止,能吃上馒头对张立宪来说都算得上一件不错的事。他在河北农村长大,父亲在县城有一份工作,收入不多。家里即使拮据,仍然订阅《旅游》《文史知识》等等杂志,以及专供他读的《中国少年报》和《中学生》。
他的父亲念书成绩不错,直到15岁失怙,辍学养家糊口。父亲始终对知识抱有渴望,后来参加自考、函授,“是真正在学。”读书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后来张立宪读得更多,尤喜19世纪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影响至深。
从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张立宪被分配到《河北日报》,住集体宿舍,有大把空闲时间,打麻将、喝酒神聊。一个朋友经常借医院的救护车,大家开着救护车去图书批发市场买书。
往后几年,他的大学同学、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张斌及刘建宏一同创办《足球之夜》,他也来到现代出版社任副总编,辗转报纸、杂志、电视台、网站和出版社各种传媒形态,各个工种和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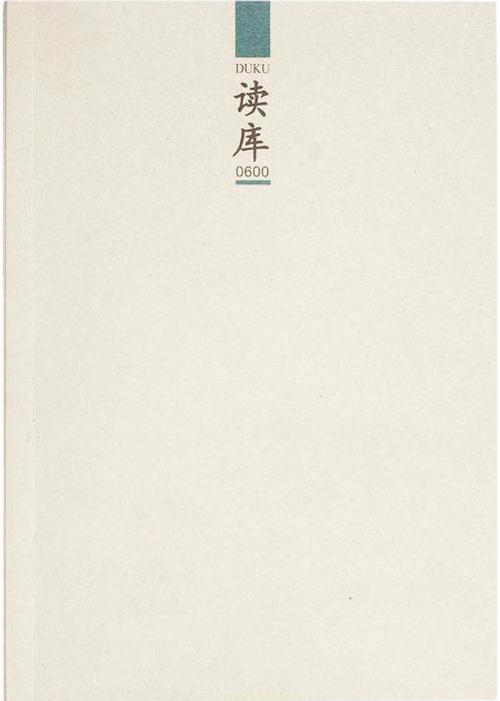
2004年11月28日,紀录片导演陈晓卿在一次水煮鱼饭局上见到张立宪,此前他只看过张在博客上写的文章,“很干净,在里面又从来不吝啬于自嘲,所以给人的感觉特别真挚。”他几乎以一个粉丝见偶像的心态去认识张立宪。
两人之后关系变好,有时候一周有五六天都在一起吃饭。自此陈晓卿认识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都是有点儿古怪、但是很有才华的人”,渐渐有了“老男人饭局”。
也是在那时候,张立宪遭遇了精神危机,许多年后他在“正午故事”的采访中描述自己当时的状态:外表看起来还不错的我……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去做,什么人都懒得见,我想给一个人发短信,这条短信我可能要劝自己两天,才能发出去,就是老觉得自己的生活什么都不值一提,自己拥有的一切都经不起推敲。
直到2005年,张立宪36岁,他在“众神之车”(他的朋友、戏剧导演牟森语,张立宪原本是坐一班大巴从河北前往北京接受一份薪资不错的新工作的,结果在缓慢的大雾迷漫的路途上盘算了人生,决定放弃)上想到了要做书的主意,然后像洪秀全落第之后一样昏睡好几天,产生了许多想法,完全沉浸在那个主意当中,最后诞生了关于《读库》的基本框架——刊载市面上极少见的三五万字的文章,每年六本,外加一本幕后花絮版的内刊。
做《读库》这件事把他从狼狈不堪的精神状态中捞了出来。
很长一段时间里,《读库》的编辑、校对、发行都由张立宪一人完成,库房就是他的家,把印刷好的《读库0600》搬到家里时,他幸福得直哼哼。再往后,“厨房与餐桌之间,仅剩一条羊肠小道可供驰骋;电视机与沙发之间,垒起了一道半人高的长城,六嫂便在长城上用书堆砌起一个坐档,比《权力的游戏》里的铁王座舒服多了。”他每天在家里写信封、装包裹,然后拎着两个袋子去邮局寄书。几天后,读者们就收到了“大白胖”——十几年前,把书包得那么厚实属少见。
他并没有宽裕的资金。他后来见到一个人,记得曾对此人怀恨在心,“因为合同中的一笔钱,两万块以内的,他应该给我,但没有给,我的月供就供不起了。别人也欠过你钱,可是那時候就是让你一下子陷入痛苦、陷入窘境。”没钱了,他就去给朋友的一个网站做主编,每个月能有一两万工资。
“然后又投入到《读库》中吗?”
“只要能付月供,就还是做《读库》了。”
打捞一部分碎片
《读库》自有它的准则,当然这来自张立宪。
他为《读库》制定过“三有三不”准则:有趣、有料、有种;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办《读库》的第二年,张立宪接受过《南方人物周刊》采访。他说,中国有多少历史残片都在似是而非中,一定要尽快去打捞,因为属于我们自己的记忆很快都会被淡忘、被湮没,难道不该为我们亲历的这个大变革时代保留一些细节和标本吗?
作家姜淑梅60岁开始学写字,七十多岁写文章。姜淑梅的女儿艾苓在绥化学院讲授写作,有时候把姜写的文章发给编辑朋友,但得到的大多数回复都说是“老年人写作”。艾苓又辗转联系到一家杂志,对方说,从来没有一个新面孔凭空出现,让她帮母亲写一个小散文介绍一下。到了终审,艾苓的散文留下了,姜淑梅的没有。
她于是把那些文章发在博客里,在一家杂志社供职的马国兴看到了,“文字很干净,没有说辞,没有成语,就事说事”,他一直订阅《读库》,心想合乎《读库》的选稿准则。他找到艾苓,等到姜淑梅写完一万三千字,打包发给张立宪。暑假发去,8月份得到张立宪回复:拟用。次年4月刊登在《读库》上。
姜淑梅大受鼓舞,“从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往前跑起来了”。艾苓呢,也在《读库》上发了《咱们学生》,写在绥化学院遇到的学生们。过去了六年,张立宪仍在综艺节目《圆桌派》中提到:“相比于清华北大的学生,大部分二本三本四本的学生,你说他们认命吗?要我我也不愿意,的确那种上升的空间、机会又很少,他们那种挣扎,远远不是清华北大学生能体会到的。”而他意识到,这部分才是大多数。
张立宪自己也写,写的时候他才能把自己整理清楚,“我可能只有本事用文字来表达。”
2020年5月底,张立宪做了一次阶段性总结,列举《读库》十八条编辑方针,其中一条是:“故事有什么魅力?我们看那么多故事,图的是什么?正如一部伟大的战争电影,首先,它一定是反战的;其次,它是告诉人们在生死之际,一个体面人会怎么做。我们在别人的故事中倾洒自己的笑与泪,就是要看看在某种极端情况下,体面人是怎么做的,以及警醒自己不体面的行为是什么。当面临类似情况时,内心可以调用一种行为模式或情感反应,或者说,人格养成就在其中。”
他仍在继续拍摄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家赵荣琛的关门弟子,青衣演员。2006年,张立宪带着摄影师开始拍,2010年他们曾从6万张照片中挑选出几百张出版,包括跟张火丁去各地演出拍的、租下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舞台连着五天拍的、进到后台拍下的演员另一面……取名《青衣张火丁》,它更像是一次程派大戏的展示。
拍到现在,照片的数量多到他已经记不清。
“它应该存在。这跟京剧式微不式微没关系,因为没有的话,会感觉缺了那一块。” 在14年的拍摄中,张立宪与张火丁本人的接触寥寥无几,但他向《经济观察报》描述过一个场景,是《锁麟囊》中张火丁上场那刻:舞台装置完毕,灯光调好后,先暗下来,再亮起时,薛湘灵从后台袅袅婷婷出来,唱了一句“怕流水年华春去渺”。张立宪坐在台下,几乎流下泪来。
他曾经讲到年龄增长带来的美学观念的变化:我不愿意用聪明来表达聪明,我不愿意用热情来表达热情,而是用笨拙表达聪明,甚至用一种冷静来表达我的热爱。
张立宪毫不避讳暴露自己的笨拙和努力,他曾经在《被认真对待的感觉》一文中写道:一些人不认真,是因为他不敢认真,他怕自己的认真反倒成为一个笑话,所以就做出一副不屑认真的样子,其实是一种逃避……“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这是钱钟书先生说的。认真也很较真,许多人认真不起。
“脉脉含情的默契”
被张立宪暗地里称作《读库》作者群中“70后四大金刚”之一的作家刘勃自嘲,“基本上我应该就代表《读库》的一个下限,就是轻浮到这个样子,不能再轻浮了”,憋不住用上些网络词汇,有时候张立宪会把他文章中过热的东西摘掉,“如果我们写一个东西要为未来负责,希望它有更长久的生命力。”
2000年左右,刘勃正要从南京大学中文系写作班毕业的时候,“很迷茫,整天在BBS泡着。”“那个时候我们还挺狗屎运的,活得那么稀里糊涂,基本按照自己的兴趣瞎搞搞弄弄,居然日子也过得不是特别那个(糟糕)。”
毕业后,刘勃到南京三江学院任教,如今他在《读库》先后发表过将近20篇作品,出版了八本书。当然,这些不能算作科研成果,也不能用来评职称,他至今仍是讲师。当然,他也不觉得自己汲汲于这些。
“我写东西其实就是我好这个,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有没有意义,但是好这个我不把它做出来,我难受。然后我就这么写了,然后有人看,啊,我非常地开心。”刘勃说,“《读库》可能也有这点意思。”
BBS时代,张立宪的形象是“京城交际花”。导致后来见了面,刘勃反而不觉得张立宪像他想象的那么能说,反倒是一种让别人愿意相信他、愿意把东西交给他的天然气场凸显出来。

新库房18组货架3300个货位上放满15年里出版的图书 图/江建华
“他从来不会对命题指手划脚,”朱石生说,他与《读库》一起完成了医学大神系列丛书。朱石生给张立宪发了第一批三篇稿子之后,继续写、继续发,写到南丁格尔的时候,张立宪说,要不咱做一个丛书吧,就按目前这个体裁,一本大约五六万字。朱石生说行,列好名单,14位人物。张立宪说好。
朱石生居住在加拿大。四五年间他们邮件往来,直到最近张立宪才知道对方的年龄、性别。甚至书已付印,出版合同还没签,等着朱石生回國再补上。
在北京的读者见面会上,张立宪说跟朱石生的交往靠的是“脉脉含情的默契”。“或许就是这个意思”,朱石生揣度,“他给我的印象是:你们作者负责写,按你们自己的意愿写。我负责选,看到好东西我就发。写得不好就搁着。就是说,把作者当作者对待,而不是因为自己有发表平台,就拿这个作权柄,把作者当文字工匠对待。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懂文字、珍惜文字的人才会有的态度。”
为了认识一个人,张立宪会大量阅读对方作品,陈晓卿通过张立宪认识了许多新朋友,甚至重新认识了身边原来认识的人,“所以说老六的个人魅力,其实是他特别善于与人沟通,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倾听者。”
或许也因此,《读库》和它周围的人维持着一种恰如其分的友谊。
《读库》在北京的库房旁边,曾造过一栋房子,由在《读库》出过书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博士毕业生袁牧设计,农村草台班子建筑队搭建,用作办公楼。完成后,张立宪开玩笑说要给袁在那儿立一个碑,注明是他的作品。袁牧说好啊好啊,这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一个没有甲方干涉、完全被信任的,虽然细节有瑕疵,但是他最满意的。
“不管怎么样,这条路上还得继续跑火车呢”
2019年11月,在北京鼓楼西剧场,《读库》按例举办年会,四下无灯,只台上给两束顶光,张立宪和白岩松坐在一大块红色布景前对谈。
张立宪讲到2019年是《读库》遇到问题最多的一年,“被敲诈,被暗算……再一件一件去面对、去申辩、去解决,可我本来就是个编书的啊。有一段时间,《读库》真有不能再做的可能,我本来以为自己可以比较轻松地接受这个现实,反正自己饿不死,以团队兄弟们的能力也能找到新的饭碗,不能做就不做吧。可就是在大概两个月前,就在鼓楼西这个场地,我在台上,台下有一位大姐,她说为什么《读库》出得这么慢,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是不是不做了?我当时本来想回答她,确实不能做了。可这几句话还没说出口,突然就有了一种心如刀割的感觉。我就没再说。《读库》不能不做,死活也得做下去。如果《读库》真不能出,我自己也要按现有的固定周期把它先编出来,哪怕暂时不印、不出版呢。”
那一年《读库》年会的主题叫“不管怎么样,这条路上还得继续跑火车呢”,这句话出自张立宪的女儿最爱看的动画《托马斯和朋友们》,“我觉得不要说我,可能所有做事情的人,他内在的精神内核就是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本身是人之常情,我觉得是颠扑不灭的真理。我们老说一个身患癌症的人多么热爱生命,精神多么强大,他必须得强大啊,要不他不就死了,对吧?”
过后再谈起那件事情,张立宪说:“人是不可能掌控一切的。我平时也会有这种评估,《读库》还能不能活下来?但是真的事到临头,你发现你舍不得它不做。”
他真的和书打交道太久了,乃至妻子怀孕七个月他们去拍孕照时,他突然想到——一个孩子从孕育到出生,原来跟一本书一样一样的,每个流程都能高度对应。想到这里,特别想在妻子的大肚皮上签下曾经写过无数遍的:可付印出版。
“他选择的路,并不是一条轻松的路,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逆水行舟。但他的个性是‘别给人添麻烦,压力再大他也不会诉苦卖惨。”朱石生说。
陈晓卿与张立宪结交多年,也从未听他说起如何难。2012年7月21日,北京暴雨,《读库》在房山的库房被冲毁,他费尽心力积攒的书、纸不告而别。陈晓卿想去帮他,他说没事儿,这有什么事儿,我们从头再来。
2019年底的求助信息一发出,陈晓卿转到自己朋友圈,大概四五个小时里,有各行各业的朋友给他打电话,说北京有闲置的库房,想捐给张立宪。陈晓卿一一转给他,后来他专门打电话说:“你不用再告诉我啦,我不想用情义来换取这个,我们是一个正经的出版公司,我还是希望用商业来解决商业的问题,不想用友谊来解决商业的问题。”
他总是信心百倍的样子,这大概是他从大学同学张斌那里学来的——要让人放心、踏实,会罩人,也罩得住人。
你放低一点,放低一点
张立宪现在稍微老一些了。
按照60岁的退休年限,51岁的张立宪还可以做9年,那么“再编个一两百本书,眼睛就看不清了,脑子就没那么好用了。如果有一本书纠缠时间太长,就不能和它纠缠了,除非它格外值得,死缠烂打好几年你都愿意”。有时候他又把一天当作一块钱,那么还有三千块钱。有一次与《读库》的员工开会,他突然说到自己的这种记账方式时,“不无嫉妒地看着旁边生于1996年的同事,想他还可以战斗小40年,就是一万四千块,“壕”啊。又自我安慰:哼,他得用五年时间才能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成熟的编辑,这就要花掉一千八;他还要安身立命成家立业,这又得花掉好几千……于是又不无心疼。但这些万元户是没有什么紧迫感的,所以大家哈哈一笑散会。

张立宪 (前) 与陈晓卿 图/受访者提供
他就想,人生不是匀速的。尤其是,死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衰老是瞬间的事。
“就像你看到这个桌子上有一支笔正在往周边滚,年轻的时候你伸手一抓就把它抓住了,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抓不住了,眼睁睁地看着它滚。或者我正坐在候车室椅子上看书,抬起头看一眼我的车子是不是要检票了,年轻时你一抬头一睁眼就能看到,然后你低头继续看书,等你到了这个年龄,抬头的瞬间眼睛是花的,要调整半天才能看清屏幕上的字,再低下头去看书,又得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整。你就老了。”
2017年他生了一场病。用增强CT看到的脑部小阴影,导致他晕眩,失去平衡能力,尤其是劳累的时候。那时候,妻子怀有身孕。他不敢告诉妻子,每天自己悄悄去社区医院输液。直到现在,妻子仍然不知道这件事。
他在成长过程中常常会想,父亲在这个年纪是什么样的,然后发现没有办法用父辈的那种生活、人生轨迹来规划自己。也是在那一年的年底,父亲去世了。
张立宪看到家里一本平时没人翻的小册子,是父亲为村子里每个家庭梳理的家庭成员关系,“爷爷叫什么,奶奶叫什么,类似于家谱一样。我们村子有几百户人家,他干这个,可能就是平时寻开心。”父亲去世后,朋友们来为他守灵,聊天时翻出这个,很多人看到自己的家庭,忍不住拿手机拍一张照片,说要记住自己家是什么樣的。虽然他不觉得这会起多大作用。
他就想,父亲做了一件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对这个村子也毫无价值,只是他自己高兴。张立宪原先做书的理念一直是让书像书,看到父亲的小册子,他觉得要让书更像书,“所谓的艰涩、所谓的冷僻,也不再顾虑,就这么做吧。你要喜欢,读就是了。”
你看,年龄对于一个编辑来说也不全是坏事。
陈晓卿觉得《读库》带给老六的比老六带给《读库》的可能会更多,“《读库》给了他快乐。”
认识张立宪之前,陈晓卿除了与电视行业的人一起吃饭,就是与拍摄所在地的官员,“互相说些仰慕的话。”“和老六在一起之后,所有的这些都发生了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他们以揭穿对方和损人为目的,他们有一句名言——瞧您又把自己当人了。
每当陈晓卿大谈纪录片的宏大主题,张立宪就说,你放低一点,放低一点,你做不了这样的事情,你作为一个专业人员,只做自己专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