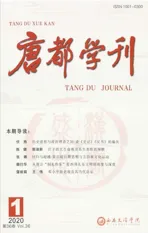汉画像胡人圆形“黥记”说献疑
2020-06-04张庆路
张庆路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在以往匈奴史的研究中,匈奴与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关系,是学术界比较容易忽视的面向。汉代关于匈奴的文字记载主要集中于《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后汉书·南匈奴传》,这些资料已被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进行了透彻的解读。除了文字史料之外,还有图像资料。汉代画像石、画像砖等图像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也刻绘了很多胡人,既有真实描绘,也有想象夸张。
关于汉代画像石中的胡人问题,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无需赘举。一些画像石上的胡人脸上有圆形图样,向来多认为是汉人所施予的黥记。通过转换研究视角与扩大史料范围,我们认为汉代胡人脸部的圆形标记可能是欧亚草原民族的古老习俗,与古代中国黥面所体现的刑罚意义大不相同。不当之处,尚乞方家叱正。
一
画像石上有各色各样的人物,如何准确地辨识出胡人,很重要的依据就是观察人物的外貌特征。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图像史料之中,胡人外貌大致具有以下特征:(1)头戴尖顶帽;(2)呈现高鼻、深目、高颧、多须的容貌;(3)发型多表现为披发或椎结状。这些判定标准为我们研究胡人图像问题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依据。至于如何去界定图像上的人物是否为胡人,或有一定的争议。然而,在一些画像石上,铭刻有标示画面人物的榜题,如“胡王”“胡将军”“胡奴门”等字样,那么画中人物无疑是胡人。
1984 年,河南省方城县杨集乡于庄村发现一方墓门柱石画像,图像右上方有“胡奴门”三字榜题,可知其是胡人。画像中的胡奴侧立,一只手握钺,扛在左肩上,另外一只手持彗,彗立在身前。画面中的胡奴高鼻多须,左脸颊上有一个圆形图案,头上有稀疏的线条,象征着头发[1]。学者认为胡奴脸上的圆形图案是统治者对奴隶施加的黥面刑罚,所以是一种黥面记号[2]。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匈奴战斗的时候,“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3]。同书《汲郑列传》记录汲黯奏言汉武帝,“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匈奴人把掳获的汉人当作奴婢役使,汉人也奴役流寓在境内的胡人,这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1967 年出土于山东省诸城县前凉台村的东汉汉阳太守孙琮墓有一幅胡人图像,画面的上边部分是一幅髡笞图,一群官吏围绕着几个或站、或跪、或坐的披头散发的羌人,有的披发之人似乎要被削发和笞杖[4]。汉阳是东汉的西北边郡,郡境之内有羌人,孙琮墓中随葬惩罚羌人的画像石,以彰显墓主生前的武功。画像中处罚羌人的一种方式是剔去他们的头发,“胡奴门”画像石中胡人稀疏的头发或许也是如此。
山东泰安岱庙的石柱上也有一个站立的人像。头戴微前弯的尖顶帽,帽后有一个向上弯翘的装饰,左脸颊也有一个圆圈图案,侧面脸部凹凸有致的线条体现出人物的高鼻深目,双手持彗。通过尖顶帽与鼻眼特征,可以断定为胡人[5]。 这一圆形标记的胡人造型,与前引河南方城的“胡奴门”画像石非常相似。
脸上有类似纹面的异族图像在先秦时期也有例子。1980年在陕西省扶风县召陈村西周宫室乙区遗址内发掘出两件蚌雕人头像。这两个人头像都是长脸,高鼻深目,窄面薄唇,头戴被割掉的尖顶硬高帽。其中一个头像右侧脸残缺,另外一个头像的脸颊各刻有一个蝌蚪状的纹面,头顶刻有一个(巫)字。雕像没有蒙古人种的相貌特征,很可能是塞种人,说明公元前8 世纪,中国中原已与中亚地区有了接触往来[6]。但是,饶宗颐先生认为这白色人种是月氏人,刻在头顶的与西亚刻在女神肩上的符号一样,是一种西方的习俗[7]。学界认为月氏人属于吐火罗人的一支[8]。

纹身是相当古老的身体装饰风俗,在古代中国的周边地区,很多民族都有纹身的传统,比如《后汉书·东夷传》记载弁辰“颇有文身者”,倭国“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文左右大小别尊卑之差”。古代日本男人不但纹身,而且黥面,以此区别尊卑等级。
先秦时期,中国境内也有一些族群有纹身现象,《礼记·王制》记载东夷“被发文身。”东南方的越人也盛行纹身之风,《春秋穀梁传·哀公十三年》:吴国“夷狄之国,祝发文身。”《史记·周本纪》:周朝古公亶父的儿子太伯、虞仲为了避位,“往如荆蛮,文身断发”。越人纹身通常纹在脖颈、手臂、背部、腿部等,这种身体艺术源于图腾崇拜,寄寓着一种荣华富贵的观念[12]。

“单于爱之”这句话揭示出不是所有汉使都去节黥面,匈奴这种看似无礼的要求,旨在希望汉朝使者认同自己的文化习俗,否则没有资格入帐见单于。匈奴与汉朝长期频繁的接触,肯定了解黥面在汉朝是一种刑罚。但从上述故事中可以看出匈奴以黥面习俗为荣,并不感到羞耻,所以其黥面的故俗并不是来自华夏文化,而是自身固有的传统,如同古代倭国男人黥面。
至迟自西周开始,中国北方戎狄便有在脸上刻画符号的纹身习俗。迄至汉朝,胡人脸上也有圆形纹面。两者之间不可能毫无联系,不排除纹面是中国北方戎狄部族的古老传统,而汉朝的匈奴又继承了这项习俗。
二
中国北方毗邻欧亚内陆草原,先秦时期的戎狄等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与欧亚草原之间长期保持着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17]。匈奴始终活跃于欧亚草原东部地区,其纹面习俗会不会与欧亚草原有某种内在联系呢?
新疆拜城县克孜尔石窟第224 窟有一幅壁画,年代是6—7 世纪的唐代,画中一位辫发突厥男子的脸颊、下巴有圆形纹面图样,他正在拿刀作剺面之状[18]。在突厥的习俗之中,剺面之俗应用范围颇为广泛,不仅用于丧葬,而且用之于送行,亦可作为诉讼冤情的表示[19]。这种剺面习俗在欧亚草原游牧世界延续甚久,起源于西亚伊朗一带,再由斯基泰人东传入蒙古草原[20]。新疆阿斯塔纳汉唐时期的古墓中发现一些死者口含波斯金银币,这种墓葬中的西方因素无疑说明古伊朗与西域之间存在经济交流[21]。
1985 年,新疆博物馆文物队在新疆且末县扎洪鲁克墓地发掘了一男三女共四具干尸,其中的一男一女的脸上有绘面,图样像羊角状,是用雄黄、雌黄、铅黄及赤铁矿绘成的纹面[22]。新疆扎洪鲁克89QZM2 墓有纹面现象,该墓主是一位老年妇女,前额就绘有一个扁形圆圈图案。尉犁县营盘遗址墓地、鄯善县苏贝希墓地发掘的古尸中也有绘面现象,其中苏贝希墓地的部分男尸纹面是几何形[23]。由此可见,这种圈类纹面文化在西域一带盛行。
现在高加索一带的达吉斯坦、格鲁吉亚等地居民仍然有在脸上纹饰圆形图案的习惯,他们声称是自古以来的固有风俗[24]。西亚伊朗草原地区与中亚西域一带的斯基泰人、塞种人等族群之间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可能共同操着东伊朗语或北伊朗语,学界统称之为“游牧伊朗人”[25]。所以西域地区的纹面很可能与这个地区长期流行的剺面习俗一样,都来自于西亚早期游牧伊朗人的一种文化传统,然后再向东传播至中国北方草原而为匈奴所继承。足见中国古代西域地区一直深受西亚游牧伊朗系民族文化的影响,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扮演着中转站的角色[26]。
有关匈奴的语言及族属,学界普遍倾向认为匈奴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或蒙古。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指出匈奴语与阿尔泰语有互不相容的地方,并且另辟蹊径,用叶尼塞语来解释匈奴语,得出匈奴语不属于阿尔泰语系而属于叶尼塞语的结论[27]。另外,有学者提示匈奴与游牧伊朗人之间有紧密的关系。关于匈奴单于号“冒顿”的含义,德国学者Muller 认为这个词语实为伊朗语,是“火神”的意思[28]。这些讯息告诉我们,在解释匈奴语言之时,不应完全从阿尔泰语出发,也要考虑到其他语言解释的可能性,亦透露出匈奴文化之中存在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
在匈奴族名来源问题上,学界一直有争议。值得留意的是,岑仲勉认为波斯《火教经》所提到的hvyaona人应该就是汉字文献“匈奴”名称的来源,匈奴与伊兰民族关系密切,匈奴文化深受西亚波斯文化的影响[29]。孙次舟也有类似的见解,认为匈奴原本是西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后来向东迁徙至中国边境[27]。
汉代画像石中胡人的外貌形象经常是头戴尖顶高帽,而这是斯基泰、塞种等游牧伊朗人的典型装扮,所以匈奴文化中有不少早期游牧伊朗人的文化成分[5]236—245。在蒙古国发现的诺因乌拉匈奴墓葬中,出土了两件人物像的毛毡织物残片,所绣人物与斯基泰人的金银器皿及陶器上的人物一样,足见匈奴与西域之间密切的经济联系[30]。
匈奴早期,其西边河西走廊地区居住着月氏与乌孙两个游牧族群,更西北的阿尔泰山、准噶尔盆地一带则是塞种人的活动区域。这些族群属于游牧伊朗人,由于地缘接壤,匈奴与之接触往来,受其文化影响,这是应该可以理解的事。后来匈奴控制西域,并设置僮仆都尉来管理西域,西域胡族成为匈奴的成员。匈奴单于冒顿曾经在月氏为人质,后来逃归匈奴,借鉴了月氏的做法,训练自己的骑兵[31]。匈奴最终击走月氏,月氏部分部落浑邪部与休屠部加入匈奴,成为匈奴的一部分[32]。所以匈奴政权内部有不少来自于早期伊朗系游牧民族,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们文化的熏染。
汉代以降,我们仍然能够找到纹面的少数民族。唐朝时期,在云南徼外,“有文面濮,俗镂面,以青涅之”[33]。宋代人范成大记录海南黎族女性,“女年将及笄,置酒会亲属女伴,自施针笔,涅为极细虫蛾花卉,而以淡粟纹遍其余地,谓之绣面女。”[34]黎族女子成年的时候,在脸颊刺上虫蛾花卉。明代人邝露记载广西壮族丁妇,云“黔面绣额,为花草、蜻蜓、蛾蝶之状。”[35]时至今日,云南独龙族仍有纹面的女子。
河南方城“胡奴门”画像、山东岱庙胡人画像的胡人脸上都有圆形图案,学界多认为是汉人对其施以黥刑的结果。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种观点,但不妨碍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重新解读这个问题。出土的先秦时期的北方戎狄人物像脸部或身上都纹有符号,尤其是甘肃灵台白草坡的西周人头銎钩戟,这个人头像的纹面与汉画像石上的胡人圆形图案很接近,很难说两者毫无关联。
西域长久以来盛行纹面,这是受到西亚游牧伊朗人的影响,然后向东传播扩散,继而匈奴吸收并继承。根据学者的研究,匈奴的语言、族属及族名来源、经济活动等,都与西方早期游牧伊朗人有着密切联系。随着匈奴帝国的崛起与扩张,很多来自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的伊朗系游牧民族加入匈奴,成为匈奴的一分子,他们的纹面传统自然而然地渗透进了匈奴文化之中。
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欧亚草原各游牧人群之间有着高密度的文化与政治接触,各个游牧人群所建立的政治体之间极具相关性,从而可以保障欧亚草原独特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能获得连续的传播与发展[36]。早期游牧伊朗人、匈奴人和突厥人先后共同分享了纹面文化传统。一些纹面胡人后来进入华夏农耕社会,汉人画工石匠把这个外貌特征如实地凿刻在石头上,流传至今,以至于学者认为是黥记。
综上所述,汉画像石上的胡人脸上圆形图案不一定是汉人所施予的黥刑记号,而是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一项古老的传统习俗。有鉴于此,我们在解读画像中的胡人资料之时,不能单纯地站在华夏文化的立场去阐释,而对欧亚草原传统的敏感与自觉,有助于我们对这些史料的再阅读,从而赋予孤立史料以全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