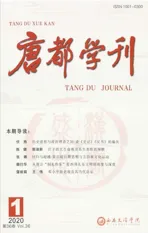柳宗元的“囚居”意识与山水描摹
——以《囚山赋》与《永州八记》为中心
2020-06-04刘城
刘 城
(广西教育学院 文学院,南宁 530023)
唐元和九年(814),因永贞革新而被远贬的柳宗元,已在湖南永州度过了九年的时光。回京的无望,多年的谪居生活,让平时颇能致其暂乐的山水在柳宗元眼中也逐渐变得逼仄、压抑,为此他颇为哀怨地写下了《囚山赋》:
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踊夫波涛。纷对回合仰伏以离迾兮,若重墉之相褒。争生角逐上轶旁出兮,其下坼裂而为壕。欣下颓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沓云雨而渍厚土兮,蒸郁勃其腥臊。阳不舒以拥隔兮,群阴沍而为曹。侧耕危获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劳。攒林麓以为丛棘兮,虎豹咆代狴牢之吠嗥。胡井眢以管视兮,穷坎险其焉逃?顾幽昧之罪加兮,虽圣犹病夫嗷嗷。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1]170—171
自然环境如此恶劣、荒蛮,令人恐惧,让柳宗元产生了此地如牢笼一般的深痛感悟,并发出“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之叹。
章士钊曾敏锐地指出,同是面对着永州山水,柳宗元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情感,其于《柳文指要》中云:“将《永州八记》与《囚山赋》对读,同一地也,而所处者感情之向背,如此其风马牛不相及。”[2]59随后,章氏又补充道:“读《八记》而乐山显,读此赋而囚山成。”[2]59章氏看到《永州八记》中的山水之乐、《囚山赋》中的山水之惧。殊不知,前者所“乐”之山水,后者所“惧”之山水,虽相异,却都是柳宗元寓永州期间抑郁之情的投射外化。只不过《永州八记》的情感是曲折婉转地流出,“乐”山水之中掩藏着难以抑制的哀愁怨恨,而《囚山赋》的情感则是不假修饰地直接宣泄,“惧”山水之时终把数年被逐弃而不得出的愤懑呐喊而出。二者殊途同归,其根源乃柳宗元被贬永州之后所产生的“囚居”意识。
《永州八记》作为柳宗元散文的代表作,其山水描摹的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之地位,学界已有充分研究及定论,仅中国知网就收论文近八十篇。关注《囚山赋》的专文却仅一篇[3]。而联系二者谈及柳宗元的山水描摹,经林纾简述之后,似未有专文论之,故本文欲加以深究,并借此探讨二者所蕴含的柳宗元之“囚居”意识,以及这种意识对柳宗元山水描摹的深刻影响。
一
柳宗元21岁进士及第,登博学宏词科,在朝任集贤殿正字、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32岁就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而进入当时改革派的核心圈。但使其“骤升”也致其“痛贬”的“永贞革新”,让他开始了一生的噩梦。贞元二十一年(805),太子李纯即位伊始即痛贬“八司马”,柳宗元出为邵州刺史,未渡长江又加贬永州,“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闲职一任就是十年。从一名朝廷新贵贬谪至“蛮夷”之地,宪宗皇帝对革新派的不赦宥,回归中央朝廷的遥遥无期,对立志“颇慕古之大有为者”[1]2192,欲“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1]1955的柳宗元来说,无疑是最为沉重的打击。
被贬往永州后,“悔念往咎”,柳宗元把自己定位为“负罪窜伏”[1]1的囚徒。虽然朝廷的罪罚并未让他真正屈服,但柳宗元却是极为刻意地把“罪”“罚”“出”“谪”等字嵌入到永州各时期所写之诗文中,有意无意地暗示着自己的罪人身份,而由此引发出自己作为朝廷“罪囚”而被拘禁、关押的“囚居”之慨:
由上表可见,柳宗元自元和元年赴永州任司马一职始,直至元和十年被诏还朝,其每年所作之诗文中均有“罪囚”身份的自我设定、强调以及对“囚居”生活的渲染。其中,33篇文章之中有28篇属于书信文体,占85%。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云:“详总书体,本在尽言,所以散郁陶,托风采;故宜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也。”[4]书信一体,其要旨在于尽情倾吐己意,抒发积郁之情,“除了那些纯属应酬性的往来书信以外,它总是具有一定目的和为了某一需要而写,而且是希望在思想感情上与对方有所交流,以引起对方的响应或同情。正因为这样,我们可以从书信中,比较多的看到生活的真实和思想感情的真实”[5]。在柳宗元的书信之中,多有着“罪囚”形象的自我塑造和“囚居”生活的渲染,这无疑是柳宗元寓居永州十年最为真实的情感体验,甚至可视为他当时的情感“底色”。正因为如此,柳诗中常出现哀鸣的“羁鸿”[1]2903,独自“响幽谷”的“羁禽”[1]2908以及“畏漂浮”的“羁木”[1]2892,不外乎是这种情绪的投射外化。
二
“罪囚”身份的自我设定,因“独被罪辜,废斥伏匿”[1]1072而出现的“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1]1092-1093的世态炎凉,重见天日遥遥无期,让柳宗元滋生了一种遭朝廷、世俗所摒弃的痛苦。贬所迥异于中原的蛮荒之景,更加重了这种遗弃感,以致在其诗文中“窜”“逐”“废”“弃”等字反复出现:
今身虽败弃。(元和元年,《上严东川寄剑门铭启》)
废逐人所弃。(元和元年,《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亲故遗忘,况于他人。(元和元年,《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
则予之弃也,适累斯人焉……以予弃于南服。(元和四年,《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
除弃废痼……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元和四年,《寄许京兆孟容书》)
自遭责逐……凡人之黜弃……自以罪大不可解。(元和四年,《与杨京兆凭书》)
以宗元弃逐枯槁。(元和四年,《上桂州李中丞荐卢遵启》)
弃逐久枯槁。(元和四年,《构法华寺西亭》)
远弃甘幽独,谁云值故人。(元和四年,《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
门有野田吏,慰我飘零魂。(元和四年,《种仙灵毗》)
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元和四五年间,《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幸以废逐伏匿,获伸其业。(元和五年,《上江陵赵相公寄所著文启》)
盛德大业,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废锢摈死,而犹欲致其志焉。(元和五年,《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
受放逐之罚,荐仍囚锢。(元和五年,《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
忧闵废锢,悼籍田之罢,意思恳恳,诚爱我厚者。(元和六年,《与杨诲之疏解车义第二书》)
某负罪沦伏,声销迹灭,固世俗之所弃,亲友之所遗,敢希大贤,曲见存念。(元和六年,《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
独弃伧人国,难窥夫子墙。(元和七年,《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
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吊影,追咎无既,自以终身沉废。(元和七年,《上岭南郑相公献所著文启》)
卒就废逐,居穷厄。(元和八、九年间,《与顾十郎书》)
自遭斥逐禁锢。(元和九年,《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
罹摈斥以窘束兮,余惟梦之为归。(时间不详,《梦归赋》)
独被罪辜,废斥伏匿。(时间不详,《答问》)
万受摈弃。(时间不详,《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时间不详,《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
在此种境况下,柳宗元“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1]1601,外出游览以抒其情,写下了诸多山水诗文,尤其是以《永州八记》为代表的山水游记更是成为中国山水文学的巅峰之作。


可见,即便在如《永州八记》般精致描摹山水之美的作品中,柳宗元虽发出了“乐居夷而忘故土”[1]1899之叹,但永州诸景更多地寄寓着他的身世之慨,投射有柳宗元的情感印记,正如清人林云铭在《古文析义》卷5中所云:“永州诸记多描写景态之奇,与游赏之趣……盖子厚迁谪之后,而楚之南实无一人可语者,故借题发挥,用寄其以贤而辱于此之慨,不可一例论也。”[6]327蔡铸在《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卷7也有类似之言:“按子厚谪居楚南,郁郁适兹土,地僻人稀,无可与语,特借山水以自遣。”[1]1939可见,外出游览山水,以景寄托、俯仰慷慨以泄其满腔郁结,实乃柳宗元山水游记的真正主旨。
三
《囚山赋》中,永州群山环绕,树林茂盛,多有虎豹等猛兽,给人以蛮荒、凶险乃至恐怖之感,此异于《永州八记》所绘之景。但实际上,《囚山赋》所写风物,也见于柳宗元其他诗文之中。作于元和四年的《寄许京兆孟容书》,其云:“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霿。”作于元和五六年间的《闵生赋》云:“余囚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壤污潦以坟洳兮,蒸沸热而恒昏。戏凫鹳乎中庭兮,蒹葭生于堂筵。雄虺蓄形于木杪兮,短狐伺景于深渊。仰矜危而俯栗兮,弭日夜之拳挛。”作于元和七年的《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云:“枭族音常聒,豺群喙竞呀。岸芦翻毒蜃,溪竹斗狂犘。野鹜行看弋,江鱼或共叉。瘴氛恒积润,讹火亟生煆。耳静烦喧蚁,魂惊怯怒蛙。”作于元和七八年的《永州韦使君新堂记》云:“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
不仅仅是在永州所作诗文如此,柳宗元在其柳州诗文中也有如此表述,如作于元和十年的《岭南江行》云:“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此诗以瘴江、黄茆、象迹、蛟涎、射工、飓母等岭南的特异风物突出贬地荒凉的居住环境,“以见谪居之所,如是种种,非复人境”[12]。明人廖文炳说:“此叙岭南风物异于中国,寓迁谪之愁也。”[6]291作于元和十一年的《寄韦珩》亦追述初到柳州所见的莽荒之景:“回眸炫晃别群玉,独赴异域穿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
关于此,柳宗元在作于元和四年的《与李翰林建书》中,已有清晰表述:
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则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
柳宗元“沉窜俟罪”[1]2233“投窜零陵”[1]2233,“恒惴栗”[1]1890而致心情抑郁烦闷,“闷即出游,游复多恐”[1]2008,游玩之所以产生恐惧是因为其地荒凉凶险,野地有毒蛇、大蜂,水中有射工、沙虱,它们在暗中发作,击中人的身体或影子,极易伤人。这里,柳宗元展示了永州让其惊惧的自然风物。但文中又提到“时到幽树好石”,有时会遇到好景,此应是诸如同作于元和四年的《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等山水游记以及相似山水诗中所写之景。但柳宗元面对这些“幽树好石”,也仅是“暂得一笑,已复不乐”,所得之乐是暂时的,他并未真正得到解脱。柳宗元举了一个例子说明原因:好比一个人囚居于圆形土牢之中,一遇到春天宜人之景,则“负墙搔摩,伸展支体”,“亦以为适”,但最终发现自己还是囚于寻丈之地而不得出,“岂能久为舒畅哉”?柳宗元引此事即为说明自己居永州,就如同被拘禁在土牢之中,即便偶遇佳景而有所乐,也不过是暂得之乐罢了(1)正如本文图表所示,在强调自己“罪囚”身份及“囚居”生活的十四首诗歌中,描写山水、游览的诗歌就有十一首,占近80%。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见出在山水诗中,柳宗元并未真正释怀自己所受之遭遇。“罪囚”形象的自我塑造及“囚居”的意识并未消弭在他所谓的山水之乐中。。故而他渴望着能够早日离开永州这个自然牢笼,如写于同年的《寄许京兆孟容书》就向许孟容表达了希望能离开此地而“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胤嗣”的愿望。但以宪宗为首的当权者显然没有宽赦柳宗元等革新派之意,即便朝廷大赦,“八司马”也不在量移的名单中。
“罪囚”身份的自我设定与强化,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健康状况的不断恶化,使得柳宗元在元和九年终于写下了《囚山赋》,把近十年贬居永州的压抑之情宣泄而出,把自抵达永州之初即自我设定的“罪囚”身份进一步强化,把永州作为禁锢自己的牢狱加以形象化,进而使“囚居”意识更为突显,同时也将自己欲逃离此地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宋人晁补之录此文于《变离骚》之中,并序之云:“《语》云:“仁者乐山。”自昔达人,有以朝市为樊笼者矣,未闻以山林为樊笼者。宗元谪南海久,厌山不可得而出,怀朝市不可得而复,丘壑草木之可爱者,皆陷井也,故赋《囚山》。”[13]可谓是一语中的。时宗元贬永州已近十年,仍未被召回,故有恨群山囚己以至不能归之怨愤。另外,此“囚”,对柳宗元而言,并非单纯指人身的不自由、受拘禁,而更多指一种被当权者猜忌打击而被贬离朝廷,致使自己的济世才能无从施展的状态。柳宗元认为这种才干的受拘迫才是真正的被“羁囚”。
《囚山赋》以牢笼喻永州之山川以抒发自己被“囚”之恨,《永州八记》借不遇之景引出自己的不遇之叹,前者是险恶莽荒之景,后者是幽僻冷寂之境,但其所蕴藉的遭弃之感,所哀叹的壮志无用之慨,并无二致。可以说,这两种不同的风物完美地统一于柳宗元的山水刻画之中,极好地为其寄托抒情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