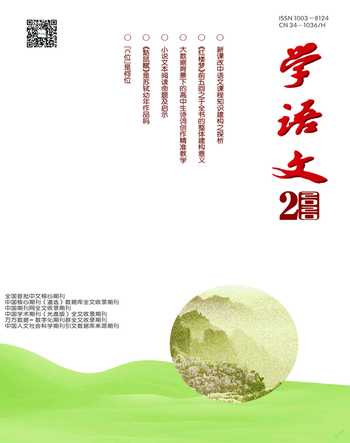试论单音节副词“就”追补句
2020-05-30张明月
张明月

摘要:副词“就”使用频率极高且语义类型丰富,本文以句末追补“就”为研究对象,通过删除、追补的手段与原句进行比较,归纳出能够进行追补的副词“就”有评注性副词、关联副词、范围副词和时间副词,而发生追补的概率随着副词“就”在句中语法功能虚化度的增加而增加;此类句末“就”追补现象的作用主要是语义补充功能和态度立场调节功能;并从语用、语法化两方面分析单音节副词“就”追补现象的形成机制。
关键词:副词;就;追补;语法化
引言
现代汉语中,副词“就”居于高频使用地位,而副词具有唯状性,在句中总是出现在谓词性结构之前。但是在日常交流中、在书面语中,我们也总是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
(1)把一包火药放在酒杯里掺和起来,一口气喝到肚里,就。(阿瑟·高顿《塔拉斯·布尔巴》)
(2)他又看了我几眼,他只觉得是一个,奇怪,有一个怪人,怎么一直在望着,看着我,他就走掉,他跟几个同学就叽哩呱啦地很开心就。(电视访谈《鲁豫有约·王杰》)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发现,本应处在句中状语位置的副词“就”位于句末了。对于这类语言现象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过研究。陆俭明(1980)将其称为“移位句”,认为凡移位句,前置部分总是说话人急于要传递给听话人的东西,后移部分则是稍带补充性的东西;张伯江、方梅(1995)则从语义角度说明了易位成分的主要类型;陆镜光(2000)以“延伸句”的解释统一了移位句和句末重复现象,认为它是言语交际的基本形式;张燕春(2004)主要讨论了易位与追补、易位与倒装的区别和联系;王晨(2014)以副词“都”为例从生成语法学的角度描述了“都”字易位句形成的句法过程,解释其形成的句法动因。樊中元(2018)解释这种现象为副词后置,探究了副词移位的类型、功能及约束条件;徐晶凝(2019)称之为追补句,探究了追补句的类型、功能及约束机制。
但是,众多学者们是就这一语言现象本身入手,或研究移位句与相关句式的區别、或是移位的句法和语义类型、或是形成移位的语音条件和功能等等,然而针对单音节副词在句末进行追补这一项还鲜有学者讨论。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个案“就”入手,探析单音节副词“就”能够追补的语义类型、追补的功能以及形成追补现象的机制。
对这一特殊语言现象的研究,学者们采用了不同的术语,如移位、易位、延伸、追补、倒装等等。本文参考张燕春(2004)对追补的解释,采用“追补”这一术语。
一、副词“就”的追补情况考察
我们据BCC语料库,结合学界研究成果,对副词“就”的追补情况进行了考察,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评注性副词“就”
副词“就”语义之一为评注性副词。
(3)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
→(3a)他的“大哥”味儿这么足,就!
(3b)他的“大哥”味儿这么足!
(4)今天是搞活动第二天远远不如第一天,今天就太闲了。
→(4a)今天是搞活动第二天远远不如第一天,今天太闲了就。
(4b)今天是搞活动第二天远远不如第一天,今天太闲了。
评注性副词在近年来的语法著作中被分析为语气副词或者情态副词,但无论是哪一种,表达的都是说话者对该事件的一种主观评价。通过将例(3)和例(3b)与例(4)和例(4b)分别对比,我们发现原句中“就”作饰谓副词,从语用上来看表达了说话者对事实情况的肯定判断;删除“就”的例(3b)、例(4b)语义表达仍然是完整的,只是语气不如原句强烈。当“就”在句末进行追补时,句子也是可以说的,是成立的,从语义表达层面来看,评注性副词“就”所要表达的肯定语气已由句中的“这么”“太”补充,因而并不形成语义缺失。两例中“就”既可以删去也能在句末追补,可见评注性副词“就”与其修饰的谓语部分结合并不紧密。
(二)时间副词“就”
副词“就”语义之二为时间副词,表示很短时间内即将发生。
(5)我就去他那了。
→(5a)我去他那了,就。
(5b)我去他那了。
(6)就到山顶了。
→(6a)到山顶了,就。
(6b)到山顶了。
通过将原句与删除掉“就”后的句子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就”在句中用作时间副词表达某动作或事件短时间内即将发生的意思。删除“就”后句子信息发生了变化,如例(5b)、(6b)表达的是事情已经发生了,可见时间副词“就”在句中不是可有可无的,有其需要承担的语法意义,体现在句子中即为该动作还未实现但即将发生。因为句子传递的信息是客观的,所以“就”不能删掉。时间副词“就”在句末进行追补时,于原位上留下空位并且语义得不到句中其他成分或语境的补充,所以追补“就”保留了原有的语法功能,依旧用作时间副词。由于句法位置的变化,此时的“就”更倾向为饰句副词。
(三)范围副词“就”
副词“就”语义之三为范围副词,表达的语义为“只(有)”。
(7)就你长耳朵了。
→(7a)你长耳朵了,就。
(7b)你长耳朵了。
(8)老两口就一个儿子。
→(8a)老两口一个儿子,就。
(8b)老两口一个儿子。
从语法层面来看,例(7)、(8)的“就”用作范围副词,强星娜(2013)认为“就你长耳朵了”这一类“就”字句是一种有标记的话题结构,其特性表现在“就”后名词性短语语义上具有消极性。所以我们不将此类“就”纳入研究范围。
通过例(8)和(8b)对比,我们发现例(8b)表意完整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而例(8)除了传递命题信息外,还表达了说话人对命题信息的态度即遗憾,所以“就”不能删。例(8)中“就”位于状语位置,其功能主要是用作饰谓副词;而例(8a)中位于句末的“就”保留了范围副词“只”的意义,但是其更重要的作用是表达出说话人对老两口只有一个儿子这件事略显遗憾的态度,而这个作用是句末这一特殊的位置赋予的,此时的“就”更偏向为饰句副词。
(四)关联副词“就”
副词“就”语义之四为关联副词,表达语篇功能。
(9)说完,就下楼去了。
→(9a)说完,下楼去了,就。
(9b)说完,下楼去了。
(10)我一折腾,别人就没法睡了。
→(10a)我一折腾,别人没法睡了,就。
(10b)我一折腾,别人没法睡了。
当“就”删掉后句子的信息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将表现在书面形式上的逻辑关系隐去了,但并没有因此改变前后两个动作之间的顺承逻辑关系。从语用上来看,状语位置上的“就”是客观性的陈述,而句末追补的“就”则表现了说话人主观性的陈述,带有一种主观的揣测。此时的“就”修饰的不再是“没法睡了”,而是用作饰句副词,修饰“我一折腾,别人没法睡了”。
(五)程度副词“就”
副词“就”语义之五为程度副词,张谊生(2000)将程度副词分为两个小类,一类是表相对义,一类是表绝对义。“就”应属于表相对义的程度副词。
(11)这个就好。
→(11a)*这个好,就。
(11b)这个好。
(12)她的字写的就好看。
→(12a)*她的字写的好看,就。
(12b)她的字写的好看。
例(11)、(12)中的副词“就”表达一种比较、对比的语义,整个句子只是作简单的陈述,语气平缓。当句中的“就”删掉后,例(11b)、(12b)句子本身的陈述语气没有发生变化,但原句中的比较义却丢失了。可见程度副词“就”在该句中位置上承担了一定的语法功能。当“就”在句末追补时,原句不成立,不能说了,因为从语用层面来说,听话人对于理解句末“就”会产生歧义。例如“*这个好,就。”我们在保证它语句通顺的前提下,既可以将它放置在句首如“就这个好”,也可以将其放于句中如“这个就好”,“就”的语义指向不明,所以程度副词“就”不能追补。
二、副词“就”追补句的功能
(一)语义补充功能
从话语语义的生成角度看,当说话人说出某个话语结构时,把主要的语义信息表述完后,发现有些语义还没有表达准确或者完整,需要再补充,因而在句末进行成分追补,完成说话人认为需要表达的完整意义。例如,
(13)后天就要预报名,要选专业,每天又低效率,怎么行啊,都十月了就。
(14)两个月的宝宝,纯母乳十余天就。
当我们撇开句末“就”不看时,例(13)中“都十月了”表示的是已经到十月份了,但是说话人清楚地知道现在还不是十月份,只是快临近十月,所以在句末追补时间副词“就”来补充“十月”的时间义。例(14)也是如此,如果删去“就”,句子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模糊,两个月的宝宝纯母乳喂养十余天怎么了?句末追補范围副词“就”不仅补充限定了母乳喂养的时间范围,而且还体现出说话人的惋惜之情。
所以时间副词和范围副词“就”追补的功能主要为语义补充。句末“就”离开了句中的状语位置而占据句末语气词的位置,我们通过说话人这样的句法处理,从语句中也能感受到说话人略显无奈的语气。
(二)态度立场调节功能
“立场”最初由Biber和Finegan(1988、1989)提出,含义十分宽泛,主要涵盖了由词汇与语法成分所表达的态度、感受、判断等意义。Conrad and Biber(2000)提出了立场的三个次范畴:认识立场、态度立场和风格立场,其中态度立场涉及对所言或所写的信息内容的情感倾向和评价表达。
(15)都失踪了,一个也联系不上,我明天就走啦,关键是时候掉链子哇就。
(16)干了两天活儿,没游泳,腰疼脖子疼肩膀疼的。一游泳,啥都好了就。
(17)该怎么说,人的生命真的好脆弱,中秋前还好好的一个人说快不行了就。
虽然从句法结构上看,上述例子中的单音节副词“就”均可以复位到句中的谓语动词前,但从语义的角度来说,复位后的句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说话人的情感。徐晶凝(2019)认为发话人之所以要将“就”以追补的方式说出,主要是出于某种情感立场表达的需要。例(15)中“就”表达出说话人略显不满的态度;例(16)中“就”表达出说话人喜悦的心情;例(17)中“就”则传递出说话人的一种遗憾语气。上文中例(13)、(14)分别为时间副词、范围副词“就”,就其本身的语法功能而言,没有任何立场而言,但是说话人以追补的形式处理,使得句子传达出说话人的主观情感。所以单音节副词“就”追补句功能之二为态度立场调节功能。
(三)小结
根据我们所收集的60条单音节副词“就”追补句,不同语义类型副词“就”追补的功能和追补句情感的差异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四类副词“就”追补均具有态度立场调节功能,并且副词“就”追补句句子感情色彩的比例分别为:消极占71.66%、积极占6.66%、中性占21.66%。从语言形式的角度看,在汉语中立场表达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单位、句法手段来实现。说话人不仅使用句末追补“就”这一句法手段来表达自己的立场,而且多以表达消极态度为主。
三、“就”追补句的形成机制
(一)语用因素
从语用的角度来看,学者们更多的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临时性的话语调整行为。但是本文所选取的语料均是书面语,即说话人没有来自交际过程中需要即时加工的压力,他们仍采用在句末追补“就”这样的句法手段,说明说话人是“故意而为之”,说话人为什么有意识地调整语序?
在汉语立场的表达中,我们可以选用极具感情色彩的词语来凸显我们的主观立场,比如:
(18)我讨厌他。
(19)我喜欢这首歌。
在上述例句中,第一人称代词后面跟着一个表示立场意义的谓语同时也是一个表评价义的词语“讨厌”“喜欢”,这些词语暗含了对指称对象“他”“这首歌”的价值判断和评价。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某些句法手段来表达立场,比如追补。
(20)今儿开始,开心的过。不去打扰别人的幸福了吧就。
(21)今天才明白。原来你的同意是个施舍。不开心了就。
在例(20)、(21)中虽然没有第一人稱代词,但是结合句意可知两例的立场表达者均是说话人自身。例(20)中有明确表达评价义的短语“不开心”,是对客体对象“你”所做行为的不满意。例(21)中虽然也有“开心”这一感情色彩鲜明的词,但是结合语境可知,说话人此时的心情满是悲伤与凄凉。副词“就”在状语位置上只起到语篇连接作用,即使删去了也不会影响说话人态度立场的表达,但是说话人却以追补的形式将“就”置于句末。句末的“就”从句法、语义上看没有任何作用。但是就句子的韵律而言,句末“就”增加了一个音节,将整个句子的韵律拉长了,换言之拉长了说话人想要表达的悲伤心境。
总之,无论是书面语还是口语,形成追补句机制的第一动因应是语用动因表现为说话人情感立场的表达、宣泄。
(二)“就”——语法化
副词“就”在句末追补除了出于语用表达的需求,还与其自身的虚化程度息息相关。马清华(2003)曾总结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四个因素为重新分析、句法位置变化、语境影响、词义变化。副词“就”的虚化于句法位置上体现,在语境中浮现。
副词“就”(除了关联副词)的典型位置是句中的状语处,修饰谓语。但是在使用中,副词“就”出现了游离的现象。当它游离至句首位置时,被看作是有标记的话题标记,如:
(22)就我这种没本事的人,偏还有人哭着喊着赖上门来。
当它游离至句末位置时,其句法属性向饰句副词转变,偏向于理解为情态表达。也就是说,无论这个词在其典型句法位置上可能表达哪种意义,位置发生游移之后,只能解读作认识情态意义。如:
(23)在这个世界给我个休息依靠的地方,一颗纯净的心,陪伴的情全够了就。
张谊生曾归纳副词连用顺序:评注性>关联>时间>频率>范围>程度>否定>协同>重复>描摹。反映在副词“就”追补句中,越是左侧的副词越游离于句子核心谓语动词,越容易在句末追补,其虚化的程度越高。
四、结语
本文主要通过删除等句法手段归纳出能够进行追补的几类副词“就”:评注性、关联、时间、范围,其追补的概率与副词“就”虚化的程度息息相关;总结了副词“就”追补的两大功能即语义补充功能和态度立场调节功能;并对其形成机制进行了探究。
参考文献:
[1]方梅、乐耀:《规约化与立场表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
[2]樊中元:《副词移位的类型、功能及约束条件》,《汉语学习》2018年第4期。
[3]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
[4]陆镜光:《句子成分的后置与话轮交替机制中的话轮后续手段》,《中国语文》2000年第4期。
[5]马清华:《汉语语法化问题的研究》,《语言研究》2003年第2期。
[6]强星娜:《作为有标记话题结构的一种“就”字句—兼与“连”字句、“像”字句比较》,《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2期。
[7]王晨:《现代汉语副词易位现象的句法解释——以“都”为例》,江苏师范大学2014年。
[8]徐晶凝:《交际互动视角下的追补句——易位句/延伸句/话尾巴句研究补遗》,《中国语文》2019年第5期。
[9]张燕春:《易位与倒装和追补》,《汉语学习》2004年第6期。
[10]张谊生:《论与汉语副词相关的虚化机制—兼论现代汉语副词的性质、分类与范围》,《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
[11]张伯江、方梅:《北京口语易位的话语现象分析》,《商务印书馆》1995年。
[12]Leech, Geoffrey. Grammars of spoken English: New outcomers of corpus-oriented research. Language Learning,2000。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8级硕士研究生)
[责编崔达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