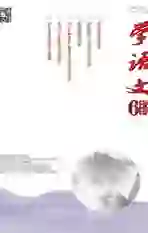《今生今世的证据》的三个精神维度
2020-05-30李燕杨大忠
李燕 杨大忠
摘要:刘亮程的散文《今生今世的证据》重在解说人与故乡的关系,它体现了作者反省的三个精神维度:灵魂拷问——对自毁证据的批判;证据消失——对过去生活的怀疑;无家可归——对精神返乡的绝望。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感受到该文的分量与价值。
关键词:《今生今世的证据》;证据;精神维度;家园
刘亮程的乡村散文《今生今世的证据》以简单朴实而又含蓄蕴藉的语言,以及独特的人生体验,揭示出人的心灵终极皈依的哲学命题。之前的语文同人解析《今生今世的证据》,往往將着重点放在对“证据”消失的原因探索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乡土文化之思上。这无疑是正确的。实际上,就情感的抒发而言,刘亮程对“今生今世的证据”的消失无疑是绝望的,这体现于作者灵魂深处的三个精神维度。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该文的分量与价值。
一、灵魂拷问:对自毁证据的批判
与其它思乡作品不同的是,《今生今世的证据》并没有将阐释的重点放在对人与故乡情感的吟咏上,而是重点解说人与故乡的关系是什么,故乡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在人与故乡之间,存在着一个联系两者的“证据”。这种“证据”是什么?林忠港老师认为:“值得注意的是,《今生今世的证据》所写的‘证据,主要不是以‘自然为中心的日月星辰、霜雪云雾,而是以‘家园为中心的一系列生活真实,如木桩、土坑、屋舍、公鸡、黑狗等人类生活的痕迹或伙伴,前者亘古如斯,恒久不变,而后者随着人的离开,都将面临坍圮或死亡的命运。”[1]这种说法是非常正确的。
那么,今生今世的证据——以“家园”为中心的一系列生活真实——消失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往往将其归结为现代经济潮流的冲击。中国社会的变化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巨大,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加上急功近利的思维膨胀,使得原本就非常脆弱的传统意义上的家园,其固有特征流失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快。短短几十年,我们就不认得回家的路了。虽然任何人都承认现代化潮流带来的巨大便利,但谁也不能否认由此而来的精神家园的荒芜与贫瘠。
但是,刘亮程在《今生今世的证据》中却从没有将家园的废失归因于社会潮流,而是以一种近乎锥心泣血的悔恨之情从自身找原因:
我走的时候,我还不懂得怜惜曾经拥有的事物,我们随便把一堵院墙推到,砍掉那些树,拆毁圈棚和炉灶,我们想它们没用处了。我们搬去的地方会有许多新东西。一切都会再有的,随着日子一天天好转。
想想吧,这哪里是刘亮程一个人的心态,而是国民的共性啊!年轻的时候,我们离开家乡,有几人能够未雨绸缪地想到这里将是我们心灵的最后归宿?在毫无远见的短浅目光的支配下,我们毫不可惜地毁掉了承载着成长历程的印记,只是因为我们当时认为“它们没用处了”,幼稚地想象会有更好的东西供我们使用——我们亲手毁掉了与我们生活直接相关的记忆。
此外,离开家乡时,我们也没有对家乡留存更多的记忆,疏忽了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却是将来抚慰心灵最好的良剂:
我走的时候还不知道向那些熟悉的东西告别。不知道回过头说一句:草,你要一年年地长下去啊。土墙,你站稳了,千万不能倒啊。房子,你能撑到哪一年就强撑到哪一年,万一你塌了,可千万把破墙圈留下,把朝南的门洞和窗口留下,把墙角的烟道和锅头留下,把破瓦片留下,最好留下一小块泥皮,即使墙皮全脱落光,也在不经意的、风雨冲刷不到的那个墙角上,留下巴掌大的一小块吧,留下泥皮上的烟垢和灰,留下划痕、朽在墙中的木头和铁钉,这些都是我今生今世的证据啊。
这里的草、土墙、房子,全部被赋予了生命的色彩。刘亮程以一种温柔的眼光、殷切的叮咛、深情的抚摸来看待这些带着生命体温的故乡意象。但遗憾的是,刘亮程的这种表达,并非年轻时离开家乡时的想法,而是多年以后重回家乡,在“今生今世的证据”杳然无迹的情况下,发出的一声痛苦的悲吟。在此时的归乡人眼里,哪怕是留存了故乡曾经的印记的一小块泥皮,都是唤醒记忆的“今生今世的证据”啊!可惜,即使是这种微不足道的证据,也早已随风而散,一去不回——我们只能以留恋、追悔与感伤的心态对待曾经的疏忽与无知。
刘亮程就这样以毫不留情的解剖自我灵魂的方式,揭示出“今生今世的证据”随风而逝的根本原因。表面上看,这是刘亮程对自己的拷问;推而广之,刘亮程曾经的思想又何尝不是全体中国人的思想痼疾。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作家,刘亮程没有回避自己的责任,他认为如果要对“今生今世的证据”缘何散失这一问题进行追责的话,我们不应当怨天尤人,不应当一味归咎于社会,而应当对我们曾经的做法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这种反省是深刻的,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犹豫和迟滞,体现出剖析灵魂的极致深度。只有最极致的自我反省,我们才能真正明确在保持“今生今世的证据”时的个人责任,才能避免再次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曾经的生活,有一天会需要证明。”
刘亮程描写乡村,与其他作家都有所不同。路遥笔下的双水村,反映了由贫穷到逐渐脱贫阶段人们思想的急剧变化;莫言笔下的高密乡村,在愚昧落后中让人领悟到疗救的艰难与希望;汪曾祺笔下,则呈现出乡村的如画风光与村民的淳朴可爱……唯有刘亮程,不回避乡村变动中的自我觉醒与反思,他运用自我批判的手法,深刻说明在乡村颠覆性的剧变中每个人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没有人能脱身事外。这就是刘亮程,一个勇于操着思想上的冷冰冰的手术刀从自我灵魂的剖析入手,进而揭示出全体国人思想痼疾的有社会担当的当代作家。
二、证据消失:对过去生活的怀疑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写你的村庄,你就写了世界。”作家王开岭也说:“没有故乡,没有身世,人何以确认自己是谁?没有地点,没有路标,人如何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2]刘亮程曾经在一次访谈中也说:“中国人共同的故乡是乡村,乡村既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生存居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对于刘亮程来说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令人丧气的是,“今生今世的证据”一旦散失,我们的精神家园也随之荒芜了,因为我们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刘亮程以一种非常沉痛的笔调,指出“今生今世的证据”散失后的严重后果:“有一天会再没有人能够相信过去。我也会对以往的一切产生怀疑。”
终有一天,我们疲惫了,衰老了,就会带着满身的尘埃回到魂牵梦绕的故土,在那里荡涤抚慰疲惫的灵魂,寻找心灵的最后慰藉。正如刘亮程在《对一个村庄的认识》中所说:“故乡对中国汉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没有宗教,故乡便成为心灵最后的归宿……故乡便是全部唯一的宗教。”
但是,当我们重返故乡时,我们还能找到过去的影子吗?故乡之所以能成为我们心灵最后的安慰所,就在于它保留着过去生活的种种印记,我们从中能重温过去,从而对一生反刍回味,抚平心灵的创痕。然而,等我们“乡音未改鬓毛衰”时再见故乡,却失望地发现了另外的场景:
那是我曾经有过的生活吗?我真的看见过大地深处的大风?更黑,更猛,朝着相反的方向,刮过动物的骨骸和根须。我真的听见过一只大鸟在夜晚的叫声?……这一切,难道不是一场一场的梦?如果没有那些旧房子和路,没有扬起又落下的尘土,没有与我一同长大仍旧活在村里的人、牲畜,没有还在吹刮着的那一场一场的风,谁会证实以往的生活——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
都是发人深省的拷问!问出了物非人是的凄凉,问出了斯物已逝的遗憾,问出了直面故乡的酸楚。故乡在刘亮程的眼里绝非完美无缺,刘亮程也写到了故乡的夜晚叫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大鸟和对自己紧追不舍的瘸腿男人,但这些缺陷也是故土情结的一部分!它们也滞留于我们的血液中,构成对故乡无尽的追忆。而今,我们找不到过去的痕迹了。
《今生今世的证据》思想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写出了对“证据”日渐消亡的痛心和无助,而且还进一步指出,即使我们重回故乡,重新见到旧房子和路、尘土、仍旧活在村里的人和牲畜、一场一场的风……但是,“即使有它们,一个人内心的生存谁又能见证?”因为这些所谓的“证据”,虽然在乡村尚可以找到相似的痕迹,但再也不是我们过去所见的“证据”了,它们只不过是乡村生活继续存在的标识或东施效颦的复制物。我们的内心对它们不会泛起任何情感的波澜。
由此可见,刘亮程对“今生今世的证据”的界定是极度严苛的。他对这些“证据”的要求是:它们必须是与我们过去的生活息息相关并且一直保留下来的旧东西,我们不仅使用过它们,与它们发生过密切的联系,而且它们还要能见证我们“内心的生存”,使我们意识到这里就是我们灵魂的归宿,我们能够以安然平和的心态在这里过完自己的后半生——“今生今世的证据”应当而且必须是永恒的。
这的确非常反常!因为没有人能够阻止时光的流逝。造物主不可能为了某个人的意愿而让时光戛然而止,让时光停留在某一个历史维度而恒久不变。如何在生命长度与宇宙永恒之间找到平衡,是千百年来人们一直积极探索的话题。没有什么事物是绝对静止的,刘亮程对“今生今世的证据”的界定似乎有点不可理喻,其实,这却是以达到极致的方式透视出浓厚的乡土之思。因为人们对故乡的回忆都是过去的某些片断,这些片断不会随着年月的增长而变形;萍漂四方的游子如同飞翔在天空的风筝,但最终还是由一条丝线将他们拉回那个原点,这个原点就是故乡,就是记忆中永不改变的幼年印象。对过去印象的回忆往往是爱之深或恨之切的表现,而回忆则是定格的、恒定的心像再现,所以,刘亮程希望“今生今世的证据”恒久不变是可以理解的。凡是经历过挫折与沧桑的人,往往都会不断重温永不磨灭的记忆,希望时光能够倒流。
所以,刘亮程对“今生今世的证据”界定之极度严苛,愿景之极度“反常”,正是乡土之情的最高体现。但是,这些“今生今世的证据”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失去了最后的皈依之地,失魂落魄,只留下了生存的虚无感和恐惧感:我们生活过吗?我们真的存在过吗?
三、无家可归:对精神返乡的绝望
刘亮程回到了故乡,发现“今生今世的证据”再也找不着了:“我回到曾经是我的现在已成别人的村庄。只几十年工夫,它变成另一个样子。”这是就刘亮程个人而言的;大而广之,不是刘亮程的“今生今世的证据”不见了,而是所有人“今生今世的证据”都将不复存在:
他们打那些土墙时,我便清楚这些墙最终会回到土里——……墙打好后,每堵墙边都留下一个坑,墙打得越高坑便越大越深。他们也不填它,顶多在坑里栽几棵树,那些坑便一直在墙边等着,一年又一年,那时我就知道一个土坑漫长等待的是什么。
土坑在漫长地等待什么?当然是等待土墙的坍塌再次将自己填平,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然后又为新一轮筑墙做好准备。就是在这样静静的时光轮回中,一代又一代人衰老、死亡直至腐朽,所有人的“今生今世的证据”都将不复存在。但在这些“证据”逐渐湮灭的过程中,每个人都依稀可见自己往日生活的影子。这在刘亮程身上的具体体现是:大红公鸡、黑狗、夕阳以及“我”在家乡的快乐、孤独、惊恐与激动……
每个人都无法阻止“今生今世的证据”在逐渐丧失,绝对无法阻止。虽然这一点是刘亮程极不情愿看到的,但刘亮程无疑也是清醒的,他也疑惑这些“证据”“对于今天的生活,它们是否变得毫无意义”。言下之意,他虽然认为“今生今世的证据”对于自己无比重要,但他人能否像自己一样看重这些“证據”,他还是存在疑惑的。
但刘亮程在文章的结尾却毋庸置疑地点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地迈上了虚无之途。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王开东老师认为该句的潜台词是:“当村庄废失,肉体回家的脚步,开始踏上了虚无之途;当家园废失,精神回家的脚步也迈上了虚无之途。”[3]也就是说,“今生今世的证据”一旦消失,我们的肉体和精神都回不了“家”了,每个人都将成为风中的飘蓬无所依归。这里隐含的是刘亮程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对精神家园的追寻,但结局是令人失望的,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再遇见“今生今世的证据”,“证据”的消失不可避免。
客观来讲,刘亮程在《在今生今世的证据》中体现出来的思想有着一定的保守性。他似乎无法融入现代文明,就像他自己所说:“我只是这座城市(乌鲁木齐)的客人,永远是。无论寄住几天或生活几十年,挣一笔钱衣锦还乡或是变成穷光蛋流落街头。”由此,《今生今世的证据》从侧面写出了乡下人进城后的孤独与隔膜,写出了社会转型时期一个特殊群体的生存境遇。无论采用哪种解读,该文都告诉我们,在竭力追求物质文明的同时,寻求精神的慰藉是多么重要。
参考文献:
[1]林忠港:《今生今世的“证据”到底是什么?——〈今生今世的证据〉教学解读》,《中学语文》2012年第11期。
[2]王开岭:《古典之殇——纪念原配的世界》,书海出版社2010年,第74页。
[3]王开东:《每个人的村庄都在沦陷——破译〈今生今世的证据〉》,《中学语文教学》2014年第4期。
(作者:李燕,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一级教师;杨大忠,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正高级教师)
[责编张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