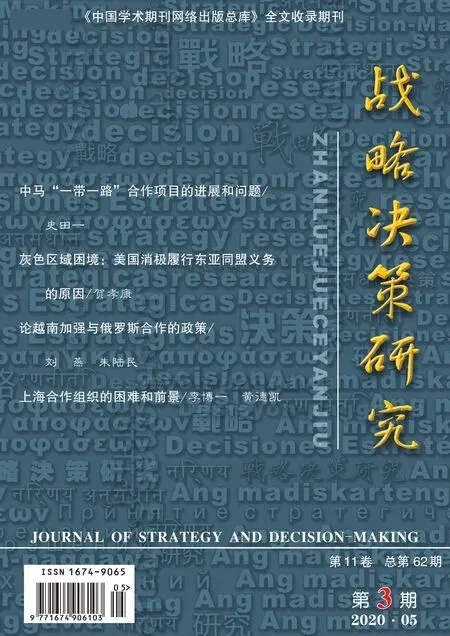上海合作组织的困难和前景
2020-05-21李博一黄德凯
李博一 黄德凯
2017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正式迎来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新成员国,实现成立以来首次扩员,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地区合作组织。①有的学者认为,上合组织吸纳观察员国与对话伙伴国也属于组织扩员的标志;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由于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并不拥有如同正式成员国那样的表决权,而不能成为组织扩员的标志。本文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上合组织的地域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更具有国际性与代表性,也确实能够给成员国带来一些安全、经济、地缘等领域的利益。有的学者乐观地预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可能会进一步加强。②Jin Wang,Dehang Kong,“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States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China Quarterly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Studies,Vol.05,No.01,2019,p.15;Miroshnychenko Tetiana M,“The Directions of Integration Activities of the SCO Countries”,Bìznes Inform,Vol.3,No.494,2019,pp.32-36;Mohsen Khezri,Muhamed Zulkhibri,Reza Ghazal,“Regional Integration,Monetary Cooperation:Evidence from Global VAR Models for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Vol.11,No.1-2,2019,pp.65-79.但也有一些学者比较谨慎,认为印巴的加入可能会给上合组织带来多重不利因素。①Denisov,Safranchuk,“ Four Problems of the SCO in Connection with Its Enlargement”,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a journal of translations,Vol.60,No.22019,pp.119-136;Svetlana Bokeriya,“The Interconnection of Global and Regional Security Systems:The Case of the United Nations,the 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and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Research Journal,Vol.14,No.1,2019,pp.21-38.本文认为,扩员之后,上合组织可能面临着权力再分配与组织再造的双重挑战,②李进峰主编:《上海合作组织15年:发展形势分析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23-31页。在组织机构内部的权力分配、机构运行效率、组织架构、功能定位等方面,可能都会遇到扩员带来的冲击。本文重点讨论这些问题,并分析上合组织发展的前景。
一、扩员之后的权力再分配问题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面临着双重的权力再分配问题。一方面,随着数量的增加,组织内部各个正式成员国所享有的决策权面临着新的洗牌。新加入的正式成员国与创始的正式成员国之间存在着因决策权分配不平衡而形成团体性对峙的可能。这可称之为制度性的权力再分配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正式成员国数目的增多,上合组织内部的正式成员国之间既有的力量对比关系、亲疏关系,以及国家影响力等方面也面临着不同程度地冲击。这种权力的再分配可称之为非制度性权力再分配。本文的分析采取后一种视角对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再分配问题进行探讨。印巴加入上合组织之后,不可避免地会谋求分享其他成员国在该组织中拥有的权力份额,从而对上合组织内部的力量对比、权力对比等带来挑战。③Degang Sun,Hend Elmahly,“NATO vs.SCO:A Comparative Study of Outside Powers’Military Presence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Gulf”,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Vol.12,No.4,2018,pp.438-456.
(一)扩员之前:中俄共同主导下的权力分配模式
“上海五国”是由中国与俄罗斯共同主导。④赵华胜:《上海合作组织评析和展望》,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页。随着五国机制转变为正式的上合组织,这一组织的制度化水平也得到进一步提升,但其内部的权力分配并没有随之发生本质改变,中俄仍旧是机制化水平更高的上合组织内部权力架构中处于主导优势的行为体。在随后的运转与调适过程中,上合组织以中俄两大力量中心作为组织引擎的地位基本未发生质的转换。①虽然上合组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吸收过新的成员国,即在印巴正式加入之前,上合组织与蒙古、阿富汗等国建立起了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等低层次的关系网络,但从严格意义上讲,这并不能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扩员,仅仅是为了地区力量平衡等考虑,而将那些在安全利益诉求方面同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之间有着相似性的国家吸引在组织外围而已。相关内容可参见:李进峰、吴宏伟、李伟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李进峰、吴宏伟、李少捷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李进峰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李进峰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李进峰主编:《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等。因此,可以说,从上海五国机制到印巴加入前的上合组织,其内部的权力构成呈现的是一种中俄共同主导下的双层格局,即中俄处于上合组织内部权力体系的顶端,哈吉塔乌等四个正式成员国则处于权力体系的另一端。也正是由于如此,上合组织在扩员之前运转的是较为顺利的,虽然各个成员国在权力分配模式等领域也存在博弈,但基本而言,未对上合组织的运行轨道产生破坏性冲击。
作为欧亚地区的两大关键行为体,中国与俄罗斯对该地区国际事务的话语权与规制权的掌控显然要比其他中等力量行为体更为显著。②Yeongmi Yun,Kicheol Park,“An Analysis of the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Issues and Prospects”,Pacific Focus,Vol.27,No.1,2012,pp.62-85.上合组织作为欧亚地区较早成立的地区性国际组织之一,自发起成立之日,其内部的权力分配比例便已锁定为中俄共同主导。这不仅符合中俄两国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主导思维,也是中俄两国权力外部性延伸的一种明显体现。作为扩员之前的上合组织的主导驱动力量,中俄在组织内部的权力地位,相对于其他成员国而言,处于一种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这与其他中等力量成员国所处的权力位置形成强烈反差③根据上合组织宪章与成立宣言等官方文件,正式成员国拥有表决权,而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则不拥有这种关键性权力。虽然如此,正式成员国之间也因国力等的大小而在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体系中占据不同位置,因而相应具有程序公正但实际影响力不同的话语表达权。具体可参见:《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等官方原始文件,http://chn.sectsco.org/documents/;有关外文文献可见:Timur Dadabaev,“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Reg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entral Asia State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3,No.85,2014,pp.102-118;Weiqing Song,“Interests,Power and China's Difficult Game in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3,No.85,2014,pp.85-101;Jing-Dong Yuan,“China's Role in Establishing and Building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9,No.67,2010,pp.855-869.(如图1所示)。

图1:正式扩员之前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组成① 在上合组织内部,只有正式成员国才享有表决权,观察员国与对话伙伴国则不享有对组织内部事务的决策权,因此,在设计这一图示时,便将蒙古等观察员国与对话伙伴国排除在外。但这并不是要忽视甚至否定这些非正式成员国的作用与影响,只是为了本文行文的方便而做出的一种取舍。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中俄主导下的权力分配模式,主要在于:(1)从权力的视角看,在上合组织的成员国中,中俄不论在综合实力还是利益诉求方面,相较于其他成员国均处于一种优势地位,其中成员国间力量的对比悬殊是形成这种权力分配模式的根本性原因。(2)从地缘的视角看,上合组织虽处欧亚地带但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欧亚地带,正如麦金德所言,这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②哈尔福德·麦金德著,林而蔚、陈江译:《历史的地理枢纽》,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页。而“心脏地带”是需要最为强大的引擎为之提供动力源。中俄不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软硬层面均符合这一标准。(3)从现实的视角看,上合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也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再次复兴的战略依托之一,面对中亚地区“三股势力”的兴起与扩散,中俄两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成立上合组织以集体的力量维护地区安全并以此为基础向世界舞台中心再次靠拢,最终顺利“表达自我与实现自我”便成为中俄共同主导上合组织的现实考虑。总之,权力界定的国家利益③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brief edition,New York,(Mac-Graw-Hill Companies,1993),pp.56-90.这一国际政治的铁律是中俄占据上合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模式顶端的根本诉求;处于欧亚心脏地带而拥有强大动力源则是中俄两国共同主导上合组织运转的物质基础;而以集体行动与团体力量“表达自我、实现自我”则是中俄在上合组织内部权力分配中处于主导位置的现实选择。
但是,这种由中俄共同主导权力分配模式却可能随着印巴的加入而发生一定的权力再分配。印度与巴基斯坦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对于其自身而言,无疑是其实现对中亚、南亚地区事务深度介入的一次有利尝试,而上合组织似乎也给印巴两国实现地区战略目标提供了一个机制平台。①Prithvi Ram Mudiam,“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the Gulf:Will India Prefer a Further Westward Expansion of the SCO or its Consolidation?”,Asian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and Islamic Studies,Vol.12,No.4,2018,pp.457-474.如今,印巴获得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资格已是不争的事实,而这一客观现实将会给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模式造成何种影响,便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
(二)扩员之后:多重力量组合下的权力分配模式
正式扩员前的上合组织在中俄这两大关键力量行为体的驱动下,不论是在内部架构方面还是在对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客观地讲,印度与巴基斯坦同时以正式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上合组织,给这一地区性国际组织带来诸多有利影响:(1)政治层面,扩大了上合组织的代表性,增强了上合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2)安全层面,有利于成员国之间以联合的方式共同面对解决地区三股势力、毒品走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3)经济层面,有利于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与资源能源互补;(4)其他层面,如有利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深入推进,与“欧亚经济走廊”等形成交叉态势,从而为本地区的国家提供更为可观的市场,形成所谓的“欧亚经济圈”等。但另外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则是,印巴获得正式成员国资格,势必会对上合组织既存的权力分配模式造成冲击。即由中俄主导的权力分配模式面临着被解构乃至重构的可能。
随着印巴这两个力量行为体的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在自身内部权力体系中将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新的“洗牌”。而这种变化,无疑将会在多个方面对上合组织产生影响。一方面,对于上合组织自身而言,新成员国的加入,不可避免地会对上合组织内部既有的权力分配模式产生冲击;另一方面,新成员国一旦获得对组织议事程序的表决权,势必会对其未来的运转造成影响。而且,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印度与巴基斯坦获得上合组织正式成员资格这一客观现实似乎正在印证上述猜想。因此,以印巴成为正式成员国为标志,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其内部游戏规则制定权、地区与国际安全事务等领域的话语权都将面临重新分配的可能。总的来说,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其内部权力分配模式将会面临如下几种可能:中俄两国仍旧是主导性力量,印巴作为新正式成员国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印度与俄罗斯达成共识,而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达成默契同“俄印”形成博弈,从而形成一种“俄印-中巴”共治下的权力分配模式。不论出现哪种权力分配模式,都会对上合组织本就低下的议事与行动效率再次造成影响。如华尔兹指出的那样,结构决定单元的选择与行为。而单元的改变也会进一步要求改变既存的权力结构以达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①Kenneth N.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Mac-Graw-Hill Companies),pp.189-220.而且权力转移的进程中,权力呈现出的多中心和扩散化的趋势一样,上海合作组织也呈现出同样的态势,这种态势总体表现为灵活性与复杂性。②薛志华:《权力转移与中等大国: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评析》,载《南亚研究季刊》2016年第2期,第46-47页。而自上合组织成立到印巴正式加入,中俄两国一直都是组织内部权力结构体系中的核心引擎,随着印巴的加入,这种双核引擎的权力分配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转换的可能。但究竟会形成何种新的权力分配模式,关键在于印度采取何种姿态。具体来说,印巴的加入将会使得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模式发生以下几种转换的可能:
1.“中俄+巴—印+哈吉塔乌”模式
如前所述,上合组织在正式吸纳印巴作为新的成员国之前,其内部的权力结构设计,是中俄作为组织的主导驱动力量而位于权力安排的顶端,其余正式成员国则处于权力分配层级的底端。而随着印巴的加入,这种权力分配模式不排除发生转换的可能。鉴于印巴两国之间的历史宿怨与现实争端等因素的影响,当前以中俄占据主导的权力分配模式可能会出现巴基斯坦靠近中俄而与其对手印度形成一种对抗模式。即以中俄为上合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模式中的一端,巴基斯坦为实现同印度抗衡的目的,向之靠拢。同样,印度为了类似的战略目标并证实其大国地位,会联合“哈吉塔乌”等其他四个正式成员国形成上合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模式的另一端,进而与“中俄+巴”这一权力的另一端形成分庭抗礼局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权力分配模式转换的可能,原因可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看。从历史看,首先是印巴之间的关系。自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以来,特别是随着印巴分治的落实,两国之间为了英国分而治之方案而遗留的“查谟-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争端多次发生冲突甚至战争;为了继续实现主导南亚这一大国梦,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关系短期内并不会随着两国同时加入同一个国际组织而发生改变;其次是中印之间的关系。印度自获得独立以来,与中国的关系可谓是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印度不甘心做一个二流国家,更不会坐视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并主导亚太地区事务,另一方面,印度又与中国有着相似的历史经历与源远流长的关系,作为金砖五国的成员之一,印度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等方面需要借鉴中国经验。因此,印度加入由中国作为主导力量之一而发起成立的国际组织,几乎不会出现同中国站在权力分配模式同一端的可能。但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如果不享有一定的权力,便会失去其加入组织的意义。因此,不排除一种可能,即印度联合“哈吉塔乌”等其他四个成员国组合成与“中俄+巴”这一权力团体相抗衡的另一权力团体。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印度加入上合组织,是要获得类似于俄罗斯那样的活动空间以及同样的发展机遇。①白联磊:《印度对上合组织的认识和诉求》,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7年第4期,第94页。而所有这些从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中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措施的态度便可得到例证。因此,印巴成为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这一扩员行为对上合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模式带来的第一种转换可能便是“中俄+巴”与“印+哈吉塔乌”这一新的权力分配模式。
2.“中巴—俄印”模式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除了上述那种可能会出现的权力再分配之外,另外一种权力再分配模式也是有比较现实的可能性——“中巴—俄印”模式。从上海五国到上合组织,其权力分配模式一直是中俄主导,哈吉塔乌等其他成员国虽然同样是正式成员国,但由于其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等均与中俄两国之间存在着悬殊对比,因此,可以说,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模式在其接收印巴成为正式成员国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基本维持在以中俄为一端,以哈吉塔乌为另一端的状态。但这一模式状态却存在着随着印巴正式加入而发生转换的可能。即是说,印巴加入并获得正式成员国资格,并不是仅仅为了加入而加入,而是意图获得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份额。因此,扩员后的上合组织的权力再分配面临着第二种可能性:中巴-俄印。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可能性,也需要从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分析。
首先是俄印关系。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前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与印度的关系较为紧密。这一方面是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南亚乃至世界事务的主导权造成的,即苏联要与美国分享世界,需借助南亚地区的关键力量——印度的支持,而印度自其独立起便一直追求大国梦,但由于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关系并不稳固,此时苏联又与中国的关系破裂,因此把结盟的对象转向印度,而印度为了获得更多的外部军事援助早日实现其大国梦便与苏联一拍即合。其次是印巴关系。印巴分治并未给南亚地区带来真正的和平。相反,由于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分治方案给印巴两国之间埋下了纷争甚至战争的祸根——克什米尔的归属权之争。巴基斯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从印度分离出来以后,一直处于被印度压制状态。甚至曾经被印度肢解——孟加拉国的建立便是例证。而且,印度为了主宰南亚地区,吞并曾经的锡金王国。巴基斯坦为了改变这种与印度在南亚地区所处的不利地位,同中国的关系开始改善,尤其是近几年中巴关系稳步发展。所以说,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为了继续同印度展开竞争与博弈,不排除与中国抱团的可能。最后是中俄关系。苏联解体前,中苏曾经是结盟关系,因意识形态之争等原因两党关系恶化并导致两国关系破裂。苏联解体后,继承苏联主要衣钵的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起初并不像今天这样。相反,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由于奉行双头鹰政策,为了国内改革的顺利进行,极力想要获得欧美国家的援助与支持,而把更多精力投放在了西方,相反对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热衷。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才逐渐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但俄罗斯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不排除一种可能:俄罗斯欲借助中国的力量与支持,抵消美国以及北约东扩带来的战略压力,最终重返世界舞台的中央。而且,一个众所周知的客观事实,就是印度之所以能够顺利成为上合组织首次正式扩员的选择对象,除了印度自身因素之外,很关键的一个外部支持或者说内部接洽者就是俄罗斯。因此可以说,印巴加入上合组织成为正式成员国,对上合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模式造成的另外一种改变就是以中巴为权力的一端,俄印为权力的另一端的权力分配模式。至于哈吉塔乌,很可能会与俄印站在同一端。这主要是因为这四个中亚国家从历史、地缘上等均同俄罗斯关系紧密。但也不排除哈吉塔乌与中巴抱团的可能性,而这主要取决于这四个国家如何看待俄罗斯对其的态度。
3.“中俄-印巴”模式或“中-俄-印-巴”模式
上述这两种权力再分配模式,从目前来看基本不会成为现实。对于第一种模式。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印巴关系在短期内几乎不存在从本质上改善的可能,因而也就几乎不存在印巴形成一端与中俄抗衡这一前景。也正因如此,哈吉塔乌便不存在选边站的问题。当然依旧会存在中俄占据上合组织内部权力分配模式主导地位的可能性,这主要是为了限制印巴的权力。对于第二种模式,同样基本不会成为现实。虽说上合组织完成首次正式扩员之后,其成员国构成发生了多重变化,但是中俄与印巴均不具备单独主导上合组织的实力,即便是具备这样的实力,它们也不会将上合组织本就低下的议事效率拉向新的低点。况且,印度是否撇开俄罗斯这个武器支援国而单独同中国甚至同中俄争夺上合组织的主导权,也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既然如此,哈吉塔乌便也同样不会面临两难选择的可能。
总之,上合组织已经完成其历史上的首次正式扩员。这次正式扩员,将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两个南亚地区的关键力量行为体引介到了中亚地区这一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对于印巴来说,这是一个可资利用的跳板,即为印巴积极介入中亚地区安全事务、应对困扰自身多年的安全问题提供一个政治解决的对话平台;但对于上合组织及其创始成员国来说,印巴的加入无疑会在多个层面对既有的权力分配模式造成震荡。而不论会出现上述分析中哪种权力再分配的前景,都会对上合组织作为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内部组织再造产生冲击。
二、扩员之后的组织再造问题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除了会面临上述权力再分配的问题,还会面临组织再造的问题。这里的组织再造不是说上合组织会面临被解构和重构的问题,而主要是指,随着新的正式成员国的加入,组织的成员国数量获得增加的同时,成员国间的利益碰撞、角色定位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简言之,随着成员国数量的持续增加,上合组织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会遭遇新的冲击与震荡。而这就是本部分将详细展开论述的内容:扩员后的上合组织所面临的组织再造难题。具体来看,随着印巴获得正式成员国资格,组织内部的正式成员国会在身份差异、价值观分歧以及利益冲突①邱昌情:《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进程、动力及影响》,载《南亚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第1页。等方面面临挑战。这多重的挑战又会进一步影响上合组织的决策效率。
(一)成员国间差异增大
一方面是成员国间宗教与文化差异的增大。上合组织内部的成员国构成可谓是一个“万花筒”:首先是俄罗斯。以东正教为主导宗教信仰的俄罗斯,其本身因横跨欧亚大陆而形成了一种欧亚视角下的双重文明观——既是一个东方国家(从地理覆盖范围上讲),也是一个西方国家(从宗教文化起源上看),这种双重身份使得俄罗斯在上合组织内部具有一种优越心理,即俄罗斯时常以东正教文明的正统自居,但却时刻不忘恢复昔日苏联甚至罗马帝国的辉煌;其次是中国。作为一个正宗地理上的东方国家,中国的儒家文化源远流长,现在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其儒家文化基因仍旧根深蒂固,而儒家倡导的仁智理念与和合思想与俄罗斯的宗教文明观存在着本质差别,两国作为上合组织的主导推动力量是否会随着印巴的加入而发生重构也是一大挑战;再次是印度与巴基斯坦。印度与巴基斯坦本属同一个国家,因英国的殖民统治在世界殖民体系瓦解之际提出实施的印巴分治方案而成为两个具有同样国际法地位的主权国家。虽然印巴两国有着这样的历史渊源,但由于两国在宗教信仰、居民构成上的不同,以及在领土划分等方面至今仍存在着纠纷使得印巴关系一直处于一种短时间内无法破解的安全困境;最后是哈吉塔乌等四个中亚国家。这四个国家也是上合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但是从目前来看,哈吉塔乌在上合组织内部并未与中国或俄罗斯处于同一战线,而是自身形成了一个小团体。从历史上看,哈吉塔乌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稳定。特别是在苏联时期,整个中亚地区基本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中亚国家几乎处于苏联卫星国的地位,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了短暂的权力真空期,这给了中亚国家获得新生的历史机遇。然而,作为苏联衣钵主要继承者的俄罗斯,却并未放松对中亚地区的再次控制。因此,可以说哈吉塔乌四国在上合组织内部的成员国构成的再建构中仍不会考虑与俄罗斯达成一致;从文化上看,哈吉塔乌的文化更为复杂多样,与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中国的儒家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教文明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随着印巴的加入,哈吉塔乌四国是否会因宗教文化基因的共同性而选择与中俄或印巴中的一方达成一定共识,仍是未知数。
另一方面是不同成员国身份定位和价值观差异的扩大。上述这一切使得上合组织这一机制化的地区对话平台必须同时面对多种文化的交锋,而且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博弈也不断再构着上合组织的章程架构。因此,可以说,随着印巴的加入,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组织身份也势必面临着新的转换与再造,而这也关系到上合组织在实现首次正式扩员后能否继续顺利运转。特别是印度作为南亚地区首屈一指的力量行为体,一直以来都以一个地区大国自居,甚至将印度洋视为“印度自己的内海”,另外可从其伙同日本、巴西等国一直谋求“入常”的外部实践得以例证。即印度不甘心做一个二流大国,其追求世界大国的“印度梦”自独立以来便未停止过。而此次加入中俄主导的上合组织,对于印度来讲,不啻为一个良机。倘若印度只是以一个普通主权国家的身份加入,那对于上合组织及其创始成员国而言,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会发生极端地对组织内部主导权的争夺;但倘若印度是以一个地区大国的心态加入上合组织且另有所图(目前来看,这种情况更为可能),对于上合组织来说,不啻为一个“地雷股”。①“Pakista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Towards a Futuristic Approach”,Policy Perspectives,Vol.14,No.1,2017,pp.121-130.上合组织正式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作为首次扩员的选择对象,也势将面临新正式成员国同既存主导国间的力量分化与重组。作为上合组织内部权力结构体系的第一层级成员,中俄的身份归属意识同印度的身份转换对于形成哪种新的权力分配模式至关重要。倘若作为上合组织权力架构主导方的中俄继续坚持以一种战略性的伙伴关系将组织的主导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那么即便印度加入了上合组织,其在组织内的权力层级安排中仍旧会处在与中俄不对称的位置,即中俄继续以主导国的身份将新晋成员国的权力严格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不至于冲击主导国的地位;作为上合组织的主导国之一,俄罗斯似乎对中国并不是绝对的完全信任,因此才在印巴申请加入上合组织时变现的更为积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俄罗斯对上合组织的扩员,特别是印度的加入日趋积极。这当然是为俄罗斯的全球战略服务—既有助于提升抗衡美国的能力,又能够借助印度牵制中国,削弱中国在上合组织中的主导地位。①由此可见,作为印巴主要是印度加入上合组织的引路人,俄罗斯似有以印度来平衡中国主导权的意图。一旦俄罗斯与印度之间形成一种隐形的联合,这对于俄罗斯而言似乎并没有损失,因为其还是上合组织内的主导国之一,其大国身份依旧,但对于印度和中国而言,情况则完全不同:对印度来说,一旦其与俄罗斯达成共识,便会分享到一定的主导权;对中国而言,则会面临主导权被分割的风险。总之,印巴的加入,不可避免地会对上合组织的成员构成造成一定冲击。而这一问题又会进一步引发上合组织内部关系架构的重塑。
(二)成员国间利益分歧增加
在印巴正式加入上合组织之前,这一地区性国际组织内部的关系结构主要是创始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及其各自的定位问题。而印巴的加入,将因两国之间的历史宿怨而给上合组织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将成为上合组织扩员后不得不面临的考验。②薛志华:《巴基斯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原因、挑战及前景分析》,载《东南亚南亚研究》2015年第4期,第33页。而与之相伴随的,则是扩员之后的上合组织是否会由一个制度化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沦为一个松散的地区安全事务论坛。因为,随着印巴这两个新成员的加入,存在着其将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纷争一起带进组织的可能,尤其是印巴之间。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形,组织内各个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势必会发生新的分化改组。与此同时,随着成员国间平衡关系的打破,其本就饱受诟病的决策效率也势将因新成员国的加入而跌入新的谷点。毕竟随着正式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其工作语言也更为难以协调,加之成员国之间利益的差异加大,上合组织在各个领域决策的难度也将加大。③葛军:《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挑战和机遇》,载《世界知识》2017年第19期,第63页。
另外,随着扩员的完成,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数量增加了,但成员国之间的分歧也会增多,特别是成员国的利己主义、机会主义等因素也会对扩员后的组织内部的关系平衡形成干扰。④李进峰:《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挑战与机遇》,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5年第6期,第37-38页。特别是印度,其从观察员国升级为正式成员国,将会给上合组织内部的关系架构造成何种冲击仍然是个未知数。同样作为一个成长的大国,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与中俄形成一种新的关系平衡,①陈玉荣:《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利与弊》,载《欧亚经济》2017年第5期,第36-37页。这三个大国如何在兼顾所有成员国利益的基础上有效协调立场,消除相互制衡,维系上合组织原有的平衡,进一步提高凝聚力,是扩员后的上合组织面临的严峻考验。②郭连成、陆佳琦:《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新机遇与新挑战》,载《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114页。总之,伴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多,上合组织将成员国的个体意愿上升为集体意愿的难度也随之上升,扩员将使上合组织并不完善的内部制度承受更大压力。毕竟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加入将会给组织带来的地域扩大、利益分化、议程增加等问题,而这反过来又会对组织协调、决策和制度建设等提出更高的要求。③李亮、曾向红:《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风险前瞻》,载《欧亚经济》2017年第5期,第21-22页。薛志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的发展战略及中国的作为—基于SWOT方法的分析视角》,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3期,第65页。陈小沁、李琛:《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分析—基于地区公共产品的视角》,载《南亚研究》2019年第2期,第1页。简言之,扩员后的上合组织面临着内部关系失衡的可能,而这又会进一步引发“集体行动的困境”。
(三)决策效率面临挑战
在印巴升格为正式成员国之前,上合组织的议事效率本就低下,饱受诟病。这主要是由于正式成员国之间的共识大于分歧、工作语言无法协调一致等原因造成的。扩员之后,随着正式成员国数量的增加,将给这种既存的问题带来更多挑战。有的学者担心,随着印巴的加入,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同新晋成员国之间的利益竞争与对组织领导权的博弈将有可能进一步激化,内部决策机制的效率问题可能会突出,该组织的决策能力有可能弱化。④丁超:《合作博弈: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与成员国间的经济关系分析》,载《欧亚经济》2017年第5期,第60、64页。
扩员之前,上合组织由中俄与哈吉塔乌共同构成正式成员国阵营,虽然还有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国,但由于二者在上合组织中并不享有表决权而对上合组织的议事规则和议事程序等组织安排几乎不会产生关键影响。如前文所述及的,扩员前,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分配模式是由中俄主导,哈吉塔乌等其他四个成员国则处于一种被主导地位。即便是如此,上合组织的决策效率也并不尽如人意。反而时常在一些共同议题上互相推诿甚至采取拖延态度。这成为上合组织决策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动因。另外,从目前上合组织的组织架构看,主要有元首理事会、政府首脑理事会(下辖九个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会议)、国家协调员理事会以及四个常设机构等。上合组织在机制安排上存在多个重叠之处,这种机制的重叠无疑是影响决策效率的又一关键因素。
印巴加入上合组织,必然会要求重构上合组织既存的共同话语体系。①许涛:《扩员后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必须面对的问题》,载《欧亚经济》2017年第5期,第32-34页。即随着成员国语言的多样化与差异性的显著提高,各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将会更为困难。②白联磊:《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新发展机遇与挑战》,载《国际问题研究》2017年第6期,第66页。曾向红、李廷康:《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学理与政治分析》,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3期,第148页;杨恕、李亮:《寻求合作共赢:上合组织吸纳印度的挑战与机遇》,载《外交评论》2018年第1期,第60-62页。首先是工作语言方面。目前上合组织的官方工作语言有汉语和俄语。而印巴的加入,尤其是印度,不排除其试图将印度的官方语言升格为上合组织的又一官方工作语言。印度如果将英语纳入上合组织的官方语言之一,尚可接受。但众所周知,印度的国家官方语言多达几十种。③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看,印度的官方语言有印地语、乌尔都语、英语等。而一旦印度试图将非英语中的某一种或某几种国家语言纳入上合组织的官方语言,其对上合组织的议事决策效率的影响可想而知。而且从印度当前的大国意识与大国姿态来看,不能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此外,一旦印度如此要求势必也会引发从众效应,诱发其他正式成员国跟风行事。其次是会议机制方面。随着印巴的加入,上合组织的会议机制也将发生一定改变,不论是元首理事会还是政府首脑理事会乃至其他机构都会面临新的洗牌。这就进一步增加了上合组织议事决策的效率困境。
不论如何,扩员对于上合组织来说已经成为客观现实。上述权力再分配与组织再造的可能是上合组织扩员后不得不面临的困境与前景。虽然从目前来看,还不能完全确定哪种权力分配模式更具现实可能性,但出于对组织自身的未来发展的考虑,必须做出上述多种可能性分析。④I.E.Denisov,I.A.Safranchuk,“FOUR SCO ENLARGEMENT PROBLEMS”,Vestnik MGIMO Universiteta,2017,pp.112-122;O.Y.Kolegova,“Development Internal Problems of Shanghay Cooperation Organizatio”,Vestnik MGIMO Universiteta,2017,pp.117-123;Denisov,Safranchuk,“Four Problems of the SCO in Connection with Its Enlargement”,Russian Politics&Law,Vol.54,No.5-6,2016,pp.494-515;Igor Evgen'evich Denisov,Ivan Alexeevich Safranchuk.Four SCO Enlargement Problems.Vestnik MGIMO Universiteta,Vol.48,No.3,2016,pp.112-122;Oksana Y.Kolegova,“Development Internal Problems of Shanghay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Vestnik MGIMO Universiteit,Vol.45,No.6,2015,pp.117-123.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可以说,扩员对上合组织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而如何应对上述挑战,将困境转化为未来继续顺利运转的有利条件,是扩员后的上合组织面临的关键问题。
三、上合组织的发展前景
不同的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定位存在差别:对于俄罗斯而言,其很可能是将上合组织作为其恢复历史荣光的跳板,即以上合组织为依托,抗衡北约东扩,扩大生存空间;对于中国来说,更多地是将上合组织视为一个多边合作、在周边区域进行治理的平台依托;对印度来讲,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即印度意图借力上合组织,抵消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为其实施东向政策寻找一个平台,同样也有可能是为其早日实现“入常”的大国梦找到一个发力的助跑器;对于巴基斯坦而言,似乎更多是继续为了与印度展开战略博弈与竞争。当然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也离不开经济社会发展的考量,但平衡印度似乎是战略所求。不论怎样,印巴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加入上合组织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①具体的相关内容可参见:拉希德·阿利莫夫:《上海合作组织的创建、发展和前景》,王宪举,胡昊,许涛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面对这一客观现实,原始的正式成员国不可大意也无需过度警惕。而是要考虑如何将可能出现的风险降到最低限度,以及怎样在充分照顾新晋正式成员国合理诉求的基础上不被上述可能出现的困境所羁绊,从而推动扩员后的上合组织继续保持一个良好的运转势头。
(一)角色再建构
扩员后的上合组织,该如何再次定义自己的身份角色?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将这一地区性国际组织不断升级进化为世界性国际组织还是在继续坚持地区事务为导向的同时,不断以世界视野来对组织自身进行改造?这是扩员后的上合组织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的角色选择关系到扩员后的上合组织能否为创始成员国与新晋正式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提供一个双方均可接受的模式。而这又关系到上合组织未来的再次扩员所面临的挑战能否有历史经验可资借鉴。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倾向于认为,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应该继续坚持以地区事务为主导方向,与此同时,对新加入的正式成员国在权力分配上进行必要的限制。以防出现权力的过度分散化或多种重组而降低组织的凝聚力,更是为之后的再次扩员提供经验。
扩员之前,上合组织的定位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这与全球性国际组织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地区性国际组织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而全球性国际组织则更多倾向于以世界性为自身的地缘视角。可以说,印巴正式加入前的上合组织之所以以地区性国际组织的身份来界定自身的外部行为,与其成立的初衷与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在中俄哈吉塔交汇之处是世界上恐怖主义、极端主义与分裂主义最为猖獗的地区之一,为了共同应对“三股势力”对中亚地区的周边安全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成立了“上海五国”。①E W Boikowa,“Issues on Humanitarian cooperation of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member stat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2018,pp.18-25;Bruna Toso de Alcntara,“SCO and Cybersecurity:Eastern Security Vision for Cyberspa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iplomacy,Vol.6,No.10,2018;K.M.Barskiy,“Participation of the SCO in Peacekeeping Activities,Prevention and Settlement of Conflicts”,Vestnik MGIMO-Universiteta,2017,pp.94-101;Baubek,Anna,Adil,“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its Activities in Ensuring Human and Social Security”,The Anthropologist,Vol.22,No.3,2015,pp.510-517.有鉴于此,为了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中俄哈吉塔五国在1996年发起成立“上海五国机制”。不论是从其名称还是其所关注的事务方面,不难看出扩员前或说成立之初的上合组织以地区事务为导向的意图。随着上海五国升级位上合组织,其地区性特征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
扩员之后,上合组织的地区事务导向有向更广领域外溢的可能:是继续坚持以地区为导向还是通过不断扩员将自身转化为一个全球性国际组织。基于上述相似的理由,我们认为,印巴加入后,上合组织仍需坚持以地区为主导方向,但这并不是要否认上合组织扩员后的全球视野。毕竟有第一次扩员,就会有下一次扩员的可能。对于不同的成员国来说,上合组织对其有着各自相异的意义或作用。就以中国为例。如前所讲,上合组织是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国主动发起并且以中国城市(上海)作为其组织名称的地区性国际组织,其对中国经略周边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可以说,中国发起成立上合组织,意在以其为自身融入全球事务的机制平台,并以此向世界“表达中国进而实现中国”。与此同时,将上合组织打造成区域合作机制的典范,为中国在周边地区进行区域治理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
(二)功能再定位
上合组织自成立至正式吸纳印巴加入的一段时间当中,其功能的三根支柱当中,安全事务是最为重要的。毕竟,上合组织的成立宗旨即在于有效打击“三股势力”,以维护成员国周边地区的安定与和平。虽然在后来的发展转轨进程中,成员国也开始陆续关注相互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等事务,但安全事务一直处于组织内部议事日程的关键位置。①Hasan H.Karrar,“Shanghai spirit two decades on:language,globalization,and space-making in Sino-Central Asian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No.247,2017,pp.111-126.况且,在上合组织的成员国构成当中,究其经济发展水平来说,目前来看只有中国的经济体量较为庞大,其他几个成员国由于各种原因,经济发展进程或转轨进程似乎并不乐观。而随着南亚地区两个重要的行为体加入,上合组织所注重的事务领域也势将面临新的定位:是继续坚持“安全、经济、人文”三根支柱并进还是以安全为主导兼顾其他。从本文的上述分析看,更倾向于后一种选择。即是说印度加入上合组织后,尽管其政治地理空间得到扩展,但是对于中国而言,上合组织最初的定位应该继续坚持。②庞大鹏:《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后中国需要关注的问题》,载《欧亚经济》2017年第5期,第41-44页。
扩员之后,以何种途径有效化解成员国之间因历史传统、文化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所造成的权力再分配与组织再造等困境?本文认为,必需着眼于组织功能的再定位与总体合作思路的转变:首先转变对组织功能的认识。如前所言,上合组织是一个地区性国际组织,且以边境地区的安全事务为三根支柱之首,这本身就从一个侧面映射出安全事务是上合组织的重点所在。而随着印巴的加入,更是为安全事务增添了诸多不稳定因素:印巴之间存在已久的紧张与对抗,是否会被两国带进上合组织?一旦出现这种状况,扩员后的上合组织将会面临停摆的风险;其次是转变经济合作模式。③许涛:《扩员后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必须面对的问题》,载《欧亚经济》2017年第5期,第35页。扩员之前,上合组织内部的权力模式呈现以中俄为主导的格局,而印巴的加入不可避免地会冲击这种权力分配模式。特别是印度,其对中国始终抱有一种怀疑警惕心理,这从其对“一带一路”等的态度即可看出。①为了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印度联合日本提出“印日自由走廊”,意图以此抵制中国对南亚地区的介入,进而抵消中国日渐提升的地区与国际影响力。对此,中国以提出构建实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走廊式经济合作。因此,上合组织内的经济合作模式可考虑通过经济走廊的方式进行。总之,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仍需坚持以安全事务为主要的机制支柱。对于中国来说,可以以此为契机逐步改善同印度之间的关系,并要防止印度与俄罗斯进行联合以平衡中国的主导权。与此同时,也要注重同各个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经贸互动,不断构造成员国间的主体间性来增加上合组织的向心力。
(三)权力再分配
随着首次正式扩员的完成以及后续运转的开启,上合组织的地理覆盖范围将由此前的以中亚地区为重点外溢扩展到欧亚大陆中部这一更广阔的“心脏地带”。成员国数量的增加、组织内部文化价值观的进一步多元化等都从不同侧面给扩员后的上合组织造成困扰。作为中国深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以及维护西北边境地区安定和平的重要机制平台,②张宁:《关于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的战略方向的分析》,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47页。上合组织是中国经略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重要平台。而扩员之后,上合组织内的权力分配模式很有可能出现转换。那么该如何凝聚共识,找准优先合作方向,防止组织论坛化发展、陷入集体行动逻辑的怪圈,是扩员后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③高焓迅:《中亚国家视阈下的上海合作组织扩员:收益认知与战略考量》,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8年第5期,第126-127页。答案是在协商一致与上海精神的基础上,坚持以中俄为主导,对印巴特别是印度的权力诉求进行必要的限制。如,可考虑即使给予了印巴正式成员国的身份资格,但对于影响到组织议事决策效率的关键权力,可不将之再进行分配。另外,需要考虑成立惩罚性机制或者降格甚至开除机制。对于在组织内部刻意破坏议事规则或者扰乱决策程序的正式成员国,可考虑将之降格为观察员国或对话伙伴国,待其行为有所改善并符合正式成员国标准时,再考虑将之升格为正式成员国;而对于极端狭隘的国家,则永久性开除其正式成员国资格等。
对主导国之一的中国来说,印巴这两个南亚地区关键行为体的加入,是上合组织不断为机制自身注入新鲜活力的必然选择。扩员,不仅仅是地理范围的扩大,从深层次讲,更多是不同文化集合体的增多,而这也将给上合组织的未来带来更多可预知和不可预知的挑战。与此同时,扩员也意味着“‘上海精神’被更多国家所认可,也意味上合组织可以成为经济联通、安全联通的重要平台,这对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顺利实施很有帮助”,①凌胜利:《上海合作组织扩员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载《欧亚经济》2017年第5期,第54页。也是中国成长为名副其实的新型世界性的负责任大国的又一平台依托。
总之,无论怎样扩员,上合组织都需要明确自身的地区性组织定位,始终坚持安全事务优先并占据主导地位,而对于可能发生的权力再分配与组织再造的前景,扩员后的上合组织需要在权力分配制定相应的奖惩机制,以防止出现如下情况:即拥有正式表决权的成员国之间因争夺权力份额或狭隘的国家利益而使上合组织陷入停摆的困境。乐观地看,虽然新晋的正式成员国同创始成员国之间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但作为“上海精神”的实施载体,上合组织在扩员后需要着力塑造各个成员国间的集体身份,以上合模式聚合成员国,以此弱化最终消解扩员后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
地区性国际组织往往并不限于谋求在本地区事务中发挥影响力,而是倾向于积极扩大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甚至以自身的理念来塑造世界。因此,地区性国际组织往往会尽可能吸纳本地区国家,扩大成员国数量,拓展其地理范围,从而更容易扩大其地区和国际影响力。②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第二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7-364页;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3-586页;卡伦·明斯特:《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157-192页。上合组织也不例外。上合组织于成立十六年之际,正式将印度与巴基斯坦吸收为新的正式成员国。随着印巴两国的加入,上合组织不可避免地会在内部权力分配模式和组织机构两个层面面临挑战。根据历史经验以及当前的国际现实,在权力再分配这一维度,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是:“中俄+巴—印+哈吉塔乌”模式,其次是“中巴—俄印”模式,最不可能出现的是“中俄-印巴”模式或“中-俄-印-巴”模式;在组织再造这一维度,会遭遇如下挑战:正式成员国构成的重组;组织内部关系架构的重置以及扩员后决策效率的困境等。面对上述双重且多维的困境与挑战,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不可轻视也无需过于担忧。对于扩员前的成员国,特别是对于主导国中俄而言,需要在进一步加强共识的基础上,将印巴的权力限定在两国可控的范围内,防止给予其过度的权力而使自身陷入被架空的窘境;对于印巴来说,加入上合组织获得正式成员国资格,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加入上合组织,给印巴两国发展经济社会、提升国际地位与国际影响力以及化解两国历史宿怨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加入上合组织,使得印巴两国面临与中俄这两大力量中心直接博弈的可能,也面临被中俄限制其在上合组织内部分权的可能。但无论如何,作为新晋正式成员国,印巴都需要一种正常的心态面对现实。唯有此,扩员后的上合组织才不致沦为一个松散的地区性议事论坛,更不至于因出现上述多种困境而陷入停摆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