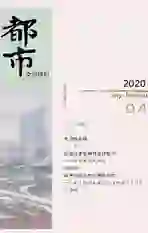纪实文学自有其独特魅力
2020-05-14畅建康
主持人语———
本期鲁顺民专访很丰富。
一个有趣现象,不少纪实作家都当过编辑,其益处在于理性化。顺民对纪实写作有思考,有主张,笔端有分量,作品影响拓展到文学圈之外,多年间早已突破了纯文学“内心小我”,与民众命运捆在一起,读者日广。
中国作家多岀乡土,为什么写好写透农村的力作却很少?顺民访谈启示人们,长期的制度安排与农民悲喜境遇扭结在一起,往往不易想清楚,唯有以多学科思考辨析生活,支撑作品筋骨,才是科学方法,否则无法探究乡村真相。作家的价值取向、理性认知和终极关怀,决定了纪实写作的成败。
白居易以果树喻诗,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优秀纪实同样拒绝调查报告。顺民作品拓进现实生活,决不意味着轻视文学要素,不要文学。多年的编与写,他强调遵循艺术创作规律,始终追寻着纪实文体之美。勤奋之下,硕果丰盈,日久成林了。
———主持人赵瑜
鲁顺民是《山西文学》主编,和他的几位前任周宗奇、张石山、韩石山一样,都是以写小说出名,但是他们的文学高峰却是纪实,这绝不是什么有趣的巧合,应该是纪实文学的魅力,以及作家的对使命的担当使然。有次和毕星星谈起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毕星星说:“山西纪实文学创作有队伍,年纪大的就不说了,年轻的鲁顺民、黄风他们也很厉害……”这不是毕星星一个人的看法。鲁顺民作为代表当前山西中坚力量的作家之一,得到文坛的肯定是理所当然的。迄今,鲁顺民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有《山西古渡口———黄河的另一种陈述》《送84位烈士回家》《天下农人》《礼失求诸野》(与张石山合作)、《潘家铮传》《朱伯芳院士传》《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开明士绅牛友兰》等数百万字,曾获“赵树理文学奖”。
纪实是山西文学创作精神的传承
畅建康(以下简称畅):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受到了全国文坛的关注,作为山西省作协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主任,你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现象的?山西纪实文学创作这边独好的风景有什么特色?
鲁顺民(以下简称鲁):就文体而言,报告文学跟山西真是有不解之缘。往远里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报告文学之一,宋之的创作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写的当然是山西的事情。后来还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为了周总理的嘱托》等报告文学名篇也诞生在山西。
就山西作家的创作而言,报告文学,或者说纪实文学受到全国文坛的关注,应该在马烽、西戎、孙谦、束为、胡正等“山药蛋派”作家开始了,在全国影响甚大。比方马烽写过《刘胡兰》,西戎写过《曲峪新歌》,孙谦写过《大寨英雄谱》,束为写过《南柳春光》,等等。尽管他们这些作品带着明显的时代局限,或者说时代的痕迹,但不能不说,这些作品是“文革”前十七年当代文学的重要构成。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晋军崛起”,报告文学创作与小说创作一样,是这个重要文学现象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出现了赵瑜、麦天枢、马骏等以报告文学名世,并产生全国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家,另一方面,其他以小说、诗歌名世的作家,也不约而同有报告文学作品问世,并引起反响。比方焦祖尧、郑义、张平、哲夫、张锐锋等。以《批评家》为阵地,报告文学批评在全国也占一席之地。比方著名学者谢泳,早年就是以报告文学批评在全国评论界崭露头角,引起关注。
所以,要说山西报告文学,或者说纪实文学创作今天能够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必须把它放置在山西文学几十年发展的大格局中来考察,脉络庶几会呈现得更加清晰一些,“晋军崛起”的内涵会更加丰赡。无疑,报告文学的创作与创作实绩,应该是山西文学的重要一翼。
近年来,以赵瑜的纪实文学《革命百里洲》获得鲁迅文学奖、《寻找巴金的黛莉》在全国引起轰动为标志,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逐渐受到全国评论界的关注。当然,作家队伍成规模有实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作品本身的影响。这里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山西的纪实文学创作,除了教科书式报告文学文体意义上的作品,比方,赵瑜等人创作的《王家岭的诉说》,聂还贵的《有一座古都叫大同》,黄风、徐茂斌的《黄河岸边的歌手》,黄风、籍满田的《滇缅之列》《大湄公河》,哲夫的《水土》,魏荣汉的《风风雨雨选村官》《中国选举报告》,皇甫琪的煤矿工人生存现状调查等等。还有具有相当文化含量的作家与作品,比方,韩石山的《李健吾传》《徐志摩传》《张颔传》,周宗奇的《清代文字狱》,陈为人的《风雨文坛五十年》以及山西作家系列传记,周宗奇的《范仲淹传》,还有青年作家李金山的《司马光传》《温庭筠传》,王秀琴的《王文素传》等等,传记文学创作成绩让人刮目相看。还有许多以小说名世的作家,也有相当分量的纪实作品,比如张石山的家族传奇系列纪实作品,蒋殊关于抗战和革命根据地当事人和重大事件的记录,都显示出独特的魅力。
与其说纪实文学创作“这边风景独好”,莫若说山西文学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人生这个传统一直没有断过,传承有续。
写纪实更过瘾
畅:我们知道你最早是以写小说受到关注的,后来却很少看到你的小说了,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纪实作品。比如《山西古渡口———黄河的另一种陈述》《送84位烈士回家》(再版改为《送烈士回家》)、《天下农人》《潘家铮传》、和张石山合著的《礼失求诸野》,还有获得赵树理文学奖的《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中国北方的农村和农民》等等,每部作品都有很不错的反响,评价很高。请问是什么原因使你把写作的重点放到纪实文学作品的创作上的?
鲁:我的写作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包括后来走上创作之路。与其说有什么理想抱负,莫若说是出于好奇,出于兴趣和爱好更准确一些。写作是这样,阅读也很杂,一切由着性子来。
总的来说,我是一个没什么理想抱负的人,而且从小就对这些词汇很排斥,甚至反感。因为这样的词汇压根就跟我们这些农家出身的孩子不沾边。这并不意味着自己写作就不严肃,不认真。当初为什么写作并不清楚,但不为什么写作肯定是明确的。后来我想,可不可以这样总结,自己的写作是出于对职业的尊重?实在是这样。读书的时候,念的是中文系,中文系的学生写一两篇小说不算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再做中學教员,至少需要“下海”给学生做范文,更不用说后来做文学编辑,你连小说都不会写,文章都不会写,怎么也说不过去。出于对职业和饭碗的尊重而写作,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确实是实情。
小说创作开始很早,那是大学一年级的时候的一篇作文。我们当时的写作老师是苏涵,他后来到厦门集美大学文学院做院长。他鼓励大家写作,鼓励大家投稿。想想上世纪八十年代,真让人怀想。文学热体现在很多地方,比方投稿,只要在信封上写上编辑部的地址,再标注“邮资总付”就可以不花钱寄出去,邮局的柜员都会多看你两眼。更让人感慨的是,投出去,用与不用,都会有回音,大多数是印刷好的退稿签。但我的小说投出去之后,很快就收到回音。这样,我的第一篇小说就发在《山西文学》1986年第3期。以后又接连发了几个。
调到《山西文学》编辑部,做的是小说编辑,当时我跟朱凡两个人分片看小说,都是自然来稿,那时候自然来稿也比较多。在此之前,虽然也写小说,但开始对山西文学全省的创作情况有全面了解,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当时有一搭没一搭地写。小说发表,一领稿费,就无声无息。用张石山的话讲,叫作“老婆看上一遍,读者就翻了一番”。后来写纪实作品,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文体意识,但是有出书意识,就想写一两本书。说起来,要感谢老领导韩石山,他讲,一个有修为的读书人,一定要有出书意识,没有一两本书拿出来,零零星星发表,总不成气候。记得老主编李国涛的祖父李辅中先生有一副对联,让我看,叫作:下榻唯存容足地,传名恃有等身书。触动很大。等身书,站起来等身有些困难,躺下等身总可以吧?韩石山先生也支持,给了几个命题作文式的任务,这样,就先是《山西古渡口———黄河的另一种陈述》,然后是《送84位烈士回家》《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的北方农村与农民》,直到最后的《天下农人》,都是在这种意识的支撑下写出来的。
再一个客观原因,是文学编辑工作的节奏适合搞这个文体。做文学编辑的都有同感,尤其是月刊,每一位同仁要拿出一整块时间来做一件事情简直不可能,一个月只有五六天空闲时间。写小说,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文气要贯通,一旦中断就再拿不起来了。而纪实的文体构成逻辑和写作节奏跟小说还有区别,时间分散开来也没有什么妨碍。
其实刚开始,也沒有说要从事纪实文学创作之类的想法,就是要写书,出书,沉甸甸地拿在手里,也能拿得出手。这种写作状态很自由,考察一个村舍,描摹一个农民,书写一种风俗,追究一段历史,写起来乐在其中。人说我善于“鬼说六道”,三言两语能把事情说清楚,而且生动。其实得益于小说训练。写着能不过瘾吗?
为天下农人写作
畅:你的纪实作品多数是农村和农民题材的,这种选择的原因是什么?
鲁:山西的作家,大多写农村,以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见长。自然来稿,也大都是农村题材。在看稿子过程中就发现,大多数作者笔下的农村,与自己在基层了解到的农村完全不一样,与现实脱节得很厉害。平时读书,喜欢读社会学和历史学书籍,大学的时候,读过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后来又读到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还有陆学艺、曹锦清、孙立平等社会学家的著作,还订阅有黄宗智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看待农村,看待农民,就有一种新角度。这样,来稿中的农村和农民就令人生疑,有的甚至仍然怀念大集体时代的农村,呼唤大集体时代的农民出现。把这个疑惑跟朱凡讨论。朱凡说:那你写啊!
想也仅仅是想一想,但是农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农民的生存状态怎么样?自己也不是太清楚。可是总感觉农村并不是别人笔下的农村。毕竟,自己就是一个农民小子,关注农村,关注农民,不必刻意,说偶然也对,说不偶然也对。从2000年走到乡村的第一步起,其实就是想弄清楚,现在的农村和农民是个什么样子,一方面给自己答疑,一方面给朋友们解惑。
刚开始也没有什么构思,整理采访笔记,越整理越多,走访一个村落,能整理出六七万字的东西出来,很成规模。就这样,就开始了所谓纪实文学的写作。刚开始,自己也不知道写的是什么,是文学,还是调查?不太清楚。
记得头一篇纪实性作品《380毫米降水线———世纪之交的北方农村与农民》在《黄河》上发表,阎晶明开玩笑说:你这文章如果不细看,还以为你为哪个人评职称写的论文。但是那篇文章一发表,在朋友们中间的反响很热烈。也正因为当时没有什么文体束缚,反而自由,文本到最后反而有陌生感。
畅:从2000年起开始调查走访农村,研究农村和农民问题,你把这个叫作“田野调查”,差不多十年时间,其成果就是花城出版社出版的40余万字的《天下农人》,这是看得见的,听说还有数十万字的没有发表。文学有时候也是做学问,需要一定的学识,包括文学之外的,并且还得沉下心来下大功夫才能有收获,是这样吧?
鲁:有一个现象不知道老畅兄注意到没有。纪实性创作,年轻的作家不能说没有,但少。上世纪八十年代,持续有一段报告文学热,赵瑜、麦天枢他们很年轻,老赵写《太行山断裂》的时候也就二十多岁。但后进的纪实作家,二十多岁的就少了。这里面可以探究的东西很多,比方说,是不是那一茬作家有更加丰富的人生阅历?是不是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有关系?是不是跟当时社会的人文环境有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不管怎么说,这个现象本身反映出,报告文学,或者纪实文学创作,至少在文体上有了深刻的变化。后来后进的纪实作家,开始报告文学创作,或者纪实文学创作,大部分都是在三十岁以上或者年龄更大之后的事情。
因此,可不可以说,报告文学创作,是一种有备而来的创作?韩石山曾跟我讲,有的人是有思想,再找材料;有的人,是有了材料之后,才有了思想;有的人,有了材料,也没有思想。思想,对一个作家很重要。纪实文学写作,大约就是有思想,才去找材料的事情。有备而来,阅历、思考、阅读,想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不到一定年龄段,似乎操作起来有些困难。或者说,没有准备,也很难介入。
就我个人而言,发表文字是一方面,思考又是一方面。因为掌握了一些社会学调查方法,还有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田野调查,个案总结,综合分析,跟文学视角有相通的地方,更多的则是不同。相通的地方,就是关注人。尤其是自己出身农家,每写一个个案,其实就是关注自己的父老,书写自己的兄弟。不同之处就很明显了,不仅靠个案来说话,还需要有足够的理论准备,用经济学、社会学模型来说话,在具体中寻找普遍,在特殊中找出平常。我写过现实的农村,写过农民工,写过由乡镇企业蜕变过来的乡村煤老板命运,还考察过合作化、生产队的破产,还有后来的土改田野调查。每一个考察点变化,莫不是思考所致,到了那个点,就得扎下去,深入下去。
大致上来讲,田野调查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整整十年时间。《天下农人》所收集的40多万文字,实际上也大致上是那十年考察记录。从2010年开始,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就没有进行下去。但思考没有中断过,因为好多疑问一直萦绕在脑子里,不想都不行。一想,当然又是新一轮的阅读。万事怕惦记,当你成天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各种相关的材料会不约而同簇拥过来,一些生僻的材料会在不经意间与你不期而遇。当某一个材料或者人物主动进入视野,是最令人欣喜的时刻。
《天下农人》里好多文章都没有发表过,就是自己考察的笔记,或者读书的想法。也没有发表的意思。林贤治先生编书的时候,收过我一些文章,后来朋友再推荐,林先生让我收集文章出一本书。把文章收集起来,大约有七八十万字的样子,删之再删,剩下四十多万字。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十年之间的走访和调查。
畅:我们知道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开放也是首先从農村开始的,农村对中国命运与前途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天下农人》记述了从共产党夺取政权开始的土改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农村,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我个人认为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兼具,是有厚度的作品。请结合《天下农人》谈谈你是如何看待中国农村的变迁。
鲁:这个题目就太大了。我不是研究专家,田野功夫得来的材料也大多感性,所以要总结出个子丑寅卯来,根本是老虎吃天。但是,中国农村百年变迁,远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你在农村任何一个角落和生活细节里都可以体会到百年历史激荡过的滚滚烟尘,不可以单独拿出来说。中国由传统的农业国,发展到今天,教科书式的描述已经足够了。大约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的农村好像不能够用“农村”这个词来表述,好多学者更愿意用过去的“乡村社会”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一下子廓清了好多过去模糊刻板印象,内涵更加丰富,它涵盖了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也涵盖了传统乡村居民的生存、秩序,还有过往,有空间感,也有纵深感。
中国立农万年,以农耕显背景,由血缘、亲缘、族缘、地缘构成的乡村社会非常成熟,农耕虽然是支撑乡村社会的经济基础,但肯定不是唯一经济依托。到乡村考察的时候,你会发现,村和庄实际上并不是一回事。村,乃以家族为核心的民居聚落,而庄,则完全依就近耕作原则形成。李家庄的人未必姓李,王家庄的人不必姓王,都是过去的田庄形式。村庄并不一定全是依托农业。村与村之间,阡陌相连,村落与城镇,又有官道、铺站、码头相瞩望,以集镇或者码头为中心,形成一个功能互补的经济辐射圈,也因为这一个一个有相当半径的经济辐射圈物流互通,最后形成富有特色的地域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固然是稳定的,但它又是流动的,更不用说乡村成员的构成,工农商学兵、致仕官员、成功商人,各色人等都有,并不全都是从事田力耕作为生的人。
当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农村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先有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后有几亿农民工进城大潮,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贡献不言而喻,城乡二元分治的结构在农民自己的推动之下开始松动,甚至开始瓦解,城市化率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0%不到,达到今天50%多。在这种情况下,再用“农村”来表述幅员辽阔的乡村社会,显然不合适。
“三农”,农村,农民,农业,是乡村社会的构成,可以分开看,不可分开说。早在2000年开始往农村跑的时候,就发现农村劳动力开始外流,进城打工的虽然不多,但已成风气。到2018年再度往农村跑,劳动力外流、人口外流已经是常态,不可逆转。2000年的时候,发现农村里还有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到2018年,村里能够见到一个孩子十分稀罕。学校撤并,弦歌不再;炊灶熄火,铁锁把门;老弱株守,生存艰难。吕梁山、太行山山区贫困村落更是如此。60多岁70岁的人都是壮劳力。今年猪肉价高,但村里很少看到有人家养猪,问为什么?答说:猪大了杀的时候,全村人都按不倒。都是老年人。
农业的内在变化还体现在农业本身。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低,这个数据每年都会公布。以山西省为例,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农业的国民经济总收入中,占比要达到80%以上,到了2005年,占比仅为5.1%,这个数据在此后虽然有波动,但波动并不大。但是,直到2019年,山西省全省农业人口还要占到总人口的30%到40%,也就是说,几乎将近一半的人口要靠这5%的产业吃饭生存,这种生存是什么质量的生存?
跟别人不同,当我看到一个个凋敝的山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多愁善感,欣慰多于感伤,甚至有些快意。不是我残忍,跟我一起长大的农家子弟,哪一个不曾做过挣脱乡土的梦?哪一个不曾为了“剥掉龙皮”奋争过?这几乎是本能。你已经出来了,凭什么让众多的同伴仍然株守家园,为你的所谓乡愁增添内容?道理不能这样讲的。
理性地看,乡村凋敝,实际上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城乡拉锯,这个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百年来的世界性景观。英美法日德,概莫能外。倒是在百年的拉锯过程中,诞生了辉煌灿烂的文学艺术,福楼拜、巴尔扎克、狄更斯、哈代,再到美国伟大的乡村民谣。尤其是三四十年之后,世界景观中的城乡拉锯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朝气充满创新精神的过程。而我们呢,却成天乡愁乡忧呀,奶奶的锅灶爷爷的烟袋,父亲的威严母亲的慈爱,村头的老树圈里的老牛,缅怀之外加妄想,呼唤回到集体化时代。这样的写作令人反感。说实话,这样的写作,还没有达到韩愈、柳宗元、孟浩然时代的悯农诗的境界。
畅:那你具体谈一下大家关心的乡村凋敝的具体原因。
鲁:原因当然很复杂,以至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固有观念,农村,只能是从事农业活动的场所,搞得城和乡完全对立起来,城乡联系也生生被割断了。为农恒务农,为农恒为农,一世为农,代代为农。农民,就得一辈子乖乖待在村里,就得乖乖待在土地上面,否则就不务正业,事实上就是让你世袭。虽然今天这个格局已经打破,但好些人还有这样的观念。这个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就是从1953年国家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开始的,从此就有了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之分,从此,城和乡被完全隔开,二元分治,流动的乡村不再流动。
我讲一件事,就可以明白这个户口制度给农村和农民造成的伤害有多大。路遥的《人生》被改编成电影,曾经感动了亿万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上世纪八十年代电影放映之后,在大专院校里的反响特别大。当然,那时候大家对这部电影深层的东西认识还不够,尽管已经戳到许多中国人,尤其农家子弟的心窝子里,但讨论仍然停留在“始乱终弃”“陈世美”之类的道德层面。后来,这部电影和谢飞导演的《黑骏马》一起参加一个国际电影节。《黑骏马》当时获了国际大奖,但在国内产生如此大轰动的《人生》却没人看得懂,评委和观众都很困惑,这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主人公那样一个有为青年,不做民办教师可以干别的啊,为什么非要回村里种地做农民?外国人当然不知道,中国有一个户口制度。户口制度把向上的通道堵死了。后来的《平凡的世界》,实际上也是书写几代农民这种无奈,这种命运,你再挣扎再扑腾,最终还要回归土地。这两部作品,经久不衰,被视为文学的常青树,但常常被人误读,一会儿是改革开放的历史畫卷,一会儿又是成长励志文本,它的深刻意义被严重低估了。难道我们听不到作品背后呼喊与呐喊?
现在好多专家为当年计划经济下的城乡二元分治辩护,为支援国家现代化说有之,为国家长治久安说有之。这个制度当初是怎么设计的先不管,但现在城乡二元分治的结果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农村就是农业生产单位,农民是身份意义上的人,制度化安排的痕迹非常明显。精准扶贫以来,精准识别,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因病因学,因这因那,实际上还是因为他们是农民,没有保障。
这就说到农村今天的凋敝。农村为什么凋敝如此?除了多年二元分治多年积攒下的问题反弹的原因之外,还有外的原因,也有内的原因。外的原因两条,内的原因也两条。
外的原因。第一,改革开放开始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化、生产队的低效组织方式走到尽头。但从全国性撤乡并镇开始,对农村实施的是一个去组织化去行政化的过程,公共服务、公共设施大踏步撤出。过去你到任何一个乡政府所在地,除了政府、学校、医院之外,邮政、储蓄、电力、财税、工商、供销、农机等等公共服务机构都有,与之相匹配的集市贸易、饮食服务、农产品加工企业都有,现在都难觅到踪影。第二,伴随以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为主题的城市改革,农村就医就学成本加大,但没办法,只能离开乡土进城去。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地分到户,农户呈原子化状态,但随着城市改革推进,却一下子使乡村的社会化程度大幅提高。农民就学就医,跟城市人口的支出并无区别。农村凋敝的根子实际上在城市那里,这个不深说。
内的原因。这就要说到农业。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努力,农业生产效率与效益大幅度提高。首轮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出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紧接着农业出现了第二轮变化,就是农业的装备水平增强,化肥使用、品种改良之外,还有机械化不同程度替代人工,农业已经趋向车间化工业化。这样的变化,几十年来几乎是不露痕迹的,所以被学者称为“隐性变化”。既是隐性,大家就感觉不到,几十年之后,突然呈现在面前,难免吃惊。
在晋北和吕梁山的一些地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耕种三四十亩地根本不算稀奇的事情,耕、种、收,全部机械化,这样就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城市打工的现金收入方式和现金收入额度是有吸引力的。这样,村里地里用不了那么多人,把劳动力推出田野,城市又需要大量的体力劳动者,把这些剩余劳动力拉了过来。一推一拉,农村青壮年外出成为风尚。在村里,你家里的年轻人如果株守家园,跟娘老子在地里劳作,会被视为没出息的表现。你看看,农村的社会伦理悄然在发生变化。
了解了农村为什么凋敝,建设新农村,振兴乡村才有参照,才可以找到突破口。
如何写好“受命之作”
畅:听说关于扶贫的长篇纪实《掷地有声》的书名是省委书记定的,无疑是“命题作文”(或者叫“受命之作”),但是我们知道这本书出来反响很好,发行超过了3万册,续小强说是他们北岳社近年来原创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这种写作的成功很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后,你又独立完成了十多万字长篇纪实《赵家洼———一个村庄的消失与重生》,发表在《中国作家》,赵瑜写了推荐语,同大多是关于扶贫的作品不同的是,你写的不是在轰轰烈烈脱贫中富起来的村庄,你写的是一个村庄的消失,视野不同,我认为这不是作家的另辟蹊径,它体现的是一个作家的思想深度,是作家的独立思考,赵瑜说“作品将社会学研究与文学性书写糅合得极好”。这无疑是写“受命之作”《掷地有声》的意外收获吧。请谈谈你如何看待“受命之作”。
鲁:《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开宗明义,是受命之作。作协机关是党群口的一个部门,经常承担这样的写作任务。承担这样的写作任务,常常出力不讨好。我跟赵瑜曾经探讨过这个问题。写作任务完成,可以交给上级部门与委托单位,写完也就写完了,最好的结果就是作为一项重点工程或者一个部门重要行动的另外一种总结形式存档,很难称之为文学作品。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你有细致的采访和调研,提出的问题也足够尖锐,但一个政策下来,还没等别人注意到,你提的问题已经解决掉了。还有,接受的任务足够重大,也足够激动人心,也确实利国利民,也采访了,也下辛苦写了,结果写到的主人公,比方地方干部,这个那个出了问题,这不是给贪官污吏树碑立传吗?还有,你写了之后,来自方方面面的审阅,涉及部门的人事纠葛,很难处理,最后即便出版了,也是一堆废纸。
受命之作,当然不能归类于报告文学,只不过长得像报告文学而已。
但是,受命可不可以进行文学创作?作家眼里的“主旋律”是不是可以与其他材料性总结或新闻通讯报道有所不同?反过来讲,请你作家去写,写出来的东西还跟其他材料性文字没有什么区别,要你作家干什么?到底可不可以呢?
可以。在《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之前,赵瑜领衔,我们曾有过采写王家岭矿难的先例,最后形成长篇报告文学《王家岭的诉说》一书,在社会上引起相当反响。这部报告文学,一是证明,多人合作,分头采访,集中讨论,单人执笔写作的方式是可以成功的,二是证明,受命之作,未必就不能彰显作家独特的观察角度与深入的思考,三是证明,受命之作,同样可以写出精品,甚至力作。后来,成书之后,我自己又把采访所得的7万多字,收入到《天下农人》里面,反响也不错。
赵瑜当初听说我们要写一部全景式反映山西脱贫攻坚的书,他很支持。告诫的同时,也多有鼓励,说这个事能完成。他讲,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受命之作,如果不是扶贫单位积极配合,凭借作家一己之力,你根本没有机会有如此广的接触面,没有如此深入的实地采访。即便写不成书,对作家本人也是一个锻炼,并不会对作家独立思考构成威胁,相反,更有利于作家进行独立思考与独立创作。
这样,我们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能说信心满怀胸有成竹,至少,不怯场。为什么呢?因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就在农村,脱贫攻坚的主要对象,就是农民,脱贫攻坚的主要手段,还是焕发出农业、农村、农民自身的活力。这样的题材,与自己平时的思考完全契合,所谓瞌睡给了一个枕头。
采访、写作,都很顺利。在写作的时候,首先,仔细梳理脱贫攻坚各项政策与百年乡村变迁的契合点,其次,把脱贫攻坚放置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农村变化的视野里考察,最后,把脱贫攻坚提升到三农问题的高度进行理论思考。事实上,也是一次有备而来的写作。
成书之后,从宣传部到扶贫办,再到扶贫干部那里,甚至在中国作协那里,这本书的反应还好,发行量超过三万册。刚开始书名不是《掷地有声》,是扶贫办和宣传部在审定的时候,据说是时任省委书记骆惠宁定的题目,具体不大清楚。但写作这本书,已经把多少年关于三农问题的思考写了进去。这不能不说是一次成功的尝试。
《掷地有声》完稿后,觉得还有些问题。视野毕竟是一省,虽然是一个点一个点深入下去的,限于篇幅,也限于采访深度,还有些东西觉得没有写完。实际上,采访过的每一个点,甚至每一个人,都能够构成一本书。比方,总书记考察过的岢岚县赵家洼村,村庄从一百多户人家,到总书记去的时候只剩下6户人家13口人,全都是老弱病残。我们采访的时候,这个村子已经消失了,剩下的人全部搬到县城的移民小区里。我觉得这个村庄虽然特殊,虽然极端,可是能不能挖掘出一些东西?这样,书写完之后,跟陈克海两个人自己驾车到了岢岚县待了8天,走访了已经搬到县城里的28户赵家洼原来的村民,从老一辈到子一辈,再到孙一辈,采访人数达50多人。最后形成《赵家洼———一个村庄的消失与重生》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写作的时候,把扶贫,把易地移民搬迁这些政策性的东西都退到背景上,集中笔力写每一个农民的家族变迁,个人的挣扎,村庄的兴盛与衰败。这个村庄从形成到消失,前后也不到100年的时光,印证了我的一个思考:村庄是流动的,并不是一个固化的存在。岢岚县的同志读了之后说:你可把一个村子翻了个底朝天。
写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约束,完全属于个人创作。
纪实作品的文学性
畅:我记得你说过认真思考纪实作品的文学性,某种程度有赵瑜的影响,请谈谈你所理解的纪实作品的文学性。
鲁:过去对于报告文学,或者纪实文学的文学性要求谈得少。既然是一种文学体裁,文学性要求必不可少,否则就是报告,而不是文学。但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体现在哪里?报告文学跟小说、散文、诗歌的文学性的区别很大吗?其实也不大。报告文学也好,纪实文学也好,其实是作家写作的文体选择,跟一个作家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不应该有区别,是题材决定你到底选择哪一种文体更合适。文体选择,是作家表达的选择,远非体制化的劃分。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被体制定位,你是小说家就写小说,散文家就写散文,写剧本就写剧本,评职称都是不同的系列,否则无法安身立命。没有道理。
讲到文学性,判断的标准很多,比方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也就是说,报告文学有新闻性的要求,最终还要落在塑造人物上面。没有人物,或者说人物的性格不具备“这一个”的特质,一篇报告文学要达到预期的效果怕是很难。
要求、标准很多,到底如何判断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或者如何在文学的维度来要求这种文体,在很大程度上,它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中国的报告文学作家都在思索,都在探索。
关于文学性,过去也有思考,但很零乱。想起大学时候上文学理论课,老师讲,文学性的最高要求,是真、善、美。当时以为是一个空洞无比的口号,后来细想,要求好高好高。
所谓真,从技术层面来讲,考察的是作家笔下的塑形能力,描摹功夫。三言两语,盐咸醋酸,来龙去脉,人物形象,活灵活现,现场再现。这是基本功,就是真,真实,真切,现场感强。
所谓善,就是抱什么心态去看待笔下的事情,书写笔下的人物。我常讲,作家应该怀菩萨之心看世界看人生,不仅自己是菩萨,笔下的人物也应该是菩萨、罗汉。不宽容,自己内心就局促焦虑,下笔就磕磕绊绊。
所谓美,当然是语言之美,结构之美。
我们山西的纪实文学作家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张石山、周宗奇、韩石山,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探索与追求。典型的就是赵瑜。谈到文学性,不能不说《寻找巴金的黛莉》。《寻找巴金的黛莉》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报告文学作品,后来居然被当作长篇小说转载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部作品的魅力所在。非虚构框架下,也能够刻画出经典文学意义上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典型环境,甚至典型故事。在叙述结构与叙述控制上,现实与历史交织,寻找与探寻相映,使这部作品具备了“这一个”的文本意义。所以,许多读者看了之后,就认为这是一部精彩的小说。
现在回过头来说赵瑜的报告文学创作,从早期的《太行山断裂》《强国梦》,到后期《马家军调查》,还有最近完成的少年记忆书写,这种文学的追求一以贯之。报告文学有一个恶咒,就是题材决定论。报告文学有无价值,看你选材是不是重大,事件是不是突发,问题是不是敏感,人物是不是足够优秀或者重要,等等。赵瑜的选材当然也脱不开这个,在某种程度上,他个人的气质与人生经历,天生就有这方面的优势。1998年抗洪,他在前线,2008年汶川地震,他在现场,2010年王家岭矿难,又冲上去。他和他的作品本身,也可能构成一个传奇文本。在写作上,赵瑜很认真,认真到让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他是现今少有的几个仍然用笔写作的作家,用什么纸,用什么笔,怎么装订,做得好仔细,甚至手稿的修改,也一个字一个字不含糊。赵瑜几十年的创作实践,至少对于山西报告文学或者纪实文学创作来讲,是一个标志,什么标志呢?是文体自觉的一个标志。这个自觉,就是始终注重报告文学的文学性。
畅:关于报告文学、非虚构、纪实文学几种说法你是怎么理解的?
鲁:这几个概念可不可以说是一个内涵与外延的关系?
老畅兄你也注意到,咱们这个访谈,开始就对文体本身很犹豫,一会儿是报告文学,一会儿是纪实文学,然后是非虚构。这个概念之所以游移不定,问题出在这种文体本身。
毫无疑问,报告文学属于纪实文学,纪实文学又属于非虚构文体。报告文学它能够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有其他文体所不能替代的东西,也有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特质,比方新闻性,及时性,“轻骑兵”,这是其他文体所不具备的。但任何一种文体要立得住,靠的不是怎么耍概念,而在于概念之下有没有足够多的经典作品与经典作家来支撑。
创作的现实是,好多纪实文学作品很难归类。比方黄灯的《大地亲人》,她写自己农村婆家成员的故事,比方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用的是社会学田野调查的方式在构思在写作。近年影响很大的一系列外国人写中国的书,《寻路中国》《江城》《打工女孩》《东北游记》等等,还有阿列克塞耶维奇的作品,罗斯、奈保尔的作品,这些作品,你说有新闻性没有?要说有新闻性,多少有些牵强。所以,各种文本在丰富这种文体的同时,给如何界定文体带来麻烦。说报告文学,他又不全是报告,不及时不当下,没办法,干脆叫纪实算了!
至于将来这个概念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到底用哪一个概念能够像小说、散文那样准确命名和界定,是另外一回事。纪实文学也好,非虚构作品也好,其实是对这种文体不同特点的强调,而不应该是全部。
畅:纪实作品的魅力在于不但有真实的故事和人物,还在于有生动真实的细节。能否结合你的写作实践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鲁:纪实性作品,顾名思义即是纪实,记录现实,不假文学虚构或想象。非虚构,是这种文体的生物学特点,娘生胎带,改变不了。当然,不可能说他就是简单的现实或者现场的再现,纪实写作,就像纪录片,就像摄影,与其说是追求真相,毋宁是从一个角度,一个高度看到的现实,远不是全部。至于作品的深度,作品的真实程度与感人程度,考验的不是笔,而是拿笔的人,考验的不是镜头,而是镜头后面的那颗头。
报告文学或者纪实文学写作过程,不同于小说、散文、诗歌创作,采访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没有充分细致深入的采访,写作几乎不可能。所以,采访也应该是纪实文学写作的一部分,这也是考验一个写作者本事的地方。
这就要说到唐德刚先生。他写过胡适、张学良、李宗仁的传记,完全用口述的形式写出来,然后再结合史料,对口述进行订正、串联、结构,口述同时又是对史实的一个丰富过程,历史因而显得生动无比。还有阿列塞耶维奇,她的作品几乎都是口述实录。有人看了之后,说不就是拿个录音机在那里录,然后整理出来嘛,很简单嘛,很小儿科嘛!其实不是的。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能够体会到作者的采访控制与采访设计。这些控制可能是临时、突然之间发生的,出现了一个节点,这个节点连叙述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然后被控制,改变或者回归叙述的主线索。
举一个例子。救援过程中,从矿井上面钻了一个大孔,然后把营养液顺着管道放下去。但是求援上来的几乎所有人都说,没有见到过那些东西。大家以为下面黑,八天八夜捂在几百米的地下,意识不是太清楚。黄风在采访的时候,也是偶尔听了一句,原来,下面被困的矿工中有经验老到的老矿工,他组织被困人员自救。从上面下来东西之后,他告诫大家不要吃,因为他在私人矿上待过,黑心的老板为了瞒住矿难事实,常常置矿工于死地,这怕是要害大家的。直到救援队进入被困现场,被困工人仍然不敢吭声,怕矿上派人下来害他们。
这些细节真是太震撼了!哪里是作家待在书斋里能够想象出来的细节?
还有,我在采访的时候,跟被采访对象聊天,尽量不把他们的叙述往矿难本身引,跟他们聊日常,聊家庭,聊孩子,聊收成。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职业意义上的矿工,无一例外,都是农民。他们如何聚集到这里,如何毫无防范堕入到苦难的深渊?矿难的背后,应该是田野,村庄,是三农问题。所以,我的采访最后虽然没有全部用到,还是积攒起七万多字收到《天下农人》里。
现实本身就是一种有想象力的存在。现实的想象力常常充满着意外与惊喜,充满着悬念与曲折,当你的眼光放宽,再放宽,一切都会如约而至簇拥到你身边。
纪实作品的知识储备
畅:写好纪实文学作品除了采訪调查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听说你每写一本书都会阅读大量有关资料,是这样吗?
鲁:前面已经说过,报告文学也好,纪实文学也好,它对作者来说,是一个有备而来的文体,如果你平时没有足够的思考、阅读积累,不可能把记忆、体验充分调动起来。
比方这些年关注农村问题,每一步深入,与阅读几乎同步。书架上关于农业方面的书籍很多,很多人奇怪,我居然还收集有品种改良方面的书,不仅仅是品种改良,气象、机械、耕作等等有关涉农事的书,我都有,都读过。为了解中国农村政策的变迁,甚至读《毛泽东年谱》《刘少奇年谱》《贺龙年谱》等等别人不太注意的书,然后顺着年谱提供的线索,再找相关讲话,相关文件和批示。当年,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江村经济》把自己的目光引向农村的,老先生的书当然要读,除此之外,民国那一茬致力于乡村建设的书都千方百计找来。现在网络发达,在网络上联系一些同好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经常感慨我们山西作家协会的人文氛围,读书环境太好了。大家坐在一起交流,小说、散文这些说得相对少一些,学问谈得多,谈文史,谈时政,甚至谈经济。我的文章里有许多比较不外行的经济学分析段落,经济学知识从哪里来的?就是在作家协会学的。
具体到写一本书。比方《潘家铮传》。潘家铮是1980年的科学院院士,1993年的工程院院士,“两院院士”,水电专家,结构力学专家,中国水电行业技术权威,是水电行业祖父级别的人物。他一生写过的文章有一千多万字,诗写得好,还写过科幻小说。写老先生的传记,他的技术著作你不能不读吧?都是公式,都是推演,十几元、百元次的大方程,想想都头大。为了搞清楚老先生的算法,读了几本数学史方面的书才能看进去。又几乎把中国水电发展史梳理了一遍,这样才敢下笔。书写出来,至少不外行。后来,另外一位院士朱伯芳先生审定《潘家铮传》,打电话恳请让我给他做传,可见《潘家铮传》写得还好。潘、朱两位老先生相差一岁,同辈人,当年已经八十八岁,不好意思推托,答应下来。有了《潘传》,朱伯芳先生的传很快就拿了下来。
吃这碗饭,不读书怎么可以?
用善直面真实
畅:纪实文学作品首先是真实,这样在作品里免不了会有些批评或者质疑,发表后自然就容易引起一些纠葛和麻烦,你是如何在真实的基础之上把握表述分寸?
鲁:这个倒不至于构成困惑。
绝对的真实怕是永远不存在的,报告文学,依所见所闻而呈现,依所想所思而再现,反映现实的同时,客观上也在参与着现实,干预着生活,本身就是与生活短兵相接的方式。文章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出一些纠葛与麻烦也正常。但也因人因事,我记得王蒙写过一篇文章,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报告文学“干预生活”的提法很厉害,不仅文章要干预生活,人也要干预生活,结果一位当时很有名的报告文学家常惹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
报告文学作品发表之后,引来麻烦,引出官司,好像也不奇怪。比方张平的《法撼汾西》发表之后,当事人甚至诉诸法律,告出版社,告作家本人。这场官司当时很轰动,可以看作是作品社会反响的一种反映。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不也一样?当事人扬言要告到法庭,甚至有律师还借此事写了一本书。我觉得这种麻烦或者纠葛再正常不过。
也有其他情况,还不仅局限于纪实性文字,有的作家写小说,描写一个人物,写一件事,也招致不必要的麻烦。这样的例子不是没有。也许有人说,事情和人物就是真实发生的,是真人真事。这就涉及纪实文学的文学性问题。前面说过,文学性的标准就是真、善、美,这三个要素须臾不可分割。但小说也好,纪实性文字也好,我在审稿和阅读的时候,经常发现有的作品足够真,语言也足够顺畅通达,但缺少善,或者干脆就不善,所谓的客观变成冷漠,所谓生动变成俗气,所谓幽默变成油嘴滑舌,这就不善,至少没有善。当善良、宽容、理解、尊重、人道、悲悯这些善的元素缺席的时候,你想想文章会是什么样子?不惹麻烦才怪了。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也不是一个分寸问题,或者度的问题,是一个作家自身的修养问题。
责任编辑阎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