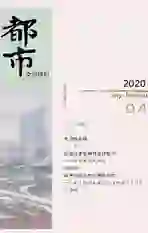生日快乐吗
2020-05-14王文
王文
翁如柏刚从大望路地铁站C口出来就有些后悔,那是一块被滚滚车流隔绝出来的孤岛,天色有点黯淡了,他想从对面马路上找到莉莉周,可是没有人在那边等谁。他有点后悔为什么不跟那个女人约定一个暗号,比如说,你喜欢比利·怀尔德吗?或者是别的什么无厘头问题。过了会儿,他又后悔为什么要牺牲一个睡懒觉的周末下午来跟她见面。
终于凑齐了一列路人横穿马路,翁如柏的焦灼心情不亚于二战时登陆诺曼底的盟军战士,可是对手在哪里呢?他再一次抬起捏在手里的手机,划开锁屏进入到他和莉莉周的聊天界面,他们的对话密密麻麻,一大段一大段不加标点符号的文字,是许多个深夜里无节制的倾诉的留存,像一夜情之后床单上留下的发丝,散发着慵懒的情欲味道。他确认这个女人是存在的,至少是个有灵魂的活人,在那上面她的头像是一个逆光的白裙女人的背影,像素太低了,连身材都看不清楚,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本人。忽然间一个新通知划过屏幕,是上周刚加的租房信息交流群,有人在问,朝阳门附近精装一室一厅小公寓有没有人要合租?他注意了一下时间,下午五点二十,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十分钟,他想问问莉莉周现在到哪儿了,可当文字敲出来之后,他又把它们一个一个清除了。
十分钟过去了,莉莉周仍然没有出现。有好几次,翁如柏几乎要跟微笑着迎面走来的女人打招呼,幸好他稍微犹豫了一下,看她们急匆匆地扎进前方人流里,不然又要费口舌解释自己认错人了。莉莉周长什么样呢,是像岩井俊二电影里那个吸引许多少年的女明星吗,不,看过这部电影的女生年纪应该有些大了,也许结婚生了孩子,也许已经离了婚过着潇洒自在的日子。
1号线上的那些地铁站翁如柏几乎都去过,不管是出门就离革命公墓不远的八宝山,还是遥远到几乎不像在北京城的苹果园。西单当然是最常去的,他和前女友可以在大悦城里消耗掉一整天,逛街逛到脚起泡,在随便哪家餐厅里吃一顿晚餐,看一部爆米花大片,然后提着优衣库或是H&M家的手提袋赶末班地铁。他在灵境胡同附近学过一段时间吉他,最后因为切菜时弄破了左手拇指无法按弦而放弃,当然这也只是个借口。大望路前面一站的国贸是拜访顾客常去的地方,他曾经在一场饭局后扶着进站口的墙吐了一地。唯独大望路,翁如柏以前竟然从没来过。这点真的有些奇怪。
翁如柏终于按捺不住点了发送键,“你在哪”三个字转了一圈之后出现在对话框里,紧接着,近乎同时,莉莉周发来同样一句话:“你在哪?”翁如柏还没来得及回复,对方突然发起了微信语音邀请,白裙女子的背影在屏幕上闪烁着,像是要跳起舞来。他抬起手机,立马听到有人喊他论坛的ID名:“麦哲伦!”声音来自于站在他身后大树下的女人。
说真的,翁如柏并没有太失望,可能他原本的期望值就不高。莉莉周个头有点矮,身上的烟灰色吊带连衣裙几乎要垂到脚裸上,跟睡裙差不多。她圆圆胖胖的脸笑起来会挤出一坨赘肉,说好听点是有些婴儿肥。头发是往后梳的,扎马尾,露出一个饱满的额头,皱纹倒是一丝都没有。年纪几乎看不出来,可能是因为长相太普通了,普通到可以冒充任一年龄段的女人。
“我俩真傻,一前一后站着也不知道问问。”莉莉周走到距离翁如柏大约两步远的位置就停下来,她拎着一个小巧的女式坤包,说话时会不自觉晃动。
“不好意思啊,我刚才看你低头玩手机,不像是在等人的样子,所以没有认出来。”翁如柏犹豫了一会,没有叫她昵称,在大庭广众之下喊一个女人“莉莉周”好像有點蠢。
“没事,我本来就不太显眼。”
“要不要先吃晚饭啊,离开场还有一个小时。”
“好啊,我也有点饿,七分饿吧。”
翁如柏觉得“七分饿”这个说法有点奇怪,他给“莉莉周”的年龄估值一下子减了五岁,对已经过完青春期的女人来说,五年简直就跟初潮到绝经一样遥远。
他们在大望路B口旁的骑楼下面走了一个来回,在每一家店铺前都逗留了一会,然后默不作声地走掉。直到翁如柏提议回到一开始经过的那家吉野家,“听说他家新推出了一款小火锅味道还不错”。莉莉周连忙附和道:“好啊,反正我也没有特别想吃的。”
进了店里之后,翁如柏让莉莉周去找位置坐下,然后自己排到长长的队伍后面。轮到离前台还有两三个人时,翁如柏突然听到收银员跟点餐的人说小火锅已经卖完了,问那人要不要点别的,那一刻他忽然感觉无比烦躁。他离开队伍去找莉莉周,看到她在靠窗的偏僻角落玩手机游戏,好像是《植物大战僵尸》。翁如柏像机器人一般复述道:“小火锅卖完了,别的你想吃什么。”莉莉周说:“都可以,你帮我随便点一样吧。”翁如柏莫名觉得有些生气,平凡不是罪过,但无趣却是,既然手机那么好玩为什么还要约他出来见面呢?他假装抬手腕看表说:“时间不早了啊,这场电影放映是不预定位置的,先到先选座,我们还是现在就出发吧。”莉莉周一边匆忙杀死一个靠近的僵尸,一边拎起膝盖上的坤包,在零星的枪声中头也不抬地说:“好啊,我们先去看电影吧。”
地铁口离郎家园16号足足有一千米距离,莉莉周走得有点慢,金属鞋跟笃笃响,遇到滚在路边的石子或易拉罐就轻轻踢开。实际上她好像不常穿高跟鞋,重心不稳,感觉总往一边倾斜,几乎要靠在翁如柏肩上,而后者缩着肩膀像是个猥琐老头。
翁如柏从西裤口袋里勾出一根剩了很久的烟,瞥了一眼身边的女人又放了回去。莉莉周靠过来小声道:“我帮你点吧。”然后从坤包里掏出打火机,是山寨的zippo,材质明显是喷漆塑料。看翁如柏有点惊讶的样子,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补充道:“我前不久跟朋友出去野餐,因为可能要生火,就随身带了一个。”
风很大,他们钻进了街角三面靠墙的空地里,莉莉周试了几次终于打出了火,明明灭灭的,翁如柏哆嗦着把烟头凑过去,映着蹿升的蓝色火苗,他注意到她左手无名指上的铂金戒指,和指缝间黄褐色的印迹。“啪嗒”一声之后,火光消失了。
一路上莉莉周都在喋喋不休地说着比利·怀尔德的事,不管是他的作品还是人生轶闻都如数家珍,好像她曾背过这位好莱坞喜剧天才的传记。她总是以疑问句结尾,比如说:“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很棒?”“我记得对不?”翁如柏一开始还认真地附和,后来渐渐发现他只要静静听着就行了。
“你是电影学院的老师吗?了解这么多。”翁如柏突然不耐烦地打住莉莉周的讲解。
“不,我就是喜欢看老片子而已,一个可以放松心情的癖好吧。”
“哦,我也是。”
“我知道,当然了,要不你怎么会在那个群里。”
翁如柏思考了一会才想起来那个群是指“朝阳群众迷影群”,上上个月他一口气加了许多微信兴趣群,领域包括健身、租房、读书、旅行、速配相亲和吃小龙虾的心得交流等等。当时他刚刚结束一段糟糕透顶的恋情,而他最好的朋友西蒙———一个有着八块腹肌的保险推销员告诉他这是认识新人和泡妞的好办法,“只要你在群里混个脸熟,就可以挨个加那些头像好看的女生的微信,然后同步推进,吹一吹自己,聊聊她们感兴趣的事,骗到本人真实照片或者直接视频,最后约长得漂亮的几个出来。”翁如柏本来就是极度内向的人,在发起了几个不尴不尬的对话全部石沉大海之后就没有动作了,直到前段时间因为偶然的机会发现有个女生跟他一样,加了以上所有微信群。
朗园入口处拉了一道电子栅栏,一个穿军大衣的保安眯着眼睛站在后面,双目无神,像是得了白内障似的。等两人正欲从栅栏旁边的缝隙中穿过时,白内障突然清了清嗓子,扭过头用浓郁的方言质问道:“干什么的。”
翁如柏愣了一下说:“来看电影。”
白内障说:“哪里放电影啊,里面在施工呢,路上都是水泥。”
翁如柏:“朗园16号馆,七点钟有比利·怀尔德回顾影展,我们买了票的,要不给你看一下。”
白内障说:“我没听说过,我只知道现在园区施工,领导交代了非请勿进,谁卖给你票的你们找谁去。”
“你们那个领导在什么地方办公,我去找他。”翁如柏的脸色明显变了,他硕大的喉结在领口下颤动着,像是藏着随时准备破壳而出的雏鸡。
“这事我能做主,不用麻烦领导了。”
翁如柏找到电子票上的联系方式,气冲冲地准备给主办方打电话,莉莉周却突然拉住他的手往外走。那气势有股不由分说的坚定,还好,她的手指是温暖而柔和的,他们的指腹贴在一起,隐约能感到对方丝丝缕缕的纹路,像是两个人的命运要彼此渗透进去一样。
“怎么了,不看电影了?”翁如柏莫名其妙地问。
“干吗非要跟一个不讲理的人死磕呢。”
莉莉周领着翁如柏绕到朗园围墙后面,有一道疑似要打通作为后门的缺口还没有建好,留下半截土墩。翁如柏在后头看到她滚着荷叶边的裙裾大幅摆动,像是要从行走的脚上开出花来,无聊地想起西蒙跟他说过,通过观察臀部可以了解到一个女人有没有生过孩子,而此时他的视野里只有一个丰满的不规则的椭圆,处于晃动与扩散中,始终无法定焦。在莉莉周扶墙跨上土墩的那一刹那,翁如柏伸手扶住她的腰,之后又从腰滑到臀部边缘,托着她踩上那些摇摇欲坠的碎砖。
翁如柏跳过去以后看到莉莉周靠着墙拨弄高跟鞋,他问:“鞋跟崴了吗?”
“不,进了点沙子。”
翁如柏搀着莉莉周坐在墙角,让她腾出一只手倒鞋里的沙子。莉莉周的小腿很结实,在光滑的肉色丝袜里绷得很紧,几乎可以切出几个层次分明的剖面来,怎么说呢,像是特大号包装的金华火腿。
“我以前在报社上班,楼下保安也很讨厌,有时候忘记带工作证了他明明认得你可就是不准进,在签到簿上签到他也要站在旁边核对时间,搞得像单位是他开的一样。广告客户来谈合作不仅要登记信息,还得打电话跟总经理请示,搞得我们双方都很烦。后来干脆随便找了个理由让物业换了一个保安过来,后来的人虽然做事马马虎虎,但却让人省心很多。”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那可能是他手上唯一的权力,他也想过一把说一不二的瘾。”
“这倒是能说通。很多女人都喜欢在老公开车时坐副驾驶座上瞎指挥,特别是倒车的时候,你方向盘往右边打一点,稍微打一点,别打那么多,你看卡住了吧,退回来重新弄……但你这么能为什么不自己开呢,无非就是想满足一下自己的控制欲而已。”
“你也是这样的女人吗?”
“我自己开车啊。”
翁如柏本来想问你也会对你老公这样吗?但总觉得有些不妥就没说出口。
朗园及其周边是原北京制药公司的厂址,因为效益不好萧条了很长时间,直到近些年转型改造成文创园区。充当艺术电影放映院的16号馆坐落于园区边缘,是药厂曾经最大的车间之一,而现在车床和流水线早已被清理一空,粗犷的钢筋柱子直接暴露在外面,没有任何多余修饰。偌大的空间里空空荡荡,后面五分之一部分是阶梯,放了几排座椅,前方挂了一块投影幕布,权做放映之用。唯一的光源来自于头顶的大型聚光灯,在水泥地板上打出蛋清一般虚幻的光晕。翁如柏和莉莉周坐在第一排,他们原先可以有更好的位置,但莉莉周却搬出小说《戏梦巴黎》里的理论说,影像经过一排排观众的目光侵蚀会被损耗和污染,变成了无生趣的二手货,而这是一个骨灰级影迷无法忍受的。
银幕上米高梅的狮子跳出来吼了一阵之后,光源熄灭了,头顶房梁上那星星点点的光点不知道是金属还是漏光,除此之外是一片浓稠的黑暗,使得整个空间像宇宙一般浩渺。翁如柏不确定应该和莉莉周保持什么样的距离,他和莉莉周的手都垂在两个座椅之间的缝隙里,轻轻一勾就能缠绕在一起。他T恤领口裸露的肩上能感受到莉莉周的发丝,痒痒的,有意无意地来回逡巡着。
翁如柏偷偷看莉莉周的侧脸,一半浸沒在黑暗中,一半沐浴着从屏幕上折返过来的光影,肉嘟嘟的脸颊不见了,只剩下一道凛冽的曲线,从眉尖一路划到下巴,像是从素描上抠下来的剪影。
莉莉周突然掐了一下翁如柏的手心,他把脸侧回去,假装在认真看电影,别人笑他也跟着笑。那边幽幽传来她的声音:“你知道为什么Baxter的上司老是借他的单身公寓与情人幽会吗,六十年代美国还没有快捷酒店,男女去宾馆开房都要带结婚证明,不然无法办理入住,所以他们连偷情都没有地方去。”
“现在倒好,人们反而不太愿意在酒店里幽会了,他们在公园里,在办公室里,在KTV,反正只要有地方能躺下来就行了。”翁如柏本来还想说在电影院里,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那你呢,你喜欢去哪里?”
“其实我很少出来玩……我觉得两个人总得有点感情才能发生关系,不然就有点脏。”翁如柏不愿意说这是他自幼儿园毕业以后第一次单独约异性出来,想必即使说了她也不会相信。
“你知道吗?比利·怀尔德一直暗恋玛丽莲·梦露。”
“没有男人会不爱她吧。”
“当比利·怀尔德初次遇见梦露的时候,她已经嫁给第三任丈夫了。拍《热情似火》那会儿,梦露怀孕了,她对自己的美貌很自信,执意要拍彩色电影,但比利·怀尔德努力说服了她,他用黑白胶片拍出了她最性感妖娆的样子。”
“那可能也是一件幸运的事,即使再美丽的女人,把你天天绑在她的床上,闻她的脚臭,忍受她的所有怪癖,总有一天也会乏味吧,还不如在一开始就保持距离,给自己留一个念想。”
“麦哲伦,你真是客观冷静的哲学家啊。”
从电影院出来以后,莉莉周问翁如柏接下来去哪里,夏末秋初的北京街头吹着令人酥麻的晚风,那温度和力道都是恰到好处的,像是在亲切地挽留人们在马路上流连。翁如柏和前女友在一起的时候,看电影是一天行程结束前的保留项目,之后就牵着手一起坐公交车回家了,现在他不知道要去哪里,甚至搞不清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站着思考了一会,从腹腔深处传来的饥饿感让翁如柏意识到他们当下最亟需解决的问题。他说:“饿了吧?先去吃点东西。”
又回到了大望路地铁站B口,两侧骑楼下的店铺大半都打烊了,只剩下一些连锁快餐店仍在营业中。翁如柏提议说去吃炸鸡汉堡,还可以从便利店买几罐啤酒带进去,莉莉周却推说这么晚了不能吃得太油腻,否则不仅会长胖而且还会刺激内分泌系统导致脸上长痘屁股生疮云云。最后他们去了那家角落里的星巴克。
昏暗的灯光下,莉莉周盘桓在玻璃橱窗前,再三比较,挑选了一份黑森林蛋糕,一份扁桃仁可颂,一份咖啡提拉米苏,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季节限定新款,翁如柏忽然明白原来女人的养生之道大都是挂在嘴边的慰藉,甚至经受不起一道甜品的考验。
两个人坐在靠窗的卡座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的金地广场和新世界百货,不远处几栋联排大厦上挂着许多色彩斑斓的logo,字母之间插进去一个虚焦的月亮。这里是北京的CBD,可一到夜间就空旷如广场一般,偶尔几个路人在玻璃窗上留下急遽消逝的侧影,像是被颠倒过来的地心引力拽向城市的另一边。
莉莉周一边小口抿着拿铁一边说着她许多年前初来北京的事,“我第一次参加面试,就是在那栋写字楼,当时才刚刚建成使用,二十一层,我记得很清楚,楼下保安说只有打卡的正式员工才能用电梯,我什么都没问就走楼梯上去了。当时穿的还是找同学借的高跟鞋,磨脚,有点疼。等我走进会议厅时全身是汗,白衬衫也湿透了,里面所有人都笑我,搞得我莫名其妙又很尴尬,后来才想起来他们一定都看见我内衣颜色了。”翁如柏掐指一算那应该是十年之前的事了,那么莉莉周现在多大?
莉莉周一开始坐得很端正,抚平裙子,双腿交叉于前,但过了一会就用左脚褪掉右脚的高跟鞋,再换另一边。她放下咖啡杯,开始端起甜品,小勺撞在瓷质盘子上发出清脆的声响。翁如柏看着她先是慢慢咀嚼,然后大口往嘴里塞东西,不管是缀在顶部的草莓,上层奶油,还是下面的蛋糕都一股脑儿消失在她整饬一新的牙缝后面。他想安慰她说:“不用担心,没人跟你抢。”但最后还是神色黯然地看着她重复吞咽的动作。
“啊,就剩这么一点了,我刚才是真的太饿了,就顾着自己吃,不好意思啊。”莉莉周把剩下的一块慕斯蛋糕推到翁如柏面前。
“没事,我今天出门之前吃了很多零食的。”翁如柏又把蛋糕推了回去。
莉莉周说要去一趟卫生间,从坤包里取出一个小盒子,然后把包交给翁如柏保管。那是一个轻奢品牌,对时尚孤陋寡闻如翁如柏也是认识的,只是好像用了很久,底部有几处脱漆的地方。拉链没有拉严,他抚摸着树藤似的皮革纹路,从敞开的缝隙里看到一叠文件还有一些零钱。他没有继续拉开窥探里面的东西,对有些起初就不知道底细的人还是永远不知道的好。
几分钟之后,莉莉周才返回,她把发带解开,长发散落在肩上,似乎重新画了眼影,补了口红,又打了浅浅一层粉底,这样比下午初见她时要妩媚许多。圆脸和不高的个子反而让她显得比实际年龄小。
“我租住的地方在做老旧小区改造,来了一群东北壮汉把阳台外墙拆了重砌,磨磨唧唧,都一周了还没修好。现在我床头离外面的大气只隔着脚手架上一层绿纱网。我去找居委会理论,他们竟然说我不是业主就不管不问。”
莉莉周没有克制住笑出声来,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就轻轻用手按了一下嘴唇,像是可以把笑声咽回到肚子里。
“哪里很搞笑吗?”翁如柏平和道。
“我突然想到了侯导拍的《风柜来的人》,一群青春期的男孩子被骗到烂尾楼上看彩色大银幕欧洲片,笑死。”
“其实我是想让你看看能不能在媒体上曝光出来,他们太过分了,需要社会关注才能让施工方重视问题。”翁如柏站起来,捡起椅子上的外套抱在怀里,现在是居高临下看着莉莉周。从这个角度他能看到她两鬓微微露出的白发,梳在耳侧的隐蔽位置。
“我工作的媒体不是都市报,《贵刊》你听说过吗,就是一本砖头厚的铜版纸杂志,封面是当季最流行的一线明星搔首弄姿,翻开一半都是奢侈品全彩广告的那种。领导不会让我做這种选题的。”
“我知道,但你总有门路……比如说媒体同行可能会感兴趣……算了,我也就心血来潮跟你一说。”
“下面我们去哪里。”沉默了很久莉莉周说。
“随便走走吹吹风吧。”翁如柏披上了外套冷冷地说。
两个人踉踉跄跄地推开玻璃门走到外面街道上,对面的大望路地铁口在雾霾弥漫的夜色下像是张开血盆大口的怪兽,零星走进去几个匆匆过客,消失在牙齿般矗立的闸门之后,却一直见不到有人从里面出来。
“现在还能赶上末班地铁。”翁如柏说。
“刚才喝了拿铁,我有点兴奋,不着急回家吧。”莉莉周的脸在晚风中涨成猪肝色,鼻尖也变红了,喝醉了一般。
“那我教你玩电子游戏吧,之前跟你说过的《生化危机》,也是打僵尸,但比手游刺激多了。我还可以带你玩《红警》《最终幻想》《穿越火线》。”
“好啊,我们去哪里玩。”
“找一家有电脑的酒店就行。”
翁如柏下午上班时就在网上查到了附近一家便宜的快捷酒店,他原以为莉莉周会稍微矜持一下,甚至是怪他图谋不轨,但结果她没有表现出一点拒绝的意思,只是简洁地回应道:“去吧。”于是翁如柏带着莉莉周不紧不慢地往目的地赶。
那家酒店在通惠河边,看地图上离得很近,但却要在迷宫一样的蜈蚣胡同里钻来钻去,怎么都找不到正确的出口。翁如柏内心有些着急,但却装作冷静地说:“不远了,还有几分钟就到了。”过了一会儿又说:“刚才看错了,得往这边走,快了快了。”莉莉周倒是没什么不满的表示,只是隔一段距离就要提一下鞋跟,似乎有些跟不上。
在近得可以看见酒店招牌时,莉莉周突然紧张兮兮地停下来,拉开坤包往里面翻。翁如柏打开手机照明功能,靠过来问:“怎么了,刚才丢了什么东西吗?”
莉莉周说:“我好像忘带身份证了。”
翁如柏说:“啊,你再找找,我们不急。”
莉莉周蹲在地上抱着包又寻找了一会,手机射出的光柱打在她胸口上,隐隐透出内衣的轮廓和蕾丝边缘,脖颈上的汗一缕缕滑落下来,像露水坠入草垛中。
“真的没带,我走之前明明从抽屉里拿出来了,可能是被别的东西遮住了,就没有装进去。”
“现在怎么办?”翁如柏关了手机照明功能,向着黑暗深处问。
“现在怎么办?”莉莉周一边舔舐嘴唇一边重复道,像是在问自己。过了会,她站起来说:“我单位就在大望路附近,车停在写字楼地下车库里,要不你跟我去一趟吧,然后我们随便去哪里都行。”
半个小时之后,两个人来到了大望路地铁C口附近的那座大厦,刚踏入停车场,头顶灯光“啪”的一声亮起来,是一片接一片的,天花板瞬间被照成煞白,像是连绵不断的云朵。
“你看过《志明与春娇》吗?开头有个发生在停车场的鬼故事。我从前很害怕晚上来这里开车,总感觉有变态者潜伏在哪个角落里。”
“那是电影里的情节,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变态者。”
“今晚倒是不怕了。”莉莉周扭过头看翁如柏,眼神直勾勾的。
“你知道吗?其实我才是变态。”翁如柏突然拉起莉莉周的手躲到一台SUV后面,然后脸抽搐起来,发出诡异的笑声。“哈哈哈哈……”那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被无限放大,叠在一起向四周飘荡着。
莉莉周捂住翁如柏的嘴说:“不要这样了,真的很吓人。”
翁如柏没有停,表情有些狰狞,“我以前在中介公司卖二手房,底薪少得可怜,根本没法维持生活。为了多拿提成我一天到晚装孙子,见了谁都笑嘻嘻,只要能签合同让我当场表演倒立都行。我有个客户是刚刚拆迁的老北京,横得很,你要是在大街上走得比他快都会瞪你一眼。有次我们因为琐事吵起来了,他拿啤酒瓶砸我,在我脑门上划了一道口子,我没报警,也没在外面声张。最后我们签了协议———那房子各方面条件再也找不出第二家了。过户不久之后我买了老鼠药,晚上偷跑过去把他家养的小奶狗毒死了。再后来我还砸过客户家的花盆、太阳能和窗玻璃,真过瘾,一旦开始就没法停住。有个傻缺新买的宝马X6被我刻了一行颜体字,臭傻逼。”他几乎要笑出眼泪来了。
莉莉周飞快跑走了,高跟鞋摩擦地板发出类似于锯东西的声音,人和声音很快消失在车库更深处。
一切都平静下来了,灯光熄灭,陷入了完全的黑暗。
翁如柏失魂落魄地往外走,他也不知道自己刚才怎么了。被响动惊醒的管理员过来查看情况,用手电筒指着翁如柏问:“干什么呢?”翁如柏什么都没说,继续低头走着。管理员拦住他说:“你是来开车的?车呢?”翁如柏说:“没有。”管理员紧紧攥着他的手腕说:“那你来搞什么,刚才声响是你弄出来的吧,这么晚了折腾什么呢。”
两个男人在沉默中对峙着,好像在较量谁更有耐心,直到一辆奶白色帕萨特停在旁边。一声鸣笛之后,车窗摇下来,莉莉周探出头对翁如柏说:“上车吧,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那语气有些亲昵,像是跟男友或丈夫说话。管理员小声嘟哝了一句就放开了翁如柏的手。
“我们去哪里?”在副驾驶座上翁如柏缓慢地开了口。今晚他们都非常疲惫,疲惫极了,也许靠在座椅上都能睡着。他打开车窗,让深夜有些寒意的风灌进来,呼呼的风声像是有人在打鼾。
“其实今天是我生日。”莉莉周没来由说了一句。
“那是不是要好好庆祝一下,现在离零点还有十分钟。”翁如柏有气无力地看了一眼手表。
“我们刚刚吃了蛋糕喝了咖啡啊,本来应该买点红酒的,不过也无所谓啦,我没那么讲究。”
车停在通惠河边的小路上,他们开始亲吻,是那种抵死缠绵的法式深吻,舌头像小动物一般游向对方口腔深处。翁如柏渐渐有了感觉,他曾以为自己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不会有了,此刻却非常明确,明确得不容置疑。
如果此时从车窗外面往里看,会发现司机和副驾驶座上两个人紧紧缠绕在一起,好像是一对連体婴儿在拼命争夺身体控制权,又好像是一个章鱼人分出许多触手来,在寂静的深海里捕捉食物。
翁如柏得到鼓励,把手伸进莉莉周的连衣裙里,沿着锁骨一路向下滑,直到爬上那高耸的双峰。他像鉴赏瓷器一般小心翼翼地抚摸着,既不急促,也不过分流连。抹胸下面好像有一层夹垫,软绵绵的,有点厚。当然这无可厚非,这世界上还有多少东西是纯天然的呢,他没有那么吹毛求疵,但还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莉莉周忽然用力推开翁如柏,但这时候翁如柏已经认识到问题所在了。他像拔萝卜一样把自己拔出那个温暖的窝,然后往后退缩了一段距离,几乎要倚在车门上,甚或是夺路而逃。
“对,我做过一个小手术……切除了一部分,不是全部,医生说最多三分之二。”
“没事,我不介意。”翁如柏别过脸说。”“对生活有影响吗?”他追问道。
“没有感觉,有时候半夜醒过来手会不自觉地往那边伸过去,然后突然想起来被切除了。”
“就是不完整的感觉?”
“也不是,本来那个东西除了哺乳之外也不是不可或缺。”
“但人类就是很奇怪,总是在意一些附加的东西,而不是活着本身。”
莉莉周打断翁如柏道:“那我们继续吗?”
翁如柏没有回答。他往自己大衣口袋里掏香烟,可只碰到几枚冰冷的硬币,竟然一根都不剩了。他望着莉莉周的脸,在月光下褪去了所有修饰,坑坑洼洼的表面像隔夜的蛋糕塌陷了几块,多少有些恶心的感觉。他慢吞吞地说:“车里有点闷,我想下去走走。”
刚刚跨出几步,翁如柏隐隐听到身后传来啜泣声,细微得像是夜里磨牙的响动。他犹豫了一会,站定之后缓缓转过身,对车上的女人沙哑地说了一句:“生日快乐。”
责任编辑杨睿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