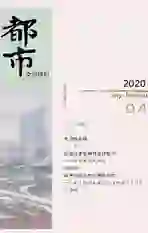苏州四章
2020-05-14刘云霞
刘云霞
诗的王国
苏州是诗的王国。
清新、抒情、恬适、浪漫。“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好像沿袭了王维的诗风,又全然没有王维画诗中避尘隐世的灰色基调。吴侬软语恰如《山居秋暝》中的山间鸟鸣、石上流泉,以清柔脆亮之“动”,描绘出动中有静的婉约新风。
亭台楼阁、泉石花木、小桥流水、柳絮笙歌……随处都是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的生动意象!即使目不识丁者,也会在这里读到飞光流彩的清新诗句;即使是木鱼顽石,也能化成其中鲜活灵动的音符。
张继,原本是尘埃般众多的游者,分明是被“江枫渔火”“月落乌啼”的浓浓诗情裹住了脚步,他一番吟哦嗟叹后,索性顺势随地泊在了枫桥之下一个永久的意境之中,千年的风烟里,他和他的《枫桥夜泊》痴心不改地驻守在那里,早已忘了今夕是何年。
木鱼声声、香火袅袅的寺庙,在完全“自我”又全无“自我”的枯寂中,原本是与诗,尤其是情景诗不相干的,故而多栖身于单调呆板的北方。但一经诗情画意的苏州浸染便立即柳暗花明了。这不,大诗人杜牧目光轻轻掠过,立刻有一个迥然有异的全新天地:
远上寒山石径斜,
白云生处有人家。
停车坐爱枫林晚,
霜叶红于二月花。
“白云、石径、人家、枫叶”,浓淡有致,远近相宜地跃动其中,使原本凝重肃穆的寒山寺倏然有了人性的灵动;由寺”而“诗”,寺一旦有了诗的语言立刻焕发出生命的光彩!
究竟是点一缕虔诚祈祷命运呢,还是秉一束诗香绚烂情怀?还真令人颇犯踌躇呢。
白居易是坐一顶官轿来的。因为脚下诗愫太浓,一步一摇、一行一颤中都是平平仄仄的韵律,为官之“闲”,“行”且“望”中,满目是写不完的诗意盎然:
阖闾城碧铺秋草,
乌鹊桥红带夕阳。
处处楼前飘管吹,
家家门外泊舟航。
———《登阊门闲望》
绿浪东西南北水,
红栏三百九十桥。
鸳鸯荡漾双双翅,
杨柳交加万万条。
———《正月三日闲行》
而最令白居易诗兴大发的还是“七里山塘”。这是身为刺史的白居易以一代诗豪的大手笔写下的最动人、最具影响力的传世“史诗”!
此时,恐怕连他自己也有些恍然:到底是在尽为官之职呢,还是在尽兴赋诗。就这样剔糟除粕,删繁就简,清淤除塞,插红播绿,三下五除二便在杂乱无章中提炼出了简洁清新的意象,开出了晓畅明快的新思路,描绘了润泽千载的美好意境。
七里山塘之“诗”,实在有着超脱凡俗的艺术魅力。白居易之后,一代代文人墨客、朝野名士争相同题和之。最大的应和者,应是清乾隆帝。他不仅口吟笔诵,频写“山塘”,后来索性御笔一挥,先后在北京万寿寺、颐和园兴土动木“写”就了完全押“韵”合“辙”于白居易之作的“七里山塘风貌”。
为官的白居易就这样在诗的苏州成了永恒。“七里山塘到虎丘”,一千多年过去了,它仍站在岸边,导引着一代代、一批批游人,在他亲手营造的“一声柔橹一销魂”的诗境里畅游。
而山塘之外的苏州人,哪一位又不是生活在诗里?
心的天堂
走进苏州,心弦立即被一双温情的手拨动了。
分明从未谋面,却又似曾相识。身为地道的北方人,面对“小桥、流水、人家”之境,突然有了一种久违的故乡的感觉———恍惚间已走进了马致远的那首元曲。但毕竟是在遥远的异域他乡,物是人非的;心底隨之涌上“枯藤、老树、昏鸦”的凄凉和“断肠人在天涯”的伤感,眼睛倏然间潮潮的。
相对于高频率、快节奏,紧张、喧闹、石质、刚性的上海,苏州恬淡、安逸、轻柔、秀丽,是名副其实的水的世界。“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巷小桥多。”一湾湾河,如少女娴静羞涩的心事,情脉脉,意朦胧;一条条巷,如少女的百转柔肠,清亮而温馨;一座座桥,如梦幻中的彩虹,连通心的故乡。
沐浴在血脉般纵横密布的水网中,不仅女儿们个个如出水芙蓉,似乎苏州的一切都充溢着水的轻柔与秀美,比如苏丝,再如苏绣。一曲苏州评弹根本无须听懂词意,弦响歌起,袅袅娜娜的声音立即飘绕起来,弹醒人一腔心事,撩动人满腹柔情,正所谓“歌喉婉转吴音糯,弦索铮琮水调新”。连通常意义上棱角分明、充满骨性的建筑物,在这里也是柔婉有加,别有一番景致:门是“别有洞天”的景之“框”,窗是图案各异的透明引景画,墙是剧中小旦轻扬手臂抛落的水袖,屋是错落有致飘然而落的童话世界……名字也是如此柔美脱俗牵动人想象的翅膀:月亮门、漏窗、云墙……
移步一景,举目皆画,“家在画中住,人在画中游”,一切都是如此纤巧精美,透出十分的讲究,一切似乎又是轻聊慢行中不经意间的产物。难道,这就是苏州?与世无争、闲适淡泊、朴实无华却有着无可比拟的内在魅力?
曾有人比喻,苏州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好一个“宁谧”与“后院”所在!在这里,谁又能不轻了步履,缓了声息,悄悄地与花草水流、与娴静的文化、与自己的心灵惬意对话!
难怪当年那些贬官,从坎坷泥泞的仕途上满心创痛一路退下时,会选择这里作为疗伤的后方。沧浪亭、狮子林、拙政园、留园、环秀山庄、网师园、艺圃、耦园、退思园……一座园林就是经历了一番挣扎与躁动又归于宁静的一颗心灵,每个园林都写满了人与自然的秘语,都是一部东方文化的百科全书!咫尺之内见乾坤,方寸之间有文章,难怪苏州园林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早就听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直不以为然。如今看来,这水影花光,亦诗亦景的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岂不就是世人安魂栖魄的天堂!
虎丘随笔
名人效应真是不得了。
“游苏州不游虎丘,乃憾事也”。大文豪苏轼随意间的一声感叹不知吸引了多少人的脚步。
其实,人们也不尽是逐苏公来的。吴王阖闾的魂灵及其相关的串串故事和传说,才是人们最原始的追逐目标,也是起初舒展于整个山丘的全部内容:“阖闾葬虎丘。十万人治葬,经三日,金精化为白虎蹲其上,因号虎山。”(《吴越春秋》)
关于吴王墓,据《吴地记》载,因以扁诸、鱼肠等剑三千殉葬,又“铜椁三重,水银灌体,金银为坑。”这使虎丘,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诱惑和悬念。
为此,秦始皇、孙权、风流才子唐伯虎等,都曾把猎奇的目光投向古墓:“秦皇凿山以求珍异,莫知所在。孙权穿之亦无所得,所凿之处遂成深涧。”但最终只是成就了“剑池”之名,为吴王墓平添一道神秘的水障,为虎丘山徒增一章人文续页而已。
在他们身后,一代代、一批批稠密的脚步纷至沓来,崖壁、山石上,门楹、寺梁上,沿山路径上,满目的书法、石刻、对联、牌匾,从帝王到平民,从偶至的过客到专门的猎宝者,到处是兴奋的眼神和不绝的赞叹。不同时代、不同游兴的人们,沿途撒下景深、大小、色泽不同的风景,一处风景、一丛故事、一团秘密,又引来一批批后来的追逐者,使渊源于“吴”的虎丘,有了“吴中第一名胜”之誉,成为苏州2500多年历史的百科全书,并在平坦、单一中,多了横岭侧峰的曲折和韵味。
我很好奇苏公当年“憾”之所在。
从苏公所在的北宋观景台望去,绝不会有建于元代的断梁殿“断梁”之奇,更不会有缀于其上的“大吴胜壤”“含古藏真”等后来者的落墨。虎丘塔新建不久,谁也不曾料到会“一斜”千年而不倒,并以领先近400年的老资格比肩于意大利比萨斜塔。那么,被苏公引以为“憾”的,除了一穴秘密,当是天作的自然之景?比如,“池暗生寒气”之剑池?比如,曾播下茬茬传说,但最终只有“生公说法,顽石点头”这句成语抽穗结果的“千人石”?比如,“塔从林外出,山向寺中藏”的虎丘之异?
那么,在今人眼里,前山十八景、后山十八景的虎丘,在彼时又该做怎样的增删浓淡?
镜头回放到唐宝历年间。作为父母官,白居易沿着自己开通的七里山塘一路走来,驻足“海涌潮辉”的水码头放眼望去,没有宋代的虎丘塔,没有元代的断梁殿,也没有缭绕着道教和神话之雾的“二仙亭”;就连他亲手撰写了墓志铭的“真娘墓”也绝不会像今人所见———因为,据史料载,除了虎丘塔、断梁殿,整个山丘建筑都不过百年。那么,他致力导引着的一方名胜之地又是怎样的一个境况呢?
在白居易之前,盛唐大书法家颜真卿早已捷足先登,他不仅挥毫泼墨留下了“真剑池”“假虎丘”的故事,也留下了“老僧只恐山移去,日落先教锁寺门”的趣闻轶事。
镜头向今天推进。在明人眼里,虎丘有九宜:宜月、宜雪、宜雨、宜烟、宜春晓、宜夏、宜秋爽、宜落木、宜夕阳;又据袁道宏《虎丘记》,在“九宜”之时,必是“游人往来,纷错如织”。如此说来,断梁殿上“塔影在波山光接屋,画船人语晓市花声”那副描写虎丘之盛的楹联,应该是哪位文人雅士在繁华而美丽的虎丘山一遭酣游后的一声赞叹?
由袁道宏《虎丘记》看明时的虎丘山:“文昌阁亦佳,晚树尤可观。面北为平远堂旧址,空旷无际,仅虞山一点在望。”而无论当时正“佳”的文昌阁,还是已沦为旧址的平远堂,对今人而言,都只有即使在案头也难读到的传说了,真所谓“山川兴废,信有时哉!”
历史,走得太远,一路风侵雨蚀尘掩,许许多多的真迹渐漫漶了起来,又有一重重岁月的植被葱葱郁郁地漫过来,留下更多道不清的“憾”,解不开的谜。
面对走了2500多年之久的虎丘,我突然对“文物、古迹”的分量有了又一重的感受。
枫桥品“愁”
恐怕连张继自己也不会想到,行走中随意撒落的一缕愁绪,会成就了一座小桥乃至他本人的千古之名。
这是怎样的一种愁绪。原本该披红挂绿、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如今却孑然一身,秋风萧瑟天气凉。脚步是如此凝重,连一滴秋露都能结成羁绊;心情是如此冷寂,连一声鸦叫也会惊出满天霜寒。就这样漫无目的地随波漂着,渐渐地,夜深了,月落了,水面上明灭着星星点点的渔火,但那是人家的温馨;江边婆娑着婀娜多姿的楓树,但那是人家的风景。属于张继的,只有溢满心间的落榜的失意和身在异乡的孤苦:
月落乌啼霜满天,
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钟声到客船。
夜啊,是如此之静,静得能听到钟声飘落水面、击打客船的声音;静得能使人在千年之外听到小舟上无眠人的叹息!是啊,才学满腹却无处绽放,志存高远却无枝可栖,怎不让人愁如流水潺湲无边。
枫桥———“封桥”,古运河在这里与苏州护城河交汇。据说,在唐时这里南北商贾云集,航运极其发达,是个极为热闹的枢纽之地。每到夜晚,为了苏州城的安全,这里都要关闭,故名“封”桥。也许,如果没有“封桥”之“封”,如果没有夜的阻隔,也不会有张继之“泊”,更不会有《枫桥夜泊》,张继,就会如千万个匆匆的过客一样,随波而去,成为历史长河中无人知晓的水滴。
正是这样的人为之封、之隔,或许还有水乡灵动之水的濡染,使张继那原本凡尘俗土般郁结的愁绪,突然间升华成涌动的才思,并在“残月、乌啼、霜天、江枫、渔火、寺影、钟声”中找到了契合的诗情,又水波般弥漫成一种清远宁静的意境。
此一种意境,一泊便千年。
这一泊,使单调的枫桥有了色彩,使平直的枫江有了韵律,使普通的枫桥五古有了引人注目的章节,使枫桥夜色有了万籁之外的回音!最终,在古老运河的盛载下,被一代代文人墨客品过、思过、叹过,使一批批游人的脚步、行者的目光相叠、相融、相汇。“画桥三百映江城,诗里枫桥独有名”,自然之枫桥,就这样汇聚了越来越多的人文色彩;无名之枫桥,就这样成为旅游史册上越来越浓的标注;水乡苏州,就这样成为大江南北越来越多人向往和追寻的旅游胜地。
品张继之“愁”,宜在水清风爽、星月相伴的夜里。此时,如果能乘一叶扁舟,在星光月色里随水波飘摇,更是一个物我两忘的理想境地。然而,这样的机会不多。多数的时候、多数的人们,只能在嘈杂的白昼,被导游的一面小旗导着,懵懵懂懂、匆匆忙忙中,新奇喧闹、走马观花后,留下的,仅一幅作为留念的照片而已。
看来,无论品诗或者观景,都需要适合的心境或环境!
关于《枫桥夜泊》中张继之“愁”,历来颇多争议。有说安史之乱、国难身贫之由,有说落榜失意、羁旅异乡之故。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幅江南水乡秋夜的美景虽跨越千年却更加新颖;那个隽永幽美的意境虽代代冲刷却更加清亮。更何况,对于后人来说,大可不必“为古人担忧”。如果一时片刻间的愁绪,能在夜泊于枫桥时,寻到共鸣的律动甚至高山流水之感,岂不也是莫大的快事?
责任编辑高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