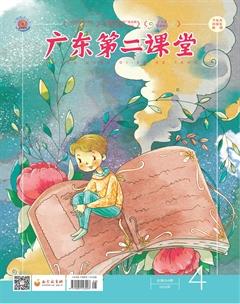清明糍
2020-05-11魏伯娣
魏伯娣
清明糍即艾糍,是增城民间的传统食品。做清明糍的原材料当然少不了艾草。每逢春季,田头水边、房前屋后就会长出一丛丛、一簇簇绿油油的艾草。绿色的叶子盘旋而上,像宝塔般异常可爱。自懂事起,清明糍便陪伴着我成长,是我酷爱的食品之一。
临近清明节,勤劳的村民们开始张罗着准备做清明糍的材料,艾草自是其一。晨光微露,早起的村民便拿着簸箕或大袋子出门。因早上地面比较湿滑,为安全起见,村民会穿上水鞋,去后山、田头、菜地摘艾草。刚采摘下来的艾草清香扑鼻,色泽喜人。为了让清明糍的口感更佳,村民更喜欢采摘艾草的嫩叶部分。艾草放得越多,清明糍就越清香可口。
人们喜欢用频婆叶或芭蕉叶包裹清明糍,所以除了艾草,村民还要准备频婆叶或芭蕉叶。在清明节前几天,就得把这些叶子采摘回来,洗净晾干,再用干燥的袋子装好防潮。包清明糍的叶子洗干净后,最好放在热水中煮一煮再晾晒,这样可以去掉叶子自身的涩味,使清明糍的口感更为香甜。
清明节到了,家家户户除了宰杀鸡鸭准备丰盛的菜肴之外,就是忙碌着做清明糍了。清明糍有很多种馅料,花生馅的、黄豆馅的、眉豆馅的、芝麻馅的……望着蒸笼里正冒着缕缕香气的清明糍,真让人垂涎三尺!在物质充裕的今天,只要掏几个钱就可以实现心愿,但我总觉得家人亲手做的清明糍那种香醇、细腻的感觉是买不到的,也是难以向旁人言表的。
我对做清明糍这门手艺自然是非专业的,在父母亲面前只不过是班门弄斧罢了,只有搭把手的份儿。工作后,我更是多年沒有做过清明糍。去年清明节,我回到父母家中,父母亲早已忙得不亦乐乎,而我也终于能如愿以偿,重温旧梦。我似孩童般站在母亲身旁,认真地观察她的一举一动,生怕错过了其中任一环节。父亲把准备好的糯米粉、艾草、黄片糖、煲熟去了壳的麦豆、洗净焯过热水晒干了的频婆叶摆放在桌子上,就等母亲大显身手了。
母亲把衣袖挽得高高的,先把艾草用清水洗净后倒入锅里,大火煮开,再用小火煮一段时间。等艾草充分煮烂,捞出来,用清水洗净,再用手压干艾草上的水,把艾草放在盆里晾凉。稍过一会儿,母亲将艾草放在砧板上用菜刀一一切碎。然后,把切碎的艾草整齐地平放在砧板上,用菜刀反复剁。母亲说,要像剁肉碎般剁均匀,剁得越细越均匀,清明糍吃起来就越细腻越柔软。
接下来是做馅料。母亲把煲熟去了壳的麦豆倒入锅里,用花生油炒香,边炒边用锅铲使劲将麦豆一一压碎。另一边,父亲也早已端坐在餐桌旁忙开了。他用刀子将一条条的黄片糖削成碎末,盛在大碗里交给母亲。母亲接过黄片糖碎末,均匀撒进锅里,与麦豆碎末一起搅拌。充分拌炒均匀后,艾糍的馅就算做好了。
母亲说,接下来的工序尤为关键,可马虎不得。只见她把适量的黄片糖放入锅中煮成液体状,然后把适量的糯米粉置入锅里,再加入刚才处理过的艾草,用铲子一起炒匀。母亲双手一刻也不闲着,左手扶锅耳稳定锅子,右手握铲子反复不停炒着,使艾草充分和糯米粉炒拌均匀。母亲马不停蹄地上下挥动铲子,嘴里也一直在唠叨:“水不可一次加太多,要慢慢加,因为艾草也带有水分。揉好的粉应该不干不湿,有弹性,像做包子揉的面那样就行了。”过了许久,粉终于和好了,母亲擦擦额头渗出的汗珠,长吁一口气,把和好的粉用盆子盛好。
开始入馅了。先抓一团粉,放掌心左右手交替揉圆后,左手持面团,右手拇指在面团中间按压,挤出个洞,再装入麦豆馅。母亲说:“这入馅也是一门学问呀,要用力把馅抓实,捏成一小长条后才好入馅。这样省了不少工夫,而且清明糍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然后,她顺势用右手食指和拇指把粉团口子轻轻捏紧,再揉搓一下,粉团便成椭圆形。父亲则在一旁往蒸笼里垫上频婆叶,在入好馅的清明糍外表抹上一层花生油,然后轻轻置于频婆叶上。一张频婆叶可以放三至四个清明糍。几盏茶工夫,宛如绿宝石般的清明糍就整整齐齐地置于蒸笼上,一排排,一列列,颇有气势。最后,用大火蒸大约20分钟便大功告成!
“吃清明糍咯!”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把头伸出窗外,招呼正在楼下玩耍的孙儿们。小朋友们闻声冲上来,迫不及待伸出胖乎乎的小手,抓起心仪的清明糍就狂嚼起来。我也不甘落后,拿起一个清明糍,仔细端详着,细嚼慢咽品尝起来。这其貌不扬的清明糍不仅包含着浓浓的亲情,也牵动着我对童年生活无限的眷恋与追忆。一阵风卷残云之后,望着挺着圆鼓鼓肚子的小朋友们,一股久违的暖流顿时从心底涌起,不断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