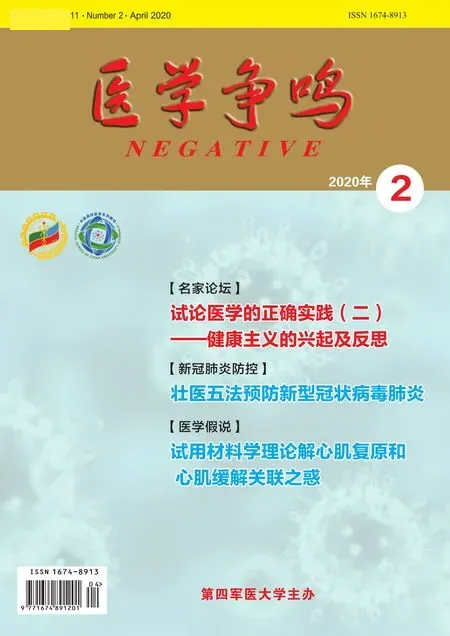试论医学的正确实践(二)
——健康主义的兴起及反思
2020-05-11樊代明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陕西西安710032
樊代明(空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陕西 西安 710032)

健康是当今人类最关注的话题,人皆知之,人皆求之,但不一定人皆懂之,也不都人善为之。人类发展至今,当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命和生活的必需条件基本解决或满足后,自身的身体健康和长寿自然成了人类最关注的问题。有人称,健康是1,其他都是0,没有健康其他都等于0。甚之,不少人主张把人力、物力、财力、精力都要用于健康促进上,这似乎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人为地、片面地、过度地、错误地追求健康,不仅会盲目耗费社会和经济资源,其本身还可能给健康带来极大问题。因为,健康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对健康的促进一定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
1 健康主义的由来
在20世纪中叶之前,威胁人类生命的主要是传染病,人类通过科学方法、改善卫生、寻找病因、研制疫苗和抗生素,在攻克传染病的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现代医学乘科技的东风,靠资本助力,很快跨入医学发展的快车道并进入鼎盛期。但到20世纪70年代,医学的地位逐渐发生改变,非传染性疾病开始流行,病因和病机发生了根本变化,老一套的科技方法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很快便使医学的成功又变成了难题。1980年,美国学者克劳福德(Robert Crawford)提出了“健康主义”的概念,英文称Healthism[1]。其含义是健康靠改变个人生活方式,应由个人负责,应将其作为公民的一种超价值追求。英国学者罗斯(Nikolas Rose)认为,从社会治理观看,健康主义既是大众对社会良好习惯的共同追求,也是个人对完美健康的热切期望。但到上世纪90年代,捷克学者P. Skrabaner对健康主义提出了反面意见,他指出,健康主义有可能将个体(少数人)的生活习惯演变成国家主张,并依此施行健康教育,敦促民众遵守所谓的“健康生活方式”,甚则形成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成为大众教育的替代品。他甚至担忧健康主义会演变为极端形式,即以健康为由为种族主义和“优生学”找借口。比如上世纪初,有些欧美国家成立专门机构来认定不宜繁育后代的不健康人,通过立法或授权对其施行强制性绝育,最终演化成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1]。
2 健康主义形成中的影响因素
2.1 健康主义受科学主义的影响
《自然》资深编委亨利·吉(Henry Gee)说过,科学不是关于真理和确定性,而关注怀疑和不确定性。科学发表的所有东西都只是对现实的近似,将来肯定有人做出更好的东西(来否定目前的结果)[2]。科学是在选定条件下的创造,比如前瞻性研究,通常是人为的满足己欲,而医学是在创造过程中的选定,比如回顾性研究,才是为人在探索规律。正如前述,科学是证实,是探索与现实近似的东西,而医学是证伪,是否定与现实近似的东西从而得到更正确的将来。这是纯自然科学,或科学与医学的不同。那么什么是科学主义呢?根据《韦氏词典》的定义,科学主义是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如哲学、社会学和人文学)并对其有效性过分信任的一种理念。科学主义是对科学方法有效的普遍性、科学理论的正确性、科学的社会应用价值等给予绝对肯定和肆意夸大。同时又贬低和否定其他人文社会学方法的有效性及其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价值和意义。科学主义是对科学的盲目乐观、盲目崇拜并引致人们产生科学乐观论和万能论,以及轻视人文社会学乃至其他学问的态度。实证主义者认为,科学可以整体涵盖自然、意识和社会的所有领域,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科学的解答,而且也应该由科学来解答。甚至,有不少科学家相信,社会和伦理问题最终都可以被还原成科学问题且得到解决[1]。当科学作为一种主流文化并被片面推向极端时,很容易被看作是人类惟一正确的文化形式。科学主义试图无限扩大范围,反客为主地侵入和主宰其他领域并赋予自己过多的价值权威,从而导致科学的文化霸权。极端科学主义者完全排斥非科学文化形态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其不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须,只有近代科学才是衡量一切知识的标准[3]。特别是在推翻了教会和宗教的专治统治之后,科学主义用其在社会产生的巨大功用与政治权力相结合,形成了极端科学主义。
健康主义受科学主义的极大影响,片面地认为只要检测人体的客观指标就能判别人体是否健康。患病就是正常标准的偏离,而这些标准又只对人体结构和功能的病理进行判识,忽视了社会心理因素。只考虑身体的标准化,很可能导致矫枉过正的医疗干预。比如对健康的身体实施外科手术(切除未发炎的阑尾)或对有患病风险的胚胎采取遗传学干预(基因编辑胚胎)。典型的例子如2013年美国明星安吉丽娜·朱莉实施预防性乳腺切除的案例,是彻头彻尾利用健康主义新理念的极端案例。朱莉带有母亲遗传突变的BRCA1基因,检测患乳腺癌的几率是81%,患卵巢癌的几率是50%,于是她先做了双乳切除,2015年又做了卵巢切除。结果发现,乳腺全部正常,卵巢只有一个良性肿瘤,且并无癌变迹象[1]。对某些疾病,特别是肿瘤科的疾病,发现有任何变异,不能武断地将其视为发病原因,更不能说就是异常,它可能是人体对环境或身体内部的一种保护性反应。在低级动物,特别是在体外观察到的一些现象,不能顺理成章地推演成人体的必然结果,比如在斑马鱼的受精卵中发现的现象不一定能作为人体生理或病理变化的根据。因为一个在体外,一个在体内。体内的现象在体外很难复制,因为体内有非常复杂而有效的调节机制参与,就像体外的胃癌细胞不能代表人体内的胃癌一样。胚胎细胞和癌细胞在体外都可以增殖,但在体内却不一样,胚胎细胞在体内能长成为一个个体,癌细胞只能长成一个癌块。胚胎细胞长成胎儿后就停止生长并自然排出体外,而癌细胞长成癌块后不但不能排出且不会继续生长。这些现象的发生可能是细胞的本质,但更多是体内的调控使然。所以肿瘤的生物学表现更多是体内调控失常的后果,而胎儿的正常生长和适时分娩更多是体内调控成功的结果。总之一句话,受精卵不是鱼,癌细胞不是癌。
一般认为科学是客观、中立、公平、公正和无私的,从而赋予其至高无上、惟它独尊的权利,把有关人类健康的一切事情都交给它去做。事实上,科学研究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受科学家(医学家)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影响,所以研究结论及其抽象的知识从根源上就不一定是客观的。400年前培根就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人们记得很熟,说得很多,但别忘了,他还说了下半句“知识就是权力”。人类的知识和权力是合二为一的。保罗·史塔(Paul Starr)认为,如何利用科学的成果要看世界上各种角色各自的目的[4]。科学的确成功地帮助人类消除了无数饥饿和疾病负担,但它又重新划定了权力世界的格局,导致一部分人用知识和权力控制其产生的庞大组织机构,从而骑压到了另一部分人的身上。因而科技,包括医学科技并不像人为想象和其貌似的那样客观、中立和公正。所以有人讲,凡是由人做的事情都难免有人为因素的参与或干预,如果管理者不加以正确引导和适时适宜的管控,有时科学本身可能成为某些行业或某些人用来控制和剥夺另一些行业或另一些人权益最有效的工具。现代医学的发展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基础理论、技术手段和伦理道德几近完全封闭的独特系统,有时社会管理、资本调控很难介入其中,或显无能为力,因此绝对不要简单认为医学是纯粹理性、客观和中立的。其中,疾病不是非黑即白,有其特殊的灰色地带,疾病的诊断和疗效都有概率性,凡此种种都可为它所用。比如一个抗癌药只对19%的病人有效,但这100个人每个都想去追求这19%的效果,人人都认为自己是19%中的一员,其实最后更多的是那81%,有些失败了还能坦然面对,可有些在人财两空时才追悔莫及,或怒举刀棒,杀向医生。实际上,这是科学研究结果和结论在医学应用上的局限性诱发和引发的矛盾现象。
2.2 健康主义受技术主义的影响
高新技术应用产业化是健康主义的另一强大推手。21世纪以来,基因测试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健康消费新市场。遗憾的是检测到基因并不直接致病,比如Helix公司创建的首个线上DNA测序商店,只要提供唾液就可进行基因测序,但在花费1 900美元后,得到的只是一堆医学价值等于零的数据。目前,健康体检和疾病的检测范围还在不断扩大,检查项目也不断增多,加之商业利益的介入,健康体检已不再是以保障健康为目的,而是重点考虑资本利益,健康主义的理念已经渗透至社会文化领域并转化为民众认可的行为。本意是让人更健康,实际上已引发了健康和道德风险,甚至会导致健康损害。正如前述,肿瘤遗传学研究本意是想去发现与癌症发生有关的“坏基因”,并用基因工程技术将其去除,以减少癌症。可结果发现,这些“坏基因”的产物是维持生命正常状态不可缺少的物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只是讲理,还要讲用。讲理是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对医学讲理,就不能搞“人定胜人”。要尊重客观规律,不能从文明向野蛮时代倒退,我们可以防患于未然,但切记不能治患于未然。
技术主体化导致医学手段与目的的换位。现代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医学的主体,并以独立的力量和自身逻辑无限制地发展,其目标已远远超过了医学的目的。特别是时下以大数据、云计算为基础构建的所谓医疗自动决策系统,“以算法决策为用,以个人数据为体,以机器学习为魂”,可以减少人为决策的偏见。但数据和算法都不具有天然中立性,难免有算法歧视出现。医疗体制的改变,如按技术分科,催生出种类繁多的临床三级甚至四级科室。比如,我国现有13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111个,二级375个,三级学科2 382个。又如世界各国科学基金申请代码都不超过500个,而我国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代码却达到2 111个。再如中华医学会分成80多个分会,有的分会又分成18个专业协作组,其他学会或协会,包括省市级学会照此办理,有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迅速助长了技术主义趋势。在专业过度分化、专科过度细化、医学知识碎片化的现今,回望古希腊、罗马或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古代文明时代,我们会有一股重回古代的冲动和神往。先贤们仰望天空,思索天地奥秘(星行、星占),他们并不考虑哪个学科、哪个专业,也不知学科是一级或二级,更不管是不是国家级重点学科,但他们的发现和发明之伟大令后人不得不折服,有一些至今仍是难解之谜。而今专业细分、专科细划,实际上是在技术主义作祟下,各自在自己的领域中按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奋发图强,申请项目,发表专著,申报成果,收获名利,层层效仿,年年照办,周而复始,虽不乏大师与成果,但更多可能是画地为牢或占山为王,甚至是用潜规则在暗度陈仓。这不仅是科学在拒绝其他非科学,技术在拒绝其他非技术,而且已呈现科学技术间相互的激烈排斥,技术主义无处不在。技术主体化、技术至上,使临床上主要看检验指标,不管病人客观感受,也不强调医生经验,不少地方或专业,临床医生已成了“离床医生”。西方人讲“躺在床上永远学不会游泳”。笔者认为:“不看病人永远成不了医生”。
2.3 健康主义受消费主义的影响
关注健康与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确实有助健康,但若将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不断扩大的健康风险因素联系,由此形成一种健康与不健康的概念,甚至意识形态,并逐渐纳入传统的医疗服务中,这不仅不会增进或促进健康,还可能进一步引发难以察觉的健康焦虑,这本身就是一种健康风险。上世纪中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人平均寿命在逐渐延长,疾病死亡率在明显降低,健康水平确实在不断提高。但同时也要看到,人们对健康的期望在与日俱增,对影响健康的因素心存忧虑,怀着焦虑的情绪执着地追求健康,构成了对健康的过度关注,这本身又成了影响健康的重大问题。比如癌症筛查会给受检者带来心理问题,特别对那些疑似癌症或查出来患癌的人来说,每每造成负面的心理压力。斯克拉巴尼克(Skrabanik)在其著作《人道主义医学之死》中调侃地说“不抽烟不酗酒,不熬夜无女友,粗茶淡饭天天走,出狱一切化乌有”[1],意思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只有在监狱才能实现,而实现后并不见得就健康,说不定一切皆空。所以刻板遵循某些“生活秘方”来管理健康本身就是一种病态,健康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健康主义强调个人责任,认为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人才具有道德责任,否则就是对自己健康不负责任的人,具有道德过错,不值得同情及帮助。
健康主义给人们呈现的是无疾病世界,潜意识是希望做到长生不老,其实只是不能实现的美好愿景。疾病是生命的组成部分,也就成了健康的组成部分。无论你喜欢与否,疾病都将与你的生命相随,最好的做法是与其和平相处,带病生存。比如,随着老年社会到来,衰老导致的不适、功能障碍、疼痛、失眠、记忆力减退、生活能力下降,无疑将在健康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众所周知,患病并非黑白分明的客观状态,很多疾病在诊断和治疗实践中既可人为设定也可人为改变,在常人与病人之间存在大量似是而非的灰色状态。其中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难以黑白划线的模糊问题,有些人穷尽一生在研究这些模糊问题,也有人利用这些问题的模糊性去欺骗民众。重要的是有一个概念必须明确,医学只能治病,救不了命(即不死)。自然力没了,超稳态失常或崩溃了,人终有一死,没法长生不死,我们要敬畏这个自然规律,道法自然。不能在生死问题上不惜一切代价与自然规律进行无效的抗争。疾痛和死亡本是生命的必要部分,医学和医生要积极主动地帮助病人。旨在发动一场消灭疾病和死亡的战争,医学显然走过头了。我们不能向民众传递医学能够消除一切病痛、能够追求长生不死的错误信息。
健康主义是当代社会文化的一种新思潮,最初流行于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继之播散到全球。中国对健康主义的概念尚未普及,但健康主义的行为已被广为接受,民众对健康的高期望与对医学的不信任这两种观念交织、碰撞。既期望医学给健康带来奇迹,又热衷选择“另类”生活方式,二者使健康主义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时尚文化,不知不觉地成了一种“开宗明义”的文明病。事实上,正如前述,健康与患病,健康人与病人之间并无明确的分界线,存在模糊的灰色地带。传统的健康观在生物医学模式影响下,认为健康就是“无病、无残、无伤”,这种单维度健康思维模式诱导医生只关注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忽视了疾病的预防,忽视了生理、病理、心理和社会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对健康的影响,加速和加深了健康主义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2.4 健康主义受资本主义的影响
医学知识在过去几十年里,已悄然走向以商业为目的、为主要本质的广告信息转变,后者成了健康主义的另一大推力。在美国,医学知识传播过程中诱发腐败已远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控制能力。这种蜕变部分源于医学杂志与企业间的“合作”。Lancet每发表一篇关于临床试验的文章可给药企带来平均278 353英镑的收入,最高可达15 517 974英镑,分别折合人民币250万元和1 350万元。有些专业杂志比Lancet更过分。2009年美国国会对Journal of Spinal Disorders & Techniques主编Thomas Zdeblich进行调查,该杂志每期都登Metronic公司产品的文章,发现他仅从Metronic收受专利使用费就达2 000万美元,外加200美元的顾问费。BMJ前主编Richard Smith说,“医学杂志已成为药企强大市场机器的延伸”。Lancet主编Richard Horton也说,“医学杂志已沦落为药企漂白‘信息’的运动场”。有些医学杂志刊登的知识已经变质,大量医生看病决策依赖的“科学证据”正在被商业利益扭曲,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医学杂志发表的大量论文更像知识性商业广告,其目的是为了推广赞助商的产品,而不是介绍提高民众健康的知识和方法。这些所谓的科学证据本质上是为了销售更多药物而专门制造的知识[4]。
指南的分歧有时也很大,指南不是共识,不是求同存异的结果。在应用过程中,同的部分逐渐变少,异的部分越来越多,于是过不了多长时间就要修改一次。临床指南的制定更是药企利用研究者和医生渗透和干预的重地,很多指南的建议充满利益冲突。有观察发现,在各种指南的制定委员会中,有6%~80%接受过药企的咨询费;4%~78%接受过药企的研究资助,持有药企股份达2%~17%,有其他相关利益者为56%~87%,所以指南的建议已不再是医患都可充分信任的信条[4]。
药企通常在“什么是疾病,什么是疗效和是否该治疗”这三个方面大下功夫,以十分善良的面孔向健康的人群疯狂扑来。NEJM前总编Marcia Amgell说,“世界的大药厂正用市场手段疯狂扑向健康人群,生活起落成了精神疾病,常见不适成了严重疾患,越来越多的正常人变成了病人”。其实药企没有多少新发明,只是不停地将老药重新包装,并称之为“新药上市”,做着换汤不换药的生意,然后以巨大的市场机器无情地推销这些药品,价格则被提高到只要能逃脱责罚的高度[4]。健康主义概念被资本,特别是资本的掌控者利用得淋漓尽致。
3 整合健康学的形成和完善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疾病谱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老年社会的不期而至,人口城镇化,加之人类对健康的迫切追求,现代健康观正在不断形成和完善中,无论是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扩展。WHO的表述为:健康除了躯体无疾,还要有生理、心理、社会交往的完好状态。这个定义是身心皆备,既考虑到人的生物学属性,也考虑到人的社会学属性,其最大的亮点是超越单纯以躯体,单纯靠生物学为基础,而是从身体、社会、心理三个维度衡量。健康是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健康概念的整合。1989年WHO又优化了健康的内涵,除躯体健康之外,增加了心理、社会适应和道德行为。既考虑到人的自然属性,又考虑到人的心理、社会和道德属性,把健康内涵扩展到了7个主题,即:①身体健康(body health),指个体的结构和功能状态,以及对病伤的反应;②情绪健康(emotional health),情绪稳定和精神愉快是情绪健康的重要标志;③心智健康(intellectual health),指个体认知、理解、思考和决定的知性能力;④灵性健康(spiritual health),指信念、观念、意志、人生态度;⑤社会健康(social health),指个体愉快、有效地扮演自己的社会角色;⑥职业健康(occupational health);⑦环境健康(environmental health)[5]。整合医学涵盖的整合健康学(holistic integrative healthology)包括了空间健康学、人间健康学、时间健康学,三者的整合融入了中医的理念,特别是时间健康学的纳入,对健康的认识可能更具全面性和合理性[6]。过去我们说知识是力量,其实碎片化的知识只有整合起来才有力量。不同学科都有自己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但医学发展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只有整合起来才能为人类的健康目的服务。其实,这在纯自然科学的领域也是如此。举一个自然科学的例子,自古以来,物理学和数学是不分家的,这在20世纪之前尤为突出,所有的数学家都是物理学家,反之亦然。古代的希腊学者,他们用物理学方法观察日、月、地球的运行规律,而同时代的中国学者用数学的方法关注地球的直径以及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最后希腊学者用几何的方法算出了太阳与地球的距离,获得了成功。中国学者没算成功,因为他们不认为地球是圆的。到了20世纪,情况变了,由于数学家将数学公理化、抽象化,引进很多名词和符号,物理学家不再跟他们来往。不过这种分离状态只经过了60年,不得不回来,因为物理学的两大支柱——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离不开19世纪的数学理论,前者要用黎曼几何,后者要用谱分析理论。反过来,两个支柱对数学都有着深刻影响。二者是水乳交融,难说哪个更重要。再举一个例子,1901—1920年的20年中,诺贝尔奖中具有交叉研究特征的比例仅为19%,但21世纪这20年来,这一比例增至40%以上,特别是化学奖,2001年以来占到了2/3,医学和生理学奖据说已达70%~80%[7]。这些事实都雄辩地说明,学科间、专业间的整合对促进科学,特别是医学发展意义非常大。
历时70多年对健康定义的讨论仍然没有定论,其实认知拓展基本上还是在沿着内涵半径做文章,但思维原点始终没有改变。不同个体的健康是否共享一个健康指标或标准尚无定论,笔者个人认为是不正确的,是完全错误的。生命包括整个人生不是一条直线和一个维度;而是一条条抛物线或多个维度。而且,健康及其判定一定是动态的,所以健康指标不能僵化地、教条地解读,应辩证分析,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整合健康学中专门提出时间健康学的原因和理由。因为一个垂暮老人不能跟一个出生婴儿或青春少年共用一个标准,同然,一小时甚至一分钟之前获得的一个检查指标不能作为一小时甚至一分钟后治疗疾病的绝对根据。随着健康指标体系的多元化,评价健康也应秉持多要素、多指南和多拐点的原则[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