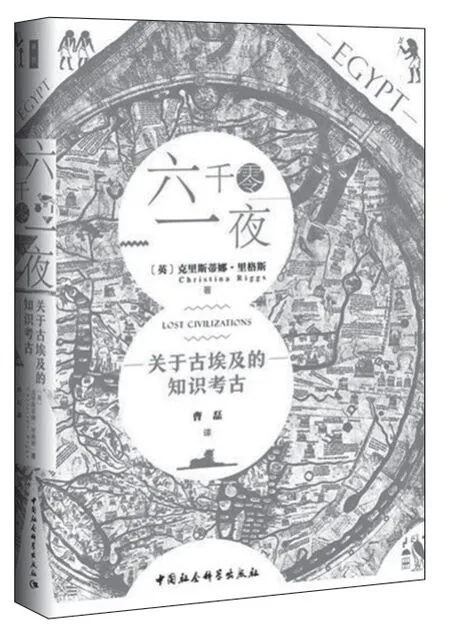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2020-05-11克里斯蒂娜里格斯曹磊
☉[英]克里斯蒂娜·里格斯 著 曹磊 译
为了重拾失落的古埃及文明,解读古埃及那些神秘的符号,人们花了很大力气用于破解那些散落在神庙中,密布在方尖碑和各种雕塑表面以及用红色或黑色墨水书写在莎草纸上的古怪文字。1801 年英军从投降的法军手里缴获了大批埃及文物,其中一块镌刻着托勒密和克娄巴特拉这两个名字的黑色石碑为托马斯·杨(英国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擅长多个领域)和商博良(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埃及学家,被誉为“埃及学之父”)的工作提供了突破性进展。这块石碑的一面同时用三种文字镌刻了同样的内容,三种文字包括世俗文字、象形文字和希腊文。最初发现石碑的法军军官显然意识到了它的价值,因此才把它从尼罗河三角洲西部的艾尔拉什德城城墙上给拆了下来,这块石碑后来就被西方人称为“罗塞达”。

“罗塞达”石碑
任何涉及罗塞达石碑的话题总要使用诸如“钥匙”“密码”“解读”之类的字眼加以修饰,就好像历史上的埃及对今天的读者而言仍然迷雾重重似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埃及对今天的很多人仍然是谜一样的存在,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经验去理解那个世界。今天的人差不多都识字,我们写下某些东西,同时自然而然地认为别人肯定能读懂它,然而普遍识字相对漫长的人类历史仍然属于新生事物,今天的某些人类群体其实也还没有做到普遍识字。当读写成为某个社会中少数人掌握的特权时,这种技能就可以成为统治阶层巩固自身的一种手段,比如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所做的那样。据可靠估计,古埃及人的识字率始终控制在2%~5%之间,从来也没有增加过,这个范围以外的人根本就是“睁眼瞎”。你可以想象一下自己待在足有100 人的房间里,所有人只能依靠其中的两三个人写电子邮件,签贷款合同,掌握政府的各种政策。不识字的人除了信任那两三个人,别无他法。
“象形文字”这个说法最早由古希腊学者提出,意思是“神圣的刻符”,古埃及人用小鸟、身体部位之类符号表示意思的做法和今天的我们用图画传达信息大同小异。象形文字又称“神圣文字”,这个说法可谓名副其实,因为它们最初的作用主要就是用来书写与神沟通的文书。这些文书被镌刻在棺材和雕像上,出现在陵墓和神庙里,也被用作珠宝、武器和家具的装饰,比如图坦卡蒙陵墓中出土的那些稀世珍宝。象形文字是古埃及人在正式场合使用的文字,这种文字的出现与古埃及艺术的发展紧密相连,或者更精确地说,与雕刻、绘画领域的发展紧密相连。书写和绘画在古埃及其实难分彼此,两者都通过线条简单勾勒面孔和肢体,都通过画面位置的上下布局暗示尊卑关系,都通过不同元素的组合传达丰富信息,而且画面中主要形象都必须统一面朝观看者的右侧,人物和动物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明显。之所以产生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古埃及人写字遵循从右到左的规则,就像阿拉伯人和希伯来人一样。有意思的是,如果客观条件需要,比如出于装饰的考虑等,古埃及象形文字也可以调过来,按从左到右的顺序书写。如果将这种技法运用到墙壁上,比如陵墓的墙壁,就可以产生一种对称美。同样依据源自文字书写习惯的法则,无论采用二维模式的绘画,还是采用三维模式的雕塑,古埃及艺术中的男性形象(女性很少成为艺术表现的对象)也都是下半身向右扭,同时左腿向前迈步。无论这些艺术品将来会被摆在哪里,派什么用场,都必须严格遵循这样的法则。

法老那尔迈调色板
象形文字出现在公元前3200 年前后,当时的埃及正处于前王朝时期末尾、早王朝时期开始的阶段,他们的艺术也在这个时期发生了突变。如果简单地下结论说象形文字的出现是为了满足新帝国统治者的需要,那可能过于武断。此前的若干世纪当中,那些用图案装饰的陶罐、石磨以及外观修长的圆柱形雕塑,已经为象形文字的最终出现作足了铺垫。目前出土的一块属于法老那尔迈的大号、双层调色板上雕刻着他本人及随从的形象,这些图案已经体现出了后来三千多年中古埃及象形文字和绘画共同遵守的规则。同样是在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某些非常容易辨识的象形文字,比如刻在调色板最上面的国王名字——狂鲶。它们按照法老王室礼仪的要求,统一用方框圈了起来。随着中央集权帝国的建立,各类文书越来越频繁地往来于埃及各地,这是官僚机构维持正常运转,保证国家信息、物资顺畅流通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象形文字蕴含的神圣意味以及苛刻的使用规范,也让它们有可能成为法老王权的某种象征。

古埃及象形文字
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中的某些符号本身没有意义,只代表说话时发出的一个声音。除了代表特定的声音,某些象形文字不仅具有阴性和阳性的区别,还可以表示单复数。另外,某些符号的含义不能只看字面意思,而是要结合上下文语境。这类词语被埃及学家称为“限定词”,它们通常被加在某些词语的后面,从而进一步说明前者的含义。例如,以“麻雀”形象出现的限定词,它加在其他词语后面就可以表示“不”或者“小”的意思。同样的道理,某个词语后面跟着的两条人腿的形象就有“行动”的意思。古埃及人读某句话时,不是所有词都要读出来,比如那些限定词;反之,现实对话交流中的某些语音也不一定能在象形文字中找到对应的符号。例如,纯元音就没有固定的符号,因为它们总要根据语境或前后词语搭配作出相应调整,实际书写时只能写一个辅音或类似于辅音字母的符号,读者阅读时要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决定发音。现代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保留了类似的习惯,书写时经常省略元音。古埃及语言从大的范围来讲属于闪米特语系,这种语言虽极具“个性”,又与属于相同家族的,比如阿拉伯语、希伯来语和阿卡德语,存在很多共性。
象形文字只是古代埃及使用的多种书写符号体系中的一种。当书记官用芦苇笔沾着墨水在莎草纸上写字时,他们使用的是更简便而流畅的符号。书写过程中,书记官会对象形文字作出简化,从而提高书写速度,最终催生出了简体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同时期的希腊人称其为“Hieratic”。虽然这个词语含有“祭司专用”的意思,但简体象形文字在古埃及的使用其实非常普遍,通常用于书写信件、文契等世俗文书。如果用于书写类似祭文或亡灵书等特殊文本,简化字通常还要在字体方面加些装饰以示尊贵。简体象形文字的出现对埃及历史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日复一日,乡村中的书记官或供职于神庙的抄写员用这些符号传播法律和政令,大量饱含知识的莎草纸卷也被创作出来。那些有幸成为后备书记官的男孩们到各自家乡的神庙中集中学习读写,他们首先接触到的也是简体字。这种情况同今天埃及考古专业的大学生们正好相反,他们学习古埃及文字是从正体象形文字入手的。
口语在人们的使用过程中随时都在发生演化,书面语则要相对稳定、滞后。如果人们选择用某种古老而刻板的书面语去记录语言,那往往是因为看重它通过漫长使用的历史而获得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比如钦定版《圣经》使用的那种书面语,现在的人们在教堂里还会连篇地背诵它们。相比正体,简体象形文字更容易跟上语言演化的步伐。埃及学家将古埃及语言中语法和词汇的演化分为早期埃及、中期埃及和晚期埃及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和古埃及历史的演化阶段并不完全重合,而且每个阶段使用的语言与之前和之后使用的语言也并不一定存在传承关系。
中期埃及统一使用正体象形文字,这种情况持续到托勒密王朝阶段,在神庙中尤其普遍。晚期埃及的语言,也就是生活在公元前1325年前后的图坦卡蒙王每天说的语言,主要用简体象形文字书写。从公元前650年前后开始,被称为“世俗文字”的符号体系逐渐进入埃及人的生活,这种文字在简体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简化。罗塞达石碑便使用了这种世俗文字,用这种文字镌刻的文本要比石碑上用正体象形文字和希腊语镌刻的相同内容文本保存情况更好。与简体象形字不同,世俗文字只能用于书写世俗文书或者那些包含有伤风化内容的文本。现存的用世俗文字书写的古埃及文献涉及范围非常广泛,内容涵盖最贴近民众生活的婚书到最形而上学的教义问答,不一而足。由于能读懂世俗文字的学者人数非常有限,这些文献中的大部分目前还在排队等待翻译。
世俗文字流行的这一历史时期,古埃及社会的主流语言是希腊语,然而这个时期以世俗文字为代表的埃及本土语言却对希腊语保持着很强的排斥倾向,拒绝从后者那里借用词汇。祭司和书记官们甚至有意识地将驱逐“外语”、保持世俗文字的纯粹性当成自身职责。在托勒密统治时期以及随后的罗马统治时期,埃及本土语言演化成为了今天人们比较熟悉的科普特语。经过这次改革,埃及人终于可以在书面语中体现元音,补充了很多象形文字体系中没有的东西。以这种文字书写的手稿大多都不会牵扯埃及传统宗教的内容,这可能是因为在罗马和拜占庭统治时期的埃及使用新文字的同时,多数埃及人已经接受了基督教。
古埃及人认为文字本身具有神奇魔力,这种魔力不仅产生于它们被写在莎草纸上的那一刹那,随着时光流逝,当莎草纸上的神奇符号变得无人能识,这些文字在人们眼中的“魔力”反而会进一步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