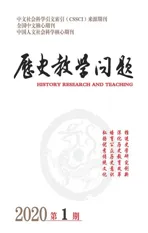南洋研究所及其南洋研究(1942—1945)
2020-05-07于延亮
于 延 亮
南洋研究所(Nanyang Research Institute)是抗战期间侨委会与教育部合办的南洋研究机构,旨在开展南洋和华侨诸问题的研究,以应对日伪对南洋华侨的蛊惑性宣传,同时为政府各部门在南洋和华侨方面的决策提供参考意见、方案和依据。研究所是民国唯一一个独立的国立南洋研究机构,弄清其历史对认识和了解国民政府的南洋政策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侨务关涉机密,除《新南洋季刊》,公开提及南洋研究所的出版物较少,资料非常有限,历来罕有注目者,研究所显得有些神秘,以致外国学者常把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误称南洋研究所。20 世纪90 年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侨委会档案开放期间,肖多和年波利用档案对研究所做了初步研究,前者梳理研究所成立及成绩,勾勒了研究所的大致轮廓,后者专门研究《新南洋季刊》有无许可证,认为该刊系无证办刊。①肖多:《略说南京国民政府南洋研究所》,《学海》1994 年第1 期;年波:《关于〈新南洋〉季刊的创办》,《学海》1994 年第6期。近年各种数据库日益丰富,有些往日无法获取的资料逐步公开,为全面研究南洋研究所提供了可能。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新旧资料,试从创办缘起、组织与规划、《新南洋季刊》内容、废置原因四方面对南洋研究所及其南洋研究加以论述。
一、创办缘起:争夺华侨
20 世纪30 年代以来,日本将自己伪装成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打着“亚洲一体化”的幌子,先后拋出“大东亚联盟”“大东亚新秩序”等一系列具有侵略性质的口号,并成立东亚联盟协会等组织,创办《东亚联盟》(1939.11—1945.10)等刊物,大肆开展东亚联盟运动,宣扬军国主义和殖民统治,妄图称霸亚洲。汪精卫叛国后,在汪伪政权庇护下,沦陷区也成立东亚联盟协会,出版《东亚联盟》(1940.7—1944.4)中文版,亦步亦趋地追随和效仿日本侵略者,开展东亚联盟运动,提出“和平建国论”,进行欺骗性宣传。1940 年夏,日本又拋出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作为基本国策,将西太平洋的广大区域统统纳入日本的生存、防卫和经济圈内,把对外扩张曲解成解放亚洲,建设东亚新秩序,美化侵略行为,麻痹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笼络和分化抗日力量。在南洋和华侨方面,汪伪设立了伪侨委会,在北京、青岛、上海、福建、广东、海南等地成了伪华侨团体,创办《侨声月刊》《侨务季刊》《华侨月刊》(厦门、青岛)和《华侨公论》等伪刊物,宣传投降言论,试图蛊惑和拉拢南洋华侨为其效命。伪侨委会还建议伪教育部在中央大学增设海外文化事业部,进行南洋和华侨研究。
面对日本和汪伪的舆论攻势,国民政府也准备加强华侨研究、宣传和教育,国民党推出一些举措推进南洋和华侨研究。1940年7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第七次会议通过《推进侨民教育案》,提出设立侨民教育文化事业研究室,分门别类地研究华侨问题。①陈树人等:《推进侨民教育案》,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暨中央全会文献汇编》第18册,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122—150 页。1941年4月五届八中全会第十次会议通过《请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施行案》,指定中央大学、中山大学、西南联大等校设安南、泰国、缅甸、马来等语系,提倡边疆语文授以边政学科,指定中研院设西南文化研究所,研究越南、泰国、缅甸、印度、南洋之语言文化、地理经济等,以供有关党政及教育机关参考。②《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提“请设置边疆语文系与西北西南文化研究所培植筹边人才而利边政施行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 编·战时建设4,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8 年,第173—175 页。党务、侨务系统先后创办《华侨先锋》(月刊)和《华侨通讯》(报纸)两种华侨刊物,各地侨务局、侨务处也在迁徙中坚持开展归侨救济、接待等工作,加上海外党部和驻外使领馆相互配合,有力地抵制了汪伪势力抢夺华侨的势头。不过40年代以来,全国的南洋研究状况不容乐观。侨委会和海外部的机构和刊物侧重侨务宣传和研究,暨南大学因学校内迁和《南洋研究》再次停刊(1941.7—1943.8),研究人员或附逆或南下,研究陷于停顿,民间相继自发成立的南洋文化学会等团体随着上海沦陷而消解,党政系统也没有相应的南洋研究机构和专业刊物。
趁欧战爆发,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在南洋迅速渗透和扩张势力,勾结泰国发动边境冲突,入侵和占领法属印度支那。而欧美列强为维护既得利益,继续奉行绥靖政策,甚至以封锁滇缅交通为代价来换取日本的妥协。身在南洋的中国学者早已洞悉日本的侵略意图,深知日本南进之目的,他们建议政府重视南洋问题研究,设立国立南洋研究机构。1941 年上半年,侨委会常委兼教育处处长余俊贤到星洲视察侨教之际,张礼千、许云樵和姚楠便借机呼吁侨委会重视南洋研究,他们刚刚在南洋成立民间南洋研究团体——中国南洋学会,希望政府尽快设立一个官方的南洋研究机构,该建议受到余氏的肯定。③姚楠:《张礼千与许云樵》,《星云椰雨集》,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图书出版部,1984 年,第71 页。余俊贤是国民党荷印总支部发起人,曾主编《民国日报》,因抨击日寇侵略济南被荷印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回国后以从事海外党务和侨务工作,晋升中央委员。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1941 年12 月余俊贤等11 人便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第十次会议提交筹设国立南洋研究院的议案。
提案回顾中国在南洋的光辉历史和欧人东来后的地位变化,反思西人研究南洋的盛况及其原因,指出中国研究南洋的优势、前途和设立南洋研究机构之目的。首先回顾秦汉至明朝的中南交往,指出其时“南洋各国,莫不诣阙奉表贡呈珍异”,对比欧人东来后的时势,凸显中国在南洋地位的沦落和中南关系的历史变化,“佛郞机灭满剌加后,吾国在南洋之声威,即成逆转”,西、荷、英、法等相继东进,南洋成为列强角逐之地;至清季,英并缅甸,法占越南,“中南关系,遂告脱辐”。其次,反思欧人的南洋研究,指出其成功原因在学术机构和学术刊物。欧人经营南洋的策略是先稳固统治,继谋产业开发,更起学术研究。国家组织大印度学会、河内远东学院、吧城皇家文艺科学学会、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暹罗学会、缅甸学会及动植物园、博物院等机构,创办荷兰《通报》、巴黎《亚洲学报》、伦敦《皇家亚洲学报》、伦敦大学《东方研究院报》等刊物,从事精密之研究和成果之刊布,提案者意识到这些研究具有服务殖民统治、促进南洋文化发展之双重目的,并且大部分依赖中国载籍,所谓“凡欲研究印度史地者,设不参证《法显传》及《大唐西域记》二书,则势必无成,设凡欲研究南洋史地、风俗、物产者,设不取材于吾国之史典及先哲之著作,亦断难穷源究本”。④《余员俊贤等十一人提“筹设国立南洋研究院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4 编·战时建设4,第194—196 页。西人充分利用中国史籍详加考证,取得了巨大的功绩和效用。反观中国与南洋既有悠久的历史关系,又有多达800 万华侨生息其间,而政府对南洋研究不甚注意。提案从“发扬民族精神,阐述吾国文化,巩固吾侨经济,提高吾侨地位”的角度出发,建议国民政府迅速设立一纯粹之学术机关——南洋研究院,以“搜集南洋有关资料及阐述南洋文化、发扬吾侨民族精神、巩固吾侨经济地位”为宗旨。该提案后附有《南洋研究院组织大纲》和《南洋研究院进行办法》。大会审查后,认为提案所论意义重大,遂将该事交侨务委员会负责办理。
二、组织与规划
决议通过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协调和筹备,1942年3 月28 日,行政院向侨委会发出训令:“筹设国立南洋研究院一案……由侨务委员会附设一研究机构,负责办理。”①《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设立南洋研究所给侨务委员会的训令》,转引肖多:《略说南京国民政府南洋研究所》,《学海》1994年第1 期,第85 页。数天后即4 月1 日,南洋研究所在重庆山洞新开市和尚坡成立,设南洋研究院的提案终于得到落实。不过,从通过提案规划到正式设立研究所中间有四个月的时间,其间这个国立南洋研究机构发生了三点变化:其一,名称变更和体制降级。计划设国立南洋研究院,首都南京设总院,马来亚、荷印、菲律宾、暹罗、缅甸、越南等南洋各属设分院,然正式成立时仅为研究所,不设任何分支机构。其二,行政和研究组的增减。该机构行政与研究两系统略有交叉,计划行政上设正副院长各一人、秘书一人、组主任各一人(须精通南洋学术)和书记等。成立时,正副所长由主管部会首长兼任,行政与学术秘书各设一人,新增总干事主持所务,新增总务和资料两组辅助研究。总务组下分事务、会计、出纳三股,各设组员二至三人,资料组设组长一人、组员四人。研究组计划分八组:史地英文组、民风考古人类学组、地质矿物组、动物组、植物组、农林渔组、法律组、边疆问题组,实际最后设立法政、经济、教育、史地四组,设总务、资料两组办理杂务和搜集资料,另设编审委员会编辑研究计划,并审议译著。其三,经费渠道和数量缩减。研究院计划通过国库拨款和侨胞劝募两种方式获取经费,因机构体制的变化和战时环境因素,财政拨款成为研究所唯一的经费渠道,开办费和经常费全部腰斩。研究所作为教育部与侨委会合办的机构,其经费全由教育部承担,在侨民教育经费项目开支。
研究所前身是侨委会和教育部下属侨民教育师资训练所(1940 年)及侨民教育教材编辑室(1941年)。其时南洋已沦陷,面向南洋的师资训练和教材编辑工作全无用武之地,在此基础上成立的研究所同样面向南洋,从事舆论宣传和学术研究等工作,可以说是从务实到务虚的转变。由部门职能而言,南洋侨民教师资训练和华侨学校教材编辑,均属华侨教育范畴,该项职能在侨委会和教育部两部会间皆有体现,部会合作建立南洋研究所也未能跳出华侨教育的范围,从历年行政院工作报告表述中便可以发现此点。研究所存续的四个年度(1942—1945)中,行政院工作报告先后三年设“南洋研究所”条,其中两年指出研究所的工作任务是引起国人对南洋的重视和介绍南洋知识。②1942 年至1944 年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南洋研究所”条主题:1942 年“创设南洋研究所”,1943 年“研究南洋问题”,1944 年“加紧南洋研究”,该条目以百余字总结当年南洋研究所的工作成绩。行政院编:《行政院工作报告(1941 年10 月至1942 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1942 年,第5 页;行政院编:《行政院工作报告(1942 年9 月至1943 年6 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1943 年,第5 页;行政院编:《行政院工作报告(1943 年7 月至1944 年3 月)》,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1944 年,第3—4 页。而由于侨教职权划分的模糊性,部会主管与协助不明确,教育部对此不甚积极,侨委会因另有侨务问题研究室,所务遂为靠党务起家的总干事余俊贤把持。③《本会及各级侨务机构之更迭与战后复员》,侨务委员会编:《侨务十五年》,南京侨务委员会,1947 年,第3 页;中央研究院编:《国立中央研究院概况(1928 年6 月至1948 年6 月)》,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1948 年,第3 页。一般认为南洋研究所撤销后划归国立编译馆,而中研院则说“南洋研究所之业务有历史语言研究所接办”,可能是教材编译工作归国立编译馆,研究业务归中研院。
研究所人员分行政和研究两类,总人数维持在30 至56 之间。行政人员包括正副所长、总干事、秘书和辅助科研的总务组和资料组。第一届所长陈树人,副所长陈立夫,总干事余俊贤,副总干事周尚。第二届所长萧吉珊,副所长何荷仁,总干事周尚,副总干事黄雄略,秘书:林乾祜、张礼千,总务:黎光群、李加勉、何矧堂、龚仁勇、谭儆吾,资料:沈某某、许崇信、彭务勤、瓈超廷、蒋清华、张季和。研究人员(见表1)分四个专业小组,详细分工,各司其职。所领导除陈树人外,几乎全部来自CC 系,研究所由此成为CC 系的天下。研究人员任用及待遇标准参照大学教授以至助教一一对级执行。人员构成上,创所之初,以有研究成果的知名学者居多,知名学者出走后,研究所只得陆续招收部分大学毕业生,充实研究队伍,新人成为南洋研究所的主体。在吸纳新成员过程中,余俊贤特别注意拉拢同乡、旧属和亲信,壮大自己的声势。①1943 年1 月18 日,余俊贤请朱希祖为研究所介绍研究员,朱希祖答应介绍福建张熙,未见下文。《朱希祖日记》(下),中华书局,2012 年,第1339 页。知名学者相继离所,虽有新进人员不断补充,但多无学术积累,研究力量持续削弱,从《新南洋季刊》刊文质量可见一斑(详后)。此外,研究所还有部分特约研究员,即聘请其他部门从事南洋研究者兼任研究员,部分离职者也被聘为特约研究员,如姚楠、张礼千等。

表1 南洋研究所研究人员表②据余俊贤《南洋研究所两年来工作概况》、叶秉球《南洋研究所》及人物资料编制。
总干事余俊贤对南洋研究所工作抱有极大的希望,企图在战后操纵和把持南洋侨务。研究所成立初期,他曾说:“只要我们能够搞得成绩出来,同时配合华侨教育总会和侨民师资训练所,这两个已在我们掌握中的机构以及其他各方的关系,那么,战后政府对于海外各地侨务问题的安排布置,不仅只限于侨教方面,就是有关整个侨民事务的处理也都将依靠我们。因此我们将来的出路,可说是海阔天空,不论在国内抑或是海外,都是有着我们的工作出路和发展前途的。”③④叶秉球:《南洋研究所》,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2,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年,第194 页,第196 页。怀抱此种宏愿,他一手把控行政事务,一手紧握研究事宜。在其授意下,研究所成立仅有五个月,便制定了长达20 余页数万字的《南洋研究所研究纲领》,事无巨细地规定了各个研究组所应研究的总体研究任务和具体事项(见表2),是一份庞大的研究计划。为完成研究计划,他要求各组研究问题要根据《纲领》,同时配合研究人员的志趣和能力。研究组每年要依照《纲领》范围,斟酌现实需要,制订年度中心研究工作。对于个人,每年开始前要拟具详细的研究计划,并按时汇报进度完成情况。1944 年余氏卸任时两年来的工作报告显示,研究所第一年侧重征集资料及罗致研究人员,第二年以研究战后南洋各属处理方案及侨务推进为中心,第三年仍以“战后侨务工作推进问题”为中心。这份报告对研究组和研究人员的分工和进展按照时间顺序分门别类作了统计。对本所无力完成的任务,他要求对外征求人员共同研究,由研究所尽量提供资料,且予以适当的经济协助。为促进研究,所外优秀的南洋研究成果,经审定后也给予奖励。

表2 南洋研究所各组研究任务
余俊贤基于扩张个人政治势力和提高个人地位所提出的庞大研究计划,在研究力量极为薄弱的情况下,所内人员根本无法完成上述任务。而研究所内耗严重,派系斗争导致主要研究力量相继离职,此后撰写调研报告和编译资料成为研究所的主要成绩。研究所开办两年多,除《新南洋季刊》外,编写文稿近500 万字,绝大部分是资料编译和研究报告。至于这些稿件的质量,在研究所奉命裁撤移交时,有人指着稿件开玩笑说:“这堆废纸只可作点火和塞老鼠洞之用。”④尽管此言有戏谑之意,却也道出了研究所在研究方面的失败。
三、《新南洋季刊》:服务抗战建国
南洋研究所职能近乎当下的政府智库,研究南洋问题的主要目的在资政,其研究南洋和华侨服务于抗战建国大业,具有强烈的现实致用性,而撰写调研报告和编译资料恰好可以适应该需求。除上述工作外,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一种定期刊物《新南洋季刊》(两期,1943 年和1944 年各一期),“以研究南洋一切知识为宗旨”,研究南洋问题,介绍南洋知识。
《新南洋季刊》刊文颇为庞杂,有介绍文章,有研究论文,还有个别史料和文艺作品,多数人员从事跨组的研究,不局于组别。按研究主题,全部文章可分为南进、民族、史地、经济、华侨、其他六类,均紧紧围绕服务抗战建国这个中心任务。第一,揭批日本南进图谋和行径,主张中南民族同源说。创刊号发表《日本南进政策之发展》《日本南侵之经济意义》《日本对南洋之初期贸易》三文,从日本南进形式、分期、目的和手段等方面,集中批判日寇的侵略。陈直夫和廖鸾扬指出,日本政府通过虚构历史进行欺骗性宣传,制造舆论美化侵略以为侵略张目。①陈直夫:《日本对南洋之初期贸易》,《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3 年1 月1 日,第23 页;廖鸾扬:《日本南进政策之发展》,《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3 年1 月1 日,第11—13 页。廖氏将日本南进分为发轫、发展、积极、实行四期,以割占台澎、继承德国南洋属地、退出国联、二战爆发为节点。前两阶段较沉寂,退出国联后加速推进。汤德明认识到日本对南洋的态度是以母国对殖民地,即以工业国自居,而奴南洋为农矿国,侵略目的是变南洋为自己的殖民地。日本占据南洋面临军事、资本、贸易、资源、劳工、运输、移民等方面的问题,盟军应加快反攻步伐,绝不可坐视日本“安然消化”南洋。②汤德明:《日本南侵之经济意义(附表)》,《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3 年1 月1 日,第16—22 页。
日本自大正南进以来大肆宣扬日马同源,除暨南大学的刘士木等学者曾对此大力批判外,学界普遍未予重视。40 年代前后,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刻,我国才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南同源,对日马同源说予以回击。罗香林从种族特征、文化特征、民族迁移三方面论证中马同源,认为马来人是中华民族的苗裔;③罗香林:《马来人与中华民族之同源关系》,《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2 期,1944 年1 月1 日,第11—14 页。曾松友则更进一步,把中南半岛各民族均看作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都是中华儿女。④曾松友:《中南半岛民族之流源》,《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2 期,1944 年1 月1 日,第38—43 页。中马同源最早由民族学家林惠祥在30 年代提出,这种学说兼具学理依据和现实用意,曾在南洋华侨中产生很大影响。抗战时期宣传民族一元说对建立民族共同体,鼓励全国人民团结一致抵抗日寇有积极作用,但一味将南洋所有民族划纳入中华民族显然不合史实,尤其研究中南民族冲突问题时,民族同源说便显得极为尴尬。
第二,介绍南洋史地知识,研究南洋史地问题,探讨南洋研究的理论方法。史地问题是《新南洋季刊》最为关注的领域,涉及:第一类选录明洪武年间的海禁令、元朝致缅甸国书两种史料;第二类介绍缅甸、高棉、暹罗、新加坡等地史地信息;第三类考证古籍中涉及南洋的专名;第四类讨论中国与中南半岛诸国关系变迁;第五类讨论南洋研究的理论方法。前四类在研究地域上侧重中南半岛,或与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有关,中南半岛近半数地区在中国战区范围内,集中介绍和研究这一地区应是适应战事发展之需。
史地问题中的前三类内容简略,偏重普及,后两类为研究性论文,多有创见。中南关系研究方面,《中暹关系的检讨》指出近百年来中暹两国关系恶化远因是1910 年华侨抗税骚动后,英法殖民者有意挑拨,加上民间发泄排华情绪,近因是1932 年曼谷政变后暹政府引入日本顾问。⑤李加勉:《中暹关系的检讨》,《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3 年1 月1 日,第26—33 页。《李福协议之附件问题研究》指出李福协议附件之法理无效,⑥刘伯奎:《李福协议之附件问题研究》,《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2 期,1944 年1 月1 日,第108—113 页。学界在研究中法战争时,较注意对越宗主权的丧失,而无人关注战后李福协议附件,刘文是研究这一问题的代表之作。《黄旗军在越暹》则还原了以黄崇英为首的广西农民起义军流寓越南从产生到被联合剿灭的过程。中法战争前后的黑旗军一直受学界关注,而助纣为虐的黄旗军则长期被忽略,直到90 年代才有学者重新研究这一问题。又如,南洋研究的理论方法方面,张礼千辨析中外对“南洋”的称谓,质疑划经纬度区间和列重要地域圈定南洋,并批评将中国南海、台湾等地划入南洋的做法。⑦张礼千:《南洋之范围》,《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3 年1 月1 日,第4 页。余俊贤、朱杰勤阐述了研究南洋的原因,认为研究南洋是基于现实和学术上之需要:一是保护800 万南洋侨胞免受殖民当局欺压,服务抗战建国大业,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和依据;①朱杰勤:《南洋史地之研究》,《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3 年1 月1 日,第7—9 页。二是改变南洋研究的落后局面,建立南洋研究的独立性,以学术手段抵制日寇侵略。②余俊贤:《三民主义的南洋研究:在南洋研究所国父纪念周演词》,《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3 年1 月1 日,第2页;余俊贤:《发刊词》,《新南洋季刊》第1 卷第1 期,1943 年1 月1 日,第2 页。对于研究南洋的方法,余俊贤认为,过去帝国主义者的旧南洋研究可别为两种:一以加强殖民统治为出发点,二以配合侵略政策为出发点,这与民族解放运动世界潮流相悖。我国应彻底地检讨、批判与扬弃旧南洋研究,确立和宣扬新南洋研究的理论与办法,即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研究南洋,依三民主义建设南洋,使南洋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威胁。
此外,《新南洋季刊》也发表部分泛泛而论之作。该刊发表华侨类文章7 篇,多乏新义,有些看来就是政策建议书。例如,《归国就学侨生之指导与救济》先提出所谓问题,再不厌其烦地罗列政府相关法规和行动,最后提几条建议。这种程式化操作在经济类文章中表现更突出,《新南洋季刊》所刊经济类文章,篇幅最大,均以介绍、应用为主。介绍者分列数项,举最新经济资料和统计数据;应用者情况亦相似,列举分析并提出应对建议。这些文章着眼复兴南洋华侨经济,但综而析之“或嫌其繁琐零乱,不足以称为善策,或嫌其夸大无当,亦殊难谓为高论”,是“未出国门而喜凭空设想者所易患之通病”。③姚楠:《战后南洋华侨经济问题之商榷》,《东方杂志》第39 卷第15 号,1943 年10 月15 日,第18 页。总体而言,上述文章无甚学术价值,但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可为政府施政之参考,且从传播南洋知识,进行社会教育的角度来看,由南洋研究所和《新南洋季刊》之创办初衷而言,上述文章则有其现实意义。
四、废置原因:痼疾重重
1945 年春,南洋研究所奉令裁撤,④肖多和年波均未在南洋研究所档案中查到撤销令,只是根据侨委会在5 月份所发指令推测南洋研究所撤销于5 月。叶秉球回忆说,撤销令于1944 年8 月下达。肖文中提到研究所1944 年11 月尚有工作简报,1945 年仍勉力维持,可知叶氏回忆有误。至于撤销日期,只能等待日后档案开放才能确定。维持仅有三年的国立南洋研究机构就此废置。南洋研究所之兴废,从根本上说在于抗战形势的变化。研究所创办之际,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刻,日伪到处散播投降主义论调,试图分化和瓦解抗日力量,国民政府为争取华侨支持和援助,由余俊贤等发起南洋研究所,吴铁城发起成立南洋华侨协会(1942 年5 月),集中从事南洋和华侨研究,大力进行救亡宣传,与日伪展开舆论战,争夺华侨为己所用。随着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中国战场形势逐渐好转,加上南洋研究所并未能发挥有效作用,遂丧失其存在意义。就研究所自身存在的诸多痼疾来看,如主管官员安插亲信、内部矛盾尖锐、研究条件有限等,使之处于分崩离析的边缘,废置早晚不可避免。
(一)主管官员安插亲信
研究所成立初衷在推进南洋研究,但自成立之日起便成为部会首长和总干事安插朋党和亲信的场所。曾在南洋研究所工作的姚楠、叶秉球、朱杰勤等人均对此有所回忆。姚楠认为,南洋研究所是个“因人而设”的机构,“一开始就成为部长和委员长安插私人的地盘”。⑤姚楠:《南洋学会的变迁》,《星云椰雨集》,第58 页;姚楠:《论我国科学院有设置南洋研究部门的必要》,上海《大公报》1949 年11 月5 日,第2 版。叶秉球甚至认为该所是CC 系“直接操纵和全部控制”的一个研究机构而已,其设立纯系CC 系私心自用,特安插本集团人员以准备抗战后操纵和把持海外侨务,其分配经费及任用职员全在余俊贤之手,他引用的人员多半是客籍同乡和旧属。⑥叶秉球:《南洋研究所》,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2,第193—194 页。朱杰勤对研究所人员情况的回忆也很具体,他说:“余俊贤把持所务,大批引用乡人(广东客家人),排挤非客家族的人,研究所故有‘客家会馆’之称。余氏引用的人,大多是程度低,薪水高的人。”⑦纪宗安:《朱杰勤先生学术系年》,《海交史研究》1996 年第1 期,第109 页。根据研究所人员籍贯,可以看出很多人员是余氏的本籍,说明朱杰勤所言不虚。余氏之所以能在研究所只手遮天,是因为正副所长由部会首长挂名,所长陈树人原属改组派,“在汪投敌后,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慑于二陈势力,完全抱着逆来顺受、与人无争的态度,徒挂所长虚名,装聋作哑和得过且过。自成立以来,未曾到所一次”,①叶秉球:《南洋研究所》,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2,第194 页。总干事余俊贤作为教育部长兼副所长陈立夫的代理人,自然手握研究所实权。在这样一个以旧属和亲信为主体的研究机构中,裙带关系主导人际交流,自然不可能取得显著的研究成果。
(二)内部矛盾尖锐
裙带关系必然引起内部矛盾。研究所人员以籍贯区分为广东和江浙两派。广东派以总干事余俊贤为首,江浙派副总干事周尚为首,各以其在所内的旧属、同学、同乡为朋党,互相攻讦。广东派攻击周尚“不学无术,不谙行政”,江浙派攻击余俊贤“只手遮天,把持所务”,双方你来我往,以致余俊贤不到所视事长达三个月,直到陈立夫亲自出马将其召回。陈氏借开会之机,试图平息两派的恶斗,但并未奏效,此种情况下,正副所长相继主动辞职。CC 系另推资历和地位相当,且出身华侨的萧吉珊、何荷仁继任。萧吉珊到任后,擢升江浙派的周尚、黄雄略为正副总干事,所务转由江浙派把持。留任的广东派继续与江浙派内耗,两个派系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研究所解散。两年内因被派系问题而排挤离职者达十余人,占所内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强。
余俊贤以海外党务起家,浸淫海外党务和侨务数十年,对南洋研究和侨务工作自有其认识;而周尚则属于临时出家,本业为医学教育研究,任教育部主管全国学校卫生和体育的专员多年,其一生之职业仅有在研究所的三四年与南洋和侨务有关,即使在所期间,他仍兼任中央大学医学教职。二者相较,余氏更有资格能力领导研究所的工作。两派之分野以省籍为主,又不纯系于属籍。梅县的黎光群因接近副总干事周尚被迫辞职,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而顺德籍的朱杰勤因厌恶乌烟瘴气的派系斗争,也不与余俊贤亲近,而屡次提出辞职,同属CC 系和同乡的萧吉珊、余俊贤因意见素不相合,亦经常发生冲突。
(三)研究所条件有限
研究所是利用侨民教师资训练所旧址创办,在经费、资料、人员方面均有不足。第一,经费拮据。南洋研究所名义上系教育部与侨委会合办,经费上却只是教育部侨民教育项目下的一个小分支。1942年,研究所成立时,预算费用比计划减少大半。计划下拨开办费50 万元,实际到位10 万元,计划经常费每年为19.2 万元(薪俸、购书、办公印刷),实际拨款比预算略微增长,达到22 万元。1943 年增至60 万元,1944 年增至95 万。考虑此时物价暴涨、货币贬值因素,这种增长是微不足道的,根本不足抵消严重的通货膨胀。
第二,资料匮乏。该所成立时,接收原单位图书、杂志2603 册及剪贴资料4600 件,不及一普通中学藏书量。研究所成立后,积极充实资料,一面在国内征购,通过主管部会向有关单位征集;一面委托使领馆选购,同时征集文物以便筹设南洋文物馆。受经费所限和南洋沦陷的影响,搜求效果不佳。由于资料缺乏,研究人员无从着手研究,而按规定研究人员要完成一定的工作任务,迫使他们不得粗制滥造,以致《新南洋季刊》所载文章有的纯属东拉西扯,敷衍塞责,“优秀的研究员既不安于位,就不肯将研究成绩拿出来,而交给研究所的都是潦草塞责,不成文理的稿,或者缴上初稿,而将修正稿另行出版”。②纪宗安:《朱杰勤先生学术系年》,《海交史研究》1996 年第1 期,第109 页。研究所编辑的“华侨丛书”迟迟不见落地,以姚楠、张礼千为代表的中国南洋学会借着研究所的招牌,将该所研究编译人员在工作期间的成果,以学会的名义出版,一个毫无经费的私立学会在1942 至1945 年间竟出版丛书达8 种,③姚楠:《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新加坡华人对东南亚研究的开拓工作》,《南天余墨》,辽宁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10 页。其他有门路的学者也纷纷将著作拿到外面出版,④1942—1945 年间研究所人员工作期间完成而未以研究所名义出版的的专书:范文涛:《郑和航海图考》,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年;缪勒著;范文涛译述:《马来半岛与欧洲之政治关系》,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年;刘伯奎:《马来人及其文化》,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年。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在南洋研究所和行政院工作报告中,研究所成果丰硕,出版专著、报告、丛书如何云云,而实际以“南洋研究所编纂”名义出版者仅姚楠著《马来亚华侨史纲要》和张礼千著《倭寇侵略中之南洋(上编)》两种而已。⑤姚楠:《马来亚华侨史纲要》,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年;张礼千:《倭寇侵略中之南洋(上)》,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 年。
第三,人员流失。南洋研究所人员队伍流动性大,每月均有人员进出。开办两年内,行政人员在20—34 人之间,研究人员在12—23 人之间,人员总数在32—56 人之间。两年来研究所历聘126 人,在职者仅41 人,服务满一年以上者38 人,始终留所工作者10 人。①余俊贤编述:《南洋研究所两年来工作概况》,重庆南洋研究所,1944 年,第3 页。绝大部分到所工作者流失,研究所始终未能维持稳定的人员队伍,总干事余俊贤感叹研究所的任务已经不是努力研究,而是如何安定人心,切实服务。造成人员流失的原因,一方面是待遇差,无法满足正常生活之需,另一方面是研究资料匮乏,无法保证正常的学术研究所需;除主管官员安插亲信外,很大程度上是尖锐的内部派系矛盾带来的人心思变,在南洋研究方面颇有贡献的姚楠、张礼千、朱杰勤在所工作几乎都不满一年便离职而去。此外,人员比例失调也是一个不小的问题。研究所开办最初两年,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的比例基本保持在1:1.5,1944 年甚至一度接1:2。本来是研究机构的南洋研究所,行政人员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研究人员,本该为南洋研究服务的行政成为研究所的主业,南洋研究沦为行政事务的点缀和装饰,这种本末倒置的人员安排对研究机构都是百害而无一利。
结 语
南洋研究所作为民国唯一的国立南洋研究机构,曾被寄予厚望,正、副所长由侨务委员会、教育部首长兼任,总干事亦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其研究计划面面俱到,比之南洋文化事业部的规划亦不逊色,如能善始善终,研究所应当能取得不错的成绩。然而开办仅三年便被撤销,实在令人惋惜。事实上,研究所成立之初即已显露不能长久的迹象,办理过程中表现出的种种问题也昭示着它早晚会被裁撤。南洋研究所创设起于应对日伪在南洋发动的宣传蛊惑攻势,意在争取南洋华侨为己所用,同时为战后建设三民主义的新南洋做准备,为国民政府的政治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和依据,具有很强的实用特征。而一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明朗,政府对此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便迅速下降,工作重心随之转移,对华侨的态度也从争取支持变成施加教育,该机构必然被解散,恢复到原来侨民教育的轨道上运行。其开办因陋就简,接收原侨教机构的场所、设备和人员,经费来源也一仍其旧——在教育部侨教经费下开列。两个主管机关中,教育部一家独大,有职无权的侨委会袖手旁观。在运行三年中,激烈的内斗严重地消耗了有限的研究力量,使其无法正常开展各项工作。由研究所主编的《新南洋季刊》从创刊到停刊近两年间,始终未能办妥期刊许可证,在国民党期刊史上也是少见的现象。②年波:《关于〈新南洋〉季刊的创办》,《学海》1994 年第6 期,第91—93 页。
当然,研究所并非一事无成,它为回国的学人提供了栖身之所,《新南洋季刊》为所内工作人员的南洋研究成果提供了发表平台,侨委会发布、行政院核定的《战后侨民教育实施方案》即是在所编《战后侨民教育实施方案》基础上删减缩编。该方案最早对战后侨教做出规划,成为战后侨教恢复重建的指导文件之一,日后的《南洋华侨教育复员计划》均本此略作修订和完善。此外,研究所还接受政府各部会委托,制定过若干有关南洋侨务和华侨教育的意见和方案等,如教育部编纂侨校教科书意见,外交部谛订新商约意见,侨委会发展南洋华侨教育、商业、法权等方案。
对于南洋研究所的撤销,社会上不是毫无反应。1946 年,参议员陆宗骐便在记者会上询问教育部长朱家骅,是否有意恢复南洋研究所或组织同样性质之南洋研究机构。③《提高教育人员待遇有无具体办法?参政员向朱教长的质问》,上海《大公报》1946 年3 月28 日,第2 版;《教育报告询问案着重复员诸问题》,《大公报》1946 年3 月28 日,第2 版。1948 年,长期任职国民党海外部的李朴生在广州发起的革新侨务促进会也提议恢复南洋研究所,隶属教育部或中研院,培植南洋研究人才。④革新侨务促进会编:《革新侨务建议》,广州革新侨务促进会,1948 年,第16 页。可惜此事终无下文,幸运的是南洋研究所撤销时,其图书设备被国立东方语专所接收,其旧址成为该校在渝期间的办学场所,该校长姚楠系原南洋研究所研究员,素来重视南洋研究,他任语专校长时接纳张礼千、朱杰勤等研究所去职人员,筹建南洋研究室,继续从事南洋问题的研究和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