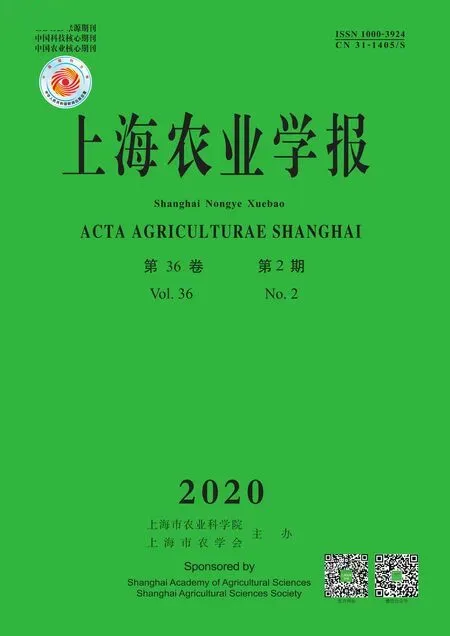乡村振兴视野下上海近代以来农耕文化的流变
2020-05-04曹红亮吴颖静俞美莲
曹红亮,吴颖静,俞美莲
(上海市农业科学院农业科技信息研究所,上海都市农业研究中心,上海201403)
1 研究背景
中国向来以农业立国,几千年来,农业在中国人心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华农耕文化就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中逐渐形成的。农业与地理环境息息相关。在我国,存在着 3 条重要的农业地理分界线,即400mm 等雨量线、青藏高原边缘线和秦岭-淮河线这 3 条分界线,把中国陆上部分划分为四大农耕文化区:北方旱地农耕文化区、南方水田农耕文化区、西北灌溉农耕文化区和青藏高寒农耕文化区。这是中国与自然地理环境相适应的传统农耕文化区域差异[1]。今天的上海市行政区域范围之内就属于南方水田农耕文化区。
农耕文化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个方面。从物质方面来说,农耕文化包括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器具、耕作方式、农村建筑、村落布局等;从非物质层面来说,农耕文化包括与农业生产相关联的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思维模式、民俗节庆、神话谣谚等等。近代以来,随着时代的变迁,上海地区农耕文化也在不断演变,而其演变的根本动因,是经济基础的变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时期的经济基础往往形成与之相应的上层建筑,农耕文化则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1843年开埠之前,上海虽然有元明清时期手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的繁荣,但其整体上还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为主,整个社会文化还是按照传统的农耕文化模式运行。在1843年开埠之后,西方商品经济模式大举进入,上海开始走向西方工业化的道路,与传统农耕文化具有明显异质性的城市商业文化在上海这座城市扎根,两种不同文化开始交融耦合。这种交融耦合没有因为20世纪30—40年代上海成为“东方巴黎”而发生商业文化压倒农耕文化的质变,也没有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城市青年上山下乡而停止,而是在不同阶段相对地此消彼长。因为从整体上来说,这段时期中国的现代工业以及现代商业文化还处在初步成长期,传统经济以及文化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上海工商业地位逐步确立,制造业崛起,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国工业中心,工厂林立,商业发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上海的农耕文化也在工业化、城市化的浪潮中逐渐走向衰微。这种衰微随着2013年中央提出建设“美丽乡村”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出现了转机,其背后的经济背景是:相较于城市的发展,我国乡村的发展依然相对滞后,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必须补齐农业农村这个短板。而对于上海来说,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让整个城市更加生态宜居,单靠城区显然是片面且难以为继的,必须启动乡村这一新引擎,必须振兴当前相对凋敝的乡村。
2 上海近代以来农耕文化的流变
根据上述对上海社会发展的情况分析,本研究将上海近代以来农耕文化的流变分为以下四个时期:即江南农耕文化传承期、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并行及耦合期、农耕文化的式微期、农耕文化的复兴与转型期。
2.1 江南农耕文化传承期(1843年上海开埠前)
今天上海管辖的范围,是在地壳运动加上长江和大海的共同漫长作用下形成的。在该区域范围内,已经发现的古文化遗址主要有崧泽遗址、广富林遗址、马桥遗址、柘林遗址、福泉山遗址等。从考古发掘出的文物可知,有石锛、石铲、石刀、陶网坠,还有已经碳化的稻谷颗粒和家猪的猪骨等,这证明在距今6 000年前,上海的先民们已经在这块土地上从事农作物种植、家畜家禽饲养和渔猎活动。随着唐宋江南的不断开发,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历代中华帝国的粮仓,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到了明清时期,以苏州、杭州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将农耕文明的繁荣发展到极致,与之相应的农耕文化也得以传承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开埠。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上海与周边的江浙地区是一个整体,逐渐形成了典型的中国江南农耕文化。从耕作方式来看,稻棉耕作文化与渔耕文化并存。江河纵横以及滨江靠海的良好自然环境造就了上海成为鱼米之乡,成为明清棉花种植及纺织业中心,也造就了上海海盐业的发达。从村落布局来看,乡村的房屋、农田、河浜、堤岸、道路、 坟地、庙宇、祠堂等自然和人文景观错落有致,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的水乡生态图景,这也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格局[2]。从生活方式来看,人们以村镇为主要聚居地,彼此协作共存,以“熟人社会”的形态共同生活,而民俗节庆是这种农耕文化的集中体现。上海农耕文化根植于吴越文化,在融汇各种文化基础上逐步形成,与中国农耕文明相关的主要风俗习惯都在此得到传承,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民俗节庆也得以弘扬。全国性的节日如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都一直传承着。地方性的民俗节庆如城隍庙会在上海异常兴盛,明代中叶后,各乡镇几乎均建立了城隍庙,至清代中叶,松江府、太仓县所辖的各县与主要市镇也都修建有城隍庙宇,使城隍信仰得到广泛普及。具有明显渔耕文化特色的妈祖信仰以及各类迎神赛会也在上海十分兴盛。根据上海县志记载,明清两代经修葺、增建和重建后供奉妈祖的庙宇有南圣妃宫、上海天后宫(清代,妈祖被朝廷敕封为天后,妈祖庙遂被称为天后宫)等好几座,在今天上海的金山、奉贤、南汇、川沙、宝山、崇明等地区也建有数量众多的妈祖庙。此外诸如关公庙、财神庙、观音庙、土地庙、刘猛将庙等也遍布明清时期上海的各个乡镇,仅青浦县金泽镇的庙宇就达四十多座[3]。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的县府治所所在地,虽然名义上是城市,商业相对发达,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农村有些不同,但在近代西方意义上的城市引入中国之前,这些城市总体上可看作是农耕文化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其内在本质还是属于农耕文化范畴。表1列举出当时部分民俗节庆。
表1 上海地区历史上部分重要民俗节庆
Table 1 Important folk festivals in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注:根据《中国民俗大系·上海卷》及相关文献整理,表中未列出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全国通行的重要传统节日
2.2 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并行与耦合期(1843年上海开埠—1978年上海改革开放)
1843年上海开埠,“华洋杂居”,上海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伴随着上海县城西北边众多西式建筑的出现,特别是成片的各国租界区的铺开,一种全新的城市商业文化开始冲击上海传统农耕文化,西方工业文明开始植入传统农耕文明的土壤之中,并不断发展壮大。上海进入了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并行与耦合期。
西方商业文化在上海兴起最直观的表现在城市建设风貌上,更深层次的则表现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相关联的生产方式和居民的生活方式上。在租界地区,由于直接受西方统治,租界内的建筑、经济、社会、政治各项制度以及宗教信仰都以租借国母国为模本。上海开埠后,重商重利主义得以张扬,经由上海港进出的繁荣的对外贸易和国内埠际贸易,直接刺激了上海及周边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展[4]。据光绪《重修华亭县志》记载,19世纪70年代中期,上海地区禾稻种植仅占全部作物种植的20%。尽管那时候上海的商业文化蓬勃兴起,但其影响范围主要还是限于城区特别是租界区内,远离城市中心的各郊区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并不大,传统旧俗的成长土壤依然浓厚[5],在郊区依然是传统农耕文化的天下。
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在上海的登陆,西方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耦合是必然的。上海在开埠之前,本来就是一个五方杂处、海纳百川的城市,“各省均有寄寓之人,首指者为广帮,次则宁、绍,次则苏帮,最次则本帮”[6]。国内各地文化在此交融,只不过是因为同为中华农耕文化体系,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具有明显异质特征的西方商业文化的进入,则使得上海地区的文化呈现出异样的风貌。首先从建筑上,上海石库门风格的出现,就体现出西方建筑样式与东方四合院内在的结合;而传统的正月初四接财神虽然是全国性民间信仰,但在商业文化影响下的上海人心中则尤受推崇。上海竹枝词所谓“香烟结篆烛生花,百子高升震耳哗。天上财神有多少,下方迎接遍家家”,反映的就是沪上民众抢接财神的热闹景象。当时上海这种异质文化的耦合状态,如果从服饰角度来形象体现,则为“穿长袍、马褂的有,穿西装、短服的也有;皮鞋、布鞋的有;礼帽、瓜皮帽的也有。各种颜色,各种式样”[7]。当然,总体上来说,这种耦合度是随着中心城区与郊区距离的增大而递减。
由此可见,上海在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的并行与耦合期,中心城区是以商业文化主导的,但农耕文化依然顽强传承着,即使出现像1930年民国政府下令废除春节这种极端现象,也依然如此;郊区是以传统农耕文化为主导,但商业文化也润物细无声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这种状况延续了130多年,虽然其中有一些起伏,如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出现的对商业的极左思想认识,以及推行所谓“革命化春节”“破四旧”等等,但总体上来说变化是不大的。
2.3 农耕文化的式微期(1978年上海改革开放—2013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建设“美丽乡村”)
上海农耕文化的式微源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上海自公元1292年建县至今,一共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城市化进程,即第一阶段为1292—1843年、第二阶段为1843—1949年、第三阶段为1949—1978年、第四阶段为1978年至今[8]。但是,从上海建县到1978年上海改革开放前,上海的城市化进程是相对缓慢的。撇开其他因素而单从城市规模来看,在上海建县到开埠之前,今天的外滩、人民广场等地全是农田;县城西门外(今肇嘉浜路和徐家汇路)河道里还可以扬帆启航;租界范围还没有扩大之前,处在城市远郊的静安寺每到四月初八浴佛节还是四周农民遛牛祈福的场所;改革开放前的上海,中心城区范围还仅仅大致局限在今天的内环之内;而上海当代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致起步于1978年,到1990年左右国家启动商品房改革之后骤然加速,发展到了今天溢出外环的规模。
为破解长期以来我国逐渐形成的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早在1984年,上海就提出“城乡开通”的发展理念,到1985年正式提出“城乡一体化”。上海“城乡一体化”的整体布局,是要在全市范围内逐步形成“1966”四级城镇体系框架,即要建设1个中心城、9个新城、60个左右新市镇、600个左右中心村。在2016—2040年上海城市总体规划中,上海市又对“1966”四级城镇体系进行了扩容升级。
一直以来,上海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模式就是走乡村城镇化和郊区工业化之路,尽可能地用先进的城市模式直接覆盖落后的农村。因为在决策部门看来,上海郊区农村城市化的发展,可以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提高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拓宽农民就业门路,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改善投资环境,为上海郊区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全面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9]。

表2 上海农村基层组织、户数和人口情况
数据来源:《上海农村统计年鉴2017》
应该说,这种模式充分利用了城市的强大活力,对于提高上海农民的生活水平来说是卓有成效的,但对传统农耕文化来说,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首先,从外部的建筑和村落布局来说,随着上海中心城区以及其他副中心新城外围的不断扩大,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商品房制度的实施,城市化进程骤然加快,传统的乡村房屋、农田、河浜、堤岸、道路、庙宇、祠堂的格局被严重破坏乃至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新式居民小区、一幢幢高楼大厦;只有在城市触角一时难以企及的远郊地区,尚能保留部分传统江南民居和农村格局。农耕文化由此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物理载体和空间布局。其次,从农村人口状况来说,城市化的推进对农村产生了强大的虹吸效应,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镇,或者通过动拆迁和城市中购房转变为城市居民,村庄以及农村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传统农耕文化时代的“熟人社会”走向瓦解。以2012—2016年为例,上海村委会个数就从1 610个降为1 582个,村民小组数由23 686个降为23 339个,农村户数由 112.08万户降为99.13万户,乡村人口数由 289.70万人降为 256.67万人(表2)。而从生产生活方式上来看,从事第一产业的农民比例较低且越来越少,第二和第三产业成为农村从业人员的主阵地(表3)。即使有很多非沪籍人口的补充,他们也只是临时的租客和寄居者,上海当前的户籍政策以及农村土地制度决定了他们与原住民之间往往仅是经济联系,而缺乏彼此的社会交往和文化联系。这样,上海农耕文化在失去了存在的物理空间的同时,又渐渐失去了“人”这一最核心的要素。这也就导致了如下一种状况的出现:历经城市化、工业化洗礼后的上海农村,多数人在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上已逐渐“去农村化”而与城市融为一体了。

表3 上海农村从业人员情况
注:根据国家统计制度规定,表中2012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中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从业人员,从2013年起,农林牧渔服务业从业人员从第一产业中划出,归入第三产业。数据来源:《上海农村统计年鉴2017》
上海市大力推进农村城市化工程是顺应民心的。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城乡二元化格局让上海郊区农民深受其苦,大家都非常期盼能够移居城镇,希望在城镇里买上高楼大厦的商品房,强烈希望摆脱被人瞧不起的“乡下人”身份而过上城市人“现代化”的生活。早在1992年对上海嘉定区马陆乡400多个农民的问卷调查就发现,希望政府能让自己移居城市(包括城镇)的农民占40%以上,当时全乡已有800多户农民在城镇买了商品房,农民要求进城定居已成了郊区一部分农民关心的“热点”之一[10]。而今天,马陆那里除了还有部分葡萄园之外,已经变成上海著名的物流园区和工业园区。可见,在农民生活的实际需求面前,那种希望农村一直保持田园牧歌式状态的思想,只是局外欣赏者无关实际痛痒的幻想。
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以“时间就是金钱”为代表的生存与发展成为包括上海在内的全国人民首要追求,农村及其农耕文化往往被视为土气的象征而不受重视。当然,上海城乡各地依旧过着春节、元宵、清明、 端午、中秋、重阳等等传统节日,有的时候也会举办一些传统庙会、舞龙舞狮之类的活动,但这些节日多半只是城市化商业文明生活的一种调剂,具有浓厚的城市商业文明色彩,其形式多样性、热闹度以及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已经大不如从前。由于上海农耕文化的根基已经基本丧失,很多具有深厚历史传统和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民俗项目也走向衰落,如七宝的皮影戏、崇明的扁担戏、南汇的锣鼓书、黄浦江的观潮、滨海地区的渔船号子和渔船山歌、南汇的哭嫁歌和哭丧歌、嘉定徐行的草编工艺、奉贤乡土纸艺、青浦商榻阿婆茶等等。这种状况大致延续到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思想的提出,才有了一定的改观。只是在强大的城市商业文化的影响辐射下,上海这种改观较之其他地区更不明显。直到2013年中央1号文件从国家层面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之后,上海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化发展问题才真正开始进入有关部门的视野,农耕文化的发展也迎来了相应的转机。
2.4 农耕文化的复兴与转型期(2013年前后至今)
“仓廪实而知礼节。”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从政府到民间百姓,都慢慢意识到精神文化才是人们内心更为本质的需求,农耕文化也是如此,它逐渐变成久居城市的人们一种难以释怀的“乡愁”。而当人们在经济上富裕之后想追寻这种“乡愁”的时候,才发现经城市化洗礼之后的农村早已面目全非,上海尤其如此。
国家显然感知到了社会的这种需求,早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就正式提出了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上又提出“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8年,浙江省安吉县正式提出“中国美丽乡村计划”,出台《建设“中国美丽乡村”行动纲要》。在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在2013年中央1号文件中,国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建设、环境保护和综合整治工作。2013年2月,农业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的意见》,新农村建设升级为“美丽乡村”建设。在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上,国家又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在2018年2月4日正式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接着,同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在第七篇中把乡村文化建设作为重要内容予以阐述。这些文件的颁布,体现了国家对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建设的高度重视。
上海农耕文化的复兴和转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毋庸讳言,对照中央的要求,上海发现,对比周边江苏、浙江乡村建设,上海农村多数地区显得不那么“美丽”,甚至还有点“凋敝”。因为上海一直以来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思维模式去改造农村,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而不是以农村为中心去建设“美丽乡村”,实现乡村振兴。上海的农民也多数按照“1966”四级城镇体系框架搬进了城市,乡村故园被主动或被动抛弃。因此,已经高度城市化的上海乡村如何走向“美丽”、如何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振兴目标,是摆在上海面前的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在国家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规划之后,上海市委、市政府立即统一思想,研究并发布了《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及《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年)》;提出上海乡村振兴的重大抓手是“363”工程,即打造“三园”工程(“美丽家园”“绿色田园”“幸福乐园”),实施六大行动计划,落实三大保障机制;提出大都市郊区乡村的振兴体现为“美在生态,富在产业,根在文化”。可见,农耕文化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地位,包括农耕文化振兴在内的乡村振兴已纳入上海市委、市政府当前最为重要的议事日程中。目前,上海农耕文化的复兴与转型才刚刚开始,如很多节日和民俗项目焕发出新的生机,也有些历史上的节庆和民俗项目重新登上时代的舞台——如豫园元宵灯会、龙华庙会、罗店龙船文化、松江关帝庙会的舞草龙、金山吕巷的小白龙舞、南汇和金山的打莲湘、浦东三林的中秋拜月习俗、三林的城隍“三巡会”展演、松江的妈祖祭拜以及江南丝竹、奉贤滚灯,等等。这些民俗的复兴与复归反映了当代上海人对民俗文化传统的认同,它饱含着民族凝聚的情感,实际上是对传统异化的一种抗争[11],只是这种复兴和转型还要经历很长一段时间。
诚然,当前上海农耕文化的复兴与转型面临诸多困难。上海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及其农村人口的锐减,已经导致农耕文化的传承失去了基本的传承主体和承载空间。青年人口流向城镇,农村传统的村舍-街巷-农田的空间布局遭到破坏,很多传统农耕文化随着时代的变迁自然走向了衰微。同时,如何实现新时代乡村的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还需要持续的探索。在上海今天的农耕文化传承中,很多时候存在明显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商业倾向,而非真的为了传承;很多传承只是停留在娱乐化的表演或旁观式的体验,而非真正沉浸式的情景融入,人们无法从中得到乡愁情感的内在满足。因此,在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上海现存农村能否在城镇化道路之外,走出一条既能实现农村经济繁荣又能实现农耕文化昌盛的新路?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3 结论与展望
上海农耕文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在世世代代的生活中累积形成的。其流变随着社会的变迁总体上体现为农耕社会-半农耕半工业社会-工业社会乃至信息社会的过程[12]。上海农耕文化的流变始终是与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的,它既具有相对稳定的传承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上海虽然是国际化大都市,但其农耕文化的传承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今天。因为它承载着祖祖辈辈上海人的集体记忆,标识着上海人的身份印记。即使人们在某个时期、某个时刻感觉不到它甚至将它遗忘,但它往往会在特定的时空成为相当一部分人的内在精神需要,成为人们心灵的一种寄托与慰藉,它是上海文化的根,不但不会消亡,相反会在时代的土壤里不断延续传承。当然,传承农耕文化应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不对历史文化过度盲目赞美;应坚持“与时俱进”的原则,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