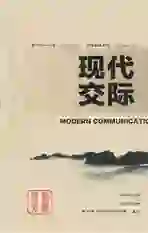口述传记《我的前半生》著作权纠纷案浅析
2020-04-27陈昕彤
摘要:《我的前半生》著作权纠纷案发生于1984年,从起诉到终审判决历经十年,被称为“天字第一号”著作权纠纷案。通过资料查阅还原了案件经过和结果,梳理了案件合作作品与否和作品体裁定性两个案件分歧点,并分析了李文达工作认证和案件特殊性,同时就口述传记执笔者的特别身份和如何避免著作权纠纷等问题进行延伸思考。
关键词:著作权 合作作品 名人自传 口述传记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20)06-0052-02
《我的前半生》最初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东北抚顺战乱管理所服役期间,由本人口述、其弟溥杰代笔的一份自传体悔罪材料(又称“灰皮书”)。1960年后,中央指示公安部对其修改整理,公安部将任务委派给群众出版社。经过共同商议,决定由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协助溥仪完成传记。1960年4月至5月,溥仪口述,李文达执笔记录,整理出16章24万字修改稿,期间李文达还曾远赴东北收集史料。1964年3月,以爱新觉罗·溥仪署名的《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
争端起源于1984年中意合拍的电影《末代皇帝》。意方提出需有《我的前半生》著作权享有者的同意并授权才能签约。此时溥仪已经逝世,由遗孀李淑贤继承著作权,由于报酬分配问题,李淑贤拒绝授权。随后李文达以作者身份与意方签订合约,李淑贤得知后将其告上法庭。
一、案件结果
(一)各方意见
对于此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国家版权局、全国人大法工委均认为《我的前半生》为合作作品,著作权为溥仪和李文达共有;社会科学院法学所认同《我的前半生》为合作作品,但认为著作权为溥仪和国家共有;最高人民法院则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我的前半生》著作权为溥仪独有,死亡后由李淑贤继承,但李文达享有适当的经济报酬。
(二)判决结果
1995年1月26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溥仪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的作者,并享有該书的著作权。李文达在该书的成书过程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是与溥仪之间不存在共同创作该书的合作关系。因为李文达并非直接侵权,所以驳回李淑贤要求李文达赔礼道歉的诉讼。李淑贤服从一审判决,但李文达的法定继承人不服从一审判决,再次上诉。1996年6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李文达方的上诉,保持原判。
二、案件分析
(一)双方分歧
1.是否为合作作品
合作作品有两个判定条件。第一,合作作者具有共同创作某一作品的合意,即将自己的创作成果合并为一个整体的“意图”。第二,合作作者具有共同创作的行为。
溥仪的创作地位显然是无可置疑的,作为传记的主人公和主要叙事者,他提供了大部分的素材。而李文达在撰写过程中也不是一个机械的记录者,他做了包括收集资料、构思、校改等工作,还进行了许多主观能动性创作,因此第二个判定条件成立。问题在于第一个条件,两人是以合作为意向进行创作的吗?1960年灰皮书完成的时候,群众出版社接收到的指示是“协助”溥仪修改材料使之能够最终出版,因此传达给李文达的也是“协助修改”任务,而非“参与创作”。无论是群众出版社还是溥仪本人,都未提出由两人合作创作《我的前半生》。在书稿完成后,溥仪曾写下“四载精勤如一日,挥毫助我书完成”的条幅赠给李文达,也说明了李文达与溥仪之间是协助关系而非合作关系,因此著作权不能由双方共享。
2.文学性传记还是一般自传
这个问题看似与本案关系不大,实则决定了李文达的主观性创作对作品是主要构成还是辅助作用。文学性传记与自传的区别在于叙述人称,文学性传记是由他人对传主的人生故事进行文学性呈现,作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空间大;而自传的传主和作者则是同一人。当时各方意见出现分歧,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是文学性传记,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是自传体文学作品。在本案的特殊情况中,虽然存在李文达第二方的参与,但是笔者认为《我的前半生》仍然是自传体作品。原因在于,其以第一人称的自传体形式叙述了溥仪的前半生经历,体现的是溥仪的个人意志。李文达尽管有主观性创作,但均要符合溥仪本人意愿,发挥空间不大。
(二)李文达的工作认证
李文达虽没有该书的著作权,但作为执笔者,仍然享有特定的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在《我的前半生》正式出版后,首版稿酬11700余元,群众出版社按照社内一般写稿人员稿酬的50%支付李文达,这一比例已经是给付非主要撰写者稿酬的最大比例,这正是出于对李文达付出大量精力的考虑。
而在精神权利方面,溥仪和中央对李文达的工作肯定也是一种精神奖励。溥仪除了送给李文达横幅外,还在日记中多次提到李文达对他完成此书的巨大帮助,认证李文达的劳动付出。
(三)本案的特殊性
案件的审理前后历经10年,惊动了三级法院,可见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首先是作品形式的特殊性。口述自传的作品形式存在两方参与者著作权的归属问题。这一点前文已经说明,故不再赘述。
其次是传主身份和传记内容的特殊性。溥仪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为政治性质的社会名人;《我的前半生》反映的是溥仪在新中国时期接受思想改造并转向党与人民的过程,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且社会影响重大,不适宜为传主之外的人署名。与之相对应的,该书产生的舆论评价也由溥仪一人承担。
最后是社会影响的特殊性。社会名人的传记创作也多由他人执笔,如果《我的前半生》著作权纠纷案判决结果改变了本书的著作权归属,可能引起无法控制的连锁反应。
三、延伸思考
(一)为了避免出现法律问题,口述传记合作者应该提前先以书面形式确定著作权归属
本案的审判困难除了在于作品本身,还在于当事人双方一开始没有做好书面约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合作以特定人物经历为题材完成的自传体作品,当事人对著作权权属有约定的,依约定;没有约定的,著作权由该特定人物享有,执笔人或整理人对作品完成付出劳动的,著作权人可以向其支付适当的报酬。”可见,某些情况下,口述传记的著作权可以由传主和参与写作人员共有,但应该有书面约定。当诉讼发生时,当事人溥仪已经去世,再做书面约定已经无从谈起,其遗孀李淑贤也无法代表本人意志,因此给本案的定夺带来很多争议。相关出版人员都应该提高自身著作权意识,将著作权归属问题用书面形式确定,以免给日后造成麻烦。
(二)执笔者放弃精神权利的同时也避免承担传记带来的社会舆论影响
传记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作品,体现的是特定个人的人生轨迹和意志,传主作为独立个体向社会输出个人价值。传主独享著作权更有利于社会对传记的认识和接受,更清楚地意识到传记中的“我”是传主本人。执笔者没有著作权初看令人为之不平,但传主独有著作权也意味着由其独自承担传记带来的社会舆论影响,未署名的执笔者避免被波及。当然,口述传记的执笔者扮演的是类似于幕后英雄的角色,可能放弃精神权利的情况也考验执笔者的奉献精神和职业责任感。
《我的前半生》著作权纠纷案作为中国著作权史上著名的大案,交织着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元素,体现着对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平衡。名人口述传记的特殊性使得著作权归属仍存在争议,除了需要当事双方的合法约定外,还要更为完善细致的法律加以规范。
参考文献:
[1]王庆祥.《我的前半生》:溥仪、李文达著作权纠纷案揭秘[J].现代交际,2007(3):11-13.
[2]叶海涛.文学性传记合作作品著作权之认定[J].知识产权,2003(2).
[3]李明德,许超.著作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127-128.
[4]熊晶晶.关于自传体作品著作权的归属[EB/OL].(2014-12-04).http://www.fabang.com/a/20141204/688335.html.
责任编辑:孙瑶
[作者简介]陈昕彤,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编辑出版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