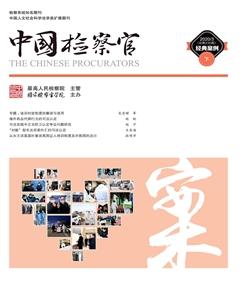“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的司法认定
2020-04-17王东海
摘 要:在非法买卖外汇犯罪活动中,以“对敲”方式实施犯罪的数量日益增多。“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具有证据链条长、行为人联系网络化、境外取证困难、境外人员违法性认识辩解空间大、管辖等法律适用争议多等司法认定难题。认定行为人实施“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应当准确理解和适用我国刑法规定的属地管辖、属人管辖、普遍管辖等管辖原则,结合行为地、结果地证据审查,解决管辖权问题;综合评估行为人供述和辩解,结合其成长经历、对我国大陆法律的认知等,确定其主观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全面审查账户资金流向、行为人之间相互联系的电子数据、境外资金账户等证据,确定非法买卖的既未遂和具体金额。
关键词:非法买卖外汇 对敲 司法认定
一、源于司法原生态的案例引入
2018年10月至2019年10月期间,行为人周某(我国大陆居民)与李某(2002年由我国大陆移民到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系香港永久居民)共谋,通过介绍他人非法买卖外汇进行牟利。在没有国家机关授权的情况下,周某与李某先后三次联系他人帮助兑换人苟某某非法兑换外汇共计人民币2.38亿余元,周某从中获利约65万元,李某从中获利约40万元。周某、李某等人非法买卖外汇的操作流程为:苟某某准备兑换外汇时便通过whatsapp软件或微信等联系周某,提出兑换外汇的汇种、金额等;周某通过微信等与李某联系,询问兑换汇率、汇入人民币的银行账号等;周某经过中间加价后[1],将汇率、打款银行账号等转给苟某某,苟某某同意后将相应人民币款项汇入李某指定的银行账户,并将其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开设的银行账户提供给周某,经由周某告知李某。李某确认收到人民币汇款后,将相应外汇汇入到苟某某提供的香港银行账户,并将已存入苟某某外汇账户的银行交易截图或确认信息发给周某,周某再转给苟某某;苟某某确认所在香港的外汇账户到款后,将信息反馈给周某,周某再反馈给李某。以此,完成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本案中,行为人所采取的非法买卖外汇模式,系“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2]——把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直接交易进行隔离,购汇人将人民币直接汇入行为人提供的人民币账户,行为人则通过境外银行账户或现金直接将外汇汇入购汇人指定的外汇账户。非法经营者和兑换者之间的人民币账户和外汇账户之间并不会发生资金往来,也难以看出非法经营者和兑换者之间有买卖外汇的现象。
由此可见,在“对敲型”非法买卖外汇犯罪过程中,行为人故意将人民币账户和外汇账户之间进行隔离,“使人民币资金和外币资金分别在境内、外形成了独立的清算循环”[3],故意造成“资金未发生物理跨境转移”[4]的假象来逃避侦查,导致了案件侦查过程中难以收集到直接证实人民币和外汇之间发生关联的银行账单等客观性证据,只能通过对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人、介绍人、外汇兑换客户的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与涉案账户资金流向账单的印证,微信聊天记录、短信记录等电子数据,以及鉴定意见等间接证据,来证实犯罪事实的发生和犯罪行为系行为人所为。这种犯罪模式的特殊性和隐蔽性,造成了司法实践中侦查取证困难[5]、行为人辩解空间大、法律适用争议多,需要加以研究,以准确对犯罪进行打击,惩罚破坏外汇管理秩序的犯罪分子。
二、罪与非罪的观点纷争
在上述案件中,行为人李某到案后,辩称在我国香港没有实施外汇管制,其行为在香港不构成犯罪。对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能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犯罪。理由为:一方面,李某实施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发生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12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港币自由兑换……”。《刑法》和《外汇管理条例》也不在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清单之中,即我国大陆的外汇管制规定和刑法的相关规定不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另一方面,李某辩称其行为在香港是合法的,从犯罪构成来看,李某对其行为缺乏违法性认识,而非法经营罪系故意犯罪,又是法定犯,李某不具有犯罪的主观故意。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1)虽然李某的身体动静发生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但刑法上的危害行为不是行为人的身体动静,关于行为的“身体动静说”早已经被理论界否定,也被司法实务界抛弃。李某的身体动静虽然发生在香港,但其利用了在我国大陆开设的银行账户,指使了在大陆工作的人员进行了转账,应当认定其非法买卖外汇的部分行为在我国大陆。(2)李某的行为侵犯了我国大陆的外汇管理秩序,犯罪结果地在我国大陆,应当适用大陆刑法对其进行定罪量刑。(3)虽然李某辩称其行为在香港是合法的,但是李某离开我国大陆时已经13岁,且一直到案发其一直与我国大陆地区具有密切的生意往来,其本人供述知道在大陆换取外汇需要到指定地点,私人不能随意买卖外汇。
应当说,第二种观点是科学的,应当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三、刑法解释视角的理论阐释
(一)李某客观上实施非法介绍、帮助买卖外汇的行为
对于非法介绍买卖外汇和通过“对敲”形式买卖外汇的行为,我国均有相关的入罪规定。《外汇管理条例》第45条规定:“私自买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倒买倒卖外汇或者非法介绍买卖外汇数额较大的,由外汇管理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了变相买卖外汇行为也应当入罪,“变相买卖外汇”常见的方式之一即本案的“对敲型”买卖外汇[6]。虽然李某辩称,其只是起到介绍作用,但是即使其只是起到介绍作用,也应当认定为其行为构成犯罪。一是,我国《外汇管理条例》对此种行为有明确规定,且李某的行为已经不单单是牵线搭桥的介绍,在已查明的三次非法买卖外汇中,其中两次李某都提供了对公账户和控制的私人账户用于资金过桥,从中获取数额较大利益,参与程度已经超出简单的介绍。二是,李某与周某共同为买家和賣家进行介绍,且从中收取数额较大的利益,不同于只是应兑换需求人的要求将非法买卖外汇人的联系方式等转告给兑换需求人,而是既为兑换需求人“代言”也为非法买卖外汇人代言,即“为非法买卖外汇的双方进行介绍”,[7]特别是积极为非法买卖外汇的行为人提供资金过桥等实质性帮助,并从中收取巨额利益,李某与周某的行为显然已经与非法买卖外汇人构成共同犯罪。因此,李某提出的“只是起到一个介绍作用”的辩解不是其逃避我国大陆刑法处罚,或者说是其免受我国刑法处罚的理由,其辩解不影响对其行为涉嫌犯罪的认定。
(二)李某主观上具有非法经营的犯罪故意和违法性认识
虽然非法经营罪是法定犯,刑法理论多数观点认为法定犯的成立需要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违法性认识可能性,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而李某也多次辩解,称其介绍买卖外汇的行为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违法,不知道在大陆通过“对敲”方式买卖外汇是违法的。但是,这都不影响对李某主观上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判定。因为李某明确供述,“我知道大陆通过银行和兑换点以外的渠道用人民币兑换外币是违法的”,知道我国大陆实行外汇管制,兑换外币必须去正规兑换点或银行,兑换时也有数额限制。这些认识足以说明,李某主观上明知在我国大陆地区,凡是在银行和授权的兑换点外兑换外汇是违法的这一事实。本案中,李某与周某共同为苟某某兑换外币的行为,显然是发生在银行和兑换点之外的,因为如果苟某某是在兑换点兑换的话就不会去找李某,且兑换的金额远远超出我国大陆法律所允许的限额,当然是违法的。至于李某辩称的“不知道在大陆通过对敲的方式兑换外汇是否违法”,不合逻辑,也不合常理,因为“对敲”的实质也是兑换外汇,“对敲”虽然采取人民币账户和外汇账户分离的方式,与一般的直接让人民币和外汇发生交易的形式不同,但其本质与一般买卖外汇并无区别,都是违反了外汇管理制度,在国家授权的银行和兑换点外兑换外汇,且李某提供的账户开户地均在中国大陆内,已经不单纯是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简单的进行介绍。因此,关于李某主观违法性认识不明知的辩解不成立。
(三)李某的行为违反我国大陆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我国《刑法》第6条规定:“犯罪的行为或者结果有一项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就认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12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港币自由兑换……”。《外汇管理条例》《刑法》也不在附件三“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清单之中,即我国大陆的外汇管制规定和刑法的相关规定不能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但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港币自由兑换……”这一规定,只是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有效,即,如果整个的买卖外汇行为发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则不以犯罪论处。本案中,行为人李某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并不是单纯发生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其与周某通过“对敲”方式完成非法买卖外汇,人民币与人民之间的资金往来发生在我国大陆,且李某提供的用于资金过桥的公司账户和私人账户均系在我国大陆办理的开户。可以说,李某的部分危害行为发生在我国大陆,已超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因此,李某的行为已经不只是单单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介绍买卖外汇,而是超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区域,直接违反了我国大陆刑法和外汇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李某的行为危害到我国大陆的金融管理秩序
我国大陆实行外汇管制政策,1998年12月29日通过并实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和2019年2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均规定,非法买卖外汇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论处。李某与他人通过“对敲”的方式非法买卖外汇,使相应的外汇买卖脱离了我国大陆的监管,直接危害到我国的金融管理秩序。李某的行为从物理性表面上看发生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但行为的实质是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通过介绍联系与在大陆的周某进行共同犯罪,其行为的最终结果也使得苟某某兑换的港币脱离了大陆的监管,其行为实质上是危害了对我国大陆的金融管理秩序。
注释:
[1]本案中的中间加价,是利用汇率差来实现。如,李某告知周某港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汇率为0.88,周某则告知苟某某兑换汇率为0.98,从而从中多收取差价,进行获利。
[2] 也有人将该种方式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称之为“资金对冲方式”。参见周庆琳、汤咏梅:《采用资金对冲方式非法经营外汇构成非法经营罪》,《人民司法》2010年第24期。
[3]外汇局福建省分局课题组:《地下钱庄经营网络化趋势及监管》,《中国外汇》2019年第15期。
[4]周慧钦、薛严清、刘闽浙:《跨境汇兑型地下钱庄的成因、特点及治理——基于福建情况分析》,《区域金融研究》2019年第3期。
[5]參见王晓峰、张洪海:《非法资金跨境转移与防范》,《中国金融》2017年第20期。
[6]参见杨兴培、吕鼎:《论非法经营罪的司法适用——以非法买卖外汇为视角》,《法治社会》2018年第6期。
[7]王东海:《“非法介绍买卖外汇”何种情形可予定罪》,《检察日报》2019年4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