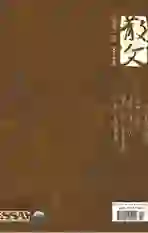水湄三篇
2020-04-14方华
方华
秋后的菖蒲,生长得繁茂葱茏,在湖塘河沟边竖起一道绿色的屏障,是水边一道美丽的风景。
“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这是唐诗人李贺的《大堤曲》。时光易逝,但菖蒲青青。人到中年,每在郁郁的菖蒲丛边彳亍,总会想起那遥远的童年。
夏末秋初,菖蒲抽薹,会结出一个个的圆柱状的棕色的蒲棒,乍一看,极似串在一根木签上被烤过的火腿肠。在我孩童时,还没有火腿肠这种食品,只知道这蒲棒采回家,母亲可以用它做枕头芯,又软又轻,枕在头颈下很舒服。
面包一般松软的蒲棒会在风中爆开,白色的绒花撒落蒲叶和水面。蒲棒成熟的时候,若和母亲一起正从菖蒲丛边走过,母亲会折下一两支给我,我鼓起小嘴使劲地吹,快乐的笑声就和着绒花在田埂上、蓝天下,随风飘散。
一日闲暇,在郊外的湖边漫步,看见蒲丛边有拍婚纱照的,摄影助理的手里即拿着几支蒲棒,在相机咔嚓咔嚓的快门揿动里,洁白的蒲花被吹散,漫天飞舞,营造出非常浪漫的氛围,让我感到意外惊喜。
幼时,母亲可能怕我们玩水失足,经常恐吓:不要到水边去,那里有蛇、水獭猫。可这样的警告实在敌不过菖蒲丛中那些诱惑。
菖蒲丛中的水域,会有野生的菱角,是物资匮乏时代孩子们喜爱的美食。也有一些零落高举的莲蓬,成为孩子们的惦念。运气好的话,还会在那些或与芦荻杂生或被黄色的浮萍花围绕的蒲丛中,捡到水禽生下的蛋。
捡到硕大的大雁或鹭鸟留下的鸟蛋,会喜滋滋地用衣角兜回家,虽然会得到母亲的一番呵斥警告,但也会在随后的饭碗中品尝到一顿难得的美味。
母亲也会破例亲自带我们到水边去。在烈日下,母亲用镰刀割下一人多高细长的蒲叶,顺便收摘一些孩子们够不着的菱角、莲蓬,丢给站在埂上的我和妹妹。割下的蒲草,母亲会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一连几日编织蒲垫、蒲扇。
夜晚,摇着小小的蒲扇扑打飞舞的萤火,或是坐在散发着香气的蒲垫上,看满天的星光,听母亲讲牛郎织女、嫦娥奔月。现在想来,真有杜牧的“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的美好意境。
《本草·菖蒲》称:“典术云:尧时天降精于庭为韭,感百阴之气为菖蒲,故曰尧韭。方士隐为水剑,因叶形也。”菖蒲叶形似剑,香味浓郁,有解毒祛邪之效,故中国人有在端午时,在门窗上悬蒲叶以避疫护佑的习俗。这种习俗在江南尤为兴盛,是江南水域密集、菖蒲丛生的缘故吗?
在我幼时,每逢端午,母亲也将蒲叶与艾草同插在门楣上,以祈佑家事安康。只是,我现在蜗居城市多年,一被所谓除旧革新的现代文明浸染,一是难得有与菖蒲亲近之机,而母亲也早已与我天各一方,端午门前悬蒲叶的习俗也渐渐淡忘失却。
某日,在一朋友家,见一硕大的陶瓷盆中养着一丛极似菖蒲的植物,只是没有水湄边的蒲叶挺拔野性,叶色是一种嫩青,不是墨绿。问朋友,竟真是菖蒲。原来,菖蒲在中国文化里还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花草四雅”,真是孤陋寡闻了。
于是得知,因菖蒲碧叶葱茏、根似白玉,凭水临石、清静高雅,又有驱蚊灭虫的功效,自古即有人莳养。据说,古人夜读,就常置一盆菖蒲于案,以免灯煙熏眼之苦。
友人告知我自古传下的莳养菖蒲的方法:“以砂栽之,至春剪洗,愈剪愈细,甚者根长二三分,叶长寸许。”怪不得我见了朋友家中的菖蒲不敢相认呢。
“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我还是喜欢那一片水域边自然生长的菖蒲,这种思念,正犹如元稹这一行诗句所表达的,思念犹如菖蒲,疯狂地滋长,满天飞舞,穿越漫漫时空。
席慕容在一首《菖蒲花》中写道:
我曾经多么希望能够遇见你 / 但是不可以 / 在那样荒凉寂静的沙洲上 // 当天色转暗风转冷 / 当我们所有的思维与动作都逐渐迟钝 / 那将是怎样的一种黄昏……
在这样一个秋天,这样一个菖蒲葳蕤的日子,想起菖蒲,想起以菖蒲作背景的那些身影,思念也如秋日蒲草一般葳蕤,只是菖蒲岁岁重生,而我们,却再不能与往事相拥。
茭白
入秋,茭白上市,是一道时鲜的蔬菜。在我们这儿,茭白被叫作“篙瓜”,私自臆想,不知是不是其形似竹笋又似瓜般能生食之故。
在我生活的这个长江以北地区,种植茭白的人家不多,大都是水边自生。像野藕野菱一般,成熟时节,自有不怕辛苦者去采收。童年的记忆中,母亲从田间劳作回来,有时就顺手在塘边沟畔折几支青叶包裹的修长茭白回家。篙瓜炒辣椒,是我幼时最常见的一种吃法。
当然,茭白绝非我记忆中简单的一种味道。
清代才子兼美食家袁枚在《随园食单》中就有对茭白入肴的一段记述:“茭白炒肉,炒鸡俱可。切整段,酱醋炙之尤佳。煨肉亦佳,须切片,以寸为度,初出瘦细者无味。”
清人薛宝辰在其《素食说略》中也有茭白入蔬的做法:
切拐刀块,以开水瀹过,加酱油、醋费,殊有水乡风味。切拐刀块,以高汤加盐,料酒煨之,亦清腴。切芡刀块,以油灼之,搭芡起锅,亦脆美。
现在想来,母亲的厨艺,当然比不得这些美食家,但也恐怕不是母亲不知道篙瓜还有其他的烧法,只是在那样一个清贫的日子,哪里有许多的食材调配,盘中简单的菜蔬,仅为佐饭下肚而已。
不过,现在日子富裕了,吃过的各类茭白佳肴恐怕比书上记载的还多,有时在家中还特意弄一个简单的篙瓜炒辣椒,享其清淡脆嫩,唇齿咀嚼间自有一种特别的回味。
其实,篙瓜在远古时期,也不称作茭白,而叫菰。
菰最早是被作为粮食作物种植的。《礼记》载:“食蜗醢而菰羹。”菰羹就是菰米饭,可见在周朝即已用菰米为粮。据记载,在唐代以前,茭白基本是被当作粮食作物栽培,它的种子被称作菰米或雕胡,是“六谷”(稌、黍、稷、粱、麦、菰)之一。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这是李白借宿安徽铜陵五松山下一农家,受到主人菰米款待后写下的诗作。陆游也有“稻饭似珠菰似玉,老农此味有谁知”“湘湖烟雨长莼丝,菰米新炊滑上匙”之句。
大约到了明代,玉米被从国外引进,广泛种植,替代了菰成为六谷之一。所以在我的家乡,现在还直接叫玉米为“六谷子”。
菰很早就被发现在被菌感染不抽穗后,膨大的茎部可为蔬。成书于秦汉间的《尔雅》记载:“邃蔬似土菌生菰草中。今江东啖之甜滑。”菰在被高产的玉米取代位置后,就彻底成为人们口中的佳肴。“岸遥人静,水多菰米。”苏轼《水龙吟》中的情景渐为鲜见。现在,偶在水边能看到结穗的菰,往往被认为是野茭白,其实,那不过是稀少的未被感染的菰。
茭白如其名字一般素白清新,可与各种原料配伍加工。此菜无论蒸、炒、炖、煮、煨都是鲜嫩糯香、柔滑适口;若是与肉、鸡、鸭等相配,烹出的菜肴则更是入味留香。茭白可生食凉拌,还可酱泡腌制。特别是凉拌、下汤,清新淡雅,很有水乡风味。
唐人张志和在《渔歌子》中吟道:“松江蟹舍主人欢。菰饭莼羹亦共餐。枫叶落,荻花干。醉宿渔舟不觉寒。”宋代也有一首咏茭诗:“翠叶森森剑有棱,柔条忪甚比轻冰,江湖若假秋风便,好与鲈莼伴季鹰。”诗中把茭白与莼菜、鲈鱼并提,可见其味美。
有这样的记载,西晋文豪张瀚,在某日秋风起时,想到故乡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于是辞别齐王,弃官南归,说:“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这段典故被后人浓缩为成语“莼鲈之思”,成了思念故乡的代名词。只是,莼菜、鲈鱼由此名闻天下,而未入语中的菰菜却鲜为人知。就像最早的粽子都是用菰叶所包,可现在人们知道的都是芦叶之类。
宋人周弼在一首《菰菜》诗中写道:“连日秋风思故乡,况复家田有茅屋。坠网重腮鲈已鲜,莼丝牵叶又流涎。急归收获苹溪畔,细拨芦花撑钓船。”又是秋风起的日子,水边伫立的茭白依然是千年守望的模样。只是,那留在每个人舌尖上的记忆,不知该有着怎样的回味?
鸡头果
路边,一农人摆了一只箩筐,边上围了几个人在瞧稀奇。伸首一望,见筐里是一个个暗绿色、拳头般大小、浑身长刺的东西。这不是“鸡头果”吗?
稀罕地买了几个。农人怕我不会摆弄,就用一把自制的镰刀似的刀具,非常麻利地帮我剥开了刺猬般的外壳,露出了里面白色的果囊和一粒粒淡黄的小圆果。
回到家里,按照农人的指示,将一粒粒的鸡头果倒入锅中,浸水煮了十几分钟。出了锅,用凉水洗净果实外面的黏滑,迫不及待地剥开小果子的外壳,吃里面白白的豌豆般大小的果肉。那小小的果肉叫鸡头米,糯米一般黏,且有嚼头。咀嚼间立即有一丝苦涩感觉,这苦涩的滋味在经过舌尖的回味后,弥生出一种特殊的甘香。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才上小学。入秋以后,学校的门口便有乡下妇女挎着柳篮卖鸡头果。篮中的鸡头果是用酒盅量着来卖的,好像是一分钱一酒盅。篮中的小果子大都是煮熟时间很长,甚至是隔夜的,果子的外壳不但变成了褐色,而且比较坚硬,需要用牙嗑开,才能吃到里面的鸡头米。硬壳被牙咬开时,满嘴的苦涩,但是为了享受到那一点小小的香糯的果肉,孩子们乐此不疲,争相摸出口袋底的几分硬币购买。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够吃到的零食实在是少得可怜,这样苦涩的鸡头果,对于我们这些馋嘴的孩子来说,真是美食。
鸡头果的叶子类似于莲叶,因此乡下便叫它鸡头莲。春天的时候,鸡头果的叶子就生出,只是它的叶子紧贴水面,上面有棱角般的鼓凸和裂皱。到了夏天,鸡头莲开出紫色的花,与莲花神似。只是花开时面向阳光结苞,苞上有青刺。因为花在苞顶,将萎时極似鸡冠,整个鸡头果乍看一如鸡头,由此得名。
唐朝有一首无名氏写的《鸡头》诗,对鸡头果作了形象的描写:
湖浪参差叠寒玉,水仙晓展钵盘绿。
淡黄根老栗皱圆,染青刺短金罂熟。
紫罗小囊光紧蹙,一掬真珠藏猬腹。
丛丛引觜傍莲洲,满川恐作天鸡哭。
幼时,也曾和小伙伴们到湖边去采鸡头果,但往往是无功而返。因为即便会水的小伙伴也很难接近鸡头莲,它茎叶上长满的尖刺让没有防护和特殊收割工具的人无法接近。
鸡头莲的茎一如藕茎,中间也有孔有丝,嫩茎剥皮即可生食,脆甜爽口。母亲有时会采一些茎秆回家,或凉拌,或炒丝,或切段佐肉红烧。
鸡头果不仅仅是孩子们喜爱的零食,也是盘中佳肴。鸡头果可与素菜烩炒,与荤腥红烧,也可煲粥下汤。其天然的野味和特别的口感,让人喜爱。据说在江南,鸡头果即与鱼、菱、藕、茭瓜、慈姑、莲蓬、水芹一起,被称作“水八鲜”,可见其美味。
一次在酒店里吃一盆甜汤,汤里有一粒粒的小白果,开始以为是寻常的小元宵,可一匙入口,感觉有异。服务生告知,这是芡实。芡实者,鸡头果的学名也。真是多年未见,别来无恙?
然而,现在的湖塘边已是难得见到大如澡盆般的鸡头莲。偶在超市里见到鸡头米,据说也是人工大批养殖。不再是一汪清水中自然的生长,怕也风味有异了。
在家中慢慢地剥食路边买来的鸡头果,眼前就浮现起儿时那一片浮满鸡头莲、开着紫莲花、结着鸡头果的水域。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