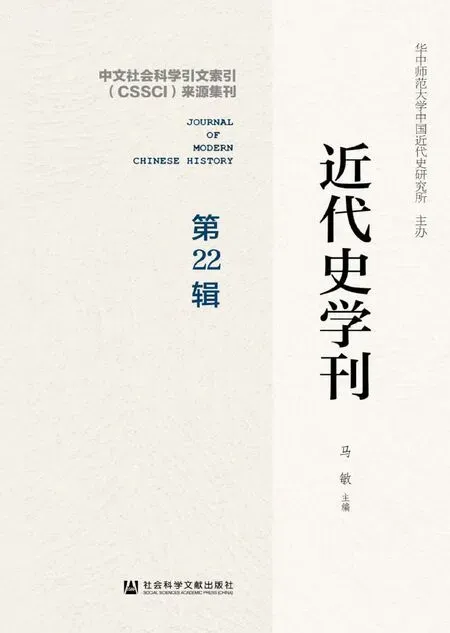胡适疑古思想再探讨
——兼论20世纪30年代的胡、顾关系
2020-04-13王学进
王学进
内容提要 疑古辨伪是胡适学术思想的重要特征。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中称,胡适曾于1929年对他说其不疑古而要信古。受顾颉刚的历史叙述影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胡适在1929年之后疑古思想发生转变,将此视为胡适与顾颉刚及古史辨派分道扬镳的肇端。二者疏离固为事实,然别有隐情,学术观点的差异并不表明胡适疑古思想发生了变化。从胡适在30年代前后的学术研究情况尤其是禅宗史研究来看,其疑古思想一以贯之,甚至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20世纪早期,疑古思潮催生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作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受胡适的影响颇大,也可以说是胡适引导他走上疑古辨伪之路。顾颉刚所言“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与胡适提倡的“历史的观念”如出一辙。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胡适,胡适的“滚雪球说”与顾颉刚的“层累说”所表达的意思几乎完全一致。两人在整理国故中对古书古史的怀疑和考辨可谓心有灵犀,相对于他人对胡适整理国故的误解和批评,顾颉刚对胡适的意图心领神会,与胡适步调高度一致。后因局势的发展,两人“南辕北辙”。顾颉刚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称:“到了一九二九年,我从广州中山大学脱离出来,那时胡适是上海中国公学的校长,我去看他,他对我说:‘现在我的思想变了,我不疑古,要信古了!’我听了这话,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突然改变的原因。”①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全集》(1),中华书局,2010,第160 页。受顾颉刚的历史叙述影响,大多数研究者认为胡适在1929年之后疑古思想发生了转变。刘起釪在《顾颉刚先生学述》中根据顾颉刚所说,认为胡适后来不再疑古,从此两人分道扬镳。①刘起釪:《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第262—263 页;路新生认为随着疑古运动的发展,胡适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胡适发表的对于考信辨伪的方法论检讨的系列论文,我们实际上也就可以将其视为‘疑古派’分化的标志”。②路新生:《诸子学研究与胡适的疑古辨伪学》,《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 期。此外,如赵润海、王学典、李政君等均认为胡适的疑古思想后来发生了转变。③参见赵润海《胡适与〈老子〉 的时代问题——一段学术史的考察》,刘青峰编《胡适与中国现代文化转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4,第397 页;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中华书局,2011,第149 页;陈勇:《试论钱穆与胡适的交谊及其学术论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3 期;李政君:《1930年前后顾颉刚学术理念的变与不变》,《史学月刊》2014年第6 期。然而通过对顾颉刚和胡适的日记和书信,特别是1930年前后两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胡适学术研究情况的考察,可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胡适的疑古思想是否发生转变仍有探讨之必要。
一日记折射下的胡顾关系
1929年2月,顾颉刚以请假之名辞别中山大学,转道香港,于3月1日抵达上海。在离开广州之前,顾颉刚给胡适写信告知:“大约是三星期内到沪,届时当和内子等赴谒。”④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全集》(39),第463 页。顾颉刚抵沪次日,即“到适之处,并晤梁实秋等”。⑤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全集》(45),第255—258 页。此为顾颉刚第一次拜访胡适。之后,顾颉刚为购书和探亲之事往来苏沪杭等地。3月20日,顾颉刚再次拜访胡适:“到伯详处,同到名达家,予与名达访适之先生。”⑥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全集》(45),第264 页。顾颉刚日记对自己的行程和探亲访友均有详细记载,从日记可以看出,他在3月拜访胡适只此两次,所记极简,没有涉及具体谈话内容。
顾颉刚来访期间,胡适刚从北平回到上海,察其日记,对顾颉刚拜访之事并无记录,只在3月3日提到:“顾颉刚得着一册抄本《二馀集》,是崔东壁的夫人成静兰的诗集,我与顾颉刚求之多年未见,今年由大名王守真先生抄来送他,他又转送给我。”①胡适:《胡适全集》(31),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327 页。此书很可能是顾颉刚3月2日拜访时所送。
3月23日,顾颉刚回到苏州老家,连日奔波,舟车劳顿,使他感到身心俱疲。“几乎日在轮毂之中,精神身体两皆劳顿矣。此数日中始得在家稍息。”②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华书局,2011,第193 页。25日,顾颉刚致信胡适,邀游苏州。28日,顾颉刚再次致信胡适,询问能否来苏,由于大战在即,“时局紧张,因封船故到甪直不方便矣”。③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全集》(39),第464 页。4月24日,顾颉刚在信中称:“先生上月来信,说十天内一定到苏州,但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十天了,还不见来,而我也要到北平了,我们只得在暑中再见了。”④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全集》(39),第464 页。可知胡适对顾颉刚的邀请应有回信,可惜在胡适往来书信中未见此信,日记亦无记载。
6月底,顾颉刚回苏州为父亲筹备六十大寿,适逢胡适在苏州参加振华女校的毕业典礼,两人再次晤面,并同游狮子林等处。据顾颉刚7月3日记:“适之先生来电话。适之先生应振华女校毕业式之招,偕师母两儿到苏州,今日偕丁庶为夫妇游天平山,晚乃来一电话。”⑤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全集》(45),第299 页。4日,顾颉刚冒雨“到苏州饭店,访适之先生及其眷属”。即日,“适之师母偕祖望来。适之先生偕丁庶为夫妇来。同到狮子林及耕荫义庄游玩”。⑥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全集》(45),第299—300 页。7月12日为顾父六十大寿,胡适此时登门应有顺便贺寿之意。因工作关系,加之长子在苏州读书,胡适经常往来沪苏两地,两人晤面机会较多。8月16日,胡适应苏州青年会之邀,再次来到苏州,顾颉刚“到苏州饭店访适之先生”。⑦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全集》(45),第313 页。8月31日,顾颉刚离苏北上,途经上海,在上海逗留一周,于9月8日赴京。其中,9月7日,顾颉刚“到适之先生处,并晤林语堂”。⑧顾颉刚:《顾颉刚日记》,《顾颉刚全集》(45),第321 页。胡适此日日记只记录了带祖望到沪江大学访问詹森教授,请其检测祖望的英文学习情况,并无顾颉刚到访记录。⑨胡适:《胡适全集》(31),第453—454 页。
从顾颉刚的行程来看,从3月到9月,他先后共五次拜访胡适,分别为3月2日、3月20日、7月4日、8月16日和9月7日,其中三次在上海,两次在苏州。此段时间,顾颉刚的日记从未间断,对自己的行程和日常事务,从会客访友到家务琐碎,悉有记载。顾颉刚生性敏感,谨小慎微,不善处理人际关系,无论家庭或亲朋,稍有矛盾和纠纷都会令他紧张不安,这也是其日记重点着墨之处。顾颉刚日记与胡适日记不同,完全是私人性的,故其情感思绪,甚至家庭矛盾和个人隐私,均可以从中察出。如果胡适真对他说过其不疑古而要信古,把他吓出一身冷汗的话,此等“大事”,理应在其日记中出现。另外,此时胡适因“诋毁”国民党成为打压对象,日记极简,且多为剪报。胡适对7月3日在苏州游览天平山的印象颇深,在日记中记录了天平山的历史风光,而对顾颉刚拜访之事没做任何记录。①胡适:《胡适全集》(31),第411—414 页。胡适此日日记时间为“十八,七,三”,疑为7月4日之误,因前一篇是7月3日,后一篇为7月5日。从日记来看,此时两人关系仍十分融洽,并非像顾颉刚晚年回忆所说开始产生裂痕。由于历史原因,顾颉刚晚年所述很可能是为了撇清与胡适的关系。
对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两人1929年之后的关系。1929年9月,顾颉刚的学生何定生编了《关于胡适之与顾颉刚》一书,颇有抑胡扬顾之意,“一时引得北平学界议论纷纷”。②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第109 页。这使顾颉刚甚感不安,生怕影响了他与胡适之间的关系。他一面斥责何定生,将其逐出师门,一面通知朴社停止发行该书,并写信向胡适说明情况。同时邀请胡适到北平去他家小住,试图消除胡适的疑虑。③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全集》(39),第466—467 页。可见,顾颉刚在处理与胡适的关系时非常谨慎。
1930年1月,顾颉刚致信胡适称,“三个月前接来书,敬悉。那时盼望先生来北平,故未复。哪知到现在还未来”,并向胡适报告在燕大的情况。④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全集》(39),第467 页。4月,顾颉刚再次致信胡适,解释前几次没有回信的原因:“所以然之故,一因讨论《易传》事,胸中颇有些意见,要写出至少须费半天功夫,而半天功夫着实不易找到。二因《清华学报》嘱我做一篇文字,那时拟定的题目是《五德始终说的历史和政治》,当时想想,有一两万字也尽够了,一个寒假也写得完了。但一落笔之后,三万四万还写不完,现在写到了六万字还不完,怕要十万字了。这两个月来的时间差不多全耗费在这研究上,很有可喜的发见。”⑤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全集》(39),第468 页。6月初,胡适到北平,“先后在北大、北师大等处讲演”。⑥耿云志:《胡适年谱》,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第151 页。由于燕京大学地处郊外,离城区较远,顾颉刚得知后,写信给胡适:“昨日钱玄同先生来,始知先生已到平四五日了。我很想立刻进城奉访,可是今日有课,明日必送讲义稿若干页,这两天无法进城。想拟星期六上午坐八点汽车到先生处,不知道那天先生有没有空?请告我。”①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全集》(39),第469 页。相信胡适看到此信应能理解,对顾颉刚的忙碌感到欣慰,曾经辛勤诱掖的学生今已逐渐成熟,独当一面。至于有人认为顾颉刚的成名掩盖了胡适的光芒,而引起胡适不快,致使两人产生罅隙,恐属臆断。
由于胡适声望正隆,俨然青年之导师,顾颉刚多次应学生之请,致信胡适请求接见指导。1930年7月3日,顾颉刚在信中称:“北大同学余譲之兄,今年在史学系毕业,兹就返湘之便,晋谒先生,特为介绍,请赐接见为幸。”并报告“《东壁遗书》序已着手,在暑假内必可寄沪,乞告汪孟邹先生是感”。感谢胡适所赠朝鲜本《五伦行实》,“承嘱勿过怀疑,自当书之座右”。同时,请求胡适为《燕京学报》赐稿,“只希望从《哲学史》稿中抽出一章就好了”。②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全集》(39),第470—471 页。
1930年11月底,胡适重返北京大学,任文学院院长。12月7日,北京大学研究所请顾颉刚为胡适四十岁生日作一篇寿文,顾颉刚因病无法应命。为此,顾颉刚特意写信向胡适致歉:“前日研究所同人嘱我作先生寿序,这是义不容辞的事,只为疾病所困,无法应命,歉仄之怀,如何可言。”并称今后将加强“锻炼身体”,“只要此后起居稍有节制,则先生五十寿辰时之论文及寿序,自当由我包办也。先生布置新房,当需灯盏,兹谨送奉纱灯一堂,以应需要,乞哂收为感”。③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全集》(39),第471 页。从上可知,两人关系在1930年前后仍十分融洽。
二 学术观点的差异与罅隙的产生
顾颉刚称其与胡适之间产生裂痕,是因为在“观象制器”和“《老子》成书年代”问题上观点相左,使胡适“大为生气”。然细察之下,此说很有疑问。1929年秋,顾颉刚作《周易卦卜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第6期),认为《易经》与《易传》中的历史观念处于完全相反的地位,“《易经》中是片断的故事,是近时代的几件故事;而《易传》中的故事都是有系统的,从邃古说起的,和这个秦汉以来所承认的这几个人在历史中所占有的地位完全一致”。所以,“我们要把时代意识不同,古史观念不同的两部书——《周易》和《易传》分开”。①顾颉刚:《周易卦卜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1929年第6 期,第1006 页。此后,他在《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中再次讨论此问题,认为《易传》“原来只是一部占卜的书,没有圣人的大道理在内”,其作者绝不是孔子,也绝非出于一人之手。《系辞传》中所说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等圣人“观象制器”,即一切的物质文明都发源于《易卦》是错误的,“制器”时看的“象”乃是自然界的“象”,而不是“卦爻的象”,是后人把“制器”归到了圣人伏羲、神农等头上。因此,他得出:“那发挥自然主义的《易传》的著作时代,最早不能过战国之末,最迟也不能过西汉之末”;“《系辞传》中这一章是京房或是京房的后学们所作的,它的时代不能早于汉元帝”。②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顾颉刚全集》(3),第233—251 页。
1930年2月1日,胡适读了顾文之后,作了一封长信,与顾颉刚讨论“观象制器”问题。胡适在信中称:“顷读你的《周易卦卜爻辞中的故事》,高兴极了。这一篇是极有价值之作。不但是那几个故事极有趣,你考订《系辞传》的著作年代也很有意思,引起我的兴趣。”他认为《系辞》出现甚早,“至少在楚汉之间人已知有此书”,“观象制器”是一种文化起源的学说,“所谓观象只是象而已,并不专指卦象,卦象只是象之一种符号而已”。胡适认为顾颉刚的看法不免苛责,“卦象只是物象的符号,见物而起意象,触类而长之,‘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此学说侧重人的心思智慧,虽有偏处,然大体未可抹杀。你的驳论太不依据历史上器物发明的程序,乃责数千年前人见了‘火上水下’的卦象何以不发明汽船,似非史学家应取的态度”。他批评顾颉刚是“受了崔述的暗示,迁怒及于《系辞》,也不是公平的判断。至于你的讲义中说制器尚象之说作于京房一流人,其说更无根据。京房死于西历前三十七年,刘歆死于纪元后二十二年,时代相去太近,况且西汉易学无论是那一家,都是术数小道,已无复有‘制器尚象’一类的重要学说”。最后,胡适强调:“以上所说,于尊作本文毫不相犯,我所指摘皆是后半的余论。至于本文的价值,此函开始已说过。我不愿此文本论因余论的小疵而掩大瑜,故草此长函讨论。久不作长书,新年中稍有余暇,遂写了几千字,千万请指教。”①胡适:《致顾颉刚》,《胡适全集》(24),第31—35 页。
从信中可以看出胡适对顾文的肯定和赞赏,但并非完全赞同他的观点。胡适此日日记载:“晚间读顾颉刚的新作《周易卦爻中的故事》(《燕京学报》6),其中有论《系辞传》中‘制器取象’的一段,引起我的注意,作长函和他讨论,约二千多字。”②胡适:《胡适全集》(32),第598 页。不难看出,胡适乃本着研究的兴趣和学术批评的态度,与顾颉刚商榷,表达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顾颉刚亦坦然接受批评。此后,顾颉刚将讲义连同与胡适、钱玄同的讨论书信刊于《燕大月刊》(1930年第6 卷第3 期),并收入《古史辨》(第3 册)中。据顾颉刚记述:“去年秋间作《周易卦卜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刊入《燕京学报》第六期。作完了之后又发生了些新见解,因就编讲义的方便,编入《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里去。适之玄同两先生见之,皆有函讨论。今以《月刊》索稿,即以讲义原文及两先生函件发表。”③顾颉刚:《论易系卜辞传中观象制器的故事》,《燕大月刊》1930年第6 卷第3 期,第1 页。此即顾后来所称:“这篇文章在《燕大月刊》上发表后,我收到了钱玄同和胡适的来信,两个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钱玄同认为‘精确不刊’,胡适则反对,说观象制器是易学里的重要学说,不该推翻。前面说过,他从一九二九年起就不疑古了,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具体例证,也是我和他在学术史上发生分歧的开始。”④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全集》(1),第169 页。事实上,胡适与之讨论的是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周易卦卜爻辞中的故事》,而非《燕大月刊》之文。
另一问题是关于老子及《老子》成书年代,顾颉刚的观点亦与胡适相左。此前,在老子和《老子》成书年代问题上,胡适与梁启超、冯友兰等有过讨论。胡适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前,“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五七〇年左右”;而孔子约“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历纪元前551)”。⑤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胡适全集》(5),第233、252 页。梁启超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后,《老子》很可能是战国末期作品。⑥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中华书局,1996,第57—58 页。1930年12月,钱穆作《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认为孔子在老子之前。1931年3月22日,顾颉刚偕钱穆拜访胡适,与胡适讨论这一问题。胡适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前,《老子》早出;钱穆认为老子在孔子之后,《老子》晚出。①胡适:《胡适全集》(32),第92—93 页。顾颉刚与钱穆观点一致,认为孔子在老子之前。1932年4月,顾颉刚作《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刊于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933年1月,胡适作《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批评梁启超、钱穆和顾颉刚等人的观点,认为他们提出的证据难以证明《老子》晚出。尤其是顾颉刚的文章,他认为考证还不够严谨,存在“断章取义”、“强为牵合”等问题,以构造“时代意识”来证明《老子》晚出的方法是很危险的。胡适称自己“并不反对这种怀疑的态度;我只盼望怀疑的人能举出充分的证据来,使我们心悦诚服的把老子移后,或把《老子》书移后”。他强调自己的辩驳是充当“魔的辩护士”,“我攻击他们的方法,是希望他们的方法更精密;我批评他们的证据,是希望他们提出更有力的证据来”。②胡适:《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胡适全集》(4),第114—139 页。
学术批评者,指其正,辨其谬,商榷异同。民国时期学术批评风气甚浓,这正是当时思想文化勃兴的原因之一。如胡适与蔡元培私交甚笃,但并不认同他的《红楼梦》研究。“当年蔡先生的《红楼梦索隐》,我曾说了许多批评的话。那时蔡先生当校长,我当教授,但他并不生气,他有这种雅量。”③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3509 页。两人在探讨和争论中将《红楼梦》研究推向纵深。陈垣称:“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惜胡、陈、伦诸先生均离平,吾文遂无可请教之人矣。”④陈垣:《致陈乐素》,陈智超编《陈垣往来书信集》,三联书店,2010,第1109 页。此“诤友”显然是指胡适,两人作文常请对方批评“指摘”。胡适有“好争”之名,在学术上有股较真劲,凡事要争个水落石出。多年后,他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修订后记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直到今天,还没有人“提出什么可以叫我心服的证据”,“把老子这个人和《老子》这部书挪移到战国后期去”。⑤胡适:《 〈中国古代哲学史〉 台北版自记》,《胡适全集》(5),第540 页。后来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和《黄帝书》则进一步证实了胡适的观点。
胡适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其所论乃正常的学术批评,并非如顾颉刚所称“不加考虑,一口拒绝”,把他“痛驳一番”,“从此以后,他就很明显地对我不满起来”。⑥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全集》(1),第170 页。此系顾颉刚后来的说辞,不足为凭。另据钱穆晚年回忆,胡适之文并非针对顾颉刚,“适之后为文一篇,专论老子年代先后,举芝生颉刚与余三人。于芝生颉刚则详,于余则略。因芝生颉刚皆主老子在庄子前,余独主老子书出庄子后。芝生颉刚说既不成立,则余说自可无辩。然余所举证据则与芝生颉刚复相异,似亦不当存而不论耳。但余与芝生颉刚相晤,则从未在此上争辩过。梁任公曾首驳适之老子在孔子前之主张。在当时似老子出孔子后已成定论。适之坚持己说,岂犹于任公意有未释耶”。①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10,第152 页。
但两人的关系在1931年之后确实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31年5—8月,顾颉刚多次致信胡适,均未得到回复。9月7日,顾颉刚再次致信胡适询问是否有“开罪之处”,因“连上数函,迄未得复,甚为惶恐。未知是我有开罪先生呢,还是有人为我飞短流长,致使先生起疑呢?如有所开罪先生,请直加斥责,勿放在肚里”。②顾颉刚:《致胡适》,《顾颉刚全集》(45),第560 页。从两人书信中未见胡适对此信做出回应,顾颉刚所说的“裂痕”很可能是指此事。但从胡适致钱玄同信来看,两人之间似乎又不存芥蒂。1932年5月10日,胡适在致钱玄同的信中称:“颉刚的信使我很高兴,姚立方的遗著的发现,是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不单是因为姚氏的主张有自身的价值,并且这事可以表示近年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明显的倾向。这倾向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在思想方面,李觏、王安石、颜元、崔述、姚际恒等人的抬头,与文学方面的曹雪芹、吴敬梓的时髦是有同一意义的。”并询问“颉刚何时回来?杭州住址何处?”请求钱玄同告知。③胡适:《致钱玄同》,《胡适全集》(24),第118 页。1933年4月26日,胡适到燕京大学演讲,顾颉刚陪同,并为之主持。④顾颉刚:《顾颉刚全集》(46),第38 页。但此后两人关系确有“遇冷”现象。12月17日是胡适的生日,只要条件允许,他都会接受拜访并宴客,宾客中自然少不了顾颉刚。1933年12月17日,胡适日记写道:“朋友来贺生日者,上下午都有人;我每年都备酒饭,但不发帖请客;朋友上午来的,则住留吃面;下午来的,则留住吃晚饭。今天来的约有五十人。”⑤胡适:《胡适全集》(32),第247 页。而此日顾颉刚在家中“校《古史辨》”,⑥顾颉刚:《顾颉刚全集》(46),第123 页。没有参加胡适生日宴会,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但是,12月30日,燕京大学国文系同学会举行年终聚餐,托顾颉刚邀请胡适参加,胡适应约。⑦胡适:《胡适全集》(32),第247 页。
从两人日记和书信来看,很可能是胡适对顾颉刚疏远,但原因不一定是学术观点的差异。胡适提倡思想言论自由,主张容忍异见,从当年与梅光迪、任鸿隽等争论到“剑拔弩张”时关系尚未破裂,如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对顾颉刚和钱穆“怀恨在心”,则厚诬了胡适的度量。顾颉刚晚年回忆显然夸大了他与胡适之间的分歧,刻意制造了两人的“矛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像因为学术观点的不同,两人早在1929年之后便已分道扬镳。究其个中原委,故是时代使然,但我们不应将此视为两人产生裂痕的原因,更不能以此认为胡适的疑古思想发生了转变。有人以胡适在老子问题上的态度作为他信古的证据,事实上胡适的疑古并非推翻全部历史,而是疑其不实之处。同样的例子还体现在《四十二章经》和《牟子理惑论》真伪之争上,胡适与梁启超等人观点相反,认为两经系真。对此,有学者认为:“往往被人们认为倾向于‘疑古’的胡适,在早期佛教史的研究领域中,却是相当‘信古’。”①葛兆光:《“聊为友谊的比赛”——从陈垣与胡适的争论说到早期中国佛教史研究的现代典范》,《历史研究》2013年第1 期。其实,胡适在早期佛教史研究中并不“信古”,只是不全疑古而已。
胡适对顾颉刚的疏远另有隐情,虽然具体原因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或许有助于了解两人的疏离。顾颉刚在成名前追随胡适,无论是学术还是生活上,胡适均给予极大帮助。后来,随着名气的扩大和经济的独立,尤其是因《古史辨》声名鹊起后,顾颉刚逐渐摆脱对胡适的依赖,开始出现骄傲情绪。胡适曾劝他不要有骄傲之心,但他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顾颉刚自我意识较强,其“到一处闹一处”的性格更是声名在外,当洪业与他谈起此事时,顾颉刚认为那是别人诋毁自己。②顾颉刚:《顾颉刚全集》(45),第505—506 页。顾颉刚无论在北京大学,还是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以及后来到燕京大学,不仅对傅斯年,甚至对性情温和的陈垣也颇有微词。成名后的顾颉刚确实表现出骄傲之情,这从他的日记中可以明显察出。虽然顾颉刚知道别人对自己“飞短流长”,但并没有认真反思,每当感到胡适对他表现冷淡或疏远时,便认为有人在背后捣鬼,蓄意破坏。
1937年,胡适赴美出任驻美大使,两人联系一度中断。1946年7月,胡适使美归来,在教育部、中央研究院及史学会举行的欢迎会上,顾颉刚逢场必到,并欲编纂《胡适文存》续集,筹备胡适六十大寿纪念文集。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4月6日,顾颉刚“到上海银行,送适之先生西行”。他在日记中不无伤感地称:“适之先生来沪两月,对我曾无一亲切之语,知见外矣。北大同学在彼后面破坏我者必多,宜有此结果也。此次赴美,莫卜归期,不知此后尚能相见,使彼改变其印象否。”①顾颉刚:《顾颉刚全集》(48),第440 页。顾颉刚的忧虑不幸言中,从此两人再也没有相见。多年后,当胡适在美国看到顾颉刚的批判文章时,非但没有指责,反表现出理解和同情。②1952年1月3日,胡适在香港《大公报》上看到顾颉刚的《从我自己看胡适》,将其作为剪报收藏在日记中,并在“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我本是跟着他走的,想不到结果他竟变成反对我”下面加上着重号。胡适:《胡适全集》(34),第158 页。
顾颉刚晚年因环境所迫,不得不与胡适划清界限。从《 〈古史辨〉 第一册自序》(1926)到《我的治学计划》(1950),再到《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1979),可看出其对胡适由尊崇到省略的过程。顾颉刚称引导他走上疑古道路的是姚际恒、崔述和郑樵,而矢口不提胡适,并言当代学者中他最佩服的、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是王国维,而非胡适。③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全集》(1),第157—162 页。虽然顾颉刚多次向王国维表达仰慕之情,请求“许附于弟子之列”,④顾颉刚:《致王国维》,马奔腾辑注《王国维未刊来往书信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第55—56 页。但并未得到回应。王国维并不认同当时的疑古思潮,顾颉刚“心仪于王国维”,其实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研究方法,顾颉刚早期的治学方法和路径都与王国维相去甚远,而近于胡适。特别是在胡适大批判中,顾颉刚精神高度紧张,常“赖药而眠”,⑤顾颉刚:《顾颉刚全集》(50),第662—666 页。足见其内心的痛苦和恐慌。《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此影响。
三 从禅宗史研究看胡适疑古思想的一贯性
1930年前后,胡适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佛教禅宗史方面,如《菩提达摩考》(1927)、《论禅宗史的纲领》(1928)、《 〈坛经〉 考之一》(1930)、《菏泽大师神会传》(1930)、《神会和尚遗集》(1931)、《禅宗在中国之发展》(1932)、《 〈四十二章经〉 考》(1933)、《 〈坛经〉 考之二》(1934)、《楞伽宗考》(1935)等。胡适的疑古思想突出表现在对佛教疑伪经以及由伪经建构起来的伪史的质疑和考辨,也即顾颉刚所说的“辨伪书”和“辨伪事”。他从源头上考证“西天二十八祖”的真伪、菩提达摩神话传说故事的来源和发展演变过程、神秀与慧能的法统地位,以及神会的历史作用等,认为从《楞伽师资记》到《付法藏因缘传》,以及《坛经》、《宝林传》、《曹溪大师别传》、《五灯会元》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伪造和作假,净觉开了恶例,神会大造,后人续之,从而“层累地”造成了佛教禅宗史。
1924年,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之初,即因对传统灯史的怀疑而停止撰写禅宗史,认为现存的禅宗史料大多数经过了后来和尚的窜改和伪造,故不可信。若要作一部可靠的禅宗信史,必须先搜求佛教早期史料,如唐朝的原料,而非五代以后被改造过的材料。1926年,胡适利用庚款会议之机,赴巴黎和伦敦查阅敦煌文献,搜集到了大量佛教早期史料,基本证实了此前对禅宗史作伪的怀疑,从而提出了“捉妖”、“打鬼”说。①胡适在《整理国故与打鬼——致浩徐先生信》中把整理国故解释成“捉妖”、“打鬼”。胡适关于整理国故前后不同的说法,曾引起研究者的颇多关注和讨论。从此信的内容、时间以及胡适的前后活动上看,此时他对整理国故的态度突然转变,把整理国故说成“打鬼”,很可能是因为敦煌佛教早期史料的发现,基本上印证了此前他对佛教禅宗史作伪的怀疑。1927年,胡适根据在巴黎和伦敦所搜集到的敦煌佛教早期史料,对比国内所存的佛教史料,特别是唐代以后的佛教史料,梳理和考证菩提达摩如何从简单的历史记载演变成复杂的传说故事,逐渐被神化。他以菩提达摩会见梁武帝为例说明传说故事由简单到复杂、由模糊到清晰的演变过程,指出“传说如同滚雪球,越滚越大,其实禁不住史学方法的日光,一照便销溶净尽了”。②胡适:《菩提达摩考——中国中古哲学史的一章》,《胡适全集》(3),第326—329 页。通过胡适对菩提达摩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到菩提达摩被神化的过程:由起自荒裔的波斯国胡人到南天竺婆罗门种,再到南天竺国王第三子,菩提达摩的身份越来越尊贵;从“初达宋境南越”到会见梁武帝,再到与梁武帝见面的具体时间和玄妙的对话内容,菩提达摩的教义越来越深奥;从折苇渡江到六次遇毒,再到只履西归,菩提达摩的形象越来越神化。他认为菩提达摩的神话传说故事“起于八世纪晚期以后,越到后来,越说越详细了,枝叶情节越多了,这可见这个神话是逐渐添造完成的”。③胡适:《楞伽宗考》,《胡适全集》(4),第215 页。胡适对史料和证据的选择“以古为尚”,取敦煌佛教早期史料论证后期禅宗史的作伪,认为菩提达摩传说故事是后人伪造的。
同样的事情还体现在慧可传说故事上。道宣《续高僧传》中对慧可的记载较为简略,仅说慧可在邺传教时,“深遭邺下禅师道恒的嫉妒”,而《传灯录》、《慧可传》中却增添了许多故事情节。胡适认为:“《传灯录》全抄袭《宝林传》(卷八)伪书,《宝林传》改窜《续僧传》的道恒为辩和,改邺下为莞城县,又加上‘匡救寺三门下’,‘邑宰翟仲侃’,‘百七岁’,‘开皇十三年三月十六日’等等详细节目,看上去‘像煞有介事’,其实全是闭眼捏造。七世纪中叶的道宣明说慧可不曾被害死,明说‘可乃从容顺俗,时惠清猷,乍托吟谣’,然而几百年后的《宝林传》却硬说他被害死了! 七世纪中叶的道宣不能详举慧可的年岁,而几百年后的《宝林传》却能详说他死的年月日和死时的岁数,这真是崔述说的‘世愈后而事愈详’了!”①胡适:《楞伽宗考》,《胡适全集》(4),第220—223 页。此即顾颉刚提出的“层累说”,所谓世愈后而事愈详,传说中的人物愈放愈大。
以此类推,胡适对禅宗的传法世系、慧能的法统,以及《坛经》的作者等均提出了质疑和考证。他认为神会是一个善于编造谎言的专家,为了争法统编造了许多故事,事实上,弘忍并没有将“法衣”传给慧能。“他是一位善于辞令的传道家,又会编造生动的故事。许多关于达摩传道的故事,如与梁武帝见面和二祖断臂求道等,起初皆系由他编造,而后加以润色,才混入中国禅宗史的整个传统历史之中。”②胡适:《禅宗在中国:它的历史和方法》,《胡适全集》(9),第311 页。胡适在与汤用彤讨论“禅宗史纲领”的信中指出:“九世纪禅宗所认之二十八祖,与宋僧契嵩以后所认之二十八祖又多有不相同,尤其是师子以下的四人。其作伪之迹显然,其中有许多笑柄。”③胡适:《论禅宗史的纲领》,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第35—38 页。从他所拟的十三条禅宗史纲领中,可以看出其欲撰写的“禅宗史”,实际就是一部疑经辨伪史。他认为不只是佛教经典存在伪造和作假,道教亦是如此,《道藏》几乎完全是“贼赃”。陶弘景本人就是一个“大骗子”,《真诰》便存在有意作伪,“四十二章之中,有二十章整个儿被偷到《真诰》里来了”。④胡适:《陶弘景的〈真诰〉 考》,《胡适全集》(4),第176—177 页。
禅宗史研究是胡适整理国故的一部分,受新文化运动和整理国故的影响,他把佛教禅宗列为整理国故的对象,认为佛教的迷信思想和出世观念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障碍,旨在“打破枷锁,吐弃国渣”,实现“再造文明”的根本目的。而整理国故又与民国疑古思潮相关联,整理国故本身就含有很深的疑古辨伪成分。根据胡适的解释,整理国故是“以汉还汉”、“以宋还宋”,①胡适:《 〈国学季刊〉 发刊宣言》,《胡适全集》(2),第8 页。“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②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全集》(1),第699 页。那么,他对禅宗史的整理也是要还其“真面目”和“真价值”。在剔除了神化和传说,还其本来面目之后,他得出禅宗的传法世系是后人伪造的、菩提达摩传说故事是后人编造的、慧能的法统是篡夺的、《坛经》是神会的伪作、佛教经典是故弄玄虚的骗人的“文字障”。撕掉了神秘的面纱,一切神奇和玄妙归于平常。诚如梁启超所论:“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生变化,宜何如者?”③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第19 页。如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他把整理国故说成“捉妖”、“打鬼”的原因,声称整理国故可以“化黑暗为光明,化神奇为臭腐,化玄妙为平常,化神圣为凡庸:这才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④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胡适全集》(3),第146—147 页。
1937年,胡适受命出任驻美大使,在禅宗史研究的黄金时期,战争打断了原本的研究进程。⑤胡适:《致顾维钧》,《胡适全集》(24),第380 页。胡适原想“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⑥胡适:《致傅斯年》,《胡适全集》(24),第381 页。但事实并非如他所料,胡适此去禅宗史研究中断了十五年之久。1952年,胡适重新回到禅宗史研究上,其对禅宗史的怀疑和批判依然没有改变。他在《口述自传》中称:“我个人虽然对了解禅宗,也曾做过若干贡献,但对我一直所坚持的立场却不稍动摇:那就是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得很重了,但是这却是我的老实话。”他把自己的禅宗史研究称作“耙粪工作”,声称要“把这种中国文化里的垃圾耙出来”,“大体上说来,我对我所持的禅宗佛教严厉批评的态度——甚至有些或多或少的横蛮理论,认为禅宗文献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欺人的伪作——这一点,我是义无反顾的。在很多(公开讨论)的场合里我都迫不得已,非挺身而出,来充当个反面角色,做个破坏的批判家不可!”①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18),第386、422—423 页。足见其态度之坚决。
学术实践是学术思想的反映,两者具有一致性。以往研究多根据顾颉刚的历史叙述,从胡适方面出发寻找其疑古思想转变的蛛丝马迹,而忽视了顾颉刚叙述的历史语境。考察胡适疑古思想转变与否不仅要根据他人记述,更应根据胡适学术研究的具体实践。根据20世纪30年代前后胡适学术研究情况,特别是禅宗史研究来看,其疑古思想并没有发生改变。疑古不是对历史的全部否定,胡适在一些问题上“信古”,不等于整体不疑古。怀疑和批判是胡适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伴随他学术研究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