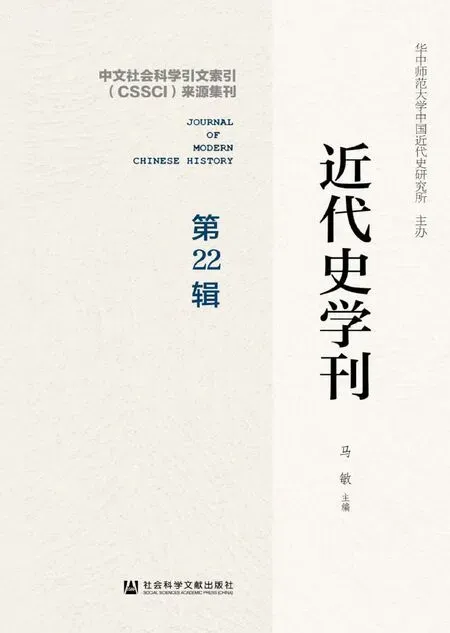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本色化运动*
——以中华基督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2020-04-13谌畅
谌 畅
内容提要 基督教传入中国后,为了更好地达成广泛传教的目的,基督教会试图采用各种方式减少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抵牾,努力融入本土社会。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基督教会以自立为目标的本色化进程迭经不同阶段,孕育出不一的成果,并产生了中华基督教会等较具代表性的自立教会。总体而论,近代中国基督教会的本色化运动存在较大的路径困难和局限性,但凭借自身努力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中国社会交融的目的。
作为舶来品的基督教会①在汉语语境里,基督教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是对信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的统称,狭义则特指基督新教。本文取其狭义。是中国近代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历程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取得社会民众的认可,中国基督教会试图通过本色化运动,努力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以达成自立目标,植根于中国社会。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的发展变迁是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有不少学人做了探析。②海内外学人围绕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参见Wallace C.Merwin,Adventure in Unity: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Grand Rapids,Wm.B,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1974;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台北,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3;章开沅:《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吴义雄:《民族主义运动与华南基督教会的本色化》,《学术研究》2004年第12 期;邢福增:《本色化与民国基督教教会史研究》,《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然而,学界对于教会本色化的内涵并未取得一致。①对于基督教会本色化,民国时期教会内部即对其定义有过讨论。其中,得到大部分教会人士认同的观点是:“一、本色教会须由中国人组织及维持;二、本色教会的形式须中国化;三、本色教会须含有中国文化的因素;四、本色教会须适合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参见《基督教在中国的演进及其趋势》,《中华归主》第68 期,1927年。其后,对教会本色化的讨论范围扩大到学术界。其中,吴义雄在综合缕析学界不同意见的基础上,指出教会本色化是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具体环境下,教会脱离外国差会和传教士的供养与控制而走向独立的进程。此种定义大体能够反映学界一般意见。参见吴义雄《华南循道会的本色化之路——以二十世纪前期为中心的考察》,《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3 期。邢福增则认为“教会本色化”并不局限于文化层面,而是涵盖了社会、政治及经济等方方面面。参见邢福增《本色化与民国基督教教会史研究》,《冲突与融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论集》。大陆学界关于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参见刘家峰编著《离异与融合:中国基督徒与本色教会的兴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同时,由于在华基督教会宗派林立,支脉众多,观测点难以选择。基于此,笔者拟在宏观把握中国近代基督教会发展的前提下,选取中华基督教会这一最大的华人本土合一教会作为研究对象,②关于中华基督教会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成果。代表性著作参见杨天宏《救赎与自救: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研究》,三联书店,2010;陈智衡:《合一非一律——中华基督教会历史》,香港,建道神学院,2013;Marina Xiaojing Wang,“Cheng Jingyi and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Ching Feng,n.s.,13(2014)。笔者则围绕民国时期中华基督教会的发展趋势和运营实态做了较为细致系统的研究。参见谌畅《自营与外援之间: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会自立路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 期;《取舍之间:中华基督教会财政运作中的西方教会影响》,《基督宗教研究》第23 辑,2018年9月;《劫后求生:抗战之后中华基督教会的复员运动》,《暨南史学》第17 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8。试图根据相关一手文献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国基督教会如何将基督教的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调和,实现自立的本色化。
一 基督教会的早期本色化运动
1807年马礼逊东来,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并伴随着欧美列强的枪炮声,借由条约体系的形成而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颇具影响的一支力量。为了实现将基督教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目标,西方教会和传教士采用各种方法,努力争取中国公众好感,试图得到中国社会的理解与支持。其中,兴办慈善事业、推动地方卫生和教育事业发展成为其选择施行的重要手段。
然而,基督教毕竟是西方列强凭借多次中外战争的胜利逼迫中国政府承认和接受的,其合法地位也是借由不平等条约的不断累积方得以确立。此种情形下,基督教先天上即作为入侵者的附庸站在与中国社会对立的一面,招致普通民众反感,在诸多方面遭到抵制。
面对基督教东来夹杂的枪炮和文化上的侵入,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初均持抵制态度。中国政府的调处不力和士绅阶层的诱导,加剧了民教之间的紧张形势,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教案,而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则直接形成了中国社会排外、反对基督教的一个高潮。
不惟如此,较之中国文化传统,基督教毕竟是一种异质文化和外来事物,对中国社会而言显然属于他者。因此,基督教想要融入有着深厚历史传统和拥有自身逻辑体系的中国社会显非易事,有时甚至因传教方法失当招致大众抵牾和排拒。同时,在中国传统社会呈崩溃之势时,基督教更在很多方面成为西方对中国社会传统最直接的挑战。譬如,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目的,而非单纯获取经济利益,而这对中国儒家传统、社会秩序、民众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①〔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第465 页。总体而言,基督教虽然为了获得中国民众的普遍认可,一直致力于提升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但该教早期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想的结果。
在此种情况下,基督教会内部和传教士进行反思和调整,试图通过改变传教方法融入中国社会。简言之,在基督教本身兼具“普世性”和“本土性”特点的情况下,为了在中国更好地传播教义,基督教会必须走上“本土化”的道路,使自身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融入中国社会,以实现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普遍传播。
那么,如何才能使基督教会走上“本土化”道路呢?西方教会和传教士针对教案频发以及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现实情形,尤其注意加强对中国精英阶层的争取,以期以点带面,带动整个社会对基督教观感的改变。为达此目标,基督教会声称对士绅信奉的儒家文化表示理解,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尊重,努力调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分歧,进而争取知识阶层的支持。同时,为了增强教会内部华人信徒的凝聚力,调动其积极性,西方传教士开始将一些权力移交给中国职员,对教会进行自主管理。遗憾的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和中国本土牧师虽然据此做出了不少尝试,但并未取得预期成效。①福汉会的郭士立、福州美以美会的宝灵、美南浸信会的陈梦南、华人教徒席胜魔等人均对教会组织人事改革、教会内部权力结构、教会具体运作等提出见解并努力实践。参见李志刚《郭士立牧师在港之历史及其所遗中文资料》,香港,道声出版社,1987,第70 页。即便如此,中国信徒仍逐渐在教会体系中取得了一定地位,越来越多的华人基督徒开始在基督教会担任牧师、布道员等神职,参与宣教、日常运作等具体事宜的决策。经过不断努力,俞国桢于1906年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华人自立教会——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终于从规划走向实践。②张化:《中国耶稣教自立会述评》,《史林》1998年第1 期。
之后,中国基督徒和西方传教士一起朝着使基督教中国化、将基督教融入中国社会的共同目标努力工作。此间,华人基督徒逐渐改变西方传教士助手或雇工的身份成为其同事,中外教牧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更加平等。与此同时,在西方教会的默许下,中国自立教会数量不断壮大。敬奠瀛建立的耶稣家庭,王明道设置的基督徒会堂,倪柝声组织的聚会所(小群),张灵生、张巴拿巴与魏保罗等成立的真耶稣会等纷纷得到中国信徒信任,并取得了一定社会影响,成为践行教会本色化的成功案例。③刘家峰:《“中外新教合作建制”与近代基督教中国化研究》,《史学月刊》2013年第10 期。不过,推进中国基督教会的本色化和自立虽是中国本土教徒努力的结果,但更是西方教会和传教士采用的一种发展策略。对传教士而言,此举不仅可以在中国民族主义逐渐觉醒的背景下将中国教牧和基督徒推向前台,减轻中国社会和政府对源出西方的基督教的疑虑和抵触,规避政治风险和道义责任,④Missions and Wesrstrn Expansion,The Economic Basis of the Church,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New York,1939,p.41.还能凭借其相对优势的组织架构和经济实力,继续在与所谓自立教会的交往过程中保持优势地位,使其工作仍置于西方教会制定的框架内。
此外,基督教会是一个依靠思想维系的宗教组织,基督徒最为关心的是精神信仰。因此,若没有适合中国本土教会的本色神学作为理论支撑,使基督徒在精神上得到指引,中国基督教的自立与本色化运动就会缺乏持续发展的内生性动力。⑤胡卫清:《汕头新中华基督教会研究》,《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 期。是以,如何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使基督教教义符合中国社会现实成为中国自立教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情形下,王治心、赵紫宸、吴雷川、刘廷芳等教会领袖结合自身实践,努力建构适应中国伦理话语的本土神学。因着华人基督教思想家的不懈努力,中国基督教本土神学体系初具规模,为中国教会的自立与本色化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不过,基督新教有别于其他宗教,其教派分支多达百余,而且分支间教义迥异、互有抵斥。各教派进入中国之后,彼此之间仍存在纷争和竞夺,并保持各自内部特性,而这往往会带来内耗,影响教会事业的发展与壮大。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消耗,也为了适应中国教会本色化的需求,更为了响应1910年爱丁堡世界传教大会的号召,中国基督教会逐步在一些具体活动领域中进行组织团结,展开联合协作。同时,为了使中国教会能够做到合一,提高运作效率,节省运营经费,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合作逐渐加强,教会经济基础得到夯实。①施云英:《中国教会应当合一的理由》,《金陵神学志》第16 卷第2 期,1934年,上海市档案馆藏,U124-0-113。简言之,在中外教会和信徒的共同努力下,义和团运动之后的二十年成为中国基督教会的高速发展时期,教会自立和本色化色彩日趋浓厚。
二 中华基督教会的本色化努力与成效
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伴随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高涨,呈风起云涌之势。此种情况下,尽管西方教会和传教士仍试图揭橥宗教自由的旗帜,力图对中国基督徒中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以限定,维持所谓的“宗教自由”,但面对中国民众坚决反帝的社会大环境,计划流于空谈。
由于西方教会和传教士无力应对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也无法对抗中国社会的理性思潮和反教情绪,②其时,胡适、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等人围绕基督教等宗教进行了深入探讨。参见张晓林《众说纷纭话宗教——20世纪20年代关于宗教本质和定义的争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 期。中国教牧主动将责任承担下来,试图真正提升自身地位。具体实践中,他们充分关注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并对教会发展中遭遇的困境进行反思,以期为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进一步展开提出针对性意见。
在反思和检讨中,以中国基督徒为主体的教内人士围绕为何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和贡献为何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进行讨论。
经过讨论,他们认为以往中国教牧对以西人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会的归属感并不强烈,为教会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不显著。不过,考虑到教会的组织、产业、规程等对当下的中国自立教会和基督徒而言仍显得过于复杂,自立教会尚无法切实展开接收西方教会产业工作的现实状况,这些教牧呼吁全体中国基督徒应不分畛域、不分中外地去建设中国本土教会,规避宗派主义,推进教会的联合工作,促进包括慈善、卫生、教育在内的基督教会事工的全面发展,实现教会的自立。①Address by Mr.T.Z.KOO at Conference on Church and Mission Administration,1927.3.1,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RG011-237-3927.
不惟如此,还有不少中国基督徒认为,中国基督教会之所以难以真正建立起自立教会,是因为华人牧师缺乏足够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中国人之所以反对基督教是因为中国教会西洋化太重,反对的目标是外国教士居多,所以中国的基督教当自谋独立,成为中华基督教。外国办理教会的人,应当将担子给中国人了。”②汪廷弼:《基督教与中国》,《真光杂志》第24 卷第11、12 合刊,1926年,第22—23 页。
此外,在国家主义和民族意识觉醒的背景下,还有教会人士指出必须努力在精神意识层面对教会进行全方位的改造,由中国基督徒承担更多的宣传责任,向中国社会大众说明基督教是一个逐步走向自立的本色化宗教。③Rev.F.J.White,D.D.,Annual Report of Shanghai College for the Year 1925,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RG011-240-3949.
为了更好地改变中国普通民众对基督教会的观感,大批华人基督徒在反思与检讨之余,积极探讨实现基督教会本色化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以期达到扩大基督新教在华影响的目的,并使普通民众相信基督教会并不与中国社会为敌,而是扎根于中国社会、为社会大众服务的。为达此目标,如何排除中国社会敌意,追求基督教会进一步发展,使教会进一步本土化,则成为教会和教徒亟待解决的问题。
实践过程中,中国基督徒在已建立自立教会的基础上正式发起了以“自治、自养、自传”为目标的本色教会运动。在此潮流中,教会内部以实现教会本土化和真正的自立自强为目标,积极探讨教会本色化的途径并积极献计献策,以期达到建成本色化教会的目标。④在中国基督教界颇孚众望的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即表示:“本色教会的成员一定是中国人,领导人物也设想是中国人,支援它的活动和机构的财源,也大半来自中国。”参见马敏《韦卓民的基督教观》,《道风:汉语神学学刊》1995年第3 期。
基督教会要实现“三自”①目前,学术界对于“三自”的概念并无统一见解,笔者认为自治、自养、自传是互为表里、互相制约的关系,教会自养是自治与自传的基础,而自治与自传反过来也推进教会的自养进程。只有真正达成“三自”,教会本色化方可以实现。目标的本色化,最终达到本土化和自立,实现经费收支自主是前提和基础。经济是一切行动的基石,经济不能自立,教会行政运作便无法维系,“自立”也就变成了高调。教会要实现“三自”目标的本色化,“自养”是其首当要务,脱离“自养”谈自立皆成空话。因此,自立教会必须做到经费自筹,经济自养,履行与权利相应的财政责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本色化教会。对此,作为中国基督教会领袖的诚静怡设计了从“差会”到“中国教会”的过渡模式。诚氏主张西方差会应当有计划地向中国教会移交财产和治权,由中国教牧逐步承担起教会教务领导工作等全部责任。②刘家峰:《从差会到教会:诚静怡基督教本色化思想解析》,《世界宗教研究》2006年第2 期。不过,诚静怡的设想只是顶层设计,落实到实践中还需自立教会针对现实状况逐次展开。实践过程中,有教会人士认为要真正促进本色化教会,形成真正意义的教会自立,必须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以本土的人才、经济建设中国人自己的教会。③邓述堃:《中华教会的自养》,《中华归主》第172 期,1937年。同时,灵性生活和物质捐输之间有着深切的关联,教徒拥有丰富的灵性生活,才对教会产生密切的感情,而只有教徒诚意捐输,教会才能实现自养、自立,完成本色化。④俞晓峰:《本色教会经济问题——自养》,《闽中会刊》第1 卷第3 期,1929年。
在中国基督徒追求教会自立的过程中,形式与内涵均必不可少。在教会逐步本色化的过程中,各教会逐步取消其名称上带有的西方色彩称号,多冠以中华基督教会的名号,争取中国社会的理解与支持。⑤陈筠:《基督教在中国之前途》,《中华归主》第192 期,1938年。同时,在教会本土化过程中,华人基督徒多次向西方教会表达接收教会产业的诉求,希望来华各差会能够将教会产业交给中国人自己处理。⑥关于西方教会向本土教会移交产业的具体案例可参见谌畅《取舍之间:中华基督教会财政运作中的西方教会影响》,《基督宗教研究》第23 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为达此目标,各地华人基督徒纷纷将自立教会改组为中华基督教会组织,并于1927年在上海正式成立全国总会,形成了全国性的教会组织。中华基督教会成立后,特别注重改善内部结构和组织,强调会内的上下级从属关系,其组织行政由全国总会、协会(大会)、区会、堂会四个层级组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由上而下的行政架构。①参见《中华基督教会典章及细则》(全国总会第三届常会修正通过),《中华基督教会广协各项章则汇编》,广东省档案馆藏,92-1-81。
形成完备的组织框架后,中华基督教会在行政自主、财政独立等方面开展了形式不一的工作,并通过设立专业性机构、完善预决算制度、提高经费利用效率、学习西方教会经济管理经验、接收差会在华产业、接受中国政府监管、争取合法法人身份等途径努力夯实教会自立基础,实现本色化目标。②对于中华基督教会追求自立的路径,在争取经费本土化与维系自身发展之间如何权衡,详见谌畅《自营与外援之间:抗战时期中华基督教会自立路径研究》,《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 期。中华基督教会的成立与壮大对中国基督教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华基督教会不断推动经费运行规范化,采用各种手段推动收支平衡,均是为了提高自身经济实力,尽可能摆脱对西方宣教会的依赖,不仰人鼻息,做到经济自立。全国总会为了解自身的经费状况,要求会计制成详细的经济报告,完成决算编审,交总会执委会留存。在此基础上,总会再对内部经费调度做统一安排。简言之,总会通过制定严密的决算制度,将教会经费统计责任落实到位,实现监管教会经费运行状况的目的。同时,由于全国总会是中华基督教会的中枢机构,其经济状况的好坏直接对下属教会产生影响,并为地方(基层)教会组织提高经费运转效率、谋求经济自立做了良好示范。
中华基督教会在不断壮大自身的同时,试图获得合法身份,取得中国官方和社会民众的认可。早在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成立之初,即拟向中央政府呈请备案,但因故未能如愿。不过,中华基督教会并未放弃,继续积极为国民政府献言献策,参与国民政府组织、推行的各种活动。③中华基督教会内部的美国传教士就曾积极参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的设计和实行。参见James C.Thomas Jr.,While China Faced West: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1928-1937,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9。全面抗战爆发前夜,中华基督教会终于得到国民政府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核准,获颁组织许可证书,在中央政府处取得了合法身份,④国民政府虽然给予中华基督教会合法身份,但重申了《指导传教士团体具体办法》,即“传教团体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并受政府监管,包括其建立的教堂、办理的学校和医院事业等,各团体除例会外,举行大会时,当地高级党部得派员参加。任何团体有违法行为,政府可以取缔有关团体”,将其中华基督教会置于官方监管之下。参见麦炳坤《中国基督教会与社会主义运动:基督教知识分子的反应与调试之路,1945—1954》,博士学位论文,香港中文大学,1996。成为当时受中国法律保护的唯一教会团体。①《为完成在政府立案事功调整本会内部案》,《总会干事部提案》,上海市档案馆藏,U-102-0-14。
如前所述,中华基督教会为了实现自立和本色化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正如吴义雄教授所言,中华基督教会的成立与发展是20世纪前期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由口号走向实践的具体代表。②吴义雄:《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与本色教会运动》,《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 期。
三 中华基督教会本色化运动的路径困难
中华基督教会总会及各级属会的成立和发展是贯彻教会自立与本色化的具体体现。实践中,中华基督教会以财政自立为目标,在经费支出和各项事业的投入分配上,均有较为完善的计划。在具体支出上,有专人负责并有严格的监管,在经费调配上,各级教会各司其职,相互配合。③教会工作开展状况及经费支出情况必须经过查账员审批、签字,在指定时间内,具报相关委员会。参见《促进各堂会事业自养案》,《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三届常会提案及各大会报告书》,广东省档案馆藏,92-1-6。不过,即令中华基督教会组织严密,工作严谨,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也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遭遇了不少困难。从外力因素论,在遭遇天灾或者国内形势动乱时,基层教会因教堂受损、教友离散而产生经济困难,动摇自立基础,不仅难以从教徒处募集经费,还要想方设法募集资金,重建教堂并帮助教徒渡过难关。④《中华基督教会典章及细则》,《中华基督教会广协各项章则汇编》,广东省档案馆藏,92-1-81。这就使中华基督教教会本不牢固的自立基础更加动摇。
外部因素的影响虽然重要,但教会内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加剧了中华基督教会的经济困难,产生了本色化困境。事实上,虽然中华基督教会一直以一个合一、紧密的自立教会组织自居,但其内部并不是没有摩擦和矛盾,尤其在经费的支配上,即使会内章程已经明文规定了各级教会的责任和义务,强调了中华基督教会以实现经济自立、教会本色化为纲领,⑤参见《中华基督教会典章及细则》(全国总会第三届常会修正通过),广东省档案馆藏,92-1-81。亦可见《中华基督教会广协各项章则汇编》,广东省档案馆藏,92-1-81。但上下级教会之间、不同区域教会之间,各有盘算,存在纠纷。
按照教会制定的章程,上级教会对下级教会承担的经济责任是有限度的。故当下级教会因某些缘故向上级教会请求补助和支援时,上级教会一般选择综合考虑自身经济状况以及下级教会的实际处境进行处理,而大多数时候会选择拒绝。为什么会出现此种情形呢?一方面,上级教会担心若轻易答应下级教会请款要求,其他属会纷纷效法,而自身又无法顾此失彼,只会增加自身经费紧张程度;另一方面,掐住了财政大权,才能真正控制下级属会,因此上级教会往往以截留补助、掐断财源作为控制属会的手段。
同时,在中华基督教会体系中,一级教会只对上下级会负责,因此在任务派发上,一般是自上而下摊派。为了减轻本层级教会的负担,该级会将自身责任交由下属教会。同理,当下级教会向上请款时,也一定经过很多个环节。环节一多,可能遇到的障碍也随之增多。因此,整个教会的财政运作远没有表明上看起来那么和谐。
从上往下看,上级教会(高层级会)特别注重对下级教会的监管。以闽中大会为例,该会除在大会内部聘用一名主管会计外,还在下属区处分设副会计。此外,闽中大会还委任总稽核及稽核委员,按期对各区会乃至基层堂会进行巡查,在区会的协助下办理区会和堂的稽核事宜。不惟如此,闽中大会还要求大会下属的教堂、学校、医院及协和各机关均层层上报,将年度预决算交由主管会计与副会计核实。①《闽中会刊》第1 卷第6 期,1930年,上海市档案馆藏,U102-0-112-525。由此可见,闽中大会试图加强对自身和下级教会经费的监管力度,以更好了解下级教会的经济状况,从而把握好整个大会的发展趋势,实现教会经济的正常运转。
闽中大会的情形并非个例,事实上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和各大(协)会制定和颁布的一系列规章制度都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不过政策的制定与落实之间存有张力,下级堂会虽然服从上级教会管理,但在执行过程中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有所抵牾,时有排拒。
由于下级教会并不能完整执行上级教会制定的政策,上级教会采用各种手段对属会经济状况进行监管,摸清属会经济实力,以更好地了解下级教会的自立和本色化状况。面对上级教会加强经济监察、加大控制力度的尝试,属会表面上十分恭敬,声称愿意配合上级工作,表现特别积极。唱高调容易,交出自身权力却很难。涉及自身权益时,下级教会并不愿意受到上级教会干涉,经常采取反制手段,努力维护自身利益。具体实践中,下级教会(属会)往往想尽办法夸大自身困难,并以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为理由,拖欠本应缴纳的各种款项,规避责任。①按照要求,下级教会有责任向上级教会缴纳经费以供教会正常运转。若会费遭到大面积拖欠,整个教会的财政运转会受到极大影响。参见王福梅《莆田基督教会(新教)之研究(1863—1949)》,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02。
当然,受限于教会章程,下级教会一般不会与上级教会起正面冲突,尽力做到谨守规程,按流程办事。
有堂有牧,乃成教会,建筑和翻新教堂是基层教会极为重要的事工。广东协会第五区会阳春堂修筑教堂即是显例。该堂会原有的礼拜堂破旧,难以满足当地教徒的宗教生活。基于此,该堂会试图修建新的礼拜堂,以让所属近二十万教徒更好地了解基督精神。然而,修筑教堂需要大量经费,仅靠阳春堂自筹显然无法完成既定的修筑方案。为此,阳春堂在举办募捐活动向当地教徒募集经费的同时,将筑堂计划上报上级区会,试图通过其向广东协会请求拨付一千元大洋的津贴。收到阳春堂的请求后,区会并不愿意介入此类事宜,答复称该堂会可直接向协会请求津贴补助。据此,阳春堂只得向广东协会去函请求援助。②《第五区会阳春堂汤颂和等致方约翰》(1930年),广东省档案馆藏,92-1-55。以上反映出中华基督教会组织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基层教会在遭遇经费困难等问题时往往需要层层向上通报,争取上级教会的首肯与帮助。
中华基督教会内部组织中教会层次越高,其掌握的资源也越多,基层堂会如能越级请求协(大)会经费支持,显然可以得到更多实利。此外,虽然按照规定区会不能规避其应尽的责任,但作为中间纽带,往往陷于两边不讨好的局面。是以处在中间层级的区会有意识地避开中间人身份,可以规避自身风险,减轻担负的责任。正如吴义雄教授的研究所表明的,中华基督教会组织往往通过内部改组,弱化区会作用,使堂会与大(协)会事实上形成垂直的上下级关系,协会—堂会成为地方教会内部的基本结构,区会则成为辅助性的机构。③吴义雄:《中华基督教会广东协会与本色教会运动》,《世界宗教研究》2002年第2 期。由此可见,教会的制度设计虽然有其规范,但仍需根据具体情形的变化进行调整。
既然中华基督教会内部已经在事实上逐步形成了协会—堂会的组织架构,其在追求教会自立与本色化的过程中,基层堂会与协(大)会之间的交往就显得格外重要。
九洲基福音堂是中山当地一所重要的教堂,教友众多。为了更好地吸引教众,吸引更多当地居民加入教会,九洲基教会打算建筑新教堂。为此,驻堂牧师致信时任广东协会执行干事的方约翰称:“殷思道牧师曾在美国贮有千余美金为本堂建筑礼拜堂所需……窃本堂近年来教务日益发达,信道日众,然以原有旧址地方狭窄每感座位不敷本堂兄妹引以为憾……因兄妹中多务农业,多贫乏,此情况实属有愿难偿,今忽闻殷牧师有此巨款拨作本堂建筑之费,聆言之下雀跃欣慰……特先组织建堂筹备委员会磋商进行事宜……该堂改建后可设座位数百并可附设学校,计该屋估价银约两千六百大元,另改建筑费需银五百元,倘措来之款不敷则由本堂兄妹负责维持,冀能达到目的而已。”①《中山香山县榄镇九洲基福音堂致方约翰》(1930年6月20日),《中华基督教会来往函件》,广东省档案馆藏,92-1-53。九洲基福音堂方面首先向广东协会表示其已凭借殷思道牧师的前期工作有了一定的筑馆经费,并表达了独立完成建堂工作的决心。乍看之下,这是一份作为下级教会的地方堂会对作为上级教会的广东协会的保证书。其保证自身能设法筹集经费,完成建筑任务。不过,仔细推敲,可发现不同意境,倘若该堂会真能自己完成建筑,在教堂完工后向协会报告即可。然而,信中该堂会只是描述新堂落成之后的美好前景,使广东协会了解建堂之于堂会扩大宣教的重要性,并说明建堂款项缺口极大,仅凭堂会自身显然无法负担。既然其无力筹措此笔经费,而筑堂又极为重要,因此堂会希望协会主动予以经费贴补的算盘跃然纸上。
此种需要协(大)会揣摩意图的求款案例并不多见,更多的基层堂会选择直接向上级教会请求帮助。例如,江门北街堂始终以寻求教会自立为目标,但因经费紧张无法拥有自己的礼拜堂,只得租楼办公,每年须缴纳房租三百余元。对此情况,该堂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礼拜堂。他们从加拿大宣教会处免费获得了建堂用地,解决了用地难题。不过,筹建礼拜堂至少需要八千元经费,远远超出了该会的承担能力,因而该会能够获得广东协会支持,在整个协会内部募捐,借助他处教会的帮助完成礼拜堂建设。②《江门北街筹建礼拜堂委员会叶爱慈等致广协会执行委员会》(1930年5月25日),广东省档案馆藏,92-1-55。面对该会的请求,广协会回复称愿意给予一定资助,但是并不同意在广东协会这一框架下从其他堂会处筹款,防止形成不充分内部挖潜即依赖外援的不良风气。③《方约翰致江门北街筹建礼拜堂委员会》(1930年5月2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92-1-55。
建筑礼拜堂引发的经费纷争和对自立的讨论并不是中华基督教会内部唯一存在的问题。上下级教会之间还会因其他经费问题产生争论和摩擦。新塘福音堂曾致信广东协会称:“今年主任之薪金敝堂只有尽力,亦得二百壹拾元无能再筹,不足之数不得不乞请贵协会额外恩怜支足。”①《新塘中华基督教福音堂致方约翰》(1931年9月17日),《中华基督教会来往函件》,广东省档案馆藏,92-1-53。自主负担教会牧师和传道薪金是教会自立与本色化的重要表现,新塘福音堂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上声称无能为力,无疑是承认自己的本色化进程并不顺利。不惟如此,新塘福音堂还因无力承担欠款请求广东协会予以帮助:“接奉9月8日大函,以敝堂租欠七年,允由贵协会支付,新租则由敝堂负责担承……既蒙贵协会允愿清偿旧欠租七年,敝堂应即承认当经议决一致通过,租金由1932年起由敝堂担责支纳也。”②《新塘中华基督教福音堂致方约翰》(1931年10月2日),《中华基督教会来往函件》,广东省档案馆藏,92-1-53。虽然基层教会存在各种问题,但广东协会作为中华基督教会在广东地区的领导者,对于属会负有管理、扶助的责任。不过,协会的援助并非没有限度,方约翰在回信中表示该堂只能从以下两种扶助方式中选择一种:第一,协会津贴该堂会三百元全年经费并偿还债务,以后主任牧师薪金等均由该堂自行负责;第二,该堂会缴纳八百元给协会,则由协会承担主任薪金并清偿以前债务,但堂租以后仍由堂会自己负责。③笔者查阅此信件时,因该信件有部分破损,无法看清日期,但该信发出后,新塘福音堂于10月29日又有回信,故此信的寄发时间应在10月2日到10月29日这段时间内。参见《方约翰致新塘中华基督教福音堂》,《中华基督教会来往函件》,广东省档案馆藏,92-1-53。由此可见,方氏明确表示广东协会并不相信新塘教会一面之词,对该堂会经济情况有着自己的评估。在此基础上,方氏还代表广东协会为该堂会提出了具体方案。
在广东协会方面看来,这已是做出妥协和让步的举动,充分展现了诚意。不过在堂会看来,广东协会的补助相当有限。此种情况下,新塘福音堂于1931年10月29日回复广东协会再次强调自身处境的艰辛,称该堂已在内部挖潜方面做了最大努力,却依然无力负担薪资和偿还债务,牧师索薪和铺主索租之势愈演愈烈,堂会无从招架。据此,其堂会干事威胁称,若广东协会再不按其要求如期拨发援助款,堂会将向协会提出总辞职。④《新塘中华基督教福音堂致方约翰》(1931年10月29日),《中华基督教会来往函件》,广东省档案馆藏,92-1-53。
基层堂会面对广东协会的资助,竟以总辞职作为威胁手段,一方面表明基层堂会经济状况确实欠佳,另一方面也说明基层堂会极力夸大自身处境的艰辛情形,在争取经费补助时寸步不让,并以激烈手段逼迫上级教会就范。面对胁迫,上级教会虽会做出适当让步,却也不会一再退让。半年之后,当该堂会致信广东协会总干事谭沃心,再度表示难以负担主任牧师每年310 元的薪水,需要广东协会作为中间人向同寅差会请求补助时,遭到了谭氏的坚决回绝。①《新塘中华基督教福音堂致谭沃心》(1932年3月28日),广东省档案馆藏,92-1-55。教会自立和本色化虽然是中华基督教会全体组织的共同目标,但上下级教会之间在经济交往上仍应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如果一方行为太出位,会影响另一方的观感,对彼此的合作产生负面影响。
由上述可见,即便是在基督教会发展较好的广东地区,其基层堂会的经济仍经常陷入困境。教会无力担负教牧薪资甚至需要举债维持运作,其所谓的自立与本色化自然流于空谈。
基层教会不仅在遭遇资金困境时寻求上级教会资助,还经常规避自身责任,拖欠需要上缴上级教会的会费,并用各种理由要求上级教会减免拖欠之款。②《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执行委员会第七届会议记录》,附件九,《总会1935—1936年预算案大纲》,广东省档案馆藏,92-1-47。在全国总会自身遭遇经费短缺时,要求各大(协)会与区会从各自行政经费中指定一项为总会行政经费,上缴总会,没有得到积极响应。③《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四届续行委员部年会记录》(1931年),上海市档案馆藏,U102-0-243-153。既然会费难以征集,总会又试图每年举行教会礼拜日捐一次,使全会上下以及全体教徒加强对总会赞助,要求各级教会在接收捐款后统一由大(协)会寄往总会,由总会会计接收并开具收据。④谭沃心、诚静怡:《订期举行教会礼拜日为总会收受教友乐捐致本会各地堂会》,《公报》第7 卷第5 期,上海市档案馆藏,U102-0-70-125。总的来讲,全国总会恳请各级教会努力合作,补充总会经费,减轻总会负担的努力因地方教会的排拒难见成效。⑤自1929年始,总会发起的总会礼拜日捐款、各级教会收入百分之二奉献总会、募足十万基金运动等各种活动均因地方教会的敷衍难以成功。参见《关于总会经费事项》,《总会事工调整案》,《总会第四届总议会议录》,上海市档案馆藏,U102-0-12。
中华基督教会虽然组织严密、架构完整,但实际上仍是一个组织繁杂、工区庞大的合一教会,其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很多摩擦和矛盾。面对这些情况,诚静怡认为必须努力调整中华基督教会的机构和组织,使各级教会彼此间的关系和做事的效率更合理化。①诚静怡:《努力面前》,《曙光杂志》,1937年7月,上海市档案馆藏,U102-0-14。不过,即使有诚氏等教会领袖给予充分的注意和关怀,在事关切身利益的情况下,各级教会都有各自的想法,并不会真正贯彻和落实总会制定的计划。虽然中华基督教会内部存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上下级教会之间也存在隔阂和纷争,但明面上均会遵守教会章程。至于实际运营则免不了一番明争暗斗。
民国时期教会的自立和本色化难以完全实现除了教会自身原因外,还与当时中国严峻的经济形势有关。同时,频仍的经济危机和自然灾害使农产品价格浮动极大,作为社会主要组成部分的农户收入大为减少,而地租负担也因为家庭总收入的减少而变得更加沉重。②科大卫:《中国解放前的农村经济》,香港牛津大学,1989,第133 页。由于中国社会是农业社会,农业人口比重极大,基督教徒以农民为主,教堂也大多分布在乡村,基层教会的主要经济来源是教徒的各项捐输。此种情况下,农民信徒经济实力下滑,生活困乏,在经济上无法奉献教会,导致了教会经济的萎靡,使教会的自立目标难以实现。
此外,西方教会和传教士始终不肯真正将教会经济权力和治理权让渡给中国教会和华人教徒,也是中华基督教会难以做到完全自立与本色化的重要原因。③参见谌畅《取舍之间:中华基督教会财政运作中的西方教会影响》,《基督宗教研究》第23 辑。
最后,在贯穿民国时期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主义高扬的历史进程中,包括中华基督教会在内的中国基督教教会一直以本色化为口号,以实现教会自立、宗教自传、经济自养为目标。然而,中国社会文化中并无宗教传统,加上基督教基层堂会数量有限、基督徒人数不足、基督教会社会参与度不够等现实条件的制约,基督教始终难以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④全面抗战期间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华西方传教士人数大为减少,传教士人数的减少虽然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国教会教牧短缺的困难,但在客观上使华人基督徒承担起更多责任、享有更多话语权,也使中国教会的本色化进程得以更好地推进。可惜的是,由于经济困顿、组织凋零、教会残破、教徒离散,中国教会没有抓住这一机会,推进本色化进程,实现自立目标。参见Bates to Doctor Reeves,1943.1.20,Archives of Miner Searle Bates Papers of Yale Divinity School,RG10-9-159。事实上,直到国民党政权崩溃,即使有部分教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立目标,①胡卫清:《未竟之业:20世纪40年代汕头教会的自立问题》,《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2 期。但能够真正完全做到自治、自传、自养的教会仍不多见,中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四 结语
近代中国出现过的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思想和政治运动,其能掀动人心于一时,大抵皆以民族主义为出发点,并基本上假借着民族主义的动力。②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和知识分子》,《联合报》(副刊)1975年5月1日。在此种情形下,基督教会想要真正融入中国社会,取得中国民众的认可,必须顺应民族主义蓬勃发展的潮流,将基督教教义与中国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解除社会各阶层的犹疑与戒心,形成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性自立教会。而基督教本色化恰恰就是一场以将基督教会完全独立于西方教会为旨归的宗教改革运动。
总体而论,虽然近代中国的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因受教会内部和外界环境的限制,在路径上存有先天性的不足,无法真正实现使基督教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的目标,但还是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观感,使基督教得以部分地融入了中国社会,并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首先,由于中国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力求贴近中国社会,逐步放弃条约体系下的种种特权,并将自身主张不断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中国社会民众得以深入了解基督教会的主张。同时,中国基督教会和基督徒并不局限于泛泛而论的口头表达,而是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历史进程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一方,反对外来侵略。据曾在中华基督教协进会任职、后任教于沪江大学的鲍哲庆(T.C.Bau)博士透露,中国基督教会通过在北伐和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中坚定站在支持本民族发展的立场,使基督教在中国普通民众心目中形象逐渐发生改变。社会大众不再认为基督教是一个极端排外、自私自利的宗教,而基督教会也逐步成为中国自己的教会。③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1940.5.25,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RG011-240-3948.
其次,虽然在以中华基督教会为代表的基督教会追求本色化进程中,其内部各级组织有时因内部利益分配不均、权责不明等问题产生龃龉,但都能把着力点放在实现教会本色化和教会自立这一共同目标之上,①需要指出的是,教会自立是教会本色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但教会自立又包含于教会本色化。将矛盾和纠纷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
最后,虽然中国的近代化属于后发外生型,②孙立平:《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 期。但中国社会内部的变迁与改造仍是促成国家近代化转型的主要因素。在这一主线下,以中华基督教会为代表的中国基督教会在追求自立与本色化的过程中,努力将教会诉求与社会需要相结合,使基督教会成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股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