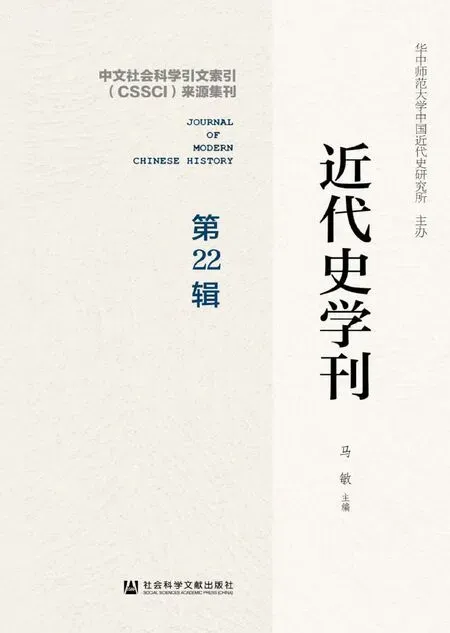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中共“五四”纪念研究(1949—1966)
2020-04-13程莎莎
周 游 程莎莎
内容提要 “五四”是一个意义丰富且具有多重面向的政治资源,其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和本身的复杂性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诠释空间。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共的诞生和发展,中共也重视对其纪念和诠解。民国时期,中共根据时代要务的变化不断赋予“五四”新意,使“五四”意义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仍不断对“五四”进行纪念、诠解和运用,如通过纪念活动建构“五四”的记忆,凸显“五四”“反帝”意义以表达政治诉求,强调和扩展“五四”的“革命”传统,使之成为一种普遍性精神资源等。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五四”纪念研究,可以看到一个政治节日在新政权建立前后的意义变化及政治运用情况。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五四”意义的丰富和多歧使其变得复杂且耐人寻味,其重要性和复杂性也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诠释空间,成为个人、学派和政党之间竞相诠解的文化和政治资源。中共是近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也是近代以来“五四”意义的主要诠释者之一,因此,对中共“五四”纪念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目前学界对“五四”的纪念已有不少探讨,但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共“五四”纪念还研究不足。①学界对“五四”纪念的研究主要有罗志田《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 期;胡国胜:《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6 期;郭若平:《塑造新思想:建国前后北京与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当代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 期;张艳:《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五四”纪念》,《史学月刊》2013年第6 期;《“青年节”抑或“文艺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五四纪念节问题探析》,《史学月刊》2015年第8期;凌云岚:《地方历史中的五四:民国时期湖南的五四纪念》,《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6 期;郭辉:《青年与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五四纪念话语的演变》,《兰州学刊》2019年第3期;欧阳哲生:《纪念“五四”的政治文化探幽——一九四九年以前各大党派报刊纪念五四运动的历史图景》,《中共党史研究》1919年第4 期;周游:《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的纪念》,《中国文化研究》2019年第2 期;张艳:《五四运动阐释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5;杨涛:《合法性争夺与民国时期青年节的演变》,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1;孙路遥:《史实与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记忆与阐释(1919—1945)》,硕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3。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如何纪念和定位“五四”,并赋予其新的意义;又如何借用“五四”纪念日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拟对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共的“五四”纪念进行研究,考察一个政治节日在新政权下的意义变化及政治运用情况。
一 民国时期中共对“五四”定位及诠释的演变
五四运动直接促进了中共的诞生和发展,中共也自然注重对“五四”符号意义的诠释和运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早期有着共产主义理想的知识分子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见证者,他们在五四运动发生后积极发文纪念“五四”。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在1919年“双十节”纪念中就撰文表示“双十”和“五四”“在中国革命史上是有同一价值的纪念日”,①李大钊:《双十与五四》(1919年10月26日),《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07 页。赋予了“五四”“革命”的意义。国民革命时期,以国共合作为背景,国民革命是中共的主要目标之一,中共也更多地以“革命”定位“五四”,将其视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如施存统1924年指出五四运动“实是一种伟大的国民革命运动,是国民革命运动底一大转机。其重要竟可说是等于辛亥革命”。②存统(施存统):《“五四”运动底意义与价值——再评寿康君底“青年的浮惰”》,《评论之评论》1924年第7 期,第5 页。
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其反帝争取民族独立的面向被中共视为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的一部分(甚至说是开端)。张太雷1925年指出:“迨至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民族运动入了他的第三期。中国的民族运动自从五四运动才渐渐变成近代的民族运动——有组织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运动。”①太雷(张太雷):《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1925年第4 卷第77、78 期,第394—395 页。关于如何定位“五四”,施存统指出,“单认五四是学生爱国运动及思想革命的纪念,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强调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民族革命的新阶段。②双林(施存统):《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向导》1925年第113 期,第1043—1044 页。
既然在中共的话语里,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革命青年就有必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的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完成“五四”未竟的革命事业。林育英将“五四精神”总结为“反抗的精神”、“合作的精神”和“不息的精神”,③育英(林育英):《五四运动的真精神》,《共进》1924年第61 期,第1—2 页。并强调这是国民革命时期最需要的精神。施存统以“五四”精神鼓励青年说革命运动“决不是一天两天能成功,也不是一次两次便能成功的”,需要不断奋斗,不能因为“一时看不见表面上的成绩便灰心”。④存统(施存统):《“五四”运动底意义与价值——再评寿康君底“青年的浮惰”》,《评论之评论》1924年第7 期,第5 页。恽代英面对“五四”后中国社会混乱黑暗的现状,将矛头指向对现实社会无动于衷的青年,将五四青年与当代青年进行比较,警醒当代青年要继承“五四”的革命传统。⑤恽代英:《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1924年第2 卷第26 期,第1—4 页。
从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到抗战爆发的国共十年对峙时期,除了左翼知识分子发表一些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纪念文章外,中共很少纪念“五四”,也没有赋予“五四”特殊的意义。直到抗战时期国共再次合作,中共又开始积极纪念五四运动,并赋予其新的意义。
抗战时期,将“五四”定位为中国抗战史的一部分就是中共赋予它的新意之一。1938年《新华日报》的“五四”纪念日“社论”就将五四运动定位为“中国最近二十年来壮烈的反抗日寇侵略的神圣斗争的发轫”。⑥社论:《纪念五四》,《新华日报》(重庆)1938年5月4日,第1 版。潘梓年也指出,“对帝国主义,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举起反抗旗帜,五四虽不是第一次,却是最显明,最有理论基础的第一次”。⑦潘梓年:《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自由中国》(汉口)1938年第2 期,第190 页。中共将“五四”编入抗战史和中国“民族解放”史的谱系之中,更有利于激起民众对日本长期侵略中国的愤慨,激发民众的抗日情绪。这样,“五四”也成为中共进行抗日动员的重要资源。1938年“五四”纪念日《新华日报》的社论就强调:“纪念五四,我们应该继承这个光荣的反对日寇斗争的革命传统,踏着先驱者史迹,继续猛进,而贯彻完成他们所开端了的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①《纪念五四》(社论),《新华日报》(重庆)1938年5月4日,第1 版。1939年胡乔木在“五四”纪念日也强调“每一个青年应该学习五四英雄的模范,坚持一定的立场,坚持为国家民族的彻底独立解放而奋斗到底,奋斗到死”。②胡乔木:《青年要发扬五四爱国精神》,《解放》1939年第70 期,第28 页。
民主与自由是“五四”的另一个重要面向,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五四”纪念中,借“五四”民主和自由意义的凸显,对国民党的独裁集权予以批评,为自身争取更多的政治空间。《抗战日报》强调“五四”的民主意义,对国民党的“罪行”进行抗议,指出应本着“‘五四’民主运动的民主主义精神,反对武断独裁,争取民主自由”。③《纪念“五四”二十二周年和第三届中国青年节》(社论),《抗战日报》1941年5月7日,第2 版。胡绳总结“五四”后的历史经验,表示只有自由才能保证思想学术的进步和民族精神的发扬。在“宪政即将实施的时候,我们不能不切实地主张在不违背抗战建国的总原则下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讲学自由,出版自由!”④胡绳:《由纪念五四想到思想自由》,《全民抗战》1940年第121 期,第1829 页。
在国共内战时期,中共一方面继续凸显“五四”民主、自由的面向,将“五四”符号作为消解国民党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国民党斗争的一个政治资源,另一方面继续强调自身与“五四”的关系,以凸显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如陈伯达在1948年的“五四”纪念日就指出五四运动最伟大的意义,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就出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由此就出现了以毛泽东思想为集中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⑤陈伯达:《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冀中教育》1949年第2 卷第3 期,第55 页。在陈伯达的叙述里,“五四”与中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凸显了“五四”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经过三年多的国共战争,1949年初国民党败局已定,新中国成立在望。此时,中共对“五四”意义也出现了新的诠释。是年“五四”纪念日,田家英对“五四”的民主与科学意义进行强调,赋予了“民主”、“科学”新的内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民主,就是以工农为基础的人民的民主;我们所追求的科学,就是建设工业化的人民国家的科学”。⑥田家英:《五四与今天》,《中国青年》1949年第7 期,第25 页。田家英对“五四”的新诠释,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民国时期中共对“五四”的定位和诠释,是与时代的要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共在不同时期不断凸显“五四”的时代意义,呈现了一个多元开放的“五四”符号,也丰富了“五四”的历史意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对“五四”的纪念又出现新的特征。
二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间的“五四”纪念活动与“五四”记忆的建构
纪念活动是一种后人意在表达某种情感和内心诉求的纪念形式,也是时人与过往事件建立联系的一种表象纽带。“五四”的纪念活动在“五四事件”发生后次年就开始进行并持续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年举行“五四”纪念活动也是一种常态,且逢五逢十大庆。这些纪念活动形式多样,类型繁多,但是纪念活动的主要目的在建构人们对往昔的记忆,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绪,进一步建构中共的政治合法性,也有以纪念活动为载体来凸显当下要务的目的。当然,这种对往昔的回忆和重述也会根据时代的需要被不断建构。
在“五四”纪念日,由亲历者对五四运动史实和意义进行讲述及诠释是纪念会的一项重要活动,这也是重构“五四”记忆的一种重要方式。新中国成立后,当年五四运动的许多参与者留在大陆,他们是活着的“五四”记忆,也是“五四”纪念活动中受邀给大家讲述“五四”历史和意义的常客。例如,1950年北京大学举行的“五四”纪念活动中,就邀请“五四”的亲历者许德珩来讲述自己参与“五四”的经历。①《在历史晚会上徐特立讲“五四”领导问题 许德珩讲“五四”历史回忆》,《光明日报》1950年5月6日,第4 版。许德珩还于5月4日当天在北京广播电台向全市人民讲述“今年纪念‘五四’的意义和对‘五四’的几点回忆”。②《京市广播电台“五四”节目预告》,《人民日报》1950年4月30日,第4 版。是年上海的“五四”青年节,包括工人、学生、军队和郊区农民一万四千余人在跑马厅举行盛大的晚会,邀请曾经参加五四运动的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向大会报告五四运动及其意义。③《万余青年欢聚跑马厅热烈庆祝青年节》,《解放日报》1950年5月4日,第1 张。又如,在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新闻系和历史档案系的联合纪念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讲述自己参加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和体会,以及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吴玉章勉励青年们向革命前辈学习,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彻底不妥协的革命精神。①《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1962年5月5日,第1 版。由于时代、环境和身份等因素的限制,讲述者在讲述“五四”的历史及意义时常常带有各种目的及诉求,对自己的经历也可能进行增删,再加之年代久远,记忆容易失真,所以回忆是否真实是存疑的,但是“五四”亲历者的讲述往往能给人一种身临其境、重访“五四”的感觉。
在新中国十七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中,除了由五四运动的亲历者讲述“五四”的历史和意义之外,也经常举办“五四”相关史料的展览。这些通过文字或图片的形式对往昔的呈现和“回放”,也是传播和构建“五四”历史记忆的一种形式。如1950年的“五四”纪念日,为纪念五四运动31 周年举办的中国青年运动史料展览中,就展出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青年的革命运动史料。②《文化部等机关联合发出启事征集五四以来青年运动史料》,《光明日报》1950年4月23日,第4 版。这次史料展览共展出1050 张照片和2053 件实物,其中就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救国日报》头版所刊载的山东问题材料,五四运动参与者提出的打倒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的口号。③柏生:《记中国青年运动史料展览》,《人民日报》1950年5月11日,第3 版。1959年天津市的“五四”纪念活动,在五四运动革命史展览会上展出了五四时期的许多传单、宣传品、群众大会的决议,有关文件、电报,当时天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和商人罢市的文件和照片等。这些照片中有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人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社员合照,1919年10月10日天津市爱国游行示威的照片,天津抵制日货时群众示威游行的照片,以及周恩来亲笔草拟的天津学生罢课宣言,等等。除此之外,展览会还介绍了四十年前五四运动席卷全国的概貌。展品中,有北京和全国各地在1919年5月巴黎和会期间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电文、传单、来往信件等。④《天津市举办“五四”运动革命史展览会》,《人民日报》1959年5月5日,第2 版。这些展示的五四运动资料都非常珍贵,也都非常直观形象地向人们展示了五四时期的历史图影,并向时人传递了五四时期的鲜活记忆。
在五四运动的纪念活动中,“五四”相关史料的展览是构建“五四”记忆的一种方式,而对“五四”历史的研究、报告和讲座等则是构建“五四”记忆的另一种途径。不像“五四”亲历者们的现身说法、讲述自己所见的五四运动,研究、报告等是在充分收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五四运动历史的建构,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待五四运动的历史,但无论如何这也是百年来承载和传播“五四”记忆的一种重要形式。例如,1954年的“五四”青年节,青年团重庆市委员会就举办了介绍五四运动历史的“青年讲座”,向广大青年介绍和宣传五四运动的历史。①《全国各大城市青年积极筹备迎接“五四”》,《人民日报》1954年4月29日,第3 版。又如,1959年上海知识界举行座谈会纪念“五四”40 周年,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徐崙就详细地介绍了五四运动在上海的情况。②《不断改造思想紧紧跟上时代》,《光明日报》1959年5月6日,第2 版。再如,1961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校史编写小组青年教师在会上报告了北大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历史。③《发扬“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1961年5月5日,第4 版。是年“五四”纪念日,《中国青年报》还刊发了北大历史系1956 级学生编写的《“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资料,④《“五四”运动中的北大学生》,《中国青年报》1961年5月4日,第3 版。等等。这些研究、报告等极大地丰富了“五四”的内容,也为后人系统地认识“五四”提供了基础。
除了上述“五四”纪念活动之外,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五四”纪念日还有联欢会、游园会等纪念活动,这些活动形式不一,主题也各式各样,但在“五四”纪念日讲述“五四”历史、构建“五四”的记忆、提炼“五四”的意义和价值无疑是“五四”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将人们在“五四”纪念日这个特殊的时刻集中在一起,也为人们共同了解“五四”的历史、感知“五四”的记忆提供了条件。当然,“五四”纪念日也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色,是时人凸显时代要务、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场域。
三 对“五四”“反帝”意义的强调与政治诉求的表达
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这也是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定位。⑤毛泽东:《五四运动》,《解放》1939年第70 期,第9 页。五四运动的这一特质使“反帝爱国”成为其众多意义中的一个重要面向。“五四”的“反帝爱国”意义贯穿整个现代中国始终,如在民国时期的“五四”纪念中,其“反帝”意义就被始终强调。国民革命时期,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背景下,中共的“五四”纪念凸显了强烈的“反帝”意义;抗战时期由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共尤为强调“五四”的“反帝”抗战意义,①社论:《纪念五四》,《新华日报》(重庆)1938年5月4日,第1 版。注重“五四”符号中民众动员的价值。新中国成立后,虽然中国民族独立的目标基本完成,但是当时美苏冷战的国际局势、美国对新政权的虎视眈眈使中国人民心有余悸,仍将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和侵略作为当时中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目标,因此,“五四”意义中“反帝”的爱国主义面向在“五四”纪念中仍被反复强调,且成为动员民众和表达政治诉求的一种重要政治资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四”纪念中,对“五四”反帝爱国意义的强调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外交等紧密相关,这也表现了“五四”符号强烈的时代特色。如在抗美援朝期间,反帝抗美的呼声日渐高涨,民众动员也如火如荼,此间“五四”纪念活动中的反帝爱国主义面向也被不断强调。1951年的“五四”纪念“宣传提纲”就指出,“五四”爱国运动的目的在于彻底打倒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纪念“五四”不仅能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也能使我们“更加仇恨中国人民的敌人,更加仇恨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也就更能加强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对于如何纪念“五四”,“宣传提纲”提出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继续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②《“五四”青年节宣传提纲》,《人民日报》1951年4月19日,第1 版。《光明日报》在“五四”纪念日的社论中也指出“五四”“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人民爱国运动的节日”,强调今天纪念“五四”,首先应该继续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精神,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③社论:《继续发扬“五四”爱国运动的精神》,《光明日报》1951年5月4日,第1 版。
中共在“五四”纪念日对“五四”反帝爱国意义的强调,将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一方面展现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爱国主义传统,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中国人民抗击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坚强决心。此时有与中国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抗美援朝、平定西藏叛乱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对第三世界国家反帝爱国运动的声援,如1960年中国对土耳其反对独裁统治和美帝国主义的声援。20世纪50年代,土耳其一直处于曼德列斯的统治下。曼德列斯政府得到美国的扶持,在内政外交上一直唯美国马首是瞻,在国内实行独裁统治。为反对独裁统治和美国对土耳其内政外交的干涉,1960年4月土耳其各大城市相继爆发大规模反对曼德列斯卖国独裁的爱国示威运动,要求结束曼德列斯的统治,遭到曼德列斯政府的血腥镇压。
在是年的“五四”纪念活动中,中国人民唤起对五四运动反帝爱国主义运动的记忆,将其作为声援土耳其反帝反独裁爱国运动的历史资源,并以此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全国各主要城市各界人民都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声援土耳其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中北京各界人民就有5 万多人。①《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十几个城市人民盛大集会》,《人民日报》1960年5月5日,第1 版。“五四”纪念日当天,《人民日报》在声援文章中回忆了41年前中国爆发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官僚卖国的五四爱国运动,其中北京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
反帝爱国是“五四”意义中一个重要面向,这一意义也使五四运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五四”纪念中被不断强调,成为中国人民唤起历史记忆、表达政治诉求的一个重要历史资源。不过,“五四”是一个意义丰富具有多重面向的历史符号,其意义不止“反帝”爱国一项,在此间的“五四”纪念中,“五四”的其他意义也被不断强调,成为可以利用的历史资源。
四 对“五四”“革命”传统的强调、意义扩展及运用
“五四”是一个具有众多面向的政治符号,也是一个不断为时人提供价值和意义支持的传统资源。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共将“五四”纪念日定位为“革命”的节日,将五四运动视为一场革命运动,赋予了“五四”强烈的“革命”意义,②参见周游《抗战时期中共对“五四”的纪念》,《中国文化研究》2019年第2 期,第7 页。“革命”也被中共视为五四运动的一个重要传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四”的“革命”传统仍然被不断强调,且被用在更为广泛的领域之中。
中共将五四运动视为一场革命运动,原因之一就在于五四运动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对五四运动的这一特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解放》1940年第98、99 期,第37 页。胡绳指出,五四运动这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是“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个最主要的优良传统。①胡绳:《五四文化运动中的革命精神》,《光明日报》1950年5月7日,第1 版。“五四”这种彻底的、不妥协的传统也被中国共产党称为“五四”的“革命”传统。
五四运动“革命”传统中所体现的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也被不断提及和运用,如上文中所论述的对“五四”反帝爱国意义的强调,就将“五四”的反帝爱国意义作为当时反对帝国主义的一种历史资源。“五四”的“革命”传统不只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精神,它还体现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突破和创造上,比如胡绳在谈论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时,就指出由于五四运动具有革命的彻底性,“当时的文化思想战线显得非常生动活泼,充满了勇敢的批判精神和大胆的创造精神”。②胡绳:《五四文化运动中的革命精神》,《光明日报》1950年5月7日,第1 版。
上面提及的反帝反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及创造与五四运动直接相关,将“五四”的“革命”传统与它们进行联结也是应有之义。不过,在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人民工作重心的转变、“革命”意义的不断扩展,“五四”“革命”传统的使用范围也不断扩展,“五四”“革命”传统中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精神也成为时人从事诸事时可资利用的一种普遍性精神资源。这样,此间的“五四”纪念中,倡导继承和发扬“五四”的“革命”传统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如上海市市长陈毅在1950年的“五四”纪念日讲话中,就一再勉励上海青年和青年团员发扬“五四”光荣的“革命”传统,坚持学习和坚守岗位,协助人民政府克服困难。③《热烈庆祝青年节 上海万余青年集会》,《人民日报》1950年5月6日,第3 版。1951年“五四”青年节,《解放日报》在社论中号召华东的广大青年继承五四运动的革命斗争传统,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新民主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④《继承“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社论),《解放日报》(外埠版)1951年5月4日,第1 张。196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五四”纪念大会上,吴玉章发表讲话,勉励青年们向革命前辈学习,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树雄心立大志。⑤《继承和发扬“五四”革命传统》,《光明日报》1962年5月5日,第1 版。
在以上三则史料中,“五四”“革命”传统中“彻底的、不妥协的”意义得以扩展,在“彻底的、不妥协的”意义的基础上,“五四”的“革命”传统意义衍生了面对困难时顽强拼搏、敢于胜利、团结进步等内容。而且,“五四”的“革命”传统意义从最初与之相关的政治、文化领域向经济、生活方面扩展,继承和发扬“五四”的“革命”传统也被运用在更多的方面,这在“大跃进”开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对“五四”“革命”传统的强调和运用,使“五四”的意义更加丰富多元,也使“五四”的“革命”意义突破政治、文化的界限,运用于经济、生活领域,成为一种能为更多人利用的普遍性的精神资源。
五 结语
“五四”是一个意义丰富且具有多重面向的政治符号,其重要性和复杂性也为人们提供了巨大的诠释空间,成为近代以来个人、学派和政党之间竞相诠解的政治资源。早期中共党人是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见证者之一,中共也是近代以来“五四”意义的主要诠解者,五四运动更是促进了中共的诞生和发展,因此,中共对“五四”的纪念格外重视,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作为执政党对“五四”的纪念更有意义。在民国时期,由于时代主题的变化,中共对“五四”的纪念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并不断赋予“五四”新意。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面临的国情与奋斗目标大为改变,对“五四”的纪念也体现出新的特征,如通过纪念活动建构“五四”记忆、凸显“五四”的“反帝”意义以表达政治诉求、强调和运用“五四”的“革命”传统使之成为一种普遍性可资利用的精神资源等。中共对“五四”的纪念、诠解和运用,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政治节日在新政权成立前后意义的变化及政治运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