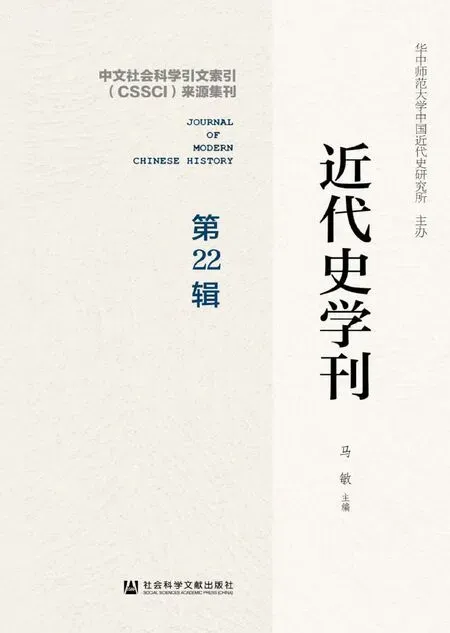冷战时代的文化反思
——1963年张君劢发起的五四科玄论战纪念
2020-04-13王志勇
王志勇
内容提要 科玄论战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历史回响不断,力图新的创获。1963年寓居美国的张君劢提议寓美学人撰文纪念科玄论战四十周年,得到谢扶雅、顾翊群、陈荣捷等人的热诚响应。身处异域的他们,结合战后世界的文化危机和思想困境,一方面批评西方文化的缺失,提倡中国智慧的价值,另一方面主张会通中西,为人类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这些新思考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由“倚门傍户”走向“思想独立”的自觉意识,见证了其建构“文化中国”的努力。
科玄论战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历史回响不断,力图新的创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存在两个世界,而非一个世界”。①〔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第32 页。英国学者丹皮尔在其新版《科学史》中写道:如果允许另一次大战发生,则科学在毁灭性武器方面的滥用,将使文化受到灾难性的威胁。②〔英〕W.C.丹皮尔:《科学史》,李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第486 页。美苏两极对抗加剧了这种文化焦虑,特别是1958年到1963年这几年,核危机频频爆发,威胁人类生存。③Jeremi Suri,Power and Protest:Global Revolution and the Rise of Dten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p.7.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20世纪后半期最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件,危机让人们警觉到核武器时代一个地区冲突可能导致整个人类毁灭的可怕未来图景。①〔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冷战》,翟强、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第81 页。在核威胁背景下,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再次成为思想界深思的课题。在西方,1959年英国学者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演讲,批评科学文化和非科学文化的分裂,引发持续争论。②〔英〕C.P.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三联书店,1994,第12—14 页。而在中国,继20世纪上半叶由“唯科学主义”走向“泛唯科学主义”之后,③〔美〕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第128 页。大陆地区陷入阶级斗争狂澜,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遭打击。港台地区,有一种力量继续在“全盘西化”路线上狂奔,甚至掀起与传统派之间新的“中西文化论战”。针对以上“世局”和“时局”,寓居海外的传统派知识分子对中国和世界文化的未来持续反思。1963年,科玄论战的最早发声者张君劢发起论战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得到谢扶雅、顾翊群、陈荣捷等学界名流的热诚响应,为四十年前的这场论战谱写了厚重的“续集”。鉴于这一发展尚未引起学界关注,本文拟对此纪念过程和文化论述略加梳理。
一 战后欧美思想界之危机与对立
科学主义与形而上学两大传统、两大思潮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始终。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使哲学回到了形而下的经验世界,自然科学的方法占领了哲学。此引起德国形而上学的复兴。康德对纯粹理性进行批判,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领域分别划定在经验、现象界和超验的自在之物,前者的方法是“先验分析论”,以认识论和逻辑学为中心;后者的方法是“先验辩证论”,以本体论和形而上学为中心。现代哲学就沿着这两个方向发展。现代哲学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潮背后,真正起支配作用的乃是科学与形而上学这两种传统的发展。而黑格尔则继康德之后,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哲学所特有的方法即辩证法。④陈锐:《西方思想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15—26 页。
近代以来,黑格尔玄学因科学勃兴而走向崩溃。科学技术非常发展之后,哲学与社会制度不能平衡发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共同趋势是科学主义的发展。精神上的失去重心,将欧洲和世界拖入两次世界大战。二战以后,西方文化问题已经演变为整个人类的文化问题。以上乃胡秋原对西方世界之观察。胡氏于1961年5月在台湾《民主潮》杂志连续刊文《由科玄之战论西洋文化危机》,其断言生命哲学与现象学推动了20世纪实存哲学的发展与玄学的复兴。二战前后盛极一时的数理逻辑、新实在论、批评实在论等哲学反对玄学,拥护经验论和科学主义,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实存哲学和逻辑实证论、分析哲学的对抗。1946年以来,西洋人正在反省之中努力克服科学主义,以求自身存在之理由和出路。历经二战灾难且面对冷战困境,在欧洲曾对人类前途无限乐观的威尔士提出“人类的灭绝”,A.韦伯宣布“欧洲时代已经终结”,各国大历史家同样感到“危机”。“危机论”日益传染美国,索罗金编《危机时代之社会学》、科赫女士编《危机时代之哲学》所谈都是“危机”,而彭涅特《此我之哲学》中所涉20个现存思想家大都谈“危机”。①胡秋原:《哲学与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第115—191 页。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到处弥漫着实用主义精神的美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特别是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一方面,冷战造成中西文化交流突然中断,50年代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中心,由此中国哲学的世界化运动转移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另一方面,不仅更多的学者开始涉足中国哲学研究,而且一改之前认定“秦汉之后无哲学”的态度,中国哲学研究的重心开始从先秦转向宋明。出现转折的原因除了新中国成立使得“中国学”意义越发突出之外,还在于寓美华人学者的大力推动。②崔玉军:《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41、93 页。但是,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哲学之价值在观点上颇有分歧甚或对立。1958年始,列文森开始出版其巨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认为人文主义的中国传统有悖于科学精神,只能成为博物馆中的收藏品。另一美国学者顾立雅则于1960年增订其1949年的著作《孔子其人其神》,改名为《孔子与中国之道》出版,称孔子的思想具有全世界全人类的重大意义。
时在美国掌教及著作者如张君劢、陈荣捷、梅贻宝、施友忠、柳无忌、谢扶雅等人,大量发表宋明形而上学的文章。③唐君毅编《儒学在世界论文集》,香港,东方人文学会,1969,第284 页。在战后美国,1958年张君劢出版英文著作《新儒家思想史》;1949—1963年陈荣捷出版有关中国哲学的英文著作11 种,其中包括856 页的《中国哲学资料汇编》,为西方研究中国哲学提供第一手资料;④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第110—111 页。1959—1966年著名哲学家方东美两次应邀赴美讲学,用优雅的英文向美国民众传播真实动人的“中国心灵”。①秦平:《方东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107 页。
罗素称:“哲学家们既是果,也是因。他们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②〔英〕罗素:《西方哲学史》,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第5 页。澎湃激荡的时代情势再次激起流寓美国的张君劢之时代责任感。李泽厚称科玄论战实质是“信仰和意识形态之争,是与选择何种社会改造方案联系在一起的”,③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第61—62 页。此实见道之论。在冷战高潮的时代环境中,此一特点和意义尤为突出和迫切。因此科玄论战四十周年之际,张君劢致函唐君毅试图发动海外学人再来一次论战,唐君毅复信称,科学和哲学各有范畴,“结论已经出来了,实不必将昔日之战火重新挑起”。④唐君毅:《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谈君劢先生的思想》,《传记文学》第28 卷第3 期,1976年3月1日。张氏乃力促友朋为文纪念,以引起新意见新讨论。同年春,台北《民主中国》即连续重刊当年张、丁二人的文章。⑤谢扶雅:《我所了解的君劢先生》,《传记文学》第28 卷第3 期,1976年3月1日。或许由于政治原因,张之促动在港台地区反应冷淡,寓居美国的华人学者陈荣捷、顾翊群、谢扶雅、方东美等人热诚响应。
由于青年时期曾留学欧美且长期寓居美国,张、陈、顾、谢、方诸人均对战后西方社会有深刻体认,同时深信中国传统价值。人生观论战的发起者张君劢早年于德国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乃现代新儒家中坚人物,于1952年由港赴美并长期居住在旧金山,并曾于1958年做环球讲学。⑥李贵忠:《张君劢年谱长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73—308 页。陈荣捷于1929年在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1936年由岭南大学赴美,先后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直至退休,被称为“北美大陆的儒家拓荒人”和“朱熹研究大家”。⑦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09—118 页。著名宗教思想家谢扶雅和陈荣捷不仅有哈佛同门之谊,还是岭南大学的同事。⑧崔玉军:《陈荣捷与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第214 页。1958年谢氏以哲理神学翻译专家身份由香港移居美国,主要研究康德哲学和中国伦理思想,与同在美国的张君劢有过密切交往。⑨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第20 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9,第344—357 页。顾翊群出身江苏淮安一学者家庭,自幼深受古典教育,青年留美,1946年起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至1966年退休。⑩顾翊群:《危机时代的中西文化》,台北,三民书局,1986,“序言”,第1—9 页。方东美为安徽桐城派方苞后人,自幼熟读中国经典,大学期间研究西方哲学,1921年与顾翊群同船赴美留学,三年时间完成硕士和博士论文后回国,早在1927年就完成了《科学哲学与人生》一书。①秦平:《方东美》,第46、48、60 页。以上诸人除张君劢为留德外,其他均为留美。因缘际会,20世纪60年代张、陈、顾、谢、方等学者会聚美利坚,凝成一“认同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科玄论战四十周年之际,在张君劢鼓荡之下此一身在异域的学者群基于共同的文化使命感而“以言行事”,推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探索人类摆脱时代困境的出路。
二 四十年来西方哲学之“折衷方案”
20年代的人生观论战可以说是张君劢一生的“心结”,此后他多次“回顾”此事。1933年人生观论战十周年之际,张氏在广西大学演讲《科学与哲学之携手》,鼓吹科学与玄学合起来才是“人类的全部智慧”。次年,张氏又于岭南大学演讲《人生观论战之回顾》,称应“知识与道德并重”,新思潮、新文化、新政治必须建立在“真善并重”的基础上。②张君劢:《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71、92 页。1963年,面对20世纪以来科学与哲学同样突飞猛进的形势,张君劢继续逐项批驳当年胡适的观点(胡氏已于1962年去世),坚称当年人生观演讲是“择善固守”。他从“以个人为本位者”、“以学派为本位者”和“存在主义”三方面梳理四十年来西方哲学之“折衷方案”,批评科学主义之偏颇与科玄对立之思维。
西方哲学以个人为本位者,怀特海、哈德门、雅斯贝尔斯为“20世纪哲学界之三杰”。怀氏以数学家物理学家而转入形上学,抛弃机械主义的“硬块宇宙说”而代之以“新宇宙观”,提出宇宙间所发生者“事”即一切遭逢(Happening),其特点为“动而不留”,可名之曰“流变力”;怀氏以“感应子”(Feeling)为世界之最后实在,此与程伊川“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有冥合之处。③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界之思想家(一)》,《人生》第27 卷第1 期,1963年11月16日。哈氏与怀氏同为“形上学之先锋”,他以事物、生命、心理、精神的“存在层构说”反对昔日之唯心论与唯物论,称前者以“最上层之精神”通澈“最下层之物质”,后者以“最下层之事物”强通“最上层之精神”,皆为“一偏之见”。雅氏则谓宇宙本体与人之生存为科学之所不问,生存之义高深幽远,惟有以灯光照之,是谓“生存照明”;宇宙大全与人之生存决非知识和定义所能把捉或穷究,人类经验之外的超越者——上帝决不能成为知识之对象,此与《中庸》“德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音无臭”之意相近。①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界之思想家(二)》,《人生》第27 卷第2 期,1963年12月1日。张氏指出:哈氏合事物、生命、心灵与精神四层而同称之为“实在”,乃清除唯心唯实二者间障碍之善法,为“折衷方案”之一种;怀氏以科学家出身,以哲学与形上学为裁判官批评数百年来科学家思想之错误,此乃“折衷方案”之又一种。
西方哲学以学派为本位者,包括英国新唯实主义与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派、实存主义。其中除逻辑实证论派主张以科学方法统一一切学术并排斥伦理学与形上学外,其他各人各派无一不走形上学之途径。新唯实主义学派以“善”为人生中最终本然之性,此正合于康德之“唯心伦理学”。实证主义的维也纳集团继承孔德“可实验者乃为真知识”的主张,视上帝、宇宙源始、道德问题为无意义,其在解决“科学为人生而存在”或“人生为科学而存在”问题之先,而斤斤于“有证验”与“无证验”之是非,不免本末倒置。②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界之思想家(二)》,《人生》第27 卷第2 期,1963年12月1日。现象学派代表人物胡塞尔超越主观元素与经验元素,谓知识之本在纯逻辑中之“理型”,其可于直观中得之;其反对心理主义之知识相对性,反对唯名主义“世间无共相,只有各个实物”的观点,主张“共相存于人之思想中而非实物世界中”,强调真理之绝对性,认“理性之共相”为真理和学问确立之前提;科学与学问皆为有“意向性”之“理型单位”,其中之“知情意”三者即为人类精神鹄的之所在;其以“损抑法”使“普遍的必然的固有的本质”自现于“纯自觉”中。现象学由“描写现象学”至“本质现象学”,最终发展为“超越现象学”,其认“纯自觉性或自我之绝对存在”为世界之最终实在,此与康德之“心为立法者”殊途归一。③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界之思想家(三)》,《人生》第27 卷第3 期,1963年12月16日。
张氏称存在主义为“三十年中欧洲最主要之思潮”,其在西欧引起“如安处室中者忽遭地震”之思想界大变动,故深论存在主义。其开创者克尔凯郭尔专以“反求诸个人之生存”为出发点,即所谓存在主义。克氏反普遍化而重个人、反客观而重主体性,因而其写作为个人日记、个人感想录,“与吾国宋明以来之语录与反省录相似,若其语涉人生之忧患令人趋于悲观,则与老庄之虚无而流为厌世者有相似之处”。其称真理即“其人本身之真理”,知识即“我何以生何以死之理念也”,其极类乎孟子“尽性知天”之“知”;其批评现代大众文化为“铲平运动”,即“铲平自己而丧失其所以为己”。海德格尔之《存在与时间》由比较“我存在”、“一狗存在”、“一石存在”、“一树存在”得人与物之存在与意义,其谓日常生活由“铲平运动”而来,为“我之物化”,属于“非真正生存”,而内心生活“脱去随班逐队之生活”为“真正生存”;其称“本其良心之昭示知所以抉择,而以一死了之者”乃可名之曰“死之意义”,此即孔孟所谓“杀身成仁”或“舍生取义”。海氏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度性”论人生之时间性与历史性,与吾国之谚“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此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以昨死回顾过去,以今生开始现在与未来”,殆“东西心同理同之见解”。①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界之思想家(三)》,《人生》第27 卷第3 期,1963年12月16日。
萨特著《存在与虚无》使存在主义成为法国社会之风尚,成为战后思想界与马克思主义、天主教、无神论并行之四大派之一。萨氏分世间之存在为“自封之存在”和“自展之存在”,前者为“呆然不动之宇宙”,后者惟人生而已,其能“有者无之,无者有之”;萨氏最称道自由,抬高自由为人生唯一准值,一概否定其他善美真之准值,不能不令人想起庄子与阮籍之“愤世绝俗”。马塞尔谓“人之存在于世界”为一种“具体境遇”,不能在抽象理论或概念中求之,而要超越环境接近上帝,惟有通过信仰、愿望、慈爱三种德性才能达于“存在之门”;其又谓“科学的思考”但有客观化,而生存主体归于消失,“哲学的思考”是透过见闻达于宇宙之奥秘。张氏认为,西方科学家以客观性为真理之唯一标准,存在主义以为入真理之堂奥者惟有以主体之体验为下手方法,则为“折衷方案”之又一种;中西交通以来每以科学公例为至宝,将宋明理学家之语录或反省录视为不足道,而存在主义起,从日记可知真理之所得,视其体验之是否真切,而不必以实验为唯一标准,此“折衷方案”之又一种。②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界之思想家(三)》,《人生》第27 卷第3 期,1963年12月16日。
基于人类生存与命运的重大关怀,张君劢梳理了西方哲学四十年的脉络。环绕着“真理与方法”,张氏讨论了真理的客观性与主体性、相对性与绝对性,以及得到真理的方法为“科学实验”抑或“个人体验”等问题;环绕着“本体与存在”,张氏讨论了唯心与唯物、知识与道德等问题,其结论为“折衷方案”。在此基础上张氏宣称:吾人处此世界大通之日,既不能不知人之长,以补己之缺,又不能失其自信,以出人裤下。因此,思想方面之知彼知己为东西交流时代不可或缺之工作。从事西方思想史者不可以一时代一学派一个人代表西方,而应将古今融会贯通,考求学派之对立者所以然之故,于对垒之中另求方案为“折衷之计”。因此,中国人无法亦不可追随西方哲学界四十年之变迁而“倚门傍户”,而应因他人思想变动透露问题之中,承受孔孟周程张朱陆王以来之遗产,毅然宣告思想独立之为得。①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四十年来西方哲学界之思想家(三)》,《人生》第27 卷第3 期,1963年12月16日。张氏观点可谓一种“会通古今中西”的文化观和方法论。
三 现代西方文化之“走向偏锋”
从60年代起,顾翊群就大量撰文讨论中西文化问题。1961年顾氏在台湾发表演讲称,西方与中国道路不同,西方拿着“科学的钥匙”往大同路上走,与中国《礼运·大同篇》追求的道德社会不同,此思想问题背后还是哲学或玄学的问题。哲学上的实证主义等“硬心肠的宗派”和道德主义等“软心肠的宗派”各有道理,不应以偏概全,如果走到偏锋,就不是人类之福。西方危机就在科学主义的“霸道”。顾氏又称,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精神,不能有了新学问就放弃旧学问。沃格林(E.Voegelin)提出的“以道德为体,以科学为用”,表明归根结底人类社会应以道德伦理为基础。因此,把中国儒家的道理向全人类发挥,可以补救西方文化的缺点。人类的情与理必须融合,儒学的中庸之道传统正是死守善道。总之,西方社会仍需“将偏锋改为中道”。②顾翊群:《危机时代的中西文化》,第1—21 页。1963年春顾翊群撰文称,西方数十年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无可讳言地使世界危机日益增加,对科学主义之迷信将引致自由社会与科学自身之毁灭。经过两次大战之后,“万古常新之哲学”即自然法思想乃重被尊重。惩治战犯之暴行、禁止消灭种族公约、人权宣言等,只有自然法方为其最允当之根据。因此,应当努力奉行儒家传统与西方之自然法传统,际此太空时代,原子战争随时可以爆发,惟此东西两大哲学之重振方可克制。新儒家哲学之重振与新士林派哲学之光大,为20世纪之重大事件。此两大学派同以重行达到“干枯的传统主义”与“无耐性之进步主义”之“适度的均衡”为目的。①顾翊群:《对张君劢先生治哲学经过之观察》,《人生》第26 卷第1 期,1963年4月16日。
顾氏称无人反对科学的“利用厚生”,自然科学方法仍有需要应用于对“人”的某种研究中,但将科学主义作为“信仰”应当反对。科学主义传统的远源是古希腊衰世兴起之“智者”诡辩派,其相信无神论的“人本主义”、轻道德而重功利,其驳斥苏格拉底之尊重天道,主张“理性之人性说”。此传统流传至今,其预言应用“科学方法”于社会之组织便可为“直线式上升的进步”,从而否定人之有尊严与存在之理由。欧美“社会人文学者”和“科学人文主义者”均以自然科学方法为研究之张本,认人类社会可望得科学方法之助而不断进步,认神学为迷信,变哲学为科学之附庸,抛弃自古相传之自然法亦即中国之“天道”等公共哲学。在政治科学领域,“伪自由主义者”迷信科学主义、进步主义,妄图不要道德之超拔人性而达世界大同之秩序,其已遭到沃格林之驳斥;凯尔森(Hans Kelsen)鼓吹之“世俗的民主社会”,以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世俗主义否定宗教的玄理的真理,已遭士林派哲学大师马理唐之驳斥,马氏反复申言民主社会必须为一道德秩序,称他们忘记了华盛顿在退休讲词中曾指出,宗教与道德是美国立国的两大支柱。西方文化百余年来之偏锋进展造成了“霸道世界”与“自我人性毁灭”,其贪权爱财好色与争斗之心将愈进步而愈增加。现代人类对世事演变之无法控制,亦类于乘客对飞奔的汽车之束手无策,此恰似“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②顾翊群:《科学与玄学的人生观论战之进一步检讨(上)》,《人生》第26 卷第6 期,1963年8月1日。
斯诺的“科学文化派”和美国的“行为科学家”、“社会工程师”均为无神论世俗主义者,科学主义仍为美国知识分子的中坚思想。进步主义诺斯士派以全力在尘世推进物质文明,遂与精神生活日益暌违。斯金纳迷信的“科学家之饱和点”可使人类进入之“后现代之世界”,不可能是“极乐园”,而只能是“勇敢新世界”或“1984年之世界”。台湾若干学子之不良习尚,至少部分应归咎于对“美国化”之醉心。治本之方在于恢复古代之精神传统,纠正现代不良思想。盖必全世界人类均能自愿遵行“中庸之道”以节制修身,重礼让而退竞争,尚仁义而鄙功利,真正的大同世界方能实现。因此,人类之命运能否挽回,关键在于迷信科学主义之“伪自由主义者”和“现代诺斯士主义者”能否转向。人之存在于生命世界为时悠久,人类不能等待科学降世,方始设法企求得到人生存在之意义。人类社会不应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而被研究,而应作为“一种充满意义之小宇宙”,在后者中之人类运用各种符号,以求自我实现。人类不能徒恃面包以生存,而必须求过一真美善圣之生活。当时,费正清氏在《美国与中国》中称孔子思想是“古今管制思想之最有成果者”,并谓《大学》的“八目”与逻辑不合,加州大学教授艾伯哈特氏在其《中国历史》中称王阳明直觉的心学为“法西斯思想”。顾氏称二人为敌视中国文化的“相对主义世俗主义的诺斯士派信徒”,其观点为“怪论”。①顾翊群:《科学与玄学的人生观论战之进一步检讨(下)》,《人生》第26 卷第7 期,1963年8月16日。
若科学与人文应当融合,又当如何融合呢?科玄论战四十周年前后,因胡适在台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讲演而引发中西文化论战,台当局重印蒋介石30年代出版之《科学的学庸》以应对,时张其昀(曾任台当局“宣传部长”、“教育部长”)在《中央日报》刊发《新儒学运动》一文,援用了“科学的人文主义”一词。顾翊群主张修正此概念,因其经杜威等科学主义者滥用后,已变为“人定胜天”之现代反儒学之西方“伪自由主义者”之信条,而与中国自尧舜周孔以下之“儒家人文主义”内容不同。故可改为“天理的人文主义”或“中庸的人文主义”,儒家之“天人合一”即西方之“超越与内在合一”。主办《人生》杂志的王道致函顾氏称,依儒家观点只能以道德统摄科学而非相反。今若以科学统摄人文,使新儒学成为科学之上的科学主义,实为本末体用之大颠倒。②顾翊群:《谈“科学的人文主义”》,《人生》第27 卷第11 期,1964年4月16日。
1964年夏,第四届东西方哲学家会议在夏威夷大学召开,陈荣捷、方东美、梅贻宝等12 位中国哲学家与会,方东美以渊博学养、无碍辩才和禅宗机锋回击英国芬里教授对中国哲学的挑战,语惊四座,大放异彩。③秦平:《方东美》,第114—116 页。方东美在其会议论文《中国形上学中之宇宙与个人》中称,西方的“超自然的形上学”将人与其所居处之宇宙“剖成两橛”,在天堂地狱之间也“划下鸿沟”,人之灵肉两者“冲突不已”;中国之“超越形上学”植根现实世界又腾冲超拔,趋入崇高理想的胜境而点化现实,它摒弃了单纯二分法,更否认“二元论”为真理。方东美会通儒道释三家哲学称,中国哲学之玄想妙悟方式比科学解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认现实世界当点化为理想形态,纳于至善完美之最高价值统会。①方东美:《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中华书局,2013,第235—262 页。
四 人类文化之出路乃“中庸之道”
1963年谢扶雅热情响应张君劢的邀请,从伦理学角度提出“新唯中论”的人生观。其文《新唯中论与“两希”》分载于香港《大学生活》、《祖国周刊》和美国《海外论坛》,称中国固有哲学为“中立的唯中论”,新唯中论是“吸收西方近代各学派之长而扬弃其极端之处的综合哲学”。②谢扶雅:《新唯中论与“两希”》,《祖国周刊》第41 卷第6 期,1963年2月4日。同年夏他详论“新唯中论的人生观”,盛赞孔子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人生智慧。包办不知以为知是一个极端,全面怀疑论是另一个极端,故代表中国正统哲学的孔子是一个“道地的中立主义者”。③谢扶雅:《新唯中论的人生观》,《祖国周刊》第43 卷第1 期,1963年7月1日。
对于新兴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瞬间永恒而与上帝相交”等高度浪漫主观的人生哲学,新唯中论者暂取保留态度,对于现代流行逻辑实证论者所主张的道德相对性,也觉其有不充足处。习俗道德固然因时因地而变迁,但道德原则如中国经籍中所见的仁义忠孝等,自有其不易性和经常性。谢氏以“孝”论证人对世界的使命。在儒家“继往开来”的人生理想下,孝是人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职责。人一出生不单与亲生父母发生直接关系,并且沐浴在过去一切传递下来的世界文化总遗产之中,最适宜的答报莫过于把这所熏陶的文化加以增殖、发展、改进、新创,这种伦理行为就可称为“孝”,故孝道乃是孝于世界文化,而不仅是善修其身以图光宗耀祖了。新唯中论者在政治上服膺民主自由的世界潮流,“从容中道”的儒家既不赞成老庄一流极端放任的无政府主义,又反对法家严刑峻法的君权专制主义。④谢扶雅:《新唯中论的人生观》,《祖国周刊》第43 卷第1 期,1963年7月1日。
谢氏反对西方哲学中浪漫主义与实证主义、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壁垒”。他认为中国固有哲学可以称作“唯中论”,孔子的“中庸”就是“唯中论的人生观”,而“新唯中论的人生观”是折衷于欧陆理想主义与英美经验主义的一种创造的综合。但唯中论不是调停双方的和事佬论调,不是机械的折半,不是妥协的调和,更不是尼赫鲁式的国际政治上的中立主义。《礼记》说“中立而不倚,强哉矫!”此“中立”是卓然独立之义,绝不致误会为投机取巧。“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所谓“用中”即是掌握左右两派而超过他们。因此,中国应尽量输入西方历代左右两大源流,而从双方壁垒打将出去,特立独行地创造新唯中论的哲学,以贡献于世界学术文化之林。①谢扶雅:《人生观论战四十周年书感》,《人生》第27 卷第1 期,1963年11月16日。
谢氏以“仁”释“中”。孔子的“仁”与基督教的“爱”、希腊正统哲学中的“知即是德,德即是福”之说相通。“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的命意所在就是“中”。仁是人我兼顾而衡平的,仁而太过就成兼爱,仁而不及则为自私。要之,孔子思想是彻头彻尾的人本主义,不偏于希腊系统的自然主义,亦不偏于希伯来系的超自然主义。仁是立、达,是实践行为,不专倚于希腊系之“为知识而知识”。谢氏又称孔子若在今日必然十分拥护科学,且具适当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经验,因仁不属于“宗教性的哲学”,也绝无浪漫主义色彩。孔学虽无逻辑实证论,但《春秋》可作独特的“语意学”读,《正名》更包括了形式逻辑的基本法则。谢氏提出“复归孔子,超越孔子,学习西方,超越西方”。逻辑实证论置重点于逻辑,实存主义则置重点于玄学,孔子把重心放在伦理上,尤其是实践的人格上,实存、实证、实践,大可以说现代世界思想的鼎足而三。实践本身是中国儒家的本香本色,实践人格的仁本是“从容中道”。但自孟子略右、荀子略左以后,忽然转成汉学的训诂与谶纬,皆远离乎实践。魏晋玄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更无不驰向论证体系,致不免忽视了进香修道的主人。所以中国必先“复归孔子”,由返孔而超孔,自然也就超越西方的两大壁垒了。②谢扶雅:《人生观论战四十周年书感》,《人生》第27 卷第1 期,1963年11月16日。
陈荣捷支持谢氏观点并做了进一步的阐发。陈氏称“仁”为“儒家哲学之中心”、“中国哲学之中心”,而孔子将“仁”由“诸德之一”发展为“诸德之全”,是“破天荒”的绝大贡献。孔子之前的文献中“仁”字均不多见,而“仁”为孔子谈论最多之主题,其在《论语》中被提及的次数远超孝、悌、天、礼等字,孔子之重视“仁”德为“不磨之事实”。孔子所论之“仁”为包含诸德之普遍道德,为知勇诸德之根据以及“中国道德思想得立永久之基础”。但由于西方思想界对“仁”存在误解,必须扩展到宋明理学以释仁,呼应和推动战后西方思想界对仁的研究的新开展。因此,陈氏从全德之仁、以爱言仁、博爱之谓仁、仁即性即理与理一分殊、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与生生、心之德爱之理等七个方面诠释仁。①陈荣捷:《仁的观念之开展与欧美之诠释》,唐君毅编 《儒学在世界论文集》,第271—283 页。当时纪念人生观论战和张君劢八十寿辰的论文合为《儒学在世界论文集》,其“序言”宣称:儒学之在今日,非特关乎中华国运,且亦与世界前途有密切关系。盖孔子非特吾人之孔子,且亦为全人类之孔子,其世界性意义早已溢出国族范围。②唐君毅编《儒学在世界论文集》,第1—2 页。
五 结论
二战之后情势大变,在两极对垒的世局和两岸分治的时局中,张君劢等寓美传统派知识分子“以言行事”,通过对科学论战四十周年的纪念与反思,以思想回应时代,以“人能弘道”的精神,批判当时流行的“进步主义”与“科学主义”,并高倡回归传统。对科学与哲学、传统与现代及中西文化关系等“旧话重提”之外,又论及本体论、存在论、真理与方法、政治与道德、知识与价值等问题,其论域在广度和深度上对四十年前均大大超越,其呈现如下特点。
其一,会通中西,毅然走向思想独立。在当年“事事趋新趋西”的时代,论战实际是日耳曼理想主义与英美经验主义的“西西之战”。劳干指称张君劢当时是“追随时尚”。③劳干:《记张君劢先生并述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影响》,《传记文学》第29 卷第3 期,1976年9月。罗志田也指出,在进步论笼罩之下双方具有“比赛更新更西”的明显倾向,张的态度明显“尊西趋新”。④罗志田:《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看后“五四”时期对“五四”基本理念的反思》,《历史研究》1999年第3 期。四十年后时移势易,顾翊群批判西方文化“走向偏锋”,张君劢、谢扶雅、陈荣捷都更多关注到西方哲学中与中国固有哲学的相通之处,并特别提出会通儒家传统与西方自然法传统以救世,最终高倡中国传统。科玄论战当事人张君劢不仅关注了二战后西方存在主义之最新进展,且由当年醉心倭伊铿而重新发现康德之价值,更明确提出反对“倚门傍户”,追求“思想独立”,致力于“濯去旧见,以来新意”,表明其对四十年前的反思与修正,纵然其思维仍有中西互释的痕迹。其二,在“对立”中为人类文化指点出路,求“为万世开太平”。身处核武时代,心忧世局,面对两极对垒、中西之争、阶级对抗、种族冲突等众多“对立”,恐怕惟有“中庸之道”才是缓解海外知识分子乃至人类内心焦虑和紧张的可行方案。其三,回归“中庸之道”,求“为往圣继绝学”。顾翊群立足历史与现实批判西方文化之“走向偏锋”,重在“破旧”;张君劢观照西方现代哲学之“折衷方案”,重在“理势”;谢扶雅“以仁释中”,提出“新唯中论”的人生观,重在“立新”;陈荣捷则将“仁”的概念从孔子拓展至宋明理学,重在“拓新”;方东美亦在美到处阐释和传播至善完美的“中国心灵”和“东方智慧”,重在“布新”。其四,关于思想史的本质,柯林武德谓思想是“对局势的回应”,洛夫乔伊谓思想是观念之“存在巨链”。由此观之,张君劢等居美诸学者对科玄论战的纪念无疑受激于冷战世局及中国时局,对科玄关系及中西文化问题的讨论攸关人类“生活方式”与“社会改造方案”的选择。同时,从其主张回归“中庸之道”并阐释“仁”之观念来看,他们的思想亦确实循着古老的传统在回答人类的“永恒问题”,体现了观念之“存在巨链”。质言之,人类思想是“回应局势”和“存在巨链”的融合之物。“中庸之道”既是“应世变”以从科玄之争、中西之争、意识形态及制度对抗等“对垒”中打将出去,亦于对“仁”、“中庸”等观念的诠释中汇入人类观念的“存在巨链”。
以上旅居美国诸学者,其学术进路虽有历史与现实、伦理学与宗教、哲学等区别,甚或其学术观点亦有某些分歧,但其“会通古今中西”为中国文化争地位、为人类文化找出路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的论述已形成一“破旧立新”、“旧邦新命”的完整逻辑,其共通共融共识之处在于“极高明而道中庸”。身处一个欧美崇尚科学主义、台湾醉心美国主义、香港弥漫殖民主义的时代氛围中,他们在西方文化的中心地带提倡“中庸之道”和“中国智慧”,表现出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为重建儒家人文精神及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当然,回向传统并非“发思古之幽”,而是为了更好地应对现实,指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