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论吐鲁番晋唐墓出土衣物疏所见之“偃明”
2020-03-25朱智立
朱智立
197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晋唐墓地中发现了一座编号为TAM383 的古墓,该墓出土的《沮渠武宣王夫人彭氏衣物疏》具有重要价值,疏中记录的随葬品有二字作,该墓发掘简报公布衣物疏释文时未释出前一个字①吐鲁番地区文物保管所:《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文物》1994年第9期,第77页。。简报发表后,日本学者小田义久以专文围绕该衣物疏展开讨论,但亦未能识别二字中的前字②[日]小田义久:《吐鲁番出土沮渠蒙逊夫人彭氏随葬衣物疏について》,《龍谷大学論集》第446号,1995年,第165頁。。其后发掘者柳洪亮在其《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一书中收录该衣物疏,并将此二字释作“柩明(铭)”③柳洪亮:《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2页。。其后的研究者如吴娅娅、稻田奈津子等人均沿袭柳洪亮的释读④吴娅娅:《吐鲁番出土衣物疏辑录及所记名物词汇释》,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21页;[日]稻田奈津子:《納棺埋葬儀礼の復元的考察―トゥルファン出土随葬衣物疏を中心に》,载佐藤信主编:《律令制と古代国家》,东京:吉川弘文館,2018年,第462頁。。笔者基于同类衣物疏文字的比较,参考历史文献记载,认为彭氏衣物疏中的这件器物应作“偃明”,或与两汉时期的丧葬用品“温明”相关。
一、随葬衣物疏中所见“偃明”
据发掘简报,彭氏墓为斜坡墓道土洞墓,早年经严重盗扰,发掘时墓室内棺木散落,随葬品所剩无几。该衣物疏卷首残缺,现存38行,内容基本是随葬品清单。从行文风格看,此件属于吐鲁番随葬衣物疏中的早期类型⑤侯灿:《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综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4 期,第35 页;刘安志:《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载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2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8页。。为便于论述,现将衣物疏随葬品中与“偃明”的讨论相关的部分依据图片迻录于下。
30 故帛练蓐(褥)一枚池缘自副
31 故竹蕈一枚缘自副
32 故疏一枚
33 故灵床一枚□自副①此行中符号代表疏中文字已无法识别。
34 故白木棺一口偃明里钉自副
35 大凉承平十年岁在戊戌十二月庚子朔
36 十八日丁巳大且渠武宣王夫人彭谨条
37 随身衣被杂物衣物疏所止经过
38 不得留难急急如律令②衣物疏释文参考前引稻田奈津子论文,见《律令制と古代国家》,第462頁。疏中第34行的“偃明”二字是笔者依己见所改。
疏中“明”字的释读并无疑问,但它是读如本字还是通假则由前字决定。“偃”字在衣物疏中的写法如图所示,检索汉唐时期敦煌地区的“偃”的异体字比对后可知(图1),疏中该字无疑是“偃”而非前人所释之“柩”字。由此可知彭氏衣物疏所记的两字实为“偃明”。

图1 “偃”字字例对比
在彭氏衣物疏之外,笔者在吐鲁番出土的随葬衣物疏中还发现三则与“偃明”相关的材料,其字迹与格式亦可资佐证,现亦将释文附于下:
(1)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高昌延昌二年长史孝寅随葬衣物疏》(72TAM170:88)①该墓虽经发掘,发掘简报中未见具体描述,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 期(合刊)。衣物疏所记“长史孝寅”即同墓所出墓表中的“张洪”,其人生前为高昌国中高级官员,见侯灿、吴美琳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上,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第78~80页。
释文:

②该符号代表此后内容因文书残缺已无法识别,下同。
(后略)
(2)阿斯塔那墓地出土《高昌重光二年张头子随葬衣物疏》(73TAM116:19)③该墓虽经发掘,发掘简报中未见具体描述。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发掘简报》,《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衣物疏所记“张头子”即同墓所出墓表中的“张洪震”,其人生前为高昌国中高级官员,见侯灿、吴美琳著:《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上,第332~333页。
释文:
2 鸡鸣枕一枚 朱衣笼一具 金刀子一枚 石恢(灰)三斛 五
3 谷具《孝经》一弓(卷)手把一双 攀天系万万九千丈
4 偃鸣一枚 白绫褶袴二具 锦被辱(褥)二具 臈(臘)钱十四
5 枚 锡人﹝一﹞具 金钱一万文 银钱二万 被锦一千张
6 杂色绫各五百匹 右上所条悉是平存所用之
7 物宜向遐龄永保难重光二年辛巳岁大德
(后略)
(3)吐鲁番木纳尔墓地出土《唐显庆元年宋武欢移文》(04TMM102:15)④吐鲁番文物局等:《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69页。移文主人“宋武欢”据同墓所出墓表可知其属于高昌国官宦世家宋氏家族,生前为高昌国中级官员,参见侯灿:《麴氏高昌王国官制研究》,载氏著《高昌楼兰研究论集》,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6页。
释文:
1 移文 脚靡一具 脚赦一枚 穴(靴)艮(跟)里一具 根袴一具 汗
2 衫一领 朱衣笼管(冠)具 白绫褶袴十具 紫绫褶袴十
3 具 白练衫袴十具 白银朱带二具 锦被蓐(褥)三具 被
4 锦一千张 杂色绫练各一千段 布畳一千疋 金钱一万文
5 银钱二万文 金刀子具 牛羊一千头 奴婢十具 金眼
6 笼具 燕明一枚《孝经》一卷 笔研(砚)具 石灰三斛 五谷
7 具 鸡鸣一枚 玉坠一双 耳抱具 攀天系(丝)万万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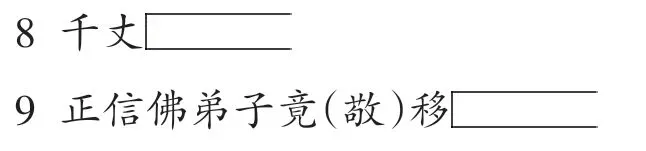
(后略)
长史孝寅衣物疏中的“偃明”无需赘述。张头子衣物疏中的“偃”后接“鸣”,鸣的中古音为明母耕韵,明则是明母庚韵,二者发音基本一致①[美]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356页。,因此这里的“鸣”通“明”字。宋武欢移文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同音互换现象,“燕明”中“燕”的中古音为影母元韵,而“偃”亦为影母元韵,彼时二字的发音一样②[美]李珍华、周长楫编撰:《汉字古今音表》,第211、218页。。
以上四则材料证明,吐鲁番地区的衣物疏中确实出现了一种名为“偃明”的物品,并且这种使用“偃明”的葬俗从北凉一直延续到了唐西州时期,亦足见汉人大族主导下的高昌社会与文化的稳定。
二、衣物疏所示“偃明”的性质
吐鲁番晋唐墓葬中出土的衣物疏在条列名物时有较为固定的格式,衣物疏的第一部分是随葬品清单,清单中的物品则基本按类别陈列,一般而言丧葬用品(主要指明器和葬具)都被集中置于清单最后,该类中会出现数量夸张的物品,与前一类“平生所用”衣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与分隔。丧葬用品之后就是第二部分的葬年、墓主和发愿文等内容。因此,通过对以上四件衣物疏中“偃明”周围物品的分析,我们能够初步确定它的性质。
首先,我们来看年代最早的彭氏衣物疏。“偃明”出现在38 行中的第34 行,行首是“白木棺一口”,行末“自副”二字是吐鲁番地区随葬衣物疏的惯用词之一,可理解为“前件物品所自带”之义,因此与“木棺”同在一行的“偃明里钉”即为棺附带的内容。这四字本有两种理解方式,其一:“偃明”和“里钉”同为棺自带的物品,二者为并列关系;其二:“偃明”被钉在棺里,“钉”是动词,“里钉”一词作为后置状语补充说明偃明的状态。笔者以为第一种解释更合理。该衣物疏内另有两处使用了“(某物)里X 自副”的格式,分别是“……里带自副”与“……里缘自副”(见图1),这里“带”与“缘”均为名词,所以“偃明”后的“钉”作为动词使用的可能性很小。同时,参考《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中“棺材一口”后单列出“干钉五枚”和《前凉姑臧郭富贵衣物疏》中“横栢棺一口”后单列出“铁钉五枚”的先例可知①史树青:《晋周芳命妻潘氏衣物疏》,《考古通讯》1956年第2 期,第96~97 页;张立东:《美国麦克林氏藏前凉姑臧郭富贵衣物疏》,《西域研究》2017年第2期,第86页。,“钉”在衣物疏内亦可单独作为一件随葬器物。至于第一种理解方式中“钉”究竟是何物,笔者以为或可参考《礼记·丧大记》中“君里棺用朱、绿,用杂金鐕。大夫里棺用玄、绿,用牛骨鐕”的记载,该条孔颖达注云“鐕,钉也。旧说云:用金钉,又用象牙钉,杂之以琢朱、绿著棺也”②(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四十四《丧大记》第二十二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181页。,据此可知先秦时这种特制的钉是装饰高等级棺木内部的一种葬具。降至汉晋,出现在衣物疏内的“里钉”也许正是“里棺”所用“鐕”的延续。因此,“偃明”与“里钉”之间应有分隔,“偃明”被钉在棺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通过彭氏衣物疏可知,“偃明”是一种真实随葬的葬具或明器,可能是棺材的组合器物。
再看另外三则材料,长史孝寅衣物疏的第4行开始出现数量严重失实的随葬品,这也就意味着从此行往后进入了丧葬用品的部分。第7行“偃明”后的“扳天”与后一行开头的“千三千三百丈”相连,可知其为“攀天丝”的讹写③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新考(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20~21页。。“攀天丝”象征升天阶梯,是高昌衣物疏中极为常见的明器④陈国灿:《从葬仪看道教“天神”观在高昌国的流行》,载《陈国灿吐鲁番敦煌出土文献史事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9页;刘安志:《吐鲁番所出衣物疏研究二题》,第155页。。
张头子衣物疏中第2 行的“鸡鸣枕”和“朱衣笼(冠)”均是高昌地区常见的葬具,“石灰”和“五谷”则是具有祛秽辟邪等功能的丧葬用品⑤韩香:《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石灰”探析——兼谈其在古代高昌地区的运用》,《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期。。第3行的“《孝经》”根据吐鲁番其他墓葬出土实物来看也应是指随葬的《孝经》抄本,其本身并非明器,但其经过汉代以来长期、广泛的推崇与神化,已经具备了近似宗教经典的神秘力量,因此被赋予明器的意义而随葬⑥刘昭瑞:《关于吐鲁番出土随葬衣物疏的几个问题》,《敦煌研究》1993年第3 期,第66~68 页;薛宗正:《以儒学为主体的高昌汉文化》,《新疆文物》1989年第1 期,第38~41 页;董永强:《唐代西州百姓陪葬〈孝经〉习俗考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第17页。。“手把一双”显是中原地区传入的手握具,“攀天丝”上文已提及,随后就是第4 行的“偃鸣(明)”,其后的两具“白绫褶袴”是白绫所做的衣裤,而两具“锦被褥”则与简报中所描述的“锦缘绢里麻里褥”相对应⑦《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发掘简报》,第172页。。73TAM116是一座夫妻合葬墓⑧该墓出土了《义和元年张头子妻孟氏墓表》,见简报第174页。,两具葬具的数量恰好能与尸身对应,可知这两种物品分别为殓服和覆尸所用被褥。十四枚“臈(锡)钱”和“锡人”显然是明器⑨陆娟娟:《吐鲁番出土文书语言研究》,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73~174页。,而一万文“金钱”和二万文“银钱”也绝非实际随葬的金银币,一千张“被锦”和五百匹“杂色绫”亦然。
宋武欢移文中从第4行开始随葬品数量出现了不合理的夸张,第5行的“银钱”“牛羊”“奴婢”均是明器,第6行“燕(偃)明”前的“金眼笼”是形似眼罩的葬具⑩陆锡兴:《吐鲁番眼笼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1期。,“《孝经》”“石灰”的性质亦无需赘述。
通过这四则衣物疏的解读,我们能够确定偃明是一种丧葬用品。“偃明”被单独列出的这一现象表明,偃明虽与棺有联系,却并非棺自身固有的组成部分,而是一件独立于棺木而存在的物品。但其究竟为葬具或明器,仅凭衣物疏尚无法确定。
三、衣物疏所见“偃明”与出土遗物的对比
在墓葬未经盗扰的情况下,衣物疏中真实存在的物品往往能够在墓室内找到对应的实物,偃明就属于该类。为了找到与偃明对应的实物,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回到衣物疏所处的墓葬中。
据79TAM383发掘简报推测,彭氏墓中葬具组合从下到上为生土棺床-苇席-木棺,遗憾的是墓中仅剩“残碎成66块”的大小不一的木板,其中只有小腰能够辨识①《吐鲁番北凉武宣王沮渠蒙逊夫人彭氏墓》,第75页。。墓内遗物共15件,尚未在衣物疏中找到对应名称的明器只有一件残缺的绢画碎片(79TAM383:5),简报中推测它是伏羲女娲画像的残件②这一点有待商榷,目前吐鲁番地区出土伏羲女娲画像的墓葬年代无一例外都在麴氏高昌以后,这一件出现在北凉时期的墓葬中,是孤例。。
长史孝寅衣物疏所在的72TAM170缺少具体的描述,葬具不明,大多数遗物未见记录。简报的《出土器物统计表》中有一件未在衣物疏中发现对应名称的明器,乃一件木雕的鸭俑(72TAM170:108)③《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次发掘简报》,第141页。。同样,张头子衣物疏所在的73TAM116 也缺少具体的墓葬描述,也有一件木雕鸭俑(73TAM116:6)④《阿斯塔那古墓群第十一次发掘简报》,第171页。。此类木鸭在吐鲁番地区麴氏高昌时期墓葬中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明器,至今没有确定器名。
宋武欢移文出土于吐鲁番的木纳尔墓地04TMM102 中,该墓在报告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墓葬已遭严重盗扰,葬具仅余骨架下的苇席残片,随葬品中未在衣物疏内发现对应名称的明器为两件木鸭(M102:5、M102:37)和一片基本残缺的伏羲女娲绢画(M102:36)⑤《吐鲁番晋唐墓地:交河沟西、木纳尔、巴达木发掘报告》,第65、66、75页。。
根据残留遗物和衣物疏的对照可知,墓内有可能对应偃明的有两种物品:木雕鸭俑和伏羲女娲绢画。从字面义出发,则伏羲女娲画像中两神怀抱或手持日、月的造型或与偃明的‘明’字有关。但同时,考虑到木鸭的形象,也不能完全排除“偃明”乃“偃鸣”之讹的可能。观察两物在墓葬中所处位置,一般以木钉挂在墓壁上的伏羲女娲画像也有被置于棺上或棺内的情况,这或许能与彭氏衣物疏所记的“自副”相对应,而木鸭则未见与棺作为组合同出的案例。尽管此两物与偃明都有某种意义上的对应,但二者数量与偃明不合。04TMM102 出土了两件木鸭,与宋武欢移文中的偃明数量不符,可知木鸭并非偃明。在出土随葬衣物疏的墓葬中,64TAM31⑥该墓在简报中未见记录,参考鲁礼鹏:《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墓葬登记表》,《新疆文物》2000年第3-4期合刊,第220页。、66TAM48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第12页。、86TAM386⑧吐鲁番地区文管所:《1986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发掘简报》,第145页。三座墓内均有绢画出土⑨同时出土绢画和衣物疏的墓葬还有59TAM303、59TAM301、59TAM302、73TAM524,但这四座墓中的衣物疏在随葬品清单部分均有部分缺失,出于谨慎考虑,不作为证据。,但其衣物疏中却并无偃明,这能够证明伏羲女娲绢画也非偃明。
王启涛曾提出,偃明可能是“一种枕头,形似月亮”,并认为其与吐鲁番出土衣物疏中作为“鸡鸣枕”省称的“鸡鸣”有关⑩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书词语考释》,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661~662页。。然而鸡鸣枕本身即为形似弯月的枕头,大量出现在衣物疏中,其使用贯穿晋唐时期的吐鲁番墓葬。在此前提下,笔者以为彼时高昌人并无必要另外使用一种与鸡鸣枕形状、功能几乎相同的葬具。
不论是已腐朽无痕或是已被盗,目前可以确定,在吐鲁番的墓葬中已无法找到能够与偃明相对应的实物。若欲一探究竟,我们或许应该在文献中寻找线索。
四、文献所见“偃明”
今本《后汉书》后所附《续汉书·礼仪志》中有一则记述东汉皇帝所用葬具的材料,此处出现了“偃月”一词,与“偃明”一名颇为相近:
登遐……小敛如礼。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月,牙桧梓宫如故事。①(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志第六,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3141~3142页。
据中华书局版点校者的理解和句读,此处的“偃月”是“东园秘器”表面的一类图案,并以现今通行的“半月”之义解释。然而,这样的理解会使得该图案与前文的“月”图案相冲突,因为在一件彩绘棺上同时绘制两种形式的月象显然并无必要,且目前出土遗物中也未见如此做法。以实物证之,就笔者管见,迄今为止除马王堆一号墓出土帛画上的月象作月牙形这一孤例以外,汉代墓葬图像中的月象一般皆为圆月,且往往在月轮中绘具象化的蟾蜍以象征月精。换言之,偃月图案在当时既不通行,也不实用。故而可以推断,材料中的“偃月”二字是不合理的。
笔者在《太平御览》卷五四五《礼仪部》二四“丧记”条下发现了与上引文献几乎相同的一则材料,其中“偃月”被“偃明”二字所取代:
续汉书礼仪志曰:登遐……小敛如礼东园匠考工令东园秘器表里洞赤画日月乌龟龙虎连璧偃明如故事。②(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百四十五《礼仪部》二四“丧记”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470页。
对比第一则材料可知,第二则材料中明显存在因传抄导致的信息缺失,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材料失去了史料价值。《太平御览》成书于太平兴国八年(984年),此时《续汉书》仍以单行本行世,其三十卷志被附于《后汉书》后合刊而行应不早于宋乾兴元年(1022年)③《后汉书》卷一,第8页。,故而《御览》中摘录的《续汉书》内容是来自单行本《续汉书》的可能性极大,较《后汉书》所附或更为原始。因此,尽管两则材料详略有差,但以第二则校勘第一则并无不妥。故而在第一则材料中“偃月”两字有误的情况下,第二则中的“偃明”便为我们提供了复原文本的依据。笔者认为,第一则材料中的“偃月”应该是“偃明”之讹,后世传抄时混淆了“月”“明”二字。据此可知,吐鲁番出土衣物疏所见之“偃明”在《续汉书·礼仪志》中已有记载,那么文献中的“偃明”是什么形象?
第一则材料中记述的主体是“东园秘器”,这是东园匠所制、皇家专用的一种彩绘漆棺,也被称作“东园画梓寿器”①《后汉书》卷十下《皇后纪下》“孝崇匽皇后”条,第442页。“东园画棺”②《后汉书》卷三四《梁统列传》,第1174页。“珠(朱)画特诏秘器”③《后汉书》卷四五《袁安传》,第1523页。等,已为学界所公认④孙机:《“温明”不是“秘器”》,《文物》1988年第3期,第94页;韩国河:《温明、秘器与便房考》,《文史哲》2003年第4期,第20页;刘卫鹏、张红玲:《东周至晋赠赗制度的变化》,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编:《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4页;祝越:《东园秘器试考》,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11页。。文献中的“表里洞赤”指的便是秘器内外遍涂红漆的特征,其后的“虡文”据孙机的解读是指汉代常见的云气神兽纹⑤孙机:《几种汉代的图案纹饰》,《文物》1982年第4期,第64页。,“画”字之后统领的内容是器表朱地上的种种彩绘纹样,“日”“月”即具象化的日象和月象,“鸟龟龙虎”或为四神图案的俗称,“连璧”即以丝带串联玉璧的图案。虡文、日月、四神和连璧的图像在汉墓中相当常见,壁画、画像石、漆棺、髹漆器具等皆是载体,作为组合出现在漆棺上的实例可参考马王堆一号墓四套棺中的朱地彩绘棺、长沙砂子塘1号西汉墓出土外棺和以1998年在楼兰LE古城东北的M1墓穴出土的彩绘木棺(98LEM1:2)为代表的的汉晋楼兰墓地木棺⑥于志勇、覃大海:《营盘墓地M15 及楼兰地区彩棺墓葬初探》,西北大学考古系等编:《西部考古》,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401~427页。。

图2 楼兰LE古城附近M1出土彩绘棺的两挡图案⑦图片为笔者自摄于国家博物馆。
“连璧”之后便是“偃明”。首先,根据吐鲁番出土衣物疏可知,偃明是真实随葬的丧葬用品,与“秘器”上画的内容性质迥异,并无可能被作为平面图案绘于棺上,故而第一则材料中“偃明”与“连璧”之间需要读断。其后的“牙桧”在此处并非形容棺木的材质,案《左传》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其下杜注云“四阿,四注椁也。翰,旁饰品;桧,上饰,皆王礼”⑧《十三经注疏》整理委员会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07页。,据此可知“桧”曾是周王所用棺木上方的一种主要的装饰,作为“王礼”的象征被沿用至东汉也是合情合理的,故而此处的“牙桧”应为棺饰,也许是象牙材质,至于具体对应何物则无从考证。而“梓宫”一词专指皇帝所用之梓木之棺当无疑问⑨韩国河:《温明、秘器与便房考》,第20页。。因此,“偃明”应与“牙桧梓宫”相连,同为一套完整东园秘器附带的设施。
由此,对于《续汉书》中所记的这套皇室葬具,笔者以自己的理解重新整合如下:
东园匠、考工令奏东园秘器:表里洞赤,虡文,画日、月、鸟、龟、龙、虎、连璧;偃明、牙桧、梓宫如故事。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确认,“偃明”原本是一种高等级葬具,其与东园秘器可构成一套葬具组合。
五、“偃明”与“温明”
通过对青岛土山屯墓群M147的发掘,借助出土衣物疏(M147:45)中“玉温明”的记载和温明实物(M146:6)的比对①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黄岛区博物馆:《山东青岛土山屯墓群四号封土与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目前我们可以确定,以江苏地区西汉末至新莽时期墓葬中出土的“漆木面罩”为代表的此类葬具就是温明。笔者以为,偃明与温明之间有三方面的对应,二者应是对同一种物品的两种称谓。
第一,《汉书·霍光传》中记载,霍光死后汉廷赐予的一系列皇家葬具中有“东园温明”,服虔注云“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②(汉)班固撰:《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948~2949页。,可见西汉时温明与秘器同为东园所造的葬具,或许本身就与漆棺配套使用。东汉时东园秘器仍在使用,但温明却未见记载。至曹魏时温明重又出现,韩暨死后魏明帝“特赐温明、秘器”③(晋)陈寿撰:《三国志》卷二十四《魏书·韩暨传》裴松之注引《楚国先贤传》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78页。,可见此时与东园秘器一起使用的依然是温明。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园)温明、秘器”的组合相当流行,似已成为诏赐葬具的定制④《晋书》中见司马孚、荀顗、司马亮、司马遵四例,《十六国春秋》中见王猛一例,《魏书》中见元澄、元羽、穆衍、叔孙俊、王洛儿、源贺、尉元、刘昶、崔光、裴叔业、胡国珍、王叡十二例,《南齐书》中见萧昭文、萧嶷、萧子良三例,《梁书》中见萧宏一例,《陈书》中见陈昌一例,《北齐书》中见段韶一例。。从以上的文献可推知,作为和东园秘器的组合,偃明与温明的角色是大致相同的。
第二,观察上文分析的吐鲁番四则衣物疏的墓主身份可知,四人中沮渠蒙逊夫人彭氏的社会等级最高,是十六国时期的王族成员;其他三人出身于麴氏高昌国的豪族世家,自身亦为高昌小王国的中级官员,毫无疑问都属于彼时的上层阶级,偃明的使用局限于此群体。虽然目前出土的温明的工艺水平因墓主身份而参差不齐,有遍饰金玉者也有素面无纹者,但通过对这些木椁墓的形制和随葬品的观察可知,使用温明的墓主地位的下限也应是财力雄厚的本地豪族⑤高伟、高海燕:《汉代漆面罩探源》,《东南文化》1997年第4期,第39页。,上限则自不待言,海昏侯墓园M1内刘贺的头部也被“镶玉璧的漆面罩”覆盖着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考古》2016年第7期,第51页。就简报描述来看,该物品应是温明。。应该说,墓葬中使用温明仍有等级限制,其并非一般平民能够使用的葬具。因此,在等级层面,偃明与温明也是相似的。
第三,从字面义来看,“温明”一名似与其实物的特征相关。结合《汉书》服虔注观察目前出土的温明,可知不论有无底板,温明均是一个匣状的封闭空间,这种设计无疑是为了遮盖墓主的遗容,换言之,以遮挡为目的的封闭结构正是温明的本质特征之一。就笔者管见,“温”字本身并无封闭之义,该字从水、昷声,“昷”字乃其核心的意符,同以该字作为意符的“辒”字则有值得注意的字义。该字仅用于辒辌车这一概念中,颜师古在《汉书·霍光传》中如此注解“辒辌”:“辒者密闭,辌者旁开窗牖,各别一乘,随事为名”①《汉书》卷六八,第2949页。,辒辌车能够作为载尸之丧车,其势必是以密闭为主要特征②参见王关成:《辒辌车刍议——兼论秦岭二号铜车的相关问题》,《文博》1989年第5期,第82页;司晓莲:《辒辌车考》,《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8期,第765页。。如此则“昷”的字义也得到了说明,故而温明之“温”应该是取“昷”字的封闭之义以描述其构造特征。

图3 温明内嵌铜镜的构造
前文所引的服虔注中提及,温明中有悬挂在尸体(也就是墓主头颅)上的镜子,这一点也为出土实物所证实。根据焦阳《再论汉代的漆木“面罩”》文中的统计⑥《再论汉代的漆木“面罩”》,第94~95页。,在目前已知的三十余件出土温明中,除具体情况不详者外,其中有7 件器内嵌铜镜,涵盖两种类型⑦焦阳在其论文中根据有无前桥和底板将出土温明分为两类,笔者亦赞同这种分法,见其《再论汉代的漆木“面罩”》,第83~85页。,且皆是镜面朝向墓主。这种在墓主头上悬镜的做法令人联想到晚唐至宋元时期流行的墓内悬镜葬俗,二者似有承继关系⑧葛林杰:《古代悬镜葬俗研究》,《考古》2016年第12期,第95页。。宋人周密《癸辛杂识》“棺盖悬镜”条云:“今世有大殓而用镜悬之棺盖,以照尸者,往往谓取光明破暗之意。按《汉书·霍光传》,光之丧,赐东园温明。服虔曰:东园处此器,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然则其来尚矣。”①(宋)周密撰、吴企明点校:《癸辛杂识》续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02页;高伟、高海燕《汉代漆面罩探源》一文中亦有论及,见其文第37页。由此可知该葬俗中镜即象征光明,具有驱邪的功能。据此反推至汉代,在道教尚未赋予铜镜以更多的宗教神秘色彩之时,镜正是因其本身象征光明的特性而被置于温明之中。比起将“明”字理解为明器、神明之义②《温明、秘器与便房考》,第20页。,以光明释之或更为合理。我们可以认为,“温明”二字就是对以封闭的木匣遮盖墓主遗容的同时在其中布置铜镜以求光明的这种结构的概括描述。
“温明”二字的字义既已得到解读,则“偃明”是否能与之互通?解决的关键在于“偃”字。该字从人、匽声,核心意符为“匽”字,“偃”“匽”互通。据《说文》卷十二下,“匽,匿也”③(汉)许慎撰:《说文解字》卷十二下“匚”部,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67页。,由此知“偃”也有藏匿之义,这与“温”字的“封闭”义大致相通,亦能够描述温明的这一特征与功用,因此用“偃明”作为“漆木面罩”的别名也是合理的。
在“温明”两字不见于东汉时期文献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东汉时因为某些原因用“偃明”替代“温明”以称呼漆面罩的假设是可以成立的,而造成这种替换的原因或许如韩国河所说,是东汉洛阳城中出现了“温明殿”④韩国河:《温明、秘器与便房考》,第20页。,出于避“讳”的需要故而选择了“偃明”的名称。
结 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作如下推测。温明原本是“东园”为皇室制作的高等级葬具,经过向大臣的下赐而逐渐为世间知晓、应用,故而在西汉晚期墓葬中能够有较多实物的发现。
东汉时,温明或改称“偃明”,尽管此时主流的墓室形制已由椁墓变为室墓,但置于棺内的漆面罩并未因此受到影响而被废弃。曹魏时,“温明”一名在中原地区重又回归,此后继续作为高等级葬具被广泛使用于诏赐赗赠中。
结合彭氏衣物疏的用例可知,“偃明”应是在东汉时传入河西,此后这一别名和与之相应的葬具葬俗得以在稳定的河西存续。自前凉始,河西的汉文化成规模地进入郡县化的吐鲁番盆地,高昌一地得到了长足发展,以至于流亡的北凉王族以此地为都。笔者以为,偃明或正是随着以彭氏为代表的河西贵族的迁徙传入了高昌。高昌北凉以后,源自中原的“漆面罩”带着其昙花一现的别名植根于边陲社会。直到唐代的统一,中原的新风再次全面地改变了吐鲁番的葬俗。
遗憾的是,河西、吐鲁番地区的中、高等级墓葬几乎难逃盗扰,墓内葬具保存情况也普遍较差。尤其是吐鲁番墓葬中的木质葬具,早年因为当地居民的生活需求而被盗取一空,遑论其他金属器具。种种原因导致迄今为止尚未在吐鲁番的晋唐墓葬中发现完整的偃明⑤如彭氏墓内残留的若干木板,虽然没有证据显示其为偃明的一部分,但亦无法完全否定这种可能性。,故而偃明的西传之路依然等待着出土实物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