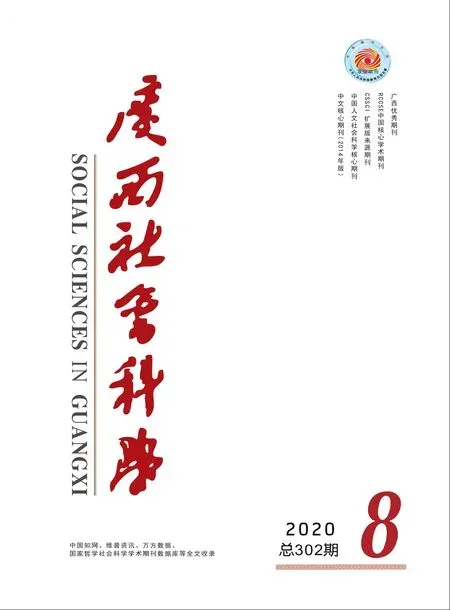记忆、认同与想象
——文化记忆视野下重读迟子建长篇小说
2020-03-16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自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以来,迟子建始终如一地勾勒着东北地域的自然风物、历史面貌、人伦情感,以其特有的文学格调和气质禀赋独立于思潮盛行、宗派林立的当代文坛。学界有论者赞誉其“是90年代中期最高艺术理想的追望者”[1]。然而,纵观研究界对迟子建作品的考察,内容多集中于其小说的“乡土性”“温情叙事”“生态意识”“死亡母题”,以及与萧红、沈从文、乌热尔图等人的比较论,从而陷入一种研究的重复中。实质上,迟子建的“整体性”创作勾连起的是东北地域的百年历史与现实,她的小说往往从个体记忆出发,最终却逾越个体叙事而完成对宏大历史的记忆重塑。将迟子建小说置于文化记忆理论视阈下解读,不仅能打开一个全新的阐释空间,更能深入探索其小说的内在意蕴与艺术价值。本文试图从记忆的载体、记忆的场域和记忆的功能三个方面来解读迟子建长篇小说所呈现的更高意义上的精神指向。
一、作为记忆载体的文学
记忆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多重影响。一方面,集体记忆以各种方式被存储下来,不断构建着我们对历史经验和现实走向的认知;另一方面,个体自身的记忆也内在地左右着我们观察和体悟世界的方式。在保存记忆的所有手段(如图像、建筑物、档案、仪式等)中,“文字被称颂为是最为可靠的记忆媒介”,“它是永生的媒介和记忆的支撑”[2]。而作为以文字为创作形式的文学始终无法切断与记忆的关系:创作主体以个体记忆为起点,经过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合理的意识幻象与隐喻,逐渐深入到集体记忆的境域,完成对记忆的重塑、保存、加固。因此,文学文本始终难以剥离与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的复杂关系,这一点在很多作家的作品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学界对“记忆”的探索发轫于大脑研究和心理学领域,经过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的研究拓展到社会心理学范畴,最后在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的推动下抵达文化研究的领域,直至最近几十年,记忆研究已逐渐“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文化研究领域开花结果”[3]。就文化研究层面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扬·阿斯曼在指出哈布瓦赫“过于重视集体记忆,以致疏忽了个体记忆的主体性及其对集体记忆的反叛性”[4]的基础上,细化和深化了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将个体记忆置于研究的重要位置,并与阿莱达·阿斯曼共同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在这一概念内涵中,文学因具有浓缩表达社会现实和集体记忆的功能,而被认为是文化记忆的有效载体。
在文化记忆理论视阈下观照20世纪中国文学,无论是“启蒙”的高亢呼声还是“救亡”的急迫呐喊,文学终未割裂社会现实而偏于一隅独立存在,20世纪中国文学承载着历史记忆的内容及其价值。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问题的宏大关怀到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对革命历史的激情书写,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的“一体化”叙事到“文革”期间的潜在写作,从新时期重新强调“人的文学”到20世纪90年代“新历史小说”以家族史勾连民族史的全新尝试,文学始终与时代潮流共进,肩负着记录历史的使命。因此,文化记忆理论对于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属性、历史建构,以及作家的身份认同等问题都具有阐释性价值。本文之所以考察当代作家迟子建的作品,是因为迟子建的文学叙事自始至终未曾远离“东北”这片神奇的土地,她的文字对于探索东北地域的历史与文化、现实与记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东北地域的集体记忆影响着作家的身份认同和文学创作,其长篇小说具有文化研究的价值。
以时间线索纵观迟子建的8部长篇小说,如果说前期的《树下》(1991)、《沉重响彻黄昏》(1995)、《热鸟》(1997)是由个人记忆营造的一个个更具成长意味的单纯故事,这个阶段的创作偏重迟子建个人生活经验与记忆的流露,符合帕慕克所言“天真的与感伤的小说家”的书写,那么从《伪满洲国》(2000)开始,迟子建的长篇小说进入成熟的创作阶段,其叙事作品走向书写地域宏大历史事实与文化现象的自觉,迟子建以历史记录者的姿态对集体记忆加以重构和衍生。这是一个将写作不断推进、思索并逐渐深入的过程,其始于作家对个体记忆进行的文学转化与表达。
细读迟子建前期的长篇小说,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文本对作家个体记忆的承载。例如,《树下》中的诸多情节便源于作家对个人生活经历的演绎。迟子建曾自述儿时被母亲“抛弃”,寄养在外祖母家,因“幼时极其难看”、懒惰、贪嘴,而不惹人喜爱[5]。在其居住地附近就是鄂伦春族人活动的森林,她经常看见树上刻着白那查山神的图案,这些都让儿时的迟子建对这个神秘的少数民族产生了好奇[6]。而童年生活在老人占大部分比例的村庄,包括青年丧父、中年丧夫的痛苦记忆,使其对死亡有着近乎痴迷的叙述[7]。结合作家的生活经验来反观文本,《树下》中的主人公七斗童年被抛弃的命运、七斗对鄂伦春民族模糊的认知,以及初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遭遇等都是个体记忆的一种文学表达。小说中姨夫一家的死便是迟子建对童年时期目睹的真实杀人案件的移用,她曾描述自己甚至看到了死者“脖子上咕噜咕噜冒着血泡的情景”[8]。此外,发表于1995年的《沉重响彻黄昏》是迟子建远离故土进入都市后苦闷、迷茫、困惑等经历的文本反映,而随后的《热鸟》虽有故作高深、情节缺乏合理性等缺陷,但主人公赵雷的“逃离”亦是作家内心深处对灵魂自由的单纯渴望。这一阶段,即使个体记忆背后也隐含了时代,但小说俨然徘徊于作家个人记忆的左右,停留在对作家个人生活经验的记录上。
从《伪满洲国》开始,迟子建不满足于对个体记忆的关注,而是试图寻找对话历史、重构集体记忆的审美通道。从处女作《树下》到成熟标志的《伪满洲国》,以及随后的《越过云层的晴朗》(2003)、《额尔古纳河右岸》(2005)、《白雪乌鸦》(2010)、《群山之巅》(2014),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清晰地勾勒出一个完整的记忆框架,即由个体记忆开始,逐渐回溯到地域记忆深处的殖民、战争、瘟疫等灾难历史,以及少数民族的文明衰落、“文革”的创伤记忆和地域的边缘性悲剧命运等宏观意义上的集体性记忆。从小说的内容上看,迟子建将个体记忆逐渐融入并转化为集体记忆,尝试用文字演绎东北近百年的历史与现实,展示一个复杂多元的历史面向。
“历史”是迟子建后期长篇小说的叙述关键词。与其他题材的小说相比,历史小说的叙事指向是对遗漏历史进行修补,以此对抗遗忘,为集体记忆提供储存空间。迟子建历史小说的独特性表现在,她选择从凡俗的生活入手,但其叙述背景往往是近现代东北历史中具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伪满洲国》从“这段历史何以给中日人民留下的烙印如此深刻”[9]的思维源点出发,对1932年到1945年间东北地域的历史进行记忆的整合与重塑。小说中无论是吉来、王金堂、王亭业、郑家晴、于小书、张秀花这样的民间人物,还是溥仪、婉容、吉冈安直等真实的历史人物,都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穿行,但作品的根底连接的却是东北地域的重大历史事件:伪满洲国统治、平顶山惨案、东北地区匪患、日本移民开拓团、731细菌实验等。《伪满洲国》用70万字的巨大容量承载着对这一阶段历史的记载与补遗,在对抗遗忘的同时,尝试回答文本最初的问题,即这段历史之所以能给中日人民留下深刻烙印,正在于其内部呈现的复杂而切实的历史真相。
这种对历史的独特理解贯穿于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的始终。《越过云层的晴朗》是动物视角下对“文革”“伤痕”的日常描写,小说中的哑巴、文医生和梅红等关键人物都被置于“文革”的时代阴影下,作品另类地书写并探讨了小人物的悲剧命运与精神伤害。《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民族的自我坚守与族群隐痛亦是从日常生活中被记取,少数民族的百年沧桑历史被浓缩于一天中,成为一种文学的备忘。随后的《白雪乌鸦》《群山之巅》延续了这种将历史真实事件融入对庸常生活的文学想象之中的写法,作者有意虚构那些被正史忽视了的活生生的个体日常,将干瘪冰冷的文献记载浸润上文学的情感汁液。但这并不意味着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沦为虚幻的空洞的主观想象,实质上其小说始终没有脱离对历史事实和现实世界的观照。这种对史实的处理方法,让我们想到现代文学史中郭沫若历史剧创作所提倡的“失事求似”原则,即尽可能真实准确地把握与表现历史的精神,对史实进行艺术化的处理。
总之,作为记忆载体的文学,不仅提供了一种承载记忆的文本形式,还在记忆的建构过程中不断进行主体性的反思、辨析、解构与重建。如《伪满洲国》以编年体的记述方式勾勒真实的历史,但随处可见的是作家对严肃历史的解构和调侃,“一只苍蝇落在了溥仪心爱的留声机上,其时他正在如醉如痴地听《游园惊梦》”[10],这样的叙述激活了沉寂的历史生命,代表着作家相对独立的思考,是对记忆表现的可能与限度的一种尝试。因此,迟子建长篇小说是建立在对集体记忆的深度剖析和独立性阐释上,不是机械地承担集体记忆的存储器之功能,而是颠覆、解构、重塑固有的记忆与认知。
二、地方:建立身份认同的“记忆场域”
相较于“文学作为记忆载体”这一强调个群记忆内容的概括,记忆的场域问题则指向具有认同意味和时空属性的阐释层面。很明显,记忆有其展演的场域,根据文化记忆理论的相关论述,博物馆、广场、朝圣地等都是能激起回忆的场所。回到文学上来理解所谓记忆的场域,我们不妨将其扩大到能够标识创作主体身份认同的地方性中,“地方”在此承担着储存和唤起个人与集体记忆的重要责任,也承受着记忆的刻写与重构[11]。举例来看,福克纳之于密西西比州牛津城,沈从文之于湖南湘西,高晓声之于苏南乡镇,莫言之于山东高密东北乡,贾平凹之于陕西商州,创作主体以历史记忆之经和现实经验之纬共同构筑一个具有巨大意义表现空间的记忆场,地方的“场域”所在成为区别作家独特性的重要依据。
迟子建的文学叙述从未远离过“东北”。在其作品中,东北是一个由辽远广阔的黑土大地、绵延无限的自然物象与恒久悠长的民间生命所构成的文学场域,被作为一个记忆场而存在。在这里,迟子建将近现代东北的百余年历史记忆串联起来、汇聚于此,既有对殖民、战争、瘟疫、政治事件等的创伤记忆,又有对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相互博弈的精神考量,重大历史事件和日常凡俗生活皆被纳入这一记忆场之中,实现了对集体记忆的重塑与强化,从而回答“我是谁”“我归属何方”这一身份认同问题。
那么,“东北”何以成为特殊的记忆场域则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换言之,历史上的东北究竟以怎样的面貌呈现意义、融通情感、激发记忆,这是理解迟子建小说的前提。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指出“东北”作为地理名词和文学表征,同时迸发于20世纪初,“东北”既是一种历史的经验,也是一种“感情结构”,召唤“东北”也同时召唤了希望与忧惧、赞叹与创伤[12]。如何理解东北的“创伤”似乎成为进入东北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键,它源于民族国家“版图”中偏于一隅的边缘位置,也与整个20世纪伴随政治、经济、文化的动荡而起伏更迭的被动性历史命运难以剥离。从地缘坐标的指认开始,山海关以北的地域统称为东北、关东或关外,从字面上看,“关外”即“关在外面”。历史上,山海关与长城意味着中原农耕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备,更意味着文化心理上的“隔绝”。特殊的地理位置生就边缘化的地域体验,历史命运由此迥异于中原和东部沿海。从清代中期作为中原流民的流落庇护之所,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惨遭沙俄日本轮番侵略殖民而一度迷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东北闭关自守,困兽犹斗,已经陷入不可避免的边缘性悲剧命运,而贫瘠荒凉的文化生态亦使其无缘话语权威。共同的地域记忆形成了一个情感上的凝聚性结构。
迟子建长篇小说跨越百余年的东北叙事便是在这复杂的“感情结构”中寻找带有恒久生命力的象征物,它能够更深刻地感喟历史命运的艰辛。而东北地域的文化记忆一定程度上也规约着迟子建的文学创作,具体到文本中,充满世俗气息的民间文化和宗教感十足的萨满文化的文学再现是迟子建就“东北”这一记忆场域展开文学叙事的两个重要方面。
就民间性而言,迟子建的长篇小说记载了具有鲜明地域文化风尚的传统民俗和岁时节日。相较于主流历史小说对“史”的偏重,迟子建将眼光凝注在东北地域时空里的“人”以及由此结构而成的民俗、传统节日、日常生活等,这些因素俨然确认并强化了集体的记忆与族群的身份。如8部长篇小说全部记录过东北的丧葬文化,首部长篇小说《树下》开篇第一章“葬礼之后”写葬礼上孝衣、孝帽、白麻布和四匹红马拉着的母亲的灵柩,直至最晚近的《群山之巅》依然展开了对丧葬文化的记录。迟子建曾表示:“东北乡村的葬礼很隆重,我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无数次葬礼,葬礼本身就是种热闹。”[13]葬礼形成的聚合性群体共同在这一场域内实现身份的确认。此外,东北地域半年的冰雪期形成了具有节日气氛的渔汛期——“童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渔汛,它几乎年年出现”[14]——以及为摆脱长期“猫冬”的寂寞而形成的挂灯笼、扭秧歌等习俗。《伪满洲国》中的人们即使生活在压抑和屈辱之中,也始终葆有着对抗“风雪”的热情,在约定俗成的节日中找到升腾起的活力和希望。“唢呐和锣鼓叫得更欢了,分成两排的秧歌队齐头并进地扭将起来。他们头戴各色稠花,手中挥舞着五颜六色的扇子,一步一颤,两肩一耸一耸的,分外有趣……秧歌的花样几乎扭了个遍。看得人眼花缭乱的。”[15]小说呈现出独具风采的东北民间文化习俗,展示出不同的人文地理景观,更承担起反映东北地域群体深层文化心理的集体记忆的传承使命。这些“地方性知识”的还原与边地民俗场景的展演,使得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蕴。
另一方面,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关于萨满文化中跳神仪式的记载最具文化研究的价值。扬·阿斯曼在阐释文化记忆的组织形式——仪式时,指出“文化记忆始终拥有专职承载者负责其传承。这些承载者包括萨满、游吟诗人、格里奥……这些人都掌握了(关于文化记忆的)知识”[16],此处提到的有关“萨满”与萨满教的跳神仪式,迟子建堪称当代文学史中对其描写最多、记录最详尽的作家。萨满教作为一种对东北民众的生产生活经验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古老宗教形态[17],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被激活和重述。《伪满洲国》对萨满教跳神仪式的盛大场面进行了还原:“远远近近的萨满神都来了,他们戴着镶有铁角的神帽,穿着怪异的服装,然后在一个空场地上跳神。参加的鄂伦春人骑着马赶来,马背上驮着完整的狍子和犴等祭品……萨满在场地中央跳,而鄂伦春的百姓则在场地四周祈祷。”[18]对萨满文化的深描体现了作家对东北地域文化形态的强烈认同,显示着宗教式的思想旨趣。同时,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禁忌习俗、祭火神仪式、风葬仪式等的记载,一定程度上展现出地域文化内部的神秘性、丰富性、独特性。如《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了鄂温克人对“白那查”山神的敬畏、人们分食猎物前的祭奠仪式以及婚丧嫁娶等诸多仪式的热闹场景。而在《群山之巅》中,唯一的鄂伦春人绣娘在“土葬”与“火葬”新规之争中毅然选择坚持族群的传统“风葬”仪式,绣娘的死隐喻了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对这一群落最后的祭奠与哀悼。随着萨满教的逐渐衰亡,这些只能通过文献记载才能看到的文化记忆内容,得以在迟子建的文学作品中复归,亦显示了扬·阿斯曼所言之艺术家作为承载者对文化记忆的维系和传承。
从迟子建的“东北”叙事来看,小说对彰显地域特色的民俗风尚和宗教仪式进行文学想象与记载,实质上是对一种地域性“感情结构”的唤醒。作为土生土长的东北作家,迟子建多维度地审视了东北的文化记忆,通过还原真实而恒久的历史瞬间,使个体在其中寻找到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就场域而言,迟子建长篇小说中分别出现了北极村、金顶镇、额尔古纳河、傅家甸、龙盏镇、盛京、奉天、哈尔滨等众多地点,如果根据皮埃尔·诺拉关于“记忆场是一种必需有历史、时代和变化参与影响的纪念场所”[19]的定义,作家似乎并没有拘泥于某一个特定的“纪念场所”而言说个人经验、记录个体记忆,而是“自觉站在文化人类学的精神高度,构建起‘北极村’与‘地球村’的独特的灵魂时空”[20]。倘若非要寻找一个体现作家构筑身份认同的“记忆场域”,那便是承载着战争、灾难、流落命运、历史隐痛与生命活力的“东北”大地。这一“地方”所在是迟子建塑造自我形象、展开历史想象、思考地域文化状貌、记载并强化集体记忆的文学叙事源点。
三、文学创作与记忆的功能维度
阿莱达·阿斯曼在推进文化记忆理论研究方面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她将回忆的模式细化为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两种,以展示记忆在选择和调动中的具体生成机制。其中,功能记忆是经过选择、连缀、意义建构的过程而产生的,无结构的、无联系的成分进入功能记忆后就变得有编排、有结构、有关联,从这一建构行为中产生了意义,而存储记忆中不具备意义的品质[21]。从这一视角来看,文学经典对记忆的取舍和调动,即是一个选择、连缀和意义建构的过程,将鲜有人问津的历史文献转换为更多受众的文学作品,便是赋予记忆以意义的行为。这一点在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中得到鲜明的显现,其小说彰显的记忆的功能性意义可以归纳为三点:激活呆板的历史文献以实现文学的再现、对抗遗忘以更好地理解当下、强调认同以应对消费时代身份淡化的难题。
首先,迟子建后期的长篇小说有着明显的“著史意识”,她用诗人化的手法激活呆板的历史文献以实现文学的再现。她的小说作为媒介将“存储性”的历史文献转化为“功能性”的文学记忆,在此,历史脱去了它单调刻板的外衣,被注入鲜活的艺术生命。迟子建在谈到《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等作品的材料准备、构思以及虚构与想象的过程时,无不涉及历史文献的搜集、整理、转换,作家将大量具有存储意味的历史文献进行编整和重构,并经过文学想象与抒情衍生为更具现实意义的记忆文本。如迟子建明确表示自己在筹备《白雪乌鸦》时,把能搜集到的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的资料悉数收归囊中,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的四维胶片的《远东报》,几乎被逐页翻过[22]。可以说,如果没有《白雪乌鸦》的问世,发生在一百年前的哈尔滨大鼠疫将依然沉寂在文献资料的夹缝中,鲜有人问津。小说采用实证手法写作的同时,不忘塑造车夫王春申、富商傅百川、点心铺老板周耀祖等串联起整个灾难故事的关键人物,他们的存在使小说避免了对历史的简单“复写”,历史记忆中的众生世相被生动地呈现出来。《伪满洲国》亦是用诗意的笔触记录了大量史实,几近埋藏的历史记忆被迟子建从史料库、书店及旧书摊的弃置书籍中拾捡起来,重新搭建起全新的历史舞台,激活沉寂已久的集体记忆。
其次,记忆的首要目的是“对抗遗忘”以更好地理解当下。迟子建在进行其长篇小说创作时不是机械地保存和单纯地索取,而是有目的地拾取材料,将那些沉潜在历史深处的逐渐被人们淡忘的真实事件通过文学形式得以重现,以此对抗遗忘,重建处于断裂危机中的记忆脉络。这是迟子建长篇小说呈现的又一记忆的功能。《白雪乌鸦》给予那些没有在史书上留存痕迹的小人物以生命的尊严和不被遗忘的权力;《伪满洲国》所记录的则是被侮辱被损害的底层群体的集体性伤痛,小说中12个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缩影的是整个东北曾被蹂躏的创伤历史;《越过云层的晴朗》展现的是“文革”的特殊年代记忆,梅红和文医生都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受害者,他们的命运起伏代表着迟子建对这一历史记忆的隐晦表达。如果不能有效处理这些历史事实,则难以重新确认当下的自我。更进一步讲,关注记忆研究“不仅是为了‘对抗遗忘’,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23],即“进行回忆的人目的不在于单纯地了解过去,而是为了确认和确定眼前的自我形象”[24]。因此,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不是对过去生活的简单记录,而是将“过去”拉入“今天”的社会背景中,寻找意义的贯通,确保记忆脉络的连续性。
再次,对迟子建长篇小说的考察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时代背景中,方能理解作家持续性地书写所承担起的形塑认同的使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融通力量使区域之间的流动性加强,地方文化被裹挟进全球文化的整合圈内,文化认同危机不断加深,社会记忆话语面临被重新改写的命运。因此,作家需要以文学的方式应对记忆紧张和身份淡化的问题。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小说对鄂温克民族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宗教信仰、狩猎文化等进行了全面“打捞”,充分展现出民族文化内部的丰富性和独特性。迟子建的长篇小说所承载的记忆功能便是赋予东北地域文化以全新的生命力,在即将消逝的文化记忆中努力寻求一种属于北国边疆的身份认同感,以此应对消费时代身份淡化的难题。
需要指出的是,有评论者质疑迟子建写作存在温情泛滥和内容同质化的问题,特别是对庸常人生的执着书写消解了历史小说的“史”的意味[25]。然而,就像我们不得不承认迟子建小说确实存在“刺眼的缺陷”一样,我们同样也无法否认其小说具备的文化研究方面的价值。这一价值既体现在文本对记忆真实的处理上,又体现在作家巧妙融入想象真实,以完成对文化记忆与历史真实的构建上。文化记忆理论主张文学可以“构建对过去的生活世界的各种想象,传播不同的历史观,寻求各种记忆之间的平衡以及反思集体记忆的过程和问题”[26],“想象”在此成为理解文学创作与记忆之间关系的重要修辞,也就是说,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的感情色彩、历史观念、虚构能力、思考层次等都会左右着文本对记忆的塑造和建构。以《白雪乌鸦》为例,小说用片段叙述的形式回溯真实的历史事件,但随处可见作家大胆的推测和过人的想象,如作品写瘟疫中的人们经历恐慌后对生死的看淡:“傅家甸人又敢聚堆儿说话了。他们在一起,谈瘟疫,谈生死,也谈天气和家长里短的事情。而且他们也不忌讳,相互品评着备下的寿衣,谁的料子好,谁的花色独特,谁的式样大方……好像他们去另一世,是个隆重的节日,马虎不得。”[27]迟子建尤其看中文本中富有生命弹性的想象真实,她曾就历史小说中史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进行过陈述:真正的历史在民间,一部作品如果单靠史实构筑而成,那会是非常匠气的,也没有光彩,她庆幸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为作品提供了想象的空间[28]。阅读迟子建的长篇小说可知,作家对记忆真实和想象真实的巧妙处理,丰富了文化记忆的内容,亦展现了作家独特的历史观念。
以此观照迟子建的长篇小说,作家在对历史的回溯与想象中不断进行身份图像的描绘,通过个人体验与文献素材的碰撞完成了对记忆的整合,从而实现历史描述和政治想象。正所谓“完美的虚构可能创造出真正的历史”[29],迟子建不厌其烦地对历史帷幔下小人物的庸常人生进行温情书写,仿若“清明上河图”一般让我们窥测到了真正的历史面貌,作品中大量的想象、推断和臆测实质上是社会群体所共同经历和想象的生活原貌的再现。倘若忽视了这点,就很难理解迟子建小说在文化记忆层面所体现的记忆的功能性意义。因此,与历史的确定性相比,文学将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注入对过去知识的记录中,不断修正和重塑历史的真实,以更为具体的方式表现着集体记忆的生动性、复杂性。迟子建的文学讲述打开了一个现实与历史之间的通道。一方面,这种文学讲述赋予过去所积淀的集体记忆、历史文化与传统在现今社会框架中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迟子建根植于东北地域百余年的历史记忆的书写,在虚构与想象之余,也为我们保留了一份真实的社会历史档案,即在呈现文学记忆“功能性”意义的同时依然不失文学作为记忆媒介的“存储性”价值。
四、结语
文学与记忆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创作主体不断地激活记忆,重审记忆,重构记忆,其实是让文学在更深的层面上回到人类存在的本身”[30]。在迟子建长篇小说讲述的地域故事中,我们看到,作者钩沉起的历史记忆不再是刻板的年份与事件的组合,小说对黑土地底层群体的人间悲喜的描绘,让我们看到了东北地域空间内部的生动性、多样性、独特性。以此来看,正史文献中被忽略掉的“人”以及被逐渐淡忘的记忆在作家的虚构和想象中得以重现,其小说因而具有了更高意义上的精神指向。从记忆的载体角度而言,迟子建长篇小说融汇了作家的个体情感与集体记忆,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样貌。就记忆的场域所在来说,“东北”无疑是迟子建小说延展意义空间的文学舞台,是凸显作家地域经验与记忆的个性标识。最后,迟子建长篇小说在彰显记忆的功能性意义的同时尝试保留一份真实的社会历史档案,用以激活沉潜的记忆,对抗漫无边际的遗忘,在社会记忆再生产中强化身份认同与归属。综上,以文化记忆理论的多重视角来考察迟子建的8部长篇小说,显然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阐释空间,并且能更深入理解其小说的内在意蕴和艺术价值。此种视角不失为拓展和深化东北地域文学研究的一次探索性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