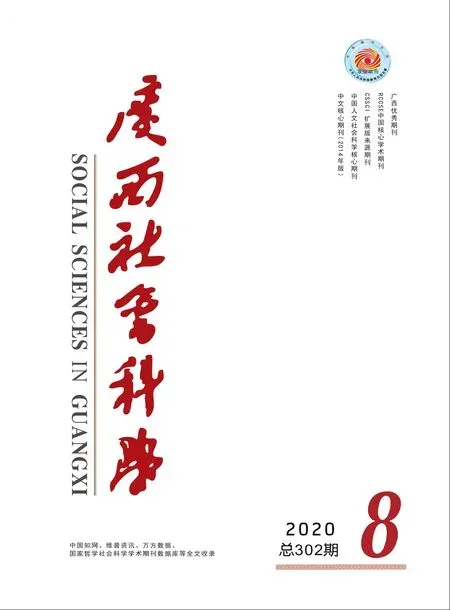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述评与展望
2020-03-16熊升银周葵刘思岑
熊升银,周葵,刘思岑
(1.泸州职业技术学院 商学院,四川 泸州 646000;2.西南财经大学 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四川 成都 611130)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万众瞩目的成绩,但总体上在人口、资源环境等领域存在众多与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1]。随着我国“五大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如何有效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各区域更可持续的发展,对提高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构筑以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目标,关系人民福祉和民族未来[2-3]。正因如此,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业已成为政府关注的重大话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4]。作为可持续发展理念重要体现的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协调发展的内涵、评价指标体系与方法以及对不同区域或对象的评价实践等方面。然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智能化进程不断推进,该研究面临着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如理论基础与方法体系仍需完善;地理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的融合协同创新度不高;理论联系实际不强,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支撑力度不够等。本文通过综述国内外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的进展、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提出我国未来研究的优先主题。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内涵的缘由与演进
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衡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生活之间相互关系的重要范畴[5],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马尔萨斯(Malthus)人口理论,马尔萨斯指出资源有限并影响着人口的增长[6]。20世纪七八十年代,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的著作《突进与和谐的增长》《短缺经济学》中提出了“只有和谐的增长才是健康增长”的思想[7-8]。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指出,促进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键要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可以看作协调发展观念的萌芽[9]。我国协调发展概念的提出可以从1984年我国生态学家马世俊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中看出[10]。《中国21世纪议程》白皮书成为研究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指导性文献[11]。有学者基于自组织、协同、控制论等系统学理论讨论了可持续发展协调性的概念和内涵[12]。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协调发展思想[1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五大发展理念”是我国推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最好体现[14-15]。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科学发展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若干种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涵[16-18]。其内涵的基本特征表现在:(1)将人口、资源和环境视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2)在发展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等维度上的适应和统一;(3)以发展过程中的良性循环为最终目标;(4)实现以人为本。还有部分学者将经济学的外部性等理论应用到实践中,但总体上该内涵理论体系还不完善,核心理论框架理论支撑还有待于加强。
二、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进展
(一)国内外总体研究进展
早在18世纪末,英国著名学者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阐述了人口必须与物质资料保持平衡[19]。20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人口对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压力问题逐渐被学者们关注,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F.A.哈珀(Frank A.Harper)的《世界的饥饿》、J.O.赫茨勒(J.O.Hertzler)的《世界人口的危机》、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等[20-21]。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提出,人们对这五系统之间协调发展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深化,这既有关于它们之间关系综合、宏观的研究,也有偏重于某个单方面、微观个案的研究[22]。如Richard和Christopher认为经济、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应保持协调发展[23],Bleischwitz、Tajibaeva研究了再生资源、经济、人类福利协调发展的关系[24-25],还有学者从政治、人口、经济、自然保护区等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进行了研究[26-27]。
我国学者研究相对较晚,1964年竺可桢先生对中国粮食作物产量潜力的探讨被认为是最早的相关研究[28]。20世纪80年代国内开展了大量关于以“多少土地,养活多少人”为核心的人口—资源系统研究[29-30]。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并从多个角度定性研究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关系[31-32]。进入21世纪以来,聚焦区域“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的目标,逐渐成为国内研究的热点。如吴绍礼指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开放的“自然经济社会”系统[33];曾嵘等认为协调发展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个复杂体系[34];刘小林综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方法[35]。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成为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本研究借助读秀中文学术搜索,截至2020年5月,书名中包含“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著作有68部,研究内容涉及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地理学、资源学、人口学等学科。在研究类别上,既有理论研究,如《后工业阶段北京市产业、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战略研究》,又有实证研究,如《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机制研究——以四川省为例》。研究主题涵盖科学内涵、战略任务、评价方法、机制建设、“短板”及对策等。从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来看,截至2020年5月,篇名中包含“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的期刊论文有1073篇、硕博士论文139篇、会议论文85篇。这进一步反映了近年来学术界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升温。
纵观国内外近百年研究进程,从范围上看从最初研究的“人口—资源”“人口—生态环境”“环境—经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两系统协调发展到“人口—资源—环境”“资源—环境—经济”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三系统协调发展。从研究方法上,逐步兴起的如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耦合协调分析(Coupling Coordination)等综合研究方法,结合GIS手段进一步推动了定量化和模式化研究,并在区域经济城镇化、产业空间、生态系统管理等领域得到广泛运用。
(二)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去评估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程度是当前研究的通常做法,评价指标体系需遵循科学性、系统性等原则。国际学术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包括了许多相关度量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指标体系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于1996年创建的DPSIR概念模型[36],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政策四个方面,包括驱动力(Driving force)、压力(Pressure)、状态(Status)、影响(Influences)和响应(Response)五个部分共142个指标,既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行为对环境的影响,也体现了人类对资源与环境恶化所作出的选择与回应[37]。
国内学者针对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子系统评价、综合评价、不同应用领域评价等,建立了不同评价指标体系。如朱启贵从经济、资源、环境、社会、人口等方面出发建立了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估指标体系[38];齐晓娟等选取人口密度、平均受教育年限等29个指标综合评价西北地区人口—资源—经济三个子系统协调发展问题[39];杨莉构建了北京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体系[40]。
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涉及各个子系统,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之间又相互影响、相互制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对象由单系统转向复合系统,应用领域也不断扩大,使得传统的评价指标体系不能满足当前研究的需求,主要表现在:(1)尚未形成统一适用的评价指标体系;(2)往往追求“大而全”的评价指标体系;(3)部分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较少涉及;(4)沿用前人指标体系较多,缺乏创新性。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发展动能和全面均衡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迫切需要评价指标体系的动态更新。
(三)评价方法
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研究目标,在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评价中往往选取不同的方法,当前国内外常用的协调发展评价方法简述如下。
1.主成分分析法(PCA)。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ysis,PCA)是皮尔逊于1901年提出的,其用于分析数据及建立数理模型,主要通过对数据建立协方差矩阵之后进行特征分解,计算结果就是相关变量的主成分及其权重[41]。具体做法是通过降维过程,将多个反映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的数值指标构建协方差矩阵,进行特征分解后得到几个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这些综合后的指标就是原来变量的主成分。国内学者主要利用PCA法开展协调发展评价,如李雪铭等运用PCA法探讨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连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情况[42];黄婷婷等利用PCA法同时评价人口—资源之间的协调度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综合协调度[43];吴文恒等运用PCA法研究了我国人口—资源—环境三系统协调发展框架模式[44]。
2.系统动力学法(SD)。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SD)模型于1956年由美国学者J.W.Forrester提出,其特点是:(1)研究社会经济系统长期发展问题,集中于组织结构和动态行为[45];(2)研究对象划分的若干子系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通过计算机实行仿真试验。由于该模型便于研究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该评价方法得到广泛运用。如英国的Slesser利用SD模型综合分析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关系[46];于春田等应用SD方法,建立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并对石家庄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进行评价[47];贾佳等构建环境—经济复合系统协调发展系统动力学模型[48]。
3.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概念于1978年由美国运筹学家A.Charnes首次提出,主要把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利用和消耗作为投入,把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作为产出,分析投入产出率来评价协调发展度[49]。DEA法总体来说简便易行,便于区域间比较等特点并在协调发展比较中广泛应用,如姚愉芳等通过DEA法,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了未来社会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50];熊国强基于DEA法,分析了陕西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程度[51];杨玉珍等运用复合DEA方法动态评价了河南省区域的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度[52]。
4.耦合协调度模型(CCM)。耦合协调度模型(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CCM)是评价协调发展的重要方法,是测量和确定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的相互配合协调程度的一种度量方式[53]。该方法得到广大学者的青睐,如杨木等用系统演化思想,建立徐州市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动态耦合度模型[54];朱江丽等利用CCM模型研究长三角城市群产业与人口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在空间上协调状况[55];王宪恩等依据CCM模型评价了四平市2009—2012年水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系统之间的协调水平[56]。
5.能值分析法(ES)。能值理论(Energy Synthesis,ES)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美国生态学家Odum首次提出,可以用于各类复合生态系统进行研究与对比[57]。目前该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对自然资源、城市等生态系统以及区域发展现状及可持续性评估等领域[58-59],如隋春花等应用能值分析法对广州城市生态—环境—社会经济三系统协调发展情况进行评价[60];张耀军等利用能值理法研究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度[61];李占玲等通过构建能值指标体系研究北京市资源—环境—经济发展的能值状况[62]。
三、问题与趋势
(一)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
协调发展概念实践于解决人口与资源矛盾的研究,后来陆续涌现出人口、经济等两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到三者及以上系统协调发展的研究方法,然而目前关于协调发展的概念和内涵尚未形成共识。人口、资源、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虽然人本社会发展理论、城乡一体化论、可持续发展论、系统工程理论、极限增长论等均指导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研究,但尚缺乏公认的理论基础。
(二)评价方法体系还不够健全
纵观国内外相关的研究,虽然对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较多,研究的内容涉及面较广,但多集中在环境与经济、人口与经济、区域之间均衡发展等两个或三个要素评价研究,“综合性”不够。首先,宏观的、综合的、着眼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性评价的研究工作还不多,评价也没有统一的方法体系,缺乏一致的综合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其次,目前过多偏重于现状的、静态的分析和评价,对区域动态变化过程的分析和发展趋势的预测研究较为缺乏,“动态性”研究不足。最后,基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综合评价的指标覆盖面较窄,对人口系统的基础和能动作用反映度较弱。
(三)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还不够接近
虽然衡量人类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程度的方法,已广泛运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63]、人口规模[64]、沿海经济带[65]、生态建设规划[66]以及环境保护[67-68]等诸多领域,但由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概念内涵不一,导致评价体系综合性和动态性不足,缺乏对实际人口、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各子系统协调发展的机制分析。许多区域存在出于政绩考虑的“唯GDP论”等因素,使得很多相关研究不能够较好地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问题,造成基础研究与社会应用的脱节。因此,未来研究需要将人口—资源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联合起来进行机制探讨与量化研究,进而更加接近于实际。
四、未来研究的优先主题
(一)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要求,不再唯GDP论英雄,而是寻求内涵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发展不协调、不充分的问题,所以寻求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更离不开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首先,要研究高质量发展的特征和内涵,明确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必定是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革开放、增长动能、城乡发展、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其次,研究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比如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在实现活力、效益与质量有机结合等方面下功夫。再次,研究高质量发展的任务,即如何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实现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等。最后,可以结合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对高质量发展设定标准路线图,例如到2035年、21世纪中叶,高质量发展应该分别达到何种标准等。
(二)加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研究
基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加强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践研究。要面对缩小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差距问题,重塑经济新格局。虽然我国目前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成果较多,但理论与应用实践之间还有差距。例如落实东部率先发展、中部崛起、东北振兴、西部开发等战略实践,基本形成了良性互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格局,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的区域发展差距依然较大,区域发展差距伴随的各种社会问题突出。因此,要运用协调发展理论强化对落后地区发展的支持和引导,有效地解决区域发展中的难题。只有通过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才能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在空间上均衡,进而实现各区域更加公平、效率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三)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同途径研究
目前,我国乡村振兴还受到诸如土地、资本、技术和人才等因素的制约,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有限,使得形成的产业规模发展受限。另外,乡村交通网络的可达性较差,区域间自然资源禀赋、经济区位发展状况存在较大差别,城乡发展水平与协调发展度比较低。要善于利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关理论,从不同方位和角度去研究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同发展。要善于结合城乡发展特点,提出操作性较强的措施助推乡村振兴与城镇化协同发展,更加注重乡村与城镇在政治、社会、生态、环境、文化等方面上多元化的协调发展以及整个区域的均衡发展,最终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文明的目标。
(四)新时代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研究
绿色发展理念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生态相互协调。要基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相关理论,实实在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要将绿色发展切实落实到社会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土地利用等各种规划中,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要通过不断优化国土空间布局、经济规模、产业结构,使社会经济要素的空间分布与人口、资源、环境因素协调和谐;要推动人民生产和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努力形成文明、节约、低碳的消费生活方式;要把控好资源环境生态红线,守住绿色底线,坚持用最严密的法治保障绿色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家园。
(五)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研究
“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核心要义是树立自然价值理念。生态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系统,是人与自然两者相互依存的关系,反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统筹优化对人类生存和永续发展的重要意义。应基于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开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估和生态系统敏感性评估,应在各地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生态保护修复工作,以便更好保护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平衡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的关系;应建立生态系统监测预警制度,开展自然资源监测预警评估,建立专业统计制度,真实反映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家底”变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