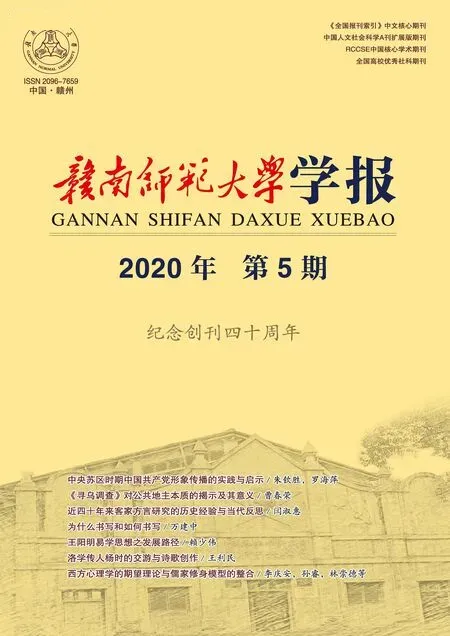《寻乌调查》对公共地主本质的揭示及其意义*
2020-03-16曹春荣
曹春荣
(中共瑞金市委 党史办,江西 瑞金 342500)
毛泽东在其《寻乌调查》一文中,以一整章的篇幅记述和分析了寻乌县的旧有土地关系。对该县包括祖宗地位、神道地主、政治地主在内的公共地主之规模、内涵、来历、用处,及其内外关系、主事者行迹的记述与分析,揭示了在“公共”“公平”“公益”旗号掩盖下的公共地主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反动,文化上守旧,生活上腐朽的罪恶本质。这对正确理解土地革命政策,深入推进土地革命,达成民主革命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祖宗地主:温情面纱下的剥削
《寻乌调查》里的所谓“祖宗地主”,即公堂地主、公堂经济,这在推崇慎终追远、尊祖睦族的客家地区相当普遍,而赣南、闽西、粤东(今之赣州、龙岩、梅州三市所在地)正是国内最主要的客家聚居地。
毛泽东了解到的寻乌县祖宗地主的名目叫公会、公堂。(1)对“公堂”的解释,有称之为贵族的厅堂或官署、衙门者,有指祠堂者,均不及其义。《寻乌调查》一文是较早揭示公堂形态与本质的著作。详见曹春荣、罗振坡撰:《客家公堂经济初探》,原载《客家学刊》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它们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后人从各自家产中抽出一份,为其先人立个公(即公会、公堂,瑞金称之为红丁公堂);一种是其先人(什么公)在世时即留出一份产业立起公来(瑞金称之为遗业公堂)。在寻乌,后一种比前一种更多。两种公会、公堂的本钱(类似基金)都是田产即田地,(2)瑞金九堡密溪村的红丁公堂起步,多取募集现钱,而后买田置产,召人耕种经营以得利生息;待利息积聚到相当数额,又买田置产,如此循环往复壮大公堂经济。详见《客家公堂经济初探》。这些田地成为公田。公田一经成立,就租与佃户,年年收租。租金租谷除祭祖用费外,所余积蓄起来再以钱借给贫民,以谷粜给贫民,所获利息、谷息又积起来。如此不断动作,积得一笔大款后便买田地。公堂因此而成公共地主。
公堂以血缘为纽带,由一姓同族或同族各支(房)设立,因而公堂之公田亦称族田。掌控族中事务,包括族田管理的,通常是有钱有势有名望的一姓“哇事人”,即豪绅地主。他们取得这种地位,表面上经由族内“公举”,实际上乃其财富势力所致。他们管理族田,表面上致力于厚植公堂经济,实际上想方设法侵蚀霸占族产。因此他们对租种族田的佃户毫不手软,无论族中农民还是外姓农民从他们手中租种田地,都须订立租佃字,照纳地租。农民与族田的关系完全是一种封建的租佃关系,也就是被剥削与剥削的关系。公堂借钱则要抵押,而索债尤其厉害,“期满利钱不清,牵牛赶猪,下田割禾,都做得出。”[1]202遗业公堂的初衷是要给其子孙留条后路,钱财多多益善的算计也决定了族田管理中的剥削性。不过,在对待族中佃户和外姓佃户上,族田管理者间或有所不同,如视情减轻租谷、劳役、礼仪等某方面的负担,公堂义仓借谷给贫苦族人渡荒等,从而表现出对族众的丝丝温情。当然,这掩盖不了祖宗地主的剥削本质。
公田增值有些分与族中子孙,这部分是怎样分的呢?《寻乌调查》列出了两种分法:一种是过年过节时从祠堂里分谷分肉,叫做“平分”;一种是“轮收”,又叫“管头”。表面看来,这样的分配也是很公平,洋溢着温情。然而,如此温情下依然存在有失公允和阶级斗争问题。
先说“平分”。祠堂里分“红丁谷”,男子都有份,女子没有份(有些族上寡妇有份)。分肉有四个项目:一是“胙肉”。从前是秀才、举人有功名的人,如今是“毕业生”分的。二是“房股肉”。每房一份。三是“老人肉”。70岁以上的人每人一份。四是“丁肉”。每个男子一份。乍一看公平,问题却出在分肉次序上:先分“胙肉”,次“老人肉”,再次“房股肉”,末为“丁肉”。有资格分得“胙肉”的,是有功名、能上学的人,他们大抵出身地主豪绅家庭,家境殷实(如富农、富裕中农),而一般农民子弟没法十年寒窗求取功名,也上不起新式高等小学和中等学堂,更与大学无缘。从《寻乌调查》所列大、中地主名录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一事实。由此可知最先分的“胙肉”,都落在了谁的手中。至于每个男子都一份的“丁肉”,却“不是每个公都有分,多数公是没有丁肉分的,这是因为公款不多,或是人太多了的原故。”[2]177这意味着贫寒农民企盼的那点“共享”,多半成了泡影。
再说“轮收”。轮收又叫“管头”(瑞金民间谓之管首),轮流替祖宗收租的意思。租收了,每年开支一小部分在祖宗的祭祀上,大部分落在管头的荷包里。“所以轮流收租名则是轮流替祖宗收租,实则是轮流替自己收租。”[2]178表面看,轮收机会均等,很公平。然而,“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2]178穷苦人闹着分田不是要分了田去耕种,而是要收回变卖,得了钱去还高利债或买明天的早饭米。由此不能不想到这些穷苦人受了怎样的剥削,才沦落到如此地步;不能不想到祖宗地主温情脉脉下,对族中穷苦人的残酷剥削。
二、神道地主:庇佑一方下的欺诈
《寻乌调查》对“神道地主”作了详尽解释,如:神道地主即神、坛、社、庙、寺、观六种。“神”是指各种各色的神(神祇、神仙),许多神都有会,像赵公会、观音会、关爷会、文昌会等。坛是立起一块石头,有的几块石头垒成一个小屋,里面遂藏了好灵验的神。“社”是与“神坛”有别的一种“社坛”,每个村子一个,藉以保佑禾苗不被虫子吃,猪牛六畜不至遭瘟,保佑人健康。“庙”是屋子,屋子里有菩萨,这些菩萨因“有功德于民”而受民祀之。“寺”是和尚的巢穴。道士斋公的叫做“观”。
以上各式各样的神神道道,或曰“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3]31它们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各个场所,受人膜拜供奉,一是因为据说它们能保佑一方“人畜清泰,财丁兴旺”。[2]178如民间所谓赵公菩萨是财神,能助人发财;观音菩萨能给人送子、保人平安;关公菩萨能替人消灾护财;文昌帝君能助人金榜题名;真君菩萨能满足人的求财求官求平安愿望等。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对劳苦大众来说,不过是心理安慰罢了,其作用更多的是为地主阶级从精神上奴役劳动群众服务,同时借以榨取劳动群众的钱财。二是供奉这些神祇的地方都立有“会”,或有田产。“凡有会都有公田,出钱弄这种神会的通通是富农地主。神会的产业百分之九十五是田地,百分之五是谷子和钱。这种田、谷、钱,叫做‘会底’。”[2]178起会目的,当然是为了神,使安神、敬神、迎神赛会等开销有着落。庙多少有庙田,也有无田的庙。和尚赖以生存作法的寺,“是剥削厉害的地方”“寺产都是大地主‘施’出的”。大地主施田给寺里和尚,是“因为佛教是大地主阶级利用的宗教”,一方面大地主好藉以“修子修孙修自己”,[2]180另一方面则藉以欺骗愚弄平民百姓,诈取他们的钱粮财物。道教和斋公所在的观的田产,其来源和剥削状况与寺一样。
不论是神会的田产,还是寺观庙的田产,这些公田都拿去招租,让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租来耕种,年年照纳地租,而承受其剥削。佃农不仅要交租给神会和寺观庙,还要担负为这些神道地主砍柴、挑水、种菜等劳役,与租种个人地主的田地无异。
神会和寺观庙的田产既然大多数由地主富农捐出、施出(也有由历代政府赐拨的),这些公田的管理权就必然由他们掌握,尤其是其中的头面人物(当地绅士)。他们采用封建剥削方式出租土地坐收地租,“为了有利他们的侵蚀(候谷价高时钱卖得多),便强迫农民交谷上仓”;[2]208以至把土地收入用于经营工商业,或放高利贷,而将大部分收入肥私。此外,他们还勾结寺观庙方,将其公田变卖,或直接据为己有。由此可见,在庇佑一方旗号下培植的神道地主,对缺少文化科学知识和政治觉悟的劳苦大众进行了怎样的欺诈盘剥。
三、政治地主:公益掩盖下的特权
《寻乌调查》把此地的政治地主分为两类,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之类属于教育性质的(也有公益性),一是桥会、路会、粮会一类属于社会公益性质的。他们之所以成了政治地主,是因为有田产,而且靠出租公田收租。像县城的考棚田年可收六百五十石谷租,县宾兴祠年可收一千五六百石谷租。
考棚田来源于前清时修建考棚,大地主捐了许多谷子,建筑余款用来置买田地而生租息,作为考棚年修经费。
宾兴田起初也由地主捐款,田散落全县各堡,多数仍由原主管理,年交收获的一半与县城宾兴祠,宾兴祠在各堡设立分局掌管田产。田产的用途作为一县学子参加乡试、会试的路费,以及中了举人、进士的奖赏,奖赏别名“花红”。废科举后,则奖赏高小、中学中专毕业生,以及大专学校学生、留学生。
建筑学宫(即孔庙)也是地主捐钱。后来祀孔经费又有结余。孔庙祀奉孔子及其门生中有成者,被树为读书人榜样。
学租为各姓地主捐集,用于奖励本姓考功名的子弟,姓姓都有。此外,各区尚有“薪水会”“文会”,性质同是奖励取功名。但“文会”系地方形式,由几姓或一区集合起来立会。(3)瑞金古智乡18姓曾于清初创立“启堂文会”,除奖赏考取功名者外,还每年定期聚集会友子弟开课,作育人才。详见曹春荣撰:《起会办学:客家兴教育才的成功之举》,原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增刊。篁乡古姓某地主(古柏的祖父)捐出100石租起的“尊育堂”,则是奖励全县读书人的。
表面看来,以上各式学田收入的奖赏似乎“遍惠士林”,人人有份,只要你能考取功名或成了毕业生。问题在于“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3]39因为“禾头根下毛(没有)饭吃”,就是农民刚打下禾(谷)交过租就没有饭吃了,“一年耕到又阿嗬”,所以“暗好学堂埃(我)毛份,有眼当个瞎眼棍”。[2]204-205由此可见,学田公项下的各种奖赏,必定如公堂里分“胙肉”一般,绝大部分要落入地主及其子弟手中。从一定意义上说,那些奖赏成了地主及其子弟享有的特权。然而,这是极不公平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3]39还有地主“捐出”的学田,也是经由剥削农民获取的,不能当作他们的仗义之举。
此外,寻乌县财政局总收入年计30 000元左右中,含考棚租2 000元左右、宾兴租3 000元左右、孔庙租300元左右,被当作豪绅及其走狗嫖赌、食着、鸦片烟的用费,[2]223更显见其特权所在。
寻乌县公益性质的桥会、路会、粮会,都有或多或少的公田,大多数系地主、商人捐的,少数原是“军田”(古时军屯之田,系官田)。桥会、路会田产用于修理桥梁、道路。“起始钱少,逐年放债堆积起来成了大数,置买田地”。有了田地,也出租给农民耕种而收取田租。“每年十二月算数、敬桥神,名之曰‘做桥会’,捐主都来吃一餐,吃了之后还分猪肉,所以桥会实在是个剥削机关。”[2]181“做桥会”也便成了地主的一项特权。
粮会的作用是代替一族人完粮,抵制政府向族内各家迫粮。粮会起始钱也不多,也是逐年放利积起来的。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学田还是会田,这些名义上的公益事业都由当地绅士把持,他们或是地主或是退职官僚,属于地方上有势力有功名之人。他们利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优势,使学田会田收入的绝大部分为其榨取,从而表现其种种特权。
四、唤起民众:真相揭示下的意义
《寻乌调查》对寻乌县公共地主种种真相的揭示,除上述者外,还有下文述及的统计数据、人物活动等。公共地主的真面目一旦被揭穿,就会使原本轻信其“公共”“公平”“公益”的善良民众惊醒过来,进而产生多重意义。
首先,《寻乌调查》统计了寻乌县三类公共地主侵占、霸占土地(所谓“公田”)的情形,为验证中共制定并实施的土地政策,开展土地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依据。
当年寻乌县全部田地中,公田、地主、农民分别占40%、30%、30%,公田和地主所占共70%。占了全县总人口70%以上的无地或少地的贫农、雇农,要想耕者有其田,根本改变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毫无疑问必须在没收地主个人土地的同时,没收被地主豪绅把持、并为地主豪绅享用的公田。另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要想推动社会发展,必先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这就需要使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农雇农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彻底摆脱对地主豪绅的封建依附关系,释放并增长对于发展生产的热情和创造力。中共正是从这一条出发,很早就提出:“要取消封建式的剥削,只有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才能实现。要破灭乡村宗法社会的政权,必须取消绅士对于所谓公有的祠堂寺庙的田产的管理权。”(4)《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的议决案》(192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斗争史料选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进而制定了没收公共地主土地,归工农民主政权重新分配,以迅速争取农民,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土地问题纲领和土地法。从《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到《兴国县土地法》(1929年4月)《土地暂行法——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1930年5月),直至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1931年11月),都明确规定要没收一切祠堂、庙宇及其他公共土地,由苏维埃政府无条件地交给农民耕种。《寻乌调查》提供的统计数据,进一步证实了党的这项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其次,《寻乌调查》以大量事实披露寻乌贫苦农民遭受公共地主和个人地主剥削压迫的惨状,以及土豪劣绅操控族产庙产学租,操纵一地至全县公共事务以自肥、以作恶、以反革命的罪行,戳破了以宗族论敌我的谎言,从而有助于启发和提高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深入进行土地斗争。
兼三区的潘明征(绰号“屎缸伯公”)是全县豪绅的领袖,光田地收租就年入10 000石谷左右,还有药店、杂货店,价值30万元。他的大儿子潘奕仁,是个秀才,做过县财政局长,管理过考棚、宾兴、牛捐、赌捐、护商捐等地方财政款项;他又做了全县保卫团总公所长,统辖七区保卫团,“全县实权都在他手里”。[2]183红军到来时,他才带着70多支枪跑往武平,被敌钟少奎收编。他的三儿子潘梦春虽然文理不通,也做过管理国家财政的财政课长。“屎缸伯公”的孙婿陈玉横,年收租300石,平远中学毕业,吉潭的土霸,新寻派主要人物,很活动(积极反革命)。“屎缸伯公”亲属潘明瑞,年收租400石,在吉潭圩还开了两间杂货水货店,是项山的反动首领。这些人沆瀣一气,横行乡里,对抗革命,眼里哪有穷宗亲穷乡邻?
大地主王菊圆是个眼里只有流氓地痞的人。他毕业于赣州第四中学,在澄江很有势力,和流氓很要好。他在澄江圩开三个店,做水货、杂货及鸦片贩卖生意,店的后楼开个鸦片烟馆,让流氓们吸食鸦片不要钱。他嫖人家的老婆,别人若不识高低也去嫖时,流氓们就要给那人以厉害的打击,直至其倾家荡产。[2]183-184这样的恶人,哪里又会认得穷宗亲穷乡邻?
类似的事例在《寻乌调查》中还有很多,它教给穷苦农民:亲不亲,阶级分。
再次,《寻乌调查》通过清理寻乌各地劣绅的反动行迹,表明要完成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消灭地主阶级及其封建剥削关系,不能不打倒豪绅地主,推翻绅权。这也是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需要。
绅士是旧时剥削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不是现任官员,却为官府倚重;他们脱离了平民百姓,却以民意代言人自居,操控地方公产与事务。他们因此不仅是公共地主代表,也成了个人地主(或本来就是个人地主)。也有既不是富农又不是地主的劣绅(有功名的顽劣),他们大半家里有些田,但不够食,就出来把持公堂,从中剥削。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一文中提到“兴国第十区永丰区,其一乡、二乡及四乡的公堂,劣绅管的占十分之六,富农管的占十分之四。第三乡,民国以前,劣绅管公堂最多,因为那时公堂要有功名的人才能管得。”[1]202中国的男子,主要是贫苦工农群众,普遍要受政权、族权、神权的支配。绅士不仅牢牢地控制着族权和神权,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干预和影响着地方政权,构成其独有的绅权。
《寻乌调查》中摆明了身份为绅士的除了潘明征等外,还有:凌鲁石,年收租三百多石,老秀才,做过多年财政局长,课长,又做考棚首士,一连干了十多年,赚了钱,在三标盖了新房子。潘明典,年收租一百多石,前清拔贡,民国法政毕业,做过陆丰、会昌两县知事,又做过本县教育局长等,有“身兼九长”之称。运动省议员落选后,还做了南昌高等法院管狱所长、九江高等法院书记官。“说话很漂亮”“又很规矩”,[2]186典型的绅士派头。赖翱虚,年收租400石,秀才,上海理化专修科毕业,做过县立高小校长、教员,运动省议员失败。两个儿子读书至中学或大学毕业,“均反革命”。[2]187汪子渊,年收租200石,篁乡的反动首领,是个大劣绅,做过保卫团总,宾兴分局长。罗佩慈,年收租200石,做过于都县长,“是个诡计多端的人”“是个反动首领,豪绅中很厉害的”人。[2]187汤佛淑,年收租200石,是个劣绅,人称土霸,小学教员讲习所毕业,新寻派走狗。易颂周,年收租200石,前清秀才,是个劣绅,与叶匪有勾结,现跑走了。还有号称“寻乌五虎将”的“潘(明典)谢(虚左)陈(叶凤)彭(子经)邝(太澜)”,其中陈、潘、彭、邝都是秀才,谢是寻乌简易师范毕业生。号为“虎将”,必定凶残狠毒、手段利辣。果然,陈就是年收租200多石的“大劣绅”。[2]188
从上述寻乌各地绅士的经济地位、政治立场、思想倾向不难看出,他们无疑是土地革命的绊脚石。唯有没收其霸占的公田公产,取消其操控地方公共事务的权力,才能彻底实现土地革命目标。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在三年前就指出了:“祠产如不收归公有则对宗法社会不能与以大打击。”“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5)1927年3月15日,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日会议时的发言。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群众,最主要的靠山就是土地,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是依靠着地主阶级,因此土地革命的成功,无疑的将消灭一切封建势力,同时也就是消灭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基础。”[4]《寻乌调查》对公共地主本质深刻有力的揭示,显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事涉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论断。
五、余论
公共地主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成了过去时,但公共地主的话题却还在时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例如,说到某地土地革命时期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会提及他恰恰是受公堂资助才得以中学甚或大学毕业。又如,当下在留住乡愁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号召下,各地普查祠堂、修复庙宇等古建筑,乃至进行整修利用。还有一些地方组织种种民间理事会,协助政府处理社会事务,也不无借鉴历史经验的意思。这些现象起码说明两个问题:
一是公共地主(主要是祖宗地主和政治地主)的某些公益性,像公堂办学助学的兴教之举,公堂义仓借谷给贫苦族人的周济之意,[1]203桥会路会的修桥补路,以及公堂为首为主兴建修缮一地大中型公共建筑,颁布诸戒诸禁以维护地方自然生态与社会秩序等,不可也不必轻易否定。这不仅因为公堂和各种会的经济有部分是大家分摊或募集的(这点在《寻乌调查》中没有反映),而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们纵然有许多糟粕,也还有些许精华所在。
二是虽然公堂有资助族中贫寒子弟读书成材之举,但他们领头造反又恰恰往往先拿公堂开刀,包括动用公堂刀枪,食用公堂积谷、资金,焚烧公堂田契债券等。这看似矛盾的现象,其实不难解释。那就是公堂之初衷,不是让贫寒子弟学成之后代表工农阶级利益,而是要他们更有本事为公堂、为宗族头面人物即有产阶级服务。然而觉悟了的这些贫寒子弟识破了这一点,不能不为了大多数穷苦人的翻身解放,造了公堂及其统治者的反。诚如马克思指出的,资产阶级开矿办厂造就了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却成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不妨说,在这个意义上,《寻乌调查》揭示公共地主本质,具有很强震撼力与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