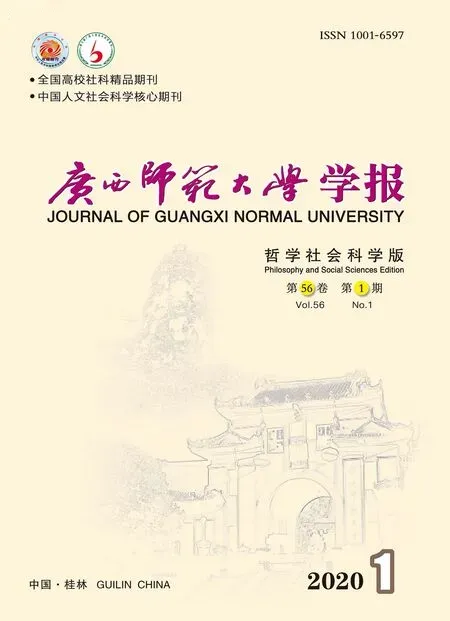神兽西来:丝绸之路上的天马和翼兽
2020-03-16
(四川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一、汉代凿通西域与中亚马神崇拜的东渐
汉代所说的西域,并不是那么遥远。一般来说,广义的西域最远大体上也就是到了地中海西岸这一带,而狭义的西域则主要指西域“三十六国”和中亚一带。汉代开通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从长安出发,然后经过西域三十六国,再越过葱岭,即翻过兴都库什山,然后进入到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这里有文献记载中的大宛、康居等“昭武九姓”,另外还有一支游牧民族叫大月氏,原居于我国北方草原,后来被匈奴一路驱赶到了中亚地区,留下的一部分叫小月氏。匈奴是汉朝的强敌,在汉王朝建国之初形成很大的威胁。所以到了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主持朝政之后,便要设法联合大月氏来共同夹击匈奴。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西域的开通和后来“丝绸之路”的形成,一开始的目的显然不是为了开展丝绸贸易。这个行为最初是从中国方面发动的,具有明显的政治和军事意图,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要去联络大月氏,和汉军形成夹击之势,以取得军事上的奇效。
张骞最远走到什么地方呢?他也就走到了大月氏这一带。但是他的使团派出的一些小分队可能走得更远一些,史书上说到了安息、帕提亚这一带,也就是说已经到了古代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但是,张骞主要活动的区域,还是在中亚这一带(包括西域三十六国)。我们通常所讲的汉代“丝绸之路”,也主要就是在这一带展开。
1978年,一支苏联考古队在著名的中亚考古学家维克多·依万诺维奇·萨瑞阿尼迪(Viktor Ivanovich Sarianidi)带领下,在阿富汗西北部席巴尔干镇附近一个小小的山丘——蒂拉丘地,发掘出一批重要的古代墓葬。他们发掘的六座墓葬当中,五位墓主人是女性,一位是男性。这个地点正好就是在史书记载的“大月氏”活动的地域之内,这就和张骞出使西域到达的大月氏联系起来了,因此学术界推测这可能就是大月氏的“五翕侯”之一的墓群。这几座墓葬里出土了大量黄金制品,总计达到21600多件。其中一些黄金制作的装饰品极富特色,有的是悬挂在女性头部的装饰品,在二号墓、三号墓中都发现了同类的装饰品,甚至在墓中还出土了年代最早的“步摇”。[1]211-293[2]52但是,考古学家们还来不及展开科学的研究和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后,阿富汗就陷入战乱之中。这些黄金制品最早收藏在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但是塔利班对异域文明充满敌意,不仅炸毁了举世著名的巴米扬大佛,也开始攻击阿富汗各地的博物馆,阿富汗国家博物馆也遭到了攻击。当时,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十分担心蒂拉丘地这批黄金宝藏的下落。一直到塔利班倒台之后,我们才知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些勇敢的阿富汗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这批国宝。直到近年阿富汗局势平定之后,这些珍宝才重见天日,开始在全世界巡回展出。
在这些黄金制品当中,有两件冠饰分别出土于两座女性死者的墓中,其母题是“一人双兽”,中间是一位女神或者叫一位女王,她的两边各有一只神兽。这是两只什么样的神兽呢?表面看上去很像是马,它有马的头,还有马的蹄子,但是它的身躯却被拉长,很像是一条龙,它的头上又长着马所不具备的角,是一只独角,所以又像是传说当中的独角兽。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这只神兽的肩上还生出了双翼,似乎还可以飞升。这样一种神兽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却是中亚古老文化中的龙神或者马神。[1]246-247[2]244-245这让我们联想起来,在古代中国也有类似的龙神和马神的记载。如《周礼·夏官》记载:“乃祭马祖……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这个观念很像是来源于古代游牧民族,他们将高大的马称为“龙”。汉代人王充在《论衡·龙虚篇》中也讲,“世俗画龙之像,马首蛇尾,由是言之,马蛇之类也”[3]332。也就是说马跟蛇、龙都是有联系的,它们在形体上是可以合成的。汉代的这些记载当中实际上透露了一个信息,龙本是虚构的动物,但在古代它还与高大的马有关,它们之间有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这个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又是怎样传到中原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当时生活在中国北方的古代少数民族。《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人古代的祭祀:“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笼城,祭其先、天地、鬼神。”[4]2892就是说匈奴人在每年的正月和五月都要举行集会和祭祀,在五月举行的这次祭祀最为隆重,叫做“笼城大会”,这个笼城写的是蒸笼的“笼”字,其实际上就是“龙”,龙蛇的这个龙。《史记索隐》引晋人崔浩注云:“西方胡,皆事龙神,故名大会处为龙城。”所以“笼”和“龙”,古音是可以通假的。这段史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匈奴人的祭祀对象,除了祭天、祭鬼神之外,龙神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祭祀对象。而这里所说的龙,很可能就是匈奴人心目中的高头大马。如果这个推测无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早在西汉和东汉时期,中国的文献典籍已经注意到龙跟马是有关系的,高大的马也是龙,是西方游牧民族心目中崇拜的马神。这个习俗的源头,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来源于西域和中亚。汉文文献中的“胡人”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汉代大概主要是指北方草原地带的一些游牧部族,更多的可能是指“西胡”,就是以匈奴、大月氏为主体的一些胡人族群。从前面我们举出的阿富汗“黄金之丘”可能属于大月支翕侯王墓地所出土的双马神冠饰来看,这些胡人的信仰体系中可能很早就有崇拜马神——也将其视为龙神——这个信仰系统存在,并且也很早就不断向东传播,逐渐进入到中原地区。
二、汉武帝通西域和“天马”的传入
那么,来自西方、中亚欧亚草原地带的“马神/龙神”崇拜是否也通过“丝绸之路”渐次影响传播到中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汉代考古材料中一些新的文化现象。
首先,在汉代考古的图像资料当中,出现了不少象征“天马”的图像,在四川地区的东汉画像中便有大量的天马。不过,目前最早的天马形象,我认为早在西汉时期便已经出现,其典型代表就是出土于甘肃地区汉代墓葬中著名的“马踏飞燕”铜马。过去虽然有不少学者解释过它的图像学意义,但我还是要问,为什么这马不踏乌龟、不踏狗熊、而是去踏着飞燕?这究竟象征着什么含义?很显然,只有当它凌空奔驰的时候,才可能把天上的飞燕踏在它的脚下。所以,它的象征意义是表示它是可以在天空中飞翔的神马,也就是天马。这铜奔马出土在甘肃是有道理的,它应该就是人们想象中的西域“天马”形象的一个最初的雏形,并通过丝绸之路传来。
在当时中国人的想象空间里面,如何表达能够飞翔的物体?中国古人是很聪明的,想要让它飞起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例如,佛教艺术中的“飞天”要飞起来,就给它画上几条飘带,让它就在空中飘舞起来了。那么,让一只奔马踏着飞燕,就可以知道飞得再高的飞燕都会被马踩踏在脚下,这马就一定是可以凌空奔驰的马,那就叫做“天马”。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达方式,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聪明,都这么善于表达。我们观察到的更多的表达“天马”的方式,就是给马背上长出一对翅膀,如同我们在阿富汗蒂拉丘地“黄金之丘”出土冠饰上看到的“一人双马”的情形。后来在四川、河南、陕西等地发现的大量汉代天马的图像,也是生有双翼的天马。
天马一词,最初是《汉书》《史记》等典籍中出现的,而且都和汉代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这个大的历史背景相关。如《汉书·西域传》载:“遭值文、景玄默,养民五世,天下殷富,财力有馀,士马强盛……闻天马、蒲陶则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后……钜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5]3928
丝绸之路的开通,是张骞出使西域带来的结果,但最初只是出于军事和国家政治的目的。等到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它的功能逐渐增加,经济、宗教、商贸各种功能都不断地丰富起来,我认为“天马”的传入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带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产物。天马、葡萄都是异域的奇珍,巨狮、大雀(什么是大雀?照我看来大雀和狮子一样,都是中原地区不见的珍稀动物,它实际上是生活在中亚、西亚一带的鸵鸟)已经成为汉代皇家苑囿(就是皇家动物园)里的观赏性动物。所以天马的出现,一定跟通西域是有联系的,这在史书里交待得很清楚。
在中原地区、四川地区保存下来许多天马的图像,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马的背上长出翅膀,成为长着翅膀的天马。天马的前面有的时候还出现胡人牵引。还有一些时候天马是由仙人牵引。仙人的形象在汉代比较容易辨识,他的头上往往有高耸的发髻,身上长出羽毛。为什么会由仙人来驾驭天马?这显然和汉代升仙的观念有关,我在后面再作分析。
这些天马的形象,很多都长出了短而丰满的双翼。有些天马图像还带着铭刻,其中的一尊便带有“天马”铭刻。但有的学者将其释读为“王马”,这是不对的,因为这个题铭的书体是汉代的八分书,“王”字和“天”字很容易混淆起来。所以,这时天马的图像上有的已经有了题名。不仅如此,在晋代,一些地方志记载还出现了祭祀天马的“天马祠”。如《华阳国志·蜀志》“会无县”条载:“会无县路通宁州,渡泸得堂狼县,故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冢,冢不闭户,其穴多有碧珠,人不可取,取之不祥。有天马河,马日千里,后死于蜀,葬江原小亭,今天马冢是也。县有天马祠。初,民家马牧山下,或产骏驹,云天马子也。今有天马径,阙迹存焉”[6]317-318。 《华阳国志·蜀志》“江原县”条也记载:“文井江上有常堤三十里,上有天马祠”[6]242。从这些距离汉代不远的文献史料可见,当时“天马”的观念和信仰沿着丝绸之路已经深入到了中国西南地区,人们心目中的天马,都是可以“日行千里”的良马,在死后还会专门为它们设立祭祀的祠堂,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会有天马出现?天马传入中土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以往研究天马,大部分学者把注意力放到了改善汉代的骑兵,说汉军和外敌作战战斗力不行,原因主要是马种不好,需要改良马种。汉通西域之后,汉武帝听说大宛有好马、汗血马,因此便不断派出使臣,后来发兵大宛,甚至征服大宛;一开始是以强迫他们贡纳的方式去寻求良马,到后来实在不行,就直接出兵征服,迫使大宛以全国之力来给汉朝贡献良马。究其原因,固然不能排除当中的确有改良马种的意义在里面,但如果我们更为仔细地梳理文献,不难发现,从大宛引进的天马,实际上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要用那么有限的马匹来改善汉军整个骑兵的马种,谈何容易?那么,还有没有别的动因呢?接下来,通过文献史料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隐藏在历史深处的潜在因素。
三、汉武帝的升仙、昆仑神话和天马之关系
汉代“天马”信仰的盛行,是和汉武帝的升仙信仰有密切关系的。在天马信仰和文献史料之间,其实潜伏着一条暗线,只是过去大家不太注意而已。简略追溯一下汉武帝的求仙——也就是祈求长生不死之路,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向海上求仙,如传说中的蓬莱仙山、瀛洲仙岛之类,但是,他的海上求仙失败了,效果不明显。后来,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汉武帝逐渐把目光移向了“陆上丝绸之路”,开始崇信“昆仑神话”。古史记载中的昆仑山,不是指今天我们实实在在地理位置上存在的昆仑山脉,而是战国秦汉以来人们信仰体系当中的一个升仙之处。随着汉代国家版图的不断扩张和西域的开通,昆仑的地理位置也不断向西移动。最初人们认为它可能是在中国的西南地方,四川的峨眉山、岷山,都曾被认为是“昆仑之丘”所在之地。汉武帝以后,昆仑的地理概念不断西移,最后被移到了“流沙”之地,很显然,已经移到今天的“沙漠丝绸之路”上去了。
那么,为什么“昆仑神话”又跟“天马”有关系呢?我们先来看几段史料。《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初,天子发书《易》,曰‘神马当从西北来’。得乌孙马好,名曰‘天马’。及得宛汗血马,益壮,更名乌孙马曰‘西极马’,宛马曰‘天马’云。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犛靬、条支、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4]3170。同样的记载也见于《汉书》中的《张骞李广利传》[5]2693-2694。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文献都出现在和西域有关的记载当中。
文献中所说的“天子”,就是汉武帝,他从《易》书当中得到了“神示”,说“神马”要从西北方向来。他先是得到了乌孙的马,把它叫做天马,后来发现还有更好的马,叫“汗血马”,产自大宛,所以就把乌孙的马改名叫“西极马”,而把大宛的马改叫“天马”。从此以后,汉武帝的求仙从寻求天马开始,动用了国家力量,不断发遣使节前往西域,先后抵达安息、犁鞬、条支等地。“犁鞬”,就是今天的东罗马,稍近一点的就是条支、身毒,“身毒”就是今天的印度。由于“天子好宛马”,以致“使者相望于道”,可见汉武帝的求仙、求天马可谓不遗余力。
这个事件并非孤证,在《史记》的《乐书》当中,也有关于天马的记载:又尝得神马渥洼水中,复次以为太一之歌。歌曲曰:“太一贡兮天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跇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后伐大宛得千里马,马名蒲梢,次作以为歌。歌诗曰:“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4]1178整个是讲汉武帝得到西域神马大宛马以后,非常高兴,他甚至在皇家举行的祭祀活动中也将这个过程写进了祭祀之歌,将愉快的心情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为此专门作歌,称为“太一之歌”,贡奉“太一”之神,歌中颂赞“太一贡兮天马下”。那么,“太一”神又是何方神圣呢?太一就是当时的上帝,也叫天帝。这里所说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汉代中国仙界的最高神,也是昆仑山上的最高神——太一神。歌词大意是说,通了天以后,太一神派了天马来迎接武帝升仙,然后讲这个天马是流着“汗血”的宝马,奔驰万里而来。这里还有一句非常精彩的话,“今安匹兮龙为友”,这正应和了前面所讲的匈奴的“龙神”和《周礼》中记载的马与龙的关系,将天马也作为龙神来看待。
循着这个线索,我们从《汉书》中找到了汉武帝所作《郊祀歌》十九首,其中颂唱道:
太一况,天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权奇,籋浮云,晻上驰。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天马来,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来,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天马来,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天马来,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天马来,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来,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5]1060-1061
在这条史料的后面,有唐人孔颖达为它作的注:“言武帝好仙,常庶几天马来,当乘之往发昆仑也。” 还引了汉代应昭的注:“阊阖,天门。玉台,上帝之所居。” 从而将汉武帝的升仙信仰、喜好天马以及和昆仑神话之间的关系,都揭示得很清楚。汉代应昭注里讲到的“阊阖”,就是昆仑的升仙之门,也叫做“天门”。在重庆三峡地区发现的汉墓木棺的棺首上,曾经发现一些圆形的铜牌饰,铜牌饰的中间刻有两个字:“天门”,守候在天门上面的是西王母,西王母的上面还有一个地位更高的神的形象,虽然他没有题铭,可以肯定那就是天帝,就是我们所说的仙界最高神“太一”。在两阙中间明确地讲了天门,所以天门跟天马形成了一套体系。[7]146-168
后来还有个叫苏林的文人,也是唐代人,给这条史料也作过一个注释:“天马上蹑浮云”,所谓“上蹑浮云”,就是说天马可以踏在浮云之上。前面我们讨论的“马踏飞燕”铜马,正是天马在天上飞翔奔跑,下踏着浮云和飞燕,这是非常形象化的艺术表现。《郊祀歌》中的第二段还形象地描述了天马来自西极,经过流沙,九夷降服,很显然,意思是天马是通过征服西域各国,从丝绸之路传来中土的。最后还有一段很精彩的歌词,“天马来,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这是说天马最后的目的地是到了“昆仑”,这正是天马和昆仑神话之间联系的确切表述,证明天马是可以乘载灵魂去往不死之地——昆仑的乘骑。这些歌词是在汉太初四年汉军征服大宛、获得天马之后写下的,从而再次证明汉武帝对大宛的征讨,对天马的追求是其重要目的,而得到大宛的天马,就等于得到了灵魂去往不死之地、可以升仙的最佳“交通工具”。
四、天马和有翼神兽
天马最典型的形象特征是带有双翼,这种生出双翼的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但是,它却寄托了当时人们可以通过这种有翼的神马升往仙界的希望。事实上,在汉代通西域之后,随着天马传来中国的,并不只限于有翼的天马,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大型的带翼的动物,我们可以将这类动物称为“有翼神兽”。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至少从春秋战国开始,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些带翼的动物形象,李零教授曾经对此作过比较系统的研究。[8]119-121[9]不过,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带翼的“神兽”形体上还较小,和我们所见到的东汉时期的大型有翼神兽区别很大。
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有翼神兽盛行的时代,我认为大体上也应该是从汉代通西域之后开始的。我们的古人已经注意到这个现象。东汉时期的应劭,在他的《风俗通义》里面就说到,当时的墓葬前面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事物。是些什么新的事物呢?就是在墓前出现了石雕的老虎形象,这是过去所没有的。(1)[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殴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故墓前立虎与柏。”应劭著、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4页。后来唐代人封演更进一步指出,秦汉以来,在帝王陵前就开始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石麒麟、石辟邪、石像、石马之类,而在人臣墓前,则出现了石羊、石虎、石人、石柱等等。(2)[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羊虎”条下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封演著、赵贞信校注:《封氏闻见记校注》,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58页。
其实在这个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的变化。商周时期的墓葬当中没有这些石刻,到了秦汉以来(其实准确地讲是汉代以来),才有了这些新的事物。不过,秦代有没有这样的大型石兽目前还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据。西汉时期,在霍去病的陵前,虽然开始出现一些纪念性的大型石刻,但是这些石刻的含义跟我们今天讲的陵前神兽,还不是一个系统,也没有发现当中有带翼的神兽之类。所以我推测,出现墓前的大型有翼神兽,很可能始于东汉时期。
早在1914年,法国人色伽兰(也译成谢阁兰)就在四川地区调查发现过一些大型的石兽,种类有石狮、石羊和石鸵鸟等。他的《西域考古记》一书刊发了许多珍贵的照片。石兽可分雌、雄两种,雄的带有性器官。石兽旁边还有石阙跟它同时共存。[10]10-13后来的调查发现,与这些石兽共存的,不仅有石阙,还有石碑。在东汉时,石阙、石碑、石兽在各个区域都有发现,但是四川地区是非常集中发现的一个区域。色伽兰调查发现的石鸵鸟是站立起来的,这是在同时期相对比较少见的一类石刻。色迦兰除了对这尊石刻像拍摄过照片外,还在书里配上了写生的线图,可以看到鸵鸟的形象非常逼真,这就是文献中所载的“大鸟”,也就是产自中亚和非洲的鸵鸟。近年来,四川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渠县境内开展调查时,重新发现了这批石兽,最重要的是发现了这件鸵鸟的残体,同时还发现有石人,这是过去没有见过的石刻组合。[11]
在四川成都附近有一个叫做芦山的县城,这里有一个石刻博物馆,收藏了九具东汉时期的大型石兽,它们有什么特点呢?第一,非常高大,属于大型的石兽;第二,有的神兽带有短羽,长出非常丰满的羽毛;第三,有性别之分,雄性的带有性器官,没有性器官的就是雌的;第四,有的头上有角,有的是一个角,也有的是双角。说明当时古人对于这些石兽已经赋予了许多象征性意义,它们不再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动物,而是在这些动物的身上添加了很多想象的元素。有的石兽原来可能是狮子的原型,有的可能是老虎的原型,但都带有双翼,这就成为我们所说的“有翼神兽”。
北魏时成书的《水经注》中有很多材料都讲到汉代在墓主人神道的前面,已经出现了石狮子、石麒麟,后来在河南、陕西、山东各地的汉墓前面,发现了许多和四川地区形态相同的大型“有翼神兽”,可以证明文献记载的可信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除了在陵墓前面发现有翼神兽以外,在四川省芦山县一个汉晋时代的城门遗址前面,还发现有镇守大门的有翼神兽。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生前到过这个遗址,看了之后他很兴奋,说这是中国目前发现的第一例镇守城门的石兽,由此表明不仅在地下世界,而且在阳间——就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世界里,也流行这类大型的有翼石兽。它们镇守在城门口的入口处,这和西亚、中亚一带古代城门前的有翼神兽很可能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有翼神兽这个母题的出现,在中国过去的艺术史上没有过,所以我们可以比较大胆地推测,它们的出现,可能还是受到了外来因素的影响,是汉通西域之后新的文化因素,和“天马”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本土。
过去有学者将这些石兽命名为“天禄”“辟邪”“麒麟”之类,并且想方设法去寻求它们的原型。[12]238-251实际上我认为,能够真正找到原型的只有狮子、犀牛、老虎、羊、马、牛等动物,还有就是“大雀”——鸵鸟,这些都是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动物。而所谓“天禄、辟邪、麒麟”等等,和“天马”一样,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动物,也叫“神兽”,给这些本来都活动在陆地上的动物长出一双翅膀来,就成为可以在天上飞翔的“有翼神兽”了。这个构想出的“天国神兽”,是人类对于另一个神灵世界的奇思妙想之一,而且从西方到东方都曾经流行一时。
关于中国有翼神兽的来源,目前学术界大体有两种基本倾向:一是外来说,二是本土起源说。外来说又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些狮形的有翼兽可能来自波斯和北印度,脱胎于古代亚述和波斯。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些有翼兽可能来自中亚波斯,大月氏的黄金艺术当中出现的有翼兽就可能和它们有些关系,受到波斯“拜火教”因素的影响。第三种观点认为是来自欧亚草原艺术中的神兽“格里芬”。[13]67-74[14]这三种观点,各执一端。其实总的来讲,这类有翼神兽的源头,我个人以为都应该从最古老的亚述文明中去寻找,这是世界上出现大型有翼神兽最早的地区,以后是古巴比伦,然后在“有翼神兽”不断演变的过程当中,又传到中亚地区,和多种宗教、多个民族的信仰相结合,产生出不同的变体,形成不同的支系。汉通西域之后,很可能从中亚、印度等地又传到了中国。当然,目前由于缺乏考古学的证据,许多具体的中间环节还不是很清楚,但总的来说,我个人是赞同外来说的,这些有翼神兽、尤其是大型的陵墓前的石兽,比较集中地出现在东汉时期,应当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和汉代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来文化的影响关系十分密切。
五、东汉时期的有翼神兽对南朝陵前石兽的影响
最后我还要谈到一点,东汉时期这些墓前的有翼神兽,对于后来南朝时期帝王陵墓前的神道石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只是汉代的有翼神兽主要流行在社会中下层,两汉帝陵前面目前还没有设置这类有翼神兽石刻的直接证据。但到了南朝,帝陵前面已经形成了一套定制,由石柱、石表、石碑和一对有翼神兽(有的一角、有的两角)配置在陵墓神道的两侧,这个定制对于后来的唐、宋、明、清帝陵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朝陵墓石刻制度的形成,目前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传播路线问题。虽然我们可以推测它是受到东汉以来墓前石兽的影响,但是具体的传播路线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在讨论关于六朝陵墓石兽的具体来源时,不少学者都引证《南史·齐豫章文献王嶷传》的一段记载:
上(齐太祖)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遂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冢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麒麟于东岗上。麒麟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帝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15]
根据这段记载,南朝刘宋时期的石表、石阙和石麒麟都是由宋孝武帝从北方的襄阳制作而来,并且甚为精巧,成为后世南朝诸陵的范品,后世没有能够超过它的。考古发现在和襄阳接壤的南阳一带的确发现过东汉时期的墓前石兽,《水经注》也有关于这个地区石麒麟的记载。只是目前在今天的襄阳一带还没有发现过这类石兽,还有待将来进一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来加以寻找。所以,关于这条传播路线的存在,我们不能轻易否定。但另一方面,我注意到,近年来在长江三峡也发现有汉晋时代的石阙、石柱和带翼的神兽,那么从今天考古学所提供的材料看,可能还要关注到长江通道的问题。从四川到重庆三峡过去有所谓“江水道”的存在,所指就是古代巴蜀之间从蜀地通过长江抵达巴地,然后顺江而下直到长江中下游的历史通道。今天在四川盆地发现的东汉墓前石阙、石兽和重庆三峡地区发现的遗物同属一类,时代上看以四川稍早、三峡稍晚,正好形成为一条传播线路,这对于我们理解南朝时期陵墓石刻的来源,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即除了从北方的襄阳传入南朝之外,还可能从西面的长江水道传到长江中下游地区。
第二个问题,是南朝石兽的造型风格问题。从目前所存世的南朝石兽来比较分析,它们之间是存在造型风格上的不同的。一方面,是由于陵墓等级的不同,可能存在着造型风格的不同,过去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南朝帝陵前的石兽与等级较低一级的南朝贵族墓前的石兽有所不同;还有因时代的关系,南朝前期刘宋时代的石刻,与后来齐、梁时期的石刻也有所变化。[16]我这里还要进一步提出,今后我们还应从南朝石刻可能存在的不同源流上加以考察。比方说来自北方地区的石兽和来自长江上游的石兽之间存在的造型风格是否有所不同,等等。
第三个问题,我们还要关注这些石刻之间组合关系的形成问题。这个问题的观察点可能要从东汉的墓前神道石刻开始。东汉时期出现了这些墓前的石人、石兽、石阙,是否已经存在着形成一定的制度化的迹象?要认真统计、分析一下,这些东汉墓前哪些有碑?哪些有阙?哪些有石表?这些石刻又有哪些种类?是否存在着一定的组合关系?比方说,在一些墓前面出现了石人,这个现象过去我们没有找到太多的例证,但是近年来在四川渠县发现的东汉石阙前面,据说就有石人了,这表明从汉代以来,可能墓前神道的两侧,就既有动物(神兽),也有石人,也有碑,也有阙,甚至还有石表、石柱之类。所以,南朝的这一套陵墓石刻制度,我认为很可能从东汉以来就已经开始在孕育,最后到南朝时期的陵墓时,有关神道石刻已经形成了一套体系。南朝形成定制以后,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唐陵和宋陵。唐、宋陵墓石刻跟南朝、北朝陵墓石刻的关系,也是中国古代陵墓制度的另一个重大问题,但相对而言,南朝陵墓的体系要更为清楚一些,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必须从东汉、南朝着手。现在国内外学术界都十分关注的一点,就是南朝的这套陵墓石刻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南朝去汉不远,所以它们之间是最好作比较的。这个问题清楚了,唐宋以后陵墓石刻的源流演变也会清楚起来。这也是我们目前讨论中国陵墓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第四个问题,是南朝陵墓前的神道石刻制度形成,与统治者对于丧葬礼制的制定与实施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两汉的时候流行厚葬,两汉以后的三国魏晋时期,曹操父子都主张薄葬。他们是不是真正实行了薄葬?现在看起来情况也不是那么简单,可能三国时期的一段时间真正实行了薄葬,但是后来制度开始松弛,实行得不那么严格。两晋时期,帝陵大多“依山为陵”,所以目前还没有发现这个时期的陵墓神道石刻。但进入到南朝的刘宋,又把汉代厚葬的某些传统继承过来,这在陵前石刻上面首先得到了体现。这些问题所涉及的一个根本性因素,是统治阶级内部对于丧葬礼制的顶层设计,以及不同层面对于这些制度的具体实施与执行的情况。在我看来,这一套陵墓体系的形成,可能有上、下两个层面的互动,我们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大型石兽的最初接受者既有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有社会各个不同的阶层。前面我讲过,汉武帝喜欢天马,他的推动是最有力的,势必影响到社会中下层,所以才会出现一个有翼神兽盛行的时代,全国各地都从东汉开始出现了大量与“天马”“有兽神兽”相关的考古遗存。东汉时期,由于汉明帝一朝改革墓祭制度,开始在陵前祭祀,有了“上陵之礼”,所以在墓前有了神道、石阙、石祠堂和石兽之属。但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目前所见的考古材料,这些大型石兽并没有发现在两汉的帝陵前面,而是在地位和品级较低的社会阶层中出现呢?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即在神道两侧设置有翼神兽之类的礼俗,最初只是出现在“人臣”墓前,后来这个习俗自下而上,最后又反射、影响到统治阶级的上层。发展到南朝的时候,终于成为帝陵前固定的一套石刻制度。目前两汉时期的帝陵前面,没有发现过这些石刻,但是到了南朝时期,很显然社会中下层的这些习俗已经被上层统治者所吸纳,开始在帝陵前面出现了等级分明的石刻组合,把这些本来是社会中下层的丧葬习俗,最终上升成为皇家丧葬礼制,形成了一个由下至上的“反向影响”过程。在中国古代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些事关国家层面的制度,不仅仅可以从文献史料的记载当中,也可以从大量的考古实物当中,去寻找历史的遗痕。
在中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同时还提出,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通过本文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自我创新能力,同时也具有融汇外来文明能力的伟大民族。尤其是通过“丝绸之路”,中华民族一方面吸收外来文明,一方面又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实现创造性的转化,从而发展了本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反过来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历史上的“汉唐盛世”,就是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具活力、也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今天,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走向伟大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新时代。重温历史、鉴古知今,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国家所倡导的“一带一路”精神的伟大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从而更加增强“四个自信”,坚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