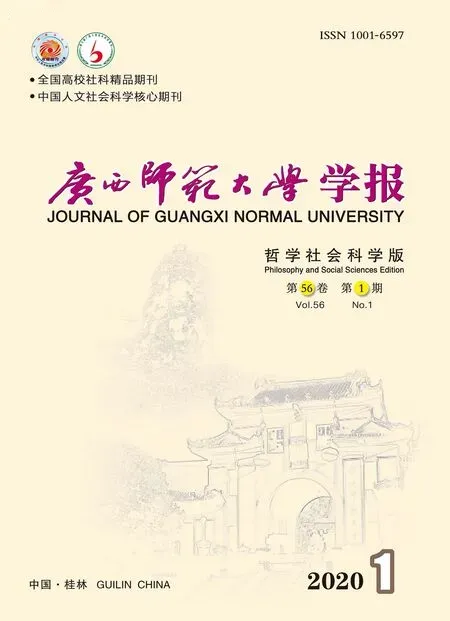社会排斥危机对儿童欺骗行为的影响: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
2020-03-16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一、问题提出
社会排斥是社会交往中存在的一种消极现象,它是指个体被他人或社会群体所拒绝、排斥、孤立或无视,使其基本归属需求和人际关系需求得不到满足[1]。个体被排斥时,常明显地体验到对方在态度上对自己的反感[2],而出现抑郁、攻击等消极情绪与行为[3-4]。托(Thau)等人指出,在社会排斥尚未确立前,被排斥者一直处于被排斥危机状态中,只有当危机状态“累加”到一定程度时,被排斥者才进入排斥阶段[5]。相比较而言,社会排斥危机在群体日常环境中比社会排斥更常见[6]。在某些情况下,排斥仅止于社会排斥危机状态中而不进入最终的社会排斥情境[7]。就概念而言,社会排斥危机是个体觉察到被他人拒绝信号时,感受到自己正处于被他人排斥的一种威胁情境。在这种威胁情境中,个体为了向群体成员“示好”会故意地、主动地做出对群体有益的欺骗行为。如约姆费斯(Umphress)等人研究就表明,员工会通过向顾客夸大同伴销售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来帮助同伴获取利益[8]。基于社会排斥的多元动机理论可知,被排斥者持有与排斥方修复关系的期待,如若被排斥者对人际关系带有可修复性信念时,便会产生更多对排斥方的亲社会行为动机[9]。社会排斥需要—威胁的时间模型(Need-threat model)也进一步指出,当被排斥者认为与排斥方的关系可以修复时,会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当认为与排斥方的关系难以修复时,会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10]。因此,与社会排斥相比,社会排斥危机更可能会引发个体为修复与排斥方的关系而出现欺骗行为。
除成人外,7岁儿童就已开始敏感于社会排斥问题,并理解被群体成员接纳与被群体成员排斥之间是一种动态的社会过程[11]。实际上,儿童群体的社会排斥现象不可避免,且会频繁地发生于校园环境中[12]。鲁杰里(Ruggieri)等人研究发现,10~14岁儿童会报告在社会排斥情境中自己的积极情绪体验和需要满足水平均有所下降。同时,相关研究还证实被排斥儿童还伴有抑郁、焦虑、孤独感、回避行为和自杀等不良的情绪与行为反应[13]。综上,社会排斥对儿童造成的伤害程度不少于对成人的伤害。另外,社会排斥危机可以引起被排斥者行使不道德行为,诸如职员偷窃雇主财物、欺骗顾客和夸大自己业绩等[14]。在校园情境中,现有研究也已证实不利处境(排斥、拒绝)是影响儿童欺骗行为的一个诱因[15]。尤其对于10岁以上儿童来说,他们已经从克服道德他律原则阶段而转向自律原则阶段,会出现与成人相似的欺骗行为[16]。但目前,社会排斥危机情境是否会影响儿童不道德行为的产生尚未得到证实。基于此,本研究拟通过实验研究探讨社会排斥危机对10岁以上儿童欺骗行为的影响。
一般来说,儿童欺骗行为可以分为反社会性欺骗行为与亲社会性欺骗行为[17]。反社会性欺骗是一种利个人的不道德行为,其目的是掩饰自己的错误或保护自己的利益[18],而亲社会性欺骗是利团体的不道德行为,其目的是有益于他人、群体或者社会的利益[19]。基什·格法特(Kish-Gephart)等人的研究表明个体的不道德行为是有益于自己而不是有益于他人,属于反社会性欺骗行为[20];但托等人的研究却发现在社会排斥危机中,群体成员的不道德行为是有利于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受益,属于亲社会性欺骗。在社会排斥危机中,被排斥者因自己的归属感需要受到威胁,使得他们更渴望得到群体其他成员的接纳,从而导致其为群体利益而行使欺骗。特别是与低归属需要者相比,高归属需要者对群体接纳的需要更为强烈,他们更愿意融入群体并维持与群体的关系[21]。这提示,归属感需要可能调节着社会排斥危机对儿童欺骗行为影响的作用。综上,儿童在校园环境中遭受社会排斥危机和社会排斥一样影响着其随后的行为,但前者是否有别于社会排斥对儿童心理有独特的威胁作用?归属需要水平在两者间的作用又是如何?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拟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H1:遭受社会排斥危机儿童比遭受社会排斥儿童会表现更多的利团体欺骗行为;H2:高归属感需要的儿童在面对社会排斥危机时,会比低归属感需要儿童做出更多利团体欺骗行为。
二、实验一:社会排斥危机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一)方法
1. 被试
从某小学随机选取132名10~11岁儿童,由于3名儿童不能理解实验任务而无法完成实验被剔除,剩余有效被试129名(男69名,女60名),平均年龄10.71 ± 0.79岁。所有被试自愿参加实验,智力正常,均能正确理解指导语,也未参与过类似实验。
2. 实验材料
(1)社会排斥和社会排斥危机任务材料。研究采用Dewall等人的偶然排斥任务范式[22]和托(Thau)等人的社会排斥危机启动任务范式。任务材料内容根据本土文化背景下小学生实际生活情境加以改编,并用E-prime编程呈现实验任务。首先,实验任务材料是根据研究者的课堂观察及学生、教师反馈而搜集8种10~11岁儿童感兴趣的课外活动,包括科技嘉年华、郊游、校外公益活动等。随后,随机选取46名10~11岁儿童(平衡性别,平均年龄10.01 ±0.31岁,被试均未参与后续研究)对上述课外活动进行5点评分,将得分最高的“科技嘉年华活动”确定为最终实验任务。其次,实验任务中的虚假人物情况资料。研究者在三个实验组中分别设置3名虚假被试,这些虚假被试的资料也是通过20名10~11岁儿童(平衡性别,平均年龄10.11±0.41岁,被试均未参与后续研究)对6名儿童的喜欢程度进行5点评分,评分排在前3名的虚假人物用于社会排斥危机组或社会排斥组,后3名的虚假人物用于控制组。最后,采用《被排斥感自评问卷》和《被排斥危机自评问卷》用于评定被排斥感和被排斥危机感。研究使用两个问卷的主要目的是评定实验任务操纵的有效性,两者均为7点计分。
(2)欺骗行为任务材料。改编自Maryam Kouchaki的问题解决数字矩阵任务范式[23]。任务材料为20个数字矩阵,每个矩阵由12个数字组成(按3×4排列),数字取值区间为[0,10],根据被试认知水平将数字的精确度由原来的两位小数变为一位小数。数字矩阵通过java编程生成,符合条件为:每次生成12个数字,每个数字均为小于10且含有一位小数的正数,12个数字中有且只有两个数相加为10,共生成20组数字。研究随机抽取20名10~11岁儿童(平衡性别,平均年龄10.09 ±0.17岁,未参与后续研究)对20组矩阵任务进行试测,结果表明每组任务解决的平均时间为7.23s~21.31s,最后选取平均解决时间在10s~15s的10组数字矩阵为真任务材料。对剩余10组数字矩阵均通过改变一个数字来保证每个矩阵中没有相加为10的两个数,将其作为假任务材料。实验任务就是要求被试从每个数字矩阵中找出相加等于10的两个数,20个矩阵任务中有10个任务为真任务,10个为不可能完成的假任务。在假任务中,被试报告解决的任务数量越多,其欺骗行为越多。
3.实验程序
首先,将被试分配到社会排斥威胁和社会排斥任务,在安静的教室对每一位被试逐一测试,主试对被试宣读指导语。主试要求被试进入实验界面,按要求依次完成活动介绍、个人介绍、成员相互了解和反馈等任务。主试在社会排斥危机组的反馈为:“小组其他三位成员都选择了不想和你一起完成最后活动,但这只是初次选择,在下一环节后,他们还会进行二次选择,最终决定你是否能够参与最后活动”;主试在社会排斥组的反馈为:“小组其他三位成员都选择不想和你一起完成最后活动,所以你不能和他们一起参与最后活动,但你可以自己完成下一环节活动”;主试在控制组的反馈为:“第一环节结束,请继续认真参与其他环节活动”。
其次,在被试完成第一阶段实验任务后,被试要填写《被排斥感自评问卷》和《被排斥危机感自评问卷》。
接着,被试继续完成欺骗行为任务。首先主试向不同实验组的被试呈现不同指导语:利团体组指导语为:“你将代表所在小组与另一小组成员进行比赛,比赛结果会通知你所属小组的其他成员,若取得胜利,你和你小组3名成员会获得额外的物质奖励”;利个人组指导语:“你与另一小组的一个成员进行比赛,比赛结果会通知你所属小组的其他成员,若取得胜利,你自己会获得额外的物质奖励”。随后,被试完成数学任务矩阵任务。
最后,实验任务结束时,主试告知被试实验中的小组成员均为虚假被试,解释活动目的仅为了实验研究,如果实验后仍感到不适,请及时与主试联系,并向被试发放小礼品以表示感谢。
4.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多因素方差分析考察社会排斥危机和社会排斥对儿童欺骗行为影响的差异。
(二)结果与讨论
1. 操纵的有效性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社会排斥危机组儿童的被拒绝危机感和小概率接纳感均显著高于控制组(t被拒绝危机感=13.03,P<0.001,Cohen’sd=2.54;t小概率接纳感=14.18,P<0.001,Cohen’sd=2.89);社会排斥组被试的未接纳感和被拒绝感均显著高于控制组(t未接纳感= 16.41,P<0.001,Cohen’sd=3.65;t被拒绝感= 14.89,P<0.001,Cohen’sd=3.23)。结果表明,研究中的社会排斥危机任务和社会排斥任务操纵均有效。
2. 社会排斥危机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采用2(社会情境:社会排斥危机组/社会排斥组)×2(欺骗行为类型:利团体/利个人)两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社会情境的主效应显著,F(1,129)=14.50,P<0.001,η2=0.19),社会排斥危机组儿童的欺骗行为显著多于社会排斥组;欺骗行为类型的主效应显著,F(1,129)=7.60,P<0.01,η2=0.06,利团体组儿童的欺骗行为显著多于利个人组儿童;社会情境与欺骗行为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2,129)=7.79,P<0.01,η2=0.11。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在社会排斥危机下,儿童利团体欺骗行为显著多于利个人欺骗行为(F=19.08,P<0.001,η2=0.17),而在社会排斥和控制条件下,利团体欺骗行为和利个人欺骗行为无显著差异,表明社会排斥危机显著影响儿童的利团体欺骗行为出现。
实验一从社会情境角度考察儿童欺骗行为,研究结果证实社会排斥危机与社会排斥一样可以影响儿童欺骗行为,且发现社会排斥危机对儿童利团体欺骗行为影响作用更为显著。结果与假设H1一致,被排斥危机组儿童比被排斥组儿童表现出了更多的利团体欺骗行为。那么,社会排斥危机如何影响儿童欺骗行为的产生?由于个体被排斥后,为挽救自己与群体成员间的关系,他们可能出现利团体的亲社会行为,以便再次获得群体的认可。只有无法改变与团体成员的关系时,他们才会出现反社会行为[24]。研究推断当个体处于被排斥危机时,可能其归属感受到了威胁而做出对群体有利的行为。因而,利团体欺骗行为就是个体为迎合群体需要而出现的反应。为此,在实验二,研究通过加入归属感变量来考察社会排斥危机对儿童欺骗行为的调节作用。
三、实验二:社会排斥危机对欺骗行为的影响:归属感需要的调节作用
(一)方法
1.被试
从某小学随机选取188名10~11岁儿童,由于4名儿童不能理解实验任务而无法完成实验被剔除,剩余有效被试 184名(男94名,女90名),平均年龄10.80 ±0.85岁。所有被试自愿参加实验,智力正常,均能正确理解指导语,也未参与过类似实验。
2.实验材料
(1)社会排斥危机材料和欺骗任务:同实验一。
(2)归属需要量表(Need To Be-long Scale,NBS) 采用Leary等人编制并修订的《归属需要量表》[25],用于测量个体对社会接纳的渴望程度和对社会排斥的厌恶程度。该量表包括10个项目,共有接纳、包容和归属感3个维度,采用7点评分,得分越高表明其归属需要越强。在本研究中,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9。在社会排斥危机任务后,主试让被试填写该量表,并根据被试得分从高到低排序,前30%的被试为高分组,后30%的被试为低分组,经检验两组被试得分差异显著(t=22.14,P<0.001,Cohen’sd=3.99)。
3.实验程序
社会排斥危机任务基本同实验一,仅在不同社会排斥危机组中对被试的指导语反馈上有所修改。在高社会排斥危机组中,主试反馈给被试:“小组其他3位成员都选择不想与你一起完成最后的活动,但这只是初次选择,在下一环节结束后,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二次选择,最终决定你是否能参加最后的活动”;在低社会排斥危机组中,反馈给被试:“小组其他3位成员有部分成员选择不想与你一起完成最后的活动,说明小组中部分成员愿意和你一起完成最后的活动,同时部分成员不愿意和你完成最后的活动。这只是初次选择,在下一环节结束后,他们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二次选择,最终决定你是否能参加最后的活动”。
4.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两组社会排斥危机的效果,以及通过多因素方差分析考察社会排斥危机和归属需要对欺骗行为的影响。
(二)结果与讨论
1. 操纵有效性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在高社会排斥危机组被试的未接纳感和被拒绝感都显著高于低社会排斥危机组(t未接纳感=12.83,P<0.001,Cohen’sd=1.90;t被拒绝感=15.00,P<0.001,Cohen’sd=2.20),说明社会排斥危机实验任务操纵是有效的。
2.社会排斥危机与归属需要对欺骗行为的影响。采用 2(社会排斥危机:高/低)×2(归属需要类型:高/低)×2(欺骗行为类型:利团体/利个人)三因素组间方差分析。结果表明,社会排斥危机主效应显著F(1,121)=16.35,P< 0.001,η2=0.13,高社会排斥危机组被试欺骗行为(M高社会排斥危机=5.68,SD高社会排斥危机=1.94)显著高于低社会排斥危机组(M低社会排斥危机=4.48,SD低社会排斥危机=1.55);归属需要类型主效应不显著F(1,121)=0.32,P>0.05。社会排斥危机与欺骗类型交互效应显著,F(1,121)=21.22,P<0.001,η2=0.16。进一步效应分析显示,仅在高社会排斥危机下,利团体欺骗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利个人欺骗行为得分(P<0.001)。社会排斥危机、归属需要类型和欺骗行为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F(1,121)=12.63,P<0.001,η2=0.10。进一步简单简单效应分析显示,仅在高社会排斥危机且利团体情境下,高归属需要儿童的欺骗行为得分显著高于低归属需要儿童(P<0.001),说明归属需要在高社会排斥危机与利团体情境中对儿童欺骗行为起调节作用。
实验二进一步考察了归属需要在社会排斥危机与欺骗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高社会排斥危机儿童的利团体欺骗行为显著高于低社会排斥危机,说明高社会排斥危机对儿童利团体欺骗行为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当加入归属需要后,研究发现高社会排斥危机条件下的高归属需要儿童的利团体欺骗行为会显著高于低归属感,证实了高社会排斥危机对高归属感需要的儿童的影响更为显著,验证了假设H2。杜瓦尔(DeWall)等人认为归属需要较高者更会关心与群体人员间的关系[22],当处于排斥危机时,高归属感需要的儿童会采取更多利团体欺骗行为以缓和与群体成员间的社交关系。
四、总讨论
社会排斥危机作为一种“非明确”排斥,是群体成员对个体发出排斥信号的过程状态。实验一探讨了儿童遭受社会排斥危机与社会排斥后的欺骗行为,结果发现处于社会排斥危机组儿童比社会排斥组表现出更多的欺骗行为,但社会排斥危机组儿童利团体欺骗行为显著多于利个人。实验二在实验一的基础上,还发现儿童的归属感需求水平对在高社会排斥危机且利团体情境下的欺骗行为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对利个体欺骗行为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结果发现,遭社会排斥危机的儿童比遭社会排斥的儿童表现出更多的欺骗行为,与以往研究的结果一致[5]。社会排斥所形成的是一种明确的排斥关系[26],而社会排斥危机则是一种尚未形成最后排斥关系的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未被接纳的个体一直处于社会排斥危机状态里。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排斥与社会排斥危机均是个体与群体形成的不良人际关系,仅在排斥程度上有所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儿童在社会排斥危机中有更多的欺骗行为,这可能是社会排斥危机使被试还无法确定自己最终被接受还是被拒绝,他们尚需进一步努力才能得到明确的结果,因而会和成人一样选择采用诸如欺骗、盗窃等不道德行为去努力修补与群体的关系。然而,研究进一步发现,儿童仅在社会排斥危机中出现了利团体欺骗行为的优势性。这可能是因不确定的排斥状态增加了处于社会排斥危机者对群体成员的关注度,并意识到群体成员有可能成为自己合作的对象,所以他们会采用利团体的欺骗行为来实现与群体成员之间建立联系的愿望。以往研究曾指出,在任何年龄阶段,人们得到自己所在群体成员的接纳对个体的身心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27]。所以,儿童为了与群体成员保持良好关系,他们会通过自身努力来让其他成员认为自己对群体有着一定的贡献性与价值性,以便进一步争取到群体成员的广泛认可。即便儿童意识到自己做出的努力行为是一种不道德行为,但为了给群体做出贡献,提高自己的接纳度,他们会弱化利团体欺骗所带有的不道德性而行使有利于团体利益的欺骗行为。
实验二继续探讨了社会排斥危机对儿童欺骗行为影响关系中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儿童在遭受社会排斥危机后,其归属感需要水平显著调节了利团体欺骗行为,即与低归属需要儿童相比,高归属需要儿童在遭受社会排斥危机中会表现出更多的欺骗行为。马内尔(Maner)等人曾解释人们在受到排斥后会出现亲社会行为的原因是与群体成员联结的归属需要未得到满足,产生了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强烈欲望,进而以亲社会行为融入群体来满足归属感需要[28]。利团体欺骗正是个体处于群体排斥危机时,为提高群体成员的接纳度,给集体赢得利益而行使的欺骗行为。可以说,社会排斥危机导致儿童的利团体行为就是个体为了维护自己与群体关系,通过为群体做出贡献,来增加自己对群体的归属感。因而,与利个体欺骗行为相比,社会排斥危机对利团体欺骗行为的影响更大。同时,归属需要较高者拥有与群体成员建立联系的需求也较高[2],当他们接到社会排斥信号而处于社会排斥危机中时,更可能采取积极的措施来缓解或弥补与群体成员间的“破裂”关系。利团体欺骗正是一种可以缓解儿童与群体之间关系的方法。特别是拥有高归属需要的儿童,在社会排斥危机情境中更易出现利团体欺骗行为来满足自己的归属感需要。
本研究不仅深化了社会排斥相关研究对儿童不良行为的影响,而且基于社会排斥危机角度的研究也细化了不同社会排斥程度对个体影响的后效差异。研究结果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找出影响儿童产生不良行为的原因。研究结果发现社会排斥危机是诱发儿童不道德行为的重要因素,也对相关部门预防与治理校园背景中的社会排斥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教师与学校也应该关注遭受排斥危机中的儿童,以防范其不道德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