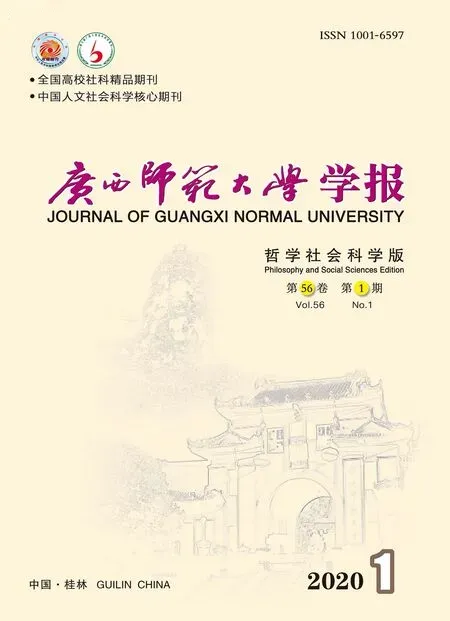论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下的执行问题
2020-03-16孙颖
孙 颖
(1.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8;2.澳门科技大学 法学院)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随着国际投资数量的日益增加,投资仲裁作为一种“定纷止争”的国际通行方式,已然成为“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投资争端”(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简称ISDS)的主要途径。依据1965年《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投资争端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或ICSID公约)设立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简称ICSID),是迄今为止处理ISDS最多的国际投资仲裁机构。
国际投资仲裁裁决的执行对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的保障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对投资者而言,投资仲裁是独立于东道国当地救济的争端解决途径,目的在于为投资者提供更为有效的保护机制。争端中投资者的利益最终要通过裁决的执行来落实,关乎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实现,因此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投资争端解决程序保障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东道国而言,如果在投资仲裁中败诉而对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则可能会被认为构成对投资者的间接征收而引发新的争端请求。如在“Saipem公司诉孟加拉国”一案中[1](1)Saipem S .v.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Bangladesh, ICSID Case No. ARB/05/7, Decision on Jurisdiction, 21 March 2007.,投资者针对商事仲裁未得到有效执行,转而就相同的问题对孟加拉国提起国际投资仲裁,并且仲裁庭认定具有管辖权。同时,该案中ICSID仲裁庭认为孟加拉国对于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行为构成对投资者的间接征收,不仅认定之前的商事仲裁有效,同时裁决东道国对于其新的违约行为进行赔偿。因此不合理地拒绝仲裁裁决的执行可能对投资者造成二次违约而加重东道国的负担。可见,仲裁裁决的实际执行是维护裁决流通性的有效措施,亦是防止重复诉讼的重要程序。
一、问题的提出
通过ICSID裁决的投资仲裁案件,其仲裁管辖依据来自《华盛顿公约》第25条管辖条款的一般规定与双边投资条约(BIT)争端解决条款的特别规定,其承认与执行程序则在《华盛顿公约》规定的机制下进行。但投资仲裁实践表明,并非所有的ISDS都在ICSID管辖下裁决与执行,有相当一部分ISDS案件是通过ICSID以外的国际商事仲裁途径加以解决,其裁决的执行自然无法适用ICSID公约机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双边投资条约(BIT)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条款,除了规定可通过ICSID仲裁解决外,还允许双方选择其他仲裁机构或临时仲裁解决投资争端。BIT下的投资争议管辖权,双方如不能通过友好方式解决争端,一般规定可选择3-5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包括ICSID、PCA(常设仲裁法院)、ICC(国际商会仲裁院)、SCC(斯德哥尔摩仲裁院)、UNCITRAL(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的临时仲裁(ad hoc)等。[2]此即所谓的“菜单式”(cafeteria style approach),实际上是由投资者自行选择。
当双方通过BIT选择非ICSID的国际商事仲裁解决投资争端时,就会产生其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2)全称为《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1958年订立于纽约),该公约于1987年4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下承认与执行的问题。ICSID是专为ISDS设立的投资仲裁机构,但ICSID之外的仲裁在性质上属于商事仲裁,通过缔约双方事先选择而得以适用。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官网统计,截至2018年12月20日,由ICSID受理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件共计569件,占投资仲裁案件总数的74%。而其余26%的投资仲裁案件,则为通过BIT的约定,主要以UNCITRAL规则为依据而在非ICSID机构作出仲裁,其中PCA达128件、SCC为47件、ICC有15件。(3)资料来源:https://investmentpolicyhub.unctad.org,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26日。
关于国际投资仲裁的承认与执行,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为数不多,仅涉及投资仲裁在ICSID体系中的执行问题,而未见针对国际投资仲裁在《纽约公约》下的执行问题研究,其实两者存在相互联系与彼此独立的关系。非ICSID投资仲裁裁决执行中所面临问题大致涉及以下方面:(1)《纽约公约》的适用范围是否包括ISDS在内;(2)非ICSID仲裁裁决执行中的程序问题与制约因素;(3)投资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国家豁免权问题;(4)非ICSID投资仲裁在我国能否得到承认与执行。
二、《纽约公约》适用于投资仲裁裁决的可行性分析
由于《纽约公约》规制的是不同国家的自然人或法人之间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理论角度阐明其能否适用于ISDS投资仲裁裁决的执行,即公约的适用范围问题。《纽约公约》系为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而特别成立的公约,目的在于设立自然人或法人间商事争议而产生国际仲裁裁决的执行机制。对于投资仲裁裁决在《纽约公约》下的执行问题,不仅应厘清商事仲裁与投资仲裁的关系,亦应解决投资仲裁对《纽约公约》的主体适用性问题。
如前所述,多数投资协定规定除了将投资争议提交ICSID仲裁解决外,双方还可选择根据《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UNCITRAL仲裁规则)解决投资争议。2013年,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对UNCITRAL仲裁规则作出重要修订,增加了第1条第4款,规定了对于依照为投资者提供保护的条约提起的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仲裁,UNCITRAL仲裁规则还包括了《投资者与国家间基于条约仲裁透明度规则》,主要原因在于UNCITRAL仲裁规则已被广泛用于ISDS。但是,根据UNCTITRAL仲裁规则作出的投资仲裁裁决,只能被视为仲裁地国的裁决,因此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一样,可以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在缔约国范围内申请承认和执行。
关于《纽约公约》的适用范围,其第1条对此的规定是:“由于自然人或法人间的争执而引起的仲裁裁决,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作成,而在另一个国家请求承认和执行时,适用本公约”。可见其主体与范围是自然人或法人之间需要承认和执行的商事仲裁裁决。但投资仲裁涉及的是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如何能通过《纽约公约》得到执行,则需要予以具体分析。
首先,国际投资活动性质上属于商事行为,而通过非ICSID机构或临时仲裁庭进行的投资仲裁则应视为国际商事仲裁的特殊形式。因此,由其裁决的实际承认与执行仍需求助于《纽约公约》,这已在实践中得到大多数缔约国的认可。商事仲裁与投资仲裁参与的主体不同,前者是解决自然人或法人平等主体之间的商事纠纷,后者是解决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纠纷,虽然在投资管理过程中投资者与东道国的权利义务并不对等,但仲裁过程中双方具有同等地位,享有同等仲裁权利义务。也有国际条约在定义商事行为时,以列举的方式将投资涵盖进去。从投资性质而言,将国际投资仲裁视为特定的国际商事仲裁并无不可。国际投资仲裁制度起始于国际商事仲裁,但两者又存在明显区别。20世纪以来,国家开始参与商贸活动,导致其法律地位从单纯的主权地位复杂化为兼具商事关系的当事人。[3]因此,虽然《纽约公约》第1条规定适用于自然人、法人之间的裁决,但因投资仲裁中国家在实施有关商业交易行为时可作为一般的民事主体,并不能成为适用《纽约公约》的障碍,缔约方的国家性质与《纽约公约》的目的其实无关。(4)根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2条,国家在实行商业交易时不享有财产豁免权,该公约第2条对于“商业交易”有明确的解释。
其次,虽然《纽约公约》并非专门调整投资者与国家仲裁裁决执行的公约,但缔约国一般在双边投资条约中约定,除了将投资争端提交ICSID管辖外,也可选择提交其他国际商事仲裁机构解决。因此,《纽约公约》可在非ICSID仲裁情况下得到适用,其适用范围可扩展到ISDS投资仲裁领域。在国际投资领域,主要适用于区域或双边投资条约中约定的通过非ICSID 投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
此外,虽然《纽约公约》第1条将适用主体范围限定于自然人或法人之间的商事仲裁裁决,但《纽约公约》第7条对此所作的补充规定表明其调整范围也可包括ISDS投资仲裁在内,即“本公约之规定不影响缔约国间所订关于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之多边或双边协定之效力,亦不剥夺任何利害关系人可依援引裁决地所在国之法律或条约所认许之方式,在其许可范围内,援用仲裁裁决之任何权利”。由此可见,公约第一条规定的是适用范围的一般原则,而第7条规定的是适用范围的特别原则。在ISDS当事人选择接受非ICSID仲裁管辖情况下,ISDS仲裁裁决亦可在《纽约公约》下得到执行,虽然裁决的执行必须符合执行地国的程序规则要求。对此,《纽约公约》第3条中规定:“各缔约国应承认仲裁裁决具有约束力,并依援引裁决地之程序规则及下列各条所载条件予以执行”。
三、《华盛顿公约》与《纽约公约》下的不同执行机制
尽管如此,ICSID与非ICSID的裁决在承认与执行机制方面仍存在着较大区别。两者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分别适用彼此独立与不同的机制。就裁决的承认而言,《华盛顿公约》赋予了ICSID裁决更高的效力。ICSID下的仲裁裁决不仅具有终局性,而且不受制于东道国或执行地国的司法审查干预,更有利于裁决的承认与执行。由于非ICSID裁决的执行依据是《纽约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因此各缔约国对于裁决的效力仍具有司法审查权。但在执行程序的法律适用方面,无论是ICSID还是非ICSID裁决,执行中均应依被申请国的国内法程序规定进行,尤其是公共秩序保留与国家豁免原则的援引或抗辩,都会对裁决的执行形成一定障碍或产生不利影响。
(一)ICSID仲裁裁决执行的特点
多数双边投资协定及不少区域投资协定一般都会规定,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间的投资争议应提交ICSID仲裁解决。由于《华盛顿公约》致力于设立独立于各国政府及其国内法的多边体系,因此对ICSID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有较完备的规定。该公约第53~55条对于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义务作了明确规定。根据公约第53条,赋予了ICSID裁决的最终效力,其仲裁裁决对争议双方均具有约束力,且不受任何上诉或除公约规定救济措施以外的任何救济措施的约束,双方当事人应该遵守裁决所规定的义务。
关于裁决执行的所在国,《华盛顿公约》并不要求投资者必须在东道国对仲裁裁决申请予以承认和执行,理论上投资者可以选择任一其认为裁决最有可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缔约国提出申请。为此,公约第54条针对所有缔约国作出进一步规定,即“任何缔约国都应该承认根据公约做出的裁决为有拘束力的,并且在其境内如同执行其本国法院的终审判决一样执行裁决中规定的金钱义务”。可见,为保证ICSID仲裁裁决的效力,《华盛顿公约》直接排除了缔约国对其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换言之,任何缔约国的法院均无权撤销或者拒绝执行ICSID作出的仲裁裁决。但具体的执行程序必须适用执行地国的国内法规定。此外,公约第55条仍然保留了东道国的执行豁免(国家豁免)作为执行裁决的例外条款。
(二)非ICSID仲裁裁决执行的特点
关于国际投资仲裁的提起方式,投资者既可基于与东道国订立的投资合同提起,也可根据其母国与东道国签署的BIT提起,由此形成了合同请求仲裁与条约请求仲裁。在ICSID仲裁中,无论是合同请求还是条约请求,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都应以《华盛顿公约》的相关规定为依据。但在非ICSID仲裁中,基于不同请求依据所提起的仲裁,在裁决执行的法律依据或适用上会有所不同。前者以适用东道国法为主,而后者则以适用投资条约为主。
因此,非ICSID仲裁的条约请求中,投资仲裁应当以投资条约为诉因。此种模式下,只要BIT中对于裁决执行有相应约定,那么对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就应首先符合BIT中对此的相应规定。随着2000年以来BIT的更新换代,近年来的BIT中逐步出现了关于仲裁执行的内容。
就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BIT而言,对于非ICSID的裁决执行规定通常有两种模式,第一种较为笼统,仅规定裁决是终局的,缔约双方应该执行。(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7条第7款。此种模式下,多数BIT中将执行的依据规定为缔约双方根据各自的法律承担相应的执行义务。(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8条第6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立陶宛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与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8条第5款。按此模式,国内法对于执行程序的相关规定就显得至关重要。第二种较为具体,不仅规定了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而且明确载明了执行的条件。例如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BIT中,要求依据UNCITRAL或者ICSID附加便利规则作出的裁决只有满足裁决作出90日之后无一争端方启动修改、取消或撤销裁决的程序,或法院已驳回前述程序而申请方未上诉的情况下,才可进入执行程序。(7)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政府关于鼓励和相互保护投资的协定》第12条第9款。由于中乌投资保护协定中第12条第5款规定了BIT适用的优先效力,因此该协定中关于裁决执行的相关规定也应当优先适用。
在非ICSID仲裁中,无论是合同请求仲裁还是条约请求仲裁,缔约双方多选定在UNCITRAL规则下组成临时仲裁。在这种情况下,则需要根据UNCITRAL规则进行仲裁。换言之,UNCITRAL下临时仲裁的关键是根据其仲裁规则进行,仲裁裁决亦为终局,对争议各方均有约束力。因此UNCITRAL规则下的仲裁裁决具有可执行性,但对执行程序未作具体规定。其在执行地国的实际承认和执行仍需求助于《纽约公约》。至于投资仲裁裁决能否作为《纽约公约》规制下的“商事仲裁裁决”,在我国得到承认和执行也是需要事先确定的前提问题。
四、投资仲裁裁决执行中的司法审查与国家豁免问题
虽然《纽约公约》第3条规定各缔约国应承认裁决具有拘束力,但实践中胜诉方申请执行裁决时仍可能面临法律障碍,因为《纽约公约》第5条第1款和第2款分别规定了东道国可以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对裁决效力进行审查。此外,对于非ICSID仲裁在《纽约公约》下的承认与执行,被申请执行国的法院除了以《纽约公约》规定的司法审查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外,还可能采纳被申请人提出的国家豁免的抗辩。
一般而言,被请求国作出对仲裁裁决的承认并不难,因为被申请方同意仲裁即构成对仲裁管辖和承认方面抗辩的放弃,但在执行方面尚存在较大障碍。如果有关国家通过“绝对豁免理论”抗辩,那么申请人申请执行获得支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是采纳“执行限制豁免”的国家,也必须由申请人证明其申请执行的财产属于商业性财产或用于商业目的。
(一)《纽约公约》下的司法审查问题
《华盛顿公约》要求缔约国无条件承认ICSID仲裁裁决的效力,而将裁决的承认与缔约国的司法审查权予以隔离,因此国内法院不能对ICSID裁决进行司法审查,虽然公约中仍有主权豁免的规定。但对非ICSID仲裁机构(如UNCITRAL临时仲裁庭)裁决的执行,除了应符合《纽约公约》所规定的原则外,还应适用与符合执行地所在国的法律。对此,《纽约公约》第5条规定了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一般原则,具体涉及其第1款所规定的5种情形,主要包括仲裁协议无效、仲裁程序未经适当通知、裁决超过仲裁申请范围、仲裁庭组成不当、裁决尚未生效或被废止。但对上述情形的审查并非由执行地国法院主动进行,而必须基于仲裁一方当事人的申请。第2款规定了在涉及可仲裁性或执行地国的公共政策时,执行地国法院可以依照职权主动审查。可见《纽约公约》赋予了缔约国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可依据《纽约公约》的以上一般原则规定以及执行地国内法所规定的具体规则,以决定是否对投资仲裁裁决予以承认与执行。
国际投资仲裁中,可仲裁性问题理论上不会成为阻碍仲裁裁决执行的理由。因为各国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时已同意将投资争端提交仲裁解决,应视为放弃了可仲裁性抗辩,前提是双方对仲裁管辖并无异议或仲裁庭已否决了当事人的管辖异议。就公共政策问题而言,各国法院在实践过程中很少以此作为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各国对公共政策的内涵并无明确界定,在实践中亦无统一适用标准,因此各国在司法审查中对公共政策的适用非常谨慎。在我国近20年适用《纽约公约》的实践中,也仅有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3464/MS/JB/JEM号仲裁裁决以违反公共政策为理由拒绝承认和执行的案例。(8)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8】民四他字第11号复函,资料来源:www.sohu.com/a/85266657_398113. 最后访问日期:2019年11月25日。
就司法审查而言,在我国,通常认为国际投资的可仲裁性问题不能成为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因为我国加入《华盛顿公约》即认可了国际投资争端是可以仲裁的。[4]而公共政策的适用范围需要根据实践案例具体情形作出判断,难以从理论上作出统一界定。各缔约国在价值观念、法律制度、社会环境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对公共政策的内容判断标准也不一致。公共政策保留作为法律适用与承认执行的例外原则,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应该审慎适用,从严掌握。
(二)《纽约公约》下的执行豁免问题
根据《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的规定,国家豁免问题可成为不予承认仲裁裁决的抗辩理由,且具有一定正当性。由于国际商事仲裁关系中国家通常不是争端一方,因此《纽约公约》并未直接规定以国家豁免作为拒绝承认和执行的理由。但按《纽约公约》第3条的规定,各缔约国在执行裁决过程中需依援引裁决地的程序规则和公约下列各条规定的条件执行。可见,各缔约国国内法中涉及国家豁免的规定也会影响裁决的执行。与ICSID仲裁裁决执行需要遵循国内立法的规定相同,在非ICSID投资仲裁中涉及通过《纽约公约》执行裁决时,东道国享有一定的执行豁免权,并可以国家财产豁免作为抗辩理由。
1.国家豁免理论在投资仲裁中的适用
国家豁免是国际法中的一项传统原则,分为管辖豁免以及执行豁免,后者主要针对国家财产豁免。根据国家豁免的一般理论,国家对诉讼管辖豁免的放弃并不等于对财产执行豁免的放弃,因为管辖豁免与执行豁免并非等同,除非有关国家对此明示放弃。[5]实践中,不少国家的法院将裁决的承认阶段与执行阶段加以区分。前者是指主权国家同意接受仲裁则意味放弃了仲裁管辖阶段及裁决承认阶段的豁免,后者系指对承认阶段豁免的放弃并不及于有关财产的执行裁决阶段,除非该财产是商业财产而不能享受豁免。以美国为例,按其《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05条和第1610条规定,国家豁免包括两方面,即管辖权豁免和执行豁免。即使某国参与了诉讼,但是并不能因此执行该国的财产。在国际投资仲裁中,国家在签订BIT中同意通过非ICSID仲裁方式解决投资争端,即被认为放弃了管辖豁免,但并不意味着放弃裁决执行方面的豁免。从法律角度,管辖豁免与执行豁免的放弃应予以分别认定。
因此在投资仲裁实践中,当国家签订了含有争端解决条款的投资协定或投资协议,就等同于声明放弃了仲裁管辖豁免,不再享有对管辖事项提出抗辩的权利。当仲裁庭作出裁决后,承认和执行往往被分割成两个独立的法律问题。无论是ICSID公约还是BIT,基本都规定了参与仲裁各方要无条件地承认裁决效力,而执行程序则必须适用有关国家的国内法进行。
2.投资仲裁中的执行豁免问题
虽然东道国有义务履行ICSID的裁决,但根据《华盛顿公约》第55条规定,“公约裁决执行的规定不得解释为背离任何缔约国现行的关于该国或任何外国执行豁免的法律”,表明国家有权依据国内法提出财产执行豁免。一般情况下,ISDS并非《纽约公约》的调整对象,所以公约未对国家豁免问题加以特别规定。但当《纽约公约》适用于非ICSID投资仲裁裁决执行问题时,基于《纽约公约》第3条的规定,东道国作为主权者应有权提出对其国家财产的执行豁免问题。
执行豁免问题的存在是制约投资仲裁执行的主要因素,应当加以解决,否则投资者只有获得东道国执行豁免的弃权后,才能获得经济赔偿。事实上,基于不同的途径获得东道国执行豁免的弃权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的谈判实力以及东道国的意愿。关于豁免执行的互惠条件,这一约定通常不被国家纳入BIT的文本中。[6]实践中,在投资协议中包括豁免条款的做法并未被普遍采用。因此,非ICSID仲裁裁决执行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豁免理论在实践中的适用范围与实际效果。
针对国家财产执行豁免的问题,实践中长期存在着“绝对豁免”与“限制豁免”两种不同主张。前者认为只要是国家财产均应予以执行豁免,后者主张只有属“非商业目的”的国家财产才能给予执行豁免。由于ISDS裁决的执行对象是国家财产,这种情况下采用“绝对豁免”显然并不可行,否则ISDS执行就失去了存在基础。
各国目前趋向于对“绝对豁免”和“限制豁免”予以区别对待,主要针对财产的性质加以区分。通常会根据“自然属性”标准(Nature of funds’ test)区分商业和非商业财产。[6]绝对豁免理论认为除非一国放弃豁免权,在任何情况下该国家在他国所有行为和财产一律享有豁免,并不区分财产性质。[7]而限制豁免理论是将国家行为区分为主权行为和非主权行为,非主权行为和用于该行为的财产不享有豁免。[8]目的在于支持商业财产是裁决的执行对象,而服务于行政或政府职能的非商业财产则不是。因此,采取“限制豁免理论”的国家也需对申请执行的财产性质进行专门审查。对于外交财产、军事财产、中央银行财产一般享有豁免权,对于本享有豁免权但用途较为复杂的财产,还应结合财产的实际用途判断是否予以豁免权。[9]
限制豁免理论允许国家执行另一国的商业财产,问题在于如何对财产进行定性。实践中判断某一财产是否是商业用途是限制豁免理论中的标尺。部分国家将证明责任划分到财产所有国。以英国为例,其《国家豁免法》第13条规定可以执行其他国家商业目的用途的财产,但有关财产的用途应由该外国国家的代表提供证明。这就需要在裁决执行的过程中,针对不同财产的性质逐一加以判断 。
通过对比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及各国关于豁免的国内立法,一般而言,外交财产(包括使馆账户)、国家中央银行账户可享受专门的执行豁免保护。[10]首先,针对外交财产,无论在仲裁实践中还是依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驻外使馆和外交使团的财产都应列为国家财产受到绝对豁免待遇,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外交账户而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表明,一国外交机构等组织履行公务所用或意图所用的财产(包括任何银行账户)不应视为商业财产。(9)参见《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21(1)(a)条。即使该国做出放弃执行豁免的表示,也不涉及其外交机构的财产。这已在美国法院裁决LETCO案[11]、Noga案(10)See CA Paris, Aug. 10, 2000, Ambassade de la Federation de Russie en France v. Compagnie Noga d` importation et d`exprotation, 128 J.D.I. 116, 121~122(2001).中得到充分的论证。
其次,针对中央银行的财产,《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公约》规定一国央行或其他货币当局的财产不应被视为商业用途的财产。(11)参见《联合国国家及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21(1)(c)条。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10条及1611(a)条也规定外国中央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自营账户”享有豁免权。这已在AIG Capital Partners Inc and another v Republic of Kazakhstan一案中得到充分体现。(12)AIG Capital Partners Inc and another v Republic of Kazakhstan (National Bank of Kazakhstan intervening), ICSID Case No. ARB/01/6 [2005] EWHC 2239 (Comm), (2006) 1 All ER 284 (QBD).此外,军事财产在性质上也应被视为非商业财产。
在非ICSID投资仲裁中,虽然多数国家都能自觉履行仲裁裁决,但在投资仲裁裁决执行案例中,财产豁免问题仍成为裁决执行的主要障碍。实践中,投资者通过执行国家商业财产获得赔偿的典型案例为Sedelamyer v. Russian Federation案。(13)Franz Sedelmayer v. The Russian Federation, SCC, Award, 7 July 1998.该案的申请人与俄罗斯发生投资纠纷,后在斯德哥尔摩仲裁院(SCC)获得有利裁决,但俄罗斯拒绝履行。申请人向德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德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俄罗斯的抗辩。由于德国没有关于国家豁免的成文法,但根据判例表明其采纳限制豁免理论,因此申请人开始寻找俄罗斯用于商业目的的财产。在其提起的多起诉讼中,仅针对俄罗斯在法兰克福的商业账户以及在科隆的房屋获得了执行。但申请人获得的赔偿远不足裁决书中所规定的数额。
3. 执行豁免的“默示放弃”理论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出现的有关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关系的理论,其核心是主张两者并非完全独立的关系。具体而言,在《纽约公约》下有些案件申请人认为一国同意参加仲裁所表明的放弃管辖豁免,即构成对仲裁裁决执行豁免的放弃。这种关于执行豁免“默示放弃”的主张在实践中获得了一定的支持。但适用条件是被执行国本身是《纽约公约》缔约国,或者该仲裁裁决是在《纽约公约》缔约国作出。[6]其理由在于,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如果规定了仲裁当事人遵守裁决的义务,那么执行豁免的适用将会受到一定的限制。[9]在Creighton v. Qatar案中,申请人与卡塔尔政府签订了一项合资建设医院的投资协议,其中约定发生纠纷后提交至ICC仲裁。在履约过程中东道国发生违约行为,ICC裁决东道国支付800万美元的赔偿金。申请人依照该裁决向法国的法院提出申请,试图执行东道国在法国的财产。根据法国的国家豁免规定,国家对其财产享有绝对豁免权。但是ICC仲裁规则第28条规定有关仲裁裁决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及时履行裁决的相关规定。因此法国最高法院判决卡塔尔同意接受ICC仲裁即意味着放弃执行豁免。(14)See Creighton Ltd (Cayman Islands) v Minister of France and Minster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Agriculture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of Qatar (2000) XXV Yearbook Conmmerecial Arbitration 458, decision of the Court Cassation of July 6,2000.
五、《纽约公约》下非ICSID仲裁在我国的适用问题
《纽约公约》调整的是国际商事仲裁执行问题,由于商事关系包括投资在内的所有具有商事性质的关系,因此投资仲裁属于商事仲裁并可适用于《纽约公约》。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非ICSID仲裁裁决能否通过《纽约公约》在我国得到承认与执行?
根据中国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的商事保留,我国只承认和执行根据我国法律属于商事关系的外国仲裁裁决。此后(198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中又对商事关系作出了进一步界定,将“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具体界定为:是指由于合同、侵权或者根据有关法律规定而产生的经济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例如货物买卖、财产租赁、工程承包、加工承揽、技术转让、合资经营、合作经营、勘探开发自然资源、保险、信贷、劳务、代理、咨询服务和海上、民用航空、铁路、公路的客货运输以及产品责任、环境污染、海上事故和所有权争议等,但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
但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1993年批准《华盛顿公约》以来,逐步开始在对外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中接受将投资者-政府争端提交ICSID国际仲裁,由于《华盛顿公约》规定了缔约国有义务承认和执行有约束力的国际投资仲裁裁决,在相当程度上修正了中国在1986年加入《纽约公约》的“商事保留”态度。[12]
从近年来中外投资保护协定中投资争端解决条款的内容看,其中有不少中外BIT中均含有双方同意将投资争议提交ICSID或非ICSID机构仲裁解决的规定及表述。例如中国-德国投资保护协定第9.3条规定:“争议应依据1965年《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提交仲裁,除非争议双方同意依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或其他仲裁规则设立专设仲裁庭”。又如中国-荷兰投资保护协定第10.3条规定:“缔约各方无条件同意应有关的投资者要求将该争议提交:(1)ICSID,依照1965年ICSID公约进行仲裁或调解,或(2)依照UNCITRAL仲裁规制建立的专设仲裁庭”。此外,中法、中葡、中韩、中瑞(士)等中外投资保护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中均有类似的规定与表述。这表明我国已同意将中外投资争端提交ICSID或者非ICSID仲裁庭,从而在事实上修改或变更了当初(1986年)加入《纽约公约》时所作的国际商事仲裁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争端的商事保留声明。虽然至今尚未发生《纽约公约》下非ICSID投资仲裁裁决在我国提出承认与执行的案例,但理论上《纽约公约》下ISDS仲裁裁决执行的机制可以在我国适用,条件是必须符合我国相关法律与程序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