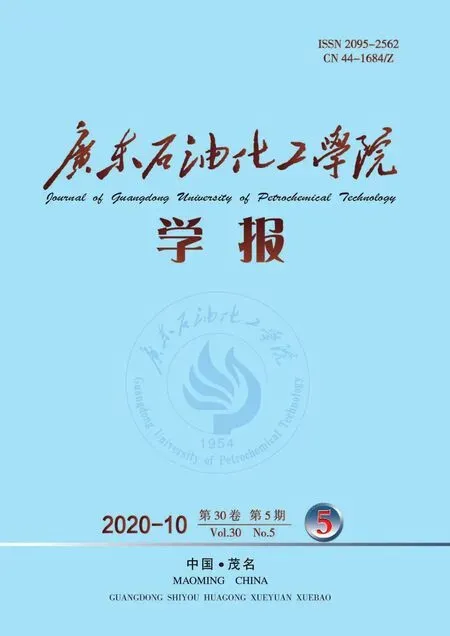唐诗中“祖先记忆”的类型化书写举隅1
2020-03-14陈文畑
陈文畑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541000)
“祖先记忆”片段大量存在于唐代文士的述祖德诗、家训诗与交游赠答诗中,作为家族制度与家族意识的诗性投影,展现了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蕴涵。本文尝试分析唐诗中“祖先记忆”的类型化内涵、书写模式,并讨论“祖先记忆”书写所包含的文士心态及情感蕴藉。
1 唐诗“祖先记忆”书写的类型化内涵
祖先记忆的书写是家族慎终追远溯源意识的表现。各姓氏及繁衍支系自上古而下不断累积关于始祖和先祖等的描述,祖先记忆是以拥有丰富的内涵,呈现于唐诗中者,大致有三。
1.1 对姓氏起源的追溯
姓氏起源一般会被追溯至上古三代的“封疆赐姓”。来自太原王氏的王勃其四言述祖德诗《倬彼我系》以追溯王氏起源为开端,“倬彼我系,出自有周。分疆锡社,派别支流”[1]671,《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王氏出自姬姓。周灵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其子宗敬为司徒,时人号曰‘王家’,因以为氏。”[2]2601王勃所言“出自有周”“分疆锡社”所指应与此同。另如杨炯与刘延嗣兄弟的唱和诗《和刘长史答十九兄》,亦以对刘氏起源的追溯“帝尧平百姓”[1]620为开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有“刘氏出自祁姓。帝尧陶唐氏子孙生子有文在手曰:‘刘累’,因以为名”[2]2244,杨炯所指应即是此;次句“高祖宅三秦”[1]620则指汉高祖刘邦定都关中建立汉朝的丰功伟绩。
1.2 对远祖功业事迹的追溯
自远古而至隋唐,朝代更迭,战乱数起,人口的迁移及流散加之家族谱牒资料的丢失,血缘家族的谱系记忆不可避免地出现错乱和断层,然而溯源情结却未曾停止,只是难以分辨或说附会的成分亦随之不断增多,对于远祖的溯源常常波及历朝同姓名人。孟浩然《书怀贻京邑同好》有“维先自邹鲁”[1]1625,其意在追孟子为“先”,李白《古风·其二十九 》中的“吾祖之流沙”[1]1678、《送于十八应四子举落第还嵩山》中的“吾祖吹橐籥”[1]1804和李绅《赠毛仙翁》“忆昔我祖神仙主,玄元皇帝周柱史”[1]5530均称道家先贤老子为“祖”并述其事迹。诸如此类溯源的可信度早已受到质疑,其在诗中的呈现,也更类似于抒发出世情怀。晚唐司马都的《送羊振文先辈往桂阳归觐》称羊振文“君家祖德惟清苦,却笑当时问绢心”[1]7002,所谓羊氏的“清苦祖德”,如《后汉书·羊续传》载东汉羊续任南洋太守时,“时权豪之家多尚奢丽,续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羸败。府丞尝献其生鱼,续受而悬于庭;丞后又进之,续乃出前所悬者以杜其意。”[3]1110司马都此处借溯羊氏先贤之风以肯定羊振文的德行清廉。
1.3 对近世先祖功业才德事迹和家风家学的追溯
相比上古三代,对于其时近世先祖的追溯,其源流显得有迹可循,对于家风家学的称道也更确凿可信。杜甫祖父为初唐诗人杜审言,对此杜甫常引以为豪,自称“诗是吾家事”[1]2533。刘禹锡有《送华阴尉张苕赴邕府使幕》,张苕为张说之孙,是以刘禹锡在诗中写到“尝披燕公传,耸若窥三辰。翊圣崇国本,像贤正朝伦。高视缅今古,清风敻无邻。兰锜照通衢,一家十朱轮。”[1]3980对张燕公的功业进行了追溯。元稹有赠予王师范的送别诗《去杭州》,王师范为初唐名臣王珪之后,元稹诗中遂有“房杜王魏之子孙,虽及百代为清门”[1]4641之说。高适系出山东士族渤海高氏,王维《送高适弟耽归临淮作》虽未明言其家族,然诗中称赞高耽“深明戴家礼,颇学毛公诗”[1]1333,应是从高氏“诗礼传家”的角度所言。
2 唐诗“祖先记忆”书写模式类型与文士心态及情感蕴藉
将祖先记忆返归诗歌书写之情境下加以考察,可以窥见诗人对于家族历史的回溯,其情怀或说心态可谓因时因事因人而异,若将其书写模式与文士心态、情感蕴藉相联系并加以类分,大致有四。
2.1 “祖先记忆”的自我表述与现实自信
关于文士对家族历史的追溯,程章灿先生认为“宣扬先世功德,追寻历史的荣耀,增强现实的自信,这也是巩固家族声誉和地位的有效手段”[4]13,对此中心态剖析甚精。自我表述“祖先记忆”在唐诗较多地出现在交游赠答诗、自我抒情诗、亲族赠答诗和家训诗中。
在赠予友人的诗歌中自述祖德以增强“现实的自信”者,如皎然的《述祖德赠湖上诸沈》,是他赴京应进士举落第后赠家乡湖州几位沈姓友人的诗歌,在遭遇了散财干谒却落第潦倒的打击之后,似诗中所写落入“一朝金尽长裾裂,吾道不行计亦拙”“岁晚高歌悲苦寒,空堂危坐百忧攒”[1]9279的落魄境地,然而诗人从祖先记忆“我祖文章有盛名,千年海内重嘉声。雪飞梁苑操奇赋,春发池塘得佳句”[1]9279中,得到了“世业相承及我身,风流自谓过时人”[1]9279的自我认同,并寄予好友以获得一种共鸣和慰藉。自我抒情者,如王勃的四言诗《倬彼我系》,其兄王励在诗序中称此诗是王勃任虢州参军时所作,作诗的原因在于“伤迫乎家贫,道未成而受禄,不得如古之君子四十强而仕也。故本其情性,原其事业,因陈先人之迹,以议出处,致天爵之艰难也”。[1]671与家族长辈述德者如权德舆的《伏蒙十六叔寄示喜庆感怀三十韵因献之》,该诗是诗人答赠叔父的诗歌,刚开始述说了家族从殷代直至诗人当时的家族历史,包括了历祖的功绩与德行,接着自谦“小生谅无似,积庆遭昌辰”“岂足议大政,所忧玷彝伦”[1]3620,并称赞叔父的学术修为和孝行等,表示对叔父“慈诲情殷勤”[1]3620的感谢。向家族晚辈述祖德以示训诫者,如陈元光的《示珦》,珦是元光之子,陈元光在诗中写道:“恩衔枫陛渥,策向桂渊弘。载笔沿儒习,持弓缵祖风。”[1]554认为自己的政治业绩是对祖风儒习的传承,并希望儿子也像自己一样承袭家族门风,能够“加壮努,勿坐鬓霜蓬”。
2.2 “祖先记忆”的自他表述与才行赞誉
“祖先记忆”的自他表述多是对他人表示赞誉的组成部分,虽或背景不同,所表达的意思大都兼具以下三个层面,一是对他人家族历史、祖先德业和家世家风的肯定,二是对他人能够继承家族前贤遗风的肯定,三是对他人现实德业的肯定。刘长卿《夏口送长宁杨明府归荆南,因寄幕府诸公》的“身承远祖遗,才出众人群”[1]1534、李白《赠友人三首》“夫子秉家义,群公难与邻”[1]1765是常见的逻辑。
唐玄宗李隆基的《送张说巡边》在诸多包含自他表述祖先记忆的诗篇中显得尤为突出。此诗作于开元十年,玄宗命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为其送行之时。诗中玄宗除了直接称赞张说“股肱申教义,戈剑靖要荒”[1]39外,更引三位张姓前贤来凸显对张说的褒扬:第一位“宝胄匡韩主,华宗辅汉王”[1]39,指的是张良;第二位“茂先惭博物”[1]39,指的是张华,第三位“平子谢文章”[1]39,指的是张衡。此处玄宗所要表达的意思,与他在《命张说兼中书令制》对张说的评价“道合忠孝,文成典礼,当朝师表,一代词宗”[5]359基本相似,而此处征引祖先之德业以示褒赞。杨炯的小诗《夜送赵纵》:“赵氏连城璧,由来天下传。送君还旧府,明月满前川。”[1]620此诗意在送别,并非以述祖为目的,却运用了嬴姓赵氏的赵惠文王与“和氏璧”的典故,暗含了对赵纵才华的肯定和对他前程的祝愿,读来饶有趣味。
2.3 “祖先记忆”的合并表述与情感共识
在诗歌中共述自己与他人两个不同家族的“祖先记忆”,一般是以此为开端引出当下与他人的某种情感共识。如张说贬岳州刺史时与赵冬曦的唱和之作《伯奴边见归田赋因投赵侍御》以张、赵二姓的祖先记忆为始:“尔家叹穷鸟,吾族赋归田。莫道荣枯异,同嗟世网牵。”[1]970诗中“穷鸟”指的是赵壹所作的《穷鸟赋》,因赵侍御与赵壹同姓,故说“尔家”;“归田”指的是张衡所作的《归田赋》,因张说与张衡同姓,故称“吾族”。其时,赵冬曦因受张说牵连同样遭贬岳州。张说以赵壹、张衡的两篇古人诗赋之情怀为契合点,触感成篇,抒发二人同因客居而不得志的失意。杜甫的《赠蜀僧闾丘师兄》亦包含对祖先记忆的合并叙述,此诗所赠闾丘师兄为曾任太常博士的闾丘均之孙,闾丘均与杜审言为同年,杜甫在此诗中先叙“闾丘笔”,再言“吾祖诗”,在追述两家世交情谊的基础上叙及自己与闾丘师兄“相遇即诸昆”[1]2304的情谊,“我住锦官城,兄居祇树园。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景晏步修廊”“夜阑接软语”[1]2304,并以“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1]2304表达对闾丘师兄的称叹,亦借此抒发相类似的出世情怀。
2.4 “祖先记忆”的旁观者表述与沧桑感慨
一些诗歌会以旁观者的口吻叙述某一家族由盛而衰的历史,进而感慨沧桑,如李颀的《行路难》和崔颢的《江畔老人愁》。李颀的《行路难》追溯“汉家名臣杨德祖”从“四代五公享茅土,父子兄弟绾银黄”“宾客填街复满座,片言出口生辉光”到“一朝谢病还乡里,穷巷苍苔绝知己”[1]1348的过程。崔颢的《江畔老人愁》通过江南少年聆听“青溪口边”衰朽老翁回忆家族从“家代仕梁陈,垂朱拖紫三十人,两朝出将复入相,五世叠鼓乘朱轮,父兄三叶皆尚主,子女四代为妃嫔”“南山赐田接御苑,北宫甲第连紫宸”[1]1325的盛况,因历经战乱最终“虽然得归到乡土,零丁贫贱长辛苦,采樵屡入历阳山,刈稻常过新林浦”[1]1325的过程。二诗均借这种对历史性变化的叙述表达对得志者“当时一顾登青云,自谓生死长随君”(《行路难》)[1]1348、“直言荣华未休歇,不觉山崩海将竭”(《江畔老人愁》)[1]1325的惋叹,并抒发对前朝士族兴落变幻的历史人生感慨。
3 唐诗“祖先记忆”书写现象的文化解读
“祖先记忆”的诗性表述发端于诗骚,至唐诗则明书暗引不胜其数,与家族制度和家族意识的绵延及对古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关系密切。
3.1 家族制度与家族意识的诗性投影
以“孝”为核心的家族伦理及其对政治伦理的渗透,加之家族特权在唐代的现实延续,姓氏与祖先作为血缘家族的本源和身份象征,自然成为带有荣耀光环的记忆。围绕祖先记忆而延伸的家风教育、谱牒修缮、家庙祭祀等家族活动,使祖先记忆和因溯源而生发的情感得以不断地重复、沉叠与绵延。“敬祖”并形之言表成了家族和社交生活中被广泛遵循的礼仪,对各种家族谱系知识的熟知成为社交技能的一部分,各种史载文献也在经意或不经意之间被纳入了家族谱系的知识框架之中。唐诗中的“祖先记忆”正是此种历史环境中家族制度与家族意识的显性诗性投影。
3.2 家族意识对诗歌创作影响的“暗示”
家族溯源意识对唐诗创作的影响是广泛的,在尤其强调家风家学家法的时代背景下,其影响还包括了思想内容、艺术形式、文体风格等,这些方面的影响相对于“祖先记忆”而言显得较为隐蔽,显性表述的“祖先记忆”则或多或少地为这一些影响的分析提供了线索或暗示。如自称“诗是吾家事”的杜甫承继并发展了杜审言的诗法诗风;自称“我祖文章有盛名”“世业相承及我身”的皎然对谢灵运以“自然”为核心的诗歌理论推崇备至,承继谢氏家族山水诗创作的题材与风格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新变;来自阳朔而自称“魏公子”[1]6924的曹邺,虽其家族溯源似乎值得推敲,却并不影响曹邺模仿建安诗风,积极创作古风乐府。这些都是家族溯源意识在唐诗创作中烙下的痕迹。
4 结语
根源于农耕文化生产生活方式、以“慎终追远”为基本特征的家族溯源意识,根植于古代士人的精神世界中,促成了多种场合、多种文体中对“祖先记忆”的书写。唐诗中的“祖先记忆”书写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唐诗“祖先记忆”内涵的探讨可为部分唐诗的解读和艺术溯源提供颇有价值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