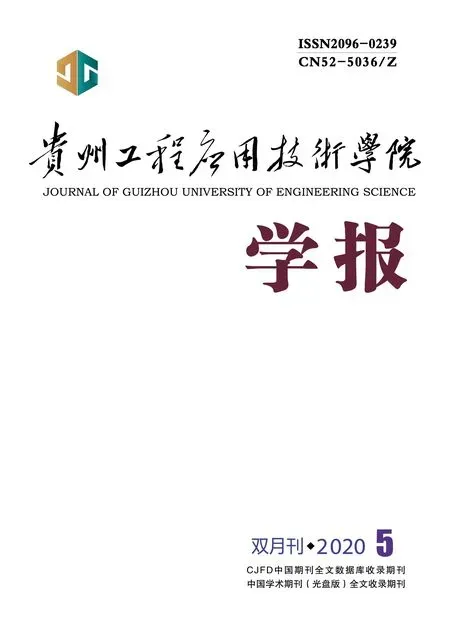大数据交易法律关系客体解析
2020-03-13阮正贤
阮正贤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贵州 贵阳 550028)
2015年4月15日,全球首个大数据交易平台贵阳大数据交易所正式运营,随后,湖北长江大数据交易所、陕西西咸新区大数据交易所、中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数据堂等大数据交易的第三方平台相继成立运营,大数据交易活动犹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据贵阳大数据交易所统计预测,2016年全国大数据交易规模达62.12亿元,2017年预计将增长70%,2018年增长96%,2019年增长81%,2020年增长45%,达到545亿元。[1]这充分说明,大数据交易活动将非常频繁,未来将发展成为一种商业常态,在经济结构中占相当的比重。然而,大数据是近年科技创新的新产物,学界对大数据的认知才开始,立法上滞后于大数据生产、利用、交易的发展实践,这不利于大数据交易的健康发展和大数据交易纠纷的解决。因此,展开对大数据的本质及大数据交易对象的剖析,梳理民事法律关系客体理论,研究大数据交易法律关系客体,对理清大数据法律关系,推动大数据的开发应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数据的本质和大数据交易的对象
“大数据”(英文名称为Big Data)一词最早出现在Gartner2001年的研究报告中,但是,至今对“大数据”未有统一的定义。Gartner给“大数据”的定义是:在新处理模式下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对“大数据”的定义是:一种规模大到获取、存储、管理、分析方面大大超出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能力范围的数据集合,其中特征表现为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多样的数据类型,价值密度低;维基百科对“大数据”的定义是:“无法在可承受的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国际数据公司将“大数据”的特征描述为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多样的数据类型,巨大的数据价值;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从“数据源、大数据硬件、大数据技术、大数据交易、大数据应用及衍生”这六个层次描述大数据的特征:大数据是体量大、结构多样、时效强特征的数据,处理大数据需要新型计算架构和智能算法等新技术,大数据交易需要对数据脱敏、定价,大数据应用强调以新的理念用于决策、发现新的知识。[1]
对大数据的定义和特征,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是,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大数据之“大”和“新”,并以此区分大数据与传统数据,又都肯定了“大数据”本质上还是数据,是海量数据的集合。数据是信息的一种呈现方式,信息是“一物的属性在其他物质上的反应、表征”[2],大数据就是人或硬件设备对客观事物、人及其行为的本质属性的反应或再现,包含了信息的内容和形式,人脑或数据硬件设备是数据的载体。信息是个比数据更宽泛的概念,知识、情报、消息、数据等在其范畴内。
大数据本质上是信息,那么大数据交易的具体对象又是什么呢?从贵阳市大数据交易所大数据交易实践可见,目前,贵阳市大数据交易所公开进行交易的数据是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建模、分析,挖掘出数据价值后的结果数据,是对基础数据收集、加工处理、分析得出的结论或数据产品、可视化的数据结果,是在大量原始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新的科学技术得出的二次数据,反应出事物之间新的关联性,本质上还是信息。商业公司之间的数据交易(含交换)主要有:一是两家或以上的数据交易参与方将各自拥有的客户信息进行交换,实现数据整合,提升数据价值;二是商业公司通过货币购买潜在客户信息,完善自身客户数据整合,获得潜在客户;三是商业公司从正规渠道获取政府信息,通过数据挖掘,捕捉商机,开发新产品,改进客户服务质量。大数据流通交易才起步,新的数据交易产品正在源源不断被开发出来。大数据交易的对象包含数据源头数据、数据结论、可视化数据结果等形形色色产品的具体形式,但是概括起来,大数据交易的对象仍然可抽象为信息。
大数据本质上还是信息,这就决定了大数据具有信息的特征。首先,信息是事物属性的反应或表征[3],一方面表明信息如同时间、空间一样,是一种客观存在,具有物质客观存在性;另一方面表明,信息不是物质本身,而是该物的属性的反应或表征,即信息是一种有别于物的客观存在。其次,信息具有可传递性和共享性。由于事物之间普遍联系性,事物的本质属性能够被多个不同的物质反应或表征,而且,这种反应或表征,还能继续为其他物质反应。本质属性被反应的物质或是反应事物本质属性的物质,均不会因本质属性被反应,或本质属性被继续反应,而丢失了这一信息,即信息可以在同一时间点,在多个空间同时存在,可呈现在不同的载体物上,这就是信息具有的可传递性,也被称为可复制性。信息所特有的这种可复制性,决定信息在相同时间和空间,可以被不同的人控制,同一信息,可以被不同的人共享。这与民法上“物”的性质不同,民法上特定物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只可能被特定的主体控制(占有),该物上之利益只可能被该占有者实现,他人因未控制该物,无法实现该物上之利益。信息的可传递性,还决定了信息不具有物理上的损耗性,不会因使用等原因,导致物理上的消耗或灭失,物不具有这一属性。再次,信息具有可确定性和可控制性。信息虽为事物内部本质属性,但是,人依据信息的可传递性,可以采取有效手段确定信息,控制信息。比如,绘画地图,就是人类通过绘画的手段再现某地地貌地形等属性的信息,进而利用该信息。最后,信息具有价值性。信息对人类的价值,或者说人类对信息的利用,古已有之。信息的价值,就是信息能够带给特定的人人身或财产上的利益。正是因为信息的这一属性,人才对其展开追逐,才会围绕着它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而需要以其为客体建立一定的法律关系。
大数据及其交易中的对象,是近年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高度发展后的产物,是新型的信息,具有普通信息或者说传统信息不具有的特征。首先,对大数据的控制,开发、交易、利用严重依赖于现代高度发展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换句话说,这类信息的载体和传递物与传统信息的不同,甚至,是人脑所不能实现的;其次,大数据具有传统信息不具有的价值点。大数据包含空前巨大的信息量及海量数据整合产生的新信息,而且信息更新快。最后,大数据和知识产权的客体不同。知识产权的客体是智力成果,即知识,本质上也属信息。知识是人类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及思维方式的认识,是人脑对物质属性和客观世界运动的反应或表征[2],是人脑这一特殊的物质对客观世界的信息进行概括、抽象、整理的结果,是人脑智力创造的成果。而大数据是人脑所不能反应的,也不是人脑创造的结果,不具有创造性,即使是数据整合得出的数据结论也不在知识产权这种智力创造信息的范围之内,其特征在于发现,而不是创造,科学发现之结果、智力规则并在知识产权客体范围之内。从大数据开发、交易、利用实践,可看出,大数据这类信息的价值在于发现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之间的关联性,而不是去能动创造、优化信息,不具有智力创造性,属于非智力信息。当然,有人会反诘,计算机软件也是数据,但它属于智力信息。对此,笔者不予否认,本文意在为不能归属于智力信息的大数据寻找权利客体之归属,能够归属于智力信息的数据自然归属于知识产权客体,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笔者无意将冠以“数据”或“大数据”称谓的信息,或在信息技术术语上归属于数据的信息当然地视为非智力信息。
二、法律关系客体和种类
“法律关系”是民法的核心概念,是大陆法系国家进行民法理论研究和民法立法、民法实施中解析民法的工具,最早由德国法学家萨维尼提出。他认为法律关系是“由法律规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法律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在法律上的体现,或者说是被法律规范了的那部分社会关系,包含主体、内容和客体三要素。
作为法律关系三要素的客体,是法律关系形成的基础,是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的依托,所以,法律关系的客体就是权利义务的客体,因法律关系中,权利本位,法律关系客体也被称为权利客体。法律关系的客体与哲学上泛指主体以外的一切为主体所认识和实践的客观事物的客体并不一致,主流观点认为,法律关系客体的概念是指“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享有的民事权利和负有的民事义务所指向的对象”[5],可见,客体是与主体相对的概念,是主体民事活动所指向的对象,是独立于主体的客观存在,能为主体带来某种利益,张文显教授将其描述为独立于主体的“自在之物”和对主体的“有用之物”[6]。主体的权利义务以该“物”为依托来展开。
客体的范围属于历史范畴,在古罗马,所有权的客体就包含作为人的奴隶[7],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这些显然已不在客体的范围内,当然,新的客体种类列入了现代客体的范围。现在,主流观点认为,权利客体为复合类型的客体,包含物(能量)、行为、人身利益(如生命、健康、身体等)、智力成果。理论界通常将有体物和准有体物的能量作为物权的客体,行为(给付)作为债权的客体,人格作为人格权的客体,智力成果作为知识产权的客体。[8]
在传统权利客体范围内,大数据及其交易对象无法找到归依之所。首先,传统民事权利客体中的“物”难以容下大数据。在古罗马法时代,物包含有体物和法律拟制的无体物,前者是指占据一定空间,能被人控制的自然物,碍于当时人类的认知能力,这一阶段的有体物限于外在有形之物,像电力、热能、磁场等并不为古罗马人所认知,不在此范围内;后者是为了便于人们更好理解所有权外的财产权利,将这些权利通过法律拟制为物,权利转让就如同物之交付,便于理解。近代德国民法典确立“物必有体”原则后[9],有体物的范围扩展至包含无形的光线、电力、热能等能量,但是,有体物被限制在:主体之外,不依赖人们感觉而存在的物质或物理的客观实在,而且,这种存在能为人们所感知和控制,具有损害性。信息无体无形,又不具有损耗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也与古罗马将权利拟制的物有本质不同,因此,自然不能将其归属于民法传统客体物的范围之内。大数据在信息范畴之内,当然也一样。
其次,传统民事权利客体中的“行为”的范围难以全部包容大数据及大数据交易对象。传统民法客体的行为是民事主体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活动,包括给付财产的行为、完成一定工作并交付完成的工作成果、提供劳务或服务的行为。如果从“行为”这一抽象的高度,大数据交易的对象是可以包含在“行为”这一客体之中的,但是,在对“行为”的内容具体展开后,“行为”的范围就难以全部包容大数据及大数据交易对象,其原因在于:在“给付财产”这类行为中,由于传统财产权的客体仅仅包含有体物、权利(法律拟制物)和智力成果,并未包括体现为非智力信息的大数据,也就是说大数据交易的对象不在此给付“财产”的范围内;在“完成一定工作并交付完成的工作成果”这类行为中,“工作成果”就是在“有体物”或“智力成果”的范围内,大数据交易的对象也不在此限,无法包容以承揽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大数据交易客体。当然在“提供劳务或服务的行为”这类行为可以包括以委托服务合同形式进行的大数据交易,但是,在以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为代表的大数据交易实践中,这类大数据交易几乎未涉及。
再次,传统民事权利客体中的“智力成果”的范围难以全部包容大数据及大数据交易对象。实质上“智力成果”与“智力信息”同构,其与非智力信息相对。反应或表征智力信息的物质基础是人脑这一特殊的物质,是人脑抽象思维的结果,具有创造性,这与大数据交易实践中,商业公司之间交易的大数据(信息)有着根本的不同,交易中的大数据反应或表征的物质基础是计算机和网络,不是人脑,是现代计算机和网络处理的结果,在于发现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寻找共性,而不具有创造性,因此,数据中的非智力类信息不可能包容于“智力成果”的范围。
最后,人格权的客体“人身利益”,也有学者称为人身要素,其分为人格要素和身份要素。人格要素表现为物质型的要素,如身体、生命、健康等;信息型的要素,如名誉、隐私等,以及能直接或间接识别个人的信息,这类信息可以表征为数据或大数据。人身要素与人身权的主体具有不可分离性,否则,该主体在物理意义上或者精神上将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因此,人身要素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其价值,也不能脱离其主体,不能被让与或其他流动,不具有财产属性,自然是不能被交易的,只能由特定的主体排他性地享有。显然,大数据交易的对象及本文意在讨论的财产性的大数据不可能归属在人格权客体的“人身利益”之内。
三、大数据交易法律关系客体
尽管大数据交易的对象具有特殊性,在传统权利客体中无法全部找到合理依归,但是,大数据交易双方之间,还是平等的商品买卖关系,在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内,性质上为民事合同法律关系,属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所以,大数据交易法律关系的客体同样可以抽象为“行为”,但是,传统“行为”的外延难以囊括大数据交易客体,需要扩充传统权利客体“行为”的外延,完善权利客体理论,才能包容数据交易的对象,厘清大数据交易法律关系客体。
(一)“给付”类型的大数据交易客体
认识这类客体首先需要扩充传统财产权的客体范围,构建支配性非智力信息财产权。在债权债务客体中“给付财产”这类行为包含有三层逻辑,一层是权利义务主体之间,实施或接受“给付”,二层是支配性的财产权利(如所有权或使用权等)的让渡,三层是转移对财产权客体(实体)的自然控制。传统支配性财产权的客体仅仅包含有体物、权利(法律拟制物)和智力成果,并未包括主要体现为非智力信息的大数据,因此,让渡的是什么权利不清。而且,由于信息与有体物相比,具有共享性,不能以对实体的自然控制,就排他实现该物上之利益,通过大数据交易获得大数据交易实体的自然控制,仅仅是获得了实现“大数据实体”上利益的物理需要,并不能当然获得该实体上之利益,取得该实体上之利益还须凭借“法律上之力”。因此,构建非智力信息财产权,将“非智力信息”与“智力成果”同列为财产权客体,才能清楚阐述“给付”类型的大数据交易客体,进而划清双方的权利义务界限。
其次,需要将具有智力信息型的大数据纳入恰当的知识产权范围,或构建支配性大数据形态的新知识产权类型。在法律上将知识产权的客体抽象为智力信息,并以是否具有“智力”,将信息划分为智力信息和非智力信息,而大数据概念是来自于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尽管从信息财产客体的角度,大数据主要体现为非智力信息,但并不排除某些大数据体现为智力信息,比如原创性的数据库,是人脑借助现代计算机技术设备的结果。因此,确定智力性大数据型的知识产权,或者说建立以“智力大数据”为客体的知识产权,是厘请此类大数据交易客体的基础,只有这样才能确定让渡的知识产权内容,转移自然控制的对象。
(二)“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型的大数据交易客体
这类交易客体主要是承揽合同和技术开发合同中的客体,合同交易实质是一方的劳动力,但是,这种劳动力已经凝聚在一定实体之中,所以,给付的对象是“劳动成果”。这里的“劳动成果”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凝聚一方劳动的实体,二是该实体之上的利益(权利),与“给付”型的客体内涵相同。所以,同样需要先构建起支配性的非智力信息财产权和知识财产权类的大数据财产权,阐述“完成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型的大数据交易客体才完整。
(三)“提供劳务或服务”型的大数据交易客体
合同交易中,“提供劳务或服务”型的客体实质上就是一方的劳动力,而且,该劳动力具有独立性,是独立的买卖对象,只是交易后,该劳动力外在表现为劳动,其作用对象不同,比如信息服务,劳动对象是信息,按摩服务劳动对象是主体人身,家电维修劳动对象是有体物等。大数据交易中,一方购买另一方的劳动服务于己方大数据,比如大数据维护服务合同等,这类交易的客体就是劳动,纯行为。此类大数据交易客体与传统的此类请求权客体相同。
大数据交易法律关系客体是制定大数据交易合同,解决大数据交易纠纷不可缺少的法律工具,通过分析可见,大数据交易法律关系之客体具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客体的具体形态不同,适用法律不同,评判交易公平的尺度和标准等也会不同。“给付”类型的大数据交易客体是“给付”信息,含智力信息或者非智力信息,前者适用知识产权转让的法律法规,后者只能是参照商品交易,或者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律法规规范交易双方的行为,交易双方是以让渡数据的排他获益权,获取对价为目的;“交付工作成果”和“提供劳务服务”型的客体,交易双方本质上是要让渡(获取)一方劳动,取得(支付)相应合同对价,所适用法律与传统请求权客体相同,评判合同的公平、履行方式等,是以让渡劳动一方所付出的劳动为依据。总之,厘清大数据交易客体属性内容,是将大数据交易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社会关系规范为法律关系的关键,是大数据确权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