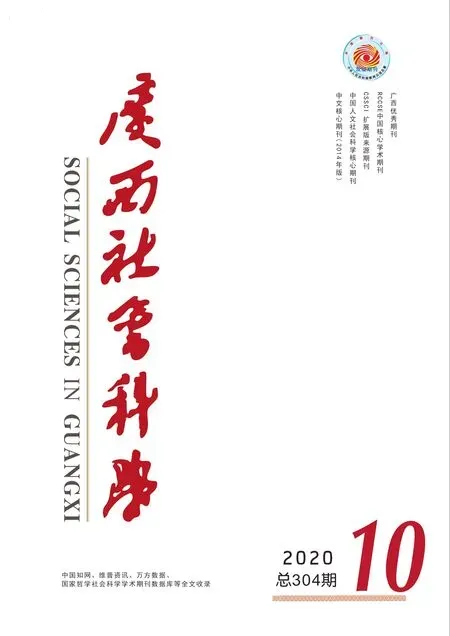官能重构、间离处置与声色修辞
——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语言异变
2020-03-12
(陕西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作家的“先锋革命”是从对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改造开始的。语言叙述在先锋作家的形式实验中被提升到本体的高度。通过小说语言的革命,先锋小说打破因果、时空的规则,获得叙事空间的拓展。因此,超越语用常规、词语超常搭配、极端化修辞等手段成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语言实验的一种常态。先锋小说对惯于意义指认、价值找寻、客观对应的现实主义文学成规来说,称得上是80年代文学的一次“语词暴动”。本文将从官能重构、间离处置、声色修辞三个方面入手,探析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语言异变。
一、对语言的官能重构
先锋小说从语言开始的形式实验,并不呼应客观的真实性,它追求的是感官体验的真实。在语用意义上,就是追求所指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先锋作家所迷恋的。这种“不确定性的语言”在文本世界中游弋,“事实上它就是为了寻求最为真实可信的表达”[1]。由此,纯粹的官能体验在先锋小说文本中得到极大的强化,感觉的、非逻辑的叙述成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语言的共同特征。
有学者称孙甘露为“汉语中的陌生人”[2],之所以会获得这样的评价,就在于孙甘露小说纯粹的官能化的语用规则。《信使之函》对语词的“代入”有着神秘的诱惑。孙甘露在这篇小说中,创造的“信是……”这个句式与马原的“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叙述语言革命的两大典型符号。如果说“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体现的是叙事的策略迂回,那么,“信是……”则体现的是语言的无限可能。“信是……”是一个用于定义的表述句式,但这样的定义充满着多义性,因为定义不来自词典的查阅,也不来自公共经验,它是由叙述主体的语词感觉自由滑动形成的,所以对于“信”的定义,在孙甘露的语言实验中本质上是不可终结的。因为,孙甘露的小说语言是“二度抽象”[3]的结果,“二度抽象”而形成的语言符号与日常生活已经无法形成语义互认。
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作品始终因对主观感觉的怪诞表达而显得特立独行,加之对暴力场面的烘托,使得余华小说中读者获得的感官体验与真实世界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对抗性。
余华所著的《十八岁出门远行》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有着“在路上”青春流浪的气质这一重要因素。对于后“文革”时代的中国年轻一代来说,“流浪”这一母题具有从“文革”的“神权”话语控制中出逃的快感。当然,这篇小说亦有“父权”经验被解构的一种时代隐喻在其中。这种中国式“成长”在余华笔下之所以会拥有超现实的文学影响力,还在于余华叙述语言的独特气质,他用完全模糊现实世界的主观化、心灵化的语言创造了一个精神远游受挫者的时代寓言。比如,起伏不止的柏油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公路高低起伏中,总有“一个叫人沮丧的弧度”;渴望住旅店时,“脑袋的地方长出了一个旅店”。这是一种让读者会产生隔膜却又能心领神会的奇异的语言。正是这则短篇小说让余华体验了另外一种文学“真实”,强烈地感受到“形式的虚伪”①余华在发表于1989年的《虚伪的作品》一文中曾说:“现在我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因此在一九八六年底写完《十八岁出门远行》后的兴奋,不是没有道理。那时候我感到这篇小说十分真实,同时我也意识到其形式的虚伪。”参见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58页。。这样的语言感觉也一直贯穿余华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文本中。《世事如烟》中的瞎子的“听”,可谓是余华对小说叙述语言予以“官能”重构的一个典型案例。比如,当4的声音单独出现时,他听得出她的“孤苦伶仃”;当4被算命先生强暴时,他听到4冲破胸膛的声音,其间还有着“裂开似的声响”。尖利的叫声冲出屋外时“四分五裂”,瞎子听到的只是碎片。瞎子迎着这声音走过去时,声音仿如“阵雨的雨点”,让他的脸上“隐隐作痛”。响亮的声音让他觉得十分尖利,仿佛“正刺入他的身体”;在4投江自杀的那天,瞎子听到4的歌声,“像是一股清澈的水流来”。
在很大程度上,“先锋性”之于苏童,并不在于文本形式,而是他感知世界的独特叙述。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苏童写陈玉金杀死自己的妻子。初秋雾霭,血气弥漫,竟然有“微微发甜”的感觉。使用“甜”这样的修饰词来写杀戮场面,这是苏童的语言独创。在《罂粟之家》中,他以反讽的笔法来写陈茂劫持刘素子的场面,甚至充满诗性的浪漫。比如,月光是“清亮亮的”,劫持者陈茂“跑出了一种飞翔的声音”,尽管他知道这并不是梦境,但这个劫持者的感觉却是“比梦境更具飞翔的感觉”,而月光下的“衰草亭子”(小说中陈茂强暴刘素子的地点)竟然对陈茂有“圣殿”一样的召唤。写刘沉草被庐方击毙,苏童选择的却是杀人者庐方的感官体验——在枪声响起来的那一瞬间,庐方仿佛听到缸中罂粟的爆炸。罂粟的气味疯狂地向庐方扑来,如同凶猛的野兽一般让人无处躲避。罂粟的气味黏附在庐方的身体上,在那之后就再也洗不掉,“直到如今,庐方还会在自己身上闻见罂粟的气味”。对于庐方这个视角的选择,苏童显然有他自己的考量,将杀人者庐方作为叙述主体,能对死亡进行某种精神还原,再现死亡体验的“虚构真实”。这样的选择也体现了苏童迥异于他人的语言革命,他的叙述形态与语词表意之间存在着极好的黏性,不会出现沉溺于纯粹的语词游戏中的先锋作家的生硬和做作。这当然源于苏童的语言天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贯钟情于对语言进行“官能”重构,这使其写作具有超越日常生活体验的先锋性。
二、对语言的间离处置
如果说现实主义小说是一种外置法则检测的文学范式,那么,先锋小说则是一种内置法则规定的文学追求。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作家崇尚的是文学的主观建构,即从外部的客观世界转向对内部主观世界的关注。“向内转”的文学选择,意味着文学题材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文学语言的新变。语言对于人的精神的规约是显而易见的。客观世界的映射法则被驱逐后,主观表意的审美功能被彰显。当“怎么写”代替“写什么”成为先锋作家的最高追求,语言也就成为他们形式实验的最重要的识别码。正是因为对于语言的叛逆,使先锋小说在获得形式自律的同时,亦拥有一种“精神形式”,即“借助语言革命打开精神空间”[4]。先锋作家的语言革命不仅要面对主流文学意识形态的规训,而且还要与日常语言拉开距离。由此,“间离化”成为先锋小说文本的重要语言特征。
“间离化”理论是布莱希特对什克洛夫斯基“陌生化”理论的发挥。布莱希特认为,“间离化”的实现,“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的理所当然,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创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5]。王一川最早注意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语言的“间离化”特征,他以“间离语言和奇幻性真实”对先锋小说的“语言形象”予以概括。而中国先锋小说文学特征得以确立,这种“间离语言”是一个重要原因。王一川对先锋小说“间离语言”的先锋性进行考察时,还提出“间离语言”的对峙概念——“真实型语言”。这种“真实型语言”对于“真实”与“典型”有着迷恋,亦相信文学语言对于世界的无所不能的表现能力,人的语言对于世界具有上帝般的全知全能性。支撑这种“真实型语言”的是基于绝对理性主义的“元叙述体”。因此,“间离语言”天然地对“真实”和“典型”具有解构作用,从而指向对“元叙述体”的拆解[6]。
先锋小说给阅读者提供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就是因为其经过“间离”处置后的语言打破了语用习惯,从而对读者习以为常的语言世界形成逼迫。比如:
1.“一代宗师阮进武死于两名武林黑道人物之手,已是十五年前的依稀往事。在阮进武之子阮海阔五岁的记忆里,天空飘满了血腥的树叶。”(《鲜血梅花》)
2.“这时灰衣女人已经走到了自己家门口了,她听到屋内女儿在咬甘蔗,声音很脆很甜。”(《世事如烟》)
3.“此刻街上自行车的铃声像阳光一样灿烂,而那一阵阵脚步声和说话声则如潮水一样生动。”(《一九八六年》)
上述三个引自余华小说的句子,其语言形象都有着主体“变形”的痕迹。在《鲜血梅花》中“血腥的树叶”,既有视觉记忆,亦有嗅觉记忆,两种“语言形象”的叠加,使得小说文本中这个小男孩的记忆表述异样而独特。在《世事如烟》中,灰衣女人听到女儿咬甘蔗的声音“脆”与“甜”,有听觉,亦有味觉,更加重灰衣女人在小说中陷入无处可逃的死亡圈套的神秘感。在《一九八六年》中,属于听觉感知的铃声、脚步声和说话声,被余华转换为视觉才能感觉到的灿烂的阳光和生动的潮水。这是小说在感觉层面所带来的“间离化”。这种“间离化”的实现,主要来自主体感觉的修辞化融通。“通感”在传统的文学手法中比比皆是,但余华小说中的通感经过个人化、主观化的变形处理,显得神秘而奇诡。
先锋小说的“间离”处置策略还体现在对语词的粗暴搭配上。先锋作家没有按语用常规来组构语词,而是完全服从于主体叙事的需要。这种文本内部的“语词暴动”,带来的是语词表征的意义重构,从而赋予小说文本以“间离化”的效果。余华在《难逃劫数》中写森林妻子的悲哀,由于经历太久的忍耐,森林一回到家,他就感觉到“妻子的悲哀像一桶冷水一样朝他倒来”,这种粗暴的比喻无疑会给读者带来超越修辞的阅读体验。写到采蝶美容手术失败后的情绪尤其精彩,“她的声音正在枯萎”,“采蝶的眼睛开始叙述起凄凉”。在《现实一种》中,余华对于细节的探幽,同样起到“间离化”的作用。他写山峰的妻子回到家看到幼子已经身亡,那种震惊、悲痛、手足无措,并不是通过人物的呼天抢地、悲号痛哭来表现,而是从物对于人的情绪的提示来写这种奇怪的感觉:这个女人在屋里找东西,她的目光从家中物件逐一扫过,发现摇篮中空无一物。这时候,这个女人突然想起躺在屋外地上的孩子。她疯了似的奔出屋子,看到一动不动的儿子时,却不知道怎么办,“但此时她想起了山峰,便转身走出去”。对于场景细节的久久盘桓,正是什克洛夫斯基所推崇的“反常”技巧,即“在一个图景的细节上耽搁许久,并加以强调,这样便产生常见的比例变形”[7]。
先锋作家对语言的“间离”处置,还有一个极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叙述者角色的模糊和零乱。“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这个句子所造成的对小说观念的冲击,首先就是在真实性上的反叛。马原直接暴露小说的虚假本质,从而使小说与历史、社会、人生的所谓“真实再现”这样的先验性出现合法性危机。这种直接在小说文本中谈论作者的句子,苏童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亦有采用,“你们是我的好朋友。我告诉你们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不叫苏童”。苏童与马原的自我叙述暴露,两者是有区别的。马原是在“声明”自己是语言幻象的制造者,而苏童则是让自己从文本中逃避,但两者都对读者造成了叙述人指认的“间离”效果。孙甘露没有在小说中出现“我是孙甘露”这样的表白,但他对模糊真实与虚构的意图亦直言不讳。在《请女人猜谜》中,孙甘露煞有介事地声明,小说人物其实都还活着,自己对于使用这些女人的真实姓名充满了歉意,同时对小说叙述中可能造成的伤害向这些女人致歉,并真诚地恳请她们的原谅。“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真实意图,就是打乱生活真实与虚构世界的界限。潘军在《南方的情绪》中也如实地坦白了写作意图,“我坐到案前,准备写一篇叫作《南方的情绪》的小说。其实一个悲剧在这之前就拉开了序幕”。不仅如此,在叙事推进的过程中,“她们从不同的角度从容地走进了我的小说,这部《南方的情绪》”。
此外,“间离”策略还来自喻指符号的主观化选择。先锋作家热衷于在文本中植入隐喻。其喻指符号并不来自公共话语的规定性,而是来自作家独特的体物认知。符号语言学家埃科视语言为一种被“各种规则”支配下的“约定的机制”,而隐喻就是对“约定的机制”的“破坏和惊扰”,同时给予了语言“更新的动力”[8]。余华清醒地认识到作家从“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无数次被重复的世界”的大众语言中突围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冲破常识”,才可能抵达“表达的真实”[9]。从这样的语言真实观出发,余华对于小说文本中的隐喻有着极致的追求,甚至可以说,隐喻本身就是余华结构文本的引爆点,既有从历史伦理指认中获得的隐喻(如《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也有从日常生活伦理中获得的隐喻(如《难逃劫数》《现实一种》)[10]。苏童习惯于通过独特的隐喻来构建文本的自律空间。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黄泥道、竹刀、枫杨树、玉瓷罐、雾瘴、影子、狗粪、黑砖楼、干草等意象构成一个“隐喻群”。王一川认为,《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叙事中之所以“飘浮着奇幻气息”,就因为苏童采用的是“弥漫全篇的总体隐喻结构”[11]。残雪小说的隐喻充满了颓废、诡异、恐怖的气息,既是她个人的寓言,也是对特定社会心理的曲折隐射。正如詹姆逊所言:“文学是社会的象征性行为。”[12]隐喻作为一种独特的象征,指向的是社会(文化)结构的深层空间,先锋小说的隐喻其实就是对“元语言”的反叛与颠覆。
三、对语言的声色修辞
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小说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叙事过程中对声音、色彩的语词痴迷,几乎是先锋作家的语用共性。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听觉系统感知的声音与视觉系统沉淀的色彩最能丰富叙述语言的丰满度。声音中既有真实的声响,还可能伴随着幻觉。声音作为人的表意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干涉外在世界”的意图较为强烈,“主体欲望”在声音中亦有直接表现[13]。色彩的镜像,往往能将心理感觉具象化。因此,先锋作家肆意“声色涂抹”,主导了文本的修辞狂欢。
格非的《褐色鸟群》被认为是“80年代最复杂、最隐晦的短篇小说之一”[14]。破解这篇小说的歧义性,声音是一条不可忽略的线索。比如,住在水边的“我”经常听到回荡在耳畔的“空旷而模糊的声响”。这种声响好像是落沙的声音,但又像是落雪的声音,它仿佛是从“拥挤的车站”或是“肃穆的墓地”传来。在给叫“棋”的女人讲述“我”的故事的夜晚,“我”迷迷糊糊地进入梦乡。在梦中,我依然听得到窗帘被微风吹拂的声音,仿佛像“潮水有节奏地漫过石子滩”,“我”还听到“棋”在呼唤“我”,“棋”的声音像是来自很遥远的地方,但听起来“童声未脱”。在“我”给“棋”讲述的故事中,那个“我”与死去丈夫的穿栗树色靴子的女人躺在她的床上时,听到“一个女人的哭泣”。当“我”与女人起身寻找未见到人影后躺下,再次听到那哭声。循着这哭声,“我”起身打开院门,看到闪电中站立的赤裸的少女。张旭东认为,声音赋予读者另外一种进入格非文本内部的可能,来自身体官能的细节性的精心打磨,昭示着那个特定年代的“抒情机制”,这种“抒情机制”中的“社会能量”和“个人欲望”值得我们去关注[15]。很显然,在格非和他的先锋同道们身处的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整个社会就充斥着个性、自由、革新的气息,这种晦涩的、极端个人化的小说文本,正是那个特殊环境下的产物。
格非将“声音”潜藏于文本的结构之中,具有一定的总体性隐喻的语用功能。而在余华小说中,声音已经失去这种“总体性”,他更热衷的是将声音作为小说叙述语言“间离化”的手段来使用。例如,《古典爱情》中卖人肉的黑店老板宰杀小姐蕙的场景,余华就是让柳生的“听”代替了“看”——
忽然隔壁屋内传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声音疼痛不已,如利剑一般直刺胸膛……这一声喊叫拖得很长,似乎集一人毕生的声音一口吐出,在茅屋之中呼啸而过,柳生仿佛看到声音刺透墙壁时的迅猛情形。
然后声音戛然而止,在这短促的间隙里,柳生听得到斧子从骨头中发出的吱吱声响。
叫喊声复又响起,这里的喊叫似乎被剁断一般,一截一截而来。柳生觉得这声音如手指一般短,一截一截十分整齐地从他身旁迅速飞过。在这被剁断的喊声里,柳生清晰地听到了斧子砍下去的一声声。斧子声与喊叫声此起彼伏,相互填补了各自声音的空隙。
这令人惊悚的场面并不是柳生亲眼所视,但却比直视更真切。余华将自己的极端化形式实验运用于对中国古典小说的戏仿,由此他的作品具有十足的“先锋感”[16]。
在视觉意义上,色彩是客观世界所谓的“真相”之一。现代派艺术家的造反,色彩革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高更说:“色彩应是思想的结果,而不是观察的结果。”[17]塞尚亦认为:“绘画意味着,把色彩感觉登记下来进行组织。色彩的结合好似把各个面的灵魂融为一体。”[18]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用文学语言来状写色彩,同样是一种思想的结果。他们对于色彩的描述并非要展现什么风景、营造什么氛围,他们希冀的是一种语言变形的效果。
马原颇为倾心毕加索的绘画,他在给学生讲述小说的虚构时谈到毕加索,他认为毕加索运用相邻对比色进行拼贴的绘画对小说有启示意义,因为这种拼贴会“生出新的美学”[19]。同时,“色彩的拼合”也能生成更为复杂的意义,在心理机制上具有触发“新的感应程序”的功能[20]。有研究者对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进行文本细剖后发现,看天葬、找野人、说情爱等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故事元素,其实被马原用三个主色块进行“内部统一”:银蓝色(雨夜)→看天葬,雪白(雪山)→找野人,斑斓色调(日常生活)→说情爱[21]。马原的色块拼贴是一种总体结构上的“涂抹”,但终究还有一种现实对应,只不过这样的色块由于故事的破碎而不易被人意识到。而马原之后的先锋作家对于色彩的调用,则从结构转向具体的语词,将客观色彩变成主观色彩,显得更为肆意和粗暴,80年代先锋作家的“色彩辞”[22]因此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23]。例如:
阮海阔在母亲的声音里端坐不动,他知道接下去将会出现什么,因此几条灰白的大道和几条翠得有些发黑的河流,开始隐约呈现出来。
一轮红日在遥远的天空里飘浮而出,无比空虚的蓝色笼罩着他的视野。置身其下,使他感到自己像一只灰黑的麻雀独自前飞。
他看到刚才离开的茅屋出现了与红日一般的颜色。红色的火焰贴着茅屋在晨风里翩翩起舞。在茅屋背后的天空中,一堆早霞也在熊熊燃烧。阮海阔那么看着,恍恍惚惚觉得茅屋的燃烧是天空里掉落的一片早霞。
上述三段引自小说《鲜血梅花》的文字有着强烈的画面感。红色火焰、熊熊燃烧的早霞,余华以这种高亮的色调来提引贯穿整篇小说的复仇线索,“红”这个鲜艳、高光、冲击力强的色彩,对于受母亲重托要寻找杀父仇人的阮海阔形成一种逼迫和挤压,加快小说叙述的节奏。而灰白(大道)、翠黑(河流)、蓝色(天空)、灰黑(麻雀)属于冷色调,缓释身背梅花剑江湖寻仇的青年阮海阔心中涌动的仇恨。两类色调的均和,对于以血还血、冤冤相报的生存哲学起到某种降解作用。
在谈及创作初期的构思方法时,苏童曾说:“从写作技术上来说,那时是用色块来构思小说的,借助于画面。”[24]苏童小说的“色彩辞”在叙事的细部着力,为小说的整体虚构提供一种局部的主观化的表达真实。在“枫杨树故乡”系列小说中,罂粟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意象。红浪翻涌的罂粟花海,当然可以解读为历史的某种隐喻。有学者将苏童小说中的罂粟视为“历史的恶之花”,认为苏童精心打磨的这个意象其实是“一个阶级的病态欲望与历史颓败相混合的象征”[25]。从历史叙事和欲望结构来探析苏童的“红罂粟”当然可行,而且也是一个较容易被认同的文学社会学视角。但从“色彩辞”的角度来看,“猩红罂粟”其实也是苏童小说叙述展开的功能性选择。这个“色块”正好契合“狂热的新文本创造运动的参与者”的形式化需求[26]。
声音与色彩在叙事中确立本体地位,与先锋小说反抗现实主义小说语用规则的精神内旨不无关联。对于声音形象的描写,其实是极为困难的。从声音形象到文学想象,本来就被过滤了波长、频率、分贝等物理属性,而只是赋予声音以一种约定俗成的拟形。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先锋作家所喜爱的,因为他们追求的就不是某种确定的意指。让语词与声音在形式实验的叙述空间中共舞,是最为理想的能指革命。文学文本中的色彩,指向客观世界,但更多是服从于主观指认。色彩正是在这样的主客观悖逆中被先锋作家所钟情的。先锋作家的“声色”修辞,不仅创造了一个主观化的文学想象空间,同时也对形式化的文本实验产生重要影响。
四、结语
“文学是语言的乌托邦”[27]。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先锋作家来说,他们选择的是一条与日常语言相背离的道路。文学语言并非一个简单的语用问题,是我说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说我,本质上就是一种基于语言的精神现象学。而语词意义上的精神还原,最重要的是语言本位的建立。先锋作家对于现实主义文学成规的抗拮,就是源于对语言世界中人的自我发现。他们在语词的玩味中找到一种特别的抒情机制——既可以隔绝于主流意识形态,也屏蔽客观真实的唯物论伦理。语言的主观性是一个本质的存在,因为它总是会带有说话人的印记。语言的主观化就是对于这种印记的捕捉。先锋作家的捕捉显然是有效的。在共时的语用维度上,他们没有盲从于所指的规定性;在历时的语用维度上,他们阉割了所指的历史性。他们在巴赫金所说的最难抵达的“稠密地带”①巴赫金指出:“在话语和所讲对象之间,在话语和讲话个人之间,有一个常常难以穿越的稠密地带,那里是别人就同一对象而发的话语,是他人就同一题目而谈的话。活生生的话语要在修辞上获得个性化,最后定型,只能是在同上述这一特殊地带相互积极作用的过程中实现。”参见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成功地完成中国当代文学表意话语的形式建构。先锋作家的文学语言实验,不仅重申语言在文学文本中的独特地位,还使其形式主义的探索具有坚定的依靠,同时也在“怎么写”这个维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学对‘语言’的还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