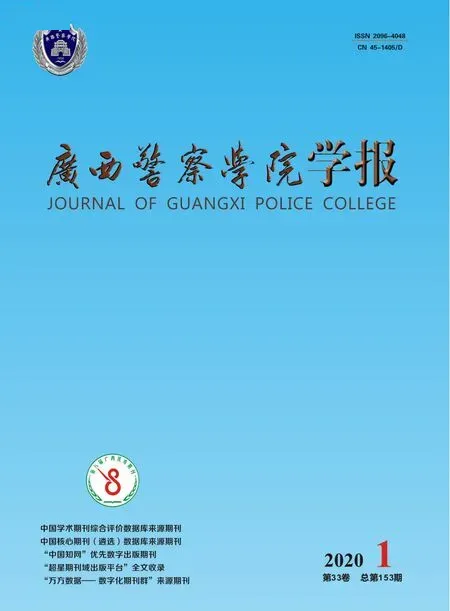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及启示
2020-03-12周立民
周立民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刑事司法系,浙江 杭州 310018)
鸦片对中国近代历史影响深远,关于鸦片史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广泛,但对于鸦片使用方法的研究尚比较薄弱。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的出现使鸦片的大规模滥用成为可能,是鸦片从药品向毒品转变的关键一步[1]。我们后来所说的毒品危害,主要是指吸食纯鸦片。人们普遍认为,吸食纯鸦片法是从鸦片与烟草混合吸食法发展而来的[2]。但是两者有很大不同,鸦片烟成瘾速度较慢,纯鸦片成瘾速度快且消费量大[3]。本文提到的“鸦片烟”是指鸦片和烟草的拌合物①对于“鸦片烟”到底是鸦片和烟草的拌合物还是纯鸦片,至今仍有不少学者没有搞清楚。实际上,清代雍正以前的“鸦片烟”和“鸦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鸦片烟”是一种以烟草为主、掺入少量鸦片的混合物,“鸦片”是纯鸦片。清乾隆中后期以后,虽然吸食纯鸦片迅速替代了吸食鸦片拌和烟草,但继续沿用了“鸦片烟”这一名词,这时“鸦片烟”成了“鸦片”的同义词,两者演变为同一概念,此系词义变化的结果。。到目前为止,除了龚缨晏、王宏斌、仲伟民、连东等少数学者外,几乎没有人对鸦片烟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进行过深入探讨。而且上述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也比较分散,相关研究没有形成系统,存在一定的疏漏。另外,对于一些关键性问题,如鸦片烟传播受限的原因,学界至今无人探讨。为了弥补前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疏漏,笔者广泛收集资料,利用历史学、传播学、禁毒学等学科知识,对相关文献资料进行深度挖掘、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即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是在哪里发明的,又是怎么传入中国的,流行时间和传播范围如何,传播受限的原因以及对当今的禁毒斗争有什么启示?
一、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的发明及其早期传播
同鸦片一样,鸦片烟是一种舶来品,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是从境外传入的。因此在分析鸦片烟在中国古代传播之前,必须先了解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的发明及其在境外的早期传播情况。
(一)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的发明
在吸食法发明之前,鸦片是吞服的。生鸦片有臭味,且味苦,为了防治热带雨林地区多发的痢疾、霍乱等疾病,无论是荷兰人还是爪哇人,都在吞食鸦片,鸦片是爪哇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吞食的鸦片剂量小,就不会造成大的危害。吸食鸦片是从吸食烟草的方法中发展而来的。正是在欧洲人将源自美洲的吸食烟草的方法在全世界广泛传播之后,才有人萌发了将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的想法。
最早将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的是爪哇人或苏门答腊人,时间是明末清初。依据是甘伯佛耳和李圭的相关记载。康熙年间,德国人甘伯佛耳记载:“咬留吧黑人吞服之外,复有一以黄烟和鸦片之法,先取水入阿片中搅和匀,以是水拌黄烟,竞吸取。”①甘伯佛耳的记载源自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在《万国公报》1889年第12期上的《罂粟源流考》一文,该文说德国医生甘伯佛耳在康熙年间著有一书,记载了鸦片与烟草拌合吸食的情况。甘伯佛耳(Engelberg Kaempfer,1651—1716年)是一个博物学者、医生、探险作家,曾加入荷兰东印度公司担任医生,在1683—1693年探险考察了俄国、波斯、印度、东南亚和日本。晚清的李圭在《鸦片事略》说:“明末,苏门答腊人变生食为吸食,其法:先取浆蒸熟,虑去渣滓,复煮和烟草叶为丸,置竹管就火吸食。”②李圭(1842—1903年),江苏人,著有《鸦片事略》二卷,成书于光绪中叶,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国鸦片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仲伟民对李圭记载的吸食法的解释为:“先把粗鸦片溶化在水中,煮沸后过滤,然后再熬成像糖浆一样的稠状物,将之与切成丝的烟草拌在一起用烟管吸食,或者与槟榔叶、麻葛等混在一起吸食”。参见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99页。李圭与甘伯佛耳两人都记述了鸦片烟的制作和使用方法,但前者记载的是爪哇人,后者记载的是苏门答腊人。其实,从地理上看,苏门答腊与爪哇一衣带水,隔巽他海峡咫尺相望,两种说法基本吻合。
(二)鸦片烟在爪哇的早期传播
关于鸦片烟在爪哇的早期传播情况,从甘伯佛耳的记载可略知一二,“咬留吧地处于孔道旁,高搭芦棚,以阿片水所调和之黄烟待客,有于之途经过者,即招之使吸。服食惯者,不能令其中止不服。”在路边的芦苇搭成的棚中就有人以“阿片水所调和之黄烟”待客,这里的“待客”应该是指兜售。这则资料说明当时在爪哇吸食鸦片烟的人很多,以至于在路边都有人兜售鸦片烟。甘伯佛耳于1689年9月到达爪哇,次年5月离开,他记载的是其在爪哇停留期间的所见所闻。由此推断,最晚在1689年,吸食鸦片烟在爪哇就已经非常流行了③对此,连东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甘伯佛耳在1689年仍然认为爪哇人吸食鸦片烟是一种‘奇怪’的用法,这至少说明在17世纪80年代,鸦片烟在东南亚各地还流传不广。”其依据还是甘伯佛耳的记载:“爪哇人有一种奇怪的鸦片用法。他们将烟草和鸦片水拌在一起(吸食),(据说)这可以让脑子更加灵活。在爪哇,我曾看到(有人)在一些芦苇(棚顶)的破房子里向路人兜售这种烟草。在巴达维亚,没有什么印度商品的销售比鸦片销售更能获利了。(如果)没有了鸦片,这些(鸦片)消费者将无法生活。没有这些从孟加拉和科罗曼德海岸运来鸦片的巴达维亚船只,他们也不会来(光顾这些店铺)。”参见连东:《中国、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鸦片“三角贸易”研究(1602—1917)》,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36—37页。笔者的理解与连东有所不同。窃以为,作为一个德国人,甘伯佛耳在到达爪哇之前,估计从来没见过“将烟草和鸦片水拌在一起(吸食)”的“鸦片用法”,所以他感到“奇怪”。因为在当时无论是欧洲人、波斯人还是阿拉伯人,都是吞食鸦片的。然而,在爪哇这种吸食方法却并不“奇怪”,甘伯佛耳说,“在爪哇,我曾看到(有人)在一些芦苇(棚顶)的破房子里向路人兜售这种烟草”,这反而说明当时在爪哇吸食鸦片烟的人很多,以至于在路边都有人兜售鸦片烟。。
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从发明到流行,需要一个过程。从明末到1689年至少有五十年的时间,足以让这种新式的成瘾性的消遣方法在爪哇一带流行开来。可见,李圭和甘伯佛耳的记述基本可以相互佐证,具有一定的可信性。当鸦片烟吸食法在爪哇流行的时候,爪哇正处于荷兰人的殖民统治之下。随着荷兰人在亚洲的殖民扩张,鸦片烟随之扩散,传入荷据时期(1624—1662年)的中国台湾,这就引申出鸦片烟在中国古代传播的问题了。
二、鸦片烟在中国古代的传播
关于鸦片烟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较少,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存在争议。这固然与史籍记载简陋有关,但也与没有全面、细致考证已有资料有关。本文拟对鸦片烟传入中国的时间、途径及后续传播情况进行分析。
(一)鸦片烟传入中国的时间和途径
对于鸦片烟传入中国的时间,除了连东④连东认为“17世纪60年代以前传入中国的可能性并不大”,他根据清代知名学者“筹台宗匠”蓝鼎元记载的“传入中国已十余年”,推测鸦片烟传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前后。参见连东:《中国、印度与东南亚之间的鸦片“三角贸易”研究(1602—1917)》,河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41页。之外,学术界基本认同美国人马士的观点:“当17世纪荷兰人盘踞中国台湾之际,吸食鸦片烟的方法传到了中国台湾,又经厦门传入了中国内陆。”[4]197马士认为鸦片烟传入中国的时间是荷兰人盘踞中国台湾之际(1624—1662年),这个时间段长达三十余年,而且跨越了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是否可以进一步缩小时间范围?荷兰的中国学专家冯客说:“这种新的消遣方式仅限于台湾海峡两岸的沿海地区,然而这一传播被明末清初的战争阻断了。清政府直到1683年才对鸦片烟有所察觉。”[5]这则资料说明鸦片烟在“明末清初的战争”之前就已经传入中国。这与马士的观点基本吻合。由此可以基本确定:鸦片烟传入中国的时间是明末,传入及初期流行的地方是闽台沿海地区。
关于鸦片烟传入中国的途径,马士认为是荷兰人将吸食法传入了中国台湾。荷兰人殖民爪哇后,大量招徕中国商船来爪哇开展贸易。因此,除了荷兰人外,也可能是在爪哇一带经商的华人将鸦片连同吸食法带回福建、台湾。
(二)鸦片烟传入中国之后的传播
据冯客的记载,鸦片烟在明末传入中国后不久就遭遇到了重大的传播挫折——“被明末清初的战争阻断”。在其后的几十年里不仅停滞不前,反而传播范围有所缩小,从传入之初的“限于台湾海峡两岸的沿海地区”到仅仅局限于台湾地区,以至于“清政府直到1683年才对鸦片烟有所察觉”。马士有类似的记载:“在一六八三康熙皇帝占领了厦门、征服了台湾和厦门附近的地方,帝国政府才第一次同这种新毒害发生直接的接触。”[4]197笔者认为,鸦片烟传播遇到重大挫折与制造鸦片烟的原料——鸦片输入受阻有关。在明朝灭亡之前,鸦片一直被当作药材进口,明朝灭亡之后,为了镇压东南沿海的抗清斗争,清政府在大陆沿海地区实行海禁,基本断绝了鸦片进口的可能,直到1683年康熙平定台湾之后“弛海禁”,沿海地区才重新恢复了鸦片输入。而无论是荷据时期,还是明郑时期,中国台湾都非常重视对外贸易,鸦片一直可以输入,使得吸食鸦片烟的风气在台湾地区始终流行,所以才有冯客说的“清政府直到1683年才对鸦片烟有所察觉”的现象。
1684年清政府解除海禁,台湾地区和厦门之间人员、物资往来频繁,吸食鸦片烟的风气在遭遇几十年的中断后再次从台湾地区传入大陆。清政府先后于1684—1686年间设立闽、粤、江、浙四个海关,实行开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鸦片作为药材持续地从海外输入,为鸦片烟继续传播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蓝鼎元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随蓝廷珍出师入台平定朱一贵事件,平台后又在台湾地区住了一年多时间,据他记载:“鸦片烟,……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这说明在1721年左右,吸食鸦片烟在台湾已经成为一种风俗,虽然这种风俗仍限于台湾和厦门一带①蓝鼎元(1680—1733年),清代福建漳浦县人,是一位对台湾历史有很大影响的官吏。蓝鼎元记载:“鸦片烟,不知始自何来,煮以铜锅,烟筒如短棍,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诱后来者。初赴饮不用钱,久则不能自已,倾家赴之矣。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为乐,后遂不可复救,一日辍饮,则面皮顿缩,唇齿龇露,脱神欲毙。然三年之后,莫不死矣。闻此为狡黠岛夷诳倾唐人财命者,愚夫不悟,传入中国已十余年,厦门多有。而台湾殊甚,殊可哀也!”参见蓝鼎元:《鹿洲初集》卷二《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四库全书本,第15-16页。这是目前中国最早关于鸦片烟的文献记录。。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抵台的清朝首任巡台御史黄叔敬也记录了当时台湾地区吸食鸦片烟的风气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危害②黄叔璥在《台湾使搓录》卷二《赤嵌笔谈》中说:“鸦片烟,用麻葛同鸦土切丝于铜挡内,煮成鸦片烟,另用竹笛,实以棕丝,群聚吸之,索值数倍于常烟。专制此者,名开鸦片烟馆。吸一二次后,便刻不能离,暖气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为导淫具,肢体萎缩,脏腑溃出,不杀身不止。官弃每为严禁,常有身被逮系,犹求缓须臾,再吸一莆者。鸦片土出咬留吧。”《台海使搓录》主要记载了首任巡台御史黄叔璥巡行台海各地的见闻。黄叔璥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抵台,次年巡期满,康熙逝世,雍正即位,黄叔璥留任一年,据此推断黄叔璥的这些记录形成于1722年左右。。作为巡台御史,黄叔璥于雍正二年(1724年)回到北京后必然要向皇帝报告巡视台湾的情况,据此推测雍正皇帝应该早在1724年就知道了鸦片烟及其危害。然而雍正皇帝并没有立即采取严厉的措施,侧面说明当时鸦片烟的流行仅局限于台湾和厦门一带,危害还不突出。
紧接着,雍正六年(1728年)广东惠州府碣石镇总兵苏明良给雍正皇帝上了一道奏折——《严禁贩卖鸦片以拯民生折》,指出吸食鸦片烟的风气在“厦门、台湾最盛”,并建议雍正皇帝“敕部通行闽粤督抚”严厉禁止“与贩鸦片及私开鸦片馆”[6]。苏明良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向皇帝提出禁毒的人。作为二品大员,苏明良不会因为一件不重要的小事而上奏皇帝,据此可推断当时鸦片烟已经严重危害了台湾和闽粤沿海地区社会的安定与发展。鉴于碣石总兵管辖粤东惠、潮二州,加上苏明良请求皇帝“敕部通行”的是“闽粤督抚”,说明鸦片烟在1728年已经传播至粤东沿海地区。另外,鉴于苏明良在任碣石总兵之前,曾在浙江宁波、湖州任职,如果鸦片烟已经传播至浙江,鉴于清政府在浙江设立了浙海关,苏明良在请求皇帝查禁鸦片时应该会将浙江纳入,不会仅限于“闽粤督抚”,据此推测鸦片烟在1728年尚未传播至浙江。
苏明良的上奏得到了雍正皇帝的重视,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正式颁布《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毒法规,标志着世界禁毒史的开始。在这一法令中,首次提出了用刑罚手段来惩治贩卖、教唆或引诱他人吸食鸦片烟的行为。禁烟令颁布后不久,福建漳州知府李治国查获了一起贩卖鸦片案件,“拿得行户陈远鸦片三十四斤,拟以军罪”,但是陈远坚称“鸦片原系药材必需,并非做就之鸦片烟”。这一案件报到福建巡抚衙门,巡抚刘世明亲自提审,令福州府传到太和堂药铺户陈书佩当场认验,陈书佩认验后供称:“验得此系鸦片,熬膏药用的,又可做鸦片丸,医治痢疾,这是并未做成烟的鸦片。”刘世明据此上奏说:“夫鸦片为医家需用之药品,惟加入烟草始淫荡害人,为干犯禁例之物。”奏折送达御案,雍正皇帝朱批要求将鸦片退还陈远本人,认为“此皆小民贸易血本,岂可将错就错,夺其生计”[7]。由此可见,清政府当时立法管制的是鸦片烟而非鸦片。陈远是福建漳州的商人,他被查获的鸦片是从广州购买的,数量达到34斤,说明当时漳州地区对鸦片的需求量已经较大。福州太和堂药铺户能准确分辨鸦片和鸦片烟,侧面说明当时鸦片烟已经传播到了福州。
雍正八年(1730年),清政府颁布了专门针对台湾的禁令——《惩治流寓台湾之人民兴贩鸦片烟条例》,规定:“台湾流寓之民……及贩卖鸦片烟者,亦分别治罪。”可见,当时鸦片烟在台湾已较为流行,否则清政府不会专门对此制定禁令。朱景英在《海东札记》卷三《记气习》中记载:“鸦片产外洋咬留吧、吕宋诸国,为渡海禁物,台地无赖人多和烟吸之。”该书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朱景英在担任台湾海防同知任内所作,说明鸦片烟在1772年仍在台湾地区流行。到乾隆中后期吸食纯鸦片法发明之后①虽然目前无法明确吸食纯鸦片法发明的时间和地点,但可以确定大约开始流行于乾隆中后期。参见王宏斌:《鸦片史事考三则》,《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232-238页。,混合吸食的方法被迅速取代,“鸦片烟”一词演化成了“鸦片”的同义词。然而,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并没有彻底消失,在一些地方仍有人在吸食烟草的时候放入一些鸦片②例如,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北京通州,副使斯当东在行程日记《英使谒见乾隆记实》中记录说:“中国官员…空闲的时间,他们就吸烟,或者嚼槟榔。他们有时把一些香料放进烟内,有时放进一些鸦片。”通州官员吸食的不是专门制造的鸦片烟(以鸦片水调和烟草制成鸦片烟丸),仅仅是在吸烟时“放进一些鸦片”,这只是一种鸦片混合烟草的吸食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鸦片烟”。另外,通州官员只是“有时放进一些鸦片”,并非一吸烟就放鸦片。,但已经达不到局部流行的程度。
综上分析,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鸦片烟大约在明末传入中国,在清乾隆中后期被吸食纯鸦片替代后基本消失,流行时间大约一百五十余年,流行范围始终局限于台湾和闽粤沿海。
对于鸦片烟是否传播至闽台粤沿海以外的地区,学界尚有一些争论。连东认为“既然烟草没有禁绝,而且又允许鸦片作为药材继续进口,那么鸦片烟的传播就根本无法阻止”[8],然而这只是他个人的臆断,他没有用证据来证明这一推断。李少明认为清政府颁布禁烟令说明当时全国吸食鸦片烟的现象已相当普遍[9]。笔者对此持保留意见。雍正禁烟令只是禁止兴贩鸦片烟和私开鸦片烟馆,并没有禁止吸食鸦片烟和输入鸦片,这反而说明当时鸦片烟并没有全面泛滥。马士记载:“在1729年,即雍正颁发谕旨的那一年,外国鸦片输入的数量一年不超过200箱……一道命令查禁吸食鸦片的煌煌谕旨当然不会对区区200箱的数量而颁发;很显然,在18世纪中,外国鸦片的输入是当作药剂而准许的。”[4]198由此推断,1729年不超过200箱的进口鸦片数量是不足以让吸食鸦片烟的风气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的。王宏斌曾做出“混合吸食鸦片与烟草的方法……清初已流行于江南地区”的结论是由于他参考了编印有误的史料③王宏斌参考的史料见《曾羽王日记》,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第1册,第312页。内容如下:“余幼时,闻有‘鸦片烟’之名,然未见有吸之者,止福建人吸之。余年三十六而遭鼎革,始于青村王继维把总衙内见有人吸此,以为目所亲睹也。自李成栋破郡城,官兵无不吸之者,由是沿及士民。二十年以来,吸之者十分中几居六七。”曾羽王《乙酉笔记》关于这段文字的原文记载是“余年三十六而遭鼎革。前此无吃烟者,止福建人用之,曾于宵村王继维把总衙内,见其吃烟,以为目所未覩。自李都督破城,官兵无不用烟,由是沿及士民。二十年来十分之八。青村南门黄君显之子,于盐锅前吃烟,烟醉,跌入锅内,即时腐烂。”曾羽王,明末清初人,根据其日记推断他大约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松江府华亭县青村人,著有《乙酉笔记》,记载了明清易代之际上海浦南一隅的纷扰变革。文中李成栋攻占松江府城是1645年,当时东南沿海战乱,从海外输入鸦片已不大可能。在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之前,为了断绝反清武装的经济来源,清政府在大陆沿海地区“迁界禁海”,成规模的鸦片贸易几乎不可能发生。如果曾羽王记载的是鸦片烟,由于缺少鸦片,不可能发生“官兵无不用烟”“二十年来十分之八”的现象。鉴于明末清初之际,吸食烟草之风正在中国迅速扩张,推测曾羽王记载的“烟”应该是烟草。,曾羽王《乙酉笔记》的原文记载的“烟”应该是烟草,因此不能以此证明清初鸦片烟已在江南地区流行。
三、鸦片烟在中国古代传播受限的原因探析
关于鸦片烟在中国古代的传播,笔者尚有一些疑惑:第一,如果说鸦片烟在明末传入中国后不久被明末清初战争阻断导致其传播受阻这一说法尚可以解释得通,那么从康熙“弛海禁”的1684年到蓝鼎元抵台的1721年,中间有三十多年的时间,照理说海禁已弛(直到1757年乾隆下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鸦片又重新被允准按照药材合法进口,而且贩卖、吸食鸦片烟又是合法的状态(直到1729年鸦片烟才被雍正皇帝立法禁止),为何吸食鸦片烟这种新的消遣方式没有像吸食烟草那样得到快速传播,依然是蓝鼎元说的“厦门多有,而台湾殊甚”的状态,甚至让蓝鼎元误认为鸦片烟“传入中国”仅仅“十余年”?第二,从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禁烟令开始,到乾隆中后期吸食鸦片烟被吸食纯鸦片所替代,中间又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在清政府对禁烟令执行不严的情况下,为何吸食鸦片烟的风气没有像后来的吸食纯鸦片那样迅速向中国内陆传播,其流行范围仍局限于台湾和闽粤沿海?这两个疑惑都与鸦片烟传播受限的原因有关。下面对此进行探讨。
(一)制造鸦片烟的原料—鸦片来源于境外
鸦片烟是鸦片和烟草的拌合物。明末烟草在中国就已广为种植,吸食烟草之风在全国流行。因此,判断鸦片烟传入中国后能否一直流行并继续传播,基本上由鸦片供应能否保障来决定。据史料分析,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鸦片几乎全部来自进口。有以下几则文字记载为证:一是明末清初学者方以智《物理小识》记载“……鸦片土,自西洋红毛荷兰人制者”;二是黄叔璥《台湾使搓录》记载“鸦片土出咬留吧”;三是广东碣石总兵苏明良在给雍正皇帝的奏折中说“鸦片一项产自外洋”;四是1747年刊行的范咸《重修台湾府志》记载“唐人”从“咬留吧”“怀其土入中国,依法制烟”;五是朱景英《海东札记》记载“鸦片产外洋咬留吧、吕宋诸国”。既然鸦片来源于进口,那么中国对外贸易的通畅与否是鸦片烟传入中国后能否进一步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通常越靠近通商口岸的地方,越有可能从境外传入吸食法和鸦片,并维持“流行”,而非一过性的零星吸食。
(二)鸦片烟得以局部流行的原因探析
鸦片烟之所以得以流行(尽管流行范围有限),与其特殊的作用有关。甘伯佛耳“能使头旋脑热,志气昏惰,而多生喜乐也”;蓝鼎元“能通宵不寐,助淫欲”;黄叔璥“吸一二次后,便刻不能离,暖气直注丹田,可竟夜不眠,土人服此为导淫具”;苏明良“初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淫荡非为”等记载说明鸦片烟被用于纵欲、消遣、享乐。这是鸦片烟得以流行的重要原因。
为何鸦片烟仅在台湾和闽粤沿海地区流行?首先,这与鸦片的可及性密切相关。闽台粤地区对外经济贸易往来密切,便于从境外输入鸦片,为鸦片烟传入后维持流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次,与台湾地区特殊的社情、环境有关。清代台湾是一个移垦社会,雍正十年(1732年)以前,清政府禁止妇女入台,台湾男女比例严重失调[10],对于孤身一人背井离乡、业余精神生活极为贫乏、生活单调无趣的男性垦民来说,吸食鸦片烟无疑是一种很好的排解寂寞、困苦的方式。蓝鼎元记载“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指的就是身无家累的“罗汉脚”们在孤单寂寞之余聚在一起吸食鸦片烟,这在当时的台湾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俗了。除了纵欲、消遣、排解寂寞困苦外,在台湾鸦片烟也被用来对付瘴疠。明末清初的台湾,瘴气弥漫,自然条件恶劣,吞鸦片、吸烟草都被用来防治瘴疠。与吞服鸦片相比,吸食鸦片烟“身体会温热”;与吸烟草相比,吸食鸦片烟比吸食烟草更有味道,更容易被台湾地区人民所接受。闽南、粤东与台湾一衣带水,台湾移民以闽南、粤东为主,台湾和闽粤沿海之间人员往来密切,为鸦片烟在闽粤沿海传播提供了便利。
(三)鸦片烟传播受限的原因探析
烟草自明末传入中国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为何鸦片烟的传播却明显受限?这与鸦片烟的可及性、价格和毒性有关。在可及性和价格方面,鸦片需从境外输入,价格昂贵,而烟草产于本地,种植广泛,容易获得,且价格低廉。这是鸦片烟传播受限而烟草传播广泛的重要原因。黄叔璥记载鸦片烟“索值数倍于常烟”,即鸦片烟的价格较烟草贵数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鸦片烟的传播,导致其传播范围远不及烟草广泛。此外,鸦片烟的毒性比烟草大,可能也影响了它的传播。蓝鼎元“能通宵不寐,助淫欲,始以为乐,后遂不可复救,一日辍饮,则面皮顿缩,唇齿龇露,脱神欲毙。然三年之后,莫不死矣”;黄叔璥“土人服此为导淫具,肢体萎缩,脏腑溃出,不杀身不止”等记载都说明吸食鸦片烟对人体有明显的毒害作用。
鸦片烟是鸦片和烟草的拌合物,吸食纯鸦片对人体健康的损害明显大于吸食鸦片烟,为何清末吸食纯鸦片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而鸦片烟的传播却明显受限?这与鸦片烟的药效、口感有关。在药效方面,与吸食纯鸦片相比,吸食鸦片烟摄入的鸦片量较少(鸦片烟只是在烟草中拌和了少量的鸦片水),因而药效不强,不能充分展示鸦片那种忘却烦忧、自我麻醉的舒畅感[11]。在口感方面,蓝鼎元“饮时以蜜糖诸品及鲜果十数碟佐之”;苏明良“但吃此烟,必列肴馔、果品,相兼而食”等记载,表明吸食鸦片烟时必须配以“蜜糖”“鲜果”等有甜味的食物,据此推断鸦片烟的口感并不好。事实上,鸦片烟就火吸食虽然避免了吞服生鸦片的刺激性臭味,鸦片燃烧(化学反应)也会释放出一定的芳香性气味,但并不能掩盖未经调制的烟草燃烧所释放出的强烈的辛、辣、苦、涩等杂味,毕竟鸦片烟的主要成分是烟草。而与之相对的是,吸食纯鸦片用的是鸦片膏,它受热汽化(物理反应)后有熟鸦片的芳香性气味。
四、鸦片烟的传播对中国的影响及禁毒斗争的启示
(一)鸦片烟的传播对中国的影响
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的出现标志着鸦片使用方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吞食到吸食。在吸食法发明之前,世界各地使用鸦片的主要方法是吞食,无论是为了防治瘴疠、疟疾、痢疾等,还是为了助性(李时珍曰“熟人房中术用之”),鸦片的使用都没有突破医学的范畴。虽然吞食鸦片对人体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但是并没有造成大的社会危害,政府也没有明文禁止吞食鸦片。然而,鸦片烟不仅毒害吸食者的身体健康(黄叔璥“肢体萎缩,脏腑溃出,不杀身不止”;苏明良“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造成吸食者家庭钱财耗尽(黄叔璥“倾家赴之”,苏明良“家业荡尽”),而且败坏当地社会风气(蓝鼎元“无赖恶少群聚夜饮,遂成风俗……诱后来者”),还引发抢劫、盗窃等犯罪(苏明良“是厦门、台湾盗贼之盛者,皆由于鸦片之根源”)。因此,清政府采用刑罚手段来惩治贩卖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标志着世界禁毒史的开端,这是中国为世界禁毒事业作出的开创性贡献。
吸食纯鸦片法是在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的基础上发明的,该法的发明使得鸦片的成瘾性和危害性极大地增强,引发的后果是中国人对鸦片的需求急剧增加,吸食鸦片的恶习在中国迅速蔓延、难以遏制。因此,尽管鸦片烟只在中国局部流行,但是它对中国社会后来的影响却非常深远。
(二)鸦片烟的传播对当今禁毒斗争的启示
与吞服鸦片相比,鸦片与烟草拌和吸食法是一种新的鸦片使用方法,通过肺部吸收入血,吸收的速度比吞服更快。蓝鼎元记载“无赖恶少”以“通宵不寐,助淫欲”“初赴饮不用钱”等“诱后来者”,这与现今吸贩毒分子以“精神百倍”“助性”“免费”等引诱他人吸毒是一样的[12]。鉴于毒品亚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应当积极开展毒品预防教育,批判毒品亚文化宣称的吸毒可以提神、解压、助性等谬论,且应当科学批判,以避免引起青少年对毒品的猎奇心理[13]。
雍正禁烟令没有禁止鸦片输入(直到1796年嘉庆皇帝才禁止鸦片输入),清代早期禁毒立法上的缺陷导致鸦片可以合法地输入中国,这就为吸食纯鸦片方法的发明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充足的鸦片(虽然吸食纯鸦片法的发明过程迄今未知)。随着乾隆中后期吸食纯鸦片法的迅速传播,中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吸食鸦片烟非法,而吸食纯鸦片却合法。而一旦国人养成了吸食纯鸦片的习惯,由于吸食纯鸦片的成瘾性远比吸食鸦片烟大,禁止的难度无疑也更大。随着中国市场对鸦片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西方商人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等到嘉庆皇帝开始严厉禁止鸦片输入时,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
研究这一段鸦片史,对于当今的禁毒斗争有着重要的启示。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鸦片几乎都来源于境外,没有鸦片就不能制造鸦片烟。因此,当今禁毒斗争应强化源头治理,严禁境外毒品渗透内流。鸦片的使用方式从吞服发展到混合烟草吸食、再到单纯吸食,在中国有长达百年的时间,雍正皇帝立法禁止鸦片烟却没有禁止鸦片,后来的乾隆皇帝也没有弥补上这个立法缺陷。这主要是因为对鸦片问题缺乏必要的调查研究,以至于未能科学预测鸦片滥用的发展趋势,错失了提前管控鸦片的良机。对当今禁毒斗争的启示有:一是应及时发现新的毒品、新的吸毒方法;二是应研究毒品流行规律,科学预测毒品发展趋势;三是应建立健全禁毒法律体系,全方位管控毒品及其前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