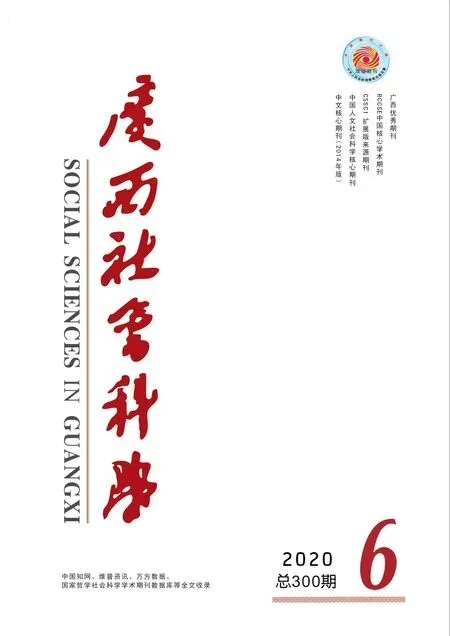文学记忆视阈下的家乡民俗学研究
——以曹文轩的盐城民俗书写为例
2020-03-11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家乡民俗学”大约于“2002年前后”被研究者正式提出,目前“已经成了有一定影响力的话题”[1]。在国外学术界,有学者主张“推进民俗学有泛化和分界两种方式”,所谓“泛化”意味着一种跨学科视野,甚至有人设想:“如果民俗学与文学和文艺理论保持更近的关系,那它是否可能早已在文化研究中占据更为中心的位置了?”[2]相比之下,中国民俗学在20世纪初便向文学“倾斜”,陈勤建发现:“中国现代引入西方民俗学科,是从‘文学切入’的”,在较长时间内呈现“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文学化倾向”[3]。
众所周知,鲁迅、周作人、废名、萧红、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曹文轩等一大批中国作家的作品充溢着丰厚的民俗学意蕴,他们记忆中的家乡风土人情可谓包罗万象,为我国民俗学研究贡献良多。本文以当代中国作家曹文轩的家乡记忆和民俗书写为例,从文学记忆这个特殊视阈,探究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相互会通的一种理念及路径。
一、永续生成的家乡记忆:透视心意现象的民俗载体
自19世纪中期以来,民俗学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各国的民俗学理论别具个性,却也不乏相通之处。被尊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的民俗学研究影响甚大,他将民俗资料分为“有形文化”“语言艺术”“心意现象”三类,福田亚西男教授认为“心意现象”指“关于意识、感觉、感情、价值观、社会规范等方面的内容”,遗憾的是,“后来的研究者很难达到第三类的深度”[4]。美国民俗学关注个人在传统演变中发挥的能动性作用,其“表演理论”不把民俗视为历史的“遗留物”,而是将它看成“现代的、流动的和不断整合、重建的”,同时将民众当作“有意识地、自觉地选择和重新塑造他们的现在和未来”的交流对象[5]。我国学者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将民俗事象分为“物质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语言民俗”,其中的“精神民俗”与“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与社会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经验”有关[6]。解读民众持续变化和更新的心意现象,是当代民俗学研究的一项重要目标。
在民俗学探究的多种心意现象之中,人类记忆现象尤其值得当今的民俗学家重视。小松和彦基于“慰灵”的文化效应而将现代民俗界定为“‘灵魂’的记忆装置”[7],高丙中宣明“民俗学是关于文化遗留物、关于传统、关于社会记忆的学问”[8]。诸多迹象表明,“记忆”是当前民俗学研究的“热点”之一。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开创的文化记忆理论对民俗研究大有助益。扬·阿斯曼断定“过去”唯有“在我们对它进行指涉时才得以产生”,因此“谁若还在‘今天’时便已企望‘明天’,就要保护‘昨天’,让它不致消失,就要借诸回忆来留住它,过去于是在回忆中被重构”[9]。阿莱达·阿斯曼对记忆的“术”和“力”作严格区分:前者侧重于信息的存储功能;后者具备“从当下出发”的“重构性”,“回忆”不可避免地受时间制约并且伴随着“遗忘”,其背后“有一种人类学的力量”[10]。依照此理,当我们面对记忆性的民俗学材料时,不必拘囿于记忆信息的“保真”性,而更应注重民俗事象为不同时空中的民众所记忆、所认同、所承传的方式及效果。事实上,日本民俗学家早就倡导民俗学“从现在的时间、地点出发”去“追溯过去”,其“最终目的并非要挖出最古老的形态”,而是要“探求变迁推移的过程,研究必然变化而确已变化了的原因和规律”[11]。以此观之,民俗学与文化记忆理论在学理上当有融通的可行性。
在文学研究方面,文化记忆理论已获应用,它启迪研究者透视作品中隐现的“延伸的场景”、采用“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双重分析法、对文本进行“互文性”解码,等等[12]。这些方法对于文学记忆视阈下的家乡民俗学研究亦有参考和借鉴的意义,为了阐发此理念,下文将对当代作家曹文轩的家乡记忆及其创作的民俗学意义予以剖析。
曹文轩,中国首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著名作家,1954年出生于江苏盐城,1974年离家赴北京大学求学,后留校任教,现为该校教授。他曾经坦言:“我虽然生活在都市,但那个空间却永恒地留存在了我的记忆中。”[13]这个“空间”指他的家乡盐城。曹文轩自述小说创作“依托”对象“十有八九是与童年的印象有关”[14],他指出他的作品《草房子》“呈现出的人物、事件、景色”既是“个人的生活积淀”,也是“同代人的经历”[15]。他的全部作品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盐城人的衣食住行、建筑服饰、婚嫁殓葬、娱乐节庆等民俗风情有生动的回忆和精细的描画,例如,《草房子》《红瓦》《青铜葵花》点明乡村的房屋构造和街巷布局;《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提到荷藕、茨菰、荸荠等带有水乡特点的农作物;《红瓦》描述农家的饭菜情况以及乡村集市的农产品;《天瓢》《草房子》《枫林渡》中列举烀藕、菱角、水果、锅贴、茶鸡蛋、花生米、水果糖等民间小吃;《草房子》《红瓦》《山羊不吃天堂草》《阿雏》《枫林渡》告诉读者:过去的盐城交通以船运为主,那里的少年较早学会撑船和划船;《红瓦》和《草房子》道出了盐城女性的服饰打扮与色尚爱好;《草房子》还提及“花花绿绿”的“新娘子船”[16],这是以往盐城普通百姓迎娶新娘的传统方式,等等。曹文轩描写的盐城民俗现象,与《盐城县志》和《盐城市志》(盐城于1983年撤县建市)等地方史料记录的相关内容基本吻合。迄今为止,很难找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盐城民俗的调查报告,鉴于此点,曹文轩对于家乡民俗的文学回忆弥足珍贵。
诚然,单个作家的家乡民俗记忆不一定准确,也不可能全面,但人类记忆的可塑性使得家乡民俗事象在无数个体心灵中永续生成,于是,作为心意现象的民俗信息得以增补和累积,每位作家都有可能在回忆中陈述某些鲜为人知的民俗细节;另一方面,在众多作家记忆中反复涌现的相同事物渐渐铸就了“经典”性的民俗事象,这种事象叠合式考察,有点类似于柳田国男的“重出立证法”,经由诸多文本的“互文性”分析方能实现。就此而论,曹文轩的盐城民俗书写堪称典型个案。
曹文轩的小说《青铜葵花》介绍了一种被盐城人称之为“毛鞋窝子”的芦花鞋:“先是将上等的芦花采回来,然后将它们均匀地搓进草绳里,再编织成鞋。那鞋很厚实,像只暖和和的鸟窝……冬天穿着,即使走在雪地里,都很暖和。”[17]在今日盐城,记得这种“毛鞋窝子”的人越来越少,其他盐城作家笔下也难得出现。不可思议的是,人类学研究者在安徽淮北平原从事田野调查时看到了“毛窝子”,这种鞋与曹文轩作品中的“毛鞋窝子”有局部相似:“毛窝子的底是用一块厚木板刻出来的,有1.5寸厚。脚掌和脚跟部分有2寸左右厚,有时会有5寸左右厚。这两个部分支撑起整个毛窝子。……有些毛窝子的底是用麻或芦苇编成。毛窝子的鞋帮部分是用芦苇花,有时加些牛毛编成的。编好的毛窝子,大约有两公分厚。毛窝子是冬天的靴子、雨天的雨鞋。”[18]调查者宣称:“毛窝子长期以来在淮北是人们越冬的主要工具。其他地方很少听说使用毛窝子。……当地人非常喜欢毛窝子,且因其他地区没有而引以为豪。”[19]曹文轩的小说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报告构成两个“互文性”文本,关于苏北“毛鞋窝子”与皖北“毛窝子”的两种叙述显示了细节性差异,由此萌生了一个尚待深入研究的民俗学疑问。
曹文轩的《草房子》《根鸟》《细米》《天瓢》等作品大量描写了盐城的旧式风车,这种风车深受盐城文人青睐:薛鸿钧的《盐城杂记》、李有干的《大芦荡》、邵玉田的《破风车水车及其他》、陈国中的《风车》、曹文芳的《香蒲草》等作品描摹了风车之物象,这些作品组成“风车”语意图像的“互文性”文本,叙事者相信“风车是盐城独有的农具,也是故乡的一大特色,在其他省县,还未曾见过”[20],尽情赞美盐城西乡“特有的灯笼式”风车[21]。根据《盐城县志》记录,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盐城西部到处可见“巧夺天工”的“八篷风车”[22],作家回忆风车故事的文学作品又与地方志形成“互文”关系,为考察盐城工匠民俗提供多元化的文献资料。
二、寻找家园的生命意识:维系文化身份的民俗功能
民俗有“教化”“规范”“维系”“调节”等社会功能,其“维系功能”能够“使群体内所有成员保持向心力与凝聚力”[23]。张士闪等学者指出“民俗代表着一种生活实践与文化认同的模式”,它可以发挥“引导个人融向社会集体的导向作用”[24]。日本民俗学家后藤兴善确信“在使用同样语言,生活于同样回忆中的人们之间,是可以产生感情的,这就是同乡人的互爱”,生者通过对死者的回忆而感受到“心灵的结合”;他将这种联结祖先、今人以及子孙的“链条”称之为“金链条”,而“民俗学者就是要把这个链条一环一环地解开”[25]。中外民俗学家关于民俗“维系”功能的阐说,与文化记忆理论的观点十分类似。阿莱达·阿斯曼辨明“文化记忆的人类学的内核是死者记忆”[26];扬·阿斯曼肯定“悼念亡者”对于集体聚合与巩固的必要性:“一个集体在回忆中建立了与亡者的联系,从而确认自己的认同。”[27]同理,民俗的维系功能反映了民众对集体文化身份的强烈认同,它使个体成员自觉保持对生命之根的回忆与敬仰。
“悼念亡者”如此紧要,无怪乎小松和彦“把慰灵祭和慰灵碑视为记忆装置”,并且觉察到:一旦记忆丧失,“作为记忆媒体的‘建筑物’、‘神话’和‘仪式’等就会被废弃”[28]。其实,使人获得文化归属感的回忆载体不啻坟墓、庙宇、神像、纪念碑等神圣之物,凡是带有文化象征意义的“被唤醒的空间”都能构成回忆的框架,“即使当它们或者说尤其是当它们不在场时,便会被当做‘故乡’在回忆里扎根”[29]。这个“被唤醒的空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物理疆域,它是被生命意义和集体身份所标识的精神家园,也是怀乡者永远追思的栖居之地,这个空间中的村镇、建筑、饮食、服饰、民具、语言、艺术、仪礼等民俗事象,都能“唤醒”人们的灵魂归属感。
曹文轩是一位执着寻找家园的作家。他早年在家乡生活20年,后定居于京,偶回故里,对盐城民俗相当熟稔。如果说专业的家乡民俗研究者难以免除“化熟为生”的伦理焦虑[30],那么,擅长“陌生化”艺术思维的作家身份反而给他带来了观感优势。他常常以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展现盐城人的生活习俗,刻画盐城人的生命精神和情感特质。周星强调:“乡愁也可以是积极性、建设性的,可以有正面评价。选择性地对旧时一些印象进行新的建构,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催生出新的仪式,产生新的认同。所以,乡愁也是一种文化实践。”[31]参照此言,曹文轩的盐城记忆及其民俗书写当属“积极性、建设性的”家乡文化实践。
曹文轩一直保持家乡文化记忆,盐城特有的民俗事象在其笔端频繁涌现。《草房子》中的秦大奶奶逝世,乡亲们将亡者抬到“门板”搭成的床上,“脚前与头前,各点了一支高高的蜡烛”;入棺之前,小说主人公桑桑的父亲“用镰刀割了一捆艾,将它们铺在棺材里”;封棺时,由于亡者生前没有儿孙,桑桑“按当地风俗”剪下一绺头发“放在老人的身旁”[32]。在所有民俗事象中,丧葬仪礼殊为重要,“不同的丧葬形态,实际上隐含着人们对于逝去的灵魂不同的处置方式”[33]。《草房子》描述的某些丧葬仪式别地也有,然而在棺材中放置生者头发的行为(盐城人谓之曰“封丁”),此习俗鲜见于他乡。据《盐城市志》所述,盐城过去流传的“封丁”是指:“由死者儿孙剪下头发少许,放入棺材的主钉眼内……如死者无儿孙,就请近门侄儿封丁,也有女婿封丁的。旧时,认为封丁为送终的标志,能享有遗产继承权。”[34]尽管曹文轩对“封丁”细节的回忆与《盐城市志》略有出入(比如说头发所放的位置不同),但核心内容基本相合,足见曹文轩对于盐城传统丧葬风俗记忆之深刻。这种旧民俗固然已被现代文明所淘汰,但作家仍可在小说故事中再现其逼真的场景,而无民俗研究者的学术伦理之顾忌。鉴于文学作品虚拟现实的艺术合法性,曹文轩在给读者展示盐城旧民俗事象之际,悄然纾解了自己的怀乡情结。小说中的儿童经由“封丁”仪式被认作祖辈最亲近的儿孙,作者的“第二自我”(即“隐含的作者”)[35]间接表达了返乡归根的生命意识。
乌丙安在论析“诞生礼、成年礼、婚礼、葬礼”四大仪礼习俗时指出:“人生仪礼在民俗观念中呈现出一种由生到死的社会生活中的过程和由死到生的信仰生活中的过程,这两种过程的衔接与循环,正是民俗传承中对人的一生及其转化的标志。”[36]在民众的心目中,成年礼也异常重要。张士闪等学者提出:“成年礼还具有结束孩提时期进入社会长大成人的标志意义,因而有时又与幼子养育习俗结合在一起”,而且“成年仪礼在风格上显得特别凝重,这毕竟是通过仪礼对于那些即将跨入社会舞台的少年人的郑重提醒”[37]。曹文轩深谙此理,他的散文《小沙弥》从中国傣族孩子的出家仪式谈到日本的成人节仪式,继而回溯自己十岁生日的剪辫仪式,引发感触:“人们一般不注意仪式本身的力量。其实,仪式本身的价值,丝毫不亚于那些内容。”[38]按照盐城地方风俗,儿童十岁生日很受重视,当天除了“由父母办饭,众亲戚前来为其进行庆贺”外,“大凡剃胎发时留有‘撑根发’,或者是留有小辫子的男孩子,应重整发型,把辫子要剪去,以此作为孩子由童年向少年跨越的一个重要标志”[39]。曹文轩以亲历者的身份记下这一民俗事件造成的心理效果:“这天,我的外祖父穿着一身整洁的衣服来到我家。……如今,这种慈祥肃穆的形象已经不多了。……他一手拿了剪子,一手托起我的小辫子,慢慢地将它剪下。……我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丢失了,丢失在了往日的岁月里,我已成了另一个人。那天,我整整一天很安静,没再胡乱地玩闹。仪式真是神奇。”[40]
当然,“剪发”在很多民俗文化中都属于非同寻常的行为,不过,各地风俗中的“剪发”动机、场合、方式等要素总有不同,曹文轩牢记入殓“封丁”与生日“剪辫”这两种别具一格的盐城地方仪礼,证明他的家乡民俗记忆既来自个人“生平式回忆”又指向群体“巩固根基式回忆”[41],很好地诠释了民俗文化对所有个体(无论在乡还是离乡)的维系功能。
民俗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不光显现于人生仪礼,也渗透于民间艺术,譬如种类繁多的民间戏曲,它们“扎根民众生活,与各地的风俗民情水乳交融”,而且“本身也成了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42]。曹文轩的小说《山羊不吃天堂草》以大量笔墨抒写农民爱唱淮剧的艺术情感,他们最爱淮剧“大悲调”,乃因“其情感,其格调,与他们的心情好像很贴切。它能淋漓尽致地将他们心中那种绵延不断的伤感和愤怒表露出来”[43]。综观盐城特色文化资源,“淮剧艺术便是其中最为突出、最为璀璨的一种”,它最初“从农民和盐民劳动号子、民歌、民间说唱发展起来”[44];从艺术风格来讲,“淮剧擅长表演悲剧、悲苦戏”,因为它既“满足了旧时人们在苦难中精神宣泄的需要,满足了善良、朴实的盐阜民众所具有的同情心”,又包含着盐城民众的苦难记忆,反映了他们的“悲壮情怀和坚韧的个性”[45]。曹文轩的文学作品蕴含悲天悯人的情感基调,赞颂普通人在灾难和困境中的生命韧性,与淮剧文化精神有相似之处。他塑造的人物形象处于情感高峰时往往哭泣,例如,秃鹤终于将功补过,他“几乎变成了号啕大哭”,周围“许多孩子也都哭了”[46];根鸟经受各种考验而最终实现梦想,他“将脸埋在百合花丛中,号啕大哭”[47];因意外事件而羞愧逃走的细米获得谅解和安慰时,他“忽然‘哇哇’大哭”[48]……这些人物以“哭泣”来传达强烈而又复杂的情感,或许与作者早年受到淮剧艺术的熏陶有一定关联。
三、烛照历史的生活叙事:折射语境变迁的民俗书写
关于民俗学的学科性质,后藤兴善在《民俗学入门》写道:“它是新的文化科学之一,是人类学、社会学的一个部门,是对人类的过去投以光明的历史科学”[49]。时至今日,人们对民俗学概念的理解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是,民俗学对人类历史生活“投以光明”的文化价值却愈加彰显。张士闪等中国民俗学家以“经过了一定的选择”的“家族故事”为例,说明家族群体为了构建“‘神圣家族’的知识谱系”,往往对“记忆”中的家族故事重新组合,进而论证“民间记忆的不稳定性和民俗知识的可变性”[50]。正因为民俗主体的创造性以及民俗记忆的选择性,民俗学有别于历史学,它更注重人类历史生活的文化意义。文化记忆理论也不同于历史学,它区分了“绝对的过去”和“相对的过去”,将回忆看成“被内化了的过去”,强调“回忆是一种进行符号编码的行为”,申明“神话是(主要以叙事形式出现的)对过去的指涉,来自那里的光辉可以将当下和未来照亮”[51]。相比较而言,民俗近似对历史实行意义编码的“神话”,富有生命力的民俗事象也能“照亮”过往、现在和将来的人类生活。
民俗内涵的变革与历史语境的变迁有关,恰如美学民俗学界的表演学派主张的那样:旧有的故事文本在“新的语境下”将会被“重新讲述”,讲述人“根据讲述语境的不同和听众的不同需要而适时地创造、调整他的故事,使之适应具体的讲述语境”[52]。由于人们的民俗记忆受社会框架规约的程度不同,他们依据新语境所讲述的故事也有差异。在从事家乡民俗学研究时,研究者应当对采集到的民俗叙事文本采取“互文”参验的考证方式;若发觉各个文本的民俗叙述龃龉不合,也不宜草率地否定其研究价值,而要进一步思考:为何有的叙事者运用(甚至是故意运用)了“不可靠”的讲述方式?它与文化语境的嬗变有无关涉?何种因素在其背后暗中生效?
仍以曹文轩作品中的盐城民俗书写为例。曹文轩审视的盐城物质民俗,包括盐城人日常生活中的“居住、服饰、饮食、生产、交通等方面的民俗事象”,它们代表盐城人“一种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并且“程度不同地凝聚着一定的文化意识”,打上盐城文化的“鲜明印记”[53]。曹文轩从文学记忆的视阈来书写盐城人的生活风俗,他在描写中融入了自己的情感和想象,所写内容固然不完全符合史实,却并非凭空臆想和捏造,其虚虚实实的文学笔调,隐隐约约折射了盐城乃至中国文化语境的时代变迁。本文拟重点分析曹文轩对盐城民居、古城和粮食的摹写方式。
与别地情形相同,盐城传统民居的构造特点与地理环境有关。盐城水乡“盛产林木和柴草”,普通人家先前“以居住草房为多”,“草”是指茅草、麦秸、芦苇、稻草等[54]。因旧社会老百姓贫富差距较大,“有钱有势的大户建有深宅大院;经济实力较强的富户建有堂屋、灶屋、厢房或围墙,形成四合院;次为砖墙瓦盖三间两厨”;同为草房子,“也因各户经济实力不同而有所区别”[55]。用砖头砌墙、茅草盖屋的房子“冬暖夏凉,一般为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所建”[56]。随着城市化建设的逐步推进,绝大多数盐城人将草房子“退出历史舞台”而被“瓦房”和“楼房”取代的现象视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57]。况且,在今天的一些盐城文人记忆中,草房子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比方说,1948年盐城东台的一位老人“不小心让火引燃灶膛外的芦花”,以致殒身于火,“还把四户邻居的草房烧得片甲不留”[58]。曹文轩对于草房子的回忆与叙述却另有一番风情,他以诗意的文笔加以赞美:茅草房系“富庶人家”攒钱所盖,这种房子“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它们“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金色阳光的照耀又使它们“显出一派华贵来”[59]。《草房子》等作品显示:当曹文轩的盐城同乡普遍地期盼物质生活向前飞跃时,他对家乡的淳朴民风和美好人情给予更多的关切与崇尚。
盐城古老的砖城城墙始建于明永乐十六年(1418年),因抗日战争时期敌机轰炸,为了“便于疏散人员”,于1939年4月拆除[60]。盐城作家许正和幼年寻访老城墙,徒然发现“没有想象中的巍峨城墙,就连一丝断垣一片残壁也没有”,于是在《盐城赋》中抒发了“一种莫名的心痛”[61]。许正和等盐城人未能亲眼所见的盐城老城墙,却在曹文轩的回忆与想象中得以重建。曹文轩的小说《天瓢》写到“瓢城”流行的一则传说:每当“河水倒灌”,瓢城人“用瓢将水㧟出去”,遂在瓢城老屋的墙上一直挂着水瓢。小说还细致地勾画了瓢城的城市景观[62]。查阅盐城历史文献得知:盐城自古即有“瓢城”之称,古时所筑的土城“西狭东阔,状如葫瓢”,遂“取瓢浮于水,不被淹没之意”[63],这个旧名蕴含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草房子》也勾勒了盐城老城墙的历史景观。当曹文轩创作这些小说时,盐城古城已消逝于幽深的历史长河,家乡人为此黯然神伤,而曹文轩却在作品中使其复现。不应忘记,曹文轩对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寻根文学”思潮了如指掌,况且“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国很多城市都开始了城市形象的建设”[64],《草房子》与《天瓢》分别于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出版,我们可以猜想:在国内各地纷纷打造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之际,盐城人对于失去了古城墙的城市空间难免遗憾,满怀乡愁的曹文轩是否借助故事叙述以重构老城记忆?另需注意的是:曹文轩的《草房子》《天瓢》《根鸟》等作品一旦写到县城,总要叙及满街的自行车和响成一片的车铃声。盐城地方志证实: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盐城自行车“逐年增多”;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自行车数量成倍增加”;在20世纪80年代,自行车成为盐城的“民用主要交通工具”[65]。可见曹文轩对盐城城市景观的描绘并非纯然虚构,他对盐城民俗的回忆与记述既有重构的元素又有事实的成分。
曹文轩作品中的民俗书写还涉及盐城的饮食与生产等多种民俗形式,其“稻麦”叙事尤含深意。据《盐城县志》所记:新中国成立前,“串场河以西为县内水稻区。60年代后期,东区旱改水成功之后,全县皆以水稻为主要粮食作物”[66]。《盐城县志》还提道:“三麦,亦是盐城县的主要粮食作物。50年代前,主要在县境东区、中区种植。60年代后期,西区沤改旱成功后,全县每年三麦种植面积一般都占耕地面积的60%左右。”[67]曹文轩的家乡位于盐城“西区”,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后,那里既种植水稻也种植小麦,但稻米是主粮,乡民“以大米作主食,兼食杂粮”[68]。据此,稻谷之美在曹文轩的家乡人眼中自然更具魅力,他的同乡作家李有干的《大芦荡》、曹文芳的《水边的故乡》等作品渲染插秧的快乐场景。曹文轩虽在《青铜葵花》里抒写稻子的清香,却在《天瓢》《红瓦》《细米》等作品里更多地讲述麦地里发生的浪漫故事。不能说曹文轩对于家乡粮食作物的描写违背了生活事实,只能说曹文轩在营造故事氛围时更钟情于麦子,内中缘由极为复杂,笔者推测:首先,这与曹文轩自幼养成的审美爱好有关,他离乡后又长期置身于北方面食环境的生活经历,这对他原有的麦子情感有所强化。其次,麦秆的高度决定了麦地仿若高粱地,比稻田具有更大的活动空间,更适合安排故事情节。另外,文学传播的文化语境也会在无形中导引作者的创作意识,由于“东亚文明主要建立在稻米文化基础上,而西亚和欧洲文明则完全是建立在小麦文化基础之上”[69],为了增强文学接受的共通性,尽量减少西方读者(吃惯了“面包”类食品)和北方读者(熟悉“高粱地”故事)的文化陌生感,等等。
林继富对“记忆场域”的辨析令人寻味:“‘记忆场域’作为民族或地域公共文化场所,凝聚了民族或地域的民众情感,记载了民族或地域的历史活动。……从这个角度上说,‘记忆场域’就具有时间维度了,成为‘存在于当下的过去’。”[70]在曹文轩等作家眼里,家乡盐城即“记忆场域”,它不单代表一个被地图框定的地理位置,更意味着文化寻根的时空索引,继往者与开来者、离乡者与在乡者均能从中找到过去的生命镜像。曹文轩总结创作经验时说过:“后来的经验,后来的知识,将浸润‘过去’、照亮‘过去’,这番浸润与照亮,才使‘过去’得以转化为有用之材。”[71]变化无穷的语境源源不绝地生发新的家乡知识,曹文轩高举“道义感、审美意义、悲悯情怀”[72]之明灯,照亮一条通往心灵故乡的回忆之路。
四、结语:作家的家乡记忆研究——文学与民俗学的双向会通
作家回忆家乡风土人情的作品是文学和民俗学的双重文本,可为家乡民俗学研究提供鲜活的文献资料,它能成为透视特定区域的民众心意之载体。基于人类记忆永续生成的特性,诸多作家的“互文性”家乡记忆文本彼此对照与互补,而且这些作品又与地方史料等其他文本形成“互文”关系,为民俗学研究增添多重视点。对于这些民俗记忆文本,研究者需要相应地采取“互文”参验的考证方式;作家的家乡记忆建立在集体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展现民俗的维系功能,也体现了人类寻找家园的生命意识;作家对家乡民俗的回忆与书写既有重构的元素又有事实的成分,他们接受文化语境的规约,却又以创作者的诗意情怀照亮过往的历史生活,赋予民俗事象以多维时间。
曹文轩的家乡民俗书写非常明晰地诠释了上述规律,为文学与民俗学研究的交汇和融通提供典范之作。由此看来,无论是文学家还是民俗学家,凡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文化实践,几乎都肩负着一种共同使命:“让我们无名的祖先群像,连同他们的喜悦与悲哀、凄惨与贫弱、进取心与牺牲精神,都能够在我们面前活生生地再现。”[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