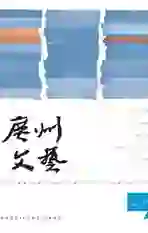好一条哲学狗
2020-03-03蒋蓝
蒋蓝
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
犬儒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鲁迅
至少从现实的立场来说,所谓的“哲学狗”比“哲学人”更有血肉,所以,人们毫不怀疑目前接触到的世界物质的构成。如果说,古希腊的哲学家还在担心自己命运的话,那么,与狗的交流可以使他们轻松很多,进一步地远离被酒色、权欲掏空了内在的人。虽然他们对狗的生理结构远没有什么兴趣,但每次对话很是专注。
自然了,犬儒必定会拒绝“狗眼看人低”“狗摇尾巴讨人欢”“狗仗人势”等等对狗的“不义”之词,更是反感于“狗腿子”的“狗急跳墙”,他们仅仅着眼于狗的低贱与卑微。而把愤世嫉俗、行为乖张的人格行为称作“犬儒”源于古希腊。把“犬儒”奉为信仰并坚持一定的主张,持有一定的理想,实践一种生活方式则成了一种主义。
我一直认为,犬儒带有更彻底的中土魏晋时代的佯狂精神,他们获得了从狗的立场观察人世的“低地角度”,从而使理性与自省获得了与大地更为紧密的接触。佯狂最早出自《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箕子谏纣不果,“乃被发佯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这不过是在被权力压抑下的反抗,故有“佯狂以忘忧”之说。中国的魏晋风度是渴望以“狂”来逃避强权,以图保持内心的尊严。犬儒更进一步,岂止权力,连就人也没有入他们的“狗眼”。佯狂是自保,犬儒是渴望以“自毁”的方式唤起理性与自省。可见两者泾渭分明,高下立判。
最早使用中文记述“哲学狗儿”第欧根尼·拉尔修故事的人,是清末外交官郭嵩焘。他在日记里记载说:“耶苏前三百二十年,有安夫子(即安提斯泰尼),言福气不在加,在减;常减除心里所要的,就是德行。所以常轻视学问知识,荣华富贵。其学生杜知尼(即第欧根尼)名尤著,常住木桶中,刻苦自励,讥弹一世。”
“犬儒主义”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拉尔修则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最有名的犬儒主义者。他的全部财产就是一根橄榄树干做的木棍,一件褴褛的衣裳(白天穿在身上,晚上盖在身上),一只讨饭袋,一只水杯。他一度成了俘虏,在俘虏市场上当众手淫,还问他们“谁想买一个主子”。他后来就住在市场上,晚上睡在木桶里,人们称此桶为“第欧根尼的大桶”。他甚至骄傲地声称自己以四海为家,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公民。第欧根尼把自己视为天然的“管理者”,实际上是以狗的生活方式来管理人类和思想。他一度毁坏货币,认为这人世间最大的污物败坏了心灵。
前不久,我读到法国哲学家萧沆的《天犬》一文,他提到第欧根尼的一个细节:“有一天,有一个人带他进了一间装饰华美的房子,告诫他说,‘千万别朝地上吐痰。而第欧根尼恰恰就想吐,于是把一口痰吐在了那个人的脸上,而且还一边大喊着解释说,这是他所能找到的唯一一个龌龊的地方,可以让他吐痰。”
这体现了他对“做人的持续恶心”,他是要把人的画皮一层层脱下来展览,让世界脸红。他只能回到狗的立场,才能获得尊严。
亚里士多德就指出,行为怪诞的第欧根尼早已是雅典的名人。柏拉图曾经在对话录中描述这类智者的行径: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它儿女的父亲吗?
当然是。
那只公狗难道不是你的吗?
当然,它是我的。
既然是你的,而且是父亲,那么这条公狗就是你的父亲,你就是那些小狗的兄弟了。
这显然是一个意在玩弄逻辑混乱的论断,是向人们证明,自己可以为任何荒诞不经的论题提供论证。这类智者的活动极大地毁坏了智者在民众中的形象,也使得犬儒在柏拉图时期的希腊世界背上了恶名,几乎成了诡辩者的代名词。柏拉图的对话录随处可见对智者的调侃和攻击。这个例证也形象地反映了狗在思维领域无处不在的“邋遢身影”。
对这个著名的哲学“公案”,十八世纪德国杰出的思想家利希滕贝格在影响深远的《格言集》中讲述:
第欧根尼穿着一身邋遢肮脏的衣服在柏拉图房间的豪华地毯上踱来踱去。
“我践踏柏拉图的骄傲。”他说。
“不错,”柏拉图反唇相讥道,“不过是以另一种骄傲。”
这就深刻地点明了犬儒用以自傲的本钱,不过是去掉了华丽外观的骄傲。实际上,这种去掉了包装的骄傲只是更为激烈罢了。
犬儒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至于这个称谓是不是肯定来源于此,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另外一种说法是指安提斯泰尼经常到雅典的一个被人们叫作“快犬”的体育场去和人们谈话、辩论,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观点的最初的追随者队伍,因而被称作“犬儒派”。“犬儒主义”则由这一学派的观点理念和生活行为演化而来。
这些人的行为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粗俗无礼,虚荣自负,傲视一切,自我欣赏。他们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结婚,则夫妻同为犬儒,而且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交合之事。犬儒主义诗人克拉底和女犬儒主义者喜帕契亚就是一对著名的犬儒夫妇。他们藐视一切权威,敢于“贬损”一切人为的德行。
被哲学家福柯誉为“那一代最出色、最有才气的”的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德塞尔托,在其《超脱》一书里,以穿透性的笔触精准地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第欧根尼:“他就在那里,蹲在桶里,赤身裸体、脏兮兮的、不声不响,周围都是垃圾;他就在那里,在广场上,行人都躲着走,怕踩着他;他当众撒尿,把东西捧在手里吃,或者干脆把掉在地上的东西就地舔起。流浪者第欧根尼把一切都抛弃了。他是狗,他就生活得像一条狗,朝着路过的人汪汪乱叫;作为狗,他的桶就是狗窝。他在外边,离开了一切内里的东西——家和团体的温暖,他离开了社会。第欧根尼把一切都抛弃了,他怀疑一切。”
古希臘的文明是产生理性智者的环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类人物呢?综合来看,犬儒主义者或称犬儒派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也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希腊的城邦制度的繁荣孕育了犬儒主义这个极端化的产儿,城邦制度的衰落催生了这个怪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把反叛城邦制度的理想民主以极端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认为是众多愚蠢的人的愚蠢念头把社会、城邦搞糟了。他们以怪异和反常的行为向现有的秩序、制度、观念、习俗挑战,精神上则躲进个人的心灵深处寻求宁静和快乐。犬儒主义作为这股向社会发起抗议力量的代表,也就自然地产生了。因此说,为公民发展提供了广大空间的城邦制度是犬儒主义出现并走向极端化的温床。
回顾人类的精神历史,每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都意味着对传统东西的挑战甚至是亵渎,挑战者抛下的不一定是白手套,也可能是一只狗爪子。
根据法国学者伊莎贝尔·布卡利在《名人死亡词典》里的说法,第根欧尼的死因众说纷纭,估计他与亚历山大同日而死。有人说第根欧尼死于与狗争夺食物,成为“哲学死于狗嘴”的范例。当主流文化的宠儿们听到饿极了的狗咬死并啃吃异端的传闻时,难免有些幸灾乐祸。有人说是因胆汁渗出而死,也有人说是他屏住呼吸窒息而亡。人们将他的坟墓修建在城门口,上面立了一座狗的雕像。
责任编辑:姚陌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