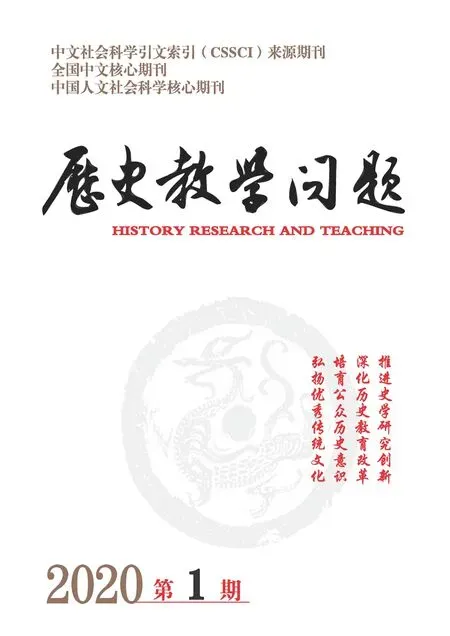试析德国军医在青岛及其腹地的医疗实践和科学考察(1897—1914)
2020-03-03袁玮蔓
袁 玮 蔓
胶澳租借地因拥有众多的医生和医生在租借地管理中的特殊发言权而被同时代人称为“医生殖民地”。①Eckart,Wolfgan g Uwe,Deutsche Ärzte in China 1897—1914,Medizin als Kulturmission im Zweiten Deutschen Kaiserreich,Stuttgart:Gustav Fischer Verlag,1989,S. 37.从1898 年1 月第一批德国驻军抵达租借地到1914 年11 月德国败于日本撤离青岛,德国海军部向租借地共派遣了84 名军医。其中每年的人数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在1898 年只有5 人,而到1913年和1914 年时,已经达到了15 人。这些军医一般在租借地工作2 至4 年,由一位总督府医生进行管理。他们是胶澳总督府在租借地进行医疗卫生建设的基础,同时他们的工作范围也扩展到了租借地的周边地区以及山东省内地。
德国军医在租借地的主要任务是防治驻军中的疾病和保护驻军的健康。为此,他们不仅参与租借地医疗卫生体制的建设,还承担科学考察的任务;在这些工作中,他们与中国居民进行了接触和交往。但是,在目前针对德国军医在租借地医学活动的研究中,主要强调的是他们在防治驻军中疾病流行方面所取得的积极成果以及对中国居民的忽视,而关于德国军医在租借地的科学考察并没有展开论述。②在中外的研究成果中,对德国在胶澳租借地医疗卫生事业进行比较详细论述的,主要有Eckart,Deutsche Ärzte in China 1897—1914;Huang,Fu-teh,Qingdao:Chinesen unter deutscher Herrschaft 1897—1914,Bochum:Projekt Verlag,1999;Biener,Annette S.:Das deutsche Pachtgebiet Tsingtau in Shantung 1897—1914,Institutioneller Wandel durch Kolonialisierung,Bonn:Wilhem Matzat,2001;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孙立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黄福得:《1897 至1914 年间德国在青岛的殖民体制与卫生建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9 期,2008 年5 月,第127—159 页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德国军医在租借地的医疗实践,不过只有Eckart、Biener 和余凯思在其中简要地提及了德国军医在租借地的科研工作。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前提下,对德国军医在租借地的医学活动,从医疗实践和科学考察两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在这一基础上初步探讨德国军医的医疗工作对当地中国人的医学观念以及对中医西传的影响,为中西医文化交流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德国军医的医疗实践
医疗实践是人类面对疾病的积极反应。针对占领初期德国胶澳驻军中传染性疾病的大肆流行情况,胶澳总督府立即采取了防治措施;同时还积极筹划和耗费巨资建立了庞大的医疗卫生体系,以逐步改善租借地的医疗卫生状况。其中德国军医作为这些医疗实践的直接实施者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他们参与租借地的公共卫生建设,比如:担任卫生警察,监管租借地,特别是华人居住区的卫生状况;①参见Eckart,Deutsche Ärzte in China 1897—1914,S. 38,S. 55,S. 52—53.担任检疫医生,负责防止外地传染病进入租借地的工作;②参见Eckart,Deutsche Ärzte in China 1897—1914,S. 38,S. 55,S. 52—53.担任法医、狱医等等。③Podestà,Hans,“Entwicklung und Gestaltung der gesundheitlichen Verhältnisse bei den Besatzungstruppen des Kiautschou- Gebietes. Im Vergleich mit der Marine und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Örtlichkeit und Klima im Tsingtau”,in:Deutsche Militärärztliche Zeitschrift 38,14(1909),S. 572.大部分军医的工作场所为1898 年开始建设和逐步投入使用的总督府野战医院(Gouvernementslazarett)。④Podestà,Hans,“Entwicklung und Gestaltung der gesundheitlichen Verhältnisse bei den Besatzungstruppen des Kiautschou- Gebietes. Im Vergleich mit der Marine und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von Örtlichkeit und Klima im Tsingtau”,in:Deutsche Militärärztliche Zeitschrift 38,14(1909),S. 572.该院位于青岛市区总督府和信号山之间,在1904 年完工,包括“五栋独立的大楼和一栋较小的楼房,给予病患,如妇女与小儿科、眼科、耳科等足够的空间,并设有一栋隔离大楼,其他还有药局、病菌检验室、手术室、X 光室、太平间、行政、餐厅等等”。⑤黄福得:《1897 至1914 年间德国在青岛的殖民体制与卫生建设》,第150 页。在基本的医疗人员方面,野战医院配有“1 位总医师、4 位看诊医师、3 位助理医师,此外还有2 位督察员、6 位女看护和6 位护士”。⑥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第300 页。其中医师的职位是由德国军医来担任的,总医师同时也是医院的管理者。
野战医院主要供德国驻军使用,也收容和医治欧籍平民。在1901 年9 月同善会(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的花之安医院(Faberhospital)建成之前,野战医院还为华人开设门诊;具体的诊治工作由两位军医来承担。为了控制驻军中性病的产生和传播,总督府在1906 年设立了用于安置性病患者的性病医院。该医院可容纳60 位病人,在经济上附属于野战医院,由一位军医专门负责。⑦参见Eckart,Deutsche Ärzte in China 1897—1914,S. 38,S. 55,S. 52—53.
除了位于青岛市区的野战医院之外,德国军医还一直负责由总督府设立在台东镇、沙子口和李村的华人诊所。⑧参见Uthemann,Walther/Fürth,Ernst,“Tsingtau. Ein kolonialhygienischer Rückblick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Deutschen Kiautschougebietes”,in:Beihefte zum 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hygiene 15,4(1911),S. 26.其中,负责李村诊所的军医同时还担任着整个李村地区医官(Bezirksamtsarzt)的职务;他不仅为李村区内其它村庄的居民定期开设门诊,⑨Huang,Fu- teh,Qingdao,S. 221.还管理着位于崂山脚下针对病重体弱士兵设立的麦克伦堡疗养院(Genesungsheim Meckenburghaus)的医疗工作。⑩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年,第304 页,第248,304,439 页。以下简称《青岛开埠十七年》。李村作为租借地的乡区,同时连接着青岛与山东的内地,被德国殖民当局视为在医疗上保卫青岛的前哨站,这也正是总督府派遣军医持续驻扎在那里的主要动机之一。
出于同一动机,当然也带有通过军医的救治行为来赢得当地“华人的信任和感激”的意图,总督府不仅在租借地内,而且在租借地周边的胶州县城、四方村等地为当地中国人设立了小型医院和门诊,并派遣军医来负责这些医疗机构里的日常工作。据记载,这些机构收治了一定数目的中国患者,而且受到了当地中国人的欢迎。[11]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胶澳发展备忘录〉全译》,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 年,第304 页,第248,304,439 页。以下简称《青岛开埠十七年》。
虽然与为德国驻军和平民提供的医疗服务相比,总督府直接针对中国居民的医疗救助,无论是在资金投入还是在设施规模上,都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出于对德国驻军和平民健康的考虑,总督府还是关注当地中国人的医疗卫生状况的。只是与直接的介入相比,它把更多的精力投入支持租借地各教会在华人中开展医疗活动。
具体来说,除了在野战医院里接收和诊治由同善会花之安医院转来的病患之外,德国军医还被派往了同善会于1902 年在高密县城和1905 年在台东镇为中国人设立的两个诊所,以及柏林会(Berliner Missionsgesellschaft)1906 年在即墨县城建立的华人门诊。其中对高密诊所的医疗援助维持至1905 年底德国军队撤离高密,其间先后有三位军医被派到该诊所工作。①关于高密诊所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德国学者葛绿蒂教授(Lydia Gerber)的文章:Lydia Gerber,“Mediating Medicine,Li Benjing,Richard Wilhelm and the Politics of Hygiene in the German Leasehold Kiaochow (1897—1914)”,in:Joanne Miyang Cho/David M. Crowe,eds.,Germany and China. Transnational Encounter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4,pp.97—112.由于天主教圣言会(Steyler Mission)一直未为其中国教区派遣专职的传教士医生,所以,其在青岛和兖州府建立的两个华人医院的医疗工作,基本上都是由德国军医来完成的。位于青岛的天主教医院成立于1905 年6 月,至1914 年,军医库尔特·麦克莱恩(Curt Mac Lean,1872—1932)、汉斯·珀德斯塔(Hans Podestà,1871—1953)等在那里工作过;兖州府的华人医院于1906 年11 月建成,总督府为其派遣了军医多尔(Dörr),他工作到了1907年6 月。
总体来看,德国军医在租借地及其周边的医疗实践,无论是直接针对德国驻军的医疗工作,还是有限地扩散到中国居民中的救治服务,都是以保护驻军身体健康,进而维护殖民统治为首要目的的。经过几年的建设,至1910 年左右,胶澳租借地的医疗卫生设施基本完善,卫生状况也有了显著的变化;据记载,驻军中患病士兵的数量,与占领初期相比呈现出了明显下降的趋势。②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第477 页,第306 页,第249 页,第306 页。
二、德国军医的科学考察
德国军医在租借地不仅进行医疗实践,还开展科学考察的工作。为了更多地获取关于中国的信息和知识,同时也出于彰显德国科学水平的动机,胶澳总督府一直支持、资助和推动对租借地及其周边地区自然、文化及社会情况的科学考察。③胶澳总督府编写的《胶澳发展备忘录》是总督府的年度工作报告,自1898 年10 月至1909 年10 月起每年出版一册,1910年之后改名为《胶澳年鉴》,篇幅大大缩减,共出版了4 期。1898 年至1909 年的每一份报告,都对当年租借地的科学工作做了具体总结,其中涉及天文气象学、细菌学、化学、动植物学、人口统计学等许多领域。而且,“按照殖民行政管理当局1905 年以后的计划,在把青岛建设成为德国的文化中心的同时,也要把德国殖民地建设成为德国在中国的一个学术中心。在这里,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和思想科学并驾齐驱”。④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第295 页。在这一背景下,大量的科学观察、调研以及研究得以进行。
在医学领域,具体的科学工作主要是由军医来完成的。他们进行考察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更有效地防治影响租借地驻军身体健康的各种疾病;另一方面,则是出自自身的学术兴趣。与德国军医在医疗实践方面较少地顾及到中国居民相比,他们的科学考察工作十分关注发生和流行在中国人中的疾病;因为通过对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及时地了解租借地欧洲区周边的健康情况,以防止疾病尤其是流行性传染病,蔓延到德国驻军及平民之中。而且,19 世纪90 年代在德国盛行的对不同种族之间假定存在的身体和外形的差异进行科学或者伪科学的研究,也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德国军医对与中国患者有关的健康及治疗问题的兴趣。⑤参见Lydia,Mediating Medicine,S. 104.
鉴于此,德国军医科学考察的范围很广,不仅涉及驻军士兵和欧籍平民,也包括可获得的有关中国居民健康以及卫生环境的情况;其中,对各种疾病的观察和研究,倾注了军医的主要精力,也构成了他们科学工作的主体部分。这方面所使用的资料,不仅直接取自于野战医院和在租借地及其周边各地诊所里所收治的病患,还由分布在山东省内的各传教机构通过寄送有关疾病在当地爆发和流行的报告和标本的方式来提供。在德国统治胶澳租借地的17 年里,后一种方式一直得以保持;其目的主要在于向总督府提供有关中国医疗情况的准确信息,“据此,总督府便可不断地了解省内的病情和及时地采取各种措施了”。⑥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第477 页,第306 页,第249 页,第306 页。
不过,总督府并不满足于此。为了“在不同地方搜集到有关这些疾病出现和传播、产生原因及传染载体方面的材料”,总督府还派遣军医深入到山东省内地进行实地的疾病调研。在这一过程中,军医不仅搜集了疾病的信息,还同当地的病人有所接触;并通过劝导的方式,使他们接受了西医的检查和治疗;更为重要的是,总督府十分信任通过这种调查方式得出的结论。⑦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第477 页,第306 页,第249 页,第306 页。所以,虽然调研活动由于人员缺乏以及战争的原因只进行了这两次,⑧但是,搜集疾病资料的习惯并没有因调研活动的结束而停止。在医疗实践中,尤其是在流行性传染病出现时,军医一直进行着类似的调研活动。比如,1909 年4 月在即墨县城爆发猩红热的时候,恩斯特·菲尔特(Ernst Fürth)医生被派到即墨,进行了5 天的实地调研;①Fürth,Ernst,“Eine Scharlachepidemie in Schantung. Ein Beitrag zur Kenntnis des chinesischen Arznei- und Seuchenwesens”,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4,1(1910),S. 12—20.在1911年春季总督府抑制鼠疫之时,贝森布鲁赫(Besenbruch)医生利用所获取的数据,研究了天花在租借地及其周边的流行情况。②Besenbruch,“Zur Epidemiologie der Pocken in Nordchina”,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6,2(1912),S. 48—53.
对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疾病资料进行细菌学层面的研究,是1890 年代后半期以来德国热带医学的重点。③Eckart,Wolfgang Uwe,“Die Medizin und das,‘Größere Deutschland’Kolonialpolitik und Tropenmedizin in Deutschland,1884—1914”,in: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13,3(1990),S. 132.在胶澳租借地,隶属于野战医院卫生化学检查站的细菌学化验室,是德国军医进行医学研究的主要场所。该化验室建成于1899 年,之后又得以现代化和扩建;其中,军医的主要工作“是隔绝病原体,制造血清,防止潜伏在保护领地内的传染病源(特别是伤寒、痢疾、霍乱、某些轻型疟疾,包括鼠疫和麻风病)”。④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第300 页。
除了疾病的观察和研究之外,出于预防疾病的目的,军医还对租借地及其周边的卫生环境进行了考察。其中最为频繁的是,为确保水质情况符合卫生学的标准,针对租借地各处的河水以及水厂和水井里的水所做的细菌学检验。⑤参见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第439—440,528,601,684—685 页。这项工作也是在细菌学化验室里完成的。
在这些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德国军医撰写了一定数量的、关于租借地及其周边地区医疗卫生状况的调研报告和学术文章。从内容上来看,它们主要是以特定疾病的专门探讨为中心。其中对驻军身体健康威胁较大的疾病是德国军医关注的主要对象;而描述和分析为获取这些疾病起源、传染途径、流行情况、防治方法所进行的实地调查、实验研究以及由此得出的结论,则构成了关于该疾病的研究性报告和文章的主要内容。痢疾和急性肠炎在驻军中的发病率很高,尤其在德国占领胶澳租借地的早期阶段,而且并没有随着租借地医疗卫生环境的改善而大幅减少,在每年的夏季仍然定期出现。基于此,很多军医都对它们进行了观察和研究。
博泽(Böse)医生在1908 年发表的《关于东亚痢疾的观察与经验》是胶澳军医中最早,也是比较全面地对痢疾展开科学论述的文章,⑥Böse,“Beobachtungen und Erfahrungen über Ruhr in Ostasien”,in:Zeitschrift für Hygiene und Infektionskrankheiten 61,1(1908),S. 1—48.认可了当时医界已经基本普遍公认的细菌性痢疾与阿米巴痢疾之间的病源区分,并从痢疾的病因、传播、诊断、分类、治疗、预防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之后,海因里希·特莱布尔(Heinrich Trembur,1871—?)医生在《对1906—1908 年青岛痢疾的观察》论文中,从病原学角度继续细化了痢疾的分类;⑦Trembur,Heinrich,“Beobachtungen über Ruhr in Tsingtau in den Jahren 1906—1908”,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2,12(1908),S. 389—399.科伯特(Kobert)和菲尔特两位医生在诊断学方面探索了细菌性痢疾和阿米巴痢疾的区分。⑧Kobert,“Beiträge zur Ruhrdiagnose”,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4,16(1910),S. 515—518;Für th,Ernst,“Über die Agglutinationen mit Blutserum von Ruhrkranken des Jahres 1909 in Tsingtau”,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4,18(1910),S. 579—588.而军医埃里克·马尔提尼(Erich Martini,1867—1953)和施塔比(Staby)则是针对当地的肠道疾病——主要是痢疾和急性肠炎——进行了研究性的报道。施塔比的文章《青岛市1908 年夏秋季肠道疾病的临床观察》主要记录了痢疾和急性肠炎的不同症状及治疗方法。⑨Staby,“Klinische Beobachtungen bei den Darmerkrankungen des Sommers und Herbstes 1908 in Tsingtau”,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4,12(1910),S. 368—375.马尔提尼的两篇文章《关于1908 年夏季青岛流行性肠道疾病的病原体》和《1907 年至1911 年间胶澳租借地及山东省中流行性肠道疾病的微生物学经验》区分了引起肠道疾病的不同病原体,并在这一基础上提出了更具针对性的预防措施。①Martini,Erich,“Über die Erreger der epidemischen Darmerkrankungen Tsingtaus im Sommer 1908”,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4,11 (1910),S. 333—343;ders:“Mikrobiologische Erfahrungen bei den epidemischen Darmerkrankungen des Schutzgebiets Kiautschou und der Provinz Schantung in den Jahren 1907—1911”,in:Zeitschrift für Hygiene und Infektionskrankheiten 69,2(1911),S. 376—396.
此外,麦克莱恩医生根据其在野战医院4 年半(1903—1907)的观察和研究,针对在病理上当时医界还没有给出明确解释的阑尾炎进行了集中探讨;提出了阑尾炎更容易在欧洲人中出现的原因不在于种族因素,而是由过量食肉的饮食习惯造成的。②Mac Lean,Curt,“Zur Aetiologie der Appendicitis”,in:Mitteilungen aus den Grenzgebieten der Medizin und Chirurgie 21,1(1909),S. 51.军医菲尔特和马丁·克莱茵堡(Martin Kreyenberg,1872—1914)对斑疹伤寒进行了病原学层面的研究,分析了斑疹伤寒发生在青岛的原因、探讨了斑疹伤寒的病原体,接受了跳蚤作为传播媒介的看法,并以此提出了预防的方法。③Fürth,Ernst,“Die Fleckfiebererkrankungen des Frühjahrs 1911 in Tsingtau und Untersuchungen über den Erreger des Fleckfiebers”,in:Zeitschrift für Hygiene und Infektionskrankheiten 70,3 (1912),S. 333–370;ders:“Neuere Untersuchungen über Fleckfieber”,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6,8 (1912),S. 241—255. Kreyenberg,Martin,“Einige Beobachtungen bei der Flecktyphusepidemie in Süd- Schantung im Frühjahr 1911”,in:Archiv 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6,14(1912),S. 483—487.菲尔特医生通过对病例粪便样本的微观检测,证实了短膜壳绦虫(Hymenolepis nana)在山东省的存在,该寄生虫自1851年在开罗被发现以来,很少出现。④Fürth,Ernst,“Ein Fall von Taenia(Hymenolepis)nana(v. Siebold)in der Provinz Schantung(China)”,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4,10(1910),S. 315—316.马尔提尼医生于1910 年确定了钩虫属(Ankylostomum)存在于山东省,同年,军医普利尔(Prieur)和菲尔特对此加以确认,同时还首次在当地发现了美洲板口线虫(Necator americanus,简称美洲钩虫),后者是1903 年新分离出来的寄生虫。⑤Prieur/Fürth,Ernst,“Ankylostomum duodenale und Necator americanus(Stiles)in Kohlenbergwerken Schantungs”,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4,19(1910),S. 601–604.
除了对疾病的探讨外,还有一些报告和文章较全面地论述了租借地的医疗卫生情况。其中军医古斯塔夫·阿曼德(Gustav Arimond,1862—?)发表于1898 年的《胶澳来信》,是胶澳军医中最早介绍租借地卫生和疾病的文章,也呈现了胶澳地区在占领初期的情况。⑥Arimond,Gustav,“Brief aus Kiautschou”,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2,4(1898),S. 236—241.其它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军医瓦尔特·乌特曼(Walther Uthemann,1863—1944)和菲尔特合作的文章《青岛——对德国胶澳地区发展的殖民卫生学回顾》。⑦Uthemann/Fürth,Tsingtau,S. 5—39.该文章在当时被称为是“详细地、极为细致和热情地书写德国在远东胶澳租借地15 年来所作出的巨大成绩的作品”。⑧Mitteilungen zu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und der Naturwissenschaften 12,1(1913),S. 107.总督府卫生顾问弗兰茨·克罗内克(Franz Kronecker,1856—1919)根据其在租借地15 年工作经历所写的长文《胶澳殖民地十五年——一项殖民医学研究》也是这方面的代表作。⑨Kronecker,Franz,Fünfzehn Jahre Kiautschou. Eine kolonialmedizinische Studie,Berlin:J.Goldschmidt,1913.这篇文章在德国当时的学界具有一定的影响,被称为是“值得一读的”作品,不仅得到了专业医学杂志,也受到了殖民方面报刊的积极推荐。⑩参见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8,21(1914),734;Koloniale Rundschau,7(1914),S. 448.
这些医学报告和专业论文,丰富了德国军医自身的学术成就,反映了他们当时的认知能力和水平;同时也构成了同时代人以及当代人了解胶澳租借地及其周边医疗卫生状况的资料来源。它们所呈现出的胶澳地区环境及健康的情况和特点,不仅在地域层面上丰富了德国热带医学的研究,而且通过对当时医学界经常探讨的一些疾病,比如:痢疾、伤寒以及寄生虫病的持续观察和探究,补充和深化了医学界对这些疾病的认识,一些研究成果和科学发现还为人类医学的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三、德国军医对中西医交流的推动
虽然德国胶澳军医与传教士医生或者民间医生相比,缺乏与当地中国居民的直接交往,但是在实际的医学实践和科学考察中,他们还是会与当地中国人及其生存环境进行接触。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传播了西方的现代医学,也观察到中国的医疗卫生情况,并把自己搜集到的有关中国医学的信息以及自己对中国医学的认识介绍到了德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德国军医在租借地及其周边的医疗工作推动了中西医的文化交流。
在当时的中国,中医基本上一直都是中国人的首选。在胶澳租借地,由于总督府对于中医的开业运营并没有任何管制措施,中国人自己开设的诊所和药店依然很多。尽管如此,在同中国居民的相互接触中,德国军医所表现出的先进的医学理念、高超的医学技术以及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所具有的人文关怀,逐渐获得了中国居民的认同。与初期占主导地位的抵触情绪相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愿意接受德国医生的治疗。他们到德国人设立的医院和诊所去问诊就医,甚至把德国医生请到家里来就诊,而且在治愈之后,还以各种方式对德国医生表示感谢:
李村门诊部的病员也逐年增加。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诊所在华人中是多么受欢迎:一对夫妇从400 里(200 公里)路外赶到李村求医。①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第439 页,第304 页。
位于中国县城胶州的门诊部,在过去的一年里共为765 名男子和167 名妇女看过病。很多人的手术获得了成功。随着信任的增加,中国民众都向德国海军医生求医问药并为表达对海军医生的感激之情在告别时总要送上一块匾和请吃一顿饭。他们也通过自愿缴费满足了临床治疗的费用,除了免费诊治和药品外,无需门诊部捐助者提供额外补助。②青岛市档案馆编:《青岛开埠十七年》,第439 页,第304 页。
这些记录摘自德国官方的报告,虽然其中不免带有美化军医在华工作和辩护德国在华殖民扩张的意图,但是仍然可以看出,中国民众对德国医生——尤其是那些成功救治了病人的医生——友好和热情的态度。
不仅在治疗的层面,德国军医的医学工作,也向租借地的中国民众传播了西方的公共卫生观念。虽然总督府在华人居住区的公共卫生建设方面并不积极,但是出于疾病预防的目的,还是针对中国人颁布了严格的卫生法令,在华人居住区引入了现代的卫生设施;特别是在传染性疾病发生的时候,德国军医往往会被派往前去调查病因,并参与疫病的消除。
为了防止1910 年11 月流行于东北并在1911年1 月蔓延至山东的鼠疫进入到胶澳租借地,总督府不仅通过严厉的检查和隔离措施在陆路和海路上封锁了租借地,而且还向中国民众积极地宣传和讲解鼠疫病情,使他们了解到鼠疫的危险,知道基本的防范方法,参与到保护租借地的工作中来。这些措施成功地保护了租借地,同时,其教化以及示范效应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中国居民传统医疗卫生观念和格局的转型。正如1911 年4 月9 日的《胶州邮报》所报道的:
如果需要清洁是进步文化的标志,那么这里的中国人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感到极度不洁是一种令人烦恼和危险的事情。他们至少看到了可以形成危险病原体的地方。这是一项人们几年以前梦寐以求的成就。现在重要的是,要保持这种新的认知,并加深和扩展它;即不是以一种给中国人带来各种尴尬和琐碎规定的方式,而是通过卫生学的教导,这些教导必须在大概每个月,以用可理解的语言撰写和清晰印刷的传单的形式,免费分发给住户,并张贴在庭院里。现在山东省的许多大城市中都发生了这样的情况。③“Kultur und Hygiene in Tapautau”,Kiautschou Post(9. 4. 1911),转引自Biener,Das deutsche Pachtgebiet Tsingtau in Shantung 1897—1914,S. 275.
对西方医学的积极反应不仅表现在民众层面。西方现代医学的有效成果也获得中国官方的支持。中国官方甚至邀请德国的医务工作者参与到政府创立新式医院、开展医学教育以及建设公共卫生秩序等现代化的医疗卫生事业中。比如,官方支持德国人在租借地及其周边设立诊所和医院,任用德国军医在济南府的华人医院里工作,参与和资助“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的建立,聘用德国医生加入到中国政府的防疫工作中,等等。
不过,当时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医学的接受还是有限的。一方面,在一些疾病,主要是内科疾病上,中国民众并不愿意寻求欧洲医生的治疗。④参见Böse,Beobachtungen und Erfahrungen,S. 25;Fürth,Eine Scharlachepidemie,S. 12—13.另一方面,在接受西方的公共卫生思想方面,中国人的观念也没有彻底地发生转变。比如:在面对疫情时,中国官员往往倾向于采用中医的传统方法;①参见Huang,Fu- teh,Qingdao,S. 241—242.而且即便在1910/1911 年的肺鼠疫之后,租借地中也仍然存在着对西方卫生理念的敌意。②参见Fürth,Neue Untersuchungen,S. 242;Martini,Erich,“Über die Bedeutung der Internationalen Pestkonferenz zu Mukden(Mandschurei)1911”,in: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38,30(1912),1420.
尽管德国军医带来的西方现代医学,无论是作为一种治疗手段,还是在理念层面,都并没有被当时的中国人作为主导医学所广泛接受,但是,他们还是为租借地及其周边的中国民众展示了现代医学的观念和手段,推动了西方医学在华传播。不仅如此,一些德国军医还利用身在中国的这个便利条件,以租借地为对象,开展了与中国医学相关的调察与研究工作,并将其获得的成果介绍到了德国。
按照当时欧洲普遍的看法,中国医学是一个充满迷信、猜想以及少许正确认识的混合体,与西方现代医学相比是十分落后和粗糙的;虽然其中存在着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但它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在实践中是无法有效保证中国人健康的;所以,中国是一个充斥着各种疾病的国家。德国军医基本上都是带着这样的先入之见来到胶澳租借地的,同时,现代医学的教育背景以及普遍的文化优越感,也推动着他们对这种负面观点的接受。不过,实际的接触和感知会使他们关于中医的认知具体化和细致化,因此,他们对中国医学的阐述,不仅在内容是多样的,在观点上也是有差异性的。
从内容上来看,德国军医很少关注中国医学的知识本身,而是比较多地论述了中国的医疗体制、公共卫生以及疾病的流行情况。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欧洲社会中流行的对中国医学的负面观点,使得他们认为没有必要,也没有兴趣去了解那个普遍被认为是原始、落后的中国医学;另一方面,他们的工作重心是保护驻军的健康,所以他们往往只在意与此目的密切相关的医学问题,如当地的卫生环境、疾病状况等;还有就是语言障碍的原因——他们缺少中文知识,无法与中国医生进行交流,也不能阅读与中国医学有关的书籍,只能通过自身的观察和体验来获取有关中国医学的信息和了解中国医学。基于此,德国军医主要记录了一些比较表面的医学现象,不过这些现象体现着中国医学的特点和水平,因而它们同样是中国医学的一部分,而且从对这些现象的描述中还可以看出他们对中国医学的观点。
具体来看,菲尔特医生针对中国医生的培养方式进行了阐述:“中国医生的职业训练是非常不同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它缺乏医学教育机构,而且从业者不需要进行我们意义上的考试。医术大多是由父亲教给儿子的,但是,许多人只是在其它职业失败后才转向医学的,例如那些没有获得高等学府的学者头衔,进而没有达到进入仕途前提条件的人。他们从大量现存的医书中获取知识,没有机会在病床前接受系统的课程。”③Fürth,Eine Scharlachepidemie,S. 17.
贝森布鲁赫医生指出了中医行业中行骗现象的存在:“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都有人从事接种职业。对疫苗接种的信任和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欺诈者在其中进行了不干净的生意。因此,一个江湖骗子走街串巷,用炼乳为相信他的群众接种。”④Besenbruch,Epidemiologie der Pocken,S. 50.
在公共卫生方面,中国人被认为是没有现代卫生观念的。⑤参见Besenbruch,Epidemiologie der Pocken,S. 48.例如:中国人的垃圾处理方式是混乱的,街道上“堆满了污物和垃圾”,存储了“各种形式的废物与粪便”;废水只要“不在空气中蒸发或被土壤吸收,就直接或通过各种弯路流入城市中的溪流或池塘”。⑥Arimond,Brief aus Kiautschou,S. 238,S. 239.“饮用水的供应特别糟糕”,它是通过从“接收相邻地区所有废水”的水道中抽取存水来完成的。⑦Arimond,Brief aus Kiautschou,S. 238,S. 239.在面对疫情时,乌特曼医生观察到,中国人不仅缺少相关的医学知识,而且冷漠、迷信。⑧参见Uthemann,Walther,“Wie begegnete das Schutzgebiet Kiautschou der andringenden Pestgefahr? Eine Schlußbetrachtung”,in:Archiv für Schiffs- und Tropen- Hygiene 16,23(1912),S. 792.虽然政府官员在流行病发生时会建立用于存储和发放药物的临时工作站,但是菲尔特医生发现,负责发放药品的官员常常在这一过程中中饱私囊。⑨参见Fürth,Eine Scharlachepidemie,S. 18—19.
基于中国医疗体制的松散混乱,公共卫生观念的缺乏,租借地常常被描述为一个疾病很多的地方:
如果一个地方处于这样不健康的状态,并且卫生条件极度危险,那么它在健康方面的坏名声被广泛知晓,会令人感到惊奇吗?最有利于人们健康的是冬季,冬季有基本符合该省大陆性气候的严寒,和经常在裸露平原上飞卷数天的刺骨北风。但是,盛夏时节会有所不同,如果潮湿和温暖结合在一起,以使休眠的病菌在准备充分的培养基中发展和繁殖。疟疾、痢疾和伤寒是这个城市的常客,也是可怕的客人,它们会在居民中,即尤其是在最恶劣卫生条件下生活的最贫困的阶层中,造成浩劫。①Arimond,Brief aus Kiautschou,S. 239.
上述表述体现了德国军医对中国医疗体制以及卫生和疾病情况的负面态度。这种态度是当时欧洲社会对中国医学主流看法的翻版。虽然不能否定其中带有的真实性——因为它们来自于德国军医在华的亲自观察——但是,一些具有感情色彩的措辞,如“堆满了污物和垃圾”“极度危险的卫生条件”等等,还是体现了他们主观的负面心态。德国军医的这些表述建构了中国医学的负面形象,即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技术上,中国医学都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借此,德国殖民者在胶澳租借地,甚至在中国开展医疗卫生活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得到了强调。
事实上,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医学,在预防和治疗疾病方面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不逊色于西方现代医学。所以,有的军医在亲眼目睹了中国医学的实际疗效之后,对中医的价值产生了局部的认同;他们摒弃了完全否定中国医学的观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中医的有效性,还客观地介绍了中医中的某些治疗手段。
比如,恩斯特·普拉尔(Ernst Prahl,1876—1931)医生虽然不认可中国医生的医术,但是在从医学角度观察和研究了山东地区的自杀现象之后,肯定了中国医生挽救中毒者生命的能力。②参见Prahl,Über Selbstmorde,S. 702—703.虽然当时欧洲的牛痘接种术更为安全,但是,贝森布鲁赫医生阐释了中国人所使用的人痘接种术,并肯定了该技术的医学价值。③参见Besenbruch,Epidemiologie der Pocken,S. 50.马尔提尼医生和药剂师瓦尔特·格罗特(Walter Grothe)对山东民间在治疗肠炎时普遍使用的“可食用的土”(essbare Erde)进行了研究,并与高岭土(Bolus alba)——当时在欧洲作为自然疗法来使用——的化学成分进行了对比;以此为基础,他们得出结论,在中国“一个与之(指高岭土)相对应的药剂——几乎是以相同的应用方式——可能已经成功地使用了几个世纪”。④Martini,Erich/Grothe,Walter,“Über essbare Erden und ihre Verwendung als Heilmittel”,in:Deutsche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36,19(1910),S. 900.
透过上述肯定的评价,可以看出,德国军医并没有完全否定中国医学。尽管这些肯定的态度并不是针对中国医学的整体,也没有深刻地影响到当时对中国医学的普遍负面看法,但是它们表现了殖民主义时代在中国医学问题方面是存在着相对客观的态度和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倾向。总体来看,虽然德国军医对中国医学的知识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兴趣,而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与胶澳驻军健康状况息息相关的卫生与疾病的问题上,但是根据在租借地的实际观察,他们把中国医学在当地当时表现出的状态介绍到了德国,对德国社会了解中国医学的现状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医疗实践和科学考察构成了德国军医在胶澳租借地医疗工作的两个主要方面。虽然军医的工作重心是维护驻军的健康,进而把租借地建设成为“模范殖民地”以及远东的“文化展示橱窗”,但是在实际的工作和生活中,他们还是深入到了当地的社会与环境中。他们向租借地传播了西方现代医学的理念和技术,同时也把他们所感受和获取到的有关中国医学的信息传递到了德国,促进了中西方的医学文化的交流。虽然德国军医只是推动中西医互动进程的一个群体,不过可以看出,在殖民主义时期,不仅有西医的东传,中国医学也被介绍到了西方;而且并不是以通常所认为的完全“污名化”的阐述方式,其中还存在着客观的描述和科学的研究。尽管,无论是从中国人对西医接受的角度来看,还是在西方社会对中医的认知层面上,这种交往都具有局限性,都还只是停留于表面,但是它推动了中西医的早期融合,为后来两种医学之间可能进行的的结合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