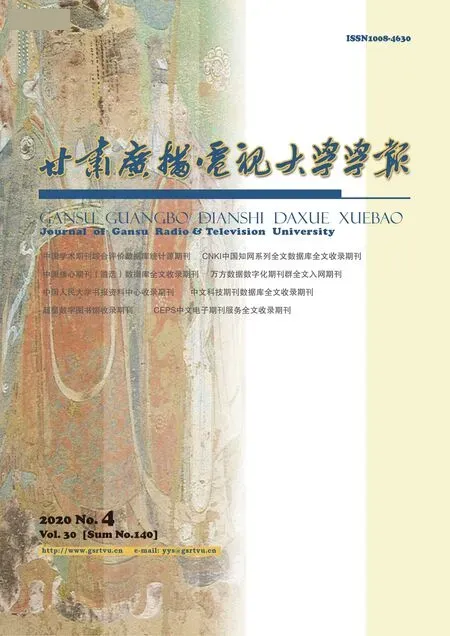叙事艺术中的沉默与发声
——读王小波《青铜时代》
2020-03-03周启星
周启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2400)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生态中,文学已然呈现出纷繁复杂的写作倾向,个人化现象较为明显,文学流派渐趋式微,文学不再鲜明地呈现出某种集体意识,而是以作家的个性化写作立场和风格赢得评论家及大众读者的注意力。20世纪90年代长篇小说的集体出现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文学正走向叙述的成熟,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现代稿酬制度以及网络文学的兴起,作家们大多对宏大历史的书写采取绕行的态度,或将其作为叙事大背景铺陈在个人化的叙事视角之中。而王小波的叙事艺术呈现出多重时空背景和人物分层,看似众声喧哗且令人眼花缭乱的叙事技巧背后,是作者面对文学生态所作出的选择,叙事控制中表达自己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态度。
一、多重叙事的自由与集中
王小波小说中独特的叙事方式和结构特点——多重的叙事结构及表达立场,并非是他所有小说叙事构篇的常规手法,而只散见于他的少数几篇小说之中,但却有着完整而臻于成熟的艺术呈现。这样的叙事特点在王小波的早期小说《绿毛水怪》中初露端倪,到了小说集《青铜时代》(收录《万寿寺》《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中,则显示出一种自觉的刻意追求。
读王小波的小说,不难感觉到他的笔下灌注着一种似闲散任意,实严肃诚恳的格调,使读者自以为可以很切实地把握他的思维,但却又实在无以言喻。造成此种状态的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小说在叙事上的多重表达,真实与虚假交织网罗以及文本情节的随意跳跃往往容易使人动摇自己的立场而迷失在小说的多重世界里。
在《绿毛水怪》《红拂夜奔》和《寻找无双》这三部小说里,都出现了一个名叫“王二”的人物。王二作为小说人物贯穿在王小波的绝大多数作品中,而他们的多处陈述又常带有作者直接发言的性质,他常以非人格化的观点来申诉具有作者人格化的言论,彼时或可将他视作作者的替身。正如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所提出的:“在他(作者)写作时,他并不是创造一个理想的,非个性的‘一般人’,而是一个‘他自己’的隐含的替身。”[1]80诚然,所有的描写都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描写本身便是一种自主观出发的行为,文学更不可能全然做到所谓客观、非人格化。那么,读者进入文本的过程,其实是辨别作者所说的话的过程,寻找王二何时充当了作者的第二自我,何时只纯粹作为故事中人的身份而存在。但即使王二时而承担了作者的一部分意识,他与作者仍旧远远不可混为一谈,不过,我们未尝不可以从王二这一人物及他所牵连出来的整个故事世界,来探看布斯所说的“隐含作者”。王二不仅是故事的主人公之一,作者还将叙事的工作推给了他,那么他势必蕴含了“隐含作者的精华和思想规范的核心”——“风格”“基调”“技巧”[1]83三者的一部分。
王二在叙事中担任了三重角色。第一,故事的叙述者。王二是以第一人称“我”自称的,他在故事中讲述着别人的故事,以一个近乎全知的视角进行叙述。第二,故事的参与者,即他自己也成了故事中的人物之一。在《绿毛水怪》里王二的篇幅很少,是旁观者与倾听者。在《红拂夜奔》中“王二”这一形象,则几乎平行于故事的主人公红拂与李靖而存在,这就形成了故事的双重营构。作者把讲故事的人推到了台前,并且讲故事的人也同时参演着故事,变成了故事中的一个主人公,甚至牵带出了他周边的世界。在《寻找无双》里王二出场的频率比较少,但也同样兼任着讲述与参演的双重身份。第三,作者的代言人。在王小波的小说里,作者并不是客观地只讲述不发言,也不是让人物通过正常可靠的渠道讲出作者想讲的话,让读者感觉不到是作者在发声,而经常是作者抢过叙事者的话筒自己发声。此时,王二就是作者的“第二自我”,甚至可以将他的声音当做隐含作者的声音。
这样的小说叙事结构看似闲散,但作者的控制方式和控制力度却表现得自由而强势,作者既给了叙事者所述故事中的纯粹主人公一个话筒,又给了叙事者一个话筒,同时自己还在幕后握有一个话筒,并且操控着话筒的发声时间、音量以及话语的虚实。比如《红拂》中王二虽以第三人称有限视角,讲述着李靖与红拂的情缘纠葛、王二与女友小孙的生活,而讲述的内容和幅度却被作者控制着。由于并非全知视角,便给分析、评论留下了可能和空间。在《青铜时代》中经常会出现作者以王二的话筒发出的对事件的讨论,而这样的讨论,立场有可能不同于故事中的纯粹主人公,这种立场到底是王二的还是作者自己的又很难分辨。能明显地感觉到的是,叙事者越位兼任了主人公,作者打破了沉默发表议论,这便造成了多重叙事表达的局面。
二、叙事控制的表达及其效果
多重叙述的小说技巧给文本带来了超越单一叙述场面的繁复效果。
首先,文本跳跃一方面带来了情节分裂和时空错位,造成故事主人公与叙述者之间的距离感,而作者的控制也在同时消弥着这种距离感。
比如《红拂》有很大的篇幅只讲李靖与红拂,语言较为现代化,并时常涉及某些现代物质语词,单线叙述之流畅冗余过之,使读者几乎要忘记了王二与小孙的故事线,但是李靖与红拂告一段落之后,文本又转回到王二与小孙。唐朝、当代,李靖红拂、王二小孙就这样互相穿插并行,两条线分属于中古与现代,他们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毫无联结的可能,但是作者通过讲述视角的转换和文本的跳跃,使他们在小说中相遇。这种叙述转换和跳跃的手法也可见之于王小波其他的小说中,其方式或是讲完一个完整事件后的直接跳跃,或是因同一个话题将两条线上的人物相提并论,通常以后者居多,以至于很巧妙地弥合了时空之间的距离,消除了跳转之间的突兀。如《寻找无双》中有这样一段:
大家就高叫:“鱼玄机,没出息!怎么能讲这种话!!”鱼玄机回嘴道:“真是岂有此理!你们怎么知道该讲什么话!……难道你们都上过法场,被绞过一道吗?当然,当然,讲这些话不对。最起码是很不虚心啦”。
据我表哥说,死刑犯中,原来有过一些很虚心的人。……还有一位老先生,被判宫刑。当众受阉前他告诉刽子手说:“我有疝气病,小的那个才是卵泡,可别割错了。”他还请教刽子手说:“我是像猪挨阉时一样呦呦叫比较好呢,还是像狗一样汪汪叫好。”不要老想着自己是个什么,要想想别人想让咱当个什么,这种态度就叫虚心啦。[2]576
这是由鱼玄机被处死时的场景转移到王二表哥的讲述,牵引的线索是“虚心”这一话题,这样的跳转无疑是完美的,尽管时空跨越非常之大,但是读者丝毫感觉不到它的不合理,作者正是通过叙述者的联想进行故事上的穿梭,而这种穿梭并不是空无依傍的,其内部有着紧密的逻辑关联。
其次,众声喧哗的噪音事实上合成一种背景轻音,从而突出作者独立意志的独白。
王小波自觉的思辨思维与包容意识,决定了他的小说是营造众声喧哗的话语场,正调与反调相碰撞,主调与杂音相伴生,甚至是多种互相抵牾的声音的“不齐声”合唱。巴赫金在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提出了“复调”的概念,即小说中“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3]4,代表不同的价值观念以及情感态度,这正是王小波小说的结构模式。所不尽相同的是,王小波小说中的各种声音并不拥有独立平等的地位,也不是“直抒己见的主体”[3]5,而是在作者统一意识的支配下彼此争胜,或是妥协。而在文本多种表达的背后,读者总能听到一个作者的话语意志,而它是单一,也是实质性的“独白”。
在王二自白式的解说中,读者实际上可以判断出作者的臧否意向。多种声音的争论无非只在同一层面上,可以看做一个问题的几个方面,作者可以提供选择,也可以表明自己的选择,但最终摆出来的却是整个问题,多个声音其实是一个合音。
在小说《寻找无双》中,无双存在的证明以及无双下落的探明过程久经波折。作者演绎了宣阳坊各位老板的反应变化、王仙客从怀疑到坚定的过程,让各种不同的声音同时显现。最终王仙客知道了无双的下落,但也说“我估计王仙客找不到无双”,“寻找无双”的过程是一个探寻真理的隐喻。实际上,王小波在这篇小说里借寻找无双之题发挥,揭露智慧被愚弄、真实被掩盖的遭遇[4]。
再次,通过主体间不同声音的表达造成观点同等地位的假象,在控制叙事中限制道德判断。马克·科里在《后现代叙事理理论》一书中选取了《爱玛》和《化身博士》的例子来说明“通过叙事视角控制距离的叙事原则是用以控制道德判断的一种手段”[5]130,将叙事者与叙述内容之间的结构距离转化成道德距离。而《化身博士》中“把时间距离当成道德距离”[5]131则是这一手段的一种变型策略。
王小波的小说除了利用第三人称的叙事视角以及时空上的距离来限制对人物的道德判断之外,还通过叙事弱化人物的性格形象。小说中的人物在叙述中升华为多种理念的呈现以供选择,这未尝不可视作是王小波利用控制叙事来控制道德判断的一种创造性策略。他放任文本中的各种观点,组织观点之间的争论,但最终不给出明确的裁决。对于人物的各种行为或思想,小说中并无明确褒贬,以致小说只限于理智及概念上的争论,并不涉及道德层面的批判或褒扬。
《寻找无双》通篇涉及到事物存在与合理性的问题,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为王仙客与众老板之间的分歧对立。无双是王仙客的表妹,但由于早年失散,王仙客只好苦苦寻找。由于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无双的身份,宣阳坊里的各位老板先后把鱼玄机和彩萍当成无双来糊弄王仙客,而实际上他们是先让自己相信这两个女人就是无双,再让王仙客相信她们就是无双。
他(孙老板)有一种很生动的思想方法,虽然我不这样想问题,但是我对它很了解。……该无双(彩萍)不清不楚,把她当真的就不合理。但是她又在大院子里吃香喝辣,作威作福。你乐意看到一个假无双在吃香喝辣,还是真的在那里吃香喝辣?当然乐意她是真的——所以就让她是真的好啦。这样倒来倒去,什么不合理的事都没了。[2]616
在孙老板们的世界中,事物存在与否实际上是一种简单的合理性判断,他们自觉消除不合理的事物,同时赋予存在的事物一个自以为合理的理由。而王仙客则坚定地相信客观的存在,锲而不舍地寻找无双,最终从罗老板的口中逼问出了无双的下落。对于无双是谁以及她究竟存在与否,王仙客与众老板与其说是把持着两种观念的人物群体,倒不如说是他们已虚化成两种不同的世界观的象征物。
此外,老板们毫无理性地从现实出发随意改变观念认知的思维方式,以致于歪曲理念,枉顾真理。但作者在小说中没有在情节上对其施以惩罚,也没有通过王二之口进行道德批判,而只是将其具象化地加以解说,让读者看清其本质,进行自由选择。亦是借叙述者之口对事理进行剖析,消除文本距离引发同情,以限制道德判断。
三、叙事诉求的隐与显
任由多种论调自由争论,而不明确表明作者的好恶倾向,同时限制作者对小说中人物的道德判断,这在文本表面似乎是作者对待思想的民主态度,但小说中是否真的没有蕴含作者明确的倾向?作者又是否真的中立而不倚?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
从容掌握判断及立场选择上的“隐”与思想精神上的“显”,让读者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文本所表达的内涵及其价值,这是王小波叙事的一大意图。以低调宽松的姿态表达极具个性化的精神诉求,营构自由民主的叙事场来实现自己主观的精神意志是其小说的特色。而王小波最终的创作意图在于表达自己对现实以及某些超越现实的事物的看法,又不致成为道德说教或者单纯的判断。
在叙事方式上,王小波创造了王二的角色代替他间接叙事,实际上就把作者的发言位置后撤,叙事视角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之间自由转换,小说中的“我”并不完全代表作者,读者与作者的距离不即不离。被叙述者可以反思,叙述者可以反思被叙述者的反思,而作者可以通过对这两者的有效调动进行更深层的思考,自由地出入文本,随时选择沉默或发声,构成递进式的“看与被看”的关系。作者在创作的同时监视着自己的写作,自觉地把握着隐与显的分寸。若要沉默则全交由被叙述者推动情节或者发出声音,有时也让叙述者越位制造情节;若要发声便经由王二之口说话,第一人称的表达又容易引起话语主权的模糊,所说的话到底是出自作者还是王二难于分辨。这反映出王小波对话语权威的回避态度,也是作家对于主观表达有意规避的写作姿态,防御的却是作家内心强烈的自我意识。王小波选择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与他个人在文革中的经历,以及20世纪90年代整体的文学生态环境有莫大关联。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生态,显示出一种对于主流话语权的自觉回避,更加倾向于个人性格边缘叙事,即使是诸如陈忠实、贾平凹、苏童、余华等当代主流文学圈的作家们,也大都选择将社会宏大历史作为虚化背景,而进行个人化或者地域化的小视角边缘叙事。文学的大主题记录与干预现实的功能,相比于此前的“归来者作家群”、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时期较为减弱。主流文坛内的作家对于历史和现实叙事态度的选择,也影响到了王小波在文坛中发声的方式。王小波在小说中使用的叙事策略,表明他自居于主流文坛之外的边缘位置,来进行个人化的言说。
而市场化的写作对于忠实于写作本身的作家来说有着不容忽视的冲击。写作不再是作家全然主观的事业,而必须考虑到读者的审美需求,以及怎样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甚至不免在一定程度上迎合读者。这意味着作者很难随心所欲地说自己的话,而是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握言说的技巧,让自己说的话有人听,并且愿意听。面对市场化的写作生态,王小波的叙事策略是在小说中制造多重叙事分层、时空跳跃以及充满知性的观点穿插,散发出个人的写作魅力,赢得一大群的阅读追随者,也就争取了一定数量的话语对象,以此进行具有接受可能的发声行为,最终实现他从容地表达自我的叙事目的。
“隐”是一种叙事策略,正如李银河说王小波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天真烂漫嘴无遮拦的孩子,他解释及揭示的对象正是世故的大众习性,民族性的思维弊病。崇尚至高的理性,用理智来面对现实人生,冲破所有被社会积淀成破坏人类真诚本性的教条规则,是他锋芒所指。“隐”的目的是为了“显”,这两种叙事技巧的娴熟运用,在文本中虚拟了一个民主的叙事场域,以叙事者身份转换的方式自由表达。此外,叙事视点在虚构的历史人物与当代人物之间往复推拉,既创造了一种别样的历史书写范式,又以历史指涉当今,担当起“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的责任[6]53,在独立的精神世界中呼吁民智与理性,重建价值判断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