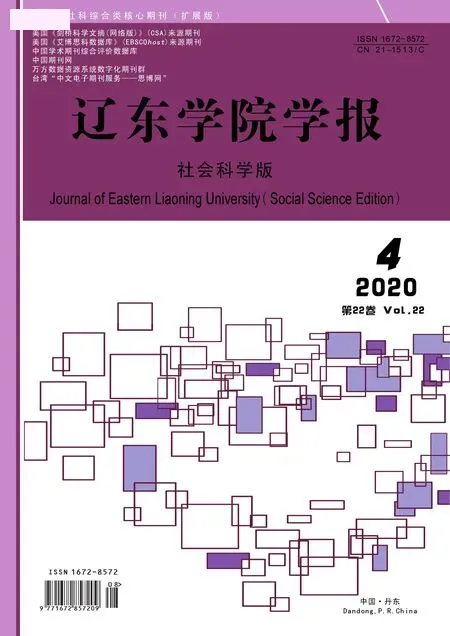苦难下的人世芳华
——加缪与迟子建对“死亡”的不同阐释
2020-03-03刘佳文
刘佳文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死亡作为一个永恒的哲学命题,它在不同的文学阶段、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国度有截然不同的表达与书写,所以它不仅仅作为哲学命题存在,在文学作品中也是永恒的母题。伴随着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人类意识的逐渐觉醒,对于个体而言,“死亡”依旧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话题。从一个更加深刻的角度思考,我们真正面对的不仅是如何直面死亡,也是在死亡面前如何生存的问题。加缪以男性的视角,细致地观察到人类生存的内在困境,灾难永不离场,它如生活般存在,而我们不间断地反抗则是生命的意义所在;迟子建则玄览众生,经历过世事沧桑,在看透了人生底色之后,以温情待之。虽然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截然不同,但其中都蕴含一种强大的韧性,对死亡的抗争和对待生命的脉脉温情。
一、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鼠疫》刻画了北非一个名叫奥兰的城市,一夜间老鼠大量死亡,人们开始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批以里厄为代表的防疫卫生队,与“死亡”进行殊死搏斗,最终看似人们战胜鼠疫,实则灾难永远没有退场。加缪表现一种存在主义的哲理,对西方天主教所表达的来世思想进行反拨,理性地回答了死亡是人生难以回避的问题,反抗是人生的常态,人类在死亡面前应该理智地做出应有的回应,而不是将此一生寄托于来世。《白雪乌鸦》则是以百年前哈尔滨的鼠疫为背景,当灾难来临时,无论行尸走肉般的王春申、尚未成年的喜岁、女流之辈翟芳桂,都表现出一种民族大义。迟子建写出小人物身上的大爱,展现了“一种独特的具有存在主义文学特质的民族忧患精神”[1],动荡中的平和之美,以死亡为依托,真正表现出人性的终极关怀。而这两种差异一方面来源于性别差异,另一方面则是生存环境。
加缪的人生充满了传奇,从一个战争孤儿到诺贝尔获奖者。他的祖上被法国政府移民到阿尔及利亚,父亲死于一战的战场,当时的加缪只有一岁,就经历生死离别。随后加缪兄弟两人跟着母亲在贫民窟里艰难度日,母亲因为父亲的去世深受刺激,几乎失聪。在求学期间,加缪患上肺结核,在叔父家疗养,当时肺结核相当于现在的癌症,难以攻克,二战期间,加缪的病情再次复发。他当时在法国南部山区进行疗养,法西斯侵略者占领了北方,正准备向南方进军,而盟军在阿尔及利亚登陆。加缪一方面忍受着与家人音信隔离的孤独;另一方面还要忍受法西斯强权的压制,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所以在开篇,加缪引用丹尼尔·笛福的话:“用另一种囚禁状况表现某种囚禁状况,犹如用某种不存在的事物表现任何真实存在的事物,都同样合情合理。”从小的这些经历,使加缪认清了生命的真实面目,现实不允许他软弱,这种环境逼迫着加缪的思考更加尖锐与深刻。所以在这部作品中,加缪不仅以鼠疫象征法西斯的暴行,更表明自己对人生、命运的思考,以及整个人类处境的认知的荒谬性。
迟子建出生于中国最北端黑龙江的漠河,元宵节出生,等于她一出生就步入寒冬,而她的命运也与寒流紧密相关,在人生最幸福的时刻,遭遇亲人的离开,这使得她早早看透生死的平等,以更温暖的心去回报东北这片黑土地。同时迟子建一直深受禅宗和佛教文化的影响,在迟子建近三十年的创作中,也曾出现瓶颈期,但我们会发现,在她的创作中那种内在的精神气息和叙述重心,宽厚、率性、素朴的情怀始终缠绕着她,她始终清楚自己的出发地和回返地在哪里。独特的地域环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迟子建的身上得到内化,从而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写作伦理。从《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到《白雪乌鸦》,我们会深切地感受到历史、现实、人性经由她的良知和情愫过滤后,虽然情感缠绵莫测、意绪起伏不定,但内在的精神气场没有任何怪啬、裂变、埋怨,更多的是敬畏和温情,是对困厄和绝望的超越。这种独特的美学追求一直潜藏在迟子建的写作深处,无形之中蕴藏在写作底色和基调之中。不同于加缪《鼠疫》的地方在于迟子建承认死亡的残酷,但她对这种残酷的人生底色已然看淡,所以选择温情、人性之美、积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残酷。《白雪乌鸦》书写一百多年前发生在哈尔滨的“鼠疫”,想通过重现记忆的方式把我们带回到过去,如果简单的“重写”与“再现”,这部作品的真正意义与价值将不复存在。而迟子建的写作诉求是将晦暗幽深的历史沉积,做出不同于史学家的“辩证”的个人性的艺术典藏,无意给历史的变异以及人事的偏颇做定论,而是看重历史情态下的世道人心,动荡下的温情。如她自己所说“四野茫茫,世界是那么寒冷,但我并不觉得孤单,因为我的心底深藏着一团由极北的雪光和月光幻化而成的亮儿,足以驱散我脚下的黑暗。”[2]263
二、对“死亡”的不同诠释
《鼠疫》表现了一种理性的思考,主人公里厄既是叙述者,又是作者思想的传达者,自始至终里厄像一个哲人一样看透生死,但依旧不忘反抗。当鼠疫结束,所有人沉浸于灾难后的狂欢时,他认为灾难像一个影子从未离开我们,人类需要做的只能是不间断的反抗,这才是生命的意义所在。《白雪乌鸦》则充满更多的感性共鸣,塑造一群带有感情的小人物,用小人物特有的情感方式对抗冰冷的“鼠疫”,透漏出迟子建行文以及人生体验中特有的温情与平和,看透生命底色后,不忘对世界与生命的热爱。
《鼠疫》与《白雪乌鸦》共同出现了一个伟大的形象,里厄和伍连德。鼠疫中的里厄在面对灾难时的态度更像是一个智者,时刻进行理性的思考,但鼠疫赋予奥兰这个城市的人们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既不冷漠,也无激情,可以用“客观”一词来形容。在鼠疫来临之前,政府迟迟不敢下定论,民众认为灾难不是真实,而是噩梦一场,总会过去的,作为一名医生的里厄勇敢地承担起救死扶伤的任务,奋不顾身的与死亡进行抗争。他深知鼠疫对他而言是无休止的失败,但面对无休止的死亡时,他不能退缩,死亡不可避免,胜利没有希望,但他仍然继续支撑着身体斗争下去。他不相信上帝,他只相信现实,做一个脚踏实地的行动者。他每天与鼠疫争分夺秒,安抚病人,顶着强大的压力与家人分离,帮助组织防疫队,同情朗贝尔的遭遇,协助卡斯特尔研究血清。他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但他从未放弃过反抗。面对人们失去理智的恐慌,他默默地担忧,但仍不停止脚步。他从未轻视鼠疫的强大,他专注于每个生命的存在,他认为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反抗的过程,结果不重要。在所有人庆祝鼠疫结束时,里厄独自思考:“痛苦的时期结束了,遗忘的时期也开始了。”[3]276人们最擅长遗忘,喜欢以惯性的方式生存,忘掉不快的一切,沉浸在自己虚构的美好之中,把幸福寄托在回忆以及未来之中。文章的结尾提道:“鼠疫杆菌不会灭绝,也永远不会消失。”[3]138格朗所记录的事件与里厄同出一人,这件事加缪本人也承认,所以在鼠疫结束时他还在怀疑:“说到底,鼠疫究竟是什么呢?鼠疫就是生活,不过如此。”[3]267而这也是加缪一直倡导的拒绝绝对的胜利,在面对不能更改的事物面前,始终保持反抗的姿态,只有反抗才能体现人的价值。在那个被死亡充斥的世界里,他们的反抗使生活和斗争有了崇高的意义,同时这一过程赋予生命特殊的意义。
如果说《鼠疫》中的里厄是一个智者的形象,那么《白雪乌鸦》中出现的伍连德,迟子建赋予他更多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医生形象。初到傅家店的他处处受阻,空有一身才华却无处施展。外国医院大门四开,医生不带口罩,无任何隔离措施,病情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步步的扩散。终于迈尼斯与纪永和的离开,使伍连德获得充分的信任,但此时的疫情已经遍布各处,死亡的数字不断上升。在这一刻,他做出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想法——焚尸,但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怎能轻而易举地被同意,人们心中依旧持传统的观念,在死时保持躯体的完整,上级的官员也不想承担此责任。他每天在焦急等待的同时,心中却已然有了决定,如果在计划时日内未得到施肇基的来信,他也准备让大火照常燃起,如若不行此法,将会有更多的人死去。在《白雪乌鸦》中,伍连德的笔墨并不多,但每一次描写都非常深刻。伍连德在接到施肇基的电报时“双手颤抖”“喜极而泣”都会给我们一种极其强烈的画面感,感受到伍连德这个人的血肉之躯。即使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人他也要面对亲人的离去,在自己梦中小儿子未出现,成为灯油,这实际上暗示他的亲生骨肉已经悄悄地离开了他。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迟子建并非讴歌什么,她只是在书写平常人的生活与感动。于驷兴说:“他没有想到,这个模样斯文的医官,骨子里是那么刚烈”[2]228。鼠疫发生之后是不选择人的,不管你是医生,当地的官员,还是走街串巷的小商贩,不管你是什么身份,谁都可能被击中。《白雪乌鸦》虽为灾难题材,但它却不是迟子建的着力之处。如她自己所言:“假如读者仅仅从小说中看到了灾难,那不是你的错,恰恰是我的失败。”[4]所以这部作品散发出一种动荡中的平和之美,通过傅家店人们在灾难面前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灾难面前所保持的美好人性,使得这种平和的气韵在这部小说中从未散去。
同时《鼠疫》中也存在对“恶”的书写,而这种观念集中体现在科塔尔的身上。他是一个行走在社会边缘的人,原本性格孤僻、沉默寡言,但这场鼠疫使得他性情大变,他走私越货,投机倒把,鼠疫所带给他的一切利益已经让他失去理智。伴随死亡数字的上升使得他的安全感随之提升,以至于当鼠疫得到控制时,他还向人群进行扫射,此时他对生命的漠视已经达到极点。表面上加缪在写鼠疫,实则控诉比鼠疫更加可怕的人类之恶。《白雪乌鸦》中也出现这样一个人——翟役生,但迟子建倡导“爱比恶更强大”。翟役生从小被送到宫中当太监,心灵变得扭曲,对自己的人生充满痛恨,对这个社会也仇视无比。他的世界观是:“想活下去,就轻贱这个世界吧”[2]232,所以他对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极度蔑视。见到死的人越多,他的心就越舒坦。金兰死后,他对世界绝望透顶,希望人类灭绝,但想起“夜空”的时候会颤抖一下,泛起暖意,流下心底的泪水,对金兰的爱与对“命根”的珍惜,说明他没忘记爱人的本能。迟子建从未放弃翟役生,正如她在作品中所传达的中心思想:唤醒人类内心深处的“善”。
三、“向死而生”的生命哲学
“鼠疫”是加缪对人生态度的一种隐喻:人类总是被命运无休止的围困。那么面对荒谬的人生,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加缪给的回答是:反抗。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明确定义“反抗”:置身于荒诞中的人对其处境有清醒的认识,孤立无援却甘愿接受这样的现实。在这部作品中加缪的思想仍处于意识层面,到《鼠疫》加缪把“反抗”提升到行动层面,还原了人们荒诞的处境。在鼠疫这个非死即生的绝境下,以里厄为代表的反抗者们,相互团结、鼓励,最终压倒人性的贪婪、自私,用实际行动获得人的尊严与人格的完整。积极与灾难斗争,争取自己的幸福与爱,获得人生存的价值和意义。《鼠疫》中强调的不是结果,而是反抗的过程,死亡并不可怕,但一定要反抗违反人的尊严和价值的生存状态。人们不可能胜利,因为灾难永远存在,并且不可控制,反抗是一个过程,不屈服,不妥协,而这恰恰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小说的结尾看似结束,实则也是一个开始,奥兰这个城市也许正在酝酿下一个灾难,谁又能把握呢?作者拒绝绝对的胜利,人的能力无法战胜死亡,但作者肯定反抗的价值。我们会发现,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似乎纵向向我们展示世界的荒诞与无理,无形之中传递一种“向死而生”的哲学观,即反抗的价值,即使到最后我们无法摆脱命运战胜苦难,但我们不屈服,这便是生命的意义。
鼠疫本是具有史诗性的“死亡”主题,但迟子建并没有把它当作“生死场”,处理为一个悲剧故事;而是通过真实存在的事实,举重若轻的承担着一次又一次死亡的重担,让人们在残酷灾难中的坚守和情感变得自然。这会让我们感觉到它并不是一部书写灾难的作品,而是在传达作者内心深处绵绵不绝的真情。迟子建似乎天然与这些灾难中的小人物存在密切的关系,不以居高临下的姿态批判什么或者怜悯什么,舍去对生死做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与追问,只是书写普通人身上的活力、温暖、爱,帮助他们剥去死亡的面罩,展露“生”的活力。对普通人生命伦理的真情书写,形成一个宏大的“生”的主题。软弱却忠厚仗义的王春申,视钱如命的纪永和,刚烈至孝的秦八碗,才德兼备的于晴秀,有情有义的翟芳桂,豪爽却落寞的傅百川,孤傲深情的陈雪卿,这些人都是鲜活的存在,无法代替,在一段共同的历史阶段演绎着各自的人生,忠于自己的内心,展现出活生生的个性和生命之光。
迟子建的叙事始终传达出一种温暖的力量。她与大自然有天然的亲近,所以她尊重一切生灵,一花一草,一石一木在她的眼里都是生命的伙伴。虽然常常看到她书写生命的脆弱,常常写死亡,但她透过死亡看到的是生命的坚守与朝气,认清生命的底色后,依然热爱。把“生”作为自己叙事的终极主题,作为一个视“文学是艺术,更是灵魂”为准则的作家,迟子建从写作伊始就坚守对生命的关照,关注自然,关注作为个体生命的普通人的认识和表现,所以迟子建笔下的小人物与现实毫无违和,似乎与生活存在天然的接近。在以《白雪乌鸦》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中,她表现出对生活的挚爱与热切的期待,以及对一切生灵的敬畏。对她的这种叙事伦理,苏童曾经评价:“它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着关注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到成为一种叙事的信仰。”[5]她用自己温暖宽柔的叙事,构建一个蕴藏着美,富有生机的精神世界。
作为一个个体,我们都难以摆脱对生命意义的考量。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依旧不乏对这类主题的探讨,余华的《活着》,富贵是“为活着而活着”,传达出一种生命的韧性;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中把“个体”置于“群体”中时,思考生命的意义所在。而迟子建则以一个女性的视角,以平和的态度思考死亡,透视“死亡”背后的“温情”,展现看透人生底色之后,依旧对生命爱的炙热。她似乎在践行福克纳式的“第三条路”,面对一切善恶的坦然和宽容,展现死亡背后“生”的力量。加缪面对死亡的方式则是“反抗”,不对未来寄予希望并不等于选择绝望、颓废的生活方式,现实虽无力改变,我们依然要保持时刻反抗的姿态。《鼠疫》和《白雪乌鸦》虽然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但它们都传达出一种普通人对待死亡的应有态度以及自身对死亡的理解,并且解释死亡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人类要认清现实之后不忘善良与美好。